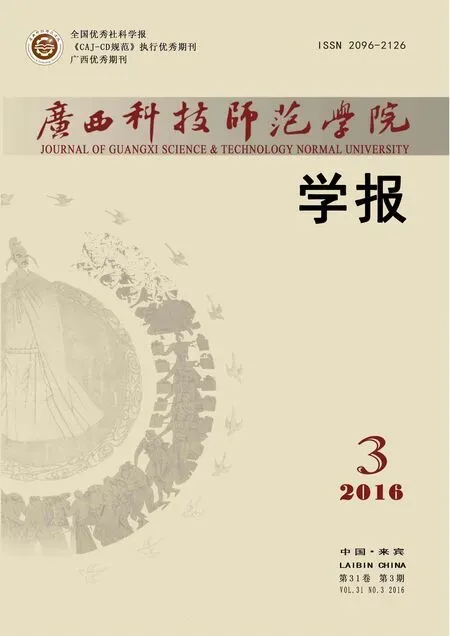论东西小说的悲剧意识
宋秀敏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1)
论东西小说的悲剧意识
宋秀敏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1)
摘要:悲剧在作家东西的小说创作中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话题,他的悲剧意识已深入骨髓,成为他创作时情感的自然流露。这种悲剧意识的由来有着深刻的根源,并在其作品中得到不断地展现,成为他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东西;悲剧;根源;表现;意义
东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到90年代中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凭借自己的智慧与才华,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名声大震,创作之路愈走愈宽。这与他的生活、求学经历及对现实的感受有很大关系。在创作中,他一贯坚持挖掘人内在的秘密,写出人心表象背后的深邃、人心的莫测与浩瀚。东西的悲剧意识像无数只手深入其作品中,故事情节与人物命运处处透露着哀伤,使读者生出一种揪心的痛,欲说不能,欲哭无泪。这种悲剧情感是东西所独有的财富,有着独特的意义。
一、悲剧意识产生的根源
东西的小说到处弥漫着悲剧的氛围,作为一个悲剧论的鼓吹者,其悲剧意识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根源,家乡贫瘠的自然环境,童年时代混乱的社会环境及特殊的家庭环境。
(一)家乡贫瘠的自然环境
东西出生在广西省天峨县谷里村,是地地道道的桂西北这方土地养育出来的儿子,这片令中外游人心驰神往的旅游胜地曾经却给东西带来很大的苦难。桂西北是广西的“西伯利亚”,因此,在地域组成上又被称为“边角废料”。在这里,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峰丛林立,石山连绵,所谓“石山王国”;耕地贫瘠稀少,干旱严重,俗称“七山一水二分田”;交通关山阻隔,极为不便,人人皆知“河池南丹(桂西北的主要城市),有钱难返”;桂西北曾有十数个国家级的贫困县,数百个国家级的特困屯,贫困人口达到80%以上[1]。
这种自然环境使东西产生一种刻骨铭心的痛,并时常出现在他的笔下。“南方于我,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那里的树木凌乱不堪,阳光里全是腐败的气息,泥巴沾满人们的双腿,有时要沾上好几天,一块一块地像鱼的鳞片。更多的时候,热浪扑人,苍蝇飞舞,水潭里的落叶正以高于北方五倍的速度腐烂。”[2]这就是南方最初给予东西的印象,是一个经常在他眼前晃来晃去、避之不及的地方,是一个他不得不接受的生存环境,他甚至为自己生存的地方被叫做南蛮之地感到羞耻,进而产生深深的自卑感。这种贫瘠感已经浸入东西的骨子里,在他的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中,读者经常可以看到他对那贫困生活的倾诉。在《篡改的命》中,东西描写了领子上的汗渍像铁锈那么黑,身上的软包打着巴掌那么大的补丁,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汪槐的形象。东西说过他曾生活的地方缺水,为了节约水,在十六岁时,他剃了个光头。由此可知,汪槐的邋遢也是有一定原因的。此外,“毒蘑菇”在《白荷》、《肚子的记忆》这两篇小说中出现也不是无缘由的,人只有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才会豁出自己的性命。他们一边享受毒蘑菇带来的短暂的快乐,一边忍受粪水带来的生不如死的折磨,这样,能死里逃生,仿佛就是生命的一次涅槃,反之,则成了临死前在阳世遭受的最后一次苦痛。这并不是东西为了创作而虚构的故事,是临死前,东西的父亲留给他的遗产,可见这种贫穷确实是一种真实,它是后人所无法想象的。
(二)混乱的社会环境
东西于1966年出生,恰巧赶上文化大革命爆发,由于母亲的前夫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事,因此他们家受到了牵连。东西说:“很小的时候,家里成份不好,母亲被人拿去批判,我站在家里的喇叭下听批判大会的现场直播,那些我平时以为善良的人,一个一个揭露我母亲的罪行。他们揭露的除了说我母亲是“四类分子”以外,其余没有一句话是真的。这给我的心灵造成了极大地震动”[3]。当时的社会环境比较混乱,一些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样做是否正确?只知道只有这样做,才能及时和“四类分子”划清界限,才能正常地生活,为了生活,他们已无暇拷问自己的良心了。
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很多人饱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有的为此失掉生命,而坚强的幸存者却永远抹不掉那段痛苦的记忆。尽管那时的东西还小,但已具备了记忆和感受现实的能力,纯洁的心灵被玷污,快乐的童年不复存在,这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小说《后悔录》将目光投向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历史,呈现了那一时期人的生存状态与情感变迁。文革时期的“禁欲”与90年代的“纵欲”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对文革形成一个绝妙的讽刺。曾广贤这个小人物的一生是灵与肉的受难史,也是一个人从“正常”到“病态”的成长史。东西的另一部小说《耳光响亮》讲述的也是与文革有关的历史,但它不是赤裸裸地批判文革,而是重点展示文革给人们留下的后遗症。文革结束了,平反昭雪、拨乱反正……这些随之而来,然而人们却不知所措,小说讲述了牛家人的荒诞生活,呈现了他们的堕落与迷惘。
(三)家庭影响下的性格弱点
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方向。虽然东西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不利于他的成长,但这些只是外在因素,相对来说,对于他性格的最终形成,其家庭却有着很大责任。东西是他的母亲在46岁生下的满仔,老来得子,父母亲戚更是对他疼爱有加。东西写道:“我是她最后的念想,是她强加给未来生活的全部意义,所以,不管是上山砍柴或是下田插秧,甚至于大雪茫茫的水利工地,她的身上总是有我。挖沟的时候我在她的背上,背石头的时候我在她的胸口。直到6岁时上小学,她才让我离开她的视线。”[4]79东西在11岁之前距离谷里村的半径不会超过2公里,他被母亲保护得太好,以致于当他独自走向社会的时候,常常充满了恐惧。
东西是一个乐于接受命运的人,不喜欢惹是生非,若石头砸到了他的脚,他从来不会想这石头来自何方,而是把一句责备的话赏给自己:“我的脚为什么碰到了别人的石头?”他又是一个胆怯的人,战战兢兢地长大,一直把自己当做是一个异类,所以,当他看到卡夫卡的《地洞》时,他找到了真正的知己。
二、悲剧意识在作品中的表现
创作是作家内心的一面镜子,是作家思想意识的反应,通过作家的作品,读者能对作家有一定的了解。东西的悲剧意识毫无掩饰地呈现在作品中,荒诞且无奈的悲剧人物形象、倾心于描写苦难的悲剧精神、象征与寓言的悲剧叙事等都是东西悲剧意识的反映。
(一)荒诞且无奈的悲剧人物形象
东西在《寻找小说的兴奋点》中提到了写人物的重要性。他认为:“好作家的背后总是站着一排人物,比如鲁迅就有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4]74东西的作品给读者留下的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对悲剧人物的书写。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可怜人,他们本该得到同情、关怀,然而命运却是悲惨的。《没有语言的生活》中聋、哑、瞎的集体亮相,王胜利的三者之集合展示的更是希望的破灭;《后悔录》中曾广贤在文革中死里逃生,却变成了一个性无能者;《耳光响亮》中牛翠柏由一个善良的孩童变成了出卖姐姐幸福的叛徒;《白荷》中白荷先是被父亲抛弃,继而为了粮食卖身,而后难产死掉;《篡改的命》中汪槐父子的命运被别人掌握着,同时,汪长尺以牺牲换来的汪大志的命运也是不幸的,等等。东西塑造了一系列悲剧人物形象。
东西常常写悲剧,悲剧意识已深入其骨髓。在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中,他既描写人物身上的质朴、醇厚的美好,同时也批判他们身上的劣根性。《篡改的命》赞美了汪槐夫妇为人父母的无私奉献精神,但也揭露了他们的狭隘思想;《目光愈拉愈长》写出了刘井对儿子倾尽全力的爱,批判了马男方的好吃懒做;《原始坑洞》写出了秦娥对谋子的舐犊之情。在以城市为题材的小说中,东西以敏锐的观察力,透过现象看本质,把现代化下的精神困境曝露在阳光下。《美丽金边的衣裳》写了丁松、希光兰等人用金钱相互捆绑的孤独与游戏化的状态;《猜到尽头》写了夫妻间的信任危机;《不要问我》写了自我迷失与认同的危机;《把嘴角挂在耳边》写了一群人为寻找“笑”而进行滑稽表演。当然,东西也表达了对处在城市边缘的小人物的同情与悲悯。《篡改的命》中汪长尺为了下一代能成为城市人,拼命地跻身于城市的一个角落,为了生存他可以帮黄葵砍手指,当着黄葵的面脱裤子,替林家柏坐牢。小文为了孩子能有好的未来去卖身挣钱。汪槐夫妇为了孙子能在城市出生,不惜欠债、沿街乞讨,等等,这部小说既是小人物的奋斗史,同时又是苦难史、悲剧史。
(二)倾心于描写苦难历程
东西的作品处处流露出对于苦难的倾心讲述,这与他幼年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很多作家把童年经验当作上天对自己的一种馈赠,童年经验是他们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源泉。曾经一位青年作家问海明威:“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海明威回道:“不愉快的童年。”可见,童年经验对作家创作的深远影响,尤其是童年的“缺失性经验”。所谓缺失性经验,即他的童年生活很不幸,或是物质匮乏,或是精神遭受摧残、压抑,生活极端抑郁、沉重[5]。东西的童年是不幸的,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对他的身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在他的作品中都有体现,《站在谷里想师专》几乎就是作者的自传。《耳光响亮》、《后悔录》、《反义词大楼》、《没有语言的生活》等都打上作者童年的印记。
东西是一个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作家,他喜欢并善于从精神和生活两个层次描写人的苦难。“在人的全部苦难中,生活苦难是一种最基本、最具有包容性和最直观的一种苦难形式,没有什么苦难能够不通过人的生活得以独立地表现,也没有什么苦难比人的生活苦难更具有个人体验的基础和可证实的真实性。”[6]东西的很多作品写到了人的生存困境问题,以农村题材的居多。《祖先》中竹芝用冬草的身体去换水田,《原始坑洞》中秦娥一家生活的拮据,《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王家人的生存困境,《篡改的命》中受伤的汪槐因没钱交住院费而被抛弃在走廊上,等等。这些苦难深入到作者身心的每一处,它不是刻意编造,而是真情实感地自然流露。与此同时,东西以城市为素材的小说中同样涉及到苦难的描写,只不过是更深层地表达。《后悔录》中曾广贤在那个年纪本该享受父母的疼惜,社会的关爱,但是文革赐给他别样的人生。他从一个性健康的青少年,经历过无辜的牢狱之灾后,成了一个性无能的中年人,他渴望性,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文革的清规戒律给他造成了终生的心理障碍,他有苦无处诉说,最终可怜到花钱请按摩小姐倾听。这部以“性”为主线的作品使读者感受到的不止是曾广贤性的困苦,还是一个正常人的受难史。另外,《篡改的命》、《耳光响亮》、《抒情时代》、《不要问我》等作品对城市人的精神苦难也给予了深刻的解剖。
(三)悲剧叙事运用象征与寓言
东西的创作是一个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集合体,他用夸张、荒诞的手法讲述最本真的故事,揭示最深刻的道理,从而使其作品具有一定的哲理性。他的小说常常会给读者一种恍惚的感觉,像做梦一样,但又那么真实。在读者认为最朴实、平淡的小说中,却依然能够得到意味深长的感受,仿佛那些事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有一种历久弥新的回响。意象不仅仅在诗歌中经常出现,在小说中同样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通过意象的运用传达某些情绪和言外之意,表达对生活的认识,营造一种诗意,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体现出他小说的诗性美学特征”[7]58。
意象在东西的小说中是多种多样的,如《草绳皮带的倒影》中象征人物命运的草绳、皮带和倒影,《原始坑洞》中象征母亲子宫的坑洞,《幻想村庄》中酒被看作生命与爱的支撑,《一个不劳动的下午》中象征苦难和毁灭的青草和大火,《迈出时间的门槛》中象征权利的枪等,这些意象都承载着不同的意蕴。在《一个不劳动的下午》中,荒草是小说描写的重要对象,队长陈裕德带领全体社员锄地,为了占冬妹的便宜,他就想做点让大家都感兴趣的事,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于是,他提出了放火烧山的想法,出乎意料的是火在风的推波助澜下,愈燃愈烈,势不可挡地扑向了村庄,为了救火,陈裕德和冬妹葬身火海。第二年春天,新任队长带着全体社员在冬天翻挖过的土地上播种,凡是去年烧过的地方现在全部芳草萋萋,生产队肥壮的牛群甩着悠闲的尾巴,在草地上吃草。看着满山遍野的青草,社员们都说那个下午好玩。东西说:“青草是我比较爱用的一个意象,它覆盖一切,包括死亡、爱情;它是遗忘的代名词。我们在忘记教训的同时,也忘记悲伤。”[8]东西用青草这个意象来表现人们的痛苦心态,而结尾的芳草萋萋是希望的象征,这给读者以轻松的感觉。“大火”也是东西常用的一个意象,大火吞没了村庄,烧毁了丑婆的家,葬送了粮所所长范建国的前程,是一种毁灭的象征。如此等等,意象在东西的小说中可谓一大特色,别有一番深意。
三、东西小说悲剧叙事的意义
悲剧在东西的创作中一再被书写,它已经成为东西小说的一大特色,它作为东西观照世界、表达自己对世界认识的一种方式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一)悲剧的美学意义
东西的小说具有神秘主义的特征,他把神秘文化作为一种观照世界和人生的文化哲学,表达对于外在世界和生命现象的情感体悟与哲理运思。意象和寓言的运用使他的小说具有神秘主义的美感,增强了作品的审美表现力和穿透力,拓展了文学的审美领域,同时也为文学作品建构起一种诗性力量。
尼采强调世界意志的“永恒生命”的性质,他的悲剧世界观具有一种审美的、积极的意义。悲剧就是把个体的痛苦和毁灭演给人看,然而,通过个体的毁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产生快感。每部真正的悲剧都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悲剧以其形而上的安慰在现象的不断毁灭中指出那生存核心的永生[9]。东西的小说有一种对死亡的喜爱,《篡改的命》中汪长尺为了儿子的未来投河自尽,《把我送到仇人身边》中赵构被同学张洪为了金钱杀害,《一个不劳动的下午》中陈裕德和冬妹被大火吞噬,《溺》中关连被水淹死,《白荷》中人的纷纷死去等,死亡在东西的笔下变成了一种习惯。在《祖先》中福嫂看着自家三十亩水田被福八一点点地送给竹芝,她心痛,她也抗争过,但迎来的却是福八的暴力,她所做的努力无济于事,最后,连自己的命也被竹芝夺去。竹芝的儿子见远无法忍受母亲的行为,他选择嫖的方式回应竹芝,直到把竹芝得来的水田嫖光,倾家荡产,最后落了个无法忍受毒魔芋带来的痛苦而投河自尽的下场。在这里,福嫂和见远的死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种解脱,他们在死亡中获得一种精神存在的永恒。冬草看见见远投河,却无动于衷,而是慢慢地欣赏这一瞬间,也许冬草更能理解死亡对于他们的意义。
(二)对自身悲剧表现领域的开拓
东西的小说创作不是一成不变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尝试创作到现在的创作风格的形成,这是一个创作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开拓与进步的过程。
从悲剧的取材上看,其取材范围由农村生活扩宽到农村和城市两个“部落”,取材区域由桂西北扩大到更广的范围;取材的年代由远及近,即由“过去时态”到“现在时态”;东西小说的创作取材由“区域勘察”到“重点开采”[7]11。这体现了作家与时俱进的精神。东西说自己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逃跑的过程,从农村到县里,从县里到地区,从地区到南宁,身处位置地不断变化拓宽了东西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资源。起初,东西小说的创作题材大多是关于农村的,像《祖先》、《原始坑洞》、《没有语言的生活》、《相貌》、《迈出时间的门槛》等都是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他在展示农村封闭、落后现实的同时,也揭露村民身上的愚昧、麻木、自私的劣根性。之后,东西进入城市,其小说取材的领域也扩大到城市,面对城市里的浮嚣与喧哗,他以一个冷静者的姿态洞察城市里的众生相,透过浮华的表象,抓住了他们生存的精神内核。《美丽金边的衣裳》、《我为什么没有小蜜》、《双份老赵》、《猜到尽头》、《我们的感情》、《戏看》、《我和我的机器》、《不要问我》、《救命》等,这些都深刻揭示了都市人生存的精神困境,猜疑、游戏、承诺、金钱、不安全感时刻缠绕着他们,吞噬着他们的灵魂。
从悲剧的形式上看,东西的小说既涉及到生存悲剧又涉及到精神悲剧。《肚子的记忆》采用由近及远的手法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王小肯因“嗜食症”而住院,假公济私的姚三才对其病因进行调查,随着调查不断深入,情节却把读者引向于发生在几十年前的悲剧故事。杨金萍由于饥饿难耐,便禁不住地吞食毒蘑菇,但又不想死,于是猪圈里的粪水便成了最好的解药,她在吞吐间种下了王小肯现在的疾病。故事由死了41年的杨金萍亲自讲述,增强了故事的可信度,使读者更深刻地感受到当时人们生存的苦难。在《白荷》中,同样再现了这一悲剧。《不要问我》讲述了自我迷失的故事,处在性欲膨胀期的大学副教授卫国酒后失态抱了一下自己的学生冯尘,事后因无地自容,逃到了另一个城市,不料皮箱在火车上被偷,从此他便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成了一个被世界抛弃的人。他得不到爱情、工作,无论他怎么解释,别人都不会相信他,最后为了还一个三陪小姐刘秧的债,参加无须身份证明的喝酒比赛,自此也结束了生命。小说深刻揭露了一个只认证不认能力的病态时代的诸多弊端。
[参考文献]
[1]陆卓宁.“桂西北作家群”的文化思索[J].理论与创作,2001(3):28-32.
[2]东西.时代的孤儿[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31.
[3]东西,张燕玲.小说还能做些什么[J].山花,2001(2):25-27.
[4]东西.谁看透了我们[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5]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4):54-64.
[6]周保欣.沉默的风景:后当代中国小说的苦难叙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44.
[7]温存超.秘密地带的解读:东西小说论[M].北京:台海出版社,2006.
[8]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97.
[9](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周国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4.
(责任编辑:雷文彪)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126(2016)03-0013-04
[收稿日期]2016-04-15
[作者简介]宋秀敏(1989—),女,河南鹿邑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On the Tragic Consciousness of Dongxi’s Novels
SONG Xiumin
(College of Literature,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Nanning,Guangxi,530000 China)
Abstract:Dongxi who always adheres to do something unconventional or unorthodox and excavates people’s inner secret things is a writer with unique writing style.His novels involve many aspects,tragedy in his novels is a commonplace topic.His tragic consciousness has become well ingrained showing feelings of his creation,emerged in his works constantly,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is creation,it has the unique significance.
Key words:Dongxi;tragedy;origin;performance;mea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