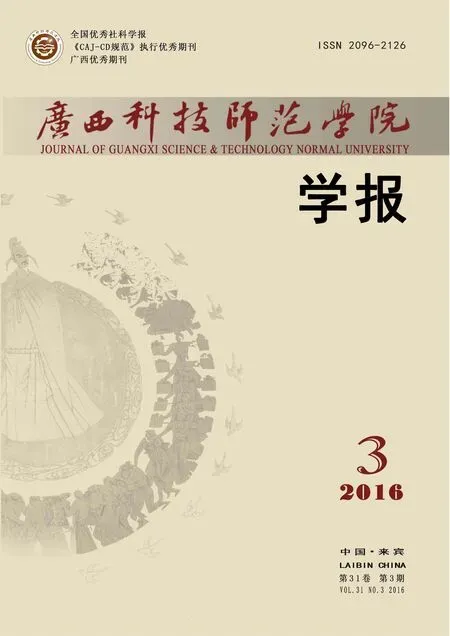论路遥的生命悲剧意识与积极抗争的人生态度
——以《平凡的世界》为例
刘朝霞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广西来宾 546199)
论路遥的生命悲剧意识与积极抗争的人生态度
——以《平凡的世界》为例
刘朝霞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广西来宾546199)
摘要:《平凡的世界》集中体现了路遥超越了个体与时代局限的生命悲剧意识及其积极抗争的人生态度。作家以平民青年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为代表的“凡人”奋斗之路与艰辛历程,揭示了幸福是相对的,痛苦才是人生的人类生存真相;并用海明威式的硬汉精神激励人们,人生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能被打败。
关键词:路遥;《平凡的世界》;悲剧意识;人生态度
对于悲剧范畴,路遥并无“一家之言”,然而作家短暂却苦难的人生经历和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赋予了他洞察生活、世事与人生的超强感知力,投射在他的创作实践上表现为鲜明而深刻的生命悲剧意识。此前,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学界多侧重于从作品人物命运的角度出发,将其单纯地理解为一种西方式的悲剧审美。笔者认为,将路遥的厚重的悲剧意识简单地界定为性格悲剧抑或社会悲剧,其实是低估了这位哲思文人对于人生本质与价值的终极探索。一个文人一生的抗争,就在于将他身受的个人凄苦转换成丰富和奇特的,属于全人类的,而非个人的文字作品。越过喧嚣与纷繁的时日,路遥的作品之所以具备相对持久的恒定价值与可读性,正是因为他像屈原一样,用生命在高歌,在书写,他关于人生悲观而本真的认识超越了个体与时代的局限,揭示了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真相——人生无所谓真正的胜利,挺住意味着一切,幸福是相对的,痛苦才是人生的正常状态,并用海明威式的硬汉精神激励我们——人生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我们可以被消灭,但是不能被打败,苦难让人成长强大,既然活着,就要认真地活着。
一、生存悲剧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凡人的奋斗史更是一部生活的苦难史。路遥带着强烈的宿命论用那只叫做命运的大手任性地将在苦海中挣扎的人们暂时拖上诺亚方舟,而正当他们感激涕零并重新燃起生之希望时,又冷不丁将他们狠狠地甩进了一个更大的漩涡。书中之人,无论贫穷、富贵,官僚、百姓,皆无一幸免。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虽无考据明确证明路遥是否受过叔本华的影响,但路遥对人生苦难的强烈感知无疑是生命痛苦本质说的潜在认同,或者说是一种中国式诠释,这种潜在认同最直观地表现为他作品当中大量的悲剧元素。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路遥的小说世界是各种悲剧的排列组合,尤以《平凡的世界》为显著代表。“平凡的世界”实际上也是一个“苦难的世界”,在这里,饥饿、病痛、天灾、人祸等触目惊心的生存悲剧无处不在。黄土高原贫瘠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特殊时期严重脱离生产力实际的错误政治导向,给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刻骨铭心的贫穷,以及由贫穷衍生出来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与摧残。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的各种需求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生理需求(呼吸、水、食物、睡眠、生理平衡、分泌、性)、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尊重、信心、成就、对他人尊重、被他人尊重等)和自我实现需求5大类。心理需要尤其是水、食物和空气,都是最基本的,维持机体所必须具备的生存资料。贫穷就意味着食物紧缺,维持生存的基本欲望受挫是可怕的,对于能量消耗高峰期的青壮年来说,尤其是一场噩梦。像孙少平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是他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馍——在旧社会,地主喂牲口都嫌没营养的粮食。可就是这样的高粱面也并不充足,因为他一顿至少可以啃掉5个这样的黑家伙,而每天高强度的劳动却是雷打不动的,所以“每当他从校门外的坡底下挑一担垃圾土,往学校后面山地里送的时候,只感到两眼冒花,天旋地转,思维完全不存在了,只是吃力而机械地蠕动着两条打颤的腿一步步在山路上爬蜒”[1]7。肉体上的折磨虽然苦得真切,但尚不足以将人打垮,精神上的摧残却是致命的。饥饿不是最可怕的,深入骨髓的自卑才是贫穷带来的最残酷的折磨。饥饿对于孙少平来说,咬紧牙关仍然可以忍受,让他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他已经十七岁了,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敏感而羞怯的心。他渴望穿着一身体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学的面前;他愿自己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也能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并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面或者黄馍。这不仅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获得尊严”[1]8。在自我认同感逐渐形成的青少年时代,物质匮乏而引发自尊受挫造成的心灵创伤是巨大的,也是无法愈合的。在一个本该意气风华、玉树临风的年纪,却只能常年穿着自家剪裁的肮脏老粗布衣服,一双缀着补丁且没了鞋带的旧黄胶鞋是多么残忍的熬煎,这直接导致了孙少平深入骨髓的自卑、敏感,而又近乎自负的要强。
二、欲望的功成与毁灭
如果说贫穷只是特殊时期和底层民众的悲剧,不具普遍性,那恰是因为他没有看清人生的本质。贫穷只是众多生存悲剧中的冰山一角,即便侥幸逃脱贫穷的一类人,他们也并不能高枕无忧,“命运或许已为我们准备了疾病、残废、视力或理性的丧失”[2]416。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生活中,诸如孙老奶奶瘫痪,金俊斌盛年溺亡,李向前车祸致残,秀莲因过度劳累罹患肺癌,“半脑壳”田二的先天性神经失常且最终死于非命的悲剧每天都在惊人地重复上演。鲁迅曾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平凡的世界》之所以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是因为路遥在触目惊心却也司空见惯的生存悲剧之外,揭示了更高层次的人生悲剧,譬如“历史造成的英雄悲剧、个人奋斗悲剧以及年轻人的爱情悲剧”[3]1。其中,尤以孙少安、孙少平一类青年的奋斗悲剧撼人心魄。孙少安的人生一开始就是一个被命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降者之路,尽管在他褴褛的衣衫下也曾经涌动过年年力争全班第一的傲骄和隐约想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念想,父亲也在全家近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艰难境地下咬紧牙供他上学,然而忠孝仁义而又早熟的特性注定他将痛苦而又自觉地接受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宿命。比起让贫穷的家和苦命的父母不堪重负,断送前程无疑会是他的坚定抉择,“他要帮助父亲养活一家人,而且要对少平和兰香的前途负起责任来”[4]145。于是当他上完两年高小后,他主动对父亲提出退学,并决心在双水村做一个出众的庄稼人。然而对命运的服从并不意味着可以善终,从此,孙少安又在命运指定的轨道上磕磕碰碰、受尽磨难:作为生产队队长,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想通过目测划分猪饲料地的保守做法来给社员创造尽可能多的一份口粮,却因此被田福堂之流的“农村政治家”举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公社大会上接受荒诞而又屈辱的批斗;他凭借自己精明的强悍和可怕的吃苦精神办起了烧砖窑,用血汗修改了家族祖祖辈辈“向人借钱”的历史,然而就在他信心满满地扩大生产规模,期待为贫困的父老乡亲们增加收入的档口,生活再次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烧砖师傅是个冒牌货,砖厂倒闭!当他一次又一次地顽强爬起,眼看就要过上梦寐以求的农民式的幸福生活之时,与他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的妻子却永远地倒下了……对于生活的苦难,路遥的关注是敏锐而深刻的,少年时代的他就开始流落四方、历经沧桑,体验深度人生。小说中孙少安的苦难史,实质上是作家个人关于人生本质的一种投射,“他那心酸的生活史使他时刻保持着对普通人痛苦的敏感而入微的体会”[5]41,并多次借这一角色畅快淋漓地宣泄了自己对于苦难的沉重体验,“痛苦,烦恼,迷茫在他的内心像洪水一样泛滥着,一切都太苦了,太沉重了,他简直不能再承受生活如此的重压。他从孩子的时候就成为了大人。他今年才二十三岁,但他感觉到他已经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没吃过几顿好饭,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没度过一天快活的日子……一种委屈的情绪使他忍不住泪水盈眶。他把烫热的脸颊贴在冰凉的树干上,两只粗糙的手抚摸着光滑的杨树皮”[1]167-168孙少平的人生悲剧与哥哥孙少安截然相反,作为觉醒的一代平民知识青年的典型代表,孙少平全部的生命活动都在于为改变自己的农民宿命而战,他割舍下对土地与亲人深沉的爱,毅然决然去过比在农村还艰难的生活。他咬紧牙关,像自己崇拜的小说主人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中的保尔柯察金一样,坚毅刚强而又希望不灭地去接受生活的一切苦难。苦重的小工活三天下来就把他秀气的学生脊背压烂了,“他无法目睹自己脊背上的惨状,只感到像带刺的葛针条刷过一般。两只手随即也肿胀起来,肉皮像被石头磨得像一层透明的纸,连毛细血管都能看见。这样的手放在新石碴儿上,就像放在刀刃上!”[4]107和哥哥孙少安一样可怕的吃苦精神再加上知识青年仁义礼智信等特有的人格品质,命运似乎对这个执着的年轻人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雇主曹书记有意招少平为上门女婿,这意味着他将在黄原城边落户,实现自己进城的这一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然而事实是“他在那里仅仅落下个空头户口而已。视土如金的阳沟不会给他土地,他实际上仍然是一颗无根草”[4]163在泪水和碱水里泡上一次又一次后,孙少平命运再次出现了一丝转机,铜城矿务局要在黄原市招收二十来名农村户口的煤矿工人,老雇主曹书记念及旧情帮他要到了这份虽然姓“公”,但城边上的农民几乎无人问津的苦工作。无论如何,按照孙少平自己的话来说——他终于有了正式的工作!也就在此前不久,他与黄原地委书记田福军的千金田晓霞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周围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一个煤黑子,女朋友却是省报的记者!有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总觉得这是一个梦幻”[5]52-53。田晓霞是在孙少平成长和奋斗的旅途中,集人生导师与灵魂伴侣于一身的一个关键人物。她在众多农村学生中一眼发现了气质非凡的孙少平,从此不断启发他、鼓舞他、开导他,给他以精神指引。她寄给少平各种各样的励志书籍,竭力提示他不要丧失远大理想,不要被环境所征服,决不能让自己的精神境界被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所淹没。在孙少平陷入人生低谷的日子,她的善解人意、温柔美丽更成为了他沉重的痛楚中最温暖的慰藉,他们志同道合、心意相通、郎才女貌,他们之间爱情的美好中带着几分神圣。然而现实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凭借着青春的激情,恋爱,通信,说些罗曼蒂克和富有诗意的话,这也许还可以。但未来真正要结婚,要建家,要生孩子,那也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5]53抛开悬殊的出身不论,一个煤矿工人和省报女记者之间的爱情注定要以悲剧的形式结束,只是我们尚不得知捉摸不透的命运具体将采取何种形式来宣判它的终结。“悲剧,其开头往往是喜剧。这喜剧在发展,剧中人喜形于色,沉湎于绚丽的梦幻中。可是突然……”[5]53正当孙少平在危险和劳累的井下作业中一边吃钢咬铁,苦中作乐,一边无比激动,甚至近乎迷狂地等待与爱人的古塔山之约时,亲爱的晓霞却再也回不到他的身边了。倘若路遥是在用孙少安的人生悲剧告诫我们,对命运俯首称臣并不能让我们免受既定的痛苦与灾难,那么孙少平的奋斗悲剧则是在诚实而又悲壮地暗示我们——你反抗或者不反抗,痛苦都在那里,公平地对每一个生命不离不弃。就这一点而论,孙少平的苦难奋斗史简直是对叔本华建立在唯意志论基础上的生命痛苦本质说的精准诠释。生存意志和欲望是人类存在的真正内在本质,人生的本质就是一团欲望,它注定了我们终其一生都将在层出不穷的矛盾和新的痛苦中度过。纵观孙少平的奋斗史,想要走出农村,改变被土地栓牢至死的强烈欲望支配着他背井离乡,受尽磨难,最终换来的却只是奋斗与爱情的双重悲剧,实际上孙少平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实现自己脱离农村的奋斗目标,他与命运的斗争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从表面上看,他是胜利的,因为他终于取得了城市户籍,但是他在精神上并没有超越农村范畴。他刚到达铜城,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因为他虽然叫做城市,实际上却更像乡村”[3]11——他在这里找到了土地般熟悉的安全感。一个久经沙场的命运的斗士,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又心甘情愿、心平气和地绕到了宿命的圆点,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在造成孙少安与孙少平两兄弟人生悲剧的一切因素中,低下的出身与社会地位似乎“功不可没”,假设他们不是农民孙少安和孙少平,他们不必为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所困扰,他们是否就可以摆脱一切痛苦,获得我们称之为“幸福”的东西?答案是否定的。“不论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不论他拥有什么,那构成生命本质的痛苦都是无法除去的,不断的努力除去痛苦,除了使痛苦改变表现的方式以外,别无其他。”[2]272看清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明白为什么一事百顺、近乎完美的田晓霞会突然殒命;衣食无忧、生活清闲的徐国强活得压抑无比;一心为民、实权在握的田福军中年丧女……“一切幸福都是虚妄不实的,唯有痛苦才是真实的。因此,到了晚年,我们,或者,至少我们中的精明世故者更情愿消除生活中的痛苦并使自己的地位安全可靠而不是去追寻绝对的幸福。”[2]206对于从天而降的喜事这类偶然发生的事件,老年人与其说感到快乐还不如说感到怀疑、忧虑甚至是沮丧。孙玉厚之所以在儿子出资重建的双水村小学“落成典礼”上表现反常,正是因为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潜意识里隐约看清了人生的本质。在孙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荣时刻,当所有亲朋好友沉浸在无限的欢乐中时,这位本该最激动的人脸上倒看不出什么特别的激动和愉快,他低倾着头,说不定在哭。红脸蛋的孙子虎娃则举着一束红艳艳的鲜花,在笑。“哭,笑,都是因为欢乐。哭的人知道而笑的人并不知道,这欢乐是多少痛苦换来的。”[5]413
三、生命不止、抗争不息
渗透于路遥笔尖的生命悲剧意识使他的作品难免带有悲观和忧郁的色彩,但他绝非消极厌世主义的代言人,而恰是以深刻的真理、壮丽的诗情和英雄的格调给我们以无尽的激励。对于生存意志即生命痛苦本质的认同,路遥与叔本华的殊途同归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二者对待生存意志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或者说是二者超越人生痛苦与欲望,以获得人世所谓“幸福”的拯救途径却不尽相同。叔本华认为,既然意欲和奋力是生命的全部,无意识自然的内在生命是一种没有终结没有休止的不断奋力,一切意欲的基础都是“需要”、缺乏,即痛苦,要摆脱它,作为意志表象的我们除了终其一生与生存意志之间进行力的紧张的不间断拉扯之外,其它别无选择:要么对生存意志采取无关心的态度,比如说转向艺术(建筑、绘画或雕刻、诗歌、悲剧、音乐;要么否定意志,但不自杀,而是转变观点,默认并接受痛苦。正如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所说,“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的人生都让人潸然泪下!”要想获得人世所谓的“幸福”(实际上只是一种无痛苦状态),就不能要求过多,幸福的构建遵循一条规则,那就是把我们的种种要求降至最低可能的限度,直到我们最后达到一种不曾满足也无法放弃的愿望为止,这将是避免极大不幸最确实可靠的方法,因为我们虽然和自己期望的命运相左,然而却使自己的生存感到满足,而且将不用在历尽磨难之后无比沉痛地获悉痛苦是生存本身中的必然现象。与出身优越、生活富足的叔本华相反,路遥从少年时代起就流落四方,受尽苦难,泪水和碱水的长期浸泡与巍峨壮阔的黄土高原,锻造了作家吃钢咬铁般的硬汉性格。因此,与叔本华冷静理性地克制生存意志不同,路遥选择的是与生存意志高度统一,肯定意志、解放欲望,并一生为其倾力而战的英雄途径。《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不同形式的奋斗虽然都以悲剧收尾,但是他们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压倒一切。尽管生活的重磨一次次压得孙少安喘不过气,有生以来遭受的各种打击却无法让这位硬铮铮的铁汉对苦难俯首称臣。无论是失学,失恋,还是创业失败,他总能在滂沱泪水的洗礼之后奋力爬起,“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生活的马车,坐在驾辕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1]168。与哥哥孙少安相比,孙少平的强大更多地存在于他广阔深邃的精神世界,具体表现为他对生活所采取的积极态度和他在极端艰难条件下的人生奋斗,这也正是田晓霞深爱着这位平民青年的深层原因。“他不伪装自己,并不因生活的窘迫就感到自己活得没有意义,甚至对苦难有一种骄傲感——只有更深邃地了解了生活的人才会在精神上如此强大。”[4]302知识与经验,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指引,让在人生路上坚强求索的孙少平“对世界了解得更广大,对人生看得更深刻,也因此对自己所处的艰难和困苦有更高意义的理解,甚至也会心平气静地对待欢乐和幸福”[4]147他甚至有点“热爱”自己的苦难,并坚信,只有血火般的洗礼才足以见证一个人活的价值,而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我们终有一天会酿造出生活之蜜。因此,在遭受挚爱离去和毁容的致命打击后,孙少平依然在噙满泪水的眼睛中看到了蓝天上“太阳永恒的微笑”——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永不言败的生命斗士。
在与苦难的抗争上,路遥向我们彰显了一种近似海明威式的硬汉精神——人可以被毁灭,但绝不能被打败!作家用自己全部的经验与热情告诫我们,不要畏惧苦难,它是人走向成熟的最好课程。苦难使人成长、强大、崇高。幸福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勇敢地去战胜困难。“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2]317
[参考文献]
[1]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2]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杨丽华.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蕴[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8:1.
[4]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5]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6]叔本华.叔本华人生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272.
(责任编辑:刘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126(2016)03-0041-04
[收稿日期]2016-05-02
[作者简介]刘朝霞(1988—),女,湖南邵阳人,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世界文学、比较文学。
On Lu Yao′s Life Tragedy Consciousness and Active Struggle: Taking Ordinary World as an Example
LIU Zhaoxia
(Guangxi Science&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Laibin,Guangxi,546199 China)
Abstract:Ordinary World epitomizes that Lu Yao goes beyond the individual and limitations of life tragedy consciousness and their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life to struggle.The writer represents two brothers“mortal”road of the struggle and difficult course civilian youths Sun Shaoan,Sun Shaoping,which reveals that the happiness is relative,the pain is the truth of human existence of life,using the spirit of Hemingway′s tough guy to motivate people,life is an endless war and people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Key words:Lu Yao;Ordinary World;tragedy consciousness;life attit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