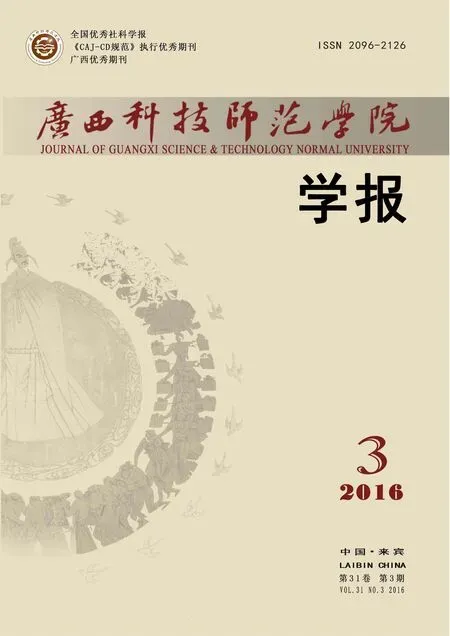《诗经》中的“弃妇诗”及其主题嬗变
阳淑华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06)
《诗经》中的“弃妇诗”及其主题嬗变
阳淑华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06)
摘要:“弃妇诗”是《诗经》中的一类重要题材,它着重反映了当时妇女在感情上所受的压迫和苦难。可以说,《诗经》中的“弃妇诗”是后代此类作品的滥觞。文章从《诗经》中的弃妇诗出发,着重探讨此类诗歌叙事主题模式的形成、弃妇形象的发展演变以及性别角色的转换,试图对弃妇诗的嬗变历程作简要论述。
关键词:《诗经》;“弃妇诗”;发展演变
妇女的命运问题,历来受到人们关注,这也是诗歌领域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诗经》三百零五篇,写女性或涉及女性问题的作品俯拾皆是,但最为令人动容的莫过于“弃妇诗”一类。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弃妇”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群体,一个遭受肉体与精神双重压迫的群体。而《诗经》以及后世中的这些篇章正是为这些生命谱写的一曲曲悲歌。
一、《诗经》中“弃妇诗”的内涵
婚姻与爱情自古以来都是文学作品中的永恒主题,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自然存在大量婚恋题材的诗歌,这些或写男女恋情,或述离后相思,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之间的感情状态。在这类主题中数量最多的是表现男女之间相恋相思的作品,表现女性爱情婚姻悲剧的“弃妇诗”数量不多,但却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为后世此类作品之滥觞。
“弃妇诗”属婚恋题材中的一类,但学者们对于《诗经》中“弃妇诗”的判定历来意见不一,综合历代治诗者的意见,涉及弃妇题材的诗篇大约有11篇,分别是《召南·江有汜》《邶风·柏舟》《邶风·日月》《邶风·终风》《邶风·谷风》《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郑风·遵大路》《小雅·我行其野》《小雅·谷风》《小雅·白华》。尚永亮先生选取了古今具有代表性的十二家观点,认为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可以确定的弃妇之作5篇:《卫风》之《氓》、《邶风》之《谷风》、《王风》之《中谷有蓷》、《小雅》之《白华》以及《召南》之《江有汜》;二是不宜列入弃妇诗之作的5篇:《邶风·日月》、《邶风·终风》、《郑风·遵大路》、《小雅·我行其野》以及《小雅·谷风》;三是“是非得失未易决”的多疑之作1篇:《邶风·柏舟》[1]。尚永亮先生在其文中材料翔实,考辨细致,结论具有说服力,笔者亦认同此观点。
《诗经》中的五首弃妇诗从内容上看异同俱存。《氓》是弃妇诗的典范之作,讲述了女主人公与氓从相识、相恋、成婚到被弃的过程,对于被弃的原因,女主人公有着清楚地认识——“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士贰其行”[2]48,自己的年老色衰和男子的薄情使这段婚姻走向悲剧。《谷风》中展示的夫妻分离的情况则是由于丈夫喜新厌旧,虽然女主人公对自己的婚姻非常珍惜,但仍旧避免不了被弃的命运,其丈夫移情别恋、迎娶新人进门后,便将其赶出家门。《中谷有蓷》是一首被离弃妇女自哀自悼的怨歌,诗中以山中干枯的益母草起兴,或是用以自比被弃后的憔悴,也有可能是暗示自己颜色已衰就如同那干枯的益母草,遂遭丈夫抛弃,诗中一唱三叹,将自己被弃后的哀怨和遇人不淑的悔恨表现的淋漓尽致。《白华》应是一首出自贵族妇人的弃妇诗,诗中的“鼓钟于宫,声闻于外”[2]228显示了女主人公身份的不同,“之子无良,二三其德”[2]229表明了女子遭弃的原因是男子的变心。这与《氓》中女主人公的被弃原因是一致的。《江有汜》历来争议较多,或认为是男子求婚失败所作,或是女子遭弃所发,程俊英、蒋见元在《诗经注析》中认为这是弃妇自怨自慰之作,笔者亦认同此看法。从诗中语句“其后也悔”、“其后也处”、“其啸也歌”可知“其”应是诗人指责的对方,即抛弃主人公的人。从“其啸也歌”可看出“其”当是男性,“啸”是带有粗野性的动作,应是形容男子的,整首诗当是女子遭情人抛弃,情人另取新人时的愤慨之声。从对这五首诗的简单分析中可看出其中的共同之处,弃妇被弃的原因皆是男子变心,此类诗歌“痴情女子负心郎”的叙事主体模式在此时初现端倪。
《诗经》中的弃妇诗,数量不多,但其所反映的中国古代妇女爱情婚姻悲剧命运的主题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诗经》为滥觞,此后汉乐府、魏晋文人、唐代诗人中均有弃妇诗的创作,甚至这种弃妇主题一直延伸到小说领域,在元杂剧及明清小说中大放异彩,并形成了独有的叙事主题模式,弃妇形象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加上创作者性别角色的转换使本来反映妇女命运的弃妇诗又获得了新的主题内涵。
二、弃妇诗叙事主题模式的形成
汉乐府诗歌是继承《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出色代表,主要反映民风民情的汉乐府民歌也同样存在“弃妇诗”,汉乐府民歌中一般认为是“弃妇诗”的有《怨歌行》、《塘上行》、《白头吟》、《上山采蘼芜》、《有所思》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六首[3]。《怨歌行》又名《团扇歌》,全篇比兴,含蓄而有魅力。此诗当是作于女子被弃之后,哀怨难耐追诉往昔,并用对比的手法表现男子前后态度的大转变。诗中以扇喻人,扇子在被需要时便“出入怀袖”,不需要时则“弃捐箧笥”,实则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含蓄而深刻地道出了女子被男子“呼之则来,挥之即去”的伤感与无奈,写出了女子对自己爱情婚姻的担忧,同时也暗含了对深情难久的负心郎的抱怨,这都是封建社会女子在不平等婚姻中半途为男子所弃的真实写照。《塘上行》同样是女子作于被弃之后,开头交代了自己被抛弃的原因——“众口铄黄金,与君生别离”,其后则用大量笔墨绘写女子被弃后的复杂心情,女子并未对抛弃自己的丈夫加以指责,而是反复诉说了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并在最后表达了对丈夫的美好祝愿,塑造了一个天真宽厚的痴情女子的形象。《白头吟》是弃妇诗中较为独特的一篇,此诗当是作于女子未被弃之时,诗中开篇便写女子要与变心男子决裂,诗中的女主人公有着崇高而真挚的感情理想,当听闻丈夫变心,另有新欢时,她觉得自己的真情遭到亵渎,便选择主动与丈夫断绝关系,并在后面表现出当爱情不再无须啼泣挽留的观念,最后更是直接表达了对男子的斥责。《上山采蘼芜》写的是一对离异后的夫妇在山中偶遇的情景,虽然关于女子被弃的原因说法不一,或认为是男子喜新厌旧,抛弃女子娶新人进门,或认为女子无子,两人不得已被拆散,但被弃后从女子的“长跪”以及问话中可看出她对前夫仍不改深情。以上汉乐府中弃妇诗大抵仍是延承“痴情女子负心郎”的叙事主题模式,并出现一些新变,如《塘上行》与《上山采蘼芜》中女子被弃原因的改变,从男子变心单一原由向多样化发展,或是男子变心,或是社会环境的影响,或是封建家长的阻挠。又如《白头吟》、《有所思》中女子态度的变化,《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严格来说不能归于“痴情女子负心郎”的模式,夫妻二人双双殉情是对爱情的坚守,但这首诗的出现具有典型意义,集中表现在刘兰芝这一人物形象上,笔者将在下文关于弃妇形象演变中对二者详加分析。
魏晋时期文人诗中逐渐出现一批弃妇诗作品,这一时期的弃妇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继承汉乐府民歌系统创作的弃妇诗,如曹植的《七哀诗》、《种葛篇》、曹丕的《燕歌行》、陆机的《班婕妤》以及窦玄妻的《古怨歌》都是此类名篇;另一类则是纯粹文人诗,诗题或以《杂诗》为名,或以《拟某作》为题,如曹植的《弃妇诗》、《杂诗五首之一》、陆机的《拟青青河畔草》就是此类代表之作。魏晋时期的弃妇诗相对以前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诗歌除了在语言上更加铺陈华丽外,在叙事内容上并无大改,大多仍是从女性角度出发,倾诉被弃后的哀怨、愁苦以及自己的眷眷深情。如曹植《七哀诗》开头表明睹一弃妇于高楼发愁,随即以代言体形式描绘了一个尚未被休但长期被弃置一旁的女子的哀怨情怀,“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独栖”,女主人公虽然哀怨,但对自己的状况有着清楚的认识——“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4]458,但即使如此女子在最后仍希望能“长逝入君怀”。其《弃妇诗》则表现女子因无子而被丈夫抛弃的情形,诗歌以比兴起首,以石榴树无实以喻自己无子,“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4]455,其后则主要表现女主人公被弃后夜不成眠,欲诉无门的悲苦心情,然而她也只是一味的自怨自艾,“收泪长叹息,何以负神灵”[4]455,并也在诗末表达了对丈夫的美好祝愿。其他的弃妇诗大致亦是如此,在表现男子无情抛弃的同时,大量笔墨用来描绘女子的被弃后的神态和哀怨心情,魏晋时期的弃妇诗相较前代来说,具体的叙事成分有所减少,而在表现女子被弃后的内心感受与其痴情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弃妇的哀怨情怀更加鲜明突出。从诗歌内容上看,魏晋弃妇诗又进一步继承丰富了“痴情女子负心郎”的叙事主体模式。
唐代弃妇诗从发展上来说是以汉乐府为“母体”的,在创作上对于汉乐府的继承十分明显。唐代弃妇诗相对前代来说数量上亦有所增加,《全唐诗》共收录弃妇诗约110首,其中有大量承袭乐府古题,以“旧瓶装新酒”的模式进行诗歌创作,如李白、岑参及崔颢等人的《长门怨》,李白、李端及刘元叔等人的《妾薄命》。李白、白居易等诗人都作过大量的弃妇诗,如李白的弃妇诗典型之作《白头吟》、《妾薄命》以及《长门怨》,描写的均是喜新厌旧、忘恩负义的丈夫抛弃妻子的主题,但李白与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部分诗作中甚至引入了自己的规劝,在《妾薄命》中发出了“以色事他人,能得几回好?”[5]的呐喊。唐代弃妇诗在叙事特征上表现出“复古”的倾向,魏晋时期文人的弃妇诗将对外描写转向了对内心的探索,着重于描写弃妇的心理感受,到了唐代其叙事特征表现出对外在客观描写的回归。如白居易的《母别子》,叙述了一位骠骑大将军立功、弃妻、另娶新人的全过程,具体叙事成分明显增加,诗中的被弃妇人不仅面临着为丈夫所弃,更面临着与两个幼子生离死别,哀痛之情难以言喻。诗人仍然花大量笔墨来描写弃妇的哀痛,但这些感情除了通过妇人之口来表达之外,还通过诸多客观描写表现出来。总观唐代弃妇诗,绝大多数是表现女子或无子或色衰而被男子所弃的叙事内容,如乔知之的《弃妾篇》、白居易的《太行路》《妇人哭》、孟郊的《去妇》以及李白的《平虏将军妻》等。总体来说,唐代弃妇诗仍是继承自《诗经》以来的叙事主体模式即“痴情女子负心郎”的叙事模式,如果说之前的这种模式还处于发生发展阶段,到唐代,“痴情女子负心郎”的模式已经完全形成并走向成熟,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常见并重要的叙事模式。这种模式不断催生了大量并且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体系中不可忽略的主题。
三、弃妇形象的发展演变
在同一叙事主体模式下的弃妇诗,有着不一样的弃妇形象。弃妇形象的塑造与形成与作者个人意愿以及社会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诗经》中的弃妇形象细分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怨恨决绝型,以《卫风·氓》、《召南·江有汜》为代表,典型的怨恨决绝型弃妇,对婚姻已经不抱希望了,她回顾被弃过程,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从爱情的浪漫主义走向生活的现实主义,最后毅然决然地与过去告别、与抛弃她的人划清界限;二是哀婉柔弱型,以《邶风·谷风》为代表,此类型的女性即使被弃也仍旧对婚姻抱有希望,乞求丈夫能够回心转意;三是独自哀伤型,以《王风·中谷有蓷》和《小雅·白华》为代表,被弃女性已经不对婚姻抱有希望,但她也只是自怨自艾,独自感叹遇人不淑,并不对现实做任何反抗。但从总体上说,她们也具有共性,在性格上勤劳善良、情感专一、为爱付出;在性情上敢爱敢恨、无所掩饰、爱恨分明、不假雕饰,部分女性呈列出炽烈奔放的性格。
到了汉乐府民歌中,弃妇形象产生新变,展现出与《诗经》中弃妇形象不同的特点。一方面是性情上的倒退,一些弃妇形象此时已经失去了《诗经》中女性的那种活泼的生命力,以《上山采蘼芜》为例,弃妇在山中偶遇前夫,不但对其并无指责,还“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女子的言行举止虽不能说其奴性性格已形成,但至少能证明女子性格的软弱,已经被“驯服”;此外《塘上行》中的女主人公亦是如此,对抛弃自己的丈夫并无怨恨指责,将被弃原由归于他人的同时还祝愿丈夫长寿安康,不得不说,这类弃妇形象已经失去了先秦时期女性活泼的生命力。而另一方面则出现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型弃妇形象,她们不甘沉默,勇于反抗。以《有所思》、《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和《白头吟》为代表,在这三位女性人物身上,她们的闪光点在于具有了反抗精神和自我意识。《诗经》中的弃妇形象大都是怨而不怒,《氓》中的女主人公虽然有了精神上的觉醒,但其反抗还尚停留在语言上,在行动上依然缺乏反抗。而刘兰芝和《有所思》及《白头吟》中的女主人公不仅对自身的状况都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能及时地作出决定,其反抗也更加决绝彻底。她在为焦母所不容时,并未委曲求全,而是抱着“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6]。的态度离开了焦家。她更具毁灭性的反抗是她的死亡,刘兰芝的殉情是对作为封建家长的焦母和兄长,以及那个封建社会的一种反抗。《白头吟》中的女主人公那种主动与变心丈夫断绝关系的性格更是前代甚至是同时代都鲜有的。《有所思》也是决绝利落,在得知男子变心后,她当即烧掉定情信物,并“当风扬其灰”,性格刚烈果敢。在中国古代封建礼教甚严的社会环境中,这类女性的反抗更具积极价值,其形象也更加光彩夺目。从《诗经》的其他篇章中可知先秦时期,男女相恋较为自由,思想也比较开放活跃,因此男女之间鲜有来自家庭社会的阻挠。而到了汉代,儒家的思想体系逐渐成为正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开始成为束缚人们的框架,男尊女卑的意识更加明显,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一类女子逐渐被束缚、被“驯服”,失去了原有活泼的生命力,而另一类女子则在压迫下反抗,更加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汉乐府弃妇诗中这类女子的出现是时代的进步、女性思想的进步,标志着她们追求自我独立以及反抗意识的萌芽。
魏晋文人笔下的弃妇形象又是一个新变。魏晋弃妇诗所塑造的弃妇形象显示出一致性,如果说《诗经》与汉乐府中的弃妇形象如同生于乡野的小家碧玉,那魏晋弃妇诗中的弃妇形象则是长于阁楼的大家闺秀。这些弃妇几乎全都以哀而不怨的姿态出现,魏晋文人以华丽的辞藻来表现弃妇的无限哀愁,而以往描写的爱恨纠缠则少有提及了,她们大都是贞洁自守的形象,对感情十分依赖,心中常怀感恩之情,自咎感极深,时时担忧被弃;这些女性在人格上又是超尘绝俗,孤芳自赏的;整个心态偏向于戚戚怨怨,愁苦哀伤,不如汉乐府中女子刚毅果决,多了几分顾惜迟疑。魏晋文人笔下的弃妇形象如同经过了一次过滤,筛掉了以往在爱恨纠缠下情欲的表现,而保留下来并一再咏叹的是弃妇的温柔敦厚和贞顺自守,自此,魏晋文人笔下的弃妇形象走向集温柔敦厚和怨而不怒的深情为一体的审美典型,同时辞藻华美也成为此类诗歌在形式上的重要特点。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是文化、经济、思想活跃发展的时代。唐代的弃妇诗在此种情况下产生,弃妇形象也显示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女子被男子无情抛弃后的悲惨命运以及女子幽怨哀伤的情怀仍是唐代弃妇诗所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如戴叔伦的《弃妇怨》:“出户不敢啼,悲风日凄凄。心知恩义绝,谁忍分明别。”[7]描绘了女子被弃后哀痛难忍的心情,白居易的《妇人苦》亦是此类主题,表现妇人被弃后无可依傍的艰苦生活。此时期坚强决绝型的弃妇形象大量涌现,如乔知之的《弃妾篇》、李白的《代赠远》和《寒女吟》等,都表现了女子与负心郎断绝关系的决然态度。这种反抗型的弃妇对自己的爱情婚姻有了新的认识,如涨潮的《江风行》:“婿贫如珠玉,婿富如埃尘,贫时不忘旧,富日多宠新。”[8]她们开始意识到婚姻中重要的是相濡以沫,互相恩爱,而升官富贵也许只是婚姻的厄运,从而发出“宁从贱相守,不愿贵相离”的呼声,其实,这也是妇女对残酷现实无法改变、退而求其次的辛酸愿望。细细体会,可看出这些言语里流露出唐代妇女追求平等的强烈愿望,体现了唐代进步的婚姻观和妇女观,当然也体现了唐代诗人的平等、民主意识,这是唐代弃妇形象的进步之处。
总之,从先秦到唐代,弃妇形象逐渐走向多元化,在这些弃妇形象的演变中也体现出了与之相应的爱情婚姻观念以及女性意识的变化发展。
四、性别角色的转换
性别角色的转换是弃妇诗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嬗变。性别角色的转换也带来了弃妇诗内涵的相应转变。从《诗经》中的弃妇诗到汉乐府民歌中的弃妇诗,所写多是女子,表现女性被弃后的情形与感受,大抵还是本义上的弃妇诗,如叶嘉莹在《迦陵论词丛稿》中提到:“《诗经》中所叙写的女性,大多是具有明确之伦理身份的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其叙写之方式,亦大多以写实之口吻出之。……《诗经》中所叙写的现实生活中之女性,可以说基本上不是什么象喻性,即使后世的说诗人可以据之为美刺讽喻之说,也只是后加的一种比附,而并非其所定之女性形象之本身所具含的特质。”[9]226-227但发展到魏晋,弃妇诗的创作转入“男子而作闺音”的新阶段。此时弃妇诗不再只是本义上的弃妇诗,而转入象喻阶段,并在后世形成了“逐臣”与“弃妻”模式传统。
自曹植始,常以弃妇自喻,表面上是诗人们采用代言体,代弃妇言,实际上是诉说自己命运坎坷和难以言喻的苦衷。曹植空有一腔抱负,但却为曹丕不容,其内心充满被闲置、被抛弃的痛苦。比如其作品《种葛篇》,表面上是写女子因色衰而被丈夫抛弃后悲痛凄惨的心境,实则以弃妇自比,“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往古皆欢遇,我独困于今。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4]435。蕴含了作者自己的生活和政治际遇。此外《浮萍篇》、《七哀诗》以及《杂诗·南国有佳人》均有以弃妇自比伤怀的含义,其他诸多作家的作品也是颇多寄寓,尤其是在自己对统治阶级的希望破灭和意欲报效国家的理想落空之后,被闲置、被抛弃的痛苦占据了诗人的内心,难以平息,遂借他人之口以抒心中之愤,借他人忧愁以浇胸中块垒。曹植在其诗中凭借这类女子的形象构建了一个比兴意象系统,此后,陆机的《班婕妤》、傅玄的《短歌行》、江淹的《班婕妤咏扇》以及到唐代的诸多作品又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这一比兴意象系统。叶嘉莹对此现象在其书中也曾指出:男性与女性在封建社会都可能会是被弃对象,女子在“夫为妻纲”的伦理中被弃,而男子在“君为臣纲”的伦理中被弃,二者“其得幸与见弃乃全然操之于高高在上的为君与为夫者的手中,至于被逐之臣与被弃之妻,则不仅全然没有自我辩解与自我保护的权利,而且在不平等的伦理关系中,还要在被逐与见弃之后,仍然要求他们保持住片面的忠贞。在此种情况下,则被逐与见弃的一方,其内心所满怀的怨悱之情,自可想见”[9]235。因此二者在命运与感受上是相通的,“遂在中国旧社会的特殊伦理关系中,形成了诗歌中以弃妇或思妇为主题却饱含象喻之潜能的一个重要传统”[9]236。
诗人们用弃妇诗来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一个传统,也在弃妇诗的发展史上形成了“逐臣”与“弃妻”的模式。与前代本义上的弃妇诗相较而言,文人用以自喻的弃妇诗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特殊意义,它可以让诗人将心中长久郁积的失意与愁怨一吐为快,但又不至于降低自认为作为男子应有的身份和尊严。但从内容上来说,自喻体的弃妇诗缺少了以往此类诗歌的生活气息,取而代之的是浓郁的文人情怀,如果说最初的自喻体弃妇诗还能准确而细致地描写弃妇的情感体验及心理状态,那么在自喻体弃妇诗形成一种固定模式后,它在这方面的表现就大不如前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模式的副作用中。弃妇诗的影响延伸至小说戏剧领域,涌现了一大批性格活泼、具有典型意义的弃妇形象,如《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等,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弃妇诗的本义在这类体裁中得到还原,成为反映社会现实和表现妇女悲惨命运的话语体系。
综上所述,以《诗经》为滥觞的弃妇诗在后世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形成了以“痴情女子负心郎”的叙事主体模式,弃妇形象也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简单走向复杂、从顺从走向反叛,性别角色的转换更是其在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转折。这些变化都是弃妇诗在发展过程中新元素不断加入的结果。在当今的诸多文学作品中,“弃妇”仍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这与中国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观念密切相关,也与中国自古以来的此类文学传统不无关联。
[参考文献]
[1]尚永亮.《诗经》弃妇诗分类考述[J].学术论坛,2012(8):66-74.
[2]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郭茂倩.乐府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彭定求.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0:1696-1697.
[6]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78:82.
[7]彭定求.全唐诗·卷二百七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0:3066.
[8]彭定求.全唐诗·卷一百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0:1159.
[9]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雷凯)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126(2016)03-0033-05
[收稿日期]2016-03-25
[作者简介]阳淑华(1993—),女,湖南怀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The Deserted Wife Poems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Its Theme Evolution
YANG Shuhua
(Liberal Arts Colleg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06 China)
Abstract:Deserted Wife Poems which reflected the women′s emotional suffering and oppression is a kind of important subject in the The Book of Songs.It can be said,the Deserted Wife Poems in The Book of Songs is the source of this kind works.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Deserted Wife Poems of the The Book of Songs,focuses on the formation of such poetic narrative theme,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figure of abandoned wives and gender role change,which attempts to briefly discuss the evolution of the abandoned wives poem.
Key words:The Book of Songs;Deserted Wife Poems;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