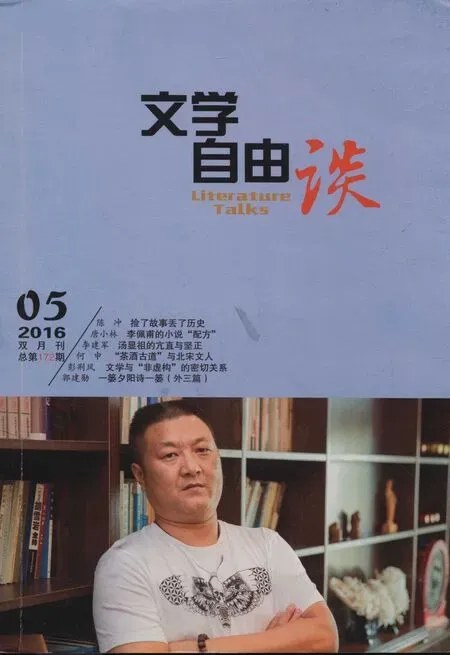有一种写作叫“口语分行写作”
□铁舞
有一种写作叫“口语分行写作”
□铁舞
对一种写作行为下定义,给它一个恰当的位置,不至于让人产生误解,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但我一直没有做成,原因是,给某种事物下定义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这个定义必须涵盖该事物的全部特征;二,它不能另有异义,它的义阈必须是明确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个叫“砸诗会”的微信群让我对一首诗做些评价,我说这首诗当归入“口语分行写作”。这句话是脱口而出,事后想想,这六个字还是挺恰当的,对认识当下的新诗写作现状还有点用处。
“口语分行写作”,是怎样一种写作呢?
先举个例子,有这样一段话:
烧吧,把一切都烧光,一丁点都不留,如果不把人烧死的话,就把东西都烧光,首先把钱,其次把各种证件(包括结婚证),再次把照片(包括所有幸福的照片,尽管所有不幸福的表情和动作从来都不摄入照片),最后把做爱的床和衣服一把火烧光,跟大家一起烧光,跟大家一起成为赤贫,跟大家一起过“第三世界”的日子,烧光,彻底烧光,然后我们穿着裤衩离婚。
我在某个学校的课堂上,把这段话做成PPT放出来,请学生评议:这是什么文体?
“说话!”
又问:“是不是诗?”
“不是!”
换一个班级,我把这段文字换个形式做出来:
烧吧
烧吧,把一切都烧光
一丁点都不留
如果不把人烧死的话
就把东西都烧光
首先把钱
其次把各种证件(包括结婚证)
再次把照片(包括所有幸福的照片)
(尽管所有不幸福的表情和动作从来都不摄入照片)
最后把做爱的床和衣服
一把火烧光
跟大家一起烧光
跟大家一起成为赤贫
跟大家一起过“第三世界”的日子烧光,彻底烧光
然后我们穿着裤衩
离婚
我请同学朗读一遍,问:“是什么文体?”
“诗。”
回答是异口同声的。
又问:“为什么说是诗?”
“诗都是这样分行的。”
看来,分行已经成为新诗(自由体诗)的外形标志。
北大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辜正坤说:“真正能把诗同其他文学样式区别开来的形式特征,只有这两点:押韵和分行。在现代意义上,分行甚至比押韵更重要。我们把一篇纯粹的散文稍加处理,分行押韵,虽然也可能是很枯燥的、蹩脚的诗,你却不能不承认它是诗,因为它具有惟有诗才具有的标志。同理,把李白和莎士比亚的最好的诗取消韵脚和分行形式,和其他散文放到一起,则我们必定认为它是散文,或是抒情散文,却绝不会认为它是狭义上的诗。”
事实上,再差的口语,你把它分行后再拿出来,别人也会把它看成是诗 (有些合起来则既不是诗,也不成散文,什么都不是)。
所以,有一种写作叫“口语分行写作”,它的妙处就是有些分行文字能被看成为诗。
上述这首诗引自 《大诗论——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年编· 2013》这本书中一篇题为《干货:诗话》的文章,作者是澳大利亚的华裔作家欧阳昱博士。在欧阳博士眼里,这首《烧吧》是一首很好的诗,他解释道:
这首诗看到最后,朋友“噗哧”一声笑出了声,觉得好玩,但也仅此而已,因为他并不知道这首诗的“秘密”,那就是它写于2009年3月份的维省大火。当时火势紧密,到了我这条街弥漫着硝烟般烟雾的程度。这首诗在中国发表,又没有些诗外信息,如果诗人死了,写诗的日期和地点全部抹去,再好的评论家,也无法把诗和现实联系在一起,就只能就诗论诗,而无法就事论诗
了。从这个角度讲,诗歌是需要秘密的,否则就是消息、信息。
这段话里,我觉得有句话说的是对的:“诗歌是需要秘密的,否则就是消息、信息。”然而我觉得他所写的这首诗的“秘密”仍然是“消息、信息”,我们知道了这些“秘密、消息”以后,还能知道些什么呢?古往今来,凡好诗都藏有秘密,这一点应成为常识。
我在课堂上做的那个实验,验证了一个事实:一旦把文字分行,人们就会把它当诗看待;一旦得到诗的“礼遇”,这段文字就闪闪发光了,诗评家就会像诗一样体会它的诗意了。这样的事,我们不是经常见到吗?分行真是很奇妙。眼下这种分行写作已经随处可见了。我有一个朋友将和孩子在一起吃饭时说的话记下来,分分行,就被认为是诗了,孩子也被看成是“小诗星”了。朋友带她一起去哈尔滨参加一个文坛活动,孩子逢人就说“我是小诗星”,拿出手机朗读自己的诗。这是真实的事。
所以,有一种写作叫“口语分行写作”,其有妙处或无妙处已经实是无所谓的,只要分行就是了!
欧阳博士的“干货”中还有一首:
起来,放下
腿子起来了
身体放下了
身体放下了
东西起来了
东西起来了
精神放下了
精神放下了
身体起来了
身体起来了
一切放下了
一切放下了
恶的起来了
作者对这首诗也颇为得意。据说,那一年作者参加第三届青海湖诗歌节后,到兰州、西安、深圳一带周游了一圈,写了40多首诗,把绝大多数拿出来投稿,其中不少还在长安诗歌节上展示了一下,唯有上面这首没有亮相,只是在朋友家的一次派对上,拿出来试读了一下,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朋友说,这一首好!一下子把前面读过的几首诗都否定了。那晚上,席间充满了一个“起来”“放下”的语序,被诗歌的韵律所主宰,大家都觉得很好玩。作者感叹,这都是些数十年如一日不读诗的人呀!
我感兴趣的是,写了40多首诗,为什么唯有这一首没有拿出去发表?这是一;二,朋友说这一首好,好在哪里?三,席间充满了“起来”“放下”的语序,那气氛是被“诗歌的韵律”(够高雅)所主宰,还是被那种调笑(娱乐)的气氛所主宰?作者的感叹,忽然让我感受到一种新诗的出路:原来,诗要写得这样才受欢迎呀!
想必作者的朋友圈以知识分子居多,数十年如一日不读诗,也叫人惊叹!而作者还坚持写诗也不容易。只能这样解释——他对诗有种特殊的趣味。
我有点好奇,于是有一次,在一个隧道工人(这些才真是从来不读诗的朋友)的聚会上,我把这首诗也朗读了一遍。他们听了以后,第一个反应是:“下作!什么‘东西’起来了!”我赶紧声明,这不是我写的诗,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博士写的。看来写这样的诗要走到民众中间去也是有问题的。知识分子的那份“高雅”,在我的工人兄弟眼里看来是“下作”——究竟谁“高雅”了谁?谁“下作”了谁?
所以,有一种写作叫“口语分行写作”,在一部分人眼里是高雅,在另一些人眼里可能是下作。
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写作?
欧阳博士有一篇妙文——一封给朋友的信,我认为是值得一读的,它有助于对这类文体——我尊重地称这是一种文体——的认识:
诗歌已经为世人不齿。当我问我教的那些80后乃至90后的学生看不看诗时,几十个人中举手的仅有一二。当我再问他们是否写诗时,这些人居然哈哈大笑起来,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太滑稽了。
这次在深圳与朋友读诗,同行的还有两个商人朋友。他们在那儿如坐针毡,完事后怨声载道,但我不怪他们,我怪那些诗人,因为他们读的诗实在距离现实、现世太遥远,太不相干……
其实口语并非口语,还是唇语、舌语,以及口腔语和嘴语。它是直接与快感、口感相连的。我以我手写我口,好像是朱自清说的,就是这么简单,但口语诗又跟口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我们写诗时,从来就没有用口去念过,只是从手上、指头上走了一遭,在心中、在脑中过了一遍,在眼睛中过了一遍,所谓口语,就是一种快感诗,追求快感的诗歌,而不是那种故作深沉,写得谁都看不懂的诗。直到今天,在中国、在澳洲,这种……诗还大有市场,特别是在澳洲。最难懂的诗,其实最容易写,我就这么写过、玩过,用英语,在澳洲大报发表过,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一切拆穿,让他们知道诗歌的真相。有个澳洲白人夸口说:他一部小说写了十年。还有一个人说:他把一首诗修改了十几次。可是我要说,我最好的诗歌永远都是一次也没有修改的。我的英文诗歌七年连续被收进澳洲最佳诗歌选,没有一首是修改过一个字的,就这么简单。
一个诗人,就是一条不断创新的河流,流到哪儿,就创作到哪儿,就像我那样,随处走,随处写,哪怕走进坟墓连骨灰都在写,通过后世来写。尽管路遥对诗人的表现颇带偏见,但他能比较敏锐地注意到“诗情”,作出这样的判断:“难道只有会写诗的人才产生诗吗?其实,所有人的情感中都具备诗情——而普通人在生活中的诗情是往往不会被职业诗人们所理解的。”这跟我前面说的情况是一样的。人人都是诗人,唯一的差别在于,有的人一生写诗,有的人一生都不写诗罢了。
我喜欢这封信,读完以后,禁不住在心里冒出两个字:真牛!这封信非常真实(因为是私信,断定是干货);但这封信里同样充满了有智慧的错误。我喜欢这种有智慧的错误,因为通过这种错误我们能看到事情真实的一面。
“诗歌已经为世人不齿”,这话肯定不对。他所教的那些80后、90后不能代表全部世人,即使80、90后是不齿诗歌的,也要问问他们的理由。也许作者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要怪那些诗人,因为他们读的诗实在距离现实、现世太遥远,太不相干。那些诗人是谁?有没有臧棣?有没有伊沙?(我特别提出他们俩,是因为在大陆,他们有代表性,以后要写入“文学史”的。)说明一下,我为什么要把大诗人臧棣拉进来,因为在微信里,有人转发过这样一条评论:
臧棣或许是一个创意天才,但是不是一个诗歌上帝呢?他的写诗方法可以在广告公司开个培训班,用这种方法激发人的思维,挖掘无限的创意能力,是很好的。但要在诗群里给人做个榜样不行。在大学课堂里给学生做个诗歌可能性的讲座是好的,也属高级层次,但
要放到诗歌普泛层面上来提倡是有问题的。
这条微信还算中肯。
的确,欧阳博士说:“口语并非口语,还是唇语、舌语,以及口腔语和嘴语。它是直接与快感、口感直接相连的……所谓口语就是一种快感诗,追求快感的诗歌,而不是那种故作深沉,写得谁都看不懂的诗。”而臧棣的诗歌是不是故作深沉且不说,很有些人写诗是写得谁都看不懂,倒是事实。
欧阳博士最牛的一句话是:“最难懂的诗,其实最容易写,我就这么写过、玩过,用英语,在澳洲大报发表过,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一切拆穿,让他们知道诗歌的真相。”对此,我们拭目以待。欧阳博士的信还让我们知道,不仅在中国,特别在澳大利亚,这种诗歌还大有市场。
所以,有一种写作叫“口语分行写作”,它原来是一种追求快感的诗,而快感也算是一种美学趣味吧!
趣味归于道,道不同,不与谋,臧棣和欧阳博士肯定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得出这个结论并不难,难的是要解决一个困惑:新诗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从古至今诗歌一直在发展,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打破了瓶子碎了一地一样。现代人追求自由,快感的口语表达是最能外显的。现代人彰显个性,像臧棣那样发明一个“诗歌的风箱”,写出一些朗读时 “谁也看不懂的诗”,中国诗歌何去何从?谁能够给个好的回答?
我举这两类诗歌为例子,想问一下,这两类诗歌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美学老人朱光潜的《诗论》中有这么两段话:
中国诗只达到幽美的境界而不能达到西方诗那样的伟大的境界。
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受。
我们今天创作现代诗是为了贡献出伟大的诗。但上举两类诗能贡献出“幽美的境界”吗?能贡献出伟大的诗吗?
我一直认为,口语向上是诗语,口语向下是口水。如今口水诗多于诗语诗,简直如滔滔黄河,奔流直下了,没有人再把创作看作是想象的自由而神妙的过程;像欧阳博士那样的“优等”(毕竟是博士)口语诗,似乎也只是为娱乐提供有点技艺性的构思和趣味而已。欧阳博士在这方面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干货”,说美国有个诗人叫DavidAntin,据说从不用笔写诗,而是直接上台说诗,没有任何准备。录音机当场录好之后,再整理成文字,感觉好极了。接着他就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一天吃早饭时,他跟老婆谈起一个他们都知道的女性的人生之路时说:“女人只要把身体打开,就有路了,到什么道,这就是道。”这话一出口,欧阳博士就觉得:哎,这不是诗又是什么?便立刻走到书房,把这段话用分行的形式写下来——注意,一定要用分行的形式,否则就只是餐桌边上的一句普通的话而已。我总觉得这种写作和真正的创作毕竟是两回事,至少不能算是很高级的;若这也算得上是诗歌大道的话,那么我要说新诗已经走到头了。与其相反的极端例子(如臧棣),在相反的方向上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写到这里,我忽然产生了一点新的联想:人类社会经历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欧阳先生那样的口语写作似乎处于这个时期;野蛮时代是学会靠人类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的方法的时期,这样打一个比方,欧阳先生又进入到这一个时期了;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我们今天照例应该处于这一个时期,可是感受不到真正的艺术在产生,依然感受到的是蒙昧和野蛮。
当我们看到大量的不堪入目的诗歌,你不要愤慨,不要不安,镇静些,你是真正热爱诗歌的人,你就把它们看作一种分行写作罢了。今天口语+分行,不口语也分行,诗也好,不诗也好,仅此而已。
所以,有一种写作叫“口语分行写作”,我们不必对它要求过高。
举欧阳昱为例,还因为他可能是一个50后的文学博士,应该是诗歌严肃纯正使命的担当者,只可惜老男孩被诗歌消费主义俘获,丧失了高级诗歌的写作能力。那么,该如何为80后、90后做出榜样呢?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真问题。
我宁愿把这个时代看成一个手稿时代,毕竟这个时代有许多思想,没有清一色的局面。任何一个世纪,都没有涌现过如此变化多端的口语、诗语、口水,它们交相混杂,莫辨真假的景象,在繁杂喧嚣中我们也许还能看到有另一种平静。
手稿时代。也许是最平静的
时代。许多作品,都收敛自己的光辉。
也许不是的,我想,这恰是崇山
准备耸起,大海正处于期待。
《大诗论——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年编》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资料集,既是资料汇集,就是为众人共同享用。这一次我算是享用了一回,让它发挥了一点资料的作用。至于欧阳昱博士的《干货:诗话》一文,确有不少精彩的议论和许多有益的指点,是值得一读的。我和欧阳博士素不相识,不揣浅陋而成此文,目的是为了探索诗道,决无攻击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