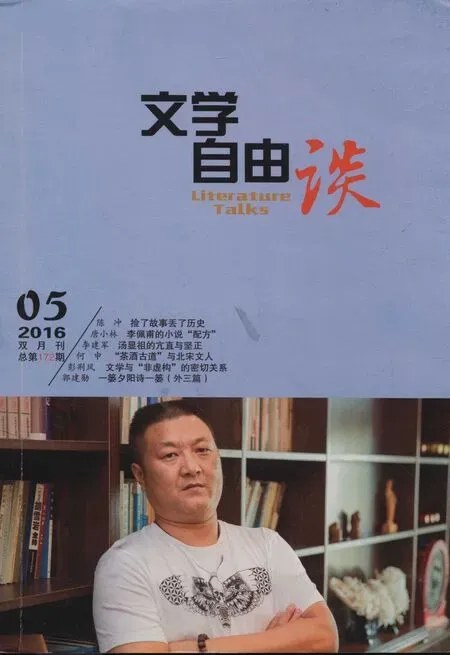“哑行者”蒋彝
□[美]陈艳群
“哑行者”蒋彝
□[美]陈艳群
年初为吾师、九十高龄的罗锦堂先生整理文稿和字画,准备将他几十年来有关蝴蝶的札记与咏蝶诗,以及他在中青年时期所绘的工笔蝴蝶图和名人题跋,结集出版。
在一叠翻拍的书画作品的照片中,我看到一幅署名“蒋彝”的墨宝,落款“彝”字的下端,极为夸张,似两条细长的腿,一立,一扬,呈45度角展开,宛如飞燕起舞,优雅轻盈。如此独特、富有动态的签名,应出自于感性的艺术家之手。我将照片递给罗先生请教。罗先生架起老花眼镜,目光直奔书法左下角的签名上,说:“蒋彝,哈哈,哑行者。”停顿片刻,寻思如何介绍此人,“他就是将Coca-Cola译成‘可口可乐’的人。”
“哦?蒋彝竟等于可口可乐?!”我顿觉豁然贯通,有似曾相识之感。可叹蒋彝之真名,潜伏于名牌底下,竟然长达近一个世纪。此于译者,岂非甚为委屈?
“蒋先生是否以此获得了译名专利权,或得到什么褒奖吗?”我好奇地追问。“没有,”罗先生说,“那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他的译名被选中后,可口可乐公司仅给了他6英镑的稿酬,就买断了使用权。一提及此事,蒋先生便甩头慨叹,说当时哪怕有一些该公司的股票也好。”
话虽如此,但我想,蒋彝先生每见此广告一次,必得意一次。成就所带来的满足往往胜过一切物质需求。
“蒋先生是个博学多能的人,其英文著作等身,且体裁宽广,有游记、诗歌、小说、散文、儿童读物等。其家学渊源,幼承庭训,沉潜丹青。书法擅四体,画风尤为独特,以中国传统画法参以西方构图色彩,令人耳目一新。他还为芭蕾舞剧设计过舞台布景呢。你知道,蒋先生还是第一个画熊猫的人,英国人称他为‘熊猫先生’。”罗先生如数家珍,侃侃而谈。
我没看走眼,蒋彝先生果然是位艺术家!
1926年,蒋彝毕业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化工系,分别在江苏、江西任教数年。青年时期踏入政坛,历任安徽芜湖、当涂和江西九江县长。“父母官”蒋彝欲为民众谋福祉,他整顿社会秩序,力图改革教育、税制、土地等不合理制度。他体察民情,亲办三宗离婚案,为提高妇女地位,捍卫她们的权益而呐喊。他欲铲除腐败政治,断绝裙带关系,怎奈那“三把火”烧得过旺,殃及权贵利益,触摸老虎尾巴而招致诋毁报复。壮志未酬的他,自怨无德无能,不能遏止贪赃枉法的军阀,以及地方的恶势力,失望之余,挂印而去。他举目四望,江山一片混乱,便将目光投向海外,欲睹西洋政府管理国家之道。于是,他决意远赴英国,研习其政治体系。
蒋彝求助于兄长和亲属,借得一笔款,同时获得江西省提供的微薄奖学金,将妻儿托付给兄长后,只身踏上了去英伦学习的航程。
在茫茫的大海上,蒋彝悄然度过了三十岁生日。三十岁要重新在异域生根,开辟一片天地,语言是先决条件。他相信事在人为,一到英国,便发奋攻读英语。两年下来,他的英语不仅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应付裕如,还用英文写出了第一本以书画为题材的图书《中国画》。
明明来此寻求治国之道,如何转向了艺文世界?罗先生告诉我:“蒋先生家学渊源。父亲是瓷片画家,他从小于父亲的膝下学习书法和绘画,功底不浅。到英国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重拾丹青,随后进入大学教授中文、书法和中国绘画。”
上世纪30年代初的英国,中国文化艺术氛围甚浓,仅伦敦就举办了好几次中国艺术展。其间,刘海粟造访伦敦,带来几十幅中国现代优秀画家的作品,将于新百灵顿画院展出。蒋彝被请去协助布展。刘海粟得知蒋彝擅丹青,邀他参展,他也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创作了几张小幅画作助兴。孰料展览期间竟卖掉一幅,这让蒋彝惊喜不已。很快,他又认识了著名汉学家骆任廷(香港的骆克道即是纪念他在此做过布政司)、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等人,并成为了他们的朋友。身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董事的骆任廷,得知学校需要中文老师,立刻想到了蒋彝,有意举荐他。蒋彝完全没有中文教学的经验,但他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很幸运地通过了系主任庄士敦的面试,进入该校,并逐渐结识了许多活跃于当代的艺文界人士。伦敦常有中国的文化界人士往来。在与徐悲鸿、刘海粟、梅兰芳等艺术大家的交往中,蒋彝越发意识到,凭自己的艺术修养,他完全能够向金发碧眼的西方人介绍中国,做个中西文化的桥梁。很快,他调整了人生坐标,朝文学艺术之路奋进,先前的政治抱负被眼前的艺术机缘和对艺术的热忱所替代。
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先有赛珍珠以中国农民为题材的英文小说《大地》问世,在欧美引起轰动,并由此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旋即林语堂来美,出版了英文《吾国吾民》文集,较为系统地把中国和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让欧美人实实领略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境界。同一时期,在大西洋东岸的英国,学英文出身的戏剧家熊式一,将中国传统剧目《王宝钏》译成英文出版,好评如潮,接着又将此剧改编为四幕喜剧,搬上英国的话剧舞台,以其“幽默轻松,异国情调,与众不同,新颖独到,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艺术特征,创造了在伦敦连续三年、达九百多场演出的中国剧种奇迹。后来,熊式一接到美国发来的邀请,移师百老汇,《王宝钏》连续演出一百多场,许多社会名流甚至罗斯福总统夫妇皆莅临捧场,赞不绝口。
在熊式一的《王宝钏》一书中,除了有当地诗人和评论家赛尔斯·阿伯克隆比作序、徐悲鸿为封面和书首画了两幅画外,还有蒋彝精心为书中人物所作的十二幅线描插图。同为江西人的熊式一,对这位初来乍到的老乡和室友所作的插图非常满意,他对蒋彝说:“蒋兄,今后咱俩合作吧,你就专门为我的书画插图。我出了名,你也有一份。”
熊式一这番话,让蒋彝内心不是滋味:个头矮他一截的熊式一将他看走眼了。他不甘于现状。他意识到,熊式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的英语功力。他告诫自己,必须花大力气尽快掌握英语这把钥匙,有了它,就能打开通往自己理想和目标的大门。
1935年11月,大型中国艺术展览会在百灵顿画院举行前夕,伦敦各大书局纷纷请专家写书介绍中国艺术。麦勋书局经理艾伦·怀特认为,艺术展是促销有关中国艺术书籍的绝佳时机,而这样的书最好由中国艺术家来写。他通过熊式一找到蒋彝,请他担当此任。蒋彝虽然心存顾虑,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无法胜任,但机会实在太诱人了,一咬牙,毅然承诺。
接下来的英文写作,让蒋彝苦不堪言,满腹的诗情画意被蹩脚的英语堵得无从抒发,自信心受挫。就在此时,一位女子出现了。她叫英妮丝·杰克逊(InnesJackson),是蒋彝“初级古代汉语班”的学生,不久前刚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又在东方学院专攻古代汉语。英妮丝对中国文化兴趣极浓,也很愿意助蒋彝一臂之力。她逐字逐句地为蒋彝修改推敲,将词不达意的语句重新组织,加工润色。终于,蒋彝的《中国画》一书赶在展览开幕前一周出版了。这次大规模的中国艺术品展览让英国和从欧洲其他地区赶来的人大饱眼福。展厅里三千多件书画、雕刻、玉器、铜器、瓷器等琳琅满目的艺术品,大都是国民政府精挑细选的珍品,英国方面更是特派萨福克号军舰专程去中国运送。正如出版商的预料,许多人是读了蒋彝的书后进入展厅的。《中国画》运用比较的方法,强调东、西方人与自然关系的区别,取材独特,集书画、人文和历史知识为一体,引导读者去欣赏东方人的智慧,拓宽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视野。
蒋彝和英妮丝之间的友谊维系了一生。这位谦虚好学、文笔娟秀而又乐于助人的英国女子,是蒋彝一生的精神支柱和写作帮手。可以说,蒋彝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得益于英妮丝在文字上的把关。
《中国画》出版一个月之后得以再版。处女作旗开得胜,让蒋彝更加坚信自己要走的路。从此,他开始了一系列的写作和中国艺术教学活动。
两年后,也就是1937年,蒋彝以“哑行者”为笔名,出版了第一本散文游记 《滨湖画记》(TheSilentTravelerInLakeland),让古板自大的英国人耳目一新,一时成为畅销书。该书非普通的游记,也不似赛珍珠和林语堂等其他作者的中国题材作品,而是别出心裁地用英语描绘了英伦的人文风物,并将中英两国文化进行对比。在书中,他使出了十八般武艺,散文、诗歌、书法、绘画和印章,多管齐下,真可谓“以诗文书画描绘英伦气息,访山水风物论中英异同”。英国作家里德(HerbertRead)在序言中说:“蒋先生闯进我国的圣地,以中国方式致敬。”可谓一语中的。蒋彝以一个中国艺术家的独特角度对西方文化进行评论,让西方作者望尘莫及,这也是他独一无二的优势。
事实上,英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大半是从中国回来的外交官或传教士偏颇的描写中获得,如男人蓄长辫、女人裹小脚、黄包车夫、吸鸦片者、乞丐等旧时中国的落后形象;如今居然有个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华人出现在他们眼前,对他们的大英帝国品头论足,还不失生动幽默地将他们的众生相和日常生活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将他们的文化特征了解得那么透彻。英国人平素习焉不察的生活细节,经东方人所持的镜子一照,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虽然有那么多可爱可贵之处,也有荒唐可笑的一面。同时,他们更是透过蒋彝多才多艺和幽默的文笔,领略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让英国人甚为讶异。所幸保守傲慢的英国人并非主观自大,而是以喜爱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一样的真诚和热情,争相购买与传阅这本书。《滨湖画记》出版后一个月即售罄,随后又增印了八次。
那是中国人民惨遭日本蹂躏之时,同时也是中国文化风行欧美之际。这看似奇怪的现象,仔细想来也有它的因缘。中国当时战乱的局势,逼迫许多国人向外求生存谋发展。一些身怀技艺的文人,如赛珍珠、林语堂、梅兰芳、徐悲鸿、熊式一和蒋彝等,都来到海外,纷纷将作品以不同形式呈现给欧美的观众与读者。日本侵华的事实对于欧美大众来说遥不可及,而眼前的中国文化和艺术却强有力地震撼着他们,从而对饱受日本蹂躏的中国同情心油然而生。谁能说,这些大国的首领、将官和外交官,在援华的政策上,没有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呢?
蒋彝开始小有名气,且一发不可收拾,各国文化人士纷纷发出邀请,企望他也为他们的城市画个像,把把他们的文化脉搏。蒋彝用四十多年的时间遍游欧美各地,采风问俗,搜珍集锦。他相继出版了关于伦敦、爱丁堡、纽约、巴黎、都柏林、波士顿、旧金山、日本、约古郡、牛津以及战时欧洲等的“哑行者画记”。这些有着蒋彝独特风格的游记,里面皆加插他的画和诗词,而诗词是用行、草、篆、隶等四种不同字体书写的。这一写作特点,始终贯穿在他每一部游记中。
一个东方人能以异域城市为题材,出版这一大批畅销的英文书籍,当非幸致。观察入微和勤于笔耕,固然是起码的条件,更重要的,还是以深入浅出的理论,发扬中华文化之精华,且世情练达、洞悉人性。西洋人开始对这位中国人刮目相看,无不觉得这 “哑者”其实是凡事心知肚明,太能说了。《中国书法》于1955年出版至今,仍为美国许多高校学习中国书法的基础教材,而《纽约画记》在上世纪50年代还荣登《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
可以说,蒋彝是当时欧美民众所认识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他的读者面从稚童到老年人,几乎各个年龄阶段皆有。唤起蒋彝为儿童创作的并非他因,正是国宝熊猫。
熊猫的发现是在19世纪末。它们生活在四川的高山深谷,不为世人所知,更鲜有一睹其芳容者。1938年的平安夜,一艘货船在雪夜中驶进伦敦的港口,为英国人民带来了一份惊喜的圣诞礼物——五只大熊猫。它们不是官方派来的“大使”,而是经人倒卖,从四川经贵州、广西、广东,最后辗转来到香港,再在海上漂泊多日而来到伦敦的。虽来路非正,但并不影响它们受欢迎的程度。伦敦动物协会将收购的其中三只分别冠以中国朝代之名——“唐”、“宋”和“明”。而不足一岁的“明”似乎比它的同伴更活泼,更招人喜爱,被选择在伦敦动物园里展出。它那毛茸茸的黑白身子,憨态可掬,其可爱的形象立刻成了许多商家争相开发的商品;英国的卡通、明信片、烟盒、珠宝、玩具、报刊杂志,甚至电视节目上,“明”的形象无处不在。
这可是个新鲜事儿。蒋彝造访了这个大明星。他边看边想,灵感随之而来:熊猫黑白分明的毛色,非常适合用中国的水墨画来表现;熊猫喜食竹,而竹子本身是中国传统绘画中常见的题材。“这是我画画的好题材!”熊猫的习性是昼伏夜动,白天总是懒洋洋地躺在那里,甚至背对着观众。作为伦敦动物协会的会员,蒋彝得到动物园的特别许可,得以晚上留在动物园,观察熊猫的习性。他画了上百张速写。回到家,铺纸染翰作画。他笔下的熊猫,有的依石,有的采竹、食竹,有的奔跃,有的独行、独笑,自得其乐,还有两小无猜、父子或一家三口的生动画面。他将熊猫的坐、卧、仰、爬、走、叫,或嬉戏或闲适的姿态,描绘得活灵活现。他以熊猫为创作题材的画不下千张。
与熊猫和其他动物“相处”久了,蒋彝萌生了写儿童书籍的想法。很快,一本本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金宝与大熊猫》《金宝游万牲园记》《金宝在动物园》《明的故事》《罗铁成》《大鼻子》等书相继在英国出版,深受儿童的喜爱。其中《明的故事》卖了25万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些轻松活泼的儿童读物曾抚平多少孩子的心灵,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
罗先生说,蒋彝移居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达十六年,此外还马不停蹄地穿梭于哈佛大学、香港大学等处演讲、教学,回到寓所就是写作和绘画。他以传播中国文化为使命,且一生从未间断。努力付出而获得的荣誉也接踵而至,他因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被评为“美国最杰出的华人”。
蒋彝数度受到邀请,客座夏威夷大学,讲授中国书画,每次停留时间一至三个月。其间他与罗先生交往密切,俩人常常在一起谈书画、佛教、诗词等。罗先生没有读过蒋先生的游记,但从他们的交谈和蒋先生送他的画册,以及为罗先生的题跋中,可以感受到蒋先生的博学多才。“你看这题跋,”罗先生指着照片说,“‘年年透视庄周梦,何幸能游百蝶乡……冉冉翩翩,至饱眼福’中的‘冉冉翩翩’就用得妙。这都是有出处的,取自曹植的《美女篇》,原文是‘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可见蒋先生读书广博,引经据典,信手拈来。
许多人写游记,总是挖掘与自己文化的不同之处,而蒋彝则喜欢发现相同点。在他看来,文化不同会产生身处异乡的孤独感,而探索两国间的共同之处,不只是一种文化的比较,且是将心安置的一种方式,可以在异域寻找和体验“归家”的感觉。
说到家,这是蒋彝最不愿揭开的一个话题。孤悬海外42年,他的情感方面是一片空白,整日面对冷火秋烟,无人问寒问暖,荣辱皆自领,其中的“苦痛”,怎三言两语能说得清啊!
那是大半辈子的苦行僧似的独身生活,“家”对他来说,有名无实,唯养家的责任和义务让他感觉到家的存在。一家六口因战争散作四处,一想到颠沛流离的妻子和子女,自己无法履行做丈夫和父亲的义务,蒋彝每每长夜垂泪。
他的生活恬淡自持。友人来访,只见“一室之内,只四壁图书,萧然一榻”。在周围的邻居看来,他是一个话语不多,但和蔼可亲、喜欢爽朗大笑、非常幽默大方的人。房东、邻居、朋友的小孩都非常喜欢他,称他为“哑叔叔”;他也常跟他们一起玩,给他们画些山水、鸟兽,或将自己的书送给他们,还给他们买糖果和冰淇淋吃。他的包里总是装满了各种小礼品。每次旅行,这些孩子们会每天查看邮箱,盼着“哑叔叔”的来信或明信片。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他就会拿他们的年纪与自家的孩子对比。在众人面前总是笑盈盈的他,内心却无时不在撕裂地痛。
他虽然洋装在身,但骨子里的传统思想依然根深蒂固。1947年,蒋彝想方设法把17岁的长子健国接到身边。他不许儿子与其他华人过多接触,哪怕是好友熊式一家也不许常去;他鼓励儿子多与英国人交朋友,扩大社交圈子;他更希望看到儿子成为一名儒雅的绅士。健国长大后,自己开了一家印刷公司,后改名为“哑行者出版社”,并娶了一位英籍女性为妻。儿媳妇心直口快,没有中国传统女性的温顺,和蒋彝见面也只是一声“哈罗”。这让蒋彝心中大为不满,断定这样的儿媳不会理解中国的文化和习俗。他曾试图劝阻儿子中断这段关系,而完全西化的儿子觉得父亲的思想太守旧,拒不相从。很明显,父子之间出现了代沟。当蒋彝移民美国时,儿子不愿一同前往,这让蒋彝大失所望,不免懊恼沮丧。好在不久小儿子健飞来到美国,多少给了他一点慰藉。后来,大儿子一家也迁来美国。难得三代同堂,却因两代人的理念不同而矛盾重重。这是孤独了大半辈子,渴望家庭温暖的蒋彝所意想不到的。
无处话孤单。不饮酒的他只能借诗句舒缓心头的愁苦:
西游怎比孙行者,
梦里江南总属空。
近识此生多不是,
不夫不父不公公。
蒋彝数次来檀岛,非常喜欢夏威夷,也打算写一本夏威夷画记。不仅喜欢,他曾在此结过一段情缘,遇上一位小他三十多岁的台湾人。两人情投意合,先后来美的蒋彝的两个儿子也表示支持,无奈年龄关系,使得对方父母坚决反对。在他的一生中,这是唯一燃起的爱情火焰。此前,他与表姐是指腹为婚,膝下虽有四个儿女,但彼此之间没有婚姻基础。四十余年的漂泊,洁身自好的他终于等来了幸福,然而,这份幸福终究跨不出传统观念的羁绊,黯然止步。
倦鸟知还,叶落归根,故乡对一个人永远有着致命的吸引力。那些年来,蒋彝像一个犹太人一样到处“流浪”,但是,心中的耶路撒冷只有一个:故乡。
终于,故国厚重的大门“咣当”一声,拉开了门栓,对外敞开了。随着这一惊天动地的巨响,纷乱而兴奋的脚步,从世界各地向国门涌去。
蒋彝内心既兴奋又紧张,将与阔别42年的妻女团圆,是难以想象的场面。这场面让他既欢喜又害怕,心神不安。他的哥哥、姐姐等亲人已不在人世。回国之旅究竟是喜重逢还是断人肠,他不能预知。他只祈求有一种方式,能弥补四十多年来亲人间生离死别的空白。
当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蒋彝从机舱走出来,深深吸一口故乡的空气。44年的夙愿,终于得偿。一声声“爸爸”、“外公”,如梦似幻。他热泪纵横,喃喃地对亲人说:“真想不到,真想不到……”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无论是与瘫痪的妻子,还是与两位女儿和孙辈们的见面,都令他百感交集。他每天去女儿家,陪伴为他吃尽苦头、替他尽孝心、抚养四儿女的贤妻。彼此回避怨言,唯享重逢的喜悦。
回国的所见所闻如浪潮,在他内心翻滚。他要把这些感受记下来,要将祖国的变化向外界传播。回到美国,他开始写《重访祖国》,而此时,他被诊断为结肠癌。他知道时间有限,终于在再度回国之前完成了这本书。他还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国去走遍大江南北,写一本《中国艺术史》。为此,他奔波于十几个省市之间,获得了不少资料,也做了大量的笔记。但病魔难敌,不久,这位艺术家因内脏衰竭而在祖国辞世。
《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相继刊出他的讣告。蒋彝去世月余后,他的新书《重访祖国》出版。诺顿出版社按照蒋彝生前的嘱托,给世界各地几十位朋友各寄一本赠书,每一册都附上一张他的签名;罗先生也是在收到出版社寄来的书中才得知老友已辞世。这是蒋彝离开纽约回祖国时,为关爱他的人送上的最后一份礼物。他早已想好了告别的方式。
“哑行者”去了天国,续写他的“天国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