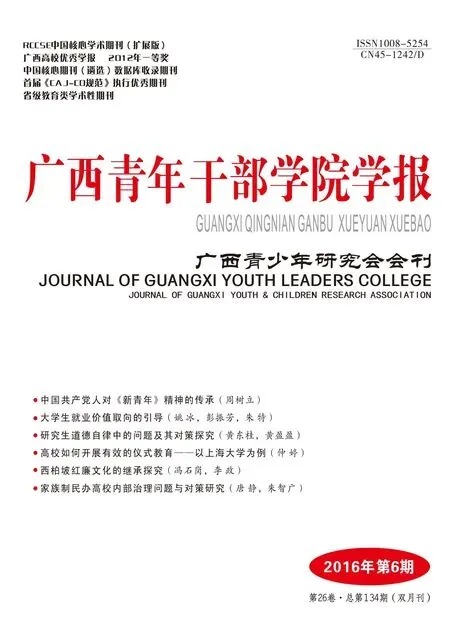中国乡村控制方式的变迁——读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有感
梁永郭,吕传旭
(河北工业大学,天津 300401)
中国乡村控制方式的变迁——读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有感
梁永郭,吕传旭
(河北工业大学,天津 300401)
几千年来的中国乡村,经历了种种社会控制方式,从宗族保甲到士绅团练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村民委员会,都传承着“礼”“法”共用、各施其长的控制手段,这种极富中国特色的控制方式也将为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和更好地实现法治下乡提供参考价值。
社会控制;中国乡村;宗族;国家政权;费正清
乡村的社会控制是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重要问题,关系着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也联系着农民的生活和命运。社会控制,又称社会约制、社会整合、社会调整等。社会控制都是通过社会力量保证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确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可以分为硬控制、软控制,也可以分为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包括法律控制、伦理控制、政治控制、资源控制等,随着中国社会历史事实的不断变迁,中国乡村的社会控制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一、传统中国——宗法与行政控制并重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乡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社会控制方式,学界有不同的观点,秦晖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这种观点在一段时间内非常盛行,但同时也有别的研究显示,宗族从来都未曾自治,血缘族群的社会虽然有一套伦理机制,但却无法摆脱皇权的控制,所以乡土中国是皇权控制下“编户齐民”的社会,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到底哪一种才是真实的乡村社会控制方式?
(一)宗族治理与乡村政治
所谓旁观者清,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从他者眼光出发几乎是轻而易举地看到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和教会[1]。中国古代乡村地区幅员辽阔,且远离京城皇权中心,由于古代的交通、人力和财力的局限,国家的权力无法深入乡村生活,人们聚族而居,依靠血缘纽带的连接形成宗族,同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复杂的、适合族人的、稳定的伦理道德机制,这一机制维护了整个宗族秩序的稳定。在古老且不发达的社会中,人们依靠共同的宗教信仰、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来实现整个宗族的稳定和团结。同样,在古代中国,几千年的华夏文明铸造了一套完整的儒家伦理机制,延续了整个封建中国。其基础是家庭伦理、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等。那么,这样一种伦理的实现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平台作用于社会并达到实现社会团结的目的呢?在这里,家族和宗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宣传平台,宗族的不断延续,使得宗族之伦理基础也在不断传承。中国古人强调教化,强调以“先进”教化“后进”,教化之道在于“以德服人”。宗族也通过对成员的教化来实现稳定的机制,教化的内容包括儒家的伦理道德,也包括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宗族还设立特殊的仪式和制度来维持本宗族的正常秩序,对于违反宗族法规的人按不同程度给予惩罚和处分。这样,在皇权因交通等各种客观原因难以控制的地方,宗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宗族的首领、士绅们也比政府官员更了解当地实情,解决了很多基层纠纷,具有高度的权威,并作为国家基本制度的一些补充,地方官员也很乐意和宗族合作,共同控制乡村。秦朝极力反对宗法制度,设三十六郡,由中央直接管理,表面看是中央权力无比强化,但社会整体实质是一盘散沙[2]。
(二)国家政权与乡村控制
在封建皇权高度集中的古代中国,广大乡村实行完全的自治是不可能的。秦晖通过对吴简关于传统乡村治理的史料研究,得出了与上述截然不同的结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应说是皇权控制之下的编户齐民社会,至少中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是如此。所谓编户齐民,即规定凡政府控制的户口都必须按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情况等项目一一载入户籍。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称为“编户齐民”。上述已经探讨过宗族在传统中国乡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以乡村控制也绝不是仅仅被皇权包围,而是国家政权与宗族共同在乡村发挥作用。中国的广大乡村,绵延2000年之久直到20世纪上半叶国民党执政时期仍断断续续实行的社会控制制度即保甲制,这一制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但实质并无太大差异。“保甲”这一名词[3],首见于宋,保甲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甲制中有上下级之间的垂直控制,也有以株连方式强迫邻里之间互相监视。保甲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秦商鞅变法之连坐法,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劳力以上的都必须分居,独立编户。同时,按军事组织把全国吏民编制起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准擅自迁居,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家连坐。秦国统一六国后,秦汉乡村实行乡亭里制,到魏晋南北朝之时又出现了“三长制”,隋唐时期,又有“邻保”之制度,其基本内容大同小异。宋朝以后,无论国家政权怎样变更,保甲制作为中央集权控制乡村的基本制度一直得以延存,而且也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制度。抗战期间,在华北沦陷区“治安强化运动”中也曾经广泛实行。1932年8月蒋介石颁布《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后,正式开始在豫鄂皖三省红军革命根据地周围地区施行。
放眼整个中国的基层控制方式的变迁,宗族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中央政权想要越过宗族实现基层直接控制,会受到交通不便、行政效率低下等因素的限制,统治者这种主观的愿望不切实际,需要仰仗宗族这一牢固的乡土社会组织建立团结稳定的中国乡村。同时,统治者也会考虑到宗族势力过大会威胁统治的问题,所以宗族和国家政权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平衡好二者关系才能实现稳定发展。
二、近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失衡,礼与法的重新整合
中国古代社会,从整体上来看,对于礼治的推崇大过法治。中国传统乡村,依血缘而居,费孝通先生口中的熟人社会[4],礼治较之法治对于乡土性浓重的村民来说更容易接受,更有人情味。但随着封建王朝的停滞不前,孤立封闭的格局终将要被打破,实质上,从宋朝以后,中国逐渐失去世界中心的地位,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并逐渐升级,到清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资本扩张、寻求市场和财富的驱使下,纷纷踏波东来。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就不得不重视正式组织控制和法的应用,这是社会变迁的必然趋势。
(一)清末民初传统宗族社会失衡
1840年以来,西方的入侵打乱了中国的社会进程,打破了皇权—宗族绅权二元超稳定的乡村控制结构,乡村控制开始失衡,传统乡村发生变化: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连续爆发了川楚白莲教等几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尤其在太平天国运动严重打击下,清朝正规的国家编制军队——八旗、绿营相继溃败。清政府深感无力,不得不允许地方操办团练来镇压农民起义。团练虽然是在保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同样是军事组织,但他们二者还是存在很大区别。保长、甲长一般是皇权任命,但团练的控制权却掌握在士绅手中,因为国家财政无法负担平叛起义所需要的资金,只有依靠地方乡绅的权威。因此,太平天国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各地方团练等武装力量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继续存在。作为乡村社会权威的保障[5],在团练举办的过程中,初期由传统士绅主事,负责组织指挥等事宜,但后期一些豪民捐资也加入到团练中来,与士绅阶层逐渐融合互相演化,重新整合士绅力量,形成了以恶霸豪绅化为特征的新乡村权威群体。“土豪劣绅”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随着个人势力的扩张,加剧了社会动荡,又出现了匪乱和秘密组织,民国初年尤为猖獗。为控制这种现象,晚清政府及民国初年都在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利延伸至乡村,除了掠夺农村资源,还使农村与中央保持一致。
这种变化所导致的结果也非常明显。首先,农村从立国之本的地位上逐渐滑落。古代中国,农业是经济命脉,小农经济在我国持续了2000多年。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军工、商业、教育、科技传入中国,洋务派打出自强、求富的旗号兴办新式工商业、学堂,这大大改变了国人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农村人逐渐向城市聚集,农村资源逐渐向城市转移,熟人社会慢慢被陌生人社会取代,礼的控制无法再像从前那样起作用,人们对法的依赖加深。其次,造成绅权势力增长,国家政权下沉,绅自小受到儒家文化熏陶有着较强的责任心和功名感,为了自保身家,积极操办团练,即使在起义平叛以后,乡绅同样拥有财权和军队,其结果就使得地方武装势力渐强,非官方的乡村控制系统逐步占据优势地位,乡村社会结构进一步失衡,国家政权建设加强,行政控制逐渐吞并了宗法政治,并占据统治地位。
(二)共产党的组织控制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领导乡村社会整合,有组织地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促进了乡村社会结构的优化[6],促进了乡村现代性因素的发育和成长,改变了自清末以来乡村社会的混乱状态,为革命根据地建设及中国乡村社会控制方式提供了一条新的有益的途径。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解决农民问题关键在于解决土地问题。《兴国土地法》的颁布,确立了土地改革的路线。在土地革命之余,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了民主政权建设。但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了千年之久,农民不知民主为何物,对于民主选举、民主参政起初参与度不是很高,但共产党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调动了农民的参与热情,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了普及。尤其是1940年3月中共中央建立“三三制”,逐渐在乡村树立了民主的意识观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改变了乡村的传统格局。
共产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乡村混乱的状态,最主要的原因是共产党具有超强的组织化功能和极具渗透力的垂直的组织系统,使共产党能够坚持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将一盘散沙凝结成一个坚固的整体,将农民与城市联系起来,将传统乡村带入现代化的组织结构之中。首先,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很多政权建设问题内化为党的组织问题,避免了封建旧王朝统治带来的各种资源的消耗;其次,除了垂直领导,还有横向组织建设,以群众组织为基础,包括农抗会、妇女联会、儿童团、民兵组织等。像中国农村这样一个缺乏组织观念的社会,近代中国中央政权下沉造成宗族乡绅的变化,农村逐渐走向“原子化”。中国共产党员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家国情怀,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组织结构相结合的产物。通过在乡村开展广泛、高度的政治动员,发展群众运动,在个人与国家之间成立中介组织,弥补农村宗族之后弥留的真空,新型的组织化结构给中国乡村带来了现代化,也渐渐形成自己的组织权威,是礼与法的高度结合,并以独特的形式运用于乡土中国,将复杂的社会控制问题处理得非常成功。
三、当今中国法治下乡的困境与控制方式的整合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只有将乡村处在“礼”与“法”的共同制约下,才能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乡村控制中的礼法二者,名虽对立,实可相通,这或许就是中庸,汉董仲舒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也实行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还有著名的“春秋决狱”,改变了以往依照客观情况“一刀切”的司法方式,对不同案件区别对待,体现了法律适用中的“礼法融合”[7],这就是中国社会控制所走过的道路,这也是中国传统与中国国情。
(一)法治下乡的困境
当今世界,开放的格局正推动着中国社会迎着现代化的潮流不断向前迈进,任何孤立、封闭、不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模式都将被摒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的转型和飞速发展,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国家,这些都需要我们尽快将法治纳入社会控制和社会治理的轨道。乡村地区是中国经济的腹地,是城市的依托,广大乡村也必然要追随时代潮流,坚持法治下乡。但自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开始,很多学者都表达过对法律进入乡村不同程度的担忧,现行的法律制度破坏了乡村原有的道德礼治,却没有起到预想的法治效果,它的贯彻和施行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引起了副作用,所以单单将法律条文、律师、法庭这些东西推向农村,并不能解决现有的问题。中国的乡村社会仍然是一个宗法、血缘、伦理主导的社会,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往往将情理、道义作为评判事实的准则,法律条文在他们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应用的依据。当前社会的发展,现代生活方式的快速转变,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希望能够让农民共享改革的成果。但强制的法治下乡,也犹如强拆农村农舍。现代生活、楼房交通对农民来说并不排斥,但要拆掉他们根深蒂固的道德、风俗和文化生活却不是我们的初衷。所以,如何更好地法治下乡、如何更好地对乡村实行社会控制成为了一个需要深思的现实问题。
(二)实现正式与非正式控制方式的整合
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我国也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传统乡村的控制方式必然要面临转型,重构乡村社会控制机制和体系,必须要考虑上述国情,坚持循序渐进,坚持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当前我国农村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村民委员会承担着社会责任和社会控制功能。村委会可以通过商讨制订和执行符合村社民情的村规民约,指导和规范村民的行为,限制和处罚不正当的行为。也可以通过社会舆论的作用,限制和约束村民的行为,开展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制止一些不良行为。针对村民的思想动向,可以进行宣传教育,使村民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这是在新的形势下社会控制方式变迁的结果。将正式组织控制和道德、风俗等控制方式结合起来,避免生硬的灌输法律规范,通过较为民主的方式,维护社会公德,维护社会秩序,遵循中国传统。由此,我非常赞同张沛在《中国:传统与变迁》译后记里的概括“变迁是传统的前景,前景是变迁的归宿”,社会事实的变迁无法不保留传统的因素,也无法完全脱离传统的影响,除了正式的基层政权组织机构之外,同时可以科学培育和建立各种民间组织机构,发挥他们的组织协调功能,利用好中介、宗教等组织,更好地实现乡村的社会控制。
农村是现代化发展的缩影,人们财富的不均也带来不同群里利益诉求不同,社会阶层出现分化,乡村人情冷漠,宗族伦理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新旧三农问题使乡村社会控制难上加难。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加强法制观念、普及法律措施,同时要立足国情,综合传统与现代的因素,用多元的思维、多元的手段进行乡村的社会控制,以史为鉴,立足现实,我们是能开辟出一条中国式的乡村社会控制制度之路的。
[1]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3-30.
[2]黄金兰.民间法:第12卷[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150-160.
[3]钟年.中国乡村社会控制的变迁[J].社会学研究, 1994(3):92-93.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35.
[5]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以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为背景[J].法学家,2010(6):113-127.
[6]蔡清伟.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研究(1949—2013)[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4:27-29.
[7]王露路.伦理视角下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礼”与“法”[J].中国社会科学,2015(7):94-103.
(责任编辑:蒋玉莲)
C912
A
1008-5254(2016)06-073-04
2016-06-26
梁永郭(1962-),男,河北唐山人,博士,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吕传旭(1992-),女,天津人,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