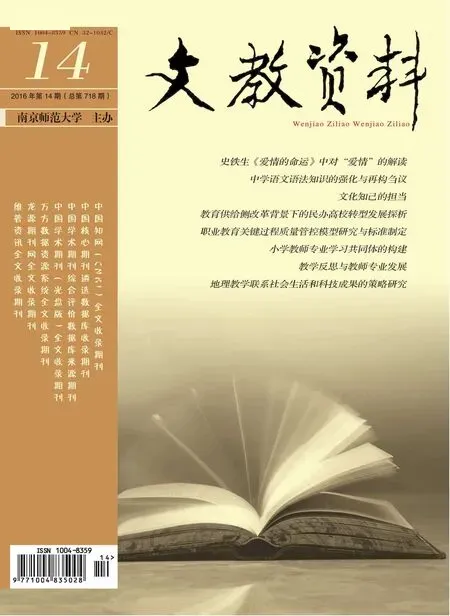从审美功利主义看宗白华谈《世说新语》
张悦欢
(华南师范大学 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006)
从审美功利主义看宗白华谈《世说新语》
张悦欢
(华南师范大学 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006)
“审美功利主义”思想是中国20世纪前半期多数美学家的一种共同美学倾向。既不同于西方现代审美主义,又区别于中国古代政治或道德功利主义文艺观。宗白华的美学亦不例外。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中,宗白华试图以中西哲学、文学资源构建新的思想文化,在浮躁沉闷的社会环境中启蒙人民构筑艺术的人生观,发挥文学、美学对人心与人格的积极作用。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一文充分展现了魏晋文人崇尚个性、立意反抗、向往自由的生命形象,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构建价值理想与生命形象的清晰的参照体系,从魏晋美学与人的生存发展关系阐释中渗透了他的审美功利主义思想。
审美功利主义 宗白华 晋人之美 中国现代美学
一、何为审美功利主义
在阐释“审美功利主义”的基本内涵时,有学者提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国人进行现代启蒙的强烈意向,加上西方现代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的碰撞、融合,铸就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这种追求审美和艺术的‘无用之用’的重要思想——‘审美功利主义’。”
此处应该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启蒙”,一是“融合”。“启蒙”一词的关键在于,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界它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启蒙与救亡”,不可否认,是中国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的主题。那么,“启蒙”与“救亡”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应该说,启蒙应该是更基础的,唯有在思想上真实地觉悟,才有可能实现救亡这一伟大理想,从而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这种从“启蒙”到“救亡”的爱国实践思路,按林毓生的说法,可以概括为一种“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种强调必须先进行思想和文化改造然后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研究问题的基本设定”。第二个关键词,是“融合”,这种美学倾向能够在20世纪的人文思想中占据一席之地,哺育它的中国本土文化,是不可忽视的。而在这片肥沃的传统文化土壤上,有另一种被称为“政治(道德)功利主义”美学传统值得了解,因为审美功利主义,是在批判它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
二、审美功利主义的基本内涵
实际上是扎根中国本土,在批判继承与学习中西文化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解决当时历史语境下的具体问题的。除了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之外,宗白华的学术生命中的审美功利主义色彩十分浓郁。
1941年,宗白华撰写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从八个方面呈现了魏晋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特性,宗先生写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嵇康的《广陵散》,同时也写晋人的艺术境界、晋人的道德观与礼法观,写人格唯美主义;魏晋的艺术精神固然值得欣赏,但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才是宗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核心。晋人的“艺术心灵”是追求精神解放,追求自由的心灵,不受世俗的羁绊、不受物质欲望的奴役,具有高远的意趣。他在文章中强调的“晋人的艺术心灵”与“美的意境”之间不可割裂的关系,都是为鼓励四十年代艰苦的中华大众,“从中国过去一个同样混乱、同样黑暗的时代中,了解人们如何追求光明,追寻美,以救济和建立他们的精神生活,化苦闷而为创造,培养壮阔的精神人格”,亦即实现救亡和启蒙的双重目的。
宗白华借谈晋人之美,为世人树立了一个不滞于物、反抗虚伪礼教的人格标本,这表现了他对个体的人格精神的关注,表达了他对精神自由的渴望。魏晋时代,一方面是腐朽黑暗的社会统治,另一方面是文人知识分子愈来愈强烈的自我觉醒和个性张扬。
全文都是从艺术的角度看人格,这就贯彻了宗白华一直奉行的艺术的人生态度。他希望,用审美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用艺术创造和整饬人生;他希望,人人都能有唯美的人生态度。而在文中,唯美的人生态度可表现于两点:
一是把玩“现在”,在刹那的现量的生活里求极量的丰富和充实,不为将来或过去而放弃现在价值的体味和创造。
这里的“价值”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宗白华举了王子猷令下人于暂住的空宅处种竹一事,说明王子猷对眼前生活品质与审美的重视。
二则美的价值是寄于过程的本身,不在于外在的目的,所谓“无所为而为”的态度。
这里依然援用王子猷的例子,夜雪忽忆戴安道,造门不前而返。魏晋时人将事情的目的性减到最低,甚至是无目的而目的,尽兴于过程,不可谓不美也。
除了树立个性的人格标本,表现晋人唯美的生活态度之外,宗白华还认为晋人之美,美在他们对自然、对探求真理、对于友谊的一往情深。
综上所述,宗白华从晋人的人格精神、唯美的生存态度及山水所蕴含的人性美等方面讨论了晋人之美。他指出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发现自然山水之灵可以寄托艺术化的心灵,发现自己则是个性的自觉和精神的自由;艺术化的心灵和精神的自由可以铸造刚健活泼的人格范型,这正是抗战时代中华民族的所需。时代精神的诉求,使得宗白华格外突出了一笔,显现了晋人人格光洁明亮的一面,从而和无惮的放纵区别开来。
孔融、嵇康、阮籍等,皆是狂狷之士,反抗庸俗的乡愿社会,反抗桎梏性灵的礼法。宗白华在这段论述中,将魏晋一代的狂狷之士的原型上溯到孔子本身,使得我们有了重新认识儒学道德真含义的机会。二十世纪前半段,人们对儒学既熟悉又陌生,人们对孔子无法摆脱却又无所适从,宗白华通过发掘了魏晋风度,重新解读儒家经典,而非仅仅将魏晋思想的解放一味归结为道学的发扬,这种清醒的学术观念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他也为时代个性精神的解放寻到传统的因子,这种关于魏晋人士的生命情调的创见有着极强的时代意义。
救亡图存与启蒙交织在一起的时代特征,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反照在宗白华身上,没有纯粹的美学思想,单纯埋首学问亦过分奢侈。时代应该流行和自我修养,建设新的国家,培育新的人格等终极目标缠绕在一起的文化。审美功利主义,是宗白华学术研究的分离不了的影子。
三、审美功利主义的初衷是好的
自“五四”时代,文化道德随着政治秩序的危机而处于断裂崩溃之中,因而创造新的文化传统,成了爱国心切知识分子的共识,中西结合、分析比较也成为一时之盛事。
同时,宗白华在文章中显露的局限性是明显的。有学者在评论《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时提出,严密的逻辑结构,推理过程运用史料,是宗白华在文章中相对忽略的部分。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两方面造成的。一是与宗白华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弥漫的审美功利主义情结有关,过于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现实作用,容易出现不客观的忽略历史事实的价值判断。如对桓温、王子猷的过分赞扬即是一例。二是宗白华的学术历程,既受到叔本华、尼采和狄尔泰思想影响,又深深浸润于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因此,他在把握美的现象时特别注重亲身感受,在论说美学的相关问题、表述其思想观念或阐释结论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严谨的逻辑。所以,他的美学论文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诗性的风格,没有明确的结论,没有三步走的论据论述,没有层次分明的推理论辩,没有严格的概念阐明。其核心内蕴常常是隐含在字里行间,要求读者细心琢磨、凝神体会。
当然,对于文学艺术,一直都有两种倾向:一是求“美”,二是求“真”。从求“美”的角度看,宗白华应是一座醒目的里程碑,但从求“真”的角度,他又确有不足。文史结合的求“真”之路,如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年代学,陈寅恪先生善于从常见书中抉发内蕴的史料运用的方法,岑仲勉先生对唐代史料的精密把握,等等,也是自成一路。七十年代末,以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一书出版为标志,国内唐代文学研究风气丕变,从一般的作家、作品研究,转向以实证为基础的多方位综合研究。可以说,现在的文学艺术研究,更注重与历史结合的严密逻辑的求“真”的研究方法。
求“真”与求“美”,在此刻对宗白华先生的研究并不是重点。从他对魏晋美学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典的意义只有在研究者的深沉的人文忧患意识激活中才能重获生命力,虽然对于古典文化的研究,文献学的知识、史料的准确度非常重要,但它若不能与文化的创新与学者的品格相融合,则只能仅止于工具的层面之上。一个成功的学者,应是能在自身与古人的对话与问道中,获得知识与心智的双重启发,使自己的学术思想获得新的价值,并把这种价值传递给更多的后来者。
而宗白华先生,做到了。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3]宗白华.宗白华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4]杜卫.审美功利主义——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