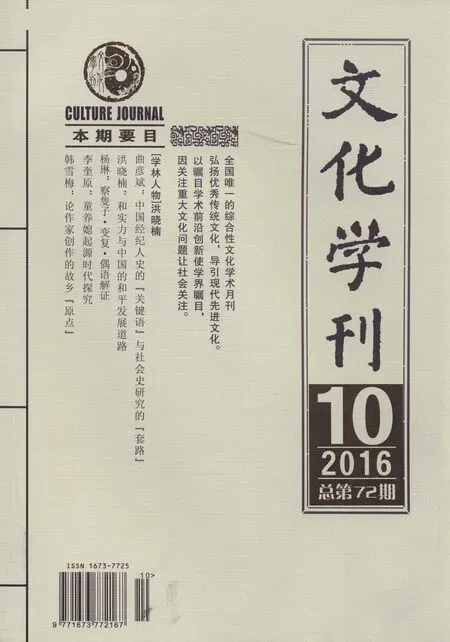论作家创作的故乡“原点”
韩雪梅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文学评论】
论作家创作的故乡“原点”
韩雪梅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对于优秀的作家来讲,生活中的地域性能够成为一种源头意义的精神力量,作家创作的故乡“原点”存在一个难以割舍的精神气场。故乡对于作家的浸润就像一块永久的文化胎记,化作文学作品的精神血脉决定着作品的生命力,之于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追求,已经构成特定的精神符号和艺术喻体,在文学的天堂中实现生命与思想的双重圆满。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乡愁记忆的古老村庄正在悄然消失,失去精神领地的作家,今后还依靠什么来创造自己独特的“文学王国”。
作家故乡;精神“原点”;文化胎记;作品生命力
弗罗斯特认为:“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1]这充分说明,人与地域两者间的特殊文化关系,对于一个人的个性形成和塑造,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围绕弗罗斯特的地域观点,可以这样解释,对于一名优秀的作家来讲,自身生活中的地域性,能够成为一种源头意义的精神力量。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遗忘他的故乡和他“成长地”的深情印记。进而,这种印记对于作家尤其是杰出的作家来讲,则更为饱满,更加浓烈。在作家的笔下,地域性不仅是单一的区间和空间的属性概念,而是他们精神和思想中独特的文化资源,是他们作品世界中灵魂与血脉的储藏器和流量图,是杰出作家与现实世界、与社会生活多维对话时的宿命意义的神情选择和诗学必然。无疑,具有宿命意义的地域性,的确成为与思想文字建立起来的一种精神归属的方式和表现生活的自主途径,似乎是文学世界中作家“群”的情感秘密、言说境界与命运寄托,正如贾平凹所说,“命运决定了我们是这样的文学品种。”[2]
贾平凹出生于陕西商洛的棣花镇。19岁那年,他从商洛的“老宅”出发,22岁开始发表作品,建筑起他长达四十三年的文学世界,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等奖项。我们仔细看看,贾平凹发表的千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中,故乡商洛的痕迹如影相随。换言之,他从写作的那时起,虽然离开了商洛,但他将故乡看作文学之旅的生命根基和精神选择,从未忘却和遗失归乡之路。长篇小说《商州三录》《山地笔记》《浮躁》《高老庄》《废都》《怀念狼》,还有近年发表的《高兴》《秦腔》《古炉》《带灯》《老生》,也包括出版的《极花》,这些长篇巨作,商洛的痕迹如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一样,“凤楼常近日,鹤梦不离云”。除此之外,贾平凹四十多年还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以及多篇散文,可以说,基本上都可以作为商洛中的平凹文学。
“我是商洛的一棵草木,一块石头,一只鸟,一只兔,一个红薯,是商洛的品种,是商洛制造。”[3]很明显,贾平凹以商洛为大本营和出发点,饱含着生命的全部体验,始终站在商洛的观察点上,了解陕西、观察中国、展望世界、感知人生,以文学的方式出发“小商洛”,回返大本营。可以确认的是,他的每一次出发与回返,故乡给予这位大作家的,绝非简单的当年零星的历史记忆,也不是一种文学创作中叙述艺术化的技术背景,而是“商洛因子”带来的生命体悟和流动在作品深处的那一颗颗包浆的灵魂。千百万字的文学作品里,人物、故事、情景、形态、语言、乃至叙述方式,都带有八百里秦腔的独特韵律,与读者的心灵实现文学乃人学的升华式撞击,进而,在他的可持续的叙述中给人们以生活的希望和超越现实与挫折的可能性。阅读贾平凹小说,一定会有这样的发现,翻看《高兴》时,得知生活中有真实的“刘高兴”,《带灯》 中会有真实的“带灯”,《极花》的胡蝶在现实中竟然也有原型。到底是故乡人物的“原型”给予作家的创作神力,还是贾平凹本身就是商洛的一个“原型”,我感到,这是在文学的世界中,一位杰出作家骨子里本能的人生把握和创作灵感的双重神奇,是整合时代记忆、诠释人心世界、创造崭新生活的社会文化变化的“结构”途径与思索。
谈到作家与故乡的“原点”关系,苏童有一段论述:“从地理意义上说,这个世界给予作家形形色色的礼物,体积不同,包装不同,但打开来看箱底,通常就是一个城市,一个村庄,或者仅仅一条街道,一片屋檐。我珍惜这件陈旧而贵重的礼物,我一直孜孜不倦地经营香椿树街小说,我期望这条街道可以汲取神奇的力量。我固守香椿树街,因为我相信,只要努力,可以把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搬到这条街上来。”[4]苏童想把整个人类搬到“香椿树街”上来,这可是真的,他为此“搬”了33年。苏童出生在苏州,在一条典型的江南小街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直到去北师大读书才离开这条小街。有人说香椿树街是作家想象的,也有人说香椿树街就是苏童真实的故乡。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香椿树街早已成为苏童故乡的标签。苏童的创作起于1983年,从那时开始,其作品中到处都有香椿树街的旧梦记忆:《骑兵》《白雪猪头》《城北的桥》《哭泣的耳朵》《城北的桥》《三棵树》《露天电影》《南方的堕落》《刺青时代》《人民的鱼》《黄雀记》等。无论自身的创作风格“标签”如何变化,但是,故乡的标签始终没有变化,还是那条阴郁的、悠长而寂寥的苏州小巷,还是一群在香椿树街上晃晃悠悠、来回奔跑的少年。只不过,在他们身上,苏童挖掘出生活的本真,透视着社会的变化,聚焦人物的灵魂。发表于2013年的长篇小说《黄雀记》,是苏童香椿树街系列的重要一部,也是苏童故乡的地标之作。小说写出了青春的残酷无情、市井的众生百态和幽暗氤氲的社会气息,让忏悔与反省在“人类”、在民族安静下来时,解剖动荡的灵魂。2015年8月,《黄雀记》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苏童说,“香椿树街”我是要写一辈子的,那里是我生命的原点。
黑龙江漠河县的北极村,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处在寒冷状态,数九隆冬温度下降至零下四十度。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最渴望的就是温暖。生长在北极村的迟子建,她的作品为什么总是给人以暖情,如同严寒中送来的一团“炭火”,这就与故乡北极村的严寒有关,与她内心的温暖有关,与作家看待世界和宽以待人紧密相联。“她的小说总有一种非常宜人的体温,如果说迟子建是敏感的,那她对于外部世界的隔膜和疑惑进入小说之后很神奇地转换为宽容,宽容使她对生活本身充满敬意,她的手从来都是摊开着,喜悦地接受着雨露阳光。”[5]1983年,迟子建凭借《北极村童话》登上文坛后,便以北极村为原点,一路走来,秉持关注生命冷暖的叙述主题,行之以人性信仰的温暖修度。故乡极寒的天气和村民的质朴善良,给予迟子建太多的体验、滋养和哲学意义的精神支持,她三次摘取鲁迅文学奖,一次获得冰心散文奖,一次获得庄重文文学奖。《额尔古纳河右岸》荣获茅盾文学奖。我们阅读其作品,总能感受到一种“人间温暖大使”般坚毅又美好的力量。因为,文学地理学的本原精髓和真正意义就在于,地域越是独到的,就越渴望观察到全局的深刻;天气越是奇寒的,就越期盼体验人间的温暖。无疑,迟子建是一位优秀的作家,立足北极村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信仰体系,持久地温化自己,柔软他人,痴情地守望和点燃人文关怀的生命光芒。
文学评论家张学昕教授认为:“一个作家的写作是有一个‘原点’的,这个原点决定着他想象的半径,而他们不同于常人的‘异秉’,则使他们对历史或现实可能获得重要的精神解码。在他们写作的精神起源和物质‘原型’之间,存在一个无法分割的精神气场”[6]。可见,作家与“故乡地域”确实有着特殊神秘的复杂关联性。更深入地说,故乡之于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追求,已经构成了特定的精神符号和艺术喻体。福克纳有句名言,“我的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是值得好好描写的,我即使写一辈子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在福克纳的笔下,一个像邮票大小的名叫“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故乡,他辛勤耕耘了一生,把故乡的土地、河流和人物都写进作品,福克纳创建了一个既属于他自己、又属于全世界的“文学王国”。故乡已化作杰出作家的艺术根系,是他们运用民族文化进行思维的牢固创作方式,无论作家以何种方式在何地进行写作,他们随身携带的唯一“行李”,就是可供他们永远开采的总也写不尽的故乡。无论作家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他们的创作,都会回到故乡的“原点”,用深情的文字逼近故乡,一次次抵达,再一次次重构,最终叶落归根,在多彩的文学天堂中实现生命与思想的双重“圆满”。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故乡对于作家的影响与浸润就像一块永久的文化胎记,化作文学作品的精神血脉,血脉的畅通与血液的浓度决定着作品的生命力。有了这块作家开采不竭的文化资源,作家就有了属于他自己的“领地”,有了这块宝贵的领地,作家就有可能成为占山为王的文学“王者”。然而,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历史阶段,时代发生着巨变,日新月异的震荡,人们生活的空间在无限地扩大,农村城镇化、城市乡村化、全球一体化,“故乡”的地域特征正严重弱化,基本上已不分南北、不分东西了。地域的同质化让人们吃着相同的垃圾快餐,每天拥挤相同的地铁,乡愁与乡音的古老村庄在中国每天都悄然消失。四处飘荡的人们,还能找到他们的故乡吗?杰出的“福克纳们”,那块邮票大小的领地还能完好地存在吗?失去了精神领地的作家,今后还依靠什么来创造独特的文学王国,这确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1]张学昕.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8.
[2]贾平凹.命运决定了我们是这样的文学品种[J].中外文化交流.2014.94.
[3]贾平凹.《老生》曾三次中断难以为继[N].人民日报.2014-12-02(24).
[4]苏童.我一直在香椿树街上[J].长篇小说选刊.2013,(6):98.
[5]苏童.关于迟子建[J].当代作家评论.2005,(1):56.
[6]张学昕.永远的商洛:平凹写作的“原点”[N].文汇读书周报.2016-03-07(5).
【责任编辑:周 丹】
I206
A
1673-7725(2016)10-0059-03
2016-08-10
韩雪梅(1987-),女,辽宁沈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