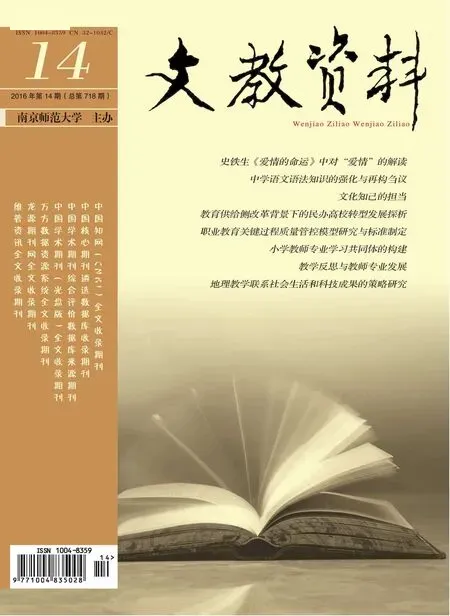《推销员之死》中的男性主体形象塑造
陆海霞
(重庆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2160)
《推销员之死》中的男性主体形象塑造
陆海霞
(重庆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2160)
剧作家阿瑟·米勒是二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三大剧作家之一,其佳作《推销员之死》于1949年面世,被认为是现代美国戏剧的精髓。剧本毫无例外地以男性角色为中心,是一个表现男性世界的文本。在对男性形象塑造的同时,深深打上了父权意识的烙印。他们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主体”,是父权意识的固化者,是历史创造的参与者和男性至上主义的厉行者。
《推销员之死》 男性 主体 形象塑造 父权意识
一、引言
《推销员之死》于1949年面世,被认为是现代美国戏剧的精髓。剧本以推销员威利·洛曼为中心而展开,威利一直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销售员,并希望两个儿子也能成为伟大的人,但梦想全都破灭,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在困境中难以自拔,最终以自杀而结局。作品问世以来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的学者们对其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和解读,其中不乏对其的女性主义研究。但是,在对《推销员之死》的女性主义研究中,主要局限在对剧中女性形象单方面的探讨,却较少有把目光直接投向男性形象的。然而在性别研究中,男性个体在内化父权意识时所受到的压抑和扭曲同样值得关注。本文拟将以父权意识为切入点,以洛曼家的男人为线索,讨论男性是如何被塑造成主体形象的,揭示父权文化对男性性别形象的操纵,男性形象同样也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
父权文化为了维护男性主体的中心地位,致力建构和规训了相应的男女性别形象,无论男性或女性人物,都是在父权意识下被塑造和建构出来的。男人一直被刻画成权威、尊严、力量为标志的主体角色,父权意识在贬低女性的同时,也建构了男性的“男性气质”和主体形象。《推》中的男性角色是按照父权文化规训和建构的男性形象,他们是父权意识的固化者,是历史创造的参与者,是男性至上主义的厉行者。
二、父权意识的固化者
传统的父权价值标准塑造和建构了女性弱者的形象,同时它告诉我们男人天生是强者的形象,强者形象保证了男人的绝对权威。因此,男性按照父权的标准塑造了自我,天经地义地扮演着强者的角色。威利正是按照父权标准要求和衡量自己,父权意识在他身上得到了固化,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对父权的维护和男性气质的崇拜和追求上。
在父权社会中,一般来说,男性气质是指男性自治、男性支配和家庭中男性独立于女性的控制。身为丈夫/父亲的男人最重要的就他得是一个家庭的供养者。这个身份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能否给家里提供物质供给。这在40年代的美国尤为重要,因为当时的大部分的美国妇女已经被重新限制在家中。这样角色分配决定男性处于中心的主体地位,统治着女性的物质和精神世界。为了维护其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他一是谎称借来的钱是自己的工作所得,二是拒绝别人的帮助。当查利在跟他打牌时提及要给他找个差事的时候,他大发雷霆地要赶走查利,并侮辱性地还击查利说:“不会用家伙干活的人不是男子汉。你叫人恶心。”[1]33可见,查利的好意却触及了威利内心最在意的伤痛,他通过对查利的贬低维护自己的男子气质。传统对性别角色的要求强调丈夫/父亲的家庭经济支柱和保护者的身份。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男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养家糊口,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担任家庭的支柱和具备男子气质是父权社会作为一个强者男人的必备的条件。因此,他一直力图为家里提供各种开销,在他葬礼那天,最后一笔按揭款的付清也证实了他作为一个家庭供养者的功绩。
通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威利被刻画成一个有事业心、进取心、并且一直怀揣着伟大梦想的人。一方面,他梦想自己能通过推销员的工作闯出一条成功的道路,另一方面,他对儿子,尤其是大儿子比夫寄予厚望,并希望他能成为响当当的人物。作为一个父亲,威利努力在儿子面前树立男子气概的模范形象。为此,在儿子们小的时候,他受到了无限的崇拜。在儿子们少年的时候,威利就注重对他们进行男子气质的训练,他总是满怀热情地给孩子们训练功课、运动。这样的训练是对儿子们的男性价值观的培养的一种重要途径。父亲总是希望儿子能够承袭自己的事业,威利希望比夫能够回来接替自己推销员的事业。最初,威利在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靠自己的辛勤工作在布鲁克林区以按揭方式买了房子,置办了各种家当。他受到妻子的爱慕和尊敬,也受到儿子们的敬仰,是洛曼家的中心。但是现实并未像想象的那样美好,二战后,美国进入了所谓的“丰裕社会”,经济持续繁荣。一方面,人们拥有了更多财富,同时对财富和物质的追求也空前高涨,另一方面,生产力大大提高,产品呈现多样化,同时产品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加剧。这样的经济环境给推销员的挑战一步步加大,产品的推销越来越难,威利的收入随之降低,他推销的佣金由几百美元降低到几十美元。他的收入只勉强地维持家里的开支,有时候甚至一无所获,他只得向邻居查利借钱来维持生计。威利的理想与现实越来越远,他感到推销员的工作并不受尊重,自己也感觉到被人嘲笑,最后被无情的老板像“橘子皮”一样抛弃掉。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自我意识学说中说,自我意识产生于自身对自身的反思中,因而自身将作为对象连同一个外在的证明被看成是同一的[2]127。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永远需要或渴望他人证明它的存在。自我意识要想自为存在必须通过对象实现。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威利自我意识的实现和自我身份的认同需要一个他者的反映和证明得以实现。生存在夹缝中的小人物威利无法在与同性在社会竞争中找到有利、处于优势的位置,老板的儿子视他为废物,像“吃了橘子扔掉皮”一样的辞掉他,好朋友查利也事业有成,有自己的公司,是威利的债主,还多次主动给威利提供工作,这激怒了威利,因为在威利内心深处,他认为接受查利的工作就等于自我尊严的丧失,亦即是沦为查利的奴隶。
父权意识文化宣扬男性天生比女性优越,与同性竞争的失利,威利需要找到一个他物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于是他试图发现比自己更底层的人——女人,通过对她们的征服来获得慰藉,寻找心理弥补[3]。在外,他寻求“某妇人”就是作为慰藉的对象,在推销的途中他与“某妇人”发生了性关系。这正应验了凯特·米利特的话:在社会的下层,男性更多的是单凭自己的性别来宣称自己的权威[4]45。威利属于社会的中下层,换言之,他未能在与同性的竞争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和价值追求。而威利中心地位和存在的价值只能是从处于客体地位的女性那里得到体现。此事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事出有因。通过威利的回忆我们得知,在此之前,比夫在威利寄予厚望的的足球比赛中失利,并没有像威利希望和吹嘘的那样成为一年能挣两万五的体育明星。而且他该毕业的时候,数学考试不及格,这无疑给威利当头一棒。另外,1932年正处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1929年随着纽约股票市场的崩溃,美国陷入空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之中,所有美国人都被卷入到大萧条的梦魇中。威利的推销员工作无疑在整个大萧条中受到严重影响,其 “家庭的供养者”的地位和一家之主的尊严受到威胁。家庭和事业双重打击下,威利陷入极度的失落当中。于是他将“某妇人”作为转嫁痛苦的对象。威利仅仅是把她当成发泄的对象,把她作为自我身份认同的“他者”,以对她的征服寻求心理平衡,建构自己的男性气质。在家,他通过对妻子林达的绝对支配维护他的主体地位。当他在社会中找不到中心位置的时候,他只得在家中维护他的父权的权威。他盛气凌人的态度和暴躁的脾气在他年老的时候变得愈来愈明显。回到家中,他居于一个享受者和被侍奉者的角色,妻子林达对他百般依顺,他却视这一切为理所当然。威利视林达是从属的、微不足道的,并且忽略她的需求,这主要表现家庭的谈话中,在洛曼家男人的对话中,他从不允许林达插嘴,并多次怒斥和打断林达的说话。威利的暴戾态度流露了他对他父权的权威受到威胁的恐惧。而对妻子的女性气质的贬低帮助威利维护了他的男性性别身份认同感。在疲惫不堪回到家中的时候,他从林达那得到安慰,因此他说林达真是他的根基,他的依靠。在生意不好的时候,他觉得无比的寂寞,他担心再也养活不了林达,再也创不出什么事业能传给儿子。养活妻子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使他有某种成就感,同时,也使他在家中获得支配性的地位。他在社会中梦想追求失败和处于低下地位的失落,在妻子那里找到了一定的弥补,因为有女人被他养活着,他的优越感会油然而生,也从中找到些许存在的意义。
三、历史创造的参与者
伍尔夫说,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男人描写战争,女人描写生孩子,而在于每个性别都在表现自身”[5]395。阿瑟·米勒也不例外。其《推》首先在角色分派中便证实了这一点。在13个人物角色中,其中8人为男性,只有5人为女性,整个剧本中只有男性的心理描写,而且剧中所有事业的参与者几乎都是男性,而女性则被排斥在外,女性角色除了林达·洛曼有相对较多的性格刻画和出场机会外,其他4位女性几乎没有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推》作为美国戏剧的精髓,当然也毫不例外地以男性角色为中心、为视角出发展示20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人的经历。
剧本以二战后40年代末的美国为背景,并以威利的回忆展现了美国过去的历史。威利穿梭在过去与现在的思绪中展现的事情与美国历史年代结合起来,我们依稀可见洛曼家族的男人们与美国重要的历史事件的联系。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是美国向西部开拓疆土的运动时期,持续百年之久的西进运动,促进了美国西部的开发。一往无前的西部冒险和坚韧不拔的拓荒实践为美国人留下了不朽的开拓精神。老洛曼离开家时正是西进运动的末期,“他把一家子都装在大棚子车里,赶上一群拉车的牲口,在大草原上就闯了出去”[1]36,这正是西部拓荒时成千上万个美国家庭的真实写照。老洛曼带着家人,把美国西部都跑遍了,他具有开拓和冒险精神,他代表的是成千上万家庭中“一家之主”西部开拓者的形象。威利的哥哥本随后毅然去了非洲丛林挖掘钻石,并在四年后腰缠万贯地出来,19世纪末正是美国殖民者在非洲探险的高潮时期,本凭借自己的野心和冒险精神获得了财富,也实现了美国梦。本呈现的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形象。“他身体壮实,六十多岁,留着小胡子,一副颐指气使的神气”[1]33。更了不起的是他征服丛林的故事,他十七岁时一头扎进非洲丛林,二十一岁出来时便发了大财。丛林象征着险恶重重商业世界,威利正处在这世界中,为生计奔波,为梦想追逐。威利从1913年开始他的推销员工作,此时正处于美国经济开始繁荣和腾飞的开端,一战后美国更是一跃成为世界商业和金融中心。征战的男人们由西部荒原和非洲丛林转战到了商界,美国社会需要的也不再是拓荒者和殖民探险者而是像威利这样的推销员。他们在商界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梦想,有的人成了商业巨头,如威利的老板霍华德、朋友查理,有的人一生为此而奋斗,如威利。而到了在戏剧故事发生的1949年的美国,拥有自己的事业便成了评判一个男人成功的标准。
父权社会的文化传统把男性塑造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而女性则充当工具和附庸。男子是世界的主人,是家庭的主宰,世界是男人的世界。男人自幼就被置于父权文化的中心位置[6]。洛曼家族三个家庭中的男人都是美国历史创造的参与者和美国梦的追逐者,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领域罢了。这些荒原开拓、殖民探险和商界征战都是专属于男人的事业,征服自然和世界的历史使命显然只是男人的专利,也是男性主体世界所肯定和赞赏的。占据了注意力中心的男性作家从自身立场和视角出发,抒写着男性中心的文本,更加进一步巩固了父权思想意识。
四、男性至上主义的厉行者
男性至上主义,又称男性沙文主义或大男子主义,即男尊女卑,是一种认为男性必定优于女性的理念。剧中洛曼家的男人是这种理念的厉行者。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女人只是他们手中的玩物和征服的对象。从他们对好、坏女人的定义到对关于女人的谈论中,处处流溢着男性至上、男性中心和对女性的歧视、贬低的大男子主义。他们对女性及女性气质的偏见和贬低实际上是对自我主体形象的建构。
美国心理学家霍妮认为,男性气质是通过贬损女性气质建构的。男性往往通过对女性的贬损而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并获得自尊的满足感和优越感。对于女性的占有一直以来都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男性地位和价值的体现。《推》中也充斥着这样的观念,主要通过洛曼家的男人们对好/坏女人的定义和关于女人的谈论中体现出来的。男人把性经历作为谈资,把女性身体作为他们权力的对象,借此寻求心理平衡,建构自己的霸权性男性气质[7]。在第一幕的开始,比夫刚从外地回到家中,重逢的兄弟两躺在卧室的床上谈论起他们玩弄过的女人来。他们的言语和笑声中充满了对女性的轻视和贬嗤。
哈皮:记得那个大个子,贝西什么的——妈的,她姓什么来着?
……
哈皮:家伙,那位可真是个不挑不拣的好货!
……
哈皮:你就说今晚咱们玩的那两个娘们吧,够漂亮的吧?……这样的,我什么时候想要都有,比夫,每当我玩腻的时候都行[1]12-16。
兄弟俩的谈话在不经意间暴露了他们男性中心主义和女性当下的生存真实。在男性看来,作为他者的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即是物,在洛曼兄弟眼中这些女人都是下贱的,是不值得尊重的。她们只不过是满足他们欲望的尤物。哈皮把对女人的玩弄作为他炫耀的资本,女人是他证明他是男性气质的媒介物。一方面,哈皮需要这些女人满足他的欲望和证明他作为男人的存在。哈皮在家中并没有像哥哥一样受到父权威利的看重和追捧,在工作中也并未能与同类的男人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其失落感可想而知,于是他将精力投向对女人的征服,从中寻找弥补。另一方面,哈皮对女人持有浓厚的歧视感,他把她们当成随意征服的猎物和发泄的工具,并对她们百般鄙夷,认为她们都不是“好女人”。
洛曼兄弟多次一起谈论着他们玩弄过的女人。在父权社会中,男性拥有性知识和言说的特权,对性的谈论是一种男权意识和男性气质的体现。男性把女性身体作为他们权力的对象,以此寻求心理平衡,建构自己的男性气质。在表示满足和荣耀的同时,哈皮对他所玩弄的女人的鄙夷是毫不掩饰。他把她们称为“货”,无论什么时候想要都有,认为她们是招手就来的妓女。在谈到他的人生志向的时候,哈皮列出了一个单子: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子和好些个女人。可见,他已经完全将女性置于一个物品的位置。虽然她们满足了他的欲望,证明了他的男性气概,可他并不想要她们,因为他觉得她们都不是“好女人”。所以他告诉比夫,他想找个“好女孩”结婚,“找一个格高尚的,经得住考验的!像妈妈那样的人”[1]17。很显然,在男人的眼中,女人,除了自己的母亲之外,都是不贞洁的、不道德的。他唾弃这些不安于家庭生活的“道德败坏”的女人,而想要一个跟林达一样的“家里的天使”。哈皮的言语和行为无疑代表了父权社会中所有男性对违背父权规范的女性的态度。
在所有洛曼家的男人之间的关于女人的谈话中,都体现了他们的对女性的歧视。而被谈论的对象——“女人”——都是不在场的。她们的“缺席”使她们失去了申辩的话语权。剧作家把叙述的权利交给了洛曼家的男人们,通过他们的言语折射了父权意识下男性对女性的价值判断。长期以来,女性习惯于在男性的价值判断中建构自我形象。这样女性配合男性的价值判断,自觉内化男性中心的价值观。正如哈皮在谈论中所说的那样:“大概得有五百个女人都特别想知道咱们在这屋里说了些什么。”[1]12这明显传达一个信息:女人们都想知道自己在男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以此为标准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博得男人的欢心。正如“女为悦己者容”一样。在这场谈论中,由于“女人”的缺席,她们无法为自己申辩,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成为男性审美的对象和满足男人需求的物品。在《推》这样一部以主要反映男性精神为话语内容的文本中,虽然对女性的刻画极少,但剧中男性角色的行为和言语中却无时、无处不在地折射出男性至上主义对女性的价值评判。
五.结语
父权文化对“男性主体”地位的建构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遍及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并且被男性集体内化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其实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女人不是生来的就为女人,而是社会文化创造出来的,同样,男人并非天生就是男人,是社会赋予他男性角色的义务。阿瑟·米勒的《推》也未跳出父权文化传统的刻板模式,其中的男性形象是在父权意识下被塑造和建构出来的,也深深地打下了父权意识的烙印。
[1]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M].英若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Callow,Heather.Masculine and Feminine in Death of a Salesman[A].In Stephen Marino(ed.).The Salesman Has a Birthday[C].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0:65-78.
[4]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5]玛丽·伊格尔顿,著.胡敏,等,译.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6]Balakian,Janet.Beyond the Male Locker Room:Death of a Salesman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A].In Approaches to Teaching Miller's Death of a Salesman,1995:116-122.
[7]邱枫.男性气质与性别政治——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家庭制造》[J].外国文学,2007(01):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