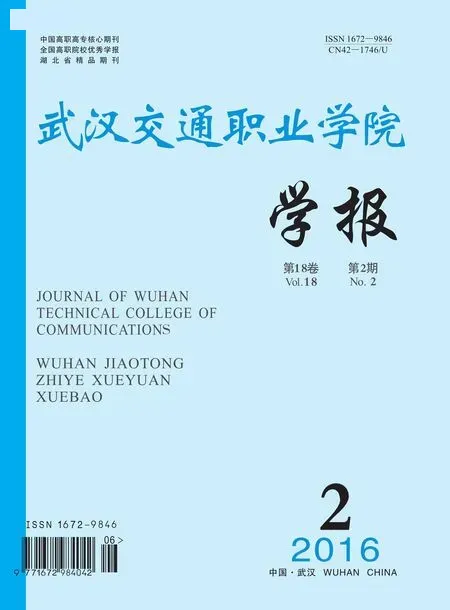危险驾驶罪的理解与适用
——以《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修改为视角
李玉琼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危险驾驶罪的理解与适用
——以《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修改为视角
李玉琼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2015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针对危险驾驶罪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超载超速驾驶、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两种行为方式,同时将机动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纳入该罪的犯罪主体范围,为全面规制危险驾驶犯罪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但是,新增规定中的“校车”“旅客运输”“严重超过”等词语在认定过程中均存在一定模糊性,有必要厘清其涵射范围,因此文章主要以《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修改为出发点,对危险驾驶罪新增入罪情节和新增主体的理解和适用进行分析。
危险驾驶;旅客运输;刑法修正案
危险驾驶罪是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加的一个罪名,该罪自确立以来,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对令民众头疼的飙车、酒驾、醉驾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起到了震慑作用,对社会秩序以及日常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虽然诸如飙车、醉驾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是面对新出现的超载运输、超速行驶、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等行为,刑法的相关规定却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刑法修正案(九)》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完善,将《刑法》第133条之一进行修改,规定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1.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2.醉酒驾驶机动车的;3.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4.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同时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此次修改通过增加入罪情节、扩大犯罪主体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了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打击力度,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两个危险驾驶罪的入罪情节:第一,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第二,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其次,《刑法修正案(九)》扩大了危险驾驶罪的犯罪主体: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对上述新增犯罪情节负有直接责任的,也将按照《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本文将对这两个方面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
一、危险驾驶罪新增入罪情节分析
(一)情节一: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超载超速驾驶行为
2011年11月16日,甘肃省正宁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校车与一辆运煤货车发生碰撞,事故共造成21人死亡(其中19人是儿童),43人受伤(其中18人重伤,26人轻伤,全部是儿童),经事后调查,该校车核载9人,实载64人,属于严重超载[1]。其实,甘肃正宁幼儿园校车事故并非个例,近年来不断有校车以及客运汽车因超员超速而发生重大交通安全事故的案件发生。《刑法修正案(九)》将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者的超员超载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是基于对社会公共政策的考量和对群众要求严惩该类行为呼吁的回应,通过适当提前刑法的介入时间,将这种行为犯罪化,纳入刑法制裁的范畴,能减少此类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保护学生以及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达到风险预防早期化的效果。但是,在《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中,相关用语的边界却不甚明晰,有必要加以分析认定。
1.“校车”范围的认定。2012年4月10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和《专用校车学生座椅系统及其车辆固定件的强度》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只有符合这两项国家标准的车辆才能从事校车业务。但是,现实情况是,在我国许多贫困地区,许多“校车”实际上并未符合上述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却仍在从事接送学生上下学的服务,甚至有的“校车”属于一车多用,既用于接送学生,同时又兼做学校或幼儿园的日常采购和其他出行用途。因此,这些“用法上”的校车是否属于《刑法》第133条所规定的“校车”?本文认为,一方面,这些“用法上”的校车应当包括在内。首先,从《刑法》第133条之表述来看,“从事校车业务”中的“业务”二字毫无疑问扩展了“校车”的范围,使其不仅仅局限于符合规定之校车,同时也包括那些虽不符合相关规定但实际上从事着校车业务的车辆;其次,从现实情况来看,实践中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中的校车也往往是这些手续不齐全、配置不合理等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校车”,故而,这些“用法上”的校车应当包含于内。另一方面,条文中的“业务”二字也具有一定的限缩意义,即在学校对校车进行一车多用的情况下,在非从事接送学校师生业务的过程中超载超速的,则不能适用于该条款,如在用校车进行学校日常采购途中超载货物或者超速行驶的,应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行政法规对相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如果危害到公共安全的,则应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总之,就该项规定中的“校车”的范围来说,本文认为应该理解为在超载超速行为发生时,实质上从事着学校师生接送业务的车辆。
2.“旅客运输”范围的认定。根据运输方式的不同,我国的客运交通系统主要由铁路、水运、公路和民航等四种现代化运输方式组成[2],因此,就“旅客运输”的通常含义来讲,其范围涵盖了铁路、水运、公路和民航四种旅客运输方式。而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危险驾驶罪的适用范围主要指的是公路上的危险驾驶行为。那么新增条款中的“旅客运输”的范围,是包含所有通常意义上的旅客运输方式还是仅限于公路旅客运输呢?就“旅客运输”在危险驾驶罪条文中所处的位置来看,其范围应当限于后者,即仅限于公路上的旅客运输。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是危险驾驶罪的入罪情节之一,其所处位置下属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的规定,因此,“旅客运输”的范围首先应当是位于“道路”上的旅客运输。而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明确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然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由此可见,本罪中的“旅客运输”范围仅限于公路旅客运输。
虽然立法将危险驾驶罪中“旅客运输”的范围仅限于公路旅客运输,但是关于这一做法,本文认为值得商榷。正如赵秉志教授、刘志伟教授等人在《关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修法建议》一文中所提,“实践中航运客轮超载引发的恶性事故也数不胜数,社会危害性与公路客车超载、超速造成的事故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3],如发生于2011年9月9日的湖南邵阳沉船事故即是一例,该事故共造成12人死亡,20人受伤,1人失踪,据事后调查,该客船仅荷载14人,然而事故发生时客船载员却达50人[4]。因此,将与公路客运业务超载超速行为性质、危害相同的航运行为也包含在“旅客运输”的范围内具有现实必要性。因此本文认为立法有必要将性质、危害相同的其他旅客运输行为等概括进去,一并予以犯罪化。
3.“严重超过”的认定。根据刑法的规定,不论是从事校车业务,还是从事旅客运输,只有在“严重超过”规定核载人数或规定时速的情况下,才能根据刑法按照危险驾驶罪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未达到“严重超过”标准的,仅由交管部门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即可。但是何为“严重超过”,刑法并没有明确的标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2条,“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超过额定乘员20%或者违反规定载货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根据上述规定,超载和超载20%分别作为两档行政罚款的适用起点,其中超过20%相对第一档罚款而言属于严重情况。同样,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的规定,“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的”,应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由此看来,超载20%、超速50%都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处罚界点。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刑法》不同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刑事处罚理应适用比行政处罚更为严格的入罪条件,因此,只有在超载至少高于20%、超速至少高于50%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才有可能具有刑事可罚性,至于其具体的处罚界点,我们只能期待最高司法机关尽快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该条规定进一步完善。
(二)情节二:违规运输危险化学物品行为
有观点认为,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稳定性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不应纳入刑法范畴,而应采取加大安全监督和行政查处力度的方法对其进行规制[5]。对此观点,本文并不赞同。首先,运输危险化学品本身具有极高的危险性。化学品属于特种物品,往往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腐蚀放射等性质,较之于一般货物运输,在道路上运输危险化学品将会对道路公共安全产生更为严重的威胁,发生事故后产生的社会危害也更大。根据国家安监总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10-2014年,我国共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326起,导致2237人死亡,其中77%的危化品事故发生在道路运输中[6]。其次,行为人的违规运输行为通常是将这种运输风险转化为现实危害的最主要原因,如发生于2014年7月19日的沪昆高速特别重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爆燃事故,经事后调查,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司机驾驶严重超载的轻型货车,且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并且其社会危害性足以上升到刑法规制的层面,将这种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存在一定的必要性。
另外,将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行为作为一种危险驾驶方式加以入刑,并不意味着凡是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都构成危险驾驶罪。《刑法》第136条也同样对危险化学品的违规运输行为进行了规制,根据该条规定,违反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管理规定,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中,由于过失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以危险物品肇事罪来认定。由此可知,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尚未发生事故但已经危及公共安全的,应当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如若因过失发生重大事故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以危险物品肇事罪来加以处罚;另外,如果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并故意冲撞人群的,则有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此,基于是否产生后果以及行为人主观心态的不同,刑法对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各种情形也规定了不同惩罚力度的罪名,具体构成何种罪名应结合行为人的主客观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并非一律构成危险驾驶罪。
二、危险驾驶罪新增犯罪主体分析
《刑法修正案(九)》针对133条新增一款,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此款将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也纳入了危险驾驶罪的犯罪主体范畴,这意味着校车、旅客运输车辆出现严重超速超载等违法行为以及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时,将不再仅仅追究驾驶员的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及管理人将视具体情况承担刑事责任。从实际情况来看,校车、客车及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责任往往不仅仅在于机动车驾驶人,更多地或许在于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校车驾驶员明知车位不够,严重超载可能会发生事故,危及学生的人身安全,但是因为经费有限无法配备足够的校车,学校管理人默许甚至强令驾驶员超载,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校车的驾驶员通常只是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的雇员,其通常要接受雇主即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的监督并且依命令行事,驾驶员往往是惮于丢掉工作而铤而走险超员超速驾驶。基于此,此次新修条款对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的责任也特别提出了规定,这将有利于全面强化学校和企业所有人和管理人的安全管理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有力推动校车、旅客运输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和进步。
(一)“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承担罪责之理论依据
与《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二款相似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发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7条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我们可以发现,《刑法》第133条之一和《解释》第7条都规定了机动车辆的所有人或管理人的责任,然而应当承认的是,在两种情况下,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却完全不同。
刑法学界通常将交通肇事罪中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归结为其存在监督管理过失,如有学者认为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本应对驾驶员安全行车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但由于过于自信而没有尽到管理职责,客观上放松管理或错误管理,利用职权强令指示驾驶员违章行车,导致驾驶员因监督者的要求而违章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被监督者过失犯罪,应属于监督过失行为”[7]。虽然危险驾驶罪中对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责任的规定与上述《解释》第7条具有一定相似性,并且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机动车驾驶员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监督管理关系,但是本文认为,危险驾驶罪中机动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在于其行为已经构成不作为的故意犯罪。
上述差异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原因:首先,两罪中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行为与刑法所要禁止的结果(在危险驾驶罪中表现为禁止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同。在交通肇事罪中,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的行为与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结果之间是间接关系,亦即危害结果的发生并非是监督者的行为直接造成的,而是由被监督者的行为直接导致的,其因果关系链条表现为“监督者未履行监督责任——被监督者违章驾驶——交通肇事(为刑法所禁止)”;而在危险驾驶罪中,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的行为与刑法所禁止的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其因果关系链条表现为“监督者未履行监督责任——被监督者超载、超速或违规运输(为刑法所禁止)”。其次,两罪中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主观方面不同。在交通肇事罪中,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虽然也是“故意”指示强令被监督者违章驾驶,但这种“故意”并非刑法意义上的故意,刑法中的故意指的是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故意,显然,监督者对交通肇事这种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是过失;而在危险驾驶罪中,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校车或旅客运输超载超速行为、违规运输化学品行为负有“直接责任”情况下,其对刑法所禁止的行为的主观心态是故意,即明知机动车的驾驶员实施了上述行为,却听之任之或者机动车的驾驶员实施上述行为正是基于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要求或命令。
(二)“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认定
通常,“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往往比较容易认定,直接根据机动车登记文件中所载即可加以确定。一般来说机动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都是个人,那么负有直接责任的主体指向的就是车主,其应负的责任是指车主本人明知驾驶员在从事校车业务或旅客运输时实施了超载、超速行为;驾驶员不具备危险化学品特种车辆的驾驶资格或没有驾驶证而仍予以聘用;明知驾驶员违反规定运输而不制止等等。
但是,在《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三项和第四项危险驾驶行为的情况下,因为驾驶员往往属于学校、客运公司或运输公司的员工,此时就可能出现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表现为学校、客运公司、运输公司的情况,即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为单位的情况。然而,刑法针对危险驾驶罪只规定了对自然人的处罚,也即危险驾驶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那么就存在一个问题,以校车为例,如果校车登记在学校名下,而危险驾驶罪又没有规定单位犯罪,此时将如何追究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的责任?本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追究学校内部对校车安全运行负有监管义务或职责所在的人。这样解释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一是我国司法解释中已有类似规定,即在单位实施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的犯罪时可以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8月13日施行的《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 情节严重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二是实践中无论是校车、客车,还是运输危化品的车辆,其所有权和管理权绝大部分都归属于单位或者单位的内部机构,如果以危险驾驶罪没有规定单位犯罪为由就不追究单位内部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无疑会导致该条规定的虚置或者难以实现刑法设立此条款的立法目的。据此,本文认为,在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为单位的情况下,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应理解为学校内部实际负有职责的人,即除驾驶员外,单位规定的对校车、客车、危化品运输车辆的安全运行负有监管义务或职责所在的人。
(三)“负有直接责任”的认定
从条文规定来看,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构成危险驾驶罪的要件是需要对第三项和第四项危险驾驶行为负有“直接责任”。那么,什么样的责任属于“直接责任”呢?“直接责任”的边界又在哪里?本文认为,结合上文中对于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承担刑事责任依据的分析来看,“直接责任”应当存在于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对于机动车驾驶人的危险驾驶行为至少存在着“明知”。具体来说,有以下两种:第一,所有人或管理人故意指使或强令他人从事校车或旅客运输超载超速或者违规运输危险化学物品的行为。这种情况所有人或管理人的主观恶性较大,所有人或管理人的指使是导致危险驾驶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第二,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明知机动车驾驶员实施了超载超速行为,或者明知驾驶员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有能力阻止却不阻止,对危险驾驶行为放任不管的。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应当认为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负有直接责任。
总之,《刑法修正案(九)》针对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提出了更高的管理监督义务,实践中所有人和管理人不能因为自己不是驾驶人就放任驾驶人随意使用车辆,而是要尽到良好的监督义务,及时阻止驾驶人的不良驾驶行为,从而降低风险。
三、结语
随着我国进入汽车时代,除醉酒驾驶和飙车行为外,其他危险驾驶行为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各种恶性校车事故、旅客运输事故、运输危险化学物品肇事事故等愈演愈烈,要求刑法对此类行为能够给予更严格规制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此背景之下,《刑法修正案(九)》将校车及旅客运输超载超速、违规运输危险化学物品行为纳入到刑法范畴,同时增加危险驾驶罪犯罪主体的做法无疑是对广大民众需求的积极回应。然而法律条文是简洁的,现实生活却是复杂多变的,对于修改后的危险驾驶罪的更好理解和适用有赖于理论上对新增条款进一步的梳理和探讨,同时也有赖于司法机关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以及刑法和相关行政法规之间的进一步衔接。
[1]甘肃正宁幼儿园校车事故[EB/OL].(2011-11-16)[2016-03-20].http://baike.baidu.com/view/11752715.htm.
[2]王苏男,贾俊芳.旅客运输[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8.
[3]赵秉志,刘志伟,阴建峰,等.关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修法建议[J].刑法论丛,2014,(4):21-22.
[4]9.9湖南邵阳沉船事故[EB/OL].(2011-09-10)[2016-03-20].http://baike.baidu.com/view/6450038.htm.
[5]程骋.“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行为入刑的合理性辨析[J].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4):57-60.
[6]任继勤,穆咏雪.危化品事故的统计分析与管理启示[J].化工管理,2015,(16):28-31.
[7]刘源,杨诚.交通肇事罪共犯问题辨析[J].法学,2012,(4):156-160.
2016-03-29
李玉琼(1991-),女,河南安阳人,华东政法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
10.3969/j.issn.1672-9846.2016.02.004
D924.3
A
1672-9846(2016)02-0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