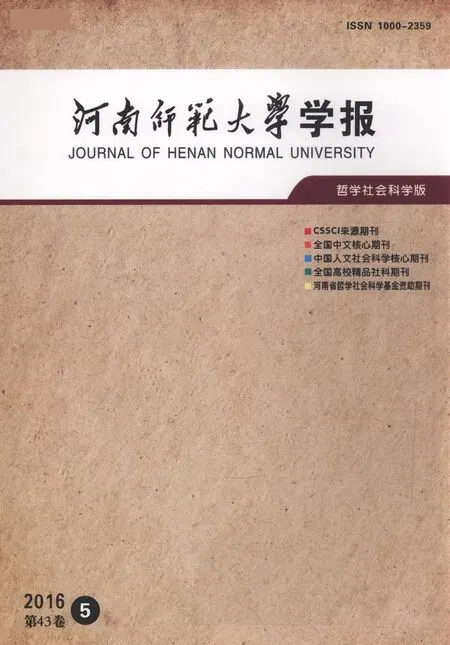思维-符号与心语说
赵 毅 衡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610065)
思维-符号与心语说
赵 毅 衡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610065)
人的思考必定是在语言中进行,还是可以在一种非语言的符号中展开,或是二者兼用,这个问题,关系到人的意义活动是不是必定需要语言。很久以来人们感觉到思维使用一种特殊的符号,近半个世纪以来陆续有人提出“心语说”引发了许多争议。本文介绍了这些争议,但是重点整理了皮尔斯的“思维-符号”理论,指出皮尔斯的理论在许多方面与“心语说”相近,而且论说得相当充分,可以被看成是“心语说”的前驱,在某些地方讨论得更为精辟。因为它比较符合意义的“翻译论”定义。
思维-符号;心语;皮尔斯;意义;翻译论
一、人靠什么思考?
赛尔曾经在上世纪之末,讨论过哲学潮流的大规模转向,他说20世纪的第一哲学是语言哲学,而21世纪的第一哲学将是“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他的看法极为精准。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出现了关于“心语”的争论。20世纪末的意义理论,不得不讨论一系列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不必触及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意识在思想时,使用是究竟什么样的符号?很多论者认为:人用语言思考。如此考虑非常干脆而且解决问题:一旦思维必然在语言中进行,思维方式也就遵循语言的规律。但是这就很难回答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在“前语言阶段”(尚未学会语言的儿童),“非语言个体”(无语言的猿类或其他高智商动物、失语症患者、没有学会社群手势语的聋哑人),“本能反应”(来不及做语言思考时),甚至是艺术家和诗人的“灵感”(无以言表的神思),或需要将语言与非语言对照时(“想不起他的话了,但他不是这意思”),或是语言意义歧出必须用思想符号校正时(不是这种“担当”,而是那种“担当”)。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我们都遇到一个幽灵般的存在,那就是我们头脑中,在语言前,在语言下,至少有一部分不按语言进行的思维。
这些情况到最后都能用语言(语言学界称为“自然语”,本文为强调其公共性,称为“社群语”,指的是同一个意思)在心中或在嘴上或书面呈现出来,但是显然要有意识地转弯抹角之后,才能用语言说明清楚(例如:“不是卦象的‘象’,而是长着象牙的‘象’”)。因此问题就出现了:非语言思维,用的是什么符号,这些符号、心象、概念,又用何种规律组合成完整的意义?甚至,社群语已经熟练的人的头脑中,是否依然有非社群语的符号思维,它与语言性的思维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是所谓“心语”问题的由来。
很多学者认为人脑中最即刻的反应是心像,图像可以直接构成经验。但是图像依然有一个如何连接,如何筹划或设计的问题。例如心里本能的思维:“这事糟了快逃!”这里至少看得出5个意义单元,可以命名为“这”、“事”、“糟了”、“快逃”、“!”。它们都来得及再现为语言吗?来不及,也没有必要,要逃的人头脑只消跳出这个“念头”,就能立即把这意义转化为行动。它们都呈现为图像吗?第一个概念“这”就无法成像,它是与主体的关系远近;“事”可以是一个抽象的指向;“糟了”是至今的变化;“!”则是模态,可能除了“逃”可以明显成为心像,其他4个意义单元很难呈现为图像。哪怕能分别成像,感知的切分只是思维最直接最本能的部分,如何形成命题才是最难分析的。这些图像也不可能靠自身串结组合成意义,也需要“元结构形式”(心中原有的关系组合模式)将它们变成内容,从而让人的身体迅速应之以行动。因此,某些人所有的时候,所有人某些时候,都会用一种非语言的方式作直觉的思维,这就是“心语说”的主要根据。
“心语”或许与动物的思维方式相差不远,动物能够做相当复杂的思考,不逊于人类。有不少报告,证明某些动物不仅能欺骗,而且能识破欺骗[1]70-74。这是掌握非语言高级符号意义活动的标志。艾柯再三说过:欺骗是符号行为的一个最基本能力。“每当存在着说谎可能时,就有一种符号功能”;“说谎可能性就是符号过程的特征”[1]70-74。而维特根斯坦指出撒谎是一种“语言游戏”,而且谎言游戏“与其他语言游戏一样,要学习才能会”[2]。这就证明前语言作为一种意义活动的工具,可以与人类文化所产生的其他符号体系相比。
既然人本能思维的基础组成,不是语言,也不完全是图像,那么人究竟如何思考?人每时每刻地思考,使用的究竟是什么?如果这是人脑中的一种“携带意义的感知”,也就是说是一种符号,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符号?
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人脑思想用的是一种非语言非心像的特殊的“心语” (Mentalese),这种“心语”非语言,实际上是用来否定人类用语言思考,因此“语”字只是比喻。要建立这样一种学说,不得不回答很多问题:“心语”是与生俱来的还是习得的?它是否有词库和句法?它是否有完备的符号体系?当我们有意识地思考时,它又是如何被“社群语”(母语,或习得语)取代或覆盖,一如母语也会被掌握的很好的习得语所覆盖?抑或成人的心语只是表面上被“社群语”覆盖,内心实际上还是按心语在操作思维,只是经常自然而迅疾地翻译成“社群语”? 如果社会文化交流靠社群共享的语言,个人化的心语能否应用于交流?这一系列问题,至今尚没有一个答案,因为至今关于“心语说”的论辩,还在争论它究竟是否存在。
人一旦进行与他人的交流,就必须用社群的语言。马克思在这问题上说的很清楚:“语言本身——这是一定集体的产物。而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也就是这个集体的现实存在,而且是它不言而喻的存在”[3]。语言哲学界大致都接受的说法是:我们的世界之边界,是我们的语言所决定的。维特根斯坦指出:“私人语言”不可能有意义,语言的群体性反过来模塑意义世界。他说我的“痛”外人不可能理解,除非用社群共同的语言,“若果没有公共语言,我们无法描述这个体验”[4]。语言学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把这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依照我们的母语来切割世界。”[5]他们的意思这世界有没有这个范畴,取决于有没有相应的语词,而且是文化认可的语词。这就对心语说提出了一个更重大的挑战:如果世界是语言构成的,心语有“塑造”这个世界的能力吗?
这些问题之复杂,任何提出或赞同“心语”的提议,都会招来无穷的追问。任何构筑出来的“心语”方案,都会遇到无穷的反例。以至于“心语”说举步维艰,至今尚未有一个得到大致赞同的理论假定。但是“心语”问题值得探讨,必须探讨,因为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思想是如何构成的,这是意义诸理论的出发点。
二、心语假说
人类是不是有一种非交流的“内部语言”?很多论者认为应当有。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就考虑过。最早提出思想语言的人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与洛克。霍布斯认为言语是心理话语转换而来的[6]。最早建议“符号学”学科的洛克认为思想是符号,而词汇是思想的符号,因此是符号的符号,所有的语词都是元符号[7]。但是他们都没有对此做详细的论证。20世纪各界学者,如心理学家维果斯基、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符号学家索绪尔,都认为应当有这样一种思维工具,但是大家都语焉不详。除了本文下面将详细讨论的皮尔斯关于“思维-符号”的文章,甚至无人做过成段的论说,可见这问题之困难。
最早以一本书的篇幅,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一个方案,并为之详细辩护的,是美国语言学家福多(Jerry Fodor),他于1975年提出“思维语言”(Language of Thought,简写为LOT,因为至今被学界认为只是一个假说,所以加了一个字母H,即Hypothesis,称为LOTH)[8]。福多的学说很多年中一直遭到质疑,始终没有得到学界比较普遍的响应,直到二十年之后,1995年平克(Steven Pinker)发表《语言本能》一书[9]。从认知学的心理实测给予此说以更有力的理论支持。最近苏珊·施耐德从神经科学角度给与声援,把这问题变成了一个生理学问题,甚至动物生理问题,以彻底摆脱语言的纠缠[10]。本文无法进入神经生理或动物学领域,本文只是把心语作为一个意义哲学课题,从符号学寻找支持。
拥护“心语说”的学者们,理论与证据各有所差别,但是基本的概念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心语”是一种人类本能的语言(或符号),是人类甚至某些动物头脑天生就具有的意义方式。“心语”是内省的,非交流的语言,只有当我们与自己说话才会用。其表意方式可能类似语言,但不会是社群交流语言那样的音节语,也不会完全是图像、意象、模型。除非当意识明显感到自己在“思维”,或是准备与别人交流时,不一定需要把它转化为社群交流语言,也不需要用某种外部媒介予以再现。
那么“心语”究竟是什么形态呢?有的学者想象这样一种“心语”由有限的“语义基元”(semantic primitives)构成,可能是头脑内部的神经冲动。原始语义基元不可能被再现,因此是无书面形态的(non-orthographical),无语音的(non-phonological),但是语义上却依然是有逻辑构造的语言,依从一定的作文构造(compositional structure),由此形成一种类似语言的“起始原型”(protoness)。
“心语”的辩护者举出一个非常特殊,但是很有力的例证:某些聋哑人,没有学过社群通行的手势语,被称为“非通用手势人”(home signer)。他们与家人用只有他们懂的一套手势交流,只是使用社群语(包括社群通行的聋哑语)的人不懂而已。一旦这样的“非通用手势人”聚到一起,他们不久就会相互交流起来,用的却并非社群通行的手势语(因为他们都没有学过),而是他们为交流临时设计的手势。可见人的思想中,哪怕没有与他人交流,也有一定的思维语言,一旦交流,就会被某种共同符号“意符化”,成为外显的符号语言。如此意符化之后,也就是被姿势、语音、文字等社群交流语言取代后,他们的“心语”就被覆盖。
“心语说”触及一个哲学上更本质的问题:究竟是语言产生思想,还是思想产生语言?心语假说的主要论敌,是20世纪占绝对优势的语言哲学。语言哲学不仅认为社群语言是社会和个人思想之间的必要媒介,而且认为社群语言决定了我们感受理解世界的方式。而按照“心语说”,思想本身是“生成性的”,有思想才必然有语言,思想产生语言符号,而不是相反。如果没有说出来与他人交流的压力,也没有学会社群语,思想产生的就只能是个人化的“思维语言”。
可以看到,任何词语很难“贴切地”表达意义,社群语言,或其他任何社群性符号体系,经常不整齐,有许多歧义与多义。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四人一桌”、“请吃菜”、“他动手术”。此时接受者不得不寻找一个比较清楚的理解,或靠上下文语境,或靠加词来确定关系,或在交流中靠“文本内元语言”来回纠正,例如要文本内说明“我说的是”、“这才是我的意思”等短语加以辅助。此时,用社群语言难以说清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显然只有是前语言或非语言的,才会是准确的。社群语之所以容易产生歧义,是相对于思维而言。这不是说思维必然清晰,而是说实际上只有对比并不歧义的思维,才能说语言歧义。
但是,正因为社群语言在我们头脑中力量之强大,我们就落入一个陷阱:“你怎么知道你的心语说的是什么?”[11]的确,要说出“说的是什么”就必须用语言,而心语是非再现的,说不出的,要再现思维,依然不得不用社群语言或符号,只是换个方式来说。例如“我们每四人一桌”、“请吃蔬菜”、“他主刀动手术”。我们只能说这些表达法更接近“心中的意思”,但是无法不用社群语再说清这心中的意思。
社群性语言(或其他符号体系)的再现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生存于社群中的人已经很难明白感觉到语言底下有“心语”在操作。心语是随时准备被社群语覆盖的某种意义载体,是我们作为原始人创造社群语的基础,或作为婴儿学习社群语的基础,也是我们想说得“更准确”时的基础,因为我们总是需要一种已经掌握的语言(元语言)来学习或应用另一种语言。概括地说,“心语”是假设一种人心天生具有的类似语言的存在,这种语言大致由某种无法付诸再现的心理表征构成,在大脑中有可能以神经脉冲方式出现。人的思想首先发生在这种天生的符号系统中,然后才有可能被翻译成后天习得的社群语言。
心语假说的首要目的是解释思想和心智如何获得意义的,而这个问题是困扰哲学和心理科学的根本问题,至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如果说心语假说有太多反例,没有能回答所有的疑问,这不证明心语假说不必要,而只能证明我们对心语的理解尚不够完美,因为前文已经提出过:不假定有“心语”,也会有很多无法回答的疑问。
以上是对“心语说”的简单介绍。本文的目的不是为“心语说”提出更有力的辩护,而是提议“心语假说”有一个理论先驱,那就是符号学的奠基者皮尔斯关于“思维-符号”的论述,皮尔斯的讨论,与心语说出乎意料地接近,因此“心语说”应当是哲学符号学考虑的一个问题。
三、皮尔斯的“思维-符号”理论
皮尔斯一生曾经多次讨论过“思维-符号”(thought-signs)这个概念,他的理论实际上应当称为“心符说”(mental semiosis),因为他强调论证思维的符号性质。皮尔斯在1868年,他29岁时的论文《四种无能的若干结果》(SomeConsequencesofFourIncapacities),作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论述[12]vol.5:283。中对此曾有长段讨论,此后一生中也多次提及。只是皮尔斯写成篇著作极少,只是在死后留下大量笔记。皮尔斯遗作被按主题整理成合集,或是按年代整理成编年全集,都是卷轶浩繁,至今却一直没有人仔细讨论过埋藏与其间的“思维-符号”问题,也没有人整理过他这方面的思想,至今也没有人指出过他的讨论很接近近年的“心语说”。
在皮尔斯看来,符号之所以能传达意义,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的思想本身就是符号”,这种人与生俱来的符号方式称为“思维-符号”,他说:“根据定义,人类思想自身就是符号;假如所有其他的符号最终都会在思维-符号中得以解释是事实的话,那么这个事实就与逻辑本身无关了。”[13]他说的“与逻辑无关”,意思是这是一切逻辑的起点。
那么“思维-符号”是不是非语言的,或前语言的?皮尔斯没有做绝对肯定的论述,但是他似乎认为思维-符号可以采取各种形式。例如他说“注意力,是指向思维-符号应用或其幅度的功能,它是思想扮演指示符的角色”[12]vol.2:428。因此,在他看来,注意力是一种思想中的指示符号,但是并不一定明确以“this-that”或“此与彼”这样的语言方式出现,它们只是一种意义的方向感觉。皮尔斯这个观察非常敏锐,实际上所有的连接词、虚词,甚至“模态动词”如“必须”“应该”“可以”等,可能最不会立即在思想中显示为语言,甚至不太会显示为图像,而最可能是某种心语方式显示,因为这些虚词的意义,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态度”。平克就指出过各种代词(冠词、指示代词、人称代词)在人的智性思维中很特殊,哪怕在熟练掌握社群语言的人心中,也往往依然会以“心语”方式出现[9]。很可能心语不需要代词,原概念重复即可。代词消除累赘,使表意简洁,而“思维-符号”无篇幅可言,也就没有对简洁的追求。
但是“思维-符号”究竟是语言的还是前语言的?皮尔斯提出:“每当我们思考时,我们向意识提交情感、形象、概念,或其他再现作为符号。但是我们的存在(我们屡屡产生的无知与错误就是存在的证明)说明向我们呈现的一切,都是我们自身的现象表现(phenomenal manifestation),正如虹是太阳与雨共同的表现。因此,当我们想到自己,我们自己在那一刹那显示为一个符号。”[14]8这是一段非常诗意的描述,皮尔斯认为我们的思想符号可以是“情感、形象、概念”,虽然皮尔斯保留说有“或其他再现”的可能,但是如果这种“自己的”思想符号,可以由语言构成,他肯定要在此提到,因为语言的表现力远远强过提到的“情感、形象、概念”这几种符号。
皮尔斯不满足于仅仅提出“思维-符号”的这三种形式,他进一步证明这样一些“自我思维符号”拥有符号表意的系列特征。在他看来,符号必须符合三个意义条件:“一个符号有三个指称:首先它是某种能够解释它的思想的符号;第二它是与这种思想等值的某个对象的符号;第三,它是使它与此对象联系起来的某个方面或某种品质的符号。”这也就是皮尔斯后来更加明确地提出的符号三联构成:“再现体”、“对象”、“解释项”。
然后他用这三个严格的条件,来衡量他讨论的“思维-符号”:“那我们就要问:思维-符号指向的是哪三个相关项呢?首先,当我们思想时,这个就是我们自身的思维-符号,指向什么呢?可能需要充分的内部发展之后,它可以通过向外表现,指向另一个人。”在这里,皮尔斯明确指出了“交流”需要语言(或其他可交流的符号),而语言的产生需要先把思维-符号做充分的“内部发展”才能得到。这样,皮尔斯就明确说明了“思维-符号”是“我们自身”,并不用于交流,交流是语言的,而语言要在心中把思维-符号做了“发展”才能达成。
那么这种思维-符号自己的(非语法的)构成原则究竟是什么?皮尔斯建议说这是一种“意义的联想延续论”。他的描述很清晰:“这种情况(指与他人交流)不管是否发生,思维-符号只能被我们自己后继的思想来解释。如果在一个思想之后,当前的思维之流依然自由地流淌,它就遵循心灵联想的规律。这样一来,前面的思想提示后面跟随的思想,也即是说,它就是后面跟随的东西的符号。” 皮尔斯生动地描写说:“可以说这样一条规律是没有例外的,即每个思维-符号都是被后一个所翻译或解释,除非所有的思想一下子全部中断,突然死亡。”[12]vol.5:285
因此,思维-符号的内在语法,并不是语言的句法,而是联想造成思维-符号单元之间的链接,链接的过程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是作为感觉的内在品质。第二是影响其他观念的能量……第三是一个观念把其他符号与其融合在一起的那种倾向。”[12]vol.6:135所有符号都是先前符号的结果,每一个符号都有一段历史,其背后都有一个传统,思维-符号活动组成前后相续的符号过程。这样的连接过程可能被中断,但是思维基本上是前后相续的,用“前因后果”意义链来说明思维单元的意义,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可以不求助于社群语的再现来给与解释。
由此,皮尔斯回答思维-符号如何符合符号的第二个标准:“思维-符号替代的是什么呢?它命名的是什么?它提出的是什么?如果想到的是外界的一个事物,那当然是这个外界事物。但是因为这个思想依然被这个事物的先前的思想所决定,它通过先前的思想去指称这个事物。”[12]vol.5:285皮尔斯的意思是,思维-符号,有可能是以外界事物为对象,那是它就是一个与外界连接的符号,它会开始遵循社群交流性符号体系的结构原则展开,例如语言会按语法展开;但是在思维内部,这个思维-符号依然按头脑里的联想延续方式展开。
然后皮尔斯解释作为符号最关紧要的第三点:“这个思维-符号在思想到的方面替代对象,这个方面就是思想的意识的直接对象,或者用另一种话来说,就是思想本身,或是这个思想在随后的思想(也就是它的符号)中被想到的方式。”这最后一点似乎有些复杂,但是这正是思维-符号理论的精粹:每个思维-符号,它的对象意义恰恰就是前面一个思想,符号本身的意义链接,就是成为一个有组合段的文本。思维-符号本身就是用符号的组成方式为自身的句法。这样的话,思维-符号就不需要外求于语言或其他的逻辑,思维-符号就是思想所用的底线工具,它可以再现成语言或其他可以用于交流的“外在符号”,但是它依然在思想的底层潜流中运行。
因此,皮尔斯在这里提出了一种双线展开理论:语言并没有中断思维-符号自己的意义发展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思维或交流哪怕在用语言进行,思维-符号的进展方式依然在延续。因此,在已经获得社群语能力的人心中,经常“心语”与社群语同时展开:“心语”不仅是前语言,也是“潜语言”。本文前面说过,歧义是针对“心语”而言的,也是靠“心语”来校正的,这就证明心语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中。同时,应当说社群语不仅是用来交流,也是为了让思想更加逻辑化,形式化。例如许多复合词、新造词、双关语,很难说是“心语”中固有的概念。对于成熟语言的人,哪些思维在语言中展开,哪些在“心语”中展开,已经很难分辨[15]。皮尔斯这种双线展开理论,可以解释很多对“心语说”的驳难。
对“心语”说最大的挑战,是追问其物载体究竟是什么?本文前面已经英国皮尔斯的看法:“思维-符号”不只是形象,而是“情感、形象、概念”。我们可以把“心像”视为形象的载体,但是情感与概念的载体是什么呢?皮尔斯解释说:“有理由认为与我心中的每一种感觉(feeling)相对应,我身体里有一种运动(motion),这就是思维-符号的品质,它与其意义并无理性的关联。”因此,思维-符号是一种身体与大脑内部的“运动感知”,但是它们携带着意义,因此是符号。皮尔斯认为这种特殊的符号载体,“可以与我说的符号的物质质地相比,它与后者唯一的不同是,它不一定必须被知觉到(felt)才能够出现思维-符号”[14]73。
为什么一般符号的载体必须被感知,而思维-符号不一定?因为这载体就是感知本身,这是与思维-符号的“非再现性”极其准确的描写。皮尔斯虽然没有称这种“运动”为“神经脉冲”,但是他指出思维-符号的载体可以是身体里的无形运动,这已经很了不起。
皮尔斯发表这个见解时,语言哲学尚未兴起,认为人的思想受语言控制的提法尚未为学界接受,因此皮尔斯没有针对“思想必用语言”的理论作针对性的论辩。但是皮尔斯已经明确地声称,“思维-符号”是前语言的,一旦被语言说出,就不再是思维-符号。我们可以看出,皮尔斯的“思维-符号”理论,与一个世纪后才出现的福多-平克“心语”理论,惊人地相近,而且论说得相当充分,应当被看成是“心语说”的前驱,在某些地方或许讨论得更为精辟。至今没有人看到这种像似,只能说明连美国思想界,对皮尔斯丰富的思想遗产,都还没有读透。
四、意义的“翻译论”
20世纪林林总总的意义理论,极其纷繁多样,“翻译论”(Translational Theory)是其中之一。这种理论的拥护者很多,包括语言哲学家蒯因,符号学家雅克布森等。他们认为,意义的最本质特征,就是能被另外一套符号再现出来。这另一套符号,可以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词语(语内翻译),可以是另一种语言(语际翻译),或是另一种符号(跨符号体系翻译),或另一种媒介的符号(跨媒介翻译)。
反过来说,一旦我们发现可以用不同的符号来再现某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可以被称为是意义,意义就是“可译性”(translability)。索绪尔提出语言的产生是由于社群“把同样的词典发给每个人”的结果[16]。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拿到这词典,对心语做了类似的翻译,才创造了语言。皮尔斯的整个符号学,都强调符号的意义在于解释,而解释就是用另一套符号进行翻译。因为符号就是意义,而意义就必须可以有别的符号来翻译,即是用别的符号做另一种再现。皮尔斯提出“解释项”为符号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他认为每个符号都必须能够表达一个解释项,广义地说,解释项可以被理解为这个符号的翻译:“除非符号能把自身翻译为另一种发展地更为充分的符号,否则此符号就不是符号”[12]vol.5:594。而“意义……它主要接受从一个符号到另一符号系统的那种翻译”[12]vol.4:127;“一个符号的意义就是它不得不被翻译成为的那个符号”[12]vol.4:132;因此,当皮尔斯说“每个思维-符号都会被翻译成或者被解释成随后一种符号”,他断然地宣称这条规则“不存在任何例外”[12]vol.5:284。这种翻译,不一定是通过某个翻译者居间,也不一定是通过意图清晰的解释行为来完成的,“翻译是一个产物,也即某个过程的一个结果,因此也就是符号过程本身。”
本文一直没有讨论机器的思维单元,福多提出心语假说,受到阿兰·图灵关于“计算机器与智能”思想的启发[17]。实际上机器语言的构成,对“心语论”非常有利:机器的设定语言从来不是可以适用于社群交流的语言,但是机器拥有强大的翻译能力,机器工作的最基本途径,就是随意转换成各种社群语与通用符号系统。
有论者认为“翻译论”也是一种意义的“符用论”(Pragmatic Theory),因为使用本身就是转换成另外的符号,例如“向前走”这句话,你可以说“我听懂了,这意思是朝正前方举步”,也可以直接走一步,用身体姿势“翻译”这句话,表示听懂了。蒯因对此有论说:“只有根据人们对社会可观察的刺激所做的明显的反应倾向,才能核实语言的意义。”[18]
皮尔斯一直在强调思维-符号的基本组成方式,就是在链式延续中被后续元素接上并且衍义下去的能力,因此皮尔斯的“思维-符号”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意义的符用论。翻译论首先强调的是意义就是一种“被翻译潜力”,用皮尔斯自己的话来说,“一个知性概念意义何在,这问题只能靠研究此符号的解释项,或表意效用本身来解决”[12]vol.5:475。显然,在皮尔斯眼里,“表意效用”与“翻译意义”本质上一致,“翻译论”与“符用论”本质上一致。
为“心语说”辩护的人说:人能够学会外语,是因为已经掌握母语;而人能够学会母语(第一个社群交流语),是因为人天生掌握了“心语”:婴儿在学习时,用社群语翻译了“心语”。这个论点引出了对“心语”理论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即所谓“无限递归论”(infinite regress):如果外语必然是通过母语翻译才能获得,那么“心语”是如何习得的?是从什么语言翻译过来的?这里的逻辑陷阱就是必须假定需要又一种语言才能获得心语。但是这个陷阱不一定存在:如果心语是进化的产物,是天赋,那么“心语”的“出发语言”,必是在动物进化过程之中形成。有人会认为是上帝赋予的,有人会认为是进化的基因,就象机器的基础语言,是程序员预先输入的。“心语”或许是继承人的动物本性,在这个符号能力进化的基础上,人才能进化成为“使用符号的动物”[19]。
正因为此,笔者认为,皮尔斯的“思维-符号”理论,虽然不是专门为一个世纪后的“心语假说”提供根据的,却暗合了“心语”的若干最重要假设。从皮尔斯的论述来看,“心语假说”并不如反驳者说的那样无根无据,而是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甚至发展成为意义研究的一个基础理论。
[1]Richard W Byrne.The Thinking Ape:Evolution Origins of Intelligence[M].Amsterdam:Elsevier,1995.
[2]Jacquette Dale.Wittgenstein on Lying as a Language Game[G]//The Third Wittgenstein:The Post-Investigations Works,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2004:159.
[3]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4.
[4]Norbert Wiley.The Semiotic Self[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121.
[5]J.L. Sapir.Culture and Personality[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9:46.
[6]R Burchfield.The English Language[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7]Winfred Noth.A Handbook of Semiotics[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24.
[8]Jerry Fodor.The Language of Thought[M].New York:Cromwell,1975.
[9]Steven Pinker.The Language Instinct:How the Mind Creates Language[M].New York:Perennial Press,2000.
[10]Susan Schneider.The Language of Thought:A New Philosophical Direction[M].Boston:MIT Press,2011.
[11]丹尼特.心灵种种[M].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1998:112.
[12]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M].Cambridge MA: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1931-1958.
[13]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M].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32.
[14]James Hoopes (ed).Peirce on Signs[M].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1.
[15]Jerry A Fodor.Concepts:Where Cognitive Science Went Wrong[M].Oxford:Clarendon,1998:28.
[16]费迪南德·索绪尔[M].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1.
[17]宋荣,高新民.思维语言——福多心灵哲学思想的逻辑起点[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2).
[18]Willard van Orman Quine.Word and Object[M].Cambridge,Mass:MIT Press,1960:6.
[19]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87.
[责任编辑 海 林]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5.022
2016-03-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123)
I0
A
1000-2359(2016)05-0125-06
赵毅衡(1943-),男,广西桂林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形式论、符号学、叙述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