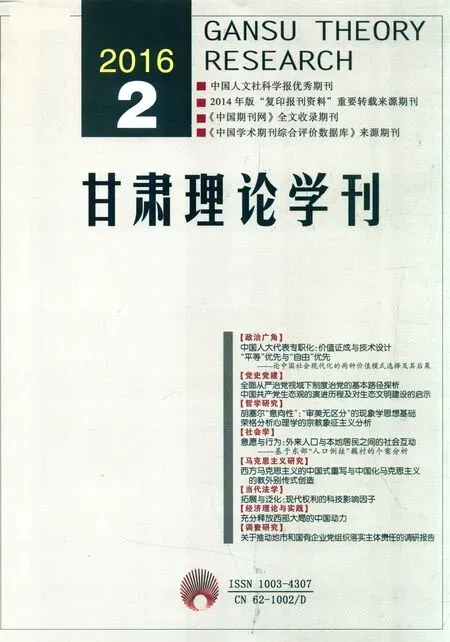藏汉佛教判教思想比较论——基于两地佛教教派判教的审视
何杰峰
( 西北政法大学 民族宗教研究院,西安 710000)
藏汉佛教判教思想比较论
——基于两地佛教教派判教的审视
何杰峰
( 西北政法大学民族宗教研究院,西安710000)
[摘要]藏汉佛教判教思想在背景、内容和影响方面既有相似性,又有诸多差异。其相似性源于两地佛教对印度佛教的秉承,而其诸多差异,除因与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各异有关外,还与两大佛教系统和印度佛教的亲疏有关。
[关键词]藏汉佛教;判教;思想
判教是融合佛教教义思想的重要形式,藏汉佛教教派时期,各教派都形成了独有的判教认识,成为它们各自教派教理思想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形成教派时期是指以公元十一世纪时宁玛派以寺院为中心的的传法体制的形成为标志至今,汉传佛教的形成教派时期是指从公元七世纪时隋代吉藏大师创立三论宗为标志至今。在这阶段里,藏传佛教先后形成了以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觉囊派、格鲁派等五大教派为代表的佛教教派,汉地佛教先后形成了以三论宗、净土宗、律宗、天台宗、华严宗、密宗、唯识宗及禅宗为代表八大佛教教派。这些教派的形成是佛教修习体系化,佛教信仰组织化、佛教利益集团化的体现,而两地教派中格鲁派及禅宗的建立,则标志着两地佛教教派地方化的完成。本文我们以历史学的视野,对两地佛教形成宗派后的的判教思想分别从背景、内容和影响三方面进行比较阐述,以此展现两地佛教教派判教思想的地方化特征。
一
从两地教派佛教判教产生的背景上来说,藏汉两地这一时期的佛教判教都反映了经论进一步翻译认识后自我表达主体意识的一种需求。就藏传佛教来说,自后弘期拉喇嘛益正沃迎请布甲巴拉开始,到公元1426年班纳吉仁钦入藏的大约420年间来藏的有73名班智达入藏,译师有192人,这相对于前弘期来藏班智达24人,译师5人来说[1]284-299,可以说有着巨大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瑜伽类的《慈氏五论》,中观思想中月称论师的相关论著,因明的《集量论》、《释量论》、《决定量论》及其所属的注释,密宗类经论,尤其是前弘期时禁止翻译的无上瑜伽部密法,在这一时期都得了大最翻译。本土佛学大师及学者的大量增多,他们在翻译经典的同时,他们还根据对经典的理解,开始了大量的著书立说。由此,在显宗教义和密宗的修持上都渐成体体系,并有了门户之见,这成为建立教派和表达判教性认识的基础。而这些经论的翻译完备及其藏地学者撰写大量佛学论著表达对佛教经义和修习实践的理解成为藏传佛教教派判教思想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同时,教派与地方割据势力的主动结合,如萨迦派与萨迦地方政权的结合,噶举派与帕竹、雅桑等地方政权的结合,觉囊派与藏巴地方政权的互应等等,使得当时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佛教教义在进行宣传时,有必要对其殊胜之处作一整体性的比较论说,这成为了藏传佛教诸教派进行判教性论说的外在需求。
就汉传佛教来说,伴随着南北朝所形成的毗昙师、成实师、摄论师、涅槃师、地论师等学派团体的出现,造就了众多广览群经,学识渊博的佛教学者。在隋唐时期全国实现统一, 南北间各种文化进一步整合的背景下,当时的佛教各学派出于维护自我思想传承,保护自我既得利益、迎合时代需求的需要,作出了具有教派性质的判教思想构建。由此所兴起的隋唐时期的佛典章疏之风*汤用彤先生考证“隋前中国佛教撰述亦不过二千数百卷。至唐元和中僧人合注疏及开元至贞元新译立为别藏,计共四千九百余卷”(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页63)。可以看到隋唐佛教的章疏远比之前要多。,造就了这一时期对佛教整体思想进行更自觉的反思和把握,这成为汉传佛教教派判教的内在动力。同时,隋唐时期政府所主张的“三教并举”治国方略,给佛教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则为这一时期的佛教进行判教思想的阐述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就其不同来说,藏传佛教的教派判教思想,是在当时藏地政治上处于分裂割据时期,文化上佛教逐步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由于受印度佛教不同师承影响,而进行的一种不自觉的判释行为。它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自我修学需要,外部力量的激发在藏传佛教各教派判教初期并不占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说显得微不足道。而汉传佛教教派判教是在政治上中原经过了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分裂后的统一,文化上多元并起的一个时期,佛教内部各学派在统一国家的社会环境下,相互间的频繁交流给佛教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活动空间的背景下产生的。虽然,各教派为显其传承清静,教法殊胜是进行教派判教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但更多的是佛教团体为争取更多信众及上层政府的支持而进行的判教,他们背后很大程度上是争夺社会资源,提高自我集团的实力,扩大自已教团影响而进行主动行为。
二
就内容来说,两地佛教的教派判教内容都体现对印度佛教教理思想的融合创新。藏传佛教各教派判教思想的融合创新一方面体现在对显密宗思想的关系安置上。由于后弘期的藏传佛教直接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发展脉络,受这一时期印度佛教密教化进程影响,使得藏传佛教各教派在教法思想的判释上都有对密宗思想的安列。同时,各派都以自已的理解,通过判教的方式对显密思想的关系作了整体的表达,由此构建出了显密宗思想的统一关系,体现出了这一时期各教派在处理显密宗关系上的融合创新。另一方面体现在各派特殊教法思想的构建上。后弘期的各教派通过判教,都对印度佛教教理思想的进一步融合,宁玛派的“大圆满”见内涵是中观、唯识、如来藏佛性融合的产物,觉囊派的“他空”见也是,格鲁派虽然以中观应成为纯正见第,而不承认胜义佛性的存在,但也认为佛性可以作为方便施舍对众生进行宣讲,并且该派也自称其思想是对中观甚深见和唯识广大行的融合,藏传佛教的其它各个教派也都如此。这种融合思想所构建出的藏传佛教各教派特殊教法,对中观、唯识、佛性思想在自派思想中位置的安置定位都体现了藏传佛教各教派判教思想中的创新特质。
就汉传佛教各教派判教思想融合创新性来说,其融合创新性一方面体现在对之前的学派判教思想的融合性吸收,隋唐时期所形成的教派判教思想都是在批判南北朝时期涅槃、成实等学派以“时”为线索的判教以及地论等学派以“宗”为标准的判教基础上而对这些判教类型进行了融合,由此形成的有着自己判教原则、方法和范围的系统化理论化的判教体系,开创了有隋唐宗派特色的判教理论,体现了各教派创新意识。另一方面体现在汉传佛教各教派间判教思想的相互融合与创新。如天台宗判教思想的“化法四教”是对三论宗“三法轮”思想融合创新的结果,而华严宗的“五教十宗”也是基于对天台宗“五时八教”判教思想的融合创新,另外,各派对“道统”体系的构建*隋唐佛教的各教派都构建设有各自的“道统”体系,如三论宗建文殊师利—鸠摩罗什—道生—昙济—河西道朗—摄山僧诠—兴皇法郎—吉藏的“道统”体系,禅宗的“六祖”之说等等,这些“道统”体系,在南北朝时期是没有的,只是到了隋唐佛教的教派时期,各教派在判教思想指导下模仿隋唐世俗社会的宗法社会体系而建立起来的,可以说这是当时隋唐教派佛教的创建。,对民众信仰的迎合等等*如天台宗经过判教认为《法华经》是最高的经典,为了让民众便于理解,符合中国人偶像崇拜的习惯,他就特别崇奉《法华经》的观音菩萨,并以推崇念观音,塑观音像的形式来推广自己的宗派,使该派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大大提高。,则都可以说是在各派判教理论指导下的内容的创新。
当然,两地在教派时期的判教思想的内容在存在着诸多不同。藏传佛教的判教思想是以继承印度佛教的晚期的宗义判教思想为主干,继而对经典、众生根器进行判释论说的,而汉传佛教则主要是以对经典的思想判释为主干的,对宗义思想的认识没有涉及;在认识原则上,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判教都是以中观缘起论为认识原则而进行的构建,并以学院式的层层分析,将中观思想以下的思想作为见修的次第予以整合及深化,而汉传佛教的教派是以如来藏本体论及佛性清净本觉的心性论为认识原则,以“时”判或“义”判的安置方法,通过对较次理论的延期和超越来排列来凸显自派所尊的主体宗教境界的高下;并且,藏传佛教中教派的判教都重视对显密思想的认识,其不同的印度佛教源流传承,使藏传佛教各派将判教的落脚点很大程度是对为进一步的次第修行作准备的,因此其判教思想很大意义是对修行的学僧来说的,对于普通信众或其它因素反映的较少;而汉传佛教由于面对的是同样一部分经典,且由于佛教是在儒道文化都很强大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发展的现实,这使的教派判教思想除了论证自派所崇经典的高妙的前提下,还有进一步吸引普通民众信仰,迎合政治支持等目的,这些在佛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藏地,是不用考虑的。
三
两地教派佛教的判教思想促进了佛教的本地化进程,对于两地的政治 文化者产生了重要影响。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判教影响体现在:(1)宗义判教深化了对宗义内涵的认识,系统化地指导了修学。在藏传佛教后弘期时的各教派在论述自派所理解的宗义的同时,都指出了它的次第性,并将其明确为自派修学的所依,如宁玛派在论述完“九乘”判教思想后就说:“九乘次第中各各层次,绝非宣示互相矛盾之理论,或引得不同果位:彼等实为修行道上之过程而已,能直接或间接令(行者)证悟而成正等觉。因修行人根器利钝不同,部分行者须由层次较低之次第起修,依其证量逐级而上。于某一次第娴熟后,再进而修习更高次第。有等利根行者,因夙生之业力,能直入最高次第,如无上瑜伽,甚至能即身而得佛果。是故,引导天赋极高之人自普通教授起修,固为浪费生命、精力及机会;反之,(钝根者)由较高次第之教授起修,不独无所利益,兼且实为错误。因此,欲入各别修习之门,重要在量力而为,及能得睿智上师指导。”[2]43格鲁派也说:“上上宗派能破下下不共之诸宗派,然了知下下宗之见,是为了知上上见之便。是故,纵取上上宗派为胜,亦不应视下下之宗派”[3]347-348等等,藏传佛教其它教派也都相似的论述。因此,藏传佛教的每一教派多是以自派的不同理解来指导具体的修学,而通过判教藏传佛教各派所明了的“见次第”修学体制,有力地指导了学僧的修学,其构解出的佛教境界次第观对于深化佛教教理思想认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对于每一个学法者的影响可谓是终生的。(2)对经典的判教有力地促进了对佛教经典内容的多方位认识了解,这一方面对藏地本土宗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加速了本教的理论化进程。另一方面通过判教对经典的论证,藏传佛教各派的教法思想在显密方面都有了印度佛教理论的支撑,从而起到了良好的教证作用,也使藏传佛教各派的核心教理如“大圆满”、“大手印”、“他空见”等成为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一面旗帜,达到了教理与教派的相统一,维护了藏传佛教各教派作为一教派的个性。而藏传佛教后弘期藏地本土宗教本教在藏传佛教的压力下开始的本教佛教化进程,所产生的对大量佛教经典的本教化改造,如将佛教经典《广品般若》改为《康勤》,《二万五千颂》改为《康穹》,《瑜伽师地论》的《抉择分》改为《本经》,《五部大陀罗尼》改为《黑白龙经》等以及佛教名词的改造,则最终实现了本教在这一时期教派化。(3)对根器的判释,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信众,最终促使了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各教派将学佛者进行上、中、下三层次的划分,并用简单的语言对普通民众进行宣讲,由此将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划分为下等根器中,使他们安于现状,忍受欺凌,不予反抗。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极少数的上层僧权集团被划为上等根器者,则成为享受特权者,由此促使的世俗权力向上层僧权者的集中,而最终发展成为政教合一的制度,应该说是很有必然性的。
汉传佛教的教派判教影响主要体现在:(1)汉传佛教各教派的不同判教形式和理路,丰富了中国佛教的认识路径。三论宗构建的“五双十教”判教理论体系,天台宗构建的“五时八教”判教理论体体系,华严宗构建的“五教十宗”等等,都依各自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佛教思想内涵进行的判释性认识,加速了佛教中国化进程,展示了中国佛教学者的自主意识,影响了后期汉传佛教发展的理路。同时,教派判教思想的构建,进一步维护了各教派的独立性。各教派通过组织自派的判教思想,一方面对同一时代的其它教派思想进行了统摄;另一方面汉传佛教的教派判教思想的表达,使各派的根本教法义理得以阐释,突显了自派所崇的经典及教法,以此于其它派别区分一开来,展示了自派的独立。(2)教派判教所表现出的批判性,加速了汉传佛教各教派间的整合。如天台宗和三论宗都崇《法华经》,但天台宗的建宗判教主要是在批判三论宗的判教思想上建立起来的,由此加速了三论宗的衰落及天台宗的兴起。华严宗和唯识宗同主“有宗”,而华严宗可以说也是在批判吸收唯识宗有关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也间接促使了唯识宗的衰落等等。隋唐时期其它教派的兴起也多是建立对之前教派思想的批判吸收基础上的,由此汉传佛教八大教派兴衰所显示的时代性,可以说很好地展现了汉传佛教各派间判教思想所具有的批判性整合力。(3)判教所表现出的思想性对中原地区社会主体文化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传佛教的教派几乎都是以对“佛性”的构建来作为判教的标准④,以此对佛性思想的推崇,对后来汉地宋明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程朱理学吸收真如佛性构建了“天命之性”的本体论思想,借鉴佛性中生死流转思想而构建了“气质之性”思想,还将佛性论思想中转迷开悟、定慧双修的宗教修行理论与实践改造为格物致知、居敬穷理的人性论修学方式等等,这些无不对宋明理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两地佛教判教思想的影响也有许多差异。汉传佛教的判教思想与教派的建宗可以说是具有一致性的,即所谓的“判教即立宗”。这使得汉传佛教各派的判教思想成为各派立宗的宣言,而在面临共同经典的条件下,判教理论成了各派对之前教派的所尊经典进行批判,进而确立自派所宗经典的权威一重要手段。而藏传佛教的各教派的形成通常来说是以寺院的建立为标志的,以寺院为标志而建立起来的教派在教法思想上的构建都是在各派各自传承的指导下进行的,系统判教思想的形成应该说和建立宗派并没有很大的一致性。另外,藏传佛教的教派判教所走的是构建性的路径,这使它们的判教对于内部僧人的学修有更大的意义,对于普通民众的决择具体信仰、认识教派差别,实际意义并不太大。汉传佛教的判教走的是批判性的路径,这种批判所促使的与其它教派之间的争鸣性交涉,对于当时汉族民众的教派决择起到了重要作用。还有,就影响程度来说,藏传佛教通过判教,所形成的藏传佛教文化,几乎构成了藏传佛教文化
的全部,由其发展而形成的政教合一制度,可以说将教派与政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在汉传佛教中是没有的。
总之,藏传佛教的教派判教与汉传佛教的教派判教,佛教思想在两地进一步实现本地化后,佛教学者基于对佛教思想认识深化后对佛教思想的整体表达,体现了两地佛教教派的自主意识和创新特质。他们的判教思想,相似性源于两地佛教对印度佛教的秉承,而其诸多差异,除因与它们各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具体不同、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各异有关外,更与这两大佛教系统与印度佛教的亲疏有关(即汉传佛教所传是经西域佛教过滤后的印度佛教,藏传佛教则直接受传于印度佛教)。他们在判教理论上的各自构建,充实了两地佛教的思想内容,在两地佛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陈庆英等,译.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
[2]义成仁波切.九乘差别广说[A].许锡恩,译.九乘次第论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
[3]二世嘉木样·恭却晋美旺波.宗义建立宝鬘论[A].班班多杰,译.藏传佛教思想史纲[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张林祥]
①王仲尧博士在其博士论文《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中说:“佛性成为中国佛教所有理论的根本归宿,成为中国佛教的价值本体问题。它是所有佛教理论的价值标准,当然也是判教的标准。”(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1998年,9页)。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Tibetan Buddha’s Teaching——Review Based on Both Buddhist Sect
HE Jie-feng
(InstituteofNationalreligious,Nor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XiAn710000)
Abstract:Tibetan and Chinese Buddha's teaching in the background,contents and effects have similarity, and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their similarities from both uphold Buddhism Indian Buddhism, with its many differences,in addition to the times with their respective specific different backgrounds,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related, and also with the two systems of Buddhism and Buddhist India about intimacy.
Keywords:Tibetan and Chinese Buddhism Buddha’s teaching
[中图分类号]B9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6)02-0063-04
[作者简介]何杰峰(1980-),河南伊川人,西北政法大学民族宗教研究院研究人员,藏学博士,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藏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2016-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