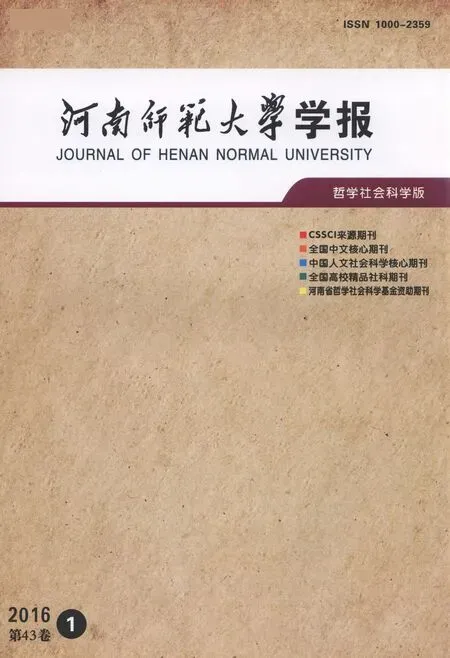语图互文修辞的理论基础及其策略
段 德 宁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语图互文修辞的理论基础及其策略
段 德 宁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互文”作为修辞学术语表明了“语图互文”这一概念所内含的修辞学视角。语言在古典修辞学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但这些修辞思想中却始终伴随着图像的幽灵。无论是中国修辞的“言象意”传统,还是西方的艺格敷词概念都存在着对于图像的修辞学关照。在当前的图像化时代,符号学的观念要求建立超越语言的修辞学研究,图像的符号学发现则昭示了图像表意的修辞可能性。语言修辞和图像修辞的结合共同结构了语图互文的修辞学维度,作为一种跨越符号媒介的转换,这种转换所带来的表意差异塑造了语图互文独特的修辞策略。
互文;语图关系;图像修辞;跨媒介转换;张力
“语图互文”意即语言文本和图像文本间的互文性关系,两者既可以共存于同一物质载体,如中国传统诗画、小说插图,也可以存在不同的载体,如文学及其改编电影。虽然语图互文现象十分普遍,但对其学理上的研究,直到近年来才在一个更深入的层面上展开,尤其是将修辞学引入到这一现象的研究中。在中国语境中,“互文”也就是“参互成文,合而见义”的意思[1],本身就是一个修辞学概念。而在西方语境中,美国学者弗兰克·J.德安杰洛(Frank J. D’Angelo)在《互文性修辞》中考察了互文性的修辞策略,并鲜明地将电影、广告、视觉形象等图像性对象包含在内[2]。因而在不同语境中都存在着将修辞学引入语图互文研究的重要契机,但是,这样一项研究仍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传统修辞学以语言作为其核心对象,图像作为不同的符号系统,是否可以纳入到修辞学的理论视野。简言之,也就是图像修辞如何可能。当从学理上确立了图像修辞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探讨语图互文的独特修辞策略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传统修辞学中的图像之维
在通常的理解中,修辞学无疑是和使用语言相关的学问。当人类获得语言能力,进而可以言说之时,如何利用语言更好地表情达意,建构人与世界的联系就成为必然要面临的问题。但是,无论中国传统修辞思想,还是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修辞学理论,都无法排除图像幽灵对语言使用的影响。
在中国,“修辞”一词最早见于《易传·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3]18虽然对于“修辞立其诚”解释存在分歧,但是查屏球通过详细的考证指出,这里的“辞”“作为解易之论,首先应是指占卜之辞”。因为在《易传》形成的年代,“个人著述”并不普遍,“以‘易’为代表的卜蓍之作”构成了最早的著述活动,“故此处所论修辞之事首先应当是指与此类活动相关的与神对话之语”[4]。就此而言,所谓“修辞立其诚”实则是虔诚地与神沟通,并将天神之意诉诸语言,形成卜辞的过程。众所周知,《周易》中无论是卜辞还是爻辞,其实都离不开相应的“象”,也即所谓的“卦象”、“爻象”。
因此,更进一步讲所谓“修辞”就是通过“象”显明“天地神人之意”,再通过“辞”表达“象”的过程。
这就关涉到“象”在这个表意过程中的必要性。《周易·系辞上》中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3]342-345同样,王弼在《周易略例》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5]就占卜之辞而言,这里的“意”并非一般人通过语言表达的个人观念和意志,而是天地神人(指圣人)所传达的自然观念和神秘意志,对于后者古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最为合适的表达。语言作为确立人类自觉存在的能力,其本身是与自然万物、天地神鬼相异质的事物。古人描绘仓颉造字时就出现了“天雨粟,鬼夜哭”的景象。张彦远释曰:“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6]可见,语言文字的创造实则将人类与神鬼造化的隐秘遁形分割开来。这种发展无疑是人类文明之必然,但在人类社会早期,仍需要某种中介来联结语言与自然神怪的神秘意志,那就是“象”。
与语言相比,“象”与自然万物之间拥有更切近的天然关系。《周易·系辞下》言:“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卦象本身就意味着对自然和社会事物的模拟和仿像。从自然与社会对象中脱胎的卦象可以说呈现出双重的特性:相似性和抽象性。相似性既意味着卦象本身的具象性,同时,也意味着卦象的变化类似于自然社会的运动发展。而卦象本身毕竟数量有限,所以它本身还具有某种抽象性。卦象的双重特性使其既模拟了自然万物及其变化,又抽演出其中的某些分类特性和变化原则。正是如此,“象”作为表意的手段,既连接着和人类血脉相连的自然,又向人类昭示着规律变化的存在。相较而言,作为内在约定俗成的语言,本身相异于自然,也并未显明地展示自然的规律性。实际上,直到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才从根本上展示了语言自身的共时系统性,但这与自然的系统性却是大异其趣的。
正是因为“象”与“言”的特性差异,在中国早期的夏商周社会,“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成为重要修辞达意策略,不独《周易》典籍本身表明这一点。第一个例子就是与《周易》具有同样卜筮性质的甲骨文卜辞。古人在龟甲或是牛肩胛骨上钻孔炙烤,以便形成被称为“兆”的裂痕,进而根据裂痕形成占卜之辞。按照李壮鹰的解读,这些龟甲牛骨上的“炙纹作为‘天意’的显示,是甲骨所真正承载的东西,而它之外的卜辞,不过是对它的辅助性的说明而已。”[7]也就是说,这种“兆”之“象”构成了卜辞传达天意的中介。另外,约略同时的青铜器铭文也存在着相似的表达语境。巫鸿就曾指出中国古代青铜器实为礼仪之物,并且常放置于宗庙这种祭祀祖先神灵的地方,因而这种礼器也同样存在着与神对话之意。《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8]青铜器,尤以青铜礼器而言,它本身就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物象,同时又都铸有不同的物象纹饰。因而,刻有铭文的青铜器也就成为象与言合一的统一体,共同传达出与神的沟通之意。
由上述事例观之,“修辞立其诚”这一“修辞”概念的源起,具有特定的历史语境,那就是由天地神人之意到象,从象再到言或辞的特殊表意场域。无论是《周易》蓍卜之辞、甲骨卜筮之辞,还是青铜器铭文,都是与神沟通对话的言辞,这些言辞本身都以“象”为中介或是伴随物。这种“象”为“辞”先,“象”“辞”共用的表意方式,还影响到书籍的撰写方式,郑玄在《通志》就指出:“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9]长沙考古发掘出的子弹库楚帛书就是典型的“图书”并置,而《山海经》等古代图书据考证也应是配以图像而存在的。这一系列的视觉化的“象”对于言辞可谓不无影响,而这种“意象言”或者说“意象辞”的表达模式却从更深层面影响着语言修辞自身的表意策略——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诗经》所使用的“兴”的手法。
在《诗经》的研究历程中,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可谓影响广泛:“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10]。有关学者根据朱熹的注解统计出,《诗经》全书共1142章,用赋共727处,用比共111处,用兴则是274处,两者方法皆用的有29处[11]。可见赋虽然最多,却只是直陈其言,真正具有修辞技巧可言的是“兴”,其所占比例甚至超过了现在常见的“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审视“起兴”之诗所处的言辞表达语境。
日本学者家井真在对《诗经》的原意研究中,认为其中的兴词最初是由咒谣发展而成的咒语,与古代礼仪习俗密不可分,而随着礼仪神圣性的消失,这些礼仪所用的咒谣便成为形式化的咒语,并在不断地传唱之中变为“兴词”之诗。因而,《诗经》中许多与鱼、花果草木、渡河等有关的兴词都具有礼仪祭祀的特定内涵[12]。由此观之,“起兴”之诗实则与上文所举《周易》等例子中的言辞表达有着相似的语境,并且具体而言,这些诗也与《周易》的某些卦爻辞有着相似之处。首先,卦爻辞在对卦象爻象的解释中多言及一些物象,并借此引出表示吉凶祸福之语,如《乾》卦以龙为物象,《渐》卦以鸿为物象,《大过》言及栋梁、枯杨,《鼎》言及鼎,《剥》言及床等等。这种以物象来言说的方式与“兴”的表意结构非常相似。其次,卦爻辞通常还会通过物象的变化来表达不同含义,如《渐》卦分别用“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陆”来表达六爻所不同的爻象,并引出不同的结果,这种情况也同样在“起兴”之诗中有所表现,如《殷其雷》中,以“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殷其雷,在南山之侧”、“殷其雷,在南山之下”来起兴不同的章节。
通过这两者的比较可以看出,《诗经》中的“兴”其实也是“意象言”或者说“意象辞”表意过程的延伸,只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象”不再是视觉可见的对象,而是由语言所指涉的“物象”,换言之,就是某些特定的“语象”。实际上,在“比”的手法中也存在语象的使用,但“兴”却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那就是起兴之语象与随后的言辞看似没有直接的联系。这一点就在于“象”在当时的语境中是可以传达天地神人之意的中介,与言辞之间仍有着巨大的差别。但这种差异性并没有得到持久的延续,当这些“象”从可见对象变成语象时,象的中介性质便慢慢消失,其结果也就是“兴”在以后的文学样式中便隐而不见,“比”这种语象使用方法得以承续。究其根源,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与天地神人沟通的语境已经逐渐改变,另一方面则是语象在语言中建立起了约定俗成的内在意义,“象”在“辞”中获得了特定的表达关联性。所以说“兴”的消隐,实则可以说是语言对于“象”的某种收编。
在中国传统修辞的渊源中,由视觉之物象到语言之“语象”,象经历了一种语言的改制,被语言之经纬所规训,同时,象也成为语言描述之内在枢纽。与之相比,西方的修辞概念略显不同,修辞在古希腊语境中“特指公共演说的公民技艺”,并且作为一门系统的学问,特别诉诸语言的逻辑力量。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研究中,以三段论为代表的逻辑力量成为言说的基础。但是这却没有彻底取消“象”在修辞语言中的某些作用。在探讨隐喻、对比、生动等语言技巧时,亚氏指出这些表达的重要效果就是让事物“呈现在眼前”[13]。
事实上,正是为了鲜活地将对象呈现出来,艺格敷词(ekphrasis)概念非常早地出现在一些古希腊修辞学手册中。根据古德黑尔的考察,早在公元一世纪塞翁给出了这个词的定义,即“艺格敷词是一种将事物生动地展现在眼前的描绘性言说。”更进一步地讲,这个词又可追溯到与亚里士多德相关的“生动”(enargeia)概念,即使事物可见的能力。按照塞翁的看法,“生动”也就成为“艺格敷词的特质”之一。按照古德黑尔在修辞学层面的分析,艺格敷词的“生动”特质就是要创造一种“幻想”(phantasia),从而促动听者“最深层次的情感”,并且这种“视觉化”带来的惊奇,“取消了事实”,从而使听者“盲目”[14]。从当时的历史语境来说,艺格敷词诉诸“视觉化”来使听者进入到“盲信”的地步,是与当时的法律诉讼、公共演讲等实用目的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映了古希腊重视视觉的哲学思想,这种“视觉的盲见”无疑会让人想到柏拉图著名的“洞穴之喻”。
因而,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言象意”的语言表意路径,还是西方在逻辑之下强调视觉化、生动化的表达对象,都是“象”在语言表达,或者说语言修辞中重要性的体现。虽然这里的“象”或是物象、或是图象、或是语象,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图像,但却是图像修辞达意之滥觞。一方面,“象”表明了传统修辞即使局限于语言,但却暗含着重要的图像之维,成为修辞达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被语言表意所收纳的图像要素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中,也必将寻求自身新的独立。
二、图像修辞研究的当代勃兴
上世纪六十年代,罗兰·巴特就提出了图像修辞概念,已经宣告了图像修辞的某种理论自觉,但是,这一思想的兴起却有着众多的时代背景。从物质层面来讲,19世纪中期发明的照相术,使图像的生成技术获得了极大的革新。这种变革带来了20世纪本雅明称为机械复制时代的图像生成方式。正是图像的增殖使得海德格尔提出世界被把握为图像,德波将当时的资本主义生活称为景观社会,这无疑是审视图像的当代语境。但是这只是构成了图像修辞勃兴的大背景,真正引发这一观念的则是诸多的思想资源。
美国哲学家皮尔士在19世纪后半期就开始着手建立一套统一的符号学体系,力求将所有符号进行一种系统的划分与归类。众多周知,皮尔士提出了不止一种符号分类的标准,这些不同的分类相互联结又会形成更细致的符号种类[15]。但其分类的基础一般都建立在“符号(Sign或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解释项(Interpretant)”的三元结构之上。正是根据这三个要素皮尔士将学号学科学分成了三种分支:
第一个被邓斯·司各特称为思辨语法(grammatica speculativa)。我们可把它叫作纯粹语法(pure grammar)。它的任务就是确定每个科学理智使用的表象必须符合什么条件,以便表象能够体现任何意义。第二个就是逻辑学本身。它是一门关于任何科学理智的表象近乎必然要符合什么条件,以便表象能够很好地把握对象,也就是说表象为真的科学。换言之,逻辑学完全就是关于表象为真之条件的形式科学。第三,模仿康德在发明新概念名称时保留与词语原有联系的方法,我称之为纯粹修辞学(pure rhetoric)。它的任务是探明在每个科学的理智中,一个符号产生另一个符号的法则,尤其是一个思想产生另一个思想[16]99。
按照皮尔士的划分,纯粹语法针对的是符号表象本身,符号表象如何体现意义;逻辑学本身着眼于表象和对象之间如何构成真值关系;最后的纯粹修辞学则关注解释项,关注符号生产的法则。在这里,皮尔士的划分绝不单单针对语言符号而言,它也包含图像符号。当从纯粹修辞学的视角来审视图像时,它所关注的既不是图像本身,也不是图像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是图像如何形成新的符号和思想。因而,当图像符号具有了解释项,从而形成新符号时,它必然同传统修辞所关注的语言一起,成为纯粹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正是出于这样相关的考虑,皮尔士模仿康德的方式命名了新概念。
当然,除了这种基础性的符号学分支划分,皮尔士更广为人知的是对于符号的一种三分法:象似符(icon)、指示符(index)和象征符(symbol)。这种划分的关键在于符号及其对象的关系。象似符在于符号本身就具有对象的某些特征,尤其是图像具有这方面的显著特征;指示符的符号与对象有着存在性的关系,它不需要解释项的存在;象征符则需要解释项的存在才能有效[16]101。一方面,皮尔士针对象似符,对其中的一部分再次划分为:形象(image)、图解(diagram)和隐喻(metaphor);另一方面,他也指出:“每个象征符在其起源上,或者是所指涉理念的形象,或者是可以唤起对于某些个别事件、人或物及其意义之回忆的相似物,或者是一个隐喻。”[17]这实质上指出了不论是建基于符号与对象的相似性,还是植根于解释项,符号都可以形成隐喻性的修辞表达。对于这样一个问题,赵宪章就曾指出:图像符号本身遵循“‘相似性’原则”,“并被严格限定在视觉的维度,从而先验地决定了它的隐喻本质。”[18]
索绪尔基于语言学而建立的符号学,与皮尔士的理论体系有着显著的差异,但也为图像修辞思想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思考共时语言学中各种语言要素关系时,索绪尔提出了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种,前者是语言要素根据连续顺序组合在一起,后者则是通过相似的形式或意义联想性的聚合在一起[19]。受此影响,雅各布森基于相似性混乱和毗邻性混乱两种失语症,系统阐释了符号表达的隐喻模式和换喻模式。这样一种结构分类不止在语言中具有意义,在整个符号领域都有其分析价值,因而,雅各布森本人也立刻将隐喻和换喻的划分运用到诗歌、绘画、电影等不同领域的探讨中[20]。这其实是在符号学的理论体系中扩展了隐喻和换喻的概念内涵;转换一个角度来说,这同样也表明了传统修辞学有着超越单纯语言符号的要素以及进行理论革新的可能性。
同样基于索绪尔的符号观念,罗兰·巴特在广告图像的分析中提出了“图像修辞”的概念。首先,他指出照片本身是一种悖论性的讯息:一方面,照片本身与对象是一种完全相似的关系,这种完美的相似使得照片与对象成为无编码的讯息(message without a code),巴特也将其称之为外延讯息;另一方面,照片同样也存在处理手段、风格化等人为因素,这构成了照片编码的讯息(message with a code),或者说是内涵讯息。正是这两种讯息形成了照片讯息的悖论性存在。实际上,从皮尔士对于符号的分类来看,巴特的分析实际上是指出了照片兼具象似符和象征符两种性质的可能。照片作为象似符只需要与对象的相似性,而当它成为象征符就要求了解释项的存在。可以说在皮尔士三元的符号结构中清晰了划分了照片的这两种区别,但是索绪尔的二元符号结构非常关注于符号的阐释编码,照片依据相似性存在的讯息只能成为悖论性的要素。
正是基于对照片的分析,罗兰·巴特在《图像修辞》一文中将广告图像分成了三个部分。“语言讯息”在广告中发挥着锚定和接替的作用。“外延图像”则是没有编码的讯息,它通过“空间的直接性和时间的在先性”展现了事物,从而形成了“真实的非真实”[21]44。最后的“内涵图像”构成了与修辞学相关的内容,因为图像的内涵所指在他看来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域”,图像通过其内涵能指来指涉意识形态,不同的能指就是不同的内涵因子,而对于内涵因子的选择与设定就构成了所谓的“修辞”。当然,这里的修辞在罗兰·巴特看来绝不会只局限于图像,他指出:“存在一个对于梦、文学和图像事例都适用的单一修辞形式是完全可能的。”[21]49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罗兰·巴特其实也具有与皮尔士相类似的符号修辞学观念,但就其所处的时代来讲,单独提出“图像修辞”对于分析广告、电影等视觉文化似乎具有更现实的意义,因此,他不仅用“图像修辞”作为分析内涵图像的小标题,而且又不合常规地将其当做整篇文章的标题。
无论是皮尔士还是罗兰·巴特都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扩展了修辞含义,而潘诺夫斯基作为艺术史家更着眼于图像本身,他的图像学理论虽然没有关于图像修辞的论述,但却同样关心图像的意义阐释问题,而且,他的研究方法也受到卡西尔符号(symbol)观念的影响。潘诺夫斯基将对图像艺术的解释划分成了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分析和图像学解释三个阶段。前图像志描述关注的是对图像自然主题的识别,也就是确定图像所对应的对象、事件本身,这实际上就是在确定皮尔士意义上的象似符(icon)。图像志的分析立足于特定历史条件的文化类型及惯例,分析图像中的故事和寓意,进一步深入到图像的程式主题。事实上,在这一层次的图像已经成为某种指示符或象征符,但是展现这一点的方法在潘诺夫斯基看来仍然只是分析的方法。只有到了图像学解释的层面,才使用了他所称为“综合直觉”的方法,从而揭示图像的内在意义,形成卡西尔所说的“文化象征史”的一部分[22]。图像学所开创的这种深层阐释模式,特别关注图像意义在历史发展中的继承、变异、断裂之处,这事实上就是将图像作为理智的对象去探讨其内在的不同的所指意义,因而意大利学者阿尔甘将潘诺夫斯基称为艺术史中的“索绪尔”[23]。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图像修辞在当代的勃兴,非常重要的理论语境就是图像的符号学发现。皮尔士、索绪尔和卡西尔的符号理论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人们对于图像的认识,使得图像超越了语言的牢笼,成为一个可以占有意义的符号形式。一方面,符号学拓展了隐喻的理论内涵,新的隐喻概念与相似性密切相关,因而,图像与对象的相似就不仅仅再是一种图像识别的感性性质,它本身就内含着一种隐喻的特质。另一方面,符号学促成了超越语言的修辞学概念,如同罗兰·巴特所言,这样一门修辞学必将致力于探讨文学、梦、电影等符号通用的修辞形式,此外,这门修辞学也必将允许存在着专门的图像修辞来深究图像符号特有的修辞策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图像修辞的提出既归功于符号学对于修辞学的影响,又在于修辞学自身就有着超越语言符号的潜力。从传统修辞无法摆脱的图像之维我们就能看到,修辞学本身不仅是语言的技巧,它更是人类表情达意的实践方法。因而,那些被语言所赋义的视觉对象,终归会因为图像化的存在而获得某种的修辞学意义。
三、语图互文:跨媒介转换的修辞策略
如上所述,图像修辞思想的提出,其实意味着一种超越传统语言符号的修辞学观念。无论是皮尔士还是罗兰·巴特提出的符号修辞学模式,都是从总体符号层面进行的修辞学探讨。同时也存在着针对文学、图像、梦、电影等不同符号类型的具体修辞策略研究。但即使拥有了这两个层面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方面尚未涉及,那就是跨符号类型间的修辞性关系。语言和图像无疑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两个符号系统,两者之间的转化与联结,也即语图互文的现象,也就成为这种研究的典型代表。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不同的符号媒介,跨媒介转换成为语图互文修辞策略的基础。
一方面,图像作为一种视觉性信息,很显然地是,语言描绘无论怎样详细,也难以达到观看所得到的细节内容和直观感受。有关研究表明,大脑所接收的信息有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剩下的6%来自其他感觉,视觉是人类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24]。相比于图像的直观性,语言的指涉或描绘只能是有针对性的,这种语言的加工过程其实就是一种修辞的过程。语言总是通过语象的描绘来试图营造图像的“视觉性”,但语言本身的“听觉性”意味着自身对图像的言说总是一种“强喻”,一种强行将对象表达出来的修辞方法[25]。
另一方面,从语言到图像的转变过程,也同样可以称为一个修辞化的过程。英伽登在讨论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时,指出“文学作品本身是一个图式化构成”,存在着多个可划分的层次。每个作品在“被再现的客体层次和外观层次”都内在地包含着“不定点”,每一次阅读,作为一次具体化行为,都意味着对这些“不定点”的消除或“填补”[26]。虽然转化为图像的语言并不都是文学作品,但是这些语言相对于图像这种“具体化”也是具有“不定点”的。语言本身作为对图像的“强喻”,就不能完全的表达视觉性的图像,当反转这一过程时,图像对于语言的每次具体化都伴随着一个主观的“填补”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意味着图像对于语言的表达其实也是一个修辞过程。
不同媒介符号的转换从本质上确立了语图互文的修辞性关系,这样一点从根本上决定着语图互文所采用的一些具体修辞策略。雅各布森提出的隐喻和转喻手法同样存在于语图互文之中,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一些更具体的修辞方式。罗兰·巴特也曾在广告图像的分析中,指出文字讯息具有锚定和接替的作用,但是这局限于某些语图互文现象之中,并不能系统地代表所有的修辞手段。事实上,详细确立具体的修辞手法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尝试根据语言表意、图像表意和综合表意的区分,将语图互文的修辞策略分为几个类型:
1.合力性的修辞策略
所谓合力性的修辞,就在于语言、图像以及语图互文三者所表达的意义相一致。这样一种情况在现实运用中可谓最为普遍,无论是新闻及其图像、广告文字及图像,还是历史插图、艺术插图等等,都主要是确保语言、图像以及最后表意结果的统一。这种修辞策略的内在诉求就是对真实的表达。一方面,这种真实可能是指符号与现实之间的真实对应性,就像是新闻图像及其文字中那样,两种符号都意图表达真实情况,所以意义表达相统一,又由于两者跨媒介的印证更加强了新闻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这种真实也可能只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转换真实性,众所周知,许多广告本身并不一定真实代表现实对象,但是广告文字和图像之间却是要表现出统一性,否则这种内在的不一致从根本上取消了广告的有效性。合力性的修辞又可视语言表意和图像表意的比重分为两类。一种情况是两种符号在表意分量上相对均衡,两者之间就可视为一种摹写性的修辞关系,古希腊所言及的艺格敷词就可视为语言对图像的摹写。一种情况则是两者之间比重相差较大,这样就构成了一种赘述或简描的关系。
2.张力性的修辞策略
当语言表意和图像表意存在一定的差别时,二者之间就可能构成一种张力性的关系,而语图互文的综合表意就产生于这种张力性的关系中。新批评理论家在分析文学语言时,曾对“张力”问题有过深入探讨。瑞恰慈曾在《修辞哲学》一书中分析了“本体”与“喻体”的具体关系,进而指出:“当放在一起的两个事物相差越远,被创造的张力当然也就越大。”[27]当张力问题只存在语言之中时,关键在于两个语象间的距离差异与联系,而在语图互文中时,语言和图像作为跨媒介的转换,本身也容易形成张力性的关系。这种张力的存在不仅在于两种符号表达对象之间的差距,也来源于跨媒介转换造成的理解距离。事实上,这种张力性的语图互文更能实现某种审美的表达效果,所以它有时是文艺创作活动的自觉追求。比如,徐渭创作的《墨葡萄图》,一般而言,中国文人画是先绘画后题诗的,纵然不论徐渭这幅画的创作顺序,单就欣赏来说,我们最先看到也应该是墨葡萄的视觉形象。当我们继而阅读题画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力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时,却可以发现诗歌的意义又指回了画面本身。“闲抛闲掷野藤中”自是和画面中的“野藤”形成了合力性的关系,“笔底明珠无处卖”却与画面中的“葡萄”构成了张力性的存在。单单在语言中表达“明珠如葡萄”或者“葡萄似明珠”都没有什么“张力”可言,但语言中的“明珠”闲抛闲掷成了画中的“葡萄”却是具有极大的变化张力。更进一步讲,画中视觉化的“葡萄”本身就作为绘画具体存在的一部分,其实就是对整幅诗画作品在视觉上的“借代”,真正构成隐喻两极的是“明珠”和“诗画本身”。这种特殊的修辞策略是单纯的语言文本所难以表达的。
3.悖论性的修辞策略
当语图互文的双方在表意张力走向极端时,一方所表达的意义就可能否定另一方的意义,从而构成了一种悖论性的表意策略。有时这种悖反的关系仅仅存在于符号之间,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反问、反讽等类似的修辞效果。许多讽刺性漫画就可能采用这样一种手段,例如,漫画的标题可能是“为了和平”,但图像内容则是某些国家侵略他国,给他国平民造成伤害。关于反问效果的一个典型例子则是马格利特的《形象的背叛》,这幅画十分逼真地画了一个烟斗,但在下面却写了一句法文:这不是一只烟斗。虽然画面看似简单,但这幅画却引来相当多的解读。福柯认为在西方传统的绘画准则里,图画都是通过相似性达到一种“确认”,而马格利特的这幅画则通过下面的语言揭示了这种确认的不真实[28]。赵宪章也指出这幅画中语言对于图像的解构正在于语言是一种强势符号,图像则是一种弱势符号,两者在相互转化中的地位并不相等[29]。
以上的解读都可说切中要点,而从语图互文修辞的角度审视这幅作品似乎可以提供另外一种解读的视角。通常人们也是先观看到这幅画作的视觉形象,也即一只烟斗,进而才阅读到文字部分“这不是一只烟斗”。就像前面的《墨葡萄图》一样,马格利特的这句话同样地又把我们带回到图像本身。只是不同于前者那种张力性关系,后者的图像和语言立刻呈现为一种悖反关系。正是在这种悖反中语言的强势促使了人们对图像进行了反思甚至是否定,这样一个表达的效果我们其实可以类比为修辞中的“反问”,换言之,这幅作品只用文字其实可以改写为:“图像中的烟斗也是一只烟斗?”在《形象的背叛》中“图像中的烟斗”已经变为直接的视觉形象,一个反问句式也直接变为否定句:“这不是一只烟斗。”但相比于直接的反问句表达,马格利特的作品经过语图的跨媒转换过程,观者也就经历了对图像的肯定,语言的否定和对图像的否定。这种跨越符号的悖反关系,借用符号之间强弱之势,最终构成了一种反问的修辞效果。一旦我们将马格利特的绘画理解为一种“反问”,那么就可以联系到保尔·德·曼针对反问的著名分析[30]。依循他的观点来看,虽然语言对图像做出了否定,但毕竟也存在着图像的肯定阶段,而图像的肯定必然会带来语言自身的“疲软”,也即是说图像中的烟斗即使被语言否定,也无法根除它在图像中是一只烟斗。这种反问的内在矛盾也正是德曼所强调的修辞学内部的矛盾。
当悖反性的语图互文表意不止发生在符号之间时,就加入了表达对象的标准,那么两种悖反的符号表意就会形成一方否证另一方的效果。如果说刚才反讽、反问的悖反只是源于符号间的真实性受到破坏,但表意的结果仍然指向了某个所希望表达的意义。那么,否证的悖反性关系则更多地是以对象真实性为依据否定了符号表意的一方。这种对真实的追求也经常发生在日常生活的论证中,或者有人通过图像来证明某些语言描述是虚假的,或者有人通过详细的语言解释来说明某些图像是片面的。传统修辞学作为辩论说服的技巧,这种语图互文的否证性关系当然也是其中的研究内容。
以上三种分类只是从表意问题出发的一种粗略划分,进行语图互文的修辞研究理应存在不同的角度,而且这种修辞研究真正的理论生命力应该来自于对具体个案的深入分析。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诗画传统,还是现代的广告图像、文学改编电影等等都为语图互文的修辞策略提供了充足的分析对象。在具体的分析实践中,一方面跨媒介转换构成了语图互文的基础,这完全可以影响阅读的顺序、理解过程的迟缓、语图之间的张力等等要素,从而最终影响修辞达意的效果;另一方面,语图互文的修辞分析也应该与独立的语言修辞、图像修辞相结合,作为一种整体的分析对象,只有综合分析其中的修辞策略才是语图互文修辞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1]唐松波,黄建霖.汉语修辞格大辞典[Z].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375-380.
[2]Frank D'Angelo.The Rhetoric of Intertextuality[J].Rhetoric Review,2010(1).
[3]王弼.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查屏球.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J].学术探索,2010(3).
[5]王弼.王弼集校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609.
[6]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俞剑华,注释.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2.
[7]李壮鹰.逸园丛录[M].济南:齐鲁书社,2005:8.
[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669.
[9]郑樵.通志·图谱略·索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29.
[10]朱熹.诗集传[M].王华宝,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2-5.
[11]严明.《诗经》精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4.
[12]家井真.《诗经》原意研究[M].陆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32-218.
[13]Aristotle.On Rhetoric[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218-226.
[14]Simon Goldhill.What is Ekphrasis for?[J].Classical Philology,2007(1).
[15]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482.
[16]Charles Sanders Peirce.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M].New York:Courier Dover Publications,1955.
[17]Charles Sanders Peirce.The Essential Peirce: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1893-1913)[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264.
[18]赵宪章.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J].文学评论,2012(2).
[19]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70-185.
[20]Roman Jakobson.Selected Writings II:Word and Language[M].Paris:Mouton,1971:254-259.
[21]Roland Barthes.Image Music Text[M].London:Fontana Press,1977.
[22]欧文·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M].戚印平,范景中,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12-13.
[23]Giulio Carlo Argan,Rebecca West.Ideology and Iconology[J].Critical Inquiry,1975(2).
[24]亚伦·皮斯,芭芭拉·皮斯.身体语言密码[M].王甜甜,黄佼,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7:151-152.
[25]弗里德里希·尼采.古修辞学描述[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3-54.
[26]罗曼·英加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M].陈燕谷,晓未,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10-12.
[27]I.A.Richards.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6:125.
[28]米歇尔·福柯.这不是一只烟斗[M].邢克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37-42.
[29]赵宪章.语图互仿的顺势与逆势——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J].中国社会科学,2011(3).
[30]保尔·德·曼.阅读的寓言:卢梭、尼采、里尔克和普鲁斯特的比喻语言[M].沈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9-21.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1.028
2015-09-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文学图像论(12AZW005)
I0
A
1000-2359(2016)01-0141-07
段德宁(1988—),男,山东济宁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语图关系理论、视觉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