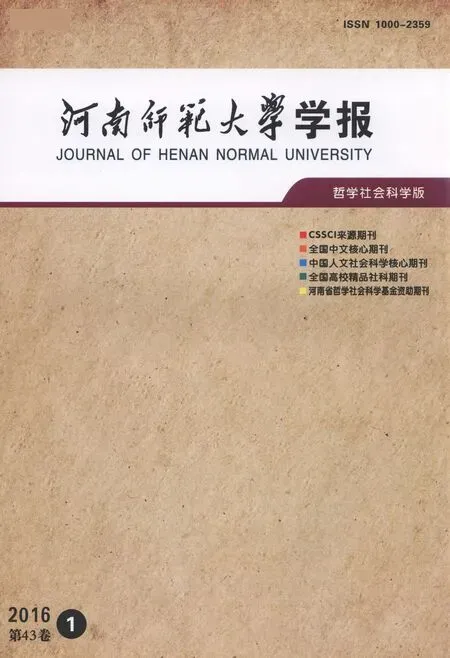霸权与常识:论葛兰西对常识的意识形态批判
李 永 虎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霸权与常识:论葛兰西对常识的意识形态批判
李 永 虎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葛兰西对常识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其霸权理论的重要组成内容。自发性的常识是一种“自在”的意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不同社会集团在文化领域相互博弈的产物,资产阶级维系自身霸权的秘密在于将自身的世界观普世化为民众的常识。知识分子与大众是教学相长的关系,只有将实践哲学和民众的自发哲学结合起来,以一种“社会化”的方式去传播真理,才能真正建立无产阶级霸权。葛兰西的常识意识形态批判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新路向,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统。
常识;霸权;自发性;实践哲学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葛兰西因创造性地提出“霸权理论”而备受瞩目,但人们在研究他的霸权思想时,却往往忽视了他对常识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笔者看来,常识批判不仅构成了葛兰西霸权理论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其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本质的出发点。意大利学者圣图奇(A. Santucci)在《葛兰西传》中提出葛兰西是第一位重视常识并对其予以认真考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在葛兰西的代表作《狱中札记》(以下简称《札记》)中,“常识”一词出现词频则超过120次之多(1971年英译版),并散见于他探讨的几乎所有重大的主题,如霸权、市民社会、教育、宗教、知识分子等。常识概念何以引起葛兰西如此重视?常识与霸权构成怎样的一种关系?知识分子又应怎样看待民众的常识呢?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试作一解析。
一、作为自发哲学的常识
葛兰西要求人们打破这样一种对哲学的偏见:哲学是一种奇怪而晦涩的知识,它只是职业哲学家才能从事的智识活动。相反,他认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世界观的构建,这一世界观反过来又规定了人们实践活动的具体形式。由此,他在《札记》的开篇即提出了“人人都是哲学家”这样一个命题:“每个人最后都会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之外开展某种形式的智识活动,也即,他是‘哲学家’、艺术家和有偏好的人,他持有一种特定的世界观。”[1]9而其所产生的哲学则被称为“适宜每个人的自发的哲学”。这种“自发的哲学”又可划分为三种:(1)语言;(2)常识;(3)宗教、民间传说。较之其他类型,葛兰西认为第二种“常识”,是个体自发哲学中存在的与人及其生活联系最紧密的概念,也是最接近哲学的、能提升人们批判性思维的片段化意识形式。更重要的是,在实践层面上,常识还是一种“社群感”(community sense)——它从心理和感情层面集中反映了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和世界观,并使之表现出相似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在这种意义上,常识成为在被统治阶级中传播最为广泛的意识形态。因此,对常识以一种务实而严谨的态度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何谓“常识”呢?英语“common sense”源于拉丁语的“sēnsus commūnis”,本意为“共同感”。而据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对其词源学的考证,“共同感”最早在苏格拉底所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传统中,原指“雄辩”、“绝妙的讲话”——通过讲话的艺术引起听众的共鸣,但它“决不只是一种修辞学的理想,它也意味着讲出正确的东西,即说出真理”[2]。而至亚里士多德提出知识形式有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两分后,“共同感”被发展为包含一种“对于理论的生活理想的批判”要素。到了近代,苏格兰“常识学派”为修正笛卡尔主体哲学所引发的过度哲学思辨,而倡导日常感觉的原始而自然的判断是认识外在世界的基础。在《札记》中,葛兰西则认为“常识”是“关于民俗的哲学,准确地讲,它总是处于民间传说和专家们的哲学、科学和经济学之间。常识创造未来的民间传说,在既定的时空中,它是大众知识的一个相对不变的阶段”[1]326。并且他还注意到,这是一个“含混不清、自相矛盾而多形态化的概念”[1]423。
首先,就其“多形态化”来说,与“哲学家的哲学”系统而严谨的理论形式相比,常识表现出显著的非体系性和非融贯一致性。“哲学是智识秩序,而宗教和常识都不能成为这样的东西”[1]325。这不仅是指常识在哲学范畴、术语表达方式上的欠缺,更指其思想内容的异质性、多样性。“(它)不是一个在时空上有同一性的个别的特殊观念,它是哲学的‘民间传说’,并像民间传说一样表现出不计其数的不同形式”[1]419。对常识和哲学的此种差别,我们可以通过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提出的“树状的”(arborescent)和“块茎的”(rhizome)两个概念来加以认识。德、瓜两人从后现代解构主义立场出发,认为西方智识传统一直以来是按照系统原则和层级原则(知识的分支)而建构出的一种“树状的”知识体系,柏拉图、笛卡尔和黑格尔都是“树状”思想家的典范,他们都以普遍化和本质化的思维欲图建立一座有着明确中心与层级、并有自我同一性的思想大厦,同时摈弃一切非同一的、异质性的思维。而这些被西方思想传统所排斥的思维正是德、瓜所称的“块茎”,“块茎则是解辖域化线的非层级化系统,它通过随意性的、不受约束的关系同其他线相连接。这些关系形成于一个‘光滑的’无边际的平面之上,而不是形成于一个‘有纹路的’、具有封闭疆界的空间之中”[3]。美国学者斯蒂芬·吉卡梅拉(S.Gencarella)就曾借用“块茎”概念,绘制出了一个常识与其他意识形态关系的模型图[4]。

从该模型中,我们看到,常识处于各种科学的和非科学的意识形式的交集上,并在这些意识形式构成的平面上多方流动、浸染并由此形成自身多样但无同一性的内容。这也是葛兰西为何会强调常识只能被作为一个集合名词来使用的原因,“存在的并不只是一种常识”[1]325。
其次,常识的“多形态化”又直接导出了它“自相矛盾”的特点。这种矛盾性用拉克劳与墨菲的后结构主义术语来说,常识是一种“漂浮的能指”——它并不具有游离于具体历史情形之外的固定本质和意义。比如,民众既有对公正和自由的强烈诉求,但又不乏规训和顺从的意识;一部分人充满了对统治阶级规范的嘲讽和叛逆,而另一部分人则宿命论似的安分守己,自觉自愿地遵守法律和伦理规范。民众行为的这种分裂表现反映出的是,常识“是‘非哲学家的哲学’,或者换句话说,是对各种社会文化环境——普通人的伦理个性就是在其中发展起来的——不加批判地予以吸收的世界观”[1]419。在葛兰西看来,在每一个体进入到意识的世界之时起,就自动陷入到某个特定社会集团之中,而常识作为个体世界观的表达,其内容主要地取决于他所从属的那个社会集团对其所施加的影响。这个意识的世界可能是人们所居住的村庄和省份,或者他所从属的某个教区,而其智识活动的来源往往是当地的神甫、族长、巫者、小知识分子等。而当民众生活、受教化于各个文化迥异的社会集团之中并吸收这些外部的观念后,他们也由此成为从属于特定社会集团的顺从主义者。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葛兰西说:“自发性是‘下层集团历史’的特征,表明了他们最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他们没有达致任何‘自为’(for itself)的阶级意识,他们的历史也因而从未对其自身产生过任何可能的重要性,或留下任何文本痕迹来表明他们的一些价值。”[1]196因此,常识表面的矛盾性实际上是其自发性的自我确证。而对葛兰西而言,这种分析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对常识自发性的批判还构成了其霸权理论的重要组成内容。
二、霸权与常识
葛兰西的常识批判理论与其霸权思想的产生是息息相关的。笔者认为,他在以霸权理论研究首开文化革命先河之时,也发现了资产阶级维系自身霸权的秘密——将自身的世界观普世化为民众的常识。先就葛兰西“霸权”的含义来看,它主要指的是“一个阶级团结和凝聚广大群众的能力”[5],并表现为政治统治和文化领导权两个方面,“但他重点强调的是后一方面,在许多场合下,葛兰西所使用的霸权就是文化霸权(即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6]。此外,葛兰西还强调文化霸权较之政治统治的优先地位,“一个社会集团在获得政权之前能够也必须行使‘领导权’(这的确是获得政权的重要条件之一)”[1]57-58。也即,无产阶级欲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必先成为文化、意识形态上的主流阶级。由此,常识批判就显得尤为必要了,因为霸权本质上就是“一种‘常识’,一种统治意识形态在其中实践和扩散的文化领域”[7]。
具体来说,正如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霸权最初是被用来“说明西欧资产阶级统治远为强大的力量及其复杂性,这使得这块大陆上的先进资本主义地区完全不会重演十月革命”[8]。在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革命史上,曾形成了由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与受其鼓舞下欧洲各地爆发革命却相继归于失败的反差结局。葛兰西由此认识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只能解释革命为何能在俄国这样的贫穷落后的国家取得成功,却不能解释西欧国家革命运动的失败。他于此将东方专制国家和有民主传统的西欧国家进行了对比分析,比较之后他指出,在东方,由于市民社会尚未成型导致国家就是一切——沙皇的专制统治无需征得民众的同意,这种意义上俄国正是列宁对“国家”定义的典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特殊强力组织”[9]。而在西方,“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1]263。统治阶级维系自身统治的方式并不完全依赖于国家的强制性权力,而主要是通过获得人民的同意来实现的。
这种同意,首先在政治领域表现为“资产阶级利用分权制,造成国家统一假象,并以立宪会议、定期选举国家元首等,对人民要求予以虚妄满足”[10]193;其次,在市民社会中表现为统治阶级依恃文化霸权地位对民众的巨大影响而获得他们的文化认同。那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又是指什么呢?“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像社团、工会、学校这样一些私人组织形式的国家领导权”[11]。显然,与马克思包含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内的“市民社会”概念不同,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专指为意识形态生产和传播提供场所与渠道的物质支撑体统,它所涉及的教会、学校、行业协会等虽多属民间组织而非国家权力工具,“既没有‘制裁’,也没有绝对的‘义务’,但是在习惯、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道德等等方面产生集体影响并且能达到客观的结果”[10]191-192。也就是说,正是透过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的哲学被以一种教化、说服的“软性”教育方式向下层集团渗透,而其最终产品就是大众哲学——流行于社会普通民众中的常识。常识越被广泛地传播,资产阶级的道德风俗和行为准则就越多地被灌输给了民众并最终将其同化。这也就解释了列宁为何能仅靠一小部分组织起来的革命力量就能轻易推翻沙皇统治,而其成功经验却不能被西欧国家复制的原因。“俄国革命的运动战虽然能打破国家机器,但很难占领欧洲国家的纵深领域,这包括构成市民社会的宗教团体、工商业行会、文化教育机构和民众习以为常的伦理规范、生活方式”[1]178。对此差异,福柯后来曾在《规训与惩罚》中生动地描述道:“愚蠢的封建主用铁链捆绑奴仆,资产阶级却用民众的思想来束缚他们。正是在人们柔弱的脑神经之上,奠定起至善大帝国不可动摇的根基。”[12]
不过,正如前述,由于自发性的常识本质上是“自在”(in itself)的意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不同社会集团在文化领域相互博弈的产物,这也就意味着目前在民众常识层面占有优势地位的资产阶级霸权不是不可改变的。相反,常识的自发性既然可以为资产阶级所利用,那无产阶级也同样可以发展出包含新思想、新制度、新文化在内的新世界观去影响民众,在使其摆脱异化意识的同时建立无产阶级自身的霸权。“在马克思提及常识的地方,还隐含着倡导新的大众信念的必要性,也就是一种新的常识以及与之相伴的一种新的文化、新的哲学,它们将像传统信念那样植根于有坚实可靠性和必然性的大众意识之中”[1]424。因此,无产阶级霸权扩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重构民众常识的过程。
而在此过程中,葛兰西强调,只有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真正的哲学”成为民众常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界观的转变才成为可能。反过来,站在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实践哲学的出发点“首先必须是对‘常识’的一种批判”[1]331。这是由实践哲学不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人们行动指南的性质所决定的。只有当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经验紧密相连时,观念就不再仅仅是被不断修正以适合现状的理论,而变成了葛兰西经常引用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物质的力量”。因此,霸权革命不是简单地主张用一种新兴哲学对抗另一种旧有哲学,或“直接用不同的领导权取代现有领导权”,而是要求分析培育新观念能够得以生长的社会条件——更直接地就是被葛兰西称之为“常识”的土壤。这一点也构成了葛兰西在知识分子应如何看待民众常识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三、知识分子与常识
葛兰西通过常识批判之于无产阶级霸权构建意义的分析,已明确了常识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意味着使之成为一个融贯一致的统一体,并把它提升到世界上最高层次的思想水平。它也意味着对一切既往哲学的批判,因为它们在大众哲学中留下层层积淀”[1]324。他进而指出,常识批判的主体是知识分子而不能是普通民众自身。“革新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于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种一致的、系统的并且经常存在的认识,变成了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1]335。不过,在具体实践中,葛兰西发现知识分子对常识的自发性存在两种错误的认知观念:一种观念认为常识的自发性因其有着历史渊源,有一定阶层的心理基础,因而是不可改变的;另一种则是轻视常识的自发性,对其不屑一顾。对前一种“不可改变”说,葛兰西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文人无视现代科学,只是从直接而粗俗的经验出发重新提倡早已被摧折已久的炼金术和巫术的传统,是名副其实的奇谈怪论,其目的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民众中的传播。而对后一种知识分子轻视常识自发性的错误观念,葛兰西则予以相当的重视,他将当时以正统自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作为此种观念的代表,对其进行了重点批判。
布哈林曾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意在向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本小册子包含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及其意识形态的研究与批判,却只字未提工人阶级自身的思想和社会活动状况。因此,在葛兰西看来,布哈林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不能与民众已有的自发哲学结合起来,以一种“社会化”的方式去传播已发现的真理,反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完全外在的形式移植、灌输给民众。“马克思主义和它革命力量之间这种一方独白似的结构关系,正像教堂和信众、神甫和农民、教师和弟子之间的关系”[13]。在这种“独白”关系中,脱离自身阶级基础的知识分子成了高高在上的说教者,民众及其自发哲学则被弃之如敝屣。这种说教方式变得越学究气和抽象化,民众就越是难以理解和内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广大民众来说始终是异质和外在的。“这些体系作为一种外部政治力量影响着广大民众……这把民众的独创思想限制在一个消极的方向上,对民众就世界和生活所具有的一种初生和混沌方式的思考,没有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酵素给予其内在的转变从而发挥其积极的影响”[1]420。
因此,在葛兰西看来,布哈林全部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不是把实践哲学作为一种历史的科学,而是抛开历史语境将其抽象化为若干教条,将其变成了思辨唯心主义的公式,以为只要向民众说明现实与观念公式之间的差距就能揭露资产阶级意识的虚假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进而就会被唤醒。而其结果是被轻视的常识难以发挥在构建无产阶级霸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相反,资产阶级的观念却一直牢牢掌控着无产阶级的头脑。于此,葛兰西指出任何要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努力都应从转变民众的常识开始。“实践哲学一开始必须立足于常识,以便证明‘人人’都是哲学家,因而,也就不是把科学的思维方式引进到每个人的个人生活中来的问题,而是对已经存在的活动加以革新,并且使之成为‘批判的’这样的问题”[1]331。在笔者看来,葛兰西所倡导的正确的教育路线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知识分子不应将自己看作是在群众常识之外发现真理、并自上而下将真理强行传授给他们的特权人物,相反,“他们应该把自己看作‘组织共识’(organizing consent)的战略家”[14]。其组织方法不应重在明晰的方法论原则的理论阐述,而必须从民众已知的事物开始,从他们初始社会条件下的自发哲学开始,因为有意义的教育总能保持知识的连贯性。“领导权不是‘抽象的’:既不是机械重复科学或理论公式,也没有混淆政治、实际行动和理论阐发的界限。这里的领导权施加给的是真正的人,他们形成于特定的历史关系中,有着明确的感情、见解以及零碎的世界观等——它们本身是一定的物质生产状况与‘偶然’凝结在一起的各种迥异社会要素的‘自发’结合。人们既没有忽视这种‘自发性’要素,更没有轻视它。相反,人们对它进行教化、引导,并剔除其杂质;旨在通过生动而具有历史效果的方式使它向现代理论看齐”[1]198。
第二,知识分子与大众应该是教学相长的关系:知识分子用实践哲学批判、引导群众的常识,使其突破非理性的迷信和狭隘的社群视角,从而给予他们一种更高层次的世界观以帮助他们批判性地建构属于自身的思维;反过来,民众和历史情境将检验知识分子的哲学,并为其理论提供历史性的语言,好的理论不仅能引起群众的共鸣而成为他们新的常识,还能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南,推动其参与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中。对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这种紧密互动的关系,葛兰西曾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女性紧身胸衣上的鲸须”[1]340:如果把群众比作女性的胸部——“它填充了本可能成为抽象形式的那个潜在空间”[14]71,知识分子则化作支撑其造型的鲸须,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共同呈现女性之美。
第三,在教育方法上,要认识到民众教育是一个建立在实际经验上的“清楚地表述和缓进累积的过程”,特别是当新世界观与统治阶级的正统观念互相冲突的时候,仅仅依靠政治的、权威的、组织的等理性因素去影响、说服群众,是难以消除其精神危机的。这就要求教育者必须“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积极地研究和发展大众心理学要素”[1]197,以培养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为“民众信奉不信奉一种意识形态,是对思想方式合理性和历史性的真正批判性检验”[1]341。对此,葛兰西给出了两点具体建议:其一,要永不怠懈地重申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民众思想的最好的教导手段”[1]394;其二,要努力培养出一种新型的、直接从群众中产生出来,而且同群众保持联系的知识分子精英。而这也成为葛兰西衡量知识分子是否具有“有机性”的一条重要标准。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如果说葛兰西对霸权理论的研究是要揭示统治集团是如何通过获得民众的共识而实现自身统治的,那么他的研究最终表明这种具有意识形态整合功效的霸权主要体现在“坚定的大众信念”之中。由此,他在深入考察常识的特征、本质及其之于无产阶级霸权建构意义的基础上,形成了他极具创造性的常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并由此开辟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的意识、心理批判的新进路。虽在当时这种进路主要是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经济决定论”的纠偏,但其影响并不限于一时,实际上,他的这种文化、心理的意识形态批判转向,客观上成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理论著述的主线,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统。比如,自20世纪3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就已开始解剖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大众心理机制,及至后来的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马尔库塞的“感性解放”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虽入手角度各异,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可看作是对葛兰西常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拓展和深化。
[1]Gramsci,A.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M].Hoare,Q.& Smith,G.(eds.and trans.).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
[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23.
[3]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11.
[4]Gencarella,S.Gramsci,Good Sense,and Critical Folklore Studies[J].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2010,47(3).
[5]乔治·拉雷恩.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M].张秀琴,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86.
[6]周凡.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5):20-31.
[7]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89-90.
[8]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01.
[9]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10]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中,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1]葛兰西.葛兰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439.
[12]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13.
[13]Patnaik,A. Gramsci’s Concept of Common Sense[J].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1988,23(5):2-10.
[14]安娜·史密斯.拉克劳与墨菲:激进民主想象[M].付琼,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71.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1.003
2015-11-19
陕西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14A15);西安外国语大学2014年科研计划青年项目(14XWC04)
B089.1
A
1000-2359(2016)01-0011-05
李永虎(1980-),男,湖北十堰人,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西安外国语大学思政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