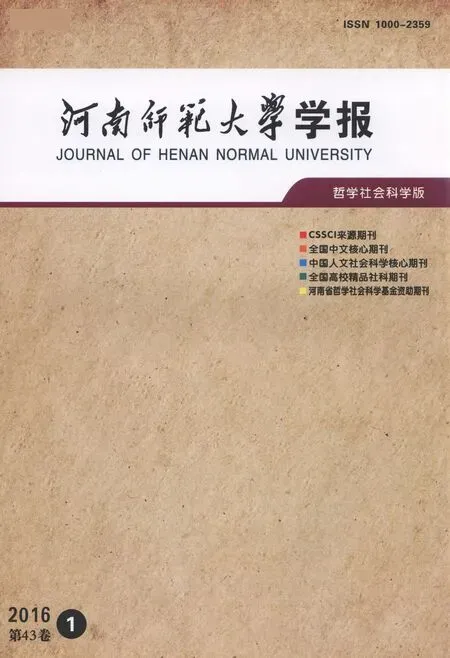再谈美国人权外交的背景、实践及评价(1977~1981)
杨 建 国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再谈美国人权外交的背景、实践及评价(1977~1981)
杨 建 国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卡特主政美国时,对外极力提倡和推行人权外交政策。这是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当局深信人权问题对当时的美国来说,既是自身道德与理想外交传统的自然延伸,又是对内外诸种压力与挑战所做出的现实性、能动性反应。在贯彻与落实的过程中,针对不同地区或政治体制的人权外交对象,依据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当局采取主动灵活性的政策与举措,而不是搞僵硬的“一刀切”。在总体上不太成功的大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和意义上切实唤醒了人权状况恶劣国家的民众的人权意识,缓解了人权遭受严重践踏的程度,而且对此后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影响深远。
卡特政府;人权外交;外交传统;国家利益
在对外交往领域,卡特政府主政美国时期留给世人最为深刻印象的就是大力提倡和推行以人权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外交政策及其实践。那么,卡特执政美国时,究竟面临着什么样复杂的内外大环境,人权外交政策推出后又是如何得到贯彻与落实的,此种政策的推行是否与美国的整体性、根本性国家利益相吻合?笔者试图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内外因辩证关系、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国家利益内部的矛盾统一为指导思想,依据所掌握的大量资料,结合美国外交的历史传统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考察和剖析,进而得出相对客观与准确的结论,以求教于学界同仁与方家。
一、卡特时期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出笼背景
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民主党人,从小在美国南部的普兰斯小镇成大,深受美国南方基督新教浸礼会教义(该教派提倡人们应以基督为信仰的核心,以基督及其教会为榜样,特别强调传统道德伦理)的影响。美国著名学者威廉·米勒对此的点评是,“(卡特)宗教信仰的政治后果……是一种鼓励”[1]。1974年12月卡特公开说,美国要在慈悲心、正直感以及献身基本人权和自由方面给全世界树立典范[2]。对于虔诚的教徒来说,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白宫的新主人,卡特的思想与政策倾向,得到其主要外交助手国务卿万斯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时任美国防长布朗的看法与其接近)的理解、认同与大力支持,就会内化为行政当局外事议程上的关注重点。比如,布热津斯基于1977年4月在备忘录中说,美国要通过“旨在影响其他国家的政府,给人权以更多关注的多边或双边性举措……有利于增进美国的国家安全”[3]66。虽说“形势比人强”,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与背景下,想有作为且勇于付诸实践的历史人物必定会在历史的政治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而且,在美国特定的政治运作体制之下,在外事领域总统的政治影响力、感召力无疑是最为强大的。卡特表示,希望并相信人权思想的广泛传播,必将成为可预见未来全世界的大潮流[4]144,“我们对人权责任与义务的承诺必须是绝对的。……不能对其他地方的自由命运听之任之,随其发展”[5]264。
当然,历史人物只能是接受他当时所面对的既成事实的历史遗产与社会大环境。从历史遗产的视角来看,在外交领域美国自立国伊始就具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双重传统,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正如卡特于1977年5月在圣姆大学演讲时所说的,美国的外交政策,既是深深根植于美国人深信不疑的核心道德与价值观之中,又是以美国雄厚的物质财富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其坚强保障[5]162。特别是针对美国这样的世界性大国与强国,在外事行为中绝不可能纯粹只追求遥远的、捉摸不定的道义、信仰与精神价值,当然也绝不可能只关注物质性的、可用金钱衡量的锱铢必较的好处与实惠。而是两者都要兼顾,在动态性平衡中找寻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有利节点。正如美国人戴维·卡拉汉所说,完全背离美国核心道德价值的对外政策一定是短命的,但是忽略或无视美国现实利益的对外政策,同样不会得到美国人的拥护和支持[6]。从内外社会环境的角度来审视,卡特总统上台前后所面临的诸种压力与强劲挑战,似乎是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所遭遇的最高峰值与聚焦时段,美国似乎首次得了严重的“帝国休克病”。特别是20世纪70年前半期在美国内部出现的“水门丑闻事件”和越南战争的不光彩结局,以及美国内经济领域的持续性衰退与危机,直接导致美国民众对政府(尤其是总统为代表的行政部门)的公信力、智慧、道德水准严重质疑,使得美国人对其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政治定期选举体制、生活方式的自信与优越感大打折扣,进而出现了美国民众心理上的极度失衡与彷徨以及70年代中后期国会外交权复兴的小高潮。这些都对总统为代表的行政当局的正统与神圣、行政能力的顺利实施构成极大的制约和挑战。卡特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实践活动充分证明,遵循道德原则是美国对外扩大影响的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源和坚实的民众基础[4]128—129。万斯则说:“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保持国家实力的根本。”[7]冷战的大背景下,外部世界对美国能够构成真正最大威胁与挑战的国家无疑是社会主义强国苏联,不论是从狭隘的地缘政治层面上的国家军事安全,还是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上正统与合法性来看,都是如此。而在尼克松—福特执政时期,极力对苏联推行“缓和”政策,在事实上并没有达到美国预想的目标。苏联较好地利用美国推行的“缓和”政策所带来的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大力推进自身的各项建设事业,和美国的实力差距大为缩小后,进而在全球各地大力推进投机性的扩张政策。这不仅使得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的关系也变得异常紧张与相互极端不信任,而且还使得新上台的政府必须得有新的政策设想。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在美苏竞争和对抗中,美国可以把苏联置于思想上的防守地位的绝佳突破点,就是人权问题[3]176。另外,当时美国在全球各地的重要战略性盟友,如韩国、菲律宾、伊朗、南非、阿根廷等,均确实存在着极为恶劣和糟糕的肆意践踏和侵犯人权的事实,内部社会关系紧张,政局动荡不稳,存在爆发暴力型革命事变或倒向苏联的可能性。美国从其国家战略性利益出发进行考量,也需要其专制独裁体制性的盟友们适度调整内部的残暴政策,改变人权领域留给世人极坏印象,缓和社会的紧张性矛盾,巩固和扩大统治基础,确保政府的亲美倾向不动摇,既有利益不受大的损害。美国人劳伦斯·肖普对此评论,人权运动有助于使美国继续干涉世界各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合法化。简言之,可使美国再次采取进攻性态势[8]。
这样来说,人权外交政策的正式出笼,既是卡特行政当局的内心自愿的主动性探索与创制,又是当时美国政府对其面临的巨大内外压力与挑战所进行能动、现实性反应。内因是基础和前提,外因是条件和催化剂。因此,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它的预期目标就是,通过人权外交,在国际上赢得广泛的道义支持,获得主动地位与进攻的机会,进而“让苏联屈服于美国,让美国称霸于世界”[9]。
二、卡特时期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实践
卡特执政美国期间,人权外交政策被首次提升到国家外交战略的层级与高度来看待与处理。人权外交政策在卡特政府时期的贯彻执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行政部门内部,以国务院为其典型代表,成立了专门负责和处理人权事务的人权与人道事务局、人权和对外援助机构间小组,确保有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18人组成)进行内部的分工与协作,而且还特别赋予其主要负责人(助理国务卿帕特里夏·德里安)有足够的职能权限与政治权威。既要负责编写并定期报告年度性国别人权报告,还要针对特定国家的人权问题提出有针对性政策建议与意见,以供当局进行决策时参考。这充分体现出卡特行政当局对人权问题的切实重视与关注,决不是仅仅流于形式与空喊口号。
其次,为在国际上造势,改善其受损严重的国家形象,缓解反美浪潮,国内增强政府对民众公信力、感召力与凝聚力,卡特上台伊始就极力推动国会尽快批准国际上公认的《联合国反种族灭绝公约》(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公约》以及《美洲人权宣言》(1977年签署)。至少在初期,为卡特当局在外部世界赢得了较为正面的正义与仁慈的声誉,重新树立起了美国“道德卫士”的伟岸形象。在国内,也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众对政府的不道德印象,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与感召力,缓和了与国会、民众之间相互极端不信任的紧张关系,拉近了心理上的距离。
再次,针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出现的肆意侵犯与践踏人权的糟糕现象与恶劣状况,卡特行政当局主要采用“悄悄外交”“公开外交”和增加或缩减对外提供的“经援”或“军援”相结合的方式和手段进行外部的鼓励或惩罚。比如:美国驻菲大使在和时任菲总统马科斯的会谈中严厉警告,在菲律宾国内实现民主,对于缓和菲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必不可少的[10]。对于韩国的人权问题,万斯曾明确指出,考虑到韩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建议将继续就人权问题向其施压,但是并不把人权问题同美国的经援和军援相挂钩[11]32。卡特于1978年2月特别强调,美国在各种人权目标以及所有对象国家中,将更多依靠美国承认其国内人权情况明显有所改善后的积极性鼓励举措;“除了特殊情况外”,将不对严重践踏人权的政府在维持治安领域给予帮助,等等[3]149。对伊朗、南非、阿根廷等的做法也大体类似。比如,卡特政府对韩国、印尼等减少军火出售,对阿根廷中断军火出售,对菲律宾、智利等国降低援助水准[12]102-103。但是这是以不彻底损坏与上述战略盟友的根本关系为底线的,战略性军事安全的考量从来不曾消失过,从来不会出现牺牲某些重要的既有经济政治利益来换取所谓人权状况的真正提升和改善。譬如,美国于1976至1980年期间向上述国家提供的“军援”总额仍高达约23亿美元,出售武器的价值总额高达137亿美元[13]。其中,美国对南美大国阿根廷提供的贷款,从1978年至1980年,就由2740万美元迅猛增长到7920万美元,约增长了4倍[14]。也就是说,卡特当局对外在大张旗鼓地倡导和推行人权政策时,并没有完全忽视或无视狭义性的国家军事安全与物质利益,而是依据人权外交对象与目标国对美国安全利益的重要程度,采取主动灵活性的实际举措,尽量在狭义性的安全与物质利益与道义精神价值观追求之间找寻最有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动态平衡的节点。对此,时任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坦承,在许多情况下基于军事安全利益的考量和权衡,美国对某些人权状况糟糕的重要国家,仍需要继续落实以前达成的援助项目[12]29。但是,对于美国的安全与利益相对不重要的第三世界国家,如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等国,则是相对更加强硬,以经济制裁为主。再者说,美国广义性的国家利益本身就内含着隐形的构成要件,比如核心价值观、政治经济基本制度、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等。这是因为,在美国人看来,“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道义之邦……它将引导世界各地人民都向美国看齐,最终心服诚服地采纳美国人崇信的核心价值观和政治体制”[15]。在当时冷战的社会大环境之下,能够直接以武力方式征服美国本土、屠杀其国民、掠夺其资源与财富的可能性极小的状态之下,能够对美国造成持久性威胁与挑战的,恐怕更多的可能是在隐形的国家利益构成要件领域,而且此种对抗和挑战是最难从根子上彻底消除的,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再其次,针对苏联,卡特当局的主要做法是,先是公开为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撑腰打气,利用不同的外交场合批评苏联政府无视或肆意侵犯人权。比如:1977年卡特刚上任就亲自给苏联著名不同政见者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萨哈罗夫教授写信;在白宫先后亲切会见著名的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布科夫斯基等;在欧洲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抨击苏联政府没有认真遵守《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赫尔辛基议定书》等关于人权的相关规定。另外,为加大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宣传战力度,卡特于1977年3月向国会提出,要给“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自由电台”再增加28台发射器,额外专项拨款4500万美元。后来,特别是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与苏联侵略阿富汗事件发生后,卡特当局采取多项实际举措对苏联进行惩罚和遏制,比如:除了军事上进行调整型部署之外,还号召联合抵制由苏联承办的1980年夏季奥运会,暂停向苏联出口谷物和高新技术,暂停与苏联之间的多项高层交流,呼吁国际性金融组织或银行停止向苏联提供新的贷款等。万斯把当时的美国对苏政策归纳为,“从战略上讲……一方面既要遏制苏联的向外迅猛渗透和扩张,另一方面又要使美国长期以来为缓和美苏关系而做的工作和努力恢复其应有的活力”[11]35。针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卡特当局的指导性原则主要有:美国应为了自身国家利益的缘故,而不是为了要和苏联搞缓和,才与东欧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美国不仅要和东欧国家内部的忠诚反对派,而且还要同其政府官员保持经常性接触和沟通,等[3]149。采取的策略和办法是区别对待,分类处理。对和苏联关系相对疏远与离心倾向较明显的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主要以鼓励和支持为主,强调其历史上就有追求独立、平等、自由的传统与渴望,强调其国内人权状况的大幅度提升和改善,提高或加大对其提供“经援”的力度;对其他和苏联关系相对紧密和离心倾向虚弱的东欧国家,则主要以公开对其国内人权状况进行批评与谴责,强调其国内人权状况没有明显改善或提升的表现。当然,不论是对前类国家推行的鼓励、引导性的“胡萝卜”为特征的人权政策,还是对后类国家实施的打压、惩戒性的“大棒”为特色的人权政策,其目的和实质均是相同的,就是以“人权”为主要内容的道德上的外交攻势,来弥补和掩盖美国当时相对衰退且处于防守地位的军事、经济实力,在苏联的“后院”煽动或点燃起更为猛烈的反苏情绪与浪潮,进而使得苏联政府不得不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人力去处理社会主义集团内部出现的裂痕与离心倾向问题,减弱其对美国的外交攻势与进行挑战的力度与强度。因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中,国家之间政治交往的过程中,选择以火对火或以牙还牙的方式来处理与竞争对手的关系,可谓“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不仅代价高昂,还会引发强烈的反弹。而如果选择以水对火的方式,以柔克刚,不仅代价相对较小,而且引发反弹的可能性、力度都会降低许多。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针对东欧国家的人权外交政策及举措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有利于对付苏联的挑衅。”[3]343—344
三、卡特时期美国人权外交的评价
卡特政府对外实施的人权政策及举措,不论是针对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针对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战略盟友们,其目的和实质都是万法归宗,即通过削弱竞争对手的实力、吸引力、凝聚力与攻势劲头,巩固和增强盟友的统治基础,改进美国在海外的国家形象,缓和或消除第三世界国家出现的反美情绪与浪潮,进而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战略性、整体性国家利益,换言之,就是尽可能地维持其霸权地位的稳固和持久,挫败外部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与挑战。
虽然,卡特执政美国时,通过万斯于1977年4月的公开演说对美国的人权政策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所谓“人权”应当包括:(1)个人人格与尊严免遭政府侵犯的权利领域,譬如:酷刑、非人道或侮辱性的待遇与惩罚、非法逮捕或监禁等。(2)满足个人及家庭成员基本住房的环境与条件、食品安全供应、工作与就业、医疗与保健、受教育机会均等与公平等公民最低限度需求的权利。(3)享有信仰与宗教自由、结社与集会自由、言论与出版自由等基本的公民和政治权利。(4)免于遭受包括种族、宗教、肤色或性别等方面在内的歧视[16]。这通常被看作卡特当局对人权的权威性官方定义。表面上来看,既有美国人异常看重的狭义性的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也包含着发展中国家特别强调和关注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但是在具体贯彻与落实的过程中,根据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却是有意或无意强调和关注的还是前者,或对后者人为忽视或重视不够。这就必然导致卡特当局倡导与推行的人权外交政策具有明显狭隘性特征。
卡特执政后期,行政当局倡导和推行的人权外交政策,就已经遭到主张现实主义外交的政治精英们的强烈不满、批评与攻击。譬如,在前国务卿基辛格看来,卡特当局所倡导和推行的人权政策,完全不顾或根本不懂国际政治实际运作的方式,是一种危险且自负的道德主义热情,有可能给美国带来极大的麻烦[17]。其实,这里涉及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如何界定问题,是仅仅注重狭义层面的军事安全问题,还是看重广义层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具体到美国来说,这就要求执政当局的政治与外交精英们在内部冲突的国家利益(既存在显性的、短期与眼前利益,又内含着隐形的、长期与持久利益)层面上,进行动态的平衡与协调,不可能总是能够面面俱到“鱼与熊掌”兼得。因此,在看待和评价卡特当局对待和处理外部世界的人权问题采取的主动性、灵活性手段与措施时,似乎不应一味强调和突出其所谓的“双重”或“多重”标准。因为在并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中,任何独立的主权国家在推行外交政策时,都是以其国家利益为最高准绳和落脚点的,美国当然也不可能例外。恰恰是卡特当局所选择的以个案进行处理的基本模式,就是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然后再采取灵活不同的举措,但是,它始终是围绕着国家利益而逐次展开与落实的。美国著名人权学者谢斯塔克认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人权是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服务的,因为可以通过“人权外交”来部分满足受专制政府迫害的民众的意愿,来推动其国家内部和平、秩序与安全的实现,间接对美国有利[18]。所以,在评价卡特政府对外推行的人权外交政策及举措时,过于强调和突出狭义性的军事安全利益和眼前物质性利益所遭受到的损失,就认定其是彻底失败是不客观、不全面、不准确的。因为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基本制度、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层面的柔性指标(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是无法用金钱来加以准确衡量的,也不是可以立即见效的,需要有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较长过程。
卡特当局对外倡导和推行人权外交政策,自然是服从和服务于其国家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主观动机的私利性并不能完全抹杀此种外交政策所造成的某些积极的客观后果,因为推行某种政策的主观性动机与客观效果之间并不总是水火不相容,也有可能会出现重合或并行不悖。具体到卡特时期人权外交政策就是,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确实唤醒了不少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里民众的人权意识,也就是说,人来到世间并不是注定就是要受苦受难的,自然天生就有追求独立、自由、平等和幸福的权利。同时切实缓解了一些独裁国家对其民众基本人权的肆意侵犯或践踏的恶劣程度,有些国家的民主进程还切实有所推进。譬如,智利当时的一位知名人权法学者证实,在智利自1977年以来没有再出现过“不同政见者”的失踪事件,此前常见的大规模武力弹压政治犯的状况也开始明显减少[19]。在卡特政府的积极努力下,巴西时任总统盖泽尔在国内废除了部分滥用武力的法规,并释放了大量政治犯;由于苏联移民政策的松动性调整,使得从迁居国外的犹太人,从1976年的14261人快速增加到1979年的51320人,等等。这些当然主要是人权遭受践踏国家民众进行长期抗争的结果,但是卡特当局从外部对其不断施加影响和压力,也是不应人为忽略的。
卡特政府届满后,继任的不论是共和党主导的政府,比如里根、老布什、小布什政府,还是民主党主导的政府,比如克林顿、奥巴马政府,在外交实践中,均毫无例外地把人权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并得到程度不同、侧重点有所差异的关注和强调。换言之,促进美国的地缘政治军事安全和提升人权是并行不悖的,人权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由此可见,卡特当局倡导和推行的人权外交政策,开启了此后美国人权外交新征程的起点,奠定了此后美国外交政策议程中不可能再无视人权问题的基本架构。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说,卡特当局的主张、做法、地位与影响,完全可与前威尔逊政府相提并论。
[1]罗莎琳.卡特夫人回忆录[M].吴为,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70.
[2]莱斯利·惠勒.吉米·卡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27.
[3]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M].邱应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4]Jimmy Carter.Keeping Faith: Memories of a President[M].New York:Bantam Books,1982.
[5]王建华.美国历届总统世界名校演说[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6]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 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M].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4:115.
[7]万斯.困难的抉择:美国对外政策的危急年代[M].郭靖安,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282.
[8]劳伦斯·肖普.卡特总统与美国政坛内幕:八十年代权力和政治[M].冬梅,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80:51.
[9]Friedbert Pfluger.Human Rights Unbound:Carter’s Human Rights Policy Reassessed[J].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1989(Fall).
[10]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76.
[11]Cyrus R. Vance.Hard Choices: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3.
[12]A. Gleen Mower,Jr. 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Carter and Reagan Experiences[M].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7.
[13]托马斯·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下册[M].李庆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864.
[14]洪国起,董国辉.透视美国人权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74.
[15]潘恩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2.
[16]Sandra Vogelgesang.What Price Principle?U.S.Policy on Human Right,Foreign Affairs[J].1978(July).
[17]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38.
[18]Jerome J· Shestack.Human Rights,the National Interest,and U.S. Foreign Policy[J].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89(November).
[19]Roberta Cohen.Reagan’s Latin Policy[N].Washington Post(1981-04-15).
Talk about Background,Practice and Evaluation of the America’s Human Rights Diplomacy(1977~1981)
YANG Jian-guo
(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During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th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f human rights was strongly advocated and implemented. The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was believed that human rights issues on that time, which was not only natural extension of American morality and ideal foreign tradition, but also the reality and dynamic response on various kinds of pressure and challenges towards America.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regions or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human rights’ diplomacy object, American Executive author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s, took active flexibility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rather than engaged in rigidly "one size fits all".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less successful on the whole, in the certain scope and significance, it’s really awaken the people's consciousness of human rights on the countries of poor human rights situation, alleviated human rights suffered severely trampled, and later the U.S. government’s human rights foreign policy ha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Carter Administration;human rights diplomacy;diplomatic tradition;national interests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1.008
2015-07-01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2015-QN-248)
K705
A
1000-2359(2016)01-0037-06
杨建国(1979—),男,汉族,山西夏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史、美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