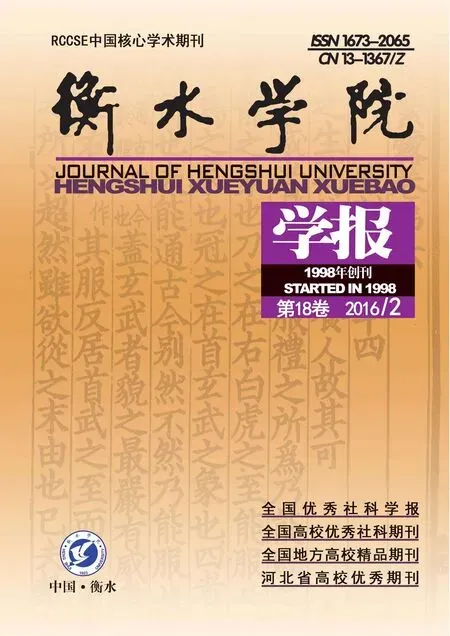董仲舒与班固史学
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董仲舒与班固史学
汪高鑫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汉代史学的发展受到汉代经学的深刻影响。董仲舒作为西汉今文经学家、公羊大师,其历史思想对于东汉史家班固的史学与史学思想有着重要影响,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影响了班固的天人观念,《汉书》不但高度重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也对天人感应论作了系统宣扬;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影响了班固的礼法观念,《汉书》接受董仲舒的德主刑辅说,同时积极宣扬德政主张;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影响了班固的大一统观,《汉书》通过断汉为史,积极颂扬西汉大一统功业,肯定“独尊儒术”之思想大一统的必要性,宣扬民族大一统的思想。
关键词:董仲舒;班固;《汉书》;史学;天人感应;德主刑辅;大一统
董仲舒是西汉儒学宗师、今文经学大家,其学术思想对于汉代社会与学术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从史学史的角度而言,董仲舒的学术思想直接影响了汉代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发展及其演变。班固是中国古代正统史学的代表,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他清楚地认识到董仲舒思想的时代价值和历史地位。与司马迁《史记》将董仲舒置于类传之中的做法不同,《汉书》为董仲舒做了专传,以此凸显了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与地位。具体到董仲舒思想之于班固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其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对于班固天人观念的影响;其二,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对于班固礼法观的影响;其三,董仲舒的大一统说对于班固大一统观的影响。以下试对此作出具体论说。
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与班固的天人观
重视阐发天人关系,是董仲舒学术的显著特点。纵观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其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宣扬天命王权说。董仲舒天命王权思想的理论出发点,是宣扬人副天数与圣王感生说。在董仲舒看来,天(近似宇宙)由天地人阴阳金木水火土“十端”构成,它“起于天,至于人而毕”[1]《天地阴阳》。在十端之天的大系统中,天与人作为最基本的关系,相互间存在着感应、授受关系。天人相互感应的媒介物便是阴阳之气,同时“天授命于人,人受命于天”[1]《为仁者天》。为了进一步论证天人之间的授受关系,董仲舒又提出“人副天数”说,肯定人是仿照天而生的,人的形体、性情、道德、政时等都与天同类[1]《人副天数》《天辨人在》。并进而认为古代圣王都是感天而生的,《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对于尧舜禹古帝王和商汤、文王等圣王祖先的感天而生有具体叙述。既然天人感应,天人授受,天人同类,圣王感生,那么天命王权也就符合逻辑地成为一种必然。
其二,宣扬天人谴告说。如果说天命王权是一种维护王权的造神的学说,那么天人谴告则是一种限制王权的学说。董仲舒认为,天命王权需要受命之符,即要天降祥瑞;而天能否降下祥瑞,则要看受命者是否能使“天下之人同心归之”。如果政治昏暗,“上下不和”,妖孽众生,“此灾异所缘而起也。”[2]《董仲舒传》董氏宣扬天人谴告说,通过天降灾异来“惊骇”统治者,其目的是期望统治者能更化弊政,建立起儒家仁义政治。所以他说:“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2]《比仁且智》很显然,天人谴告说是为了限制至高无上的君权胡作非为,而从天那里找到的一种制衡的力量。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对于汉代史学的天人观念有普遍影响,史家司马迁深受董氏学说的影响,通过撰述《史记》以“究天人之际”,系统阐发其天人观念。班固史学也表现出重视探讨天人关系的特点,并且明显表现出深受董氏天人观影响的痕迹。具体来说,班固受董氏天人观念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汉书》高度重视董仲舒的天人对策。《汉书·董仲舒传》关于董仲舒事迹的记载比较简略,却以大量的篇幅详细地记载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通观《汉书》所记“天人三策”,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董仲舒的天人观。《汉书》的传记特点,体现了班固对于董仲舒“天人三策”学术思想价值的充分肯定。如果从经学倾向而言,司马迁受董仲舒今文经学影响很大,然而司马迁既没有意识到董仲舒学术在汉代的重要地位,更没有认识到天人观念在董氏学说中的价值,这恐怕是《史记》未给董仲舒单独立传、没有载录“天人三策”的原因所在吧!班固的经学观受古文经学影响较深,之所以为今文家董仲舒独立做传,一方面是肯定其学术思想在汉代思想史上的影响,《汉书·董仲舒传》借用刘向、刘歆父子的评价,称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为群儒首”;另一方面传记用很长篇幅系统记述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也充分说明董氏天人观颇为班固所认同和欣赏。
其二,《汉书》重视宣扬天人感应思想。《汉书·五行志上》对于《五行志》的撰述旨趣作如是说: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传《春秋》,著于篇。
纵观《汉书·五行志》,即是通过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等人的过程中,对自己的五行灾异思想作了叙述。班固的天人感应思想还反映在所整理的《白虎通》一书。该书是班固奉命整理的关于汉章帝召开的讨论五经异同的白虎观会议的内容,其中《灾变》《封禅》等多篇内容涉及到天人感应理论。如说“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3]《封禅》。反之,“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3]《灾变》。这些天人感应思想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毫无二致。虽然该书基本观点代表了官方意识形态,却也暗合了整理者班固的天人观。
此外,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重要思想之一是宣扬天命王权,这一思想也贯穿于《汉书》之中。只是董仲舒为今文经学家,他的天命王权的理论前提是人副天数、圣人感生,而深受古文经学影响的班固,在宣扬天命王权的时候,则主要是接受了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的圣王同祖说。在《汉书》的《高帝纪》《律历志》以及所作《典引》诸文中,班固系统宣扬了汉为尧后的思想,通过缔造尧至刘邦之刘汉世系,从而论证了刘汉皇权的合理合法性。
二、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与班固的礼法观
儒家学说是内圣外王之学,如何实现外王理想,董仲舒从治国者的角度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思想。董氏德主刑辅说的理论根基则是他的阴阳学说。在董仲舒的天有十端论中,包含着阴与阳,同时阴阳也是天道存在的基本状态或运行规律,“天道之常,一阴一阳”[1]《阴阳义》。这种阴阳之道即是大千世界的运行规律,也是人类社会政治与伦理的基本规范,政治统治与伦理道德需要遵循阴阳之义。如“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里所谓三纲,即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而所求之天,即是求之阴阳,亦即符合阴阳规律,因为在社会伦理当中,“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制约阴,故而“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1]《基义》。同时,“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1]《天辨在人》。而这种阴阳之道在政治统治当中则表现为德与刑,“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2]《董仲舒传》。既然天道阳贵阴贱,政治统治就应当贵德贱刑,“任德不任刑”。这便是董仲舒德主刑辅说的内在逻辑。
纵观董仲舒的贵德思想,其内涵十分丰富,基本旨意如下:其一,仁爱民众。董仲舒认为,孔子《春秋》就是教人讲仁义的,而“仁之法在爱人”,“不爱,奚足谓仁?”[1]《仁义法》在董仲舒看来,爱民才是政治统治的根本,直接决定着君王的功业和政治的兴衰。其二,勿与民争利。仁爱民众不是一句空话,落实到具体的治民理政实践中,就是要体恤百姓的疾苦,减轻他们的徭役与赋税负担,特别是不应该与民争利,从而导致贫富矛盾激化。董仲舒说:“夫天亦有所分予。予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1]《董仲舒传》“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1]《度制》其三,行教化。董仲舒认为,政治统治仅仅从物质上满足百姓的利益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施以教化,使百姓“贵孝弟而好礼义,重仁廉而轻财利。”[1]《为仁者天》董仲舒还以堤防作比喻,肯定教化的重要性。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也,其堤防坏也。”[2]《董仲舒传》
当然,“任德不任刑”,不等于不要刑法。道理很简单,天道有阴阳,天不废阴,政治就不能废刑。所以他说:“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1]《天辨在人》董仲舒认为,刑作为一种辅助作用,它与德之间的比例百与一的关系,好比天道“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于刑罚,犹此也”[1]《基义》。尽管刑罚在政治统治中运用的比重很小,那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辅助。故此,董仲舒认为君王虽然要推行德政,却也不可失去自己的威权,所作《威德所生》篇,便具体论述了君主应该“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的重要性。
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对班固史学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首先,接受了董仲舒的德主刑辅说,肯定礼乐与刑法并用的重要性。《汉书·刑法志》明确提出:“文德者,帝王之利器也;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这样的表述,同董仲舒《威德所生》所表达的威德并用思想完全一致。在班固看来,政治统治德与威、礼与法是缺一不可的,“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2]《礼乐志》。班固认为政治需要发挥礼乐的作用,他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乐可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故而“治道非礼乐不成”[2]《礼乐志》。同时刑罚也不可或缺,《礼乐志》借用董仲舒“阳为德,阴为刑”“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功”等语,肯定了刑法之于政治,就如同阴之于天道一样重要。
其次,大力宣扬董仲舒提倡的德政思想。德政思想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董仲舒承继了先秦孔孟富民、教民的德政思想,班固作为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史家,其在《汉书》中对德政思想做了宣扬。第一,通过揭露西汉暴政,对百姓疾苦寄予同情。西汉很长一段时间实行郡国并行制,很多诸侯王独霸一方,为非作歹,穷凶极恶,《景十三王传》对此作了如实记载。如记载江都易王刘建一贯肆意淫乱,任意草菅人命,“凡杀不辜三十五人”;广川王刘去也是个嗜杀成性之徒,他杀人的手段极其狠毒,像割股、剥皮、支解等等,都是他惯用的杀人手段。对于这样一个悖虐之徒,议者皆主张治其罪,然而天子却“不忍治王于法”。西汉一代诸侯王的暴虐绝不仅见于此二例,正如班固在传后所说:“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西汉后期政治十分昏暗,民不聊生。在《王贡两龚鲍传》中,班固借贡禹奏言元帝述百姓因大饥荒而饿死的惨状,以此揭露了统治者对待老百姓的麻木不仁的态度。贡禹说:“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故当若此乎!”这里一方面老百姓因大饥而死,一方面统治者们却“厩马食粟”,贡禹的奏言无疑是对元帝统治的一种莫大的讽刺,同时也把罪责直接指向了这个“受命于天”的君主。班固记录诸侯王的暴行和贡禹的指责,其实也表达了自己对于西汉暴政、昏政的极度不满,同时寄予了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西汉百姓的同情。
第二,提出了一些具体德政主张。一是要解决土地问题。在《食货志》中,班固赞同董仲舒的关于土地问题的看法,认为秦朝的灭亡,与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汉朝建立起来后,却对此“循而未改”,结果土地问题依然严重,直接影响了政治稳定。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就必须要“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然而现实中西汉的土地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到了后期,随着统治的腐败,土地兼并情况则更加日益严重,一些有见识的大臣又重新开始提出限田的主张。如哀帝时的大臣师丹就认为:“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钜万,而贫弱俞困。”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改作政治,实行限田。二是要轻徭薄赋,养育民力。《食货志》肯定汉初以来劝民农桑、轻徭薄赋的政策,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养育民力的政策,造就了文景盛世局面。汉武帝时期,由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结果导致国库空虚,百姓贫苦。他赞同董仲舒的建议,认为要解决这种“天下虚耗”局面的办法,就是要“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食货志》的论述,足见董氏德政主张对于班固影响之深。
三、董仲舒的大一统说与班固的大一统观
汉武帝时代是大一统政治巩固时期,作为这一时代的经学大师,董仲舒迎合时代大一统政治的需要,积极阐发大一统思想。董仲舒以治《春秋》公羊学闻名于时,而公羊学的特点之一即是重视阐发《春秋》大一统之义。这里所谓大一统之“大”,是推崇、张大之义;“一统”则是指国家统一。在《春秋》三传中,只有《公羊传》从《春秋》开篇经文“元年春王正月”句中阐发出大一统之义,其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就将“王正月”与“大一统”联系在一起。董仲舒关于大一统之义的阐发,便是沿着《公羊传》的思路展开的,只是《公羊传》主张一统于周文王,而董仲舒则认为应一统于受命于天、改制作科的新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说:“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
纵观董仲舒的大一统说,主要思想内涵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立元正始”的政治大一统。董仲舒认为,《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元年”并非虚置之辞,其间也蕴含了大一统之义。《春秋繁露》的很多篇章对“元”的含义作了论述,如《玉英》篇说:《春秋》“谓一元者,大始也。”《重政》篇说:“《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王道》篇说:“《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天人三策》也对“元”的含义作了阐释,认为“《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由此可见,董仲舒的“元”论具有本体论的意味。在政治现实中,君王即是国之元始,天下应该统一于君王。董仲舒还从君这一名号中阐发出元始的含义,《深察名号》说:“深察君号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权科、温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君。”当然,确定君的元始地位,这是政治大一统的先决条件,而要真正实现政治大一统,还必须要“正始”,即是强调君王要仁爱修德。《仁义法》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正始”即是要以义正己,以仁待民。
其二,“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天人三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董仲舒传》这段话清楚地告诉人们,政治大一统必须思想大一统,而思想大一统则必须统一到儒家学说上来。关于政治统一与思想统一的关系,董仲舒之前不但有过学术探讨,而且也有政治实践。秦朝为迎合大一统政治的建立,采取了独尊法术的做法;汉初为巩固大一统政治,则采取了黄老思想。董仲舒的主张,只是思想统一的再次抉择。然而这次思想统一抉择影响深远,因为儒家思想从此成为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统治思想。当然,董仲舒之“儒”,其实已经将法家等诸家思想锻造于其中了,它迎合了时代大一统政治的需要。
其三,“王者爱及四夷”的民族大一统。儒家传统夷夏观讲“异内外”,孔子称赞春秋时期的攘夷霸业,孟子认为“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4]《滕文公上》,《公羊传》重视宣扬《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5]成公十五年的思想。然而,儒家传统夷夏观又普遍重视以礼义辨别夷夏,主张以夏统夷、德化四夷。孔子认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6]《子路》。孟子强调以夏化夷,强调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4]《滕文公上》《公羊传》的夷夏观念更为开明,认为夷夏之辨的本质在于礼义文化,故而“退于夷狄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①。董仲舒继承了先儒与《公羊传》的夷夏观念,一方面以礼义文化的标准来分辨夷夏,如《精华》篇将夷夏之别区分为中国、大夷和小夷三等,强调小夷避大夷、大夷避中国、中国避天子;却又认为这种分辨需“从变从义”,即是依照礼义文化的标准来变动地看待夷夏之辨。另一方面,董仲舒从大一统思想出发,也强调夷夏一统。《仁义法》篇从儒家仁义思想角度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董仲舒看来,君王推行仁政,不仅要仁爱华夏民众,也应用仁爱之心对待四方夷狄,因为华夏臣民与四方夷狄都是君王的子民。所以董仲舒说:“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1]《仁义法》肯定华夏统治者的仁爱之心是王天下、统夷夏的基础。
如果说董仲舒是西汉大一统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参与者,那么,班固则是西汉大一统历史的记述者。受到时代大一统政治和董仲舒大一统理论的影响,《汉书》的断汉为史也蕴含了丰富的大一统思想。首先,积极颂扬西汉大一统功业。班固之所以断汉为史,是认为汉朝建立起了“盛于周”的大一统功业,应该有一部史书与之相配,而现实中记述汉史的《史记》却是将其“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2]《叙传》。在班固看来,这样的历史撰述,是无法反映汉朝大一统盛世历史的。《汉书》对于西汉大一统政治的颂扬,其一是体现在典章制度的叙述上。《汉书》作有十志,系统反映汉朝各项典章制度,其中反映政治典章制度的有《礼乐志》《刑法志》《郊祀志》《地理志》和《沟洫志》,反映经济典章制度的有《食货志》,反映文化典章制度的有《艺文志》《律历志》《天文志》和《五行志》,在具体叙述上,注意各项典章制度演变与发展变化。其二是体现在对汉朝大一统地域的描绘上。汉朝大一统政治与其开疆拓土功业分不开,《汉书》不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对汉朝开疆拓土的过程作了叙述,《地理志》对由此奠定的一统疆域作了记述:“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州……”
其次,认同“独尊儒术”之思想大一统的必要性。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不见于《史记》,《汉书》所记“天人三策”则系统地载录了这一思想内容。《汉书》的记述,既是一种纪实,也是一种思想共鸣。班固是中国古代正统史学的代表,其史学与史学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统帅的。班彪、班固父子有一个著名的“史公三失”论,是讲司马迁史学所谓的三个过失,两人表述相近,用班固的话来说,是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2]《司马迁传》。“三失”中最关键的一条是“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其他两条都由此派生。其实司马迁史学也是推崇儒学的,《史记》以“继《春秋》”为己任,以“折中于夫子”“考信于六艺”为原则,班固却依然说其“是非颇谬于圣人”,实际上是以自己所信奉的神学化、绝对化的儒学来对照司马迁并不纯粹的儒学所得出的结论;而班固这种绝对化、神学化的儒学,便是对董仲舒独尊儒学、神学化儒家思想的一种继承。
最后,民族史撰述蕴含的民族大一统思想。《汉书》继承了《史记》的民族史撰述思想与方法,所作三篇民族史传《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和《西域传》,记述范围大致囊括了汉代中国周边各民族,因此,《汉书》反映的是汉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体现了各民族大一统的思想。同时在民族观上,《汉书》继承了董仲舒德化四夷的思想。如在《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班固肯定了汉文帝以恩德安抚尉佗的做法,明确主张对于夷狄应该实行“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政策。该传还充分肯定了各民族相互交往的意义,认为巴蜀之民正是由于与各地进行商贸往来,才“以此巴蜀殷富”的。在《西域传》中,班固主张实行德化夷狄之策。他一方面肯定文景盛世少生边事的做法:“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一方面则指出武帝由于连年征伐,晚年“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即使如对待匈奴,班固从维护大一统政治出发,对于其主动归化也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如《汉书·萧望之传》就肯定了汉朝天子对待来朝的呼韩邪单于以位在诸侯王之上之礼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有利于四夷乡风慕化之举,是国家“万世之长策”。
注释:
① 参见《韩愈全集·原道》,原文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参考文献:
[1] 董仲舒.春秋繁露[M].苏舆义证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班固.白虎通[M].陈立疏证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
[4] 焦循.孟子正义[M].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
[5] 阮元.十三经注疏:第五册[M].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6] 刘宝楠.论语正义[M].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张申府与张岱年研究”栏目特约主持人按语:
张岱年先生给朱贻庭先生关于《中国伦理学史》的信札共16通,本刊分5次以影印形式刊出,至本期则全部刊登完毕。这为我们今后深入学习与弘扬张先生中国伦理思想提供了一份具有原件影印特色的重要文献资料。
如何认识中西哲学之异同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而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张耀南、马鸥亚两位先生以“本体论”为例对“张岱年先生‘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之格式”的问题,作了相当系统而详尽的分析。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通过比较是认识中西哲学(以及张岱年先生的“本体论”思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法。张耀南、马鸥亚两位先生的文章充分肯定张岱年先生始终不愿直接以“西式本体论”释读中土哲学,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张岱年先生的“本体论”思想应如何评述,有兴趣者可继读研究之。该文并对当下学界寄以厚望:宜突破“近代学术框架”以“西化比”或“全盘西化”为上品的格局,而建构以“化西比”或“全盘化西”为“最高理想”的学术典范。张岱年先生的研究以及张耀南、马鸥亚两位先生的再研究,给了我们很多启迪,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作继续探索与深入研究。
——国际知名学者、哲学家、安徽大学资深教授 钱耕森
Dong Zhongshu and Ban Gu’s Historiography
WANG Gaoxin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the Han Dynasty history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Han Dynasty.Dong Zhongshu was a scholar who belonged to the school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Han Dynasty and a master of Gong Yang Study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His historical thoughts had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thoughts of Ban Gu, a historian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Dong Zhongshu’s theory of the telepathy between nature and man influenced Ban Gu’s notions of nature and man.Han Shu not only highly valued Dong Zhongshu’s “Tian Ren San Ce” (Dong Zhongshu’s three answers to Emperor Wu’s questions about nature and man), but also systematically advocated the theory of the telepathy between nature and man.In additon, Dong Zhongshu’s thoughts of “morality given priority over penalty” influenced Ban Gu’s notion of proprieties.Han Shu accepted Dong Zhongshu’s thoughts and positively advocated the policy of benevolent rules.What’s more, Dong Zhongshu’s theory of grand unification also influenced Ban Gu’s notion of grand unification.Han Shu, as a book only on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praised the achievement of the grand unification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ffirmed the necessity of the unified thought of “respecting Confucianism only” and promoted the thought of national unification.
Keywords:Dong Zhongshu; Ban Gu; Han Shu; historiography; telepathy between nature and man; morality given priority over penalty; grand unification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6)02-0016-06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6.02.003
收稿日期:2015-02-10
作者简介:汪高鑫(1961-),男,安徽休宁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