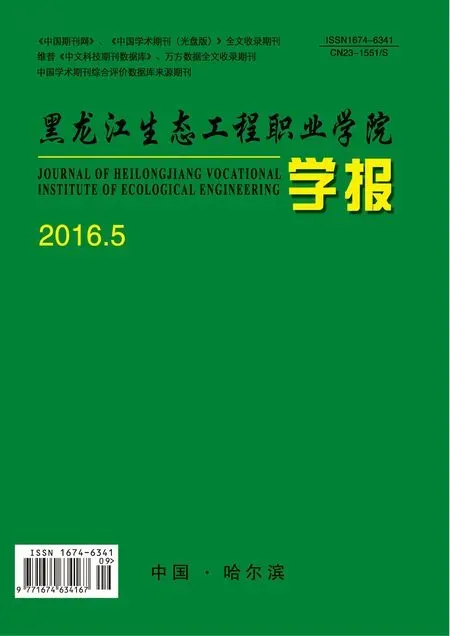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问题探讨
纪 茗 珠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问题探讨
纪 茗 珠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不真正不作为犯由于立法上不明确,理论界意见不统一,导致在司法审判的实践中不能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容易造成司法不公,不利于保障人权。研究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是解决不真正不作为犯问题的关键。明确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本质,理清其义务来源,使争议问题在学术上形成统一,并通过立法对典型的不真正不作为犯加以规定,使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作为义务;不真正不作为;不作为犯
在刑法理论中,作为和不作为均是危害行为分类的一种。其中不作为又可以分为真正的不作为和不真正的不作为。不作为犯罪的成立以存在特定的作为义务为前提。现在刑法学界通常认为,真正的不作为是刑法中规定了作为义务并将不作为纳入犯罪构成的犯罪,真正的不作为犯罪在学界没有较大争议,所以值得讨论和思考的是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不真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例如诸多“见死不救”的案件,司法实践在解决类似问题时并无标准确定的依据,判案经常会引起较大争议。因此,明确统一不真正不作为犯理论体系,给司法实践提供指导就变得十分重要,而其中明确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又是重中之重的问题。
1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的界定
下而故意不履行该义务。判断一个犯罪是作为还是不作为,首要的是判断什么样的行为是为刑法所需要评价的,再根据其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具体判断是作为的方式抑或是不作为的方式。不作为犯罪的典型特征是刑法并未对其义务内容加以规制,但不真正不作为犯并不缺少作为义务,其作为义务来源与真正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并无差异。据此,笔者认为,刑法之中的不真正不作为犯指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且没有被刑法明确规定其义务的作为义务人,有能力履行但不履行具有履行可能性的作为义务,以致发生了应当避免的危害结果的犯罪。
义务是贯穿于法学之中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法律义务是国家制定或承认,法律关系主体应这样行为或者不这样行为的一种限制或约束[1]。针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理论界还存在较大争议,通说的“四来源说”较多的是从形式方面来判定,不过也有一部分学者开始对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根据从形式列举之外的实质层面进行研究和探讨[2]。笔者认为,单独地从形式方面或者单独地从实质方面判断不真正不作为义务的来源都是偏颇的,在考虑不真正不作为义务来源时需要将形式层面和实质层面相结合。
不真正不作为犯违反命令性规范,刑法出于对于法益的保护,对正在发生的指向结果的因果进程放任不管、不介入的态度也予以处罚[3],这便是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原因所在。首先,现实存在现实紧迫的危险,行为人负有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不作为犯罪与作为犯罪一样,同样具有着使风险现实化或者增加风险的可能性。其次,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要有刑法之外的法律条文明文规定。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刑法的作为义务本应包含自身且同时还应包括民法、行政法律等非刑事法律。刑法作为义务是一种积极的、针对特定人员的义务,作为义务人基于特定法律规定而对享有权利人应积极地做出特定行为[4]。正是因为刑事法律的欠缺,所以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至少应该被其他法律明确规定。否则,在无任何法律依据而要求行为人承担作为义务未免是强人所难。再次,具有结果回避的可能性。典型的如行为人因自己的先行行为而对受害人负有救助义务,但事后鉴定结果表明,受害人的死亡完全由其先行行为导致,与行为人的不救助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已经不存在救助的可能性,此时只能成立相应的作为犯罪。最后,不真正不作为犯引发的危害后果与作为犯罪具有等价性。例如,警察甲发现乙正在持刀追杀自己的妻子,在具有履行救助义务的情况下,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被害身亡,由于警察甲的行为与不作为的玩忽职守罪具有等价性,与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之间不具有等价性,故对于警察甲仅仅构成玩忽职守罪。
2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发生根据
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通说“四来源说”分为法律规定、先行行为、职务业务行为以及合同行为四种情形。然而这种表述在定罪量刑之中并不能很好地诠释各类情况,笔者从司法实践的角度,以一个较为崭新的思路对其进行分类,主要如下:
2.1因持有危险物品或者制造风险而产生的作为义务
行为人因持有可能造成他人法益受到侵害的危险物品的存在,负有防止危险发生的义务。行为人对危险物品的持有必须是要达到对其有支配能力的地位。最常见的是:饲养大型动物,例如藏獒;对放射性物品的存放;有毒有害物品的存放,等等。因制造风险而产生的作为义务也可以理解为因自己的先行行为引起的法益侵害危险的防止义务。比如,黑夜中将汽车停在高速公路上,则负有义务防止后面的车辆追尾。
2.2基于危险源的支配而产生的作为义务
行为人对危险源的支配与控制地位会使其承担刑法上的作为义务。首先,因开设公共场所而产生的作为义务。公共场所是供公众从事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所的总称。公共场所本身并不是危险源,只是在这公共场所之中发生了危险,开设场所的人负有控制危险源的义务。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如在公共汽车上,乘务人员具有保护乘客的义务。开设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员对其所管控的领域具有支配地位,负有保证义务,担当保证人的角色。但管理者只负有在其支配范围内的排除危险的作为义务,因管理原因而导致损害则必须负有救助义务,否则要相应地承担不作为的责任;而对于支配范围内,行为人自身引发的危险,则并不必然地承担责任。其次,对自己支配的建筑物、汽车等场所内发生的危险具有阻止义务。对于马路上摔倒的人,路过的行为人不具有救助的义务;而若是行为人摔倒在自己家的庭院之中,则院落的支配者就负有救助的义务。
2.3基于法益的无助而产生的作为义务
法益的无助性是指法益的权利人在濒临危险之时对自己的境况无能为力,需要外界干预才能避免自身法益受到侵害的情况。通常表现如:婴儿需要母亲的喂养;驾校学员需要教练指引开车并防止危险的发生。此外,还包括因自愿承担而产生的作为义务,即在行为人无缘由救助他人,使其脱离现存的危险后不继续实施救助,从而使被救助者陷入比救助之前更加危险的情境,在此情况下,行为人则负有继续提供救助的义务。例如,甲在外出游玩时,见到草坪之中有被人遗弃的弃婴,心生怜悯,便将其抱回家中抚养。甲因为自愿承担而具有了义务,不能再将弃婴放回原处或者抛弃,否则就可能构成相应的不作为犯罪。
通过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发生根据进行以上的分类,仍然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这就需要在司法实践之中具体问题具体进行把握。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正当防卫是基于不法侵害而实施的行为,对于给侵害人造成的危险状态不负有救助的义务,不能够成为不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仅在特殊情况下负有一定的作为义务。例如:甲见义勇为制止了正在实施不法侵害的乙,致使乙身受重伤,但在正当防卫的限度之内,乙忏悔要求甲实施救援,但甲不予理会,乙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肯定甲对可能过当的危险具有保证人地位,甲的不救助导致乙死亡,属于防卫过当。乙的死亡虽然与甲的不救助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同时基于法益的无助性,甲也负有一定的作为义务。与之相对的刑法另一免责事由——紧急避险所引起的危害后果,行为人当然地负有作为义务。紧急避险行为所损害的是无辜第三者的权益,对给无辜者造成的损害对其来说是无端的、不法的侵害,自然负有作为义务。第二,行为人自杀、自残问题。首先,人生而自由,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存与否;成年人有权利允许他人对自己进行轻伤以下的故意伤害身体健康的权利;其次,可以运用相当因果关系说中介因素中断理论诠释行为人自杀、自残问题;再次,行为人的风险是由自身的行为所直接导致的结果,并不能引起行为人的作为义务。
3 不真正不作为犯中的典型争议问题
刑法条文中并未明确规定不真正不作为的作为义务,对具体案件进行评析时,判断是否成立不作为犯罪以及成立何种不作为犯罪,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不真正不作为犯罪不仅要具备形式内容,还要看行为人是否履行作为义务的实质内容。面对纷繁复杂的犯罪现象,笔者就以下典型争议问题进行探讨:
3.1不真正不作为犯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许多学者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缺乏刑法规定的义务,认定犯罪缺乏刑法依据,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任何刑法理论都需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对此,大陆法系通说认为,对不真正不作为犯进行处罚,在形式上存在着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质疑,但在实质上并不存在冲突。仅从形式的角度出发,的确应对此提出质疑;但是从社会观念上看,这样的不作为无疑是当罚的。因此,关于不真正不作为犯,不应当认为刑法上没有处罚规定,而应当认为在形式上是作为犯的规定中实质上一并包含着不真正不作为犯。
我国刑法条文中某些条款具体规定了不作为的义务,但是更多数的条文并没有就义务作更加明确的规定。例如,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从条文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故意杀人罪并没有明确规定不作为的作为义务,即要求不作为行为人具有防止他人死亡的义务。但是,现实情况行为人以杀人的故意采用不作为的手段实施杀害行为,理所当然要判定为杀人罪。条文描述故意杀人,也并没有明确说明禁止杀人,但我们却可以理解为禁止他人故意致人死亡,是一种禁止性规范。众所周知,适用刑法条文不能照本宣科教条地理解条文含义,刑法适用需要解释。因此,不真正不作为的作为义务应该包括在合理合法的刑法解释中。从另一方面讲,如果刑法能通过立法手段明确不作为的义务,则更能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也更能够为司法实践提供可以参照的标准和依据。
3.2犯罪行为能否成为先行行为
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先行行为只要足以产生某种危险,就可以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而不必要求先行行为必须具违法的性质[5]。笔者认为,对于犯罪行为能否成为先行行为,应当分情况予以判明。首先,在刑法对某种犯罪行为引发的重结果进行了评价,先前的犯罪行为则不能成为先行行为。例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本身就已经触犯刑法的情况下,同时又致人死亡或者重伤,对此结果只能以结果加重犯论处,而不再单独以不作为犯罪来处理。典型的例子还有交通肇事罪,肇事构成交通肇事罪后逃亡,导致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而死亡,此时显然不能在给肇事者定一个故意杀人罪,只需要按照加重结果的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提升法定量刑即可。其次,在刑法对加重的结果没有进行评价的情况下,如果先前的犯罪行为导致了另外一个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此时行为人具有防止该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例如,甲深夜从他人房梁进入,实施入室盗窃,不慎将房梁上的柱子踩断砸到房主乙,乙身受重伤后,向甲进行求救,甲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逃跑,乙因失血过多而死亡。盗窃罪并不能评价他人死亡的严重结果,并且甲负有救助乙的作为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先前的犯罪则可以成为先行行为,而对甲则应以盗窃罪和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将犯罪行为划分到先行行为之中,有利于实现刑法的协调以及解决正当防卫等问题。在此需要注意另外两点:第一,一般过失行为也可以成为先前行为。例如,行为人在给家中养殖的花浇水时,不慎花盆坠落砸到正在楼下行走的甲,在明知不及时抢救就会造成甲死亡的情况下,行为人依然不进行救助,其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就可能成立。第二,非犯罪行为也可能产生不真正不作为的作为义务。例如,十四周岁的甲在生日的当天将一枚自制的炸弹,安置于繁华地段的某商场地下停车场,设定炸弹于第二天上午八点准时爆炸。此时,由于甲不满十四周岁(生日当天不计入其中),在刑法意义上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因而甲的行为不是犯罪行为。但是在生日当天十二点之后,甲由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转化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人,此时甲就具有一个阻止炸弹爆炸的作为义务,在甲没有解除炸弹任其爆炸的情况下,甲就是不真正不作为犯,即以不作为方式实施了爆炸罪。
综上所述,我国刑法理论体系是通过作为犯罪来组建的,通过刑法的规制来规定行为人应为与不应为。归根到底,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要注重实质层面与形式层面相结合,依据作为义务来进行判断。司法实践所面临的问题对刑法作为义务的理论不断提出新的挑战,法律的滞后性虽然是无法避免的,但准确地界定不真正不作为义务的范围对司法实践仍然举足轻重,只有与时俱进,调整不真正不作为犯罪的相关理论才能更好地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
[1]朱景文.法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71.
[2]樊华中.论不纯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D].成都:西南政法大学,2009.
[3][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97.
[4]栾莉著.刑法作为义务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50.
[5]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36.
责任编辑:卢宏业
10.3969/j.issn.1674-6341.2016.05.023
2016-03-09
纪茗珠(1990—),女,山东烟台人,法学院2015级硕士(法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法。
D914
A
1674-6341(2016)05-005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