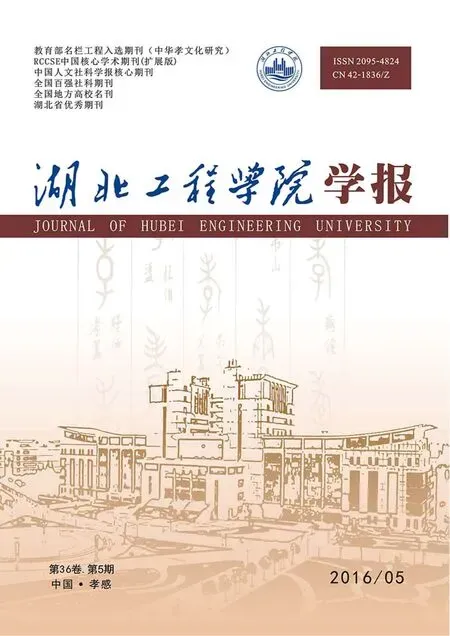新世纪湖北小说底层叙事的独特性
江胜清
(湖北工程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新世纪湖北小说底层叙事的独特性
江胜清
(湖北工程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新世纪以来,随着作家视点的下移,底层叙事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创作思潮,也是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文学现象。与全国其他地域的底层叙事相比,湖北小说底层叙事自成一家,特色鲜明。而底层叙事主体的精英化、底层叙事的多元化、底层叙事的辩证性等是其突出的表现。总之,湖北是新世纪底层叙事的重镇,是新世纪中国底层叙事多重奏中的一个重要构成,是新世纪底层叙事的一个重要收获。
新世纪;湖北小说;底层叙事;独特性
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学环境以及读者审美观念和阅读方式的改变,中国文学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出现许多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底层叙事即是其中之一。“‘底层文学’自2004年前后发轫以来,在几年期间获得广泛响应,成为近二十年来文坛进入‘无主潮’阶段后最大的也可称唯一的‘主潮’。”[1]
湖北是新世纪底层叙事的重镇。刘继明是底层叙事的倡导者和发动者,他与李云雷关于底层叙事的探讨,拉开了新世纪中国底层叙事的大幕;他也是底层叙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刘继明的带动下,方方、陈应松、刘醒龙、池莉、叶梅等作家悉数登场,纷纷投身底层叙事文学大潮之中。
湖北之所以成为新世纪底层叙事的重镇,是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与新时期湖北文学传统密不可分。新时期以来,湖北作家一直坚守现实主义的写作路线,关注改革变动中活生生的中国现实,其关注的视野始终放在社会的基层,新世纪底层叙事是这一叙事传统的自然延续和发展。其次,新时期湖北作家大多来自农村,多有底层社会的经历。因此,他们对社会底层有着特别的情感。再次,20世纪90年代湖北作家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潮流主要是新写实,方方、池莉正是借新写实浪潮而轰动全国,新写实是关注那个时代的底层,相当于90年代的底层叙事。
与其他区域的底层叙事相比,新世纪湖北小说自有其优势和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底层叙事主体的精英化
新世纪中国小说底层叙事作家群可以分为草根作家群和精英作家群[2]。前者有张伟明、林坚、安子、周崇贤、王十月等,大多由“打工者”蜕变而成,主要集中在广东;后者以孙惠芬、荆永鸣、罗伟章、陈应松、方方、胡学文等为代表,分散在全国各地,是由一些成名作家华丽转身所致。
新世纪湖北小说底层叙事的主体,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的精英作家群(王十月是底层叙事草根作家的代表,但因其很早就离开湖北,在深圳打工,成为南漂一族,新世纪后登上文坛,因此,他并未被纳入新世纪湖北作家的范围之中)。他们不仅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也得到评论界的充分肯定,还成就了湖北文学的光荣,使湖北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大省。这之中既有方方、池莉、刘醒龙、陈应松、叶梅等50后作家,也有刘继明、张执浩、曹军庆、姚鄂梅等60后作家。
到了新世纪,这些奠定湖北文学大省基础、铸就20世纪90年代湖北文学辉煌的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将创作视野转向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底层叙事。
有的华丽转身,如方方、陈应松、刘继明等。方方由关注都市知识分子命运转向思考乡村底层女性的悲剧,由观照都市市民生存状况转向审视都市下岗工人的现实;陈应松从水乡走进神秘神奇的神农架,由追寻水乡诗意到探寻神农架之谜;刘继明走出“文化关怀”,开始直面农民工惨淡的人生,完成了“先锋的‘底层’转向”。[3]
有的重拾旧梦,如刘醒龙。刘醒龙踏着凤凰琴的音符走出“大别山之谜”,在分享现实艰难、探访圣天门口之后,重拾凤凰琴,再奏动人的乐章。
有的小试牛刀、浅尝即止,如池莉、叶梅、邓一光、姚鄂梅、张执浩、曹军庆等。虽偶一为之,却不时给人惊喜。
新世纪以来,湖北作家创作了一大批底层叙事的小说。方方《奔跑的火光》《出门寻死》《万箭穿心》《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陈应松《马嘶岭血案》《太平狗》《松鸦为什么鸣叫》《八里荒轶事》等,刘继明《放声歌唱》《我们夫妇之间》等,刘醒龙《天行者》,叶梅《五月飞蛾》等,都在全国引起轰动,产生较大的影响。
“文明素养”示范。采用推荐和寻访相结合的方法,在全市范围大力实施“万千百”工程。展示“万家文明风”。在全市各主要媒体开辟专栏,发掘、推出家庭文明新事,用凡人小事打动人,用身边事引领身边人,将发动的过程变为再教育的过程,以此带动全社会风气的不断好转。选树“千人公德榜”。在新闻媒体、大型户外媒体等设立“千人公德榜”,及时宣传弘扬社会公德的典型,汇聚点滴“善小”,形成强大的道德正能量。上好“百堂道德课”。利用“万家文明风”展示和“千人公德榜”设立的契机,广泛收集身边典型人物的典型事迹,使之成为全市道德教育的生动教材。
二、底层叙事的多元化
底层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底层叙事涉及的领域也很广泛,因此,无论是底层叙事的方式、还是底层叙事的对象都具有多样性。有学者将新时期以来湖北作家的底层叙事概括为四种形态:“喜剧形态、荒诞形态、伦理形态、悲剧形态”[4],从一个侧面印证出湖北作家底层叙事的多样化。
伴随着经济持续迅猛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贫困人口日益减少,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到了新世纪,中国社会阶层中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底层主要有中西部偏远农村农民、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城市下岗职工等三个社会群体,而新世纪文学底层叙事也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方面。作为新世纪全国底层叙事的重要构成,新世纪湖北小说的底层叙事呈现出与全国同步的态势。
展示中西部偏远农村乡村苦难和贫困,是新世纪湖北小说底层叙事的一个重要表现。陈应松、方方都有不俗的表现,尤其是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最为突出。新世纪之初,陈应松离开了喧嚣的武汉到宁静的神农架挂职锻炼,他的创作灵感被神秘的神农架激活,他终于找到了施展自己创作才华的创作领域,也开辟了自己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地,他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井喷的态势,一发而不可收。继《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之后,他接连推出了《马嘶岭血案》《火烧云》《太平狗》《豹子最后的舞蹈》《八里荒轶事》《猎人峰》等“神农架系列小说”,将湖北西北部山区村民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艰难的生存状态,艺术地展示在读者面前。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既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事件,也是湖北底层叙事的重要收获。
表现进城求生的农民工的艰辛和无奈,是新世纪湖北小说底层叙事最主要的构成。农民工群体的庞大、在而不属的尴尬、生存的艰难以及城乡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成为新世纪底层叙事的宠儿,涉及作家之众、产生作品之多,都令人惊叹。王十月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遗憾的是,他一直以“南漂”的身份游走在深圳等地,未能纳入湖北文学的视野。严格说来,湖北小说在书写农民工进城求生这一方面并无优势,也未形成规模,不过,刘继明、叶梅、姚鄂梅等作家在这方面的探索,也卓有成效。刘继明《放声歌唱》、叶梅《五月飞蛾》、姚鄂梅《一线天》、陈应松《太平狗》等,都表现了湖北作家对农民工生存境遇的关注,达到了应有的高度,体现出湖北作家独特的思考。
再现城市下岗工人的失落和困顿,也是新世纪湖北小说底层叙事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方方在这方面尤为突出,最有成就。新世纪以来,方方在爱情叙事和历史叙事上取得突破的同时,更关注底层叙事,《出门寻死》《中北路空无一人》《万箭穿心》等小说对城市下岗职工生存状态进行了持续关注,表达了个性化的思考,不仅体现了方方一以贯之的特色,也代表了中国作家思考的新高度。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外,新世纪湖北小说底层叙事还在两个特殊的维度有着独特的发现。一是方方大学生底层叙事。《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十月》2013年第2期)将新世纪贫困大学生纳入叙事范畴,将人们心目中象牙塔中天子骄子收入底层叙事之中,这部长篇小说是继何建明报告文学《落泪是金》之后又一部关注大学校园大学生贫困的作品,读罢令人唏嘘不已、扼腕叹息。二是刘醒龙的乡村教师底层叙事。刘醒龙在20世纪80年代以一部反映乡村民办教师生活的中篇小说《凤凰琴》登上文坛,一鸣惊人,赢得巨大声誉。民办教师是中国社会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尽管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毕竟曾是中国教育的一个特殊标记,无疑是中国教师中的底层。新世纪,刘醒龙怀着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特别情感和独特认知,重新聚焦于此,在《凤凰琴》的基础上,再度发掘和拓展,推出长篇小说《天行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作者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对处于教师底层的民办教师进行了新的关注和审视,表现了作家的新思考,小说又一次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荣获茅盾文学奖,成为新世纪小说底层叙事的一个重要收获。
三、底层叙事的辩证性
正视乡村贫困落后又展示村民的淳朴善良。正视乡村贫困是新世纪小说底层叙事一个普遍追求,湖北作家也不例外。湖北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人口比重大,农业不太发达,这也是制约湖北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因素。新世纪湖北小说家展示乡村贫困时,更多的是将其目光聚焦湖北西北部农村。陈应松笔下的神农架、叶梅文学中的故乡恩施、方方小说中的十堰等,都或隐或现、或浓或淡地展示了湖北乡村的贫困。九财叔因20元钱而残忍杀害勘探队7名队员,涂自强为了节省路费,毅然决然徒步跋涉几百公里到武汉上大学,这些都是乡村贫困和落后的一个缩影。乡村尽管贫困和落后,但湖北小说家却依然能从乡村苦难中发现村民的淳朴善良。《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伯纬为了兑现自己的一个承诺,利用古老的“赶尸”方法,将在工地爆炸身亡的王皋的尸体从崇山峻岭中带回家乡安葬;后来定居桠子口,每当发生翻车事故时,他总是冒着危险下到山谷救死扶伤,不思回报,无怨无悔。《八里荒轶事》中的端加荣饱受丈夫戕害,又屡遭村长愚弄,求助乡政府却投诉无门,即便如此,她从未丧失生活的希望,而以超出常人的坚韧,在人迹罕至的八里荒开荒种地,艰难谋生,即便是女儿被野兽咬死也决不放弃。
展现都市下岗工人生活的艰难又透视其活着的坚韧。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转型,原本风光无限的国有企业夕阳西斜,渐成明日黄花,作为社会阶层中“老大”的工人也褪去了昔日的荣光,下岗工人成为城市沦陷的标志,也是新世纪中国城市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在底层叙事大潮的涤荡下,许多作家不约而同地注视这一独特的都市生存图景,方方《出门寻死》《万箭穿心》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小说既展现了下岗工人生活的艰难,又表现了下岗工人的坚韧。《出门寻死》是叙述下岗女工何汉晴的“烦恼人生”:自己下岗多年,一心操持家务,不仅要忍受便秘的痛苦,还要承担做不完的家务,更要遭受公婆的打压、小姑的刁难和丈夫的埋怨……在生活的重压下,她万念俱灰,出门寻死,以求解脱。但偌大的都市竟连一个寻死之地也难寻觅,最终在汉江桥上找到一个好的所在,很快又被告知知音桥有一个女人正准备投江自杀。于是,她转而开始与女子交流,劝其放弃轻生念头,为了孩子好好活着,在她的劝导下,女子最终回心转意,放弃轻生。她也在劝解别人的过程中,找回了生活的信心和活下去的勇气。《万箭穿心》中的李宝莉虽然下岗却有一个温馨的家:丈夫马学武是一个工厂办公室主任,不仅拥有一套四居室的江景房,还有一个惹人喜爱的儿子。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温馨的家轰然坍塌:马学武随着地位的提升产生了追求“家外有家”的浪漫,在外与另一女子频频约会,甚至开房。李宝莉跟踪发现后向公安局举报,导致马学武最终身败名裂、自杀身亡。在经历重大家庭变故后,李宝莉怀着一丝内疚,毅然用柔弱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担。她摇身一变成了汉正街的“女扁担”,以自己的艰辛劳作,支撑起摇摇欲坠的家,但她无私的付出并未换来应有的回报:儿子成人后拒绝接纳母亲,公婆在孙子成人后将她无情地逐出家门。李宝莉最终孤零零地回到汉正街,依旧延续着她的扁担生涯,而支撑她坚定走完人生之路的信念是:人生“纵使万箭穿心,也得扛住”。
再现农民工都市谋生的艰辛又凸现农民工的追求。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与农民工的付出是密不可分的,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智慧装扮着城市的容颜,筑起了城市最漂亮的高楼和美轮美奂的商城,但他们却成为城市美丽背后的阴影。在“别人的城市”里,他们在而不属,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反而遭受诸多歧视和不公。“中国的‘农民进城’是充满艰辛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进城并没有得到正面的认可, 20世纪80年代曾被戴上‘盲流’的帽子,很难在城市立足。90年代开放了,但进城务工还要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收取各种各样的管理费用,一些没有办全证件和没有找到工作的农民常被作为‘三无人员’而遭到收容和遣返。”[5]新世纪湖北小说正视农民工进城谋生的艰辛,刘继明《放声歌唱》中的主人公钱高粱,本是中国乡村一名打丧鼓的民间艺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自己钟爱的民间艺术而进城务工,在建筑工地因工伤而致残,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救治,也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求助法院但哭诉无门,只能在法院的办公大楼上唱丧歌。陈应松《太平狗》讲述神农架山民程大种到武汉打工的故事,在城市,程大种从城市姨妈待客之道中感受了都市人情的冷漠,在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关心他的只有一只追随而来的太平狗,都市之世态炎凉可见一斑。最后他被禁闭在一个黑工厂的高墙内如奴隶般地工作,不幸惨死。湖北作家在艺术再现农民工都市谋生艰辛时,与其他地区作家并无区别,但他们并不是一味地表现困难,也正面表现农民工的追求。叶梅《五月飞蛾》在农民工题材小说中可以说是别出心裁。与一般表现女性农民工自我迷失和自甘堕落不同,《五月飞蛾》没有刻意暴露打工妹的阴暗生活,而是展示打工妹自立自强的阳光心态和独立谋生的理想追求。二妹满怀憧憬告别乡村来到都市,同其他女孩不同,她并不满足赚点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城市人,或者以青春作代价换来一个城市人的名分,而是要在保全自己人格的前提下学得谋生技能,用勤劳的双手创造自己的世界,二妹因此也成为底层叙事小说中一个独特的存在,成为一盏暗夜中照亮人心灵的灯火。小说反其义用之,给“飞蛾扑火”这一成语注入了新的内涵,给新世纪女性农民工叙事小说涂上一缕阳光,带来一些温暖。
表现城乡尖锐对立又哀叹乡村美好的消失。表现城乡尖锐对立,是涉农底层叙事小说的共同价值取向。在底层叙事小说中,城市像一个巨大的魔兽,肆意践踏着乡村美丽,无情地吞噬着青春和生命。安安由乡村纯洁少女蜕变为都市按摩女郎(《五月飞蛾》),多才多艺的乡村民间艺人钱高粱在城市变成残疾人(《放声歌唱》),淳朴善良的程大种一次都市打工之行换来的却是魂归故里。不仅如此,城市还以其巨大的优势挤压着乡村。城市人的过度开放和破坏,打破了乡村的平和宁静,抹掉了乡村的美好和美丽,农村已成为农民“想要挣脱和逃离的生死场,而不是希望的田野”[6]。而城市对乡村的过度挤压,必然会引起乡村的反抗或报复,《马嘶岭血案》中的九财叔正是在城市对乡村任性的鄙夷和践踏中,慢慢滋生仇恨,最终导致仇恨大爆发,九财叔也因此成为乡村对抗城市的典型。在表现城乡尖锐对立的同时,湖北底层叙事小说也对乡村美丽和美好的逝去,表现出无比的慨叹和无限的感伤。陈应松的《狂犬事件》《豹子最后的舞蹈》等小说揭示出城市文明导致乡村生态的恶化和乡民生存的困境。《放声歌唱》借钱高粱进城求生的悲惨境遇,折射出“打丧鼓”这一民间歌舞的衰落,表现了农民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迷失,而且在文化上也失去了主体性。
总之,新世纪湖北底层叙事小说自成一家,别具特色,体现了湖北作家独立的思考。新世纪湖北底层叙事小说不仅壮大了底层叙事队伍,而且提升了底层叙事的品质,它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底层叙事大潮中一个重要构成,也是新世纪底层叙事华章中的重要收获,在新世纪中国文学中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
[1] 邵燕君.从现实主义文学到“新左翼文学”——由曹征路《问苍茫》看“底层文学”的发展和困境[J].南方文坛,2009(2):50.
[2] 周水涛.新时期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7-9.
[3] 李云雷.先锋的“底层”转向——刘继明近期创作论[J].小说评论,2008(2):131.
[4] 李遇春.新时期湖北作家底层书写一瞥[J].小说评论,2008(2):94.
[5] 严正.中国城市发展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76.
[6] 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J].读书,2005(7):74.
(责任编辑:李天喜)
2016-07-11
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2012D008)
江胜清(1966- ),男,湖北孝感人,湖北工程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I206.7
A
2095-4824(2016)05-005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