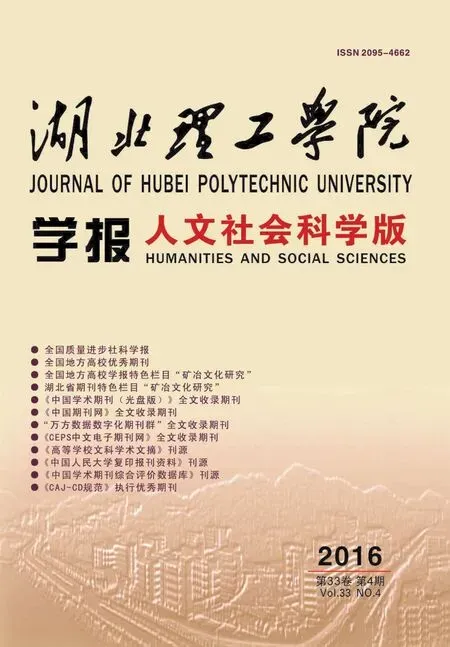先秦道家休闲哲学之身体论结构
江 渝
(三峡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先秦道家休闲哲学之身体论结构
江 渝
(三峡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先秦道家(以老庄为中心)之休闲哲学,其核心在于关注个体生命在社会规训、政治压力下的保全与展开;全身成为道家休闲智慧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道家由此建立起一套身体论的休闲智慧,安身以止贪欲,心斋以致真知;身之大患的解决,可以物化以忘俗形,可以逍遥游以自得:这二者可代表道家休身之具体策略。
道家;老子;庄子;休闲哲学;身体
中国古代休闲活动,其根基是身体的休养闲适,全身、保身是其出发点,也是推动休闲行为展开的一股内在动力。中国俗语常用的“保重”,直接的意思就是保持健康的体重勿消瘦。《晋书·夏侯湛传》有言:“方将保重啬神,独善其身。”[1]点明保重的目的还是在“身”上。古人又常言:“努力加餐饭”(《昭明文选·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胃口好身体好才是真的好,也正是这种观念的形象表达。
追索“休闲”的古代语源,可见其与全身观念关系密切。“休”,甲骨文像一个人在大树下歇息,是劳作间隙的小休小憩[2]。《诗经·生民之什·民劳》有言,“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就是讲休的珍贵价值,在于从劳动中的小解脱。正是劳人的辛勤工作,才使得贵族得以休闲享乐。“无弃尔劳,以为王休”,站在王的立场上,他其实也不愿意民“休”,故而会以“游手好闲”之类的消极用语来谈论民之休,小百姓也只能去“忙里偷闲”。“闲”,其休闲的意义是从“閒”字间隙之意(晚上月亮出来了,照在门上显出条小缝隙)借用过来的,似乎可以说是对夜晚休息之意的比兴引申[3]。由此可见,休、闲,都是人从劳动中的小解脱、小自由、小闲暇。毕竟,白天还得工作,“小休”不比“王休”。“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民力不堪,其皆入室……”(《淮南子·时则训》)这短暂的放松,首先是对身体的解放,可以摆脱劳动纠缠;其次才是心灵的愉悦感受,才是自由的呼吸。西方学者皮珀追溯“闲暇”在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意思,指出它是指“学习和教育的场所”,在古代,人们“称这种场所为‘闲暇’,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校’”[4]。西方传统的休闲具有了超越的宗教性质,精神—灵魂可以在闲暇、休憩中自我超越,获得绝对的纯粹的自由。这与咱们国人休闲观之忙里偷闲的出发点大有区别。
中国文化对身体的看重几乎是众口一词。孙隆基从“吃”的角度,指出了中国文化的重身思维,认为国人特别看重进补养身,以“揾身”而“安身”,追求肉体的长存久续[5]。这种肉体性的生存状态,还进而发展为“肉身性”的语言习性[6],以及“重己”、“先己”的主体精神。《吕氏春秋》特标《重己》《先己》与《必己》之篇目,云:“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吕氏春秋·先己》)。不论是“重己”之主体优先思维,还是养身之生活宗旨活动,其共同点都在于对自我存在尤其是肉身存在的保重。它们均“强调‘全身’的至高价值”,将“自身”的物质存在视为一切“道德行为和其他实践活动的前提……对于生命的看重和着意研究,逐渐演变成一种民族的社会和学术的风尚,上升为一种具有哲学、伦理和审美意义的观念。”[7]
重身、全身之观念在中国古代休闲哲学思想中占有其结构性的地位。身全而后才能自得,身体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古人休闲活动的实际展开与理论思考。身体的保重在先秦道家看来尤其重要,画家梅墨生认为:“老庄是教授中国人享受悠闲之福的始祖,又是教授中国人具有‘活命哲学的’观念的始祖。”[8]本文试图揭示与梳理先秦道家(以老庄为中心)休闲哲学中的身体论结构:道家之休闲,其核心关注就在于个体生命在社会规训、政治压力下的保全与展开;于是非常自然,“保身”成为道家休闲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道家由此出发建立起了一套身体论的休闲智慧;身之大患如何解决?可以虚静以止欲,可以心斋以致知,可以物化以忘形,可以逍遥以自得:可谓道家休身之具体策略。总而言之,身体与休闲,在道家看来是同一人生经历的不同面向。
一、亡身不真:休身宗旨
全身保命,身闲自安,实是古人首要的存在目标。《庄子·应帝王》中的接舆有言:“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接舆说得明白,全身避害,是连飞鸟鼷鼠都知道的本能,人最重要的德行也就是如此罢了,治理天下,或者被天下治理,保命避祸都是每个人的基本出发点。先秦不论儒家道家,对生命都持坚定的保重态度,正是国人怕死重生状况的理论表达。“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身体、生命为根本要害,必须好好保护。庄子反复申说身体之于个人的重要性,“善夭善老,善始善终”(《庄子·大宗师》)的生命状态,需要我们小心地去“养身”、“保身”才可实现,如果忽视了身体而忘情于俗世,“行事之情而忘其身”,必将“身为刑戮”(《庄子·人间世》)。“亡身不真”(《庄子·大宗师》),真实个体的真实生命,首要条件就是要全身、保身、养身。
(一)亡身不真
春秋战国之乱世,封建解体,礼崩乐坏,战争成为社会常态。于此水火之际,人对生死之变看得分外切身,于重身全身的重要性体察得尤其真实。有学者言之:“庄子……人生哲学的终的,也正是士阶层在乱世中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求生存的哲学。”[9]
道家休身以自得的思想也就是在此大环境中开始萌芽生长起来的[10]128。战国中后期的道家思想先驱们,都对身体十分看重。比如杨朱,《孟子·尽心上》记载:“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持此种思想者在当时还大有人在;《吕氏春秋·审为》还记载了一位詹何“重生则轻利”的说法,以及另一位子华子的重身理论。这些道家思想的滥觞者们的重身思想还较为零散,到了老庄,就已经将其发展为一个体系性的身体休闲理论了。
对身之大患,老子言之凿凿:“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老子》)汉代河上公注之曰:“有身忧其勤劳,念其饥寒,触情从欲,则遇祸患也。使吾无有身体,得道自然,轻举升云,出入无间,与道通神,当有何患?”[11]身体被看作逍遥生存的首要障碍,似乎人生之乐与身体之在有着矛盾冲突。对老子的“无身”观,惯唱反调的袁枚在《牍外余言》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道天下大乐,以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又何乐?盖人先有身而后有吾,无身则无吾矣。吾与身不能外而二之也。”[12]这样的看法其实是误解了老子对身之隐患的担忧。有身才有我,有我才有我之乐,这是从正面谈身为乐之基本条件;相辅相成,身也同样是痛苦与逼迫的基础;而老子恰是忧心于人们对乐的眷恋与痛的畏惧中所隐藏的危险。说到底,袁枚与老子各自的讲法并不矛盾。
正因为人之重身重我,才使得我之被束被缚成为了可能;也正因为身之患,才使得我有了被压抑的危险与可能:这才是老子所关怀的大问题。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特别表述了他主奴辩证法的逻辑,两个平等者的对抗,胜利者因其不畏死亡的恐怖,失败者却因其贪恋此生、重视生命而沦为奴隶。对于死亡的恐惧,由此成为了人类社会压迫、奴役、精神演化的原初动力。人的身体的有限性、有死性从此具有了原生的哲学意味[13]。道家哲学在此与之异曲同工,《庄子·逍遥游》记载了宋钘“见侮不辱”的思想:“宋荣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同样,在《吕氏春秋·正名》中还记载有尹文子“见侮而不斗”的言论。老庄对于这样的思想倾向是甚为赞许的:“老子曰:……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荣辱之理,举世誉之而不益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文子·上礼》)他们都认为,面对死亡的挑战与威胁,全身保命才是上策。
面对死亡,畏死者沦为奴隶,无法逃避被主人统治的政治命运。道家全身保命之思考,也同样起于他们对政治压迫的莫大拒绝,对被人奴役的巨大恐惧。“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庄子·齐物论》不去与人争斗取利,为求自保,不得不选择无视政治乃至拒绝政治[10]478。面对外界的压力,规避方外,那些庄子所谓的“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和“避世之人”都是好榜样。
(二)安时处顺
古人说得好:“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14]小老百姓希求摆脱帝力的奴役,帝力却要以农为本,在农民的辛勤劳动之上享受“天休”的快乐,在这个向内压榨来提高生产力获取GDP的社会里,在这个彼此利用、层层剥削的社会里,不论士农工商,不论身闲心闲,逃避政治权力都是不得不为的选择。“余立于宇宙之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庄子·让王》)避免与帝力接触,才可能“逍遥于天地”,二者的关联不言而喻。
为了珍惜生命、逃离政治的戕害,而休身闲性,国人这样的选择是苟且,是小休;而在思想感情上的技巧就是自我安慰、自我欺骗,美其名曰“知足”。这是老庄一派在国人心目之中产生的消极的影响。《老子》云“去甚、去奢、去泰”。就是在要求我们放低身段,不要有超过全身保命的更高要求,“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庄子也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要求越低越容易满足,越不容易失意。“为腹不为目”,重生不重名,别太多心灵精神上的虚幻想法。老庄对师旷、离朱们大加训斥,“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庄子·胠箧》)。希望人们别去迷于声色,只要安身知足就好了,欲望是会自我繁殖的东西,当它日渐滋长之后,为了填满欲壑,奴役与暴力是唯一的选择。如果需要休闲娱乐,在劳动中就可以满足了,“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劳动者的休闲娱乐,与劳动不可分离,这样既照顾了政治的要求,又避免了欲望的迷乱。
这种知足的思想被发展开来,就成为了知命、顺天、自然的休闲心法,庄子反复申言,“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庄子·大宗师》)。老庄选择了一条顺时而动、不与争锋的全身保命之道,希望得以从帝力下全身。正如胡伟希先生指出的那样,中国“休闲理论要教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仅仅去化解人生的痛苦,不如说是如何去面对这些痛苦或苦难”[15]。道家休闲哲学的出发点,不过是为了一身性命之暂得休憩罢了。
二、大知闲闲:休身智慧
不论是知足知止,还是顺时而动,其关键都在于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即认识自身的欲望、需要,以恰当合适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身之要求。这直接导致了道家哲学对欲望的知识论思想,这才是道家休闲哲学的积极智慧。一方面,是认识何为欲望,另一方面是确定一种正确解决欲望的行动知识;这两方面都实现之后,就能让人获得一种闲逸放达的自由享受了。
(一)无欲忘形
道家所止之欲为不当之欲,为满足一己之私而去奴役他人的权力欲。“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16]106一方面,道家不仅自我无欲,还要求他人乃至整个社会都无所欲,“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正如陈鼓应所解说的那样,老子在此并不是“要灭除自然的本能,而是消解贪欲的扩张”[17]。老子大谈“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人,将以愚之”(《老子》)。其实这都是在讲如何避免被治之法。只有在根本上清除了人心之中的贪念,奴役的政治统治才可能从基础上被根除。
另一方面,道家在面对死亡与奴役之际,却又不仅仅是局限于消极地全身保命,而是由之萌生出自己的哲学智慧。正如科耶夫通过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解说所指,“当面对面地注视死亡揭示的否定性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和体现精神的智者的力量就显示出来了”[18]。道家哲人也同样通过死亡,通过直面这个所谓的唯一的哲学问题,从而开凿出一套道家的知识论智慧,是为庄子所言之“一知之所知”(《庄子·德充符》)。面对欲望及其导致的社会压迫,老庄希望人们能够以恰当的心灵智慧来应对,首先,就要求人们“涤除玄览”(《老子》),如明镜照物般地面对整个世界,这样“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如此就能不被欲望所迷惑,不为欲望所摆布。人们摆脱了自己的陈规旧习,也就可能一同摆脱了自己习染生成的欲求贪念,并由此产生出真知识、真性情。徐复观就此阐发道:“欲望藉知识在伸长,知识也常以欲望为动机;……庄子‘离形’,也和老子之所谓无欲一样,并不是根本否定欲望,而是不让欲望得到知识的推波助澜,以至于溢出于各自性分之外。”[19]只有正确地建立起一套面对自我、面对欲望(包括畏死重生之欲)的大智慧,破除心中对欲望的旧习旧知,才可能发现真我,真实的全身保身才可能展开。
不再受错误的欲望摆置,不再从中获得不当的享乐,真正的快乐也才有可能实现;而由此建立起来的身心快乐,就不再是世俗欲望的低级满足,而是身心俱静处生发出来的自由的休闲心境,“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庄子·养生主》),这是对常情常欲的超越之乐,是身心在休逸闲静中的从容泰然。这种快乐与知识超越了世俗的利害之欲,成为与道相合的不知(世俗之知)的智慧。老子所言之“道可道非常道”之“道”,庄子所述之“四问而四不知”(《庄子·应帝王》)之“知”,正是道家被死亡恐惧所逼问出的大智慧。“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庄子·齐物论》),闲静之知为大知,这就是道家休身之乐,重视恬淡安详的平静心境。《庄子·让王》讲了一则颜回宁愿贫穷,简单生活,足以自娱,足以自乐即可,清心寡欲,回到道之单纯虚静的无为境界,也“不愿仕”的寓言故事。比较之下,儒家休身自得之乐,最后却变成了以礼(法、理)灭人欲的结果。身之大乐也就是身之大患,重身反过来也可能被人以身制;只有在无心无欲之乐中,才可能避免进一步推演出的身为物役的下场。《白虎通德论》云:“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20]《毛诗序》言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弹琴吟诗,本来为的是作乐休闲,却反而成了治身的外在约束,老庄对“五声五色”的批判,其理论预见性就在于此。
(二)闲闲自得
老庄所提倡的这种闲闲大知,之所以能够使人摆脱欲望的奴役,是由于它与道相联通,让人在自得于道中求取了更为真实的身全形完。
道为中国思想的终极追求目标,道不外人,道需要人去“德”,道德者,德(得)道也。《管子·心术上》云:“德者得也。”道的获得是古人最为重视的事情,《老子》说:“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尊重“道”,需要通过“得”来实现,“道德”可贵,毋宁说“得道”更为人重视。道作为天下万物之最终本根,把握住了道,就等于超越万物狭隘的差别利害,道家忘形而求道,去小知求大知,止欲而顺天,都是希望“将‘道’……成为自己的东西掌握在手中,由此最终克服人的异化,确立起主体性”[10]211-212。这样的个体才真正是一个完整的人,道家也正是在这种发展、扩充、完善的意义上来讲究全身之道的。
个体要想办法去得道、明道、悟道,办法不在身外,就在本身,是为“自得”。比如《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达】,深不可志(识),故强为之容。曰:与(豫)呵其若冬【涉水。犹呵其若】畏四【邻。俨呵】其若客,涣呵其若淩(凌)泽(释)。”[16]290-293将得道的途径归结为人自身内在的感悟、体味,道之玄妙不可言说,无法用理性去确凿认识,只能在身体性的体验中去自我品咂。庄子也特别看重“自适”得道之途:“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庄子·骈拇》)“自适”而非“适人”,适者,身体心灵的愉悦闲适,郭庆藩解为:“悦乐众人之耳目,焉能自适其情性耶!”[21]适于人,则“促龄夭命”,身体大受损伤,徒然悦乐众人之耳目,焉能自适其情性之体?自适自足自得其乐,这种心闲无事的心灵状态就是一种休闲的境界,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将此心境与画道联系起来,“夫内自足然后神闲意定,神闲意定则思不竭而笔不困也”[22]。自得于己,不假于外,与道合一,所以神闲意定,内心快活,可以笔思不辍,心手双畅。以自我之体验、体会、体悟、体味、体察来与道相合,是道家特别看重的自得之道,“‘知道’是一种认知,‘会’是一种体验”[23]。将身体置放于道之闲静超脱的状态中,休身,而且休心,虚静以享“天乐”,《庄子·天道》云:“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天乐,在乎天行,在乎全身得道,在乎通于万物,这正是道家休闲哲学的自得之乐。
《老子》认为,身与道在本质上同一,身由道生,万物以道归一,求道之法莫近于以身自得。而老子之身是单纯朴素之体,与道之虚静空明相匹配,道之圆浑单纯需要身之纯粹无伪来对待,所以需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通过“致虚极,守静笃”的身体功夫,让身与道调谐,如此与道相近,道身合一。身体欲望的扩展与膨胀,都是对身体单纯性的销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守住身体之本来纯洁状态,才有可能自得于道。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老子》)身体之自得之关键,正在于它是阻碍道之落实的最大弱点,身得则自得,身灭则全灭,身体的脆弱性反过来导致了全身休身以自得的合理性。“圣人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老子》)只有在对身体原初本来状态的护持之下,圣人之治才可能实现,“圣人治”,点出了休身之道的社会性、政治性维度,身之存亡与否究竟不仅仅是只在于己,还与他人相关,与天下相关。“控制好内心的情欲,闭塞住耳目的聪明,自身就是自然、完足的整体,又何必以天下为务呢。”[24]
三、物化与逍遥:休身策略
存身于政治世界,仅仅获得了理智上的闲心静性,还无法现实地全身保命,道家进而在操作层面上提出了休身工夫论,即物化与逍遥。
人之有身,必有其欲,身与欲的连接,必将产生差别、利害,进而导致心灵与行动中的失衡。身体本身即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根本问题。无身似乎最为完美,但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臆想,究其根本,又是另一种不合度的非份之欲。另一途径就是追求长生乃至不死,这又是一种重生欲望的极端膨胀,后世的那些房中、丹鼎长生之术都是其消极发展下的结果。面对身之大患,老庄并不“采取敌视的态度,而是主张‘忘形’(形有所忘)”,“不为形所拘限(位),不使形取得了生活上的主导权。再进而以自己的德,养自己的形,使形与德合而为一,以使其能‘尽其所受于天’”[25]。身之养恰是心之养,正是人发展自身内外修为的一个必然历程。具体的操作方式,可以庄子的物化、逍遥游为代表。
(一)物化
所谓物化的休身策略,就是将身体放入大化流行中,不以其独立的存在为限制,而是在万物一体的高度上来面对身体必然的有限性。《庄子·大宗师》有这样的故事:
“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
子来的意思,就是让人们不要刻意地担心自己的身体,也不要恣意修整自己的身体,而是要将其与万物一视同仁。面对天下万物的差异利害,我们需要将自己藏于其中,不再人为造作地高扬自身的独特性。“……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范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终,人犹效之,又况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乎!”(《庄子·大宗师》)将自身与万物齐同,藏身于天下,才可“善夭善老”以全身,才可获得真正的至乐。世俗生命只是“范人之形”者的快乐,我们其实需要在全身休身的物化转换之下,才能真正与天和,享天乐[26]。
道家认为,这种将身体转化于万物的物化并非一个痛苦的过程,而是一次次身体休养呵护的享受,“道家的转生、轮回被认为是快乐的,这一快乐当然就没有需要克服的,只是单纯地享受它就行了”[10]289。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道家物化休身的过程是一种独特的休闲体验,它一方面似乎在压抑身体,在忘形;另一方面却又是通过深层次的休养,拓展出了个体生命的另一心灵境界。这种体验正是道家摆脱了尘世奴役后所希望追求的自由快感,正是一种带有超越性质的休闲体验。《庄子·田子方》中老聃有云:“吾游心于物之初。……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在物化于天地之境界,至美至乐,心无所持,心无所欲,心无所畏,这种自失忘我之感受与当代休闲哲学所描述的休闲“畅”感(flow)[27]在体验上近似,却在活动性质上有所不同。道家休闲从虚静中入手,“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云云,各归其根。归根曰静”(《老子》)。以静而自得,《管子·心术上》云:“阴则能制阳矣,静则能制动矣。故曰:‘静乃自得。’”自得于己,自得其乐,道家休闲哲学与西方带有挑战性、运动性的休闲思维方式大有区别[28]。
(二)逍遥游
面对现实的残酷,道家休身的第二种策略就是逍遥游于天地之间,以全身完身:“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或者更为彻底,“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庄子·山木》)。个体身处制度之下,身之大患阻梗在自得之路上。庄子的解决方式就是让身体在逍遥游荡中获得自由自得之全,不为某些具体的、时空性的利益、仁义之类束缚,“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庄子·骈拇》)。身体需要摆脱现实中的礼法约束,让他在天地之间自由逍遥,“至人神矣!……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齐物论》)。自得之道,就是自我放浪之道,就是“相忘于江湖”之道,这样自得的完整性才可能得到保证。自我与社会间天然的纽带(人总有父母、亲戚、邻里等社会关系)在儒家修身自得的道路上走向了以礼(法、理)杀人的反面,庄子之逍遥游正在此处截断了这个恶性发展的可能性,“不以众人之观易其情貌,亦不谓众人之不观不易其情貌。独往独来,独出独入,孰能碍之?”(《列子·力命》)与整个社会不相往来,独立于天地而自得,列子之论正由此推演出来。
追求长生不老、成仙成神是国人重生观念的自然推演。跳出五行外,超出尘世中,得成大道就可休闲身心、自由逍遥了。《庄子》中的那些“至人”“真人”就是这样的有闲阶级神仙。他们“死生无变于己”(《庄子·齐物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庄子·大宗师》)。《庄子》以逍遥游概括了这些仙人们休闲的自由境界,身心俱畅,灵肉皆闲:“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游于六合之外”(《庄子·徐无鬼》)。超出天地规则,自由翱游,这一游,实现的才是中国式休闲的自由心境:“游心乎德之和”(《庄子·德充符》);“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庄子·应帝王》)。最后至于“无己”“无功”“无名”的自由状态,与天地自然、与道合一。这种休闲的自由体验,既是一种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审美快感,更是一种状态,是与道合一的境界。静态之“道”是中国休闲哲学与西方休闲自由行为区别之处。中国古人在休闲中并非要摆脱什么,而是要达到矛盾的自然消解;不是要去解决问题,而是要去消灭问题本身。我们没有什么更高的信仰和超脱,身体的解脱与逍遥,既是我们的出发点,又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逍遥本身已经达至最高境界了,于是,休闲既是一种过程,也变成了一种境界。
[1] 许嘉璐.晋书[M]∥二十四史全译.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1234.
[2] 象形字典.休[EB/OL].(2015-04-11)[2015-06-20].http://www.vividict.com/WordInfo.aspx?id=1492.
[3] 象形字典.闲[EB/OL].(2015-04-11)[2015-06-20].http://www.vividict.com/WordInfo.aspx?id=3159.
[4] 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6.
[5]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25.
[6]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M].北京:三联书店,1996:148.
[7] 杨儒宾.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93:104.
[8] 梅墨生.中国人的悠闲[M].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17.
[9] 孙以楷,甄长松.庄子通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114.
[10] 池田知久.道家思想的新研究[M].郑州 :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9.
[11] 河上公章句.宋刊老子道德经[M].福建:福州人民出版社,2008:24.
[12] 王雅红.才子四书[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59.
[1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8.
[14] 二十五别史·帝王世纪[M].济南:齐鲁书社,2000:13.
[15] 胡伟希.论中国休闲哲学的当代价值及其未来发展[J].学习论坛,2004(9):40.
[16]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7]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74.
[18] 科耶夫.黑格尔导读[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653.
[19]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63.
[20] 班固.白虎通德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1.
[21] 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234.
[22] 王伯敏,任道斌.画学集成(下)[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317.
[23] 杜维明.十年机缘待儒学[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64.
[24] 周与沉.身体:思想与修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39.
[25]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337.
[26] 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5.
[27] 凯利.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32.
[28] 章海荣,方起东.休闲学概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27-29.
(责任编辑 陈咏梅)
On Body Theory's Structure of Pre-Qin Taoist Leisure Philosophy
JIANGYu
(Art Academy,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Yichang Hubei 443002)
Pre-Qin Taoist' (represented by Lao Tzu and Chuang Tzu) leisure philosophy focused on individual life's surviving and developing under social rules and political pressure. Surviving as base and aim, Taoism tried to create a set of leisure wisdom through which one could ease the tension, desire and come near to the truth. Objectification and peripateticism were two prominent strategies for Taoism by which to solve the life's issue.
Taoism;Lao Tzu;Chuang Tzu;Leisure Philosophy;body
2015-06-28
江渝,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书画艺术哲学与休闲哲学。
10.3969/j.ISSN.2095-4662.2016.04.005
G122
A
2095-4662(2016)04-002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