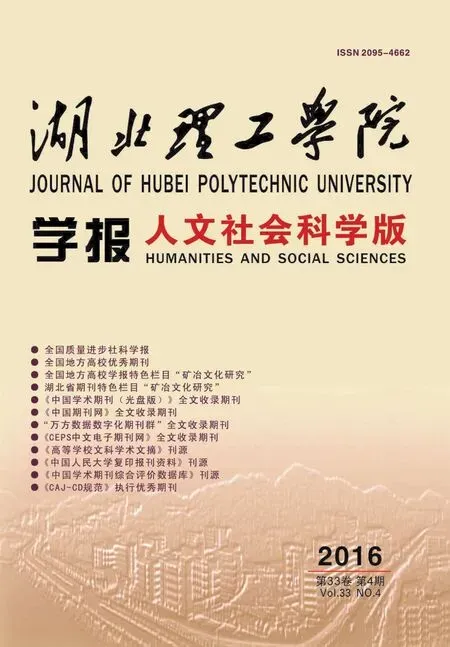科隆狂欢节的文化考察
陆 扬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科隆狂欢节的文化考察
陆 扬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欧洲狂欢节是中世纪的传统,作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民间文化的典范形式,被认为是创建了一个幻想世界,在此,高雅与低俗、官方与民间、经典与怪诞的分野悉数不见。科隆狂欢节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狂欢节,源自基督教传统,但也经历了世俗化的过程。1823年成立的“科隆狂欢节组委会”,如今已是欧洲城市相关节庆组织的楷模。科隆狂欢节的高潮是“玫瑰星期一”游行,以百吨计数的巧克力糖果消耗,不过是成本一端。科隆狂欢节的盛大场面,同样是资本运作的一个丰硕成果,与昔年巴赫金津津乐道的那种民间自生自发,对统治意识形态表现出桀骜不驯的叛逆精神的狂欢节模态,已经迥异其趣。
狂欢节;科隆;玫瑰星期一
一、狂欢节的由来
狂欢节(Carnival)通常音义兼译为“嘉年华”,意为快乐的年华。但年华举凡快乐多不长久;快乐年华长久下去,便不复为嘉。可是人生得意的时候多半不在乎尽欢不尽欢,口口声声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其实是心里边有苦难言。这就像我们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忧愁和焦虑是一条漫长的曲线,难得蹦出几个快乐的亮点。所以,快乐的年华总是留存在我们的记忆和憧憬之中。这一切同狂欢节有什么关系?自然是多有关系。因为这一幅苦难人生的漫长画卷,应是狂欢节诞生的哲学基础之所在。
英国社会学家麦克·费瑟斯通在阐述所谓的波西米亚精神和布尔乔亚格调可以怎样联手,来创造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时,举譬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离经叛道的政治学与诗学》(1986年)书中的观点,认为欧洲的狂欢节传统是下衍了一种放浪形骸的波西米亚流浪艺术活力,可以和讲究道德君子的布尔乔亚风度合璧,成为中产阶级品味标识的两翼。故此:
波西米亚艺术家可视为是在生产“大杂烩式的象征型节目”,与早期狂欢节形式提供的类似节目一脉相承。中产阶级的波西米亚艺术,特别是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从狂欢节传统那里改头换面接过了许多象征性的颠覆与忤逆。因而我们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狂欢传统中许多栩栩如生的侧面,诸如断断续续、流动不居的意象链,声色犬马,情感大释放,以及万变归一等等,它们如今同后现代主义和日常生活审美化,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1]。
费瑟斯通这里提醒我们所谓的波西米亚精神是接续了早期狂欢节的形式。早期狂欢节的形式作为一种典型的民间文化传统,其细节面貌今天多已缈不可考。它纵情歌舞、形神俱醉的基本形态,很自然使我们想起古希腊的狄俄尼索斯祭祀歌舞。按照尼采的看法,导致悲剧起源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冲动,都与克服人生苦难特别是死亡恐惧直接有关。《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向我们转述了佛律癸亚王的一个故事。传说中,有一次弥达斯在森林中追捕能够未卜先知的马人西勒诺斯,抓到他后即问:对人来说,这世上最好的东西是什么?西勒诺斯听闻一愣,逼问半晌后,尖笑一声道:可怜的浮生!为什么逼我说出实话!最好的东西是不要出生;其次好的是立刻就死!尼采认为这个故事深深反映了希腊人对死亡的恐惧心理,因为它其实是说,最可怕的是立刻就死,其次可怕的是人终有一死。荷马由是观之,便好似一个梦幻艺术家,用生的幻相遮掩了死的真实:
在这些神灵的明丽阳光下,人感到生存是值得努力追求的,而荷马式人物的真正悲痛在于和生存分离,尤其是过早分离。因此,关于这些人物,现在人们可以逆西勒诺斯的智慧而断言:“对于他们,最坏的是立即要死,其次坏的是迟早要死。”这种悲哀一旦响起,他就针对着短命的阿喀琉斯,针对着人类时代树叶般的更替变化,针对着英雄时代的衰落,一再重新发出。渴望活下去,哪怕是作为一个奴隶活下去,这种想法在最伟大的英雄也并非不足取[2]。
尼采的意思是,阿波罗冲动可以超度死亡,让个体生命在幻觉中渡过苦海。但是尼采认为悲剧中更为重要的是那一种与世界本体息息相通的情绪,一种融入宇宙天地的陶然忘我之境,这就是缘起于具有毁灭和否定个体生命倾向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冲动。酒神冲动不是对死亡的遮盖和回避,生命在这一原始本能的纵情发泄中,与大自然重新合而为一。它不是形象,而是音乐,是从世界心灵中直泻出来的原始旋律。日神与酒神冲动合流而得悲剧诞生。与之比较,用奇装异服和又丑又怪面具装备起来的狂欢节没有悲剧的庄严辉煌,它更接近被认为是缘起于“菲勒斯颂歌”即下里巴人歌唱男人阳物的喜剧。但是,诚如音乐一如既往在狂欢节中占据主位,从其根源上说,狂欢节的内涵当不限于戏拟和反讽的姑且尽欢机制,它一样在演绎超越苦难的崇高体验。
但是狂欢节说到底是欧洲中世纪的传统。尼采归纳的酒神精神也好,日神精神也好,一般被用来阐释悲剧的诞生,并不用来证明狂欢节的诞生。狂欢节作为一年一度盛开在从罗马到科隆的欧洲大地上的特殊节庆,它的源头是似乎同它格格不入的中世纪以来基督教社会和文化。而按照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等著述中的独到阐释,狂欢节作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民间文化的典范形式,是创建了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第二世界”,在狂欢节文化里,高雅与低俗、官方与民间、经典与怪诞等等的分野悉数不见,或者说,是盘根错节纠缠在一起了,特别是怪诞的离经叛道,而且音乐一路贯穿下来。以德国为例,文艺复兴以来,以《音乐会》(Das Konzert)为题的绘画多不胜数,题材表现固然有雍容华贵的宫廷音乐会,但更多是乡间酒肆放浪不羁的即兴吟唱,交头接耳、仰面朝天、耳鬓厮磨,它未必不是民间形式的另外一种狂欢图景。时至今日,一旦狂欢节到来,音乐必响彻云霄,鼓乐和铜管乐的声波颤抖着穿透空气,可以一连穿过好几个街区。狂欢的节日,也是音乐的节日。
狂欢节最终从鼓吹无条件服从的基督教信仰里脱胎而出,应有它的必然性。基督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禁欲主义。但是禁欲过度,必迎来它的反动。这在薄伽丘《十日谈》中即有淋漓尽致的描述。如第三天里的魔鬼进地狱一类此一时期流行的俚俗故事,是为中世纪禁欲主义物极必反的一个结果。比较起来,最终酝酿出狂欢节兴起的修道院生活的定期“出轨”行为,显得中规中矩。所谓“出轨”,是指僧侣和修女们获准在每一年特殊的时日里,暂别清规戒律,允许随心所欲、装疯卖傻一回。他们可以载歌载舞、大吃大喝、搂抱亲吻,一时间不再顾忌须得时时谨小慎微的宗教身份。1729年科隆本笃会莫里修斯女修道院中一位修女,在一封信里这样描述过她们的狂欢节细节生活,“我们自己过了狂欢节,非常开心……到了夜里,院长去睡觉了,我们就喝茶、喝咖啡、喝巧克力,还打牌了”[3]。在今天看来,这位修女描述的狂欢场景相当平淡,但是可以想见,比较修女们平日高墙里青灯孤影的日常修道生活,它就算得上是大吃大喝、为所欲为了。
二、科隆狂欢节
科隆应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公元前38年,罗马皇帝屋大维遣女婿阿格里帕(Marcus Agrippa)大将北征蛮族,借先时凯撒余威,大军摧枯拉朽,一路北上直抵莱茵河边,安营扎寨,与东岸的土著部落隔河相峙。当其时,阿格里帕邀得河东的一支日耳曼部落乌尔比人迁往西岸,填补被凯撒荡平的先时蛮族地盘,在罗马人的疆界里定居下来。由此形成莱茵河畔一个罗马军团和日耳曼土著共生共荣的军事要塞。乌尔比人最初选择的核心定居点是莱茵河里的一个小岛。小岛今已不存,但是我们知道它的方位大体是在今天科隆老城 Heumarkt 一带。作为科隆城市的源起,Heumarkt 也是今日科隆狂欢节的起点。2015年11月11日,科隆狂欢节的大幕就是在此间中央广场上一个临时搭起的舞台上亮丽拉开的。多年以后,阿格里帕的外孙女阿格里皮娜做了罗马皇后,她想起自己莱茵河畔的故乡,那个罗马人和乌尔比人共同经营起来的小城,恳请夫君将它升格为市。罗马皇帝当即允诺,下诏赐予此间罗马城市的一切权利,将之命名为科洛尼亚·克劳迪亚·阿拉·阿格里皮内西姆(Colonia Claudia Ara Agrippinensium)。科洛尼亚意为拓居地,克劳迪亚名出是时罗马皇帝,阿拉是乌尔比人修建的中心祭坛,阿格里皮内西姆皇后母家姓氏,名出这个城市的先祖阿格里帕。这个冗长的城市名字后面的一连串修饰语最终褪去,独剩下科洛尼亚,并且定名为科隆。但是即便今日,在欧洲许多国家,科隆(Köln)这个城市的拼法,依然是原初的Colonia(科洛尼亚)。即便二战后期科隆经历了盟军毁灭性的大轰炸,罗马时期的建筑遗迹和雕塑残片依然顽强地保存了下来。毗邻大教堂的罗马中世纪博物馆,奇迹般藏有战时挖防空洞发现的一大块罗马时期哪个贵族人家的狄俄尼索斯宴饮图马赛克地板。这真叫人叹为观止,在城市频临灭顶之灾的时候,科隆人依然念念不忘珍藏自己城市的光辉历史。由是观之,中部和北部欧洲规模最大、声名也最为响亮的狂欢节出现在科隆,当是在意料之中。
狂欢节不是修道院的专利。它的宗旨是无论贫贱富贵、老弱妇幼,面对一切人等开放。在这里,日常生活中社会等级的限制一时间似乎消失无踪。平民戴上王冠,百姓庄严肃穆披上牧师长袍;男女易装互扮互演,一概尽心所欲、恣意欢乐,而不必承担真实生活中角色倒错的任何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狂欢节也是不折不扣的愚人节。小丑就是狂欢节的主角。教堂也好,市井也好,快乐也好,悲哀也好,组织也好,自发也好,就像愚人说话没遮没拦,任何人不必信以为真。这个以愚人唱主角的狂欢传统同样是由来已久。福柯《癫狂史》中写到,文艺复兴时期有所谓的“愚人船”,将真真假假的疯子傻子装进船里,由着它去随波逐流。这照例是理性压制异端的惯例故事,可是由于场面具有喜剧性,在福柯看来,反倒是成就了一个愚人的狂欢节。歌颂愚人在德国尤其根深源长。16世纪著名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愚人颂》(Moriae Encomium),光从书名看,就是跟他的英国好友托马尔·莫尔(Thomas More)不大不小开了一个谐音玩笑。作者将“愚人”化身为一个妙龄女子,让她自报家门说是财神普鲁托斯(Plutus )的后裔,谁要开罪了他没人能救,可是一旦有了他的相助,连朱庇特都不在话下。愚人嬉笑怒骂之间,我们发现常常能够一语中的,例如愚人说:
艺术家的自负真是丑名远扬。他们宁可丧失地产,不愿才气有半点缺损,这在演员、歌手、演说家和诗人尤其如此。他们越是糟糕,越是盛气逼人、目空一切,也越是引来掌声如雷。最糟的总是取悦于最多的,因为如我前面所说,老百姓的绝大多数都是傻瓜。如果最为贫乏的艺术家最是自得,而且被最多的人所崇拜,他何必又要真正的技能?[4]
愚人的立论是,凡是顺应自然之道,都是可圈可点。诚如,老百姓安贫乐道,看似愚不可及,实则自得其乐;精英们高高在上、自命不凡,到头来只能是自取其辱。在这里,易容扮装和装疯卖傻等等一应狂欢节的因素,可以说已经是埋伏其中了。当然,《愚人颂》作为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经典,其深刻的社会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狂欢节是冬天的节日。它在冬日里酝酿春暖花开时分的到来。按照基督教的传统,它是大斋(Lent)到来之前的节日,是为大斋前夜到圣灰(Ash Wednesday)星期三的这一段时光。所谓圣灰星期三,即是大斋首日。其来源是《旧约》里的有关记述,如《约珥书》中的这一段话:“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大斋本身,可视为迎接封斋日和复活节到来的一段准备时光。禁食、哭泣、悲哀、撕裂衣服甚至撕裂心肠,在所有这些严格的宗教斋戒到来之前,我们先姑且狂欢吧。据记载,科隆狂欢节的最早记录,可以追踪到公元1341年,这是在基督教成为欧洲主导意识形态800年之后。可以想见,在壁垒森严的宗教生活中体验狂欢节期间的快乐,这快乐其实是相当有限的。是以,戴上面具,变身愚人,无疑是最好的解脱之道。
狂欢节(Carnival)的字面义是“不吃肉”,所以狂欢节也是谢肉节。其拉丁词源中,carnis是肉,levare是取走。两者拼合,即有狂欢节的诞生。德语中表示狂欢节的另两个语词Fastnacht和Faster-Abend,无疑也能见出这一点来。大斋期间,斋戒的是肉。最初它是大斋到来之前饿上三天,且作狂欢。这大斋之前的三个狂欢日,天长地久,最终发展成为持续数周的狂欢节,直到圣灰星期三为止。圣灰星期三是大斋节的首日。大斋节为期四旬,以纪念耶稣曾经在旷野40天,粉碎了撒旦的诱惑。是日教士每在信众额上涂灰,象征当年耶稣苦难。虽然,谢肉在当代社会基本上已经失去苦行意义,即便以鱼替代之,那毋宁说也是一个更为昂贵的替代品。但是,斋戒的姿态究竟还是有办法表达的,比如戒车、戒手机、戒电视。
科隆狂欢节每年于11月11日上午11点宣布开始。在莱茵河流域,狂欢节的歌声响彻通年,各种节庆活动也时有举行。但是狂欢节始终是一年一度,按时而来。科隆狂欢节于每年11月11日上午11时举行轰动全城的盛大开幕式,三个“11”并立,但是它与中国近年开始流行的“光棍节”毫无关系。这是收获的季节。在农业社会里,一年劳顿下来,此时正可期待收成的到来。在基督教里,11月11日是圣马丁节。圣马丁原本是罗马士兵,后受洗成为僧侣,一生安贫乐道,庇护穷人,友善儿童。传说他将大氅一撕两片,分一片给路边乞丐,暴风雪里救了乞丐一命。是夜圣马丁做了一梦,梦见耶稣披上了他的半片大氅,告诉天使说,是罗马士兵马丁给我披了这衣裳。但是圣马丁节并不是斋戒,它多少相似于美国的感恩节,这期间大吃大喝庆祝大地的丰实馈赠。这也情有可原,11月11日,这个特定的日子标志冬天的来临、秋日的终结,粮食早已收获在库,牲宰和税收也按部就班鸣锣开张。
理论上说,狂欢节历时3月余,结束前一周再次沸腾,在“玫瑰星期一”的街头大游行中达到高潮,然后嘎然终止。不似开幕式结束之后各路军马纷纷偃旗息鼓,卸妆回家;“玫瑰星期一”游行结束后,场里场外人众依然是意犹未尽,欢唱酣饮每至夜深。午夜时分的地铁上,依然举目皆是盛装披挂,或者是半卸半挂的情侣和三三两两的老年、壮年、青年和少年。这是一个疯狂的星期一,方队与花车在按部就班,在激昂的铜管乐和鼓乐声中有条不紊前进。巧克力、橡皮糖和鲜花不停抛洒向街边同样感染了狂欢气氛的观众,数量总共高达百吨计。这个成本无疑是相当可观的,可以说是为了狂欢不计血本。所以组织和预算,毫无疑问是每年狂欢节活动首先要筹谋周全的。
三、玫瑰星期一
“玫瑰星期一”游行第一次登场科隆是在1823年2月10日中午。科隆狂欢节的组委会,也第一次有了它的雏形。委员均为科隆使命,然并非专职,大都另有生计。此外,此一时期几近完成的科隆大教堂的建筑工程,无疑比较起狂欢节的筹备,更是城市文化的重中之重。狂欢节组委会毕竟诞生了。在此之前有无数社团,各自为政,分摊成本,如今有了统一的组织,它的全名就叫做“科隆狂欢节组委会:源自1823年”(Festkomitee Kölner Karneval von 1823)。随着年复一年游行和狂欢越做越大,科隆不知不觉就成了欧洲城市的楷模,以至于其他城市的市民,也蜂拥而至。组委会自觉责任重大,人员也逐渐固定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11人的核心委员会。1827年的筹备会议上,有人提出组委会须得统一顶戴,大家深以为然。红黄间色的尖顶小丑高帽子,由此成为这一年组委会成员的统一头饰,日后成为科隆狂欢节的标志性顶戴。
时至今日,科隆狂欢节组委会已经下辖百余个狂欢社团。各社团有不同的行业背景,旨趣分歧在所难免,故而组委会订立了统一章程[5]43:
1)科隆狂欢节是科隆最重要的城市文化特色之一,其待遇及地位当照此办理;
2)科隆狂欢节应当是所有人的节日,面向大众、全面开放、臻于统合;
3)科隆狂欢节当有助于童稚青年乐观人生及未来;
4)科隆狂欢节须为公众竖立自身之正面形象;
5)科隆狂欢节积极推进传统和文化继承,与此同时,当展望未来、富于创新;
6)科隆狂欢节应有义务志愿者筹划承办;
7)科隆狂欢节承担社会责任;
8)科隆狂欢节必须具备坚实之经济基础;
9)科隆狂欢节应维持优质,以相应的高标准来加以衡量;
10)科隆狂欢节应有镜鉴功能,在价值和独立基础上有所社会批判;
11)科隆狂欢节具有轻松幽默基调。
这些条规无疑是相当细致的,从狂欢节的定位、性质,到社会责任、经济基础,乃至幽默基调和独立批判精神的两相协调,悉尽囊括其中。这很难说是以资产阶级道德即布尔乔亚品味来约束乃至扼杀巴赫金等推崇备至的波西米亚反叛精神。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一切欢乐节庆,不以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度之将寸步难行。科隆狂欢节的以上11条规章,即为例证。
科隆狂欢节是欧洲最为盛大且影响最为广泛的狂欢节。在全球范围,它的规模仅次于巴西狂欢节。作为科隆为时数月的访客,笔者有幸见证了“玫瑰星期一”的盛大游行。2016年的“玫瑰星期一”与中国春节正巧重合。科隆跟德国其他城市一样,没有专门区划的中国城。北邻杜塞多夫所谓的日本城,也不过是火车站附近一条大街两边的若干日本商铺。科隆有的只是亚洲超市和亚洲饭店。到了节假日期间,这些地方往往显得冷清。但是今年例外,“玫瑰星期一”的豪华奢侈和喧嚣,足以将冬春之交这个城市上空的一切冷寂扫荡一空。是日下了些零星小雨,然后雨过天晴,阳光明媚。天气预报原本或有大雨狂风,北邻城市杜塞多夫甚至改变日程,往后推延了2月8日的玫瑰游行。但是,科隆义无反顾、一如既往启动了游行。果然是老天保佑狂欢节!笔者与同济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和一个香港学生,早早约好地铁站聚首,来到城市南边玫瑰游行的起点克洛德维格广场。说是广场,其实只是有一个标志性城堡的地名。按照计划,从这里到市中心新市场一带的游行终点,大体15分钟地铁距离的路程,是要用3.5小时走完。但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间杂着几百辆彩车,光是静止不动,从头到尾排队下来,长度就超出了游行的距离!是以各个单元完好协调,按部就班准时到达现场,井然有序、从容出发。彩车则三三两两停泊在附近的几条马路边上。在号角吹响、玫瑰游行大军出动之前,整个科隆城市笼罩在静谧且神秘的空气里。
游行拉开帷幕。我们很快发现,出发点几乎水泄不通,于是钻回地铁,北上两站路程,到游行路线开端部分的一条小街上,从容当起了观众。由于是观众,角色意识似乎可以淡漠一些,一身素装站在街边,便也心安理得。不似11月11日万人空巷的狂欢节开幕式,脸上不涂油彩、身上不披挂点什么,不足以扬眉吐气出门上街。游行队伍在嘹亮的管乐声中雄赳赳踏步过来了。方队和彩车有条不紊,在夹道欢呼声中徐徐前行。彩车几无例外都是用形形色色的高头大马的大马力拖拉机牵引,有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棕色的。让人纳闷的是,后工业时代,科隆从哪里调配征集过来这许许多多貌似巨无霸的红红绿绿拖拉机,甚至,还出现了挖掘机。拖拉机车头或者裸露,或者装饰。装饰最多的是马,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白马,清一色的奔腾姿态中的白马,清一色的萌态可掬的白马。马与人类的亲密关系,似久已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哲学话题。记得伊拉斯谟的《愚人颂》里,愚人就列数过马如何与它的主人一起同仇敌忾,胜了比赛,便趾高气扬;败下阵来,便垂头丧气。
更有巧克力和鲜花。“玫瑰星期一”的盛大游行不光中饱眼球,它还是名副其实的巧克力飨宴。游行方队和车队每隔一段距离,便有鲜花、糖果、巧克力给养车跟随,方队里除了乐手,人人配置一个大布袋,一面走路,一面不时从布袋里掏出巧克力和大都是单株包装的鲜花,向街道两边人群抛洒。但见窗户里有人探出身体欢呼,便将鲜花、糖果、巧克力,高高投掷进去。漂亮的姑娘和孩子们,那是花雨和巧克力雨袭击的首要目标。此时此刻,天上掉馅饼已经没有意义了。所有的人实实在在沐浴在从天而降的巧克力和鲜花之中。假如没有事先准备好袋子,假如游行队伍出发现场有人发放袋子你不以为然,那么,很快你就发觉身上口袋鼓鼓囊囊装满糖果,对于游行队伍前赴后继抛洒过来的巧克力和鲜花,再也无能为力了。这是超级儿童节。它似乎会导致秩序混乱,但事实上秩序并不混乱。科隆狂欢节组委会念及狂欢节中的儿童安全,专门制定过一个提请带孩子家长的注意事项[5]117:
1)勿单独行动,团体观看为好;
2)穿暖和了;
3)带上袋子装糖果巧克力;
4)别捡掉在彩车之间的糖果,注意安全;
5)离马远点;
6)接住或者捡起糖果巧克力吧,但是别跟游行队伍讨要;
7)事先上厕所,别多喝水;
8)永远别把糖果扔将回去;
9)若游行队伍行走缓慢,没必要带孩子从头观看到底;
10)若是寒冷天气,中间找地方暖和一下;
11)约定碰头地点,交换电话号码,以防在人群中走失;
12)带婴幼儿的家庭,可就近观看全市将近50处的小型游行,以便于照看孩子,一样有糖果巧克力。
这些注意事项都是相当平实可行的,不光是提醒,也是必须,它们保证了游行队伍和狂欢观众的安全和快乐。比如气候,就像今年的2月8日,“玫瑰星期一”盛装游行正当一年里最冷的季节,故衣服穿暖和了,中间找地方暖和一会,然后来继续观看游行,都是必要的。好在科隆虽然地处北陲,但是受惠于北大西洋暖流,气候却是德国所有大城市里最暖和的。它比东面的柏林、北面的汉堡,以及南面的慕尼黑,甚至纬度远低于它的北京都要暖和得多。科隆狂欢节诞生在这个温暖的北方都市,真是得天独厚。但是也不尽然。例如第六则提请观众多多接住或者捡起抛洒过来的巧克力糖果,但是别跟游行队伍讨要。可是分明大家都在高呼“坎贝拉,坎贝拉”,意思就是“给我吧,给我吧”。哪里的呼声高,巧克力就应声过去。就整个科隆来看,“玫瑰星期一”这一天,游行消耗的巧克力达数百吨计。
狂欢节的成本由此可见,应是相当高昂的。鲜花、巧克力仅为一端。2000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出版《天堂中的布波族:新上层阶级及其成功史》一书中,率先使用了“布波族”(Bobos)一词,它作为“布尔乔亚波西米亚族”(Bourgeois Bohemians),也就是中产阶级波西米亚的缩写,用来指后工业社会新型中产阶级的新型狂野不羁波西米亚艺术趣味。同传统相比,这个今日社会的主流精英已经很少有意识来对抗主流文化,对于异端和不同意见,也表现出高度宽容。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从而形成一个新型中产阶级[6]。说到底,趣味再高雅、再狂野,也必须要有资本来做后盾。一切艺术品位,假如失去资本支撑,将不足一道。如此来看科隆狂欢节的盛大场面,我们可以发现,它是资本运作的一个丰硕成果,与昔年巴赫金津津乐道的那种民间自生自发,对统治意识形态表现出桀骜不驯叛逆精神的狂欢节模态,已经迥异其趣了。
[1] Mike Featherstone.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1:79.
[2] 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12.
[3] P.Fuchs und M.Schwering,Kölner Karneval.Seine Bräuche,seine Akteure,seine Geschichte[M].Köln:Greven,1997:169.
[4] D.Erasmus.The Praise of the Folly[M]∥Maynard Mack.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Vol.1).New York: W W Norton & Co Inc,1979:1270.
[5] Wolfgang Oelsner.Cologne Carnival[M].Cologne:J.P.Bachem Verlag,2014.
[6] David Brooks.Bobos in Paradise: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M].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0.
(责任编辑 陈咏梅)
A Cultural Study of Cologne Carnival
LUYa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s a typical folk event tracing back to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Carnival is believed to be a fantastic world in which the division between highbrow and lowbrow, official and mass, classic and grotesque disappeared totally. Cologne carnival, originated from a Christian tradition though, witnesses the evolution of secularization as well. The climax of the carnival is Rose Monday parade, of which the budget is far more than hundreds of tons of candy and chocolate. It indicates that the spectacle of the carnival is also a rich product of capital operation, which in a large degree, has deviated from the rebellious carnival mode described by Mikhail Bakhtin.
carnival;Cologne;Rose Monday
2016-04-21
陆扬,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美学、文化研究。
10.3969/j.ISSN.2095-4662.2016.04.003
G112
A
2095-4662(2016)04-0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