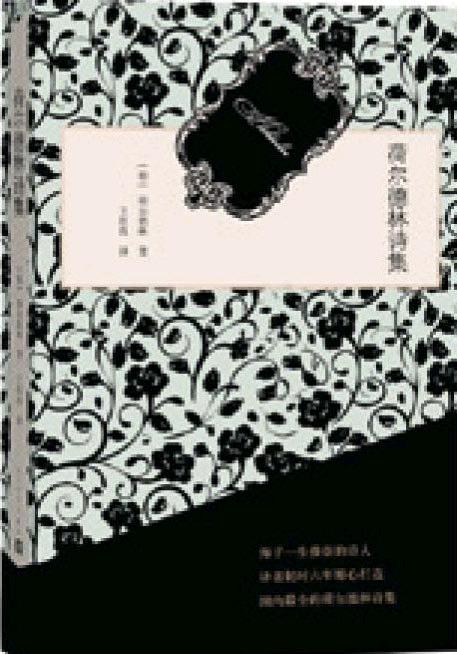湛蓝色的生命感
刘晗
海德格尔把普遍技术化的“世界时代”标识为“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当人们沉醉于价值和思想的虚无、时代的变迁而忘乎所以时,诗人荷尔德林则在诗歌中浅声低吟呼唤人性的回归,其创作被认为是十八至十九世纪之交德国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柔媚的湛蓝中》(In lieblicher Bl?ue blühet)是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lderlin)(1770—1843)后期所作的一首诗歌,被译为“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名句正是出自本诗。纵观过往的思想史,荷尔德林的诗歌在其死后得到了广泛传播,这得益于德国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其诗歌内涵的哲学阐释,借其诗歌以明其思想。甚至不妨说,荷尔德林的诗歌为海德格尔提供了鲜活的思想意象,海德格尔的诗化思想又为阐释荷尔德林的诗歌提供了生存论的视角。
海德格尔认为,荷尔德林是最纯粹的诗人,他受诗的天命召唤,直写诗之本质,是诗之本质的化身。上帝的缺席、诸神隐退,在这个贫困和黑暗的时代,荷尔德林在《如当节日的时候……》一文中,把自然视为神圣者以及一切创造者,同样,海德格尔也把自然、神性和“此在”视为一体。在其后期的思想中,更是把对“此在”的情感转化为对语言和诗歌的体验。在《什么是召唤思》中,海德格尔所说的“什么是召唤思”的原本意义是“什么召唤我们去思”,即把Was hei?t Denken理解为Was hei?t uns denken,这样hei?t就显出了召唤的意味。 承诺(Verhei?en)即应诺传召之意,因此Hei?en即有应诺传召使自己进入到场和在场(Ankommen und Anwesen)中去。 海德格尔把召唤我们去思的东西命名为最激发思的东西,这种召唤是本己的且是一如既往的,其中包含了双重含义:即召唤作为“此在”的人固有的神性以及在时代背景下召唤语言和诗意对“此在”的反思。这种“应诺吐露”即是对“此在”的言说,正如他所言:“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就是这样通过语言对思进行道说(Sage),在语言和思中窥见“此在”,对他而言,关注“此在”是贫困时代的当务之急。
海德格尔曾借用荷尔德林的哀歌《面包与葡萄酒》提出同样疑问:“……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的祭司/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诗人华兹华斯曾说过:“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对于荷尔德林来说,这种情感的流露是指向作为“此在”的人与自然的。
“在柔媚的湛蓝中/教堂钟楼盛开金属尖顶/燕语低回,蔚蓝环抱/旭日冉冉升起,尽染金属尖顶/风中,风向标在高处瑟瑟作响……”诗歌中所呈现的教堂周边的景色如风景画一般:蓝天、鸟鸣、旭日以及随风飘动的风向标所作的奏鸣曲都映衬着庄严而神圣的教堂。教堂作为宗教仪式举行的场所,在诗中必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荷尔德林为何要将视角放置在教堂呢?
教堂是神性之光闪耀之地,就如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描述的两个特征,即建立(Aufstellen)一个世界(Welt)和制造(Her-stellen)大地(Erde) ,诗歌中的教堂和希腊神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希腊神庙阒然无声地开启着世界,同时把世界重又置回到大地之中……神的这种现身在场(Anwesen)时在自身中对一个神圣领域的扩展和勾勒。”
自然的美景伴着教堂的赞美诗,这是神对人“诗意地栖居”的渲染,是神在对人栖居的召唤。这就是为何荷尔德林不把人的栖居处选为高楼大厦或者茅草屋的原因。在《荷尔德林文集》的《论宗教》中,他把宗教定义为人与世界的“更为深情的关系”,一种更高的、超出人与世界的机械关联之上的天命,在此天命中,人与世界“相与为一”。 在教堂钟底的人会获得宁静的一生,教堂的钟声是对人信仰的召唤,而人的情感也同时归附于其中。这是荷尔德林在借宗教向人传递一种“更为深情的关系”,而人也把这种情感反馈给世界,这正是对荷尔德林借诗歌表明自身宗教观的印证,他认为宗教的本质就在于其具有的诗性。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哪里有贫乏,哪里就有诗性。
近代哲学家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之后,理性主义大行其道,理性和科学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尺,神性在逐渐隐退和泯灭。在古希腊时代,希腊神话在希腊人看来是真实的生活,他们认为世界是人神共处的世界,人性和神性并存,因此人充满了对神秘大自然的敬畏感。但是,现代人却认为这些古希腊传说来自想象。因此,在诗歌中呼唤神性成为荷尔德林的主题:
“……/上苍,始终至善至美/拥有富足、德行与愉悦/人或可仿效/当生命充满艰辛,人/或许会仰天倾诉:我就欲如此这般/诚然。只要良善纯真尚与心灵同在/人就会不再尤怨地用神性度测自身/神莫测而不可知?神如苍天彰明较著/我宁愿相信后者/神本人的尺规/劬劳功烈,然而诗意地/人栖居在大地上……”
海德格尔之所以推崇荷尔德林,是因为他认同在诗中所渗透的“人是半神的”的思想,正如诗歌中所言,“上苍的至善至美,人或可效仿”。若人对自然和人加以利用,就会导致了人之神性的泯灭。在世界黑夜时代里,当大多数人沉浸在被科技和工业化渲染的城市之中,无限度、无节制地追求着物质和欲望的满足时,他们根本无法意识到自身的生存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重创——西方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由尼采的“上帝死了”判定虚无主义时代的到来,由此人类的精神生活陷入“无根”的状态以及由于现代技术所造成的生存灾难。
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即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本质是虚无主义。哲学起源于神的不在场,在没有神性之光照耀的黑夜世界中,因此才去寻找存在的根据所在。此时,并非所有人都迷失了方向,那些曾被柏拉图驱逐出理想国的诗人们则身处广阔的大地和绿野田园之中,荷尔德林就是在这黯然失色的贫困时代中跋涉的诗人中的一位。他们在黑暗中承担起拯救整个民族的重担,用诗歌呼唤神性的复归和存在的本真状态,把一切伪装(Verstellen)着的假象都还原其本来面目,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然而,作为“此在”的人为何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呢?
正如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所言,“……大地是一切涌现者的返身隐匿之所,并且是作为这样一种把一切涌现者返身隐匿起来的涌现。在涌现中,大地现身而为庇护者(das Bergende)……” 人此时立于大地,是自然的一部分,死后又将归附大地中,始终是自然一部分,这样看来,人是自然中永恒的栖居者;而“诗意”正是要唤起人的神性。在诗歌中,上苍的至善至美是人效仿和倾诉的对象,而神如苍天彰明。因此,呼唤神性的重生既是操心所在,是时代的强音,也是海德格尔的期冀所在——天地人神四位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