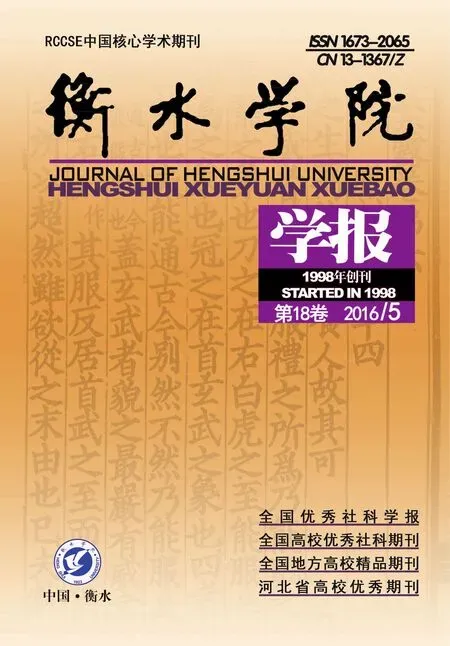法哲学视域下《管子》“教训成俗”说
程梅花,卢舒程
(阜阳师范学院 a. 学报编辑部;b.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法哲学视域下《管子》“教训成俗”说
程梅花a,卢舒程b
(阜阳师范学院 a. 学报编辑部;b.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管子》“教训成俗”说提出了使社会道德法律规范内化为民众行为习惯和社会习俗的基础、条件和方法,是其法哲学方法论思想的一部分。其要义可归结为四个方面:构筑“教训成俗”的物质基础——重本先农,取民有度,体恤保障;建设公平合理的制度文化——一臵其仪,正法直度;形成自上而下的良性示范效应——治官化民,其要在上;营造无隙可乘的防范环境——形势不得为非。
《管子》;教训成俗;法哲学
“教训成俗”说出自《管子·权修》篇,原文是:
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
所谓“邪行”“淫事”,即背离社会道德、法律规范的行为,这种行为多了,刑罚自然也随之变得繁多。作者认为“教”“训”是避免“邪行”“淫事”的方法,但“教”“训”必须达到“成俗”的效果,才能使“刑罚省”。在“教训成俗”中,“教训”是规范民众行为的方法,“成俗”是“教训”的理想效果。那么,什么是“教”“训”和“成俗”呢?《说文》的解释是:“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训,说教也。”“俗,习也。”段玉裁注云:“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伸之凡顺皆曰训。”“习者,数飞也。引申之凡相效谓之习。……《曲礼》‘入国而问俗’,注:‘俗谓常所行与所恶也。’汉《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①看来“教”“训”主要是通过行为示范、说教道理的方法,让民众认知、仿效符合社会道德法律规范的行为。而“成俗”就是通过反复的示范、说教、认知、模仿,使这种规范化的行为成为经常性的习惯。习惯成自然,习惯养成之后,社会上背离道德法律规范的行为就自然会减少,受到刑罚惩处的人也相应会减少。
将“教训成俗”视为治国牧民的基本方略是《管子》中多篇一贯的观点,仅“成俗”一词就出现在《权修》《法禁》《法法》《君臣上》四篇中。“训”字出现9次,有些篇章中的“顺”即“训”,“教”字出现149次,其中“教训”一词出现6次。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篇章虽未直接使用这些字词,却阐述了相关的观点。
如何“教训成俗”?《权修》有一段概括性的论述:
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臵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
提出了规范民众行为的基本逻辑,可以归结为几个主要环节:首先,要通过创造物质条件建立感情基础;其次,要实行并公开明确、统一、公平的道德法律规范和行为准则;第三,统治者和管理者要率先模范地遵行;第四,营造无隙可乘的防范环境。
一、构筑“教训成俗”的物质基础——重本先农,取民有度,体恤保障
“厚爱利足以亲之”,这句话把建立亲近的感情作为施政的前提,又把感情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治国者不仅要“爱利”百姓,而且其政策措施要足以在感情上感动百姓,才能取得百姓的信任。
《牧民》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两句话充分说明了物质生活条件是人们道德意识自觉和行为规范化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构筑“教训成俗”的物质基础呢?《管子》从生产、赋税、保障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方法论原则。
在生产环节,《管子》反复强调“重本事”“禁末产”“农事先”等,《乘马》还提出了“均地分力,使民知时”的农业发展方法。认为“均地分力”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作用。尤其英明的是作者将生产与赋税联系起来,充分认识到赋税对百姓生产生活的影响,所以在“均地分力”的基础上,还必须“与之分货”“审其分”,使“民知得正”。意即明确审慎地制定赋税制度,让民众心里清楚地知道生产成果有多少要上交官府,有多少属于自己,这样,才能使“民尽力”。
至于如何“审其分”,《乘马》主张“相地而衰征”,这是《管子》一项赫赫有名的政策主张。“相地而衰征”,首先要“正地”,因为“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正地”即对全国的土地资源进行客观准确的核算,将各种不同土地根据实际情况以不同比例折算成耕地,然后公平合理地分配给生产者,再根据土地的质量和产量制定不同的税率,按不同的标准征收赋税。
关于赋税,《权修》提出了“取于民有度”的基本原则:
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该篇作者深刻认识到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土地和民力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资源,两者都是有限的;这里“人君之欲”可以广泛地理解为统治集团的个人消费欲望和政府部门的公共消费欲望,这些欲望如果不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就会无限地膨胀。因此,取于民是否有度,关键在于统治者能否“用之有止”。张佩纶认为这段话是《牧民》“上无量则民乃妄”句的解[1],说明统治者的消费行为会影响民众的行为方式。统治者自己不遵守规范,民众也不会听从“教训”,对民众的规范更不可能“成俗”。所以《法法》作者认为明智的统治者:“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这就叫“用之有止”,“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统治者“用之有止”,才能“取于民有度”;“取于民有度”才能保证各行各业生产的正常秩序。
对于老幼孤寡、贫病残障者,《入国》提出了“九惠之教”,即由政府实行的九种福利保障制度,包括“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振困”和“接绝”。通过物质生活条件的保障和精神上的慰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他们对社会可能产生的不满,避免被生活所迫违反规范。值得一提的是“九惠之教”都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常规化的施行,不是作秀式的、以点代面的偶尔为之。只有常规化的普遍的保障才能切实起到稳定社会秩序、规范生计无着者行为的作用。
2006年6月21日《参考消息》第15版一篇来自6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题为 “中国住宅区‘城堡化’令人深思”的文章,介绍中国一些城市小区,特别是高档小区戒备森严的“城堡化”以及小区与外界结合地带最不安全,居民不得不自组“伏击队”的现象之后,作者分析了原因:认为这种现象与贫富分化的加剧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有关,并指出“在福利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低收入者基本没有什么动机去抢劫盗窃”。这种现象表明了一个社会中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多纳税救济穷困,富人不只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等于对自身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投资。《管子》作者似乎早在两千年前就认识到对穷困者的救济与保障是国家和统治者的责任,这不仅是为了穷困者,也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在。
二、建设公平合理的制度文化——一置其仪,正法直度
《管子》虽然认为一切社会规章制度、行为准则都是君主制定的,但同时强调了君主立法要遵循的两项客观准则:“一置其仪”和“正法直度”。
“一置其仪”即君主制定的规章制度要有统一性,这一条体现的是“公平”原则。《法禁》说:“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余不强而治矣。”②这里“议”指有所偏颇,向某些集团或阶层倾斜,“赦”是设立特殊因由使一些罪行勉于处罚,“假”是设立特殊条件将爵禄授予没有合法资格的人,这些都是不公平的制度规章。没有这些例外规条的制度规章才是具有“合法性”的法,也才能被民众普遍认同、自觉遵循,成为习俗。有这些例外规条,人们就会想方设法钻制度规范的空子,不去遵循一般的常规制度。《法禁》指出能否“一置其仪”的利弊在于:“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
“正法直度”是合理原则的体现,亦即“善法”的要求。《版法》说:
凡将立事,正彼天植,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
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版法解》诠释曰:
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则不私近亲,不孽疏远。
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仪。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国乱。
立法者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志,心志端正才不会区别对待近亲和疏远,立法者应像风雨一样普施甘霖,通过正直的法度使举国上下都得到法律的保障。一个国家没有法度,人们的行为就没有规范,做事情也没有标准;但如果法律不中正、度量不合理,一样会导致国家的混乱。
那么“正法直度”的标准是什么呢?《管子》认为国家法度的根本依据是“道”或“天道”,“道”的具体表现则是事物的“义理”和民之“众心”。
《管子》中“道”字凡509见,有多重含义,如:道路、引导、方法等。其中作为哲学范畴的“道”,是指整个宇宙万物的总根源、根本规律和终极依据。如:“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形势》),“道,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心术上》),“大道可安而不可说”(《心术上》)等。《管子》中作为哲学范畴的“道”和《心术上》篇提出的“静因之道”都是老子“道论”的继承和发展。老子思想中作为宇宙总根源的“道”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无为,所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二章》),道虽然是万物的总根源,却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或游离于万物之外的主宰者,而是内在于万物之中,体现为万物自身的本性和规律,“道”的作为就是使万物各自顺其自然本性和规律生存、发展、消亡,“无为”就是“道”治理宇宙的方式,其结果则是“无不为”,一切都能得其所、尽其性、遂其生。所以,老子主张人间统治者——“帝王”或“圣人”治理国家应该效法“道”,实行“无为而治”的方略。《管子·心术上》所提倡的“静因之道”,通常被纳入认识论范畴,其实也是一种治国之道,是老子“无为而治”的方法论。
何谓“静因之道”?《心术上》篇讲得很清楚:
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
有道之人没有先入之见,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任何事物,尊重事物之自然,亦即“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静因之道”就是要根据事物固有的本性和规律对待事物,从事物本身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意志出发。所以说:“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这正是《管子》要求君主立法所应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心术上》“经”③说: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故必知不言之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殊形异执,不与万物异理,故可以为天下始。
《心术上》“解”说: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故曰“圣人”。“不言之言”,应也。应也者,以其为之者人也。执其名,务其应,所以成,此应之道也。“无为之事”,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
这里所说的“名”不仅指事物的概念,还包括用来纲纪事物的规章制度等,而且主要指后者,因此可与广义的“法”相对应。“形”也不仅仅指事物的外形,而是主要指事物的固有属性和规律。“名当”可以理解为君主人为制定的规章制度等与事物固有的属性、规律相符合,能做到这一点的君主才可以称为“圣人”。“解”把“不言之言,无为之事”诠释为“因”“应”,“因”“应”不是不为,而是以客观事物的本性和规律为依据,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为所当为。由此可见,《管子》所理解的“无为而治”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以其形因为之名”,即以客观事物固有的属性和规律为依据制定人应该遵循的社会法纪规范。
《管子》认为国家法纪根源于“道”、体现“道”,才能被民众接受,《形势解》指出:“民之从有道也,如饥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阴也。故有道则民归之,无道则民去之。”“行天道,出公理,则远者自亲;废天道,行私为,则子母相怨。”《君臣上》也认为:“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则下虽有奸伪之心,不敢试也。”只有符合“道”的政策措施才能成功落实;只有符合“道”的法制禁令才能令行禁止。“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
作为宇宙万物总根源和终极依据的“道”毕竟太抽象、太笼统了。具体点说,君主立法要如何以“道”为依据呢?或者说,君主要从哪里把握事物的“道”呢?对此,《管子》认为,“理义”和“民心”就是“道”的体现,“得理义”“顺民心”就能得“道”。
《君臣上》说:“是故别交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道德定而民有轨矣。”《心术上》说:“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理”是“道”在具体事物中的体现,或者说是不同事物所得的“道”,“德”与“理”其实是“名殊而体一”,“德”是从得于道的角度讲事物的本性和规律,“理”是从事物自身及其相互之间的区别角度讲事物的特性;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理”,但所有事物的“理”都得于“道”,因而都是“德”,可以说“德”是“理”的总名,“理”是“德”的体现。而“义”比“理”更加具体,是事物的“理”在具体的时间、空间和环境条件下的具体表现,是“理”在当下的准则。
这里的“理义”是事物共性和个性、一般规律与特殊状况的统一,君主立法能够达到这种统一,才是善法,也才能行之有效。《七法》说:“错仪画制,不知则不可。”何谓“则”?“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则”和本质、规律、必然性等是同一系列的概念。如果君主能“论道行理”,“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莫敢开私焉”。作为立法者,君主必须“得理义”,或者说,能够“得理义”,才是理想的君主,也才能成功地实现治国的目标。这也是《管子》多篇作者笔下“圣人”的风范:“圣人之求事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故义则求之,不义则止。可则求之,不可则止。”(《形势解》)“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尽天地之道。景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恶声美,是以圣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类来也。”(《宙合》)事物之“则”是“唱之”者,君主之“法”是“和之”者,“和之不差”就能尽“道”。“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七法》)。
“民心”也是“道”的体现,但《管子》要求君主尊重的“民心”,并不是每个人或某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众人之心。《君臣上》明确指出:“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这段话让人想起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的“合力”的论述。他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2]
恩格斯认为历史既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又是由无数单个人的意志相互交错,组成的合力创造的。每一个人的意志都既不能完全实现,又不是零。
《管子》的“众心”说当然不能和恩格斯的“合力”说相提并论。但是“众心”说的确很有见地,也很辩证。听信单个人的意志,包括君主个人的意志都是“愚”,只有综合众人的意志才能“圣”,在《管子》中多处强调“公”,反对“私”,包括君主在内的任何单个人的意志都是“私”,只有“众心”会聚之处才是“公”,“公”是“道”的根本特质,所以“圣德”“公道”“民心”在“公”的特质上是一致的。君主不想逆历史潮流而动,就必须尊重民心,以民心为立法依据:“罪人当名曰刑,出令当时曰政,当故不改曰法,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正》)“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
总之,“得理义”“顺民心”是令行禁止,国家法纪规章制度得到臣民认同和遵循的前提,君主依“道”立法,在遵循理义、尊重民心的基础上制定规章制度、政策法律,做出各种决策,是使法为善法、避免决策错误的根本方法,即法律制度本身合法性的有效保障。有人认为,即使法为恶法,也比无法强。《管子》认为从治国效果上看,恶法和无法一样与治国目标相背离。《七臣七主》篇说:“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只有善法才能够以刑去刑,深入人心,成为自觉遵循的社会习俗。
三、形成自上而下的良性示范效应——治官化民,其要在上
常言道“身教重于言教”,社会行为模式的形成通常都是上行下效的结果,《管子》充分认识到君主自身行为对臣民的巨大示范效应,要想将臣民的行为纳入道德法律规范之中,君主首先要成为道德自律、遵纪守法的模范。
《君臣上》说:“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君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道德品行,才能够对群臣百官和百姓起到示范教化的作用。君主要想使自己品行端正、高尚,就必须首先“治心”,因为:“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君臣下》)“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于形容,见于肤色。善气迎人,亲于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戎兵。不言之声,疾于雷鼓;心气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惩过,气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内业》)人的言行举止是听从其内心观念指挥的。内心的意念看似隐蔽,却不由自主地表现于外在的神气、面貌、形象和行为中,所以君主藏于内心的无形的心气意念,往往比有形的赏罚更能影响臣民的思想行为。“治心”的关键在于节制私欲和个人好恶。《禁藏》指出:“夫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不听钟鼓,非恶乐也,为其伤于本事,而妨于教也。故先慎于己而后彼,官亦慎内而后外,民亦务本而去末。”“明王”之所以能够节制自己“美宫室”“听钟鼓”的欲望,是因为他们有清醒的价值取向:君主的价值不是体现在纵欲享乐上,而是体现在“教”上。充分认识到君主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源头,自己的言行举止就是整个社会风尚的航标。
《牧民》指出:“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七臣七主》也认为:“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则民好垦草莱,主好货则人贾市,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吴王好剑而国士轻死。死与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恶也,然而为之者何也?从主之所欲也。”如果君主放纵自己的欲望和好恶,就会引导整个社会偏离正轨。
《形势》提出:“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唯夜行者独有也。”“四方所归,心行者也。”所谓“夜行”“心行”,《形势解》诠释为:“明主之使远者来而近者亲也,为之在心。所谓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矣。”君主要实心诚意地以道德自律,而不是将德行视为一种“文饰”,无论远近,四方之人都能感觉到是真心行德,还是“假仁义行”。
法律规范尽管具有国家强制力,但要想使法律规范内化为社会习俗,单靠强制力是不够的。《法法》指出:“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臣民效法君主,不是听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做。如果君主不依法行事,臣民也会无视法律,上下皆视法律制度为虚文,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君臣下》也说:“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君主应该率先守法,做遵纪守法的模范。《任法》称能做到这一点的君主为“圣君”“上主”,《明法》说是“先王之治国”的特点。
尽管君主手里握着立法大权,但法律制度一旦制定,君主也不能凌驾于法之上,或游离于法之外。这在君主专制制度下自然只能是一种理想,但作为一种目标和理论上的原则,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管子》充分认识到当权者的行为对民众行为的示范效应,反复告诫统治者:要规范民众的行为,必先规范自己的行为。此乃能否“教训成俗”的关键。
四、营造无隙可乘的防范环境——形势不得为非
《八观》篇说: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闬不可以毋阖,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闾闬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故形势不得为非,则奸邪之人悫愿;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宪令著明,则蛮夷之人不敢犯;赏庆信必,则有功者劝;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罚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闭其门,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罚寡而民以治矣。
防范环境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首先是硬件设施的防范功能要周全,如果不周全就会成为人们做坏事的一个外在诱因。因此,硬件设施建设要符合法律规范的标准。比如法律禁止偷盗,那么财产就应该收藏好。如果关防不严,轻易就能盗得,就会诱人偷盗。其次是软环境,主要是法治文化的建设,笔者对法治文化建设提出三个准则:严、明、信必。
严,即严格、公正地执行法律,不留丝毫通融松动的余地,使那些不把法律当回事的人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和不容置疑的严肃性;明,即各种行为规范要明确公开,使众所周知;信必,即信赏必罚。
执法者和执法机构能够落实这三个准则,就能避免侥幸心理的产生,普遍树立法律信用,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除了这三个法治准则之外,《权修》篇还提出了这些准则落实的切入点:“禁微邪”。
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则必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治之本也。④
《牧民》将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提到维系国家存亡的高度强调道德规范建设的意义。“禁微邪”是“四维”建设的切入点。个人习惯、社会习俗都是从小事逐渐养成的,在小事上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和习俗,才能避免在大事上犯大错。
卢梭认为,一个孩子从小在没有邪恶和犯罪、不道德现象的环境中长大,就会自然而然地将这些视为不正常的病态,习惯性地抗拒这些现象。中国孟母三迁的故事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当今有个识别假钞的训练,整个训练过程中学员们都看不到一张假钞,让他们认识的只是真钞。教员认为,只要他们充分认识了真钞,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鉴别假钞的能力,所以识别假钞的方法就是认识真钞。《管子》“形势不得为非”的“教训成俗”方略,深刻而充分地体现了这个教育原理。当然,周密防范,尤其是硬件的“闭”“塞”,只是环境建设初期的必要措施,防范的目的是达到无须防范的效果,等到“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之时,硬件的“闭”“塞”禁防就成为多余的了。那时这种关防的功能就由外在的设施转移到内在的价值观和信念,由他律转化为自律,由强制勉强变为自觉自动。
注释:
①《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一二七上、九一上、三七六上。
② 俞樾云:“‘议’当为‘俄’字之误。《说文》‘俄,行顷也’,法制不俄,言法制平正不顷侧也。”《管子集校》第214页。
③《管子》书中有几篇定名为“某某解”,如“牧民解”“形势解”等,后人把被解的篇就相应地称为“经”。还有些篇,前面概述要义,后面逐句训解,两部分包含在一篇之中,如《宙合》《心术上》等,我们不妨也分别称为“经”“解”。
④ 此节最后一句据郭沫若说改。《管子集校》第45页,郭沫若案:“‘禁微邪’乃牧民者之事,不属于民。‘禁’上当夺‘则必’二字,下‘民之’至‘禁微邪’十七字当衍。”
⑤ 其中“令行禁止”5见,“上下和”3见,“令不行”24见,“上下不和”5见,“下怨上”5见。出现在
《牧民》《形势》《权修》《立政》《七法》《版法》《重令》《法法》《兵法》《问》《任法》《七臣七主》和四篇《解》等16篇中。
[1] 郭沫若.管子集校[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40.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8-479.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On the Theory of “Teaching and Training being Assimilated into Custom” in Guanz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Philosophy
CHENG Meihuaa, LU Shuchengb
(a.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b.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236037, China)
The theory of “teaching and training being assimilated into custom” in Guanzi, part of his methodological idea of legal philosophy, points out the bases, conditions and methods for assimilating social principles, law and regulations into people’s habit of conduct and social custom. Its essentials may be summed up as four aspects: to construct the material bases for “teachings and training being assimilated into custom”——giving priority to developing agriculture, taking from the people limitedly, sympathizing with people and protecting their interests; to construct fair and just system culture——working out consistent manners, rectifying law and rules; form positive demonstration effects from top down so as to administer officials and cultivate citizens; to construct strict precaution environment under which no crimes are allowed.
Guanzi; teaching and training being assimilated into custom; legal philosophy
B226.1
A
1673-2065(2016)05-0057-07
10.3969/j.issn.1673-2065.2016.05.011
2016-08-18
安徽高校省级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SK2016A0687)
程梅花(1965-),女,安徽潜山人,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卢舒程(1990-),男,安徽阜阳人,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在读硕士。
——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中的史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