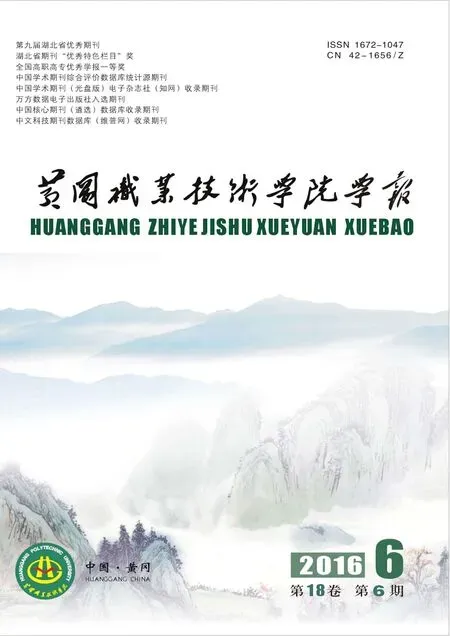小说命名与文化语境
马 硕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小说命名与文化语境
马 硕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小说的命名与一定的文化语境相关。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思维,继而影响到小说的创作及命题方式。在西方文学中,许多现实主义初期的小说倾向于以人物姓名作为小说题目,而中国现代小说则偏重于以概括性的、形象性的字词作为题目。这种小说命名的不同反映了不同语境下的思维差别。本文描述了中西小说命题的特色,分析了产生差别的原因,试图找到小说命题的规律。
小说题目;文化语境;文化思维
小说在文学的各种题材中扮演了“启世”的特殊功用,首先是它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以包罗万象的恢弘气度呈现的社会中各个阶层、各种景象,是其它文体所不能达到的。其次是它所表现出的时代性,只有小说是更易于涵养出风波迭起的社会变迁。这种集时间性、空间性多维一体的文体具有独特的魅力。相比于其他文体的题目,小说的题目用或直白、或抽象、或概括、或隐喻的方式,表达出作者的观点。因此,对小说命题差异性的探索,有益于寻找出在不同语境下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从而对小说命题的发展上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一、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命名
西方近代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涌现出了相当数量的文学巨擘,以表现社会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为例,这些文学大师多以社会为背景,对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都做出了细致而充分地刻画。这些作家运用多种写作手法,为近代的欧洲文学浓墨重彩地勾勒出一卷卷饱含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文学长卷。
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源远流长,从史诗巨著到第一部反射现实的小说《十日谈》,许多作家在以模仿、表现见长的西方文化背景下,在小说命题上使用了大量的客观存在事物,如人物姓名、事件或事物的名称等。西方小说表现的着眼点在于人的社会属性,以重视人的个体存在、表现人物个体意义为特点的西方价值观让文学作品大都以个人为中心辐射点,通过描写典型人物来反映社会及时代的思潮。这种思维表现在小说的命题上,以特定的小说主人公的名字进行命名,成为现实主义早期阶段小说其一大特点。法国作家群中有巴尔扎克的代表作《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通俗小说大家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小仲马的《茶花女》,自然主义大师左拉的《娜娜》《卢贡·马卡尔家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羊脂球》等,英国作家群中有夏洛特的《简爱》、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等,俄国现实主义大师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等,美国作家群中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德莱塞的《嘉莉妹妹》等。“对于一部小说来说,这样的命名方式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作品的主人公,同时也昭示了该小说以其人其事为主要线索的结构方式”[1]。这些以人物作为题目的作品无不表现出作家对社会的透视,以主人公的人生镶嵌到历史的社会背景中,形成作者对时代的思考和认知,又反映出文化视角的不同切入点。这样的写作特点与命题方式则显得更加直接和客观。
文学对现实的表现是立体的、多面的。在以人物姓名命名的小说之外,还有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及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纳撒尼尔的《红字》,麦尔维尔的《白鲸》等作品。这些并非以主人公姓名命题的巨著,但也塑造了许多经典的人物形象。如《飘》中的美丽、傲慢的女主人公斯嘉丽,从一个醉心于玩乐的少女在战争的无情中,快速成长成为了一个有头脑有担当的妇女。斯嘉丽在面对家里百废待兴的境况时,脱口而出的“不管怎么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几乎可以看成是独立而坚强的美国精神。在近几百年中科技理性的影响下,西方的文化思维深含着“存在”的意识,关注于思维的创造者、使用者——人的感受。这些作品在刻画个体典型人物的同时,体现了西方价值观中对于人类自由的关怀,对于人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思考,具有总结及象征的意义。
二、西方现实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现代小说
以长篇章回小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小说,有着分回标目、段落整齐又首尾完整的特点。最具代表性的“四大名著”,在两方面体现出小说命题特点。一是浓缩概括,《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西游记》在命题上都是对内容的提炼,且“善于借助小说命名宣扬儒家道德伦理规范、强化小说的社会功用。忠孝节义是小说命名寓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2]。二是主观表现,以意象的组合形成象征效果,来表达作者的心理感悟。现代小说大家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燕归来》等,充分继承了章回小说的特点。在他的小说作品命题上,多数以浓缩概括为主,夹杂主观意象,展示出了词藻秀美、寓意深刻,富有传统韵味的小说题目。
我国的传统小说较少以人物姓名作为题目,但偶尔也能见到,例如古典名著《金瓶梅》,就是以三位女主人公名字各取一字来命名的。有一类被称之为笔记小说的类别,专门以人物为主体,并以人物姓名做为题目。笔记小说是一种具有小说的性质,介于随笔和小说之间的微型小说。它以人物速写的方式,通过若干件典型事例去刻画人物和交待故事情节。笔记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汉魏时期就已经有关于志怪、传奇、杂录、琐闻、传记、随笔之类的著作,起源可以追溯到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它简洁而生动,往往通过一个人的一件事或者几件事去反映人物的形象。因此,笔记小说大多数都以所描绘的人物来作为作品的题目进行命名。古典笔记小说如《聊斋志异》、清代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等,都属于以作者所闻、所询的志怪异事,以速写的手法生动地突出人物。
但这类以人物姓名命题的小说,如《香玉》和本文中所探讨的在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以人物姓名命题的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是题材的不同。笔记小说主要是对奇闻异事的搜集,而不涉及各种人物的关系和所表达的思想立意。传统意义的小说则或采用象征、抒情,或采用客观写实的叙事手法,对一个或多个主题的中心进行阐述。其次是叙述手法的不同。笔记小说多以速写的方式进行人物形象的勾勒,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则采用多层次、多方位的描写,对不仅是人物,更是人物背后的社会进行全面描绘。再次是结构的不同。笔记小说简短紧凑,很难在一个短小的篇幅里展现出作者通过小说所期冀表达的思想,而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则可以有足够的空间进行主旨呈现。因此,尽管笔记小说也具有小说的性质,但同样是以人物姓名所命题,《聂小倩》和《倪焕之》无论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还是对现实的反映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差别。
现代文学时期作品的命名,有学者认为其命名是“括意型”,如鲁迅的《祝福》《药》《伤逝》,茅盾的《蚀》《虹》《霜叶红似二月花》,巴金的《家》《寒夜》《憩园》,许地山的《缀网劳蛛》,老舍的《四世同堂》《正红旗下》,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作品。这些既传承于传统小说表现,又深受西方小说架构影响的中国现代小说,大部分在题目的命名上都展示出一种意象性。这些命名“极为关注作品内涵与思想意义的提炼概括,通常采用政治象征、双关隐喻等手段,让自身获得双重或多重意义诉说,尽可能地给出作品的思想深度信息”[3]。在这些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作者都赋予了主要人物和从属人物饱满而鲜活的灵魂,借着这些被塑造的灵魂展开整体叙事。如李劼人受《包法利夫人》的影响而创作出的《死水微澜》,通过描写在辛亥革命前后,一个农村女子蔡大嫂与几个不同男子的爱恨、婚恋,而引出的各个社会阶层的百态。用《死水微澜》命题,既有纪实的意义,又更多的是对当时社会、家庭、革命等各方面的一种象征。
以巴金为例。巴金的创作,既有来自“五四”遗风的激昂,又有游学于法国、受到法国启蒙主义余波影响的先锋性。巴金的作品题目几乎都是以意象性的词语对内容进行概括,从早期的《灭亡》到《萌芽》,从《激流三部曲》到《抗战三部曲》,以及《寒夜》《憩园》,这些书名都体现了富含中国特色的意象的深意。如《寒夜》中多次出现了“夜”,对寒夜的描写不仅是映衬当时的恶劣自然环境,更是表现出恶劣的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经常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心凉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应该正是巴金所创作《寒夜》的根本表达。巴金在后来谈到“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中书名的拟定时说,并不是单纯地描写着爱情事件的本身,只是借用爱情的关系来实现主人公的性格[4]。
再以老舍创作为例。这些在西洋受到过文化冲击的作家,创作思维大都是中体西用的。他们在作品的形式、表达手法上充分借鉴了西方小说的现有经验,但在构思主体、作品的情感表达方面仍是中式思维。老舍在初期的模仿上,中体西用的创作结合还未真正形成其自身的特点。在创作《四世同堂》时,老舍没有太多地使用“老舍式幽默”的态度,而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从关注社会到关注群体,再以关注群体定格细化到关注个人。《四世同堂》是祁老太爷、祁大爷、祁瑞宣兄弟与两个孩子的人生缩影,对于中国的“四世同堂”这个名词,有着多重的含义。这是一种祝福,是一种喜庆,更是一种福、禄、寿的象征。这四代人以不同的命运发展线索,寄托了老舍对生命的关怀,对人生价值的拷问,体现出落眼于“人”的关怀精神。董学文认为:“‘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与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与塑造。”[5]在小说《骆驼祥子》上,老舍的这种从个体的人物到社会的人文关怀精神体现得更为彻底。以人物外号加名字做为小说的题目,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存环境,社会对于祥子的戕害。还有老舍在1933年出版的作品《离婚》,从点题到破题,是简短而极其关键的一句,“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人和反对离婚。”[6]而不以《张大哥》来命名,就有了一种写意的美感。
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老舍在旅英期间发表的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都是以小说中的主人公作为小说题目,通过人物的经历或成长过程来表现社会。老舍的这三部早期的作品人物不多,故事情节也不复杂,但对于他模仿狄更斯的创作笔调还是比较明显的。狄更斯善于描写小人物。在老舍创作《骆驼祥子》中对祥子的形象设计上多少有些《大卫·科波菲尔》的影子。狄更斯与老舍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从苦难的生活中锻造出独立的人格,不屈的精神。因此,狄更斯在艺术上的幽默,在人物形象上对于精神的塑造,在心理分析上的细致入微,这些都对老舍在之后以底层京味语言展示其作品中形态各异的人物,塑造老舍式幽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老舍之外,鲁迅、叶绍均、茅盾、李劼人等受西方文艺思潮所影响的作家都或多或少地有着相同的认知。鲁迅游学于日本,但其文学理论的架构,对于小说的观点形成则深深受到了西洋文化的影响。鲁迅在果戈里《狂人日记》影响下创作的同名小说是结合了现实,以一类人或者说是整个民族作为典型而进行特写的描绘。而《孔乙己》《阿Q正传》则是以色彩描绘的手法,从人物内心独白、行为特点及所处的社会环境展示了作者所期冀的刻画形式。还有叶绍钧的《倪焕之》,丁玲早期的作品《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庐隐的《曼丽》《丽石的日记》等,这些以人物姓名作为小说题目的作品,无不是以个体的人物去反射群体。但也有例外,孤岛作家师陀有篇以人物名为小说题的《阿嚏》就有些不同,并不是将水鬼阿嚏来象征代表一类群体,或是将阿嚏作为典型人物进行描写,而是通过对阿嚏的形象表现,展示给人以心旷神怡的神话谐趣。师陀认为:“自己的风格与读的西方作家的作品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读的中国古代作品有关。例如‘意识流’‘象征主义’,列御寇在春秋末年已经运用了。还有屈原的诗篇,更是多种多样:有象征主义、有现代主义、有写实主义,还有意识流。”[7]中国小说题目的选取方面体现的含蓄,注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在中国“含蓄”文化习惯的影响下,中国现代小说在命题的选择上,偏向于或以反映小说的主旨,或以总结小说的意义,或以概括小说的内容而进行命名,而较少直接采用小说主人公的姓名。“好题一半文”,小说题目虽是建立在内容的基础之上,但对小说内容又是一次升华。这不仅仅体现出作者对自己创作意向的归纳,更是对内容的深入反射。中国现代作家的写作虽然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但因为中西方文化语境不同,因此,在实际的创作实践中仍是要源于自身的传统,使文学之根生长在中国的深厚土壤之中。中国现代作家的写作,其实是经历了一个由学习西方,到立足中国文化语境进行再创作的过程。
三、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小说命名
中西方小说题目表现出来的差异,是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的外在表现。不同的文化语境对于不同民族的精神特点与思维方式有着明显影响。对于西方小说而言,趋向海洋的社会环境与敢于冒险的生活方式使其精神上体现出自由的亮色。因此,在文艺创作上表现更多的是对于个人自由与人性嬗变的关注。而对于中国小说来说,其改革的契机正处于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由小农经济支撑起来的封闭自足的狭隘思想已进入陌路,亟需一种有开阔气度的文明给自己的文化打一针强心剂,于是一种强烈的学习风气占了上风。中国的现代作家在小说创作的发轫期,受到了西方创作方式和理念的深刻影响,文化先驱们大量引入了西方的小说,如清末翻译家林纾就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而见称于世,代表作品有从《茶花女》翻译来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从《汤姆叔叔的小屋》翻译来的《黑奴吁天录》,从《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翻译来的《滑稽外史》等一百多部作品。西方小说反射下的社会充满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与之相似,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社会背景也充斥着跌宕起伏。在中国现代小说中,人的社会属性大于人的自然属性,从小说的内容表现中可以看出,人存在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之间。人物本身的性格特点来源于社会的影响,而不是自我价值、内心张力的书写。因此,直接以人物姓名作为小说的题目,不足以涵盖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链接。
无论是老舍还是扛起了现代文学小说旗帜的鲁迅,乃至茅盾、巴金等人,在汲取了一定的西方小说的营养后,在后来更多的小说创作中,有意识地从读者接受出发,表现出对作品意象的重视,以有别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视角进行写作。如鲁迅的《祝福》《药》,巴金的《家》《春》《秋》,沈雁冰的《子夜》,钱钟书的《围城》,都通过一种对精神象征的概括去描述社会背景下的人物群体,再集中聚焦在个人的人物身上。特别是《药》,这种象征性的表达尤为明显。鲁迅在创造华老栓和夏瑜这两个人物时,有意赋予他们连起来就代表中华民族的“华”“夏”两个字为姓,而“药”又岂仅是将人血馒头治疗华小栓的病,更是为如何重建国民性的叩问。《围城》也是如此,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描述,深刻地表现出在当时社会下知识分子这类群体对生活、对婚姻的集体困境。
这种由大到小的写作思维体现了中国人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儒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思维模式,已如血脉渗透般深入到了每个知识分子的灵魂里,作为作家,首先就是有一种对社会、对国民的使命感。黄子平等学者在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提出:“通过‘干预灵魂’来‘干预生活’便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自觉的使命感,文学借此既走出了象牙之塔,与民族与大众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又总能挣脱‘文以载道’的旧巢臼,沿着符合艺术规律的轨道艰难地发展。”[7]这种思维对作家的写作影响就是从大到小、深入而浅出地将自己的使命感和价值观,通过对人物的塑化来进行表达,最后进行观点定格。在作品中,关注人物还是关注社会的差异性就直观地体现在了作品题目上面。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直观地从作品题目上看出作者的创作视角与关注倾向。小说题目无论是用以西化思维的个体形象由点及面到体的放射命题,还是以中式思维从社会到群体再到个体人物的聚焦方式命题,都是以一种最直观的方式表达出了作者的写作意向。
一部小说的题目是其作品整体内容的灵魂。从作品的取题上,这种写作倾向传达出了直接的信号。特定人物形象的塑造,象征着一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群体,老舍在后来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的创作中,更深入地表现出了这种通过关怀个体的人物来关注群体,以至社会的特点。师陀受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的影响而创作的长篇小说《马兰》,通过对都市多维度的审视,采用了“马兰”这个意向性的题目。作者以物喻人,又以人比物,这种多重视角体现了作家在创作小说背后对人性坚强的赞许,对生命的礼赞。文学作品中没有绝对的个体存在。所谓的个体,一般是指以文学描写的角度,在特定的视域下,从个体去透视整体。在以人物来表现社会的写作手法中,很多作家在作品中都凸显了这种特点。
小说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以文字的形式展示出社会文化景象。由于中西文化的背景不同,小说的题目也根据其内容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以题目作为内容的窗口,可窥视到作品的主体意义。“中国小说的题名始终和小说自身的特点、中国文化的特点、时代的演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小说标题的内容和命题方式的演变确能直观地透视到历史的沧桑和时代的变迁,确能独到地体味出不同小说流派的艺术作派和风格特征”[8]。作者在小说的命题上,力求以或直观或概括的原则来进行。因此,题目作为小说最直观的标示,无论在西方现实主义思潮下的作品,还是中国反映社会现实的现代小说,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重要作用,并值得深入去研究其内涵与外延的关系。
[1]金琼.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命名与题词艺术[J].学术研究,2015(04).
[2]程国赋.论明清小说寓意法命名的内涵与特点[J].文学评论,2016(01).
[3]张洪峰.小说命名姿态解读[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01).
[4]巴金.雾总序[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6-17.
[5]董学文,金永兵.中国当代文学理论(1978~200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65.
[6]老舍.离婚[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01.
[7]师陀语,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425.
[8]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949~2009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90.
[9]丁妮.小说题名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4.
[责任编辑:南东求]
The Naming of Novels and the Culture Context
Ma Shuo
(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00Gansu)
The naming of novel is related to a certain cultural context.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different cultural thinking is produced, which influences the creation of the novel and the way of the proposition. In western literature, many realistic novels tend to take the name as the title of the novel, while the Chinese modern novels focus on the general, the image of the word as the title. The different naming of the novel reflects different thinking in different contex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novels,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and tries to find the law of the proposition of the novel.
Novel title; Cultural context; Cultural thinking
2016-11-11
马 硕,女,广东广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054
A
1672-1047(2016)06-0083-05
10.3969/j.issn.1672-1047.2016.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