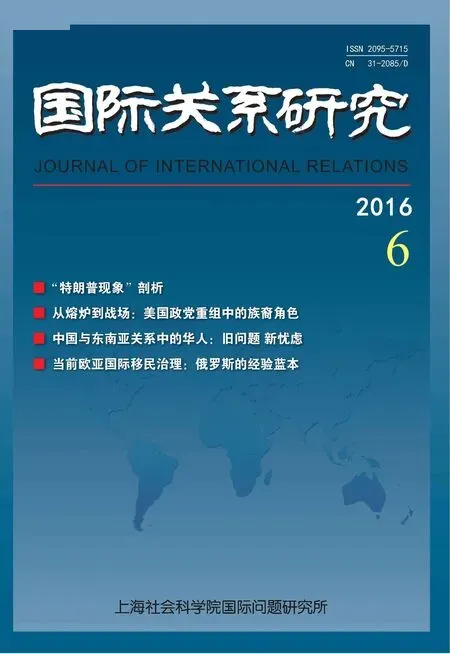网状伙伴外交、同盟体系与“一带一路”的机制建设
顾 炜
网状伙伴外交、同盟体系与“一带一路”的机制建设
顾 炜
网状伙伴外交作为中国提出的重要外交理念,以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目标。相较于传统的同盟体系,网状伙伴外交具有持续性和多元性、内向性和平等性、包容性和灵活性、现实性和现时性等优点,也存在脆弱性和复杂性等不足。开展网状伙伴外交有助于“一带一路”框架内的机制建设。开展网状伙伴外交与建设“一带一路”具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两者都是长期性和持久性的工作,需要中国付出更多的耐心和努力。
网状伙伴外交 伙伴关系网络 同盟体系 机制建设 一带一路
近年来,中国外交取得了积极丰硕的成果,并提出了许多新理念和新概念。“网状伙伴外交”正是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由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在2014年5月的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出,并积极倡导和践行。相较传统的同盟体系,网状伙伴外交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这促使各国愿意在发展对外关系时选择开展网状伙伴外交。借助网状伙伴外交,中国不断推动着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构建。而“一带一路”建设与网状伙伴外交的开展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有力地塑造着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一、网状伙伴外交与伙伴关系网络
中俄两国在2014年5月的联合声明中指出,“双方支持开展网状伙伴外交的各种努力。网状伙伴外交旨在在国际事务中建立伙伴合作的灵活机制。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中俄印等机制已成为类似灵活机制的高效范例。”*《中俄签署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联合声明(全文)》,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5-20/6192687.shtml。联合声明中的这一表述,意味着网状伙伴外交概念的首次提出。此后,学界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初步研究。成志杰认为,网状伙伴外交是一种灵活机制,是中俄双边合作关系在多边机制内的表现,可以被看作是伙伴外交与网状外交的综合。*成志杰:《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中俄合作的新路径》,《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第121~124页。笔者通过对比联合声明的中俄文文本,认为中文文本在俄文文本使用“网状外交”的基础上增加了“伙伴”一词,更加强调了伙伴关系是开展网状外交的基础。*顾炜:《中俄网状伙伴外交的概念内涵和实现路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5期,第135页。列别杰娃认为,网状伙伴外交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О.В. Лебедева,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я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 Право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ХХI век, 2015, №1(34), C.86~91.这意味着开展网状伙伴外交的国家之间具有平等性关系。
与对“网状伙伴外交”这一新概念的初步研究不同,学界对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网络和伙伴战略等概念和问题的研究更加充分和扎实,并在近年来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Sean Kay, “What i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47, No. 3, 2000, pp.15~24;唐健:《伙伴战略与伙伴关系:理论框架、效用评估和未来趋势》,《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1期,第50~78页。除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外,相当多的论述是围绕中国的伙伴关系和伙伴战略展开的。例如:陈志敏:《伙伴战略:世纪之交中国的现实理想主义外交战略》,《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3期,第12~20页;金正昆:《伙伴战略:中国外交的理性选择》,《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7期,第43~48页;陶季邑:《美国学术界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伙伴外交战略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13~120页;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65~95页;Feng Zhongping and Huang Jing,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 diplomacy: engaging with a changing world, ESPO working paper n. 8, June 2014。但也有一些研究涉及其他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例如:刘世龙:《战后日美伙伴关系的三个发展阶段》,《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第63~77页;宋黎磊:《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意图、推进与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第85~102页;Nadia Alexandrova-Arbatova, The EU-Russia partnership: a new context, ESPO policy brief 5, July 2012;等。伙伴关系是各国在平等基础上为实现共同利益和目标而建立的以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外交关系。*门洪华等在定义伙伴关系时强调了共同利益、共同行动、共同目标、独立自主等要素,认为伙伴关系是一种国际合作关系。参见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68页。在伙伴关系一词前加上不同的定语,可以表明两国之间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和发展程度。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同俄罗斯建立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具有最高定位的伙伴关系,俄罗斯也因此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此外,中国与其他国家还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等伙伴关系。*对中国与不同国家建立的不同伙伴关系的初步评述,参见陈晓晨:《中国对外“伙伴关系”大盘点》,http://pit.ifeng.com/a/20160421/48533527_0.shtml。
尽管具体名称和定位存在差别,但中国丰富的外交实践使学界认为中国在执行一种伙伴战略或者说伙伴关系战略。金正昆认为,伙伴战略可以作为中国外交的理性选择,因为其既有助于广泛合作的开展,也可以保持独立自主。*金正昆:《伙伴战略:中国外交的理性选择》,《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7期,第43~48页。这是对伙伴战略作用的积极评价。门洪华等人通过对伙伴关系战略的系统研究,认为相较于中国的战略实践,对伙伴关系战略的理论研究和战略评估明显滞后,而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也存在地位不清晰、成效不明确和层次不分明等问题。*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65~95页。
无论对伙伴战略持有怎样的看法,在实践中,中国确实一直在推动与更多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开展伙伴合作。这些国家类型众多,分布广泛,一张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初具其形。由此,201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11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这是中国在建设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为自己设定的重要目标。构建伙伴关系本身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特色,*《王毅: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特色》,2014年12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2/24/c_1113763159.htm。在构建伙伴关系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伙伴关系网络,则是源于中国外交实践的“路径依赖”。*孙茹:《构建伙伴关系网:中国不结盟政策的升级版》,《世界知识》2015年第6期,第60页。伙伴关系网络的构建也将不仅在经济合作领域,也将在政治安全领域发挥应有的效应。*有关伙伴关系网络的安全效应,参见张锐:《试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政治安全效应》,《国际展望》2016年第5期,第40~59页;刘博文、方长平:《周边伙伴关系网络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当代亚太》2016年第3期,第68~100页。因此,中国外交需要持续推进伙伴关系网络的构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伙伴关系网络是一个相对静态的概念,强调中国通过与其他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不仅拓展了本国的国际影响,更在全球建立起一个对中国友好、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的伙伴关系网,各种伙伴关系共同组成了伙伴关系网络。而网状伙伴外交则是一个更具动态性的概念,强调国家间以伙伴身份开展外交活动,通过不同机制的构建和运行促进伙伴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因此,开展网状伙伴外交有助于建立和维护伙伴关系,并促进伙伴关系网络的构建。
二、网状伙伴外交与同盟体系的比较
学者们在讨论“伙伴关系”时,经常与“同盟”的概念和实践进行比较,探讨伙伴关系相较于同盟的优劣之处。而网状伙伴外交界定的是多个国家在伙伴关系基础上通过各种灵活机制开展伙伴合作的外交活动,其开展有助于构建伙伴关系网络。因此,“网状伙伴外交”作为新概念和国家间关系发展的新理念,其所对应的传统概念应是“同盟体系”。相较历史和现实中的同盟体系,网状伙伴外交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也是中俄等国积极倡导开展网状伙伴外交的重要原因。
(一)俾斯麦的同盟体系
历史上最有名的同盟体系当属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在19世纪后期建立的同盟体系。在德国通过三场战争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后,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和巩固国家统一的成果,在俾斯麦的精心策划下,德国开始构建同盟体系。
第一步,将德国与奥匈帝国联合,实现德国东侧安全地带的延展。1879年10月,德国与奥匈帝国签订同盟条约,确立了共同反对沙俄的目标。第二步,通过奥匈帝国拉拢塞尔维亚。凭借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关系,德国与塞尔维亚密切了联系。1881年6月,奥塞同盟成立,塞尔维亚变成了奥匈帝国的附庸国。第三步,接纳意大利。1882年,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三国签订同盟条约,建立了第一个三国同盟。1883年10月,罗马尼亚与奥匈帝国订立同盟条约,之后德国加入,这同样是一个具有反俄性质的同盟。通过上述三步,俾斯麦的同盟体系得以建立。
俾斯麦的同盟体系主要由3个三国同盟组成,即俄德奥三皇同盟、德奥意三国同盟和德奥罗三国同盟。其核心目标是孤立法国、防止法国向德国复仇。在此之外的另一个功能是德国在奥匈帝国对抗沙俄时对奥匈帝国进行支持。这一同盟体系具有5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外部针对性。每一个同盟都有特定的外部敌人,也就是三国的共同敌人。例如,俄德奥三皇同盟的主要目标是孤立法国,防止法国对德国进行复仇;而德奥意三国同盟的主要出发点是对抗沙俄,是奥匈帝国与俄罗斯矛盾的集中体现。第二,共同作战。同盟条约的签署,意味着盟国之间具有共同对敌的军事义务,这一方面给同盟国家彼此提供了安全支持和保障,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某个国家可能被盟国绑架,被拖进战争中。第三,具有期限和时效。19世纪后期的同盟是传统的结盟关系,盟国订立针对共同敌人的盟约,而盟约具有时效性和固定期限。但形势发展往往会迅速于同盟内部权利义务的调整,应变能力差成为同盟体系的软肋。第四,秘密性。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同盟条约都含有秘密条款,表明了真实的结盟原因。两国在同第三国建立三国同盟后,两国的结盟条约也通常不会公开,这意味着同盟国之间缺乏公开性和彼此信任,容易导致相互猜忌等问题。第五,盟国之间的关系不平等。两个实力差距较大的国家结成同盟,彼此之间的关系通常具有不平等性,较弱的国家需要较强的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关系的不平等导致权利义务的分配方面存在隐患,对同盟体系的发展是不利因素。
实际上,俾斯麦同盟体系的中心是德奥同盟,但德国和奥匈帝国各怀鬼胎,对彼此之间合作的需求和期望达到的目标存在差别,而权力变移的影响使得各国在同盟内的发言权并不相同,由此导致同盟体系存在明显的脆弱性。1887年,德奥意三国同盟面临续约问题,意大利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分别签约,实际上损害了三国同盟的牢固性和整个同盟体系的生命力。在对待沙俄的问题上,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并没有积极强烈的敌视和对抗意愿,它实际上不愿意支持奥匈帝国对抗俄罗斯,采取的替代性办法是促使英国同奥匈帝国合作对抗俄罗斯,从而减轻德国承担的责任和盟友义务。与此同时,俾斯麦始终认为德奥同盟实际上只是一个防守同盟,如果俄罗斯攻击奥匈帝国,德国才会协助奥匈帝国对抗俄罗斯。因此,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德国与奥匈帝国实际上存有异心,这是德奥同盟存续的隐患。与此相类似,英意奥签署《第一次地中海协定》的目的是针对法国,而第二次地中海协定就是针对俄国。但到俄德奥三皇条约满期时,俾斯麦就提议用德俄双边协定代替三皇条约,以博得俄罗斯的好感,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德奥同盟,抛弃了奥匈帝国。最终,在权力变移和私心的影响下,俾斯麦的同盟体系逐步瓦解,最终没能阻止一战的爆发,也没有为德国带来持续的和平。
(二)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
二战后,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同盟体系,这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形成的同盟体系。与俾斯麦的同盟体系呈现隐性中心的特点不同,*俾斯麦构筑同盟体系本质上是为了德国的国家利益,但在表面上它仍然是以德奥同盟为核心,所以该同盟体系呈现隐性中心的特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非常明确地以美国为中心,通过美韩同盟、美日同盟、美菲同盟等双边同盟的形式辐射开来,形成一种轮辐体系。这一同盟体系,在冷战时期帮助美国有效地应对了苏联在亚洲的威胁,防止共产主义蔓延而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塑造了日韩等国家的对外政策,维护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不仅维护了亚太的稳定,也为地区经济合作勾画了蓝图。*James Baker,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1991/1992, p. 5.
但这一同盟体系与俾斯麦的同盟体系一样,也具有很多问题,并在冷战结束后被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首先,美国的各个盟国之间存在关系不睦的现实。例如,韩国和日本之间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长期存在争端,这不仅减损了同盟体系对维持地区稳定和威慑敌人的效果,也严重影响了该同盟体系的网联性。换句话说,由于盟国之间难以形成紧密联系,所以美国的同盟体系并不具备“网状”的特点,而仅仅是多个双边同盟的组合体。也正因如此,美国在近年来加快推进亚太同盟体系的转型,以建立小型三边合作(如美日澳、美日韩、美日印等)的方式,探索同盟体系的“网络化”。*杨毅:《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维系与转型》,《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6期,第106~113页;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39~50页。其次,亚太同盟体系的不平等性始终存在。尽管美国在冷战后多次调整了与盟国之间的盟约内容,但同盟关系的不平等和不对等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方面,美国存在对自身实力被过度消耗和同盟国过度搭便车的疑虑。美国作为同盟体系的中心,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维持体系的运行,成本耗费巨大,这对同盟体系的持久性构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同盟国的心理也十分复杂,既想获得独立平等的地位,又害怕真的被美国抛弃。美国与盟国之间因不平等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和“副作用”,*孙茹:《美国的同盟体系及其功效》,《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7期,第11页。都影响了同盟体系作用的持续发挥。再次,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依然固守传统思维。尽管冷战结束后美国在诸多方面对亚太同盟体系做出了调整,但整体上这一同盟体系并没有跳出传统同盟的框架,依然需要找到一个保持同盟凝聚力的外部敌人。如果敌人发生变化,威胁来源不同,则同盟也有极大可能发生变化,同盟体系的持续性和效用令人怀疑。
(三)网状伙伴外交的优势和不足
1.网状伙伴外交的优势
在学者们的初步研究中,网状伙伴外交具有多边性、协调性、合作性、灵活性和战略性等特点,*成志杰:《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中俄合作的新路径》,《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第126~129页。但如果对比历史上的俾斯麦同盟体系和现实中仍然存在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网状伙伴外交的自身优势则体现在更多方面。
(1)网状伙伴外交具有持续性和多元性的特点。传统的同盟体系建立在各项盟约的基础上,而盟约通常是具有固定期限的,一旦约期届满,就涉及到是否需要续约的问题,也就是盟约的时效性问题。在考虑续约时,参与同盟体系的国家必然要根据最新的形势重新评估自己在同盟中的成本和收益,如果认为续签盟约不能最大化本国的利益,或者各国无法谈妥新的盟约条件,那么盟约将无法续签,同盟体系就面临着调整或重塑的需要。例如,俾斯麦时期的很多同盟都是五年期限,如此短暂的盟约和变动快速的国际形势,都使各国不断盘算各自的成本收益,同盟条约不断需要调整,也就严重损害了同盟体系的持续性。而网状伙伴外交通常不涉及断续问题,它所形成的机制或组织框架,通常没有约定具体的实施期限,一旦机制得以建立和健康运行,其所带来的收益就将不断惠及各国,并使各国的合作意愿不断增强。因此,网状伙伴外交更具持久性和延续性,它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外交模式,与同盟体系的阶段存在形成明显差别。
按照普遍被接受的联盟定义,联盟是两个或多个国家在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的正式或非正式安排,或者说是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Ole R. Holsti, Terrence P. Hopmann and John D. Sullivan, 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3, p.4. ;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2. ; Arnold Wolfers, “Alliances,” in David L. Sills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268.因此,通常情况下,由各个联盟组成的同盟体系也具有单一性特征,无论是俾斯麦的同盟体系还是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都聚焦于军事和安全领域,通常只涉及一个方面的功能,特别聚焦于高级政治领域。而网状伙伴外交更加多元,参与其中的各国既可以在军事领域建立合作机制,也可以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展伙伴合作。不仅合作领域具有多元特点,既可涉及高级政治,也可在低级政治领域加强合作;而且在合作形式上,网状伙伴外交的机制种类也更加多样,既可以像传统同盟那样订立规约,也可采用进行元首会晤和建立政府部门间对话机制等方式。
(2)网状伙伴外交具有内向性和平等性的特点。传统的同盟体系中,国家为了制衡威胁而与其他国家结盟,*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有明确的对象和目标,针对特定的外部敌人。例如,法国是俾斯麦构建同盟体系的主要防范对象,美国的同盟体系在建立之初是为了应对亚洲的共产主义威胁。但在这种同盟体系中,一旦敌对目标有所变化,或者有一方不再采取敌对立场,同盟就面临失效或瓦解,同盟体系也将失去基本架构。正如俾斯麦时期所示,奥匈帝国参与同盟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法国而是俄国,但德国对俄罗斯的敌对态度显然要软化许多,两国在结盟目标上的差异导致俾斯麦同盟体系的核心环节——德奥同盟存在脆弱性和易变性。而苏联解体一度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面临着无敌可树的尴尬局面,这也是美国同韩日等国调整盟约的重要原因。基辛格认为俾斯麦的同盟体系起到了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防止德国潜在的敌国结成联盟,另一方面也可以约束德国盟国的行动。*[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所以,联盟也具有降低成员内部冲突和作为内部控制工具的作用,但究其根本,联盟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反对共同的外部敌人,*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4;克里斯托弗·格尔皮:《作为内部控制工具的联盟》,载[德]赫尔戈·哈夫滕多恩等主编,尉洪池等译:《不完美的联盟:时空维度的安全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94~124页。因此,同盟体系在整体上具有明确的外向性敌对特点。但网状伙伴外交是内向性的,它不针对第三方,不是为了应对某个明确的敌人,也不以树敌为目的。构建和开展网状伙伴外交,更多是着眼于自身成长,强调各国通过外交活动加强合作和协调,巩固伙伴关系,促进各国的发展和共同进步。网状伙伴外交的目标指向是内向性的,也因而具有更多的建设性色彩。
从内部关系来看,参与开展网状伙伴外交的国家都是平等个体,各国通过互利共赢的合作共同成长,每个参与其中的国家都会付出相应的合作成本,也各有利益收获。尽管利益差异仍然存在,但因为网状伙伴外交的多元性特点,使各国能够从不同的合作框架或合作机制中受益,对收益的预期可以避免各国出现不甘和不平衡心理。而传统的同盟体系,有时是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但也存在相当多的大国胁迫小国的情况,同盟内部存在不平等关系,不仅成本付出不平等,获得的收益也不平等。例如,在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中,美国为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提供安全保护,后者则成为美国的附庸。同盟内部的不平等关系导致大国经常担心受到小国的牵连,被卷入不必要的冲突中,而小国也时常担心被大国抛弃,成为某种利益交换的牺牲品。这些心理的出现都不利于同盟体系的持续运转。
(3)网状伙伴外交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的特点。网状伙伴外交的多元性特点意味着它必然要具有包容性,对外是开放的,并不封闭。如果一个国家有合作意愿,不必认同全部理念或所有方面,只需在某个领域满足一定的条件或者同相关国家就某个具体问题建立合作机制,就可以同各国进行合作,参与到网状伙伴外交中。这有助于在照顾多方利益的基础上扩大合作范围。而同盟体系的排他性特征,使得同盟外的国家很难参与合作,无论这一同盟体系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如果要扩大体系成员,那么就必须订立新的盟约,就像俾斯麦在德奥同盟基础上建立德奥意三国同盟时所作的那样。这种排他性特点虽然保证了同盟体系的稳定性和纯粹性,但也是导致同盟体系最终走向僵硬的重要原因。
而与同盟体系时常走向僵硬结局不同,网状伙伴外交具有鲜明的灵活性和弹性,它倡导结合具体问题建立具体合作机制,优化各项资源配置,使参与机制建设的国家能够从伙伴合作中切实获益,排除了传统同盟体系僵化的可能性。包容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使网状伙伴外交具有了较强的生命力,可以通过自身发展和灵活运行持续促进各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4)网状伙伴外交具有现实性和现时性的特点。联盟通常具有预警作用,因为国家建立同盟大多是针对可能的敌人采取的先发行动,但这很容易导致成本的浪费。因为某个国家或许根本不是敌人,又或许这个敌人没有发动进攻的意愿,又或者是能力上并不能构成真正威胁。例如,俾斯麦建立同盟体系主要是应对法国可能的复仇行动,但德国在19世纪末期最大的敌人或者说主要敌人实际上是俄国和英国,且法国已经明显衰落而不具有构成真正威胁的能力。因此,同盟体系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付出了额外的成本和代价。而网状伙伴外交并没有树立一个假想敌,它着眼于现实中确实存在的问题,意在通过现时和当下的合作与建设,促进彼此利益的实现。各国付出的成本被切实用于当前的实际需要,成本实现了物尽其用。
2.网状伙伴外交的不足
尽管网状伙伴外交具有相当多的优势,但也必须承认其所存在的不足。
(1)网状伙伴外交缺乏严格和明确的权利义务规定,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伙伴关系本身仅仅表明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水平,彼此不处于敌对状态,有开展合作和发展相互关系的意愿。且伙伴关系是分层次的,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到战略伙伴等,在不同定位的伙伴关系中,国家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具有不同的约定。因此,在伙伴关系网络基础上开展伙伴外交,在提供灵活性的同时,也附带了一定的脆弱性,很难对伙伴国的行为加以硬性约束,更多时候仅仅是凭借对方的良好意愿和自我约束。一旦国家间在某领域或某问题上存在摩擦,伙伴外交就可能面临难以行动的尴尬。
(2)网状伙伴外交的复杂性较强,对参与开展或意图构建这种外交模式的国家的外交智慧和外交技术构成挑战。灵活性和多元性的特点使网状伙伴外交呈现出复杂性:所有国家不能被一刀切地进行分类,需要独立认识和单独对待;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和合作机制类型的多样性,都意味着构建网状伙伴外交的过程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究竟同哪个国家或哪些国家在何种领域建立怎样的地区机制开展外交活动,需要国家认真分析各国的特点和不同的利益需要,通过协商协作开展伙伴外交,并确定具体的合作方式。这种复杂性也意味着变动性的存在,这会让没有参与构建的国家产生不确定性,无法弄清楚相关国家的真实意图,从而影响国际和地区体系的稳定。这些特点对国家的外交智慧和外交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网状伙伴外交是一个需要耐心和坚持的长期性工程。网状伙伴外交的持久性特点,意味着它不可能像同盟条约或同盟体系的建立那样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需要不断建设和持续开展才能看到成效。因此,构建和开展网状伙伴外交需要国家付出耐心和坚持,这是一项长期性工程。
三、网状伙伴外交与“一带一路”中的机制建设
自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以来,学界对“一带一路”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富有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在政策和实践层面,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也正在全面铺开。从网状伙伴外交的基本理念和优势特点来看,建设“一带一路”与开展网状伙伴外交具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
(一)网状伙伴外交契合“一带一路”的机制建设需要
“一带一路”倡议推出以来,得到了周边和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也正在同各国积极合作,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从当前的整体建设情况上看,中国主要在两个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方面,中国同有关国家达成共识,同意将各国国家发展的大战略进行对接。例如,中国已经同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国达成了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哈方的“光明之路”战略和蒙古的“草原之路”战略进行对接的共识。中俄两国在2015年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欧亚经济联盟开展对接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5/09/c_127780866.htm。另一方面,中国也已经同相关国家开展了具体的建设项目,如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开通渝新欧专列等加快贸易畅通和开展人文交流合作以促进民心相通等。对“一带一路”建设而言,上述两个方面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推动了“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但无论是项目成果的巩固还是战略对接的落实,实际上都需要更多中观层次的工作,这集中表现为“一带一路”的机制建设工作。
有相当多的观点认为,“一带一路”不应是一种规模宏大的合作机制,也不需要将一体化作为发展目标或用一个封闭性组织来框定所有合作。*陈玉荣、汤中超:《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第126~132页。但这并不意味着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不需要探索机制建设的相关问题,恰恰相反的是,“一带一路”在深入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机制建设,形成有助于“一带一路”建设开展的合作机制。
合作机制是战略合作和项目合作之间有机沟通与紧密结合的桥梁,大量合作项目取得的成果需要合作机制加以巩固和维护,高层达成的战略对接意向及由此开展的战略合作也需要由合作机制进行具体落实。建设“一带一路”需要的合作机制不应是大而全的,而应在形式、种类、涉及领域、成员国组成等方面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有的机制可以由众多国家参与,例如涵盖了诸多成员的亚信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机制,中国倡导并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吸引了众多的国家;而有的机制可能仅仅涉及两三个国家,例如中俄蒙三方元首会晤机制只有3个国家参与。合作机制应具有多种形态,例如,类似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合作机制已经是较为成熟的组织形态,而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等是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合作机制。在经济领域,召开经贸论坛、开通货运班列等都可以为建立自贸区或关税同盟等更深入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打下良好基础。在安全领域,开展军事交流、共同打击跨境犯罪、设立安全论坛等也都有助于合作机制的塑造与深化。多样性的合作机制为各国参与建设“一带一路”提供了多种选择,各国可以在不同领域以多种方式开展合作。不同机制对“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着不同作用,共同组成了“一带一路”的机制架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网状伙伴外交无论是概念内涵还是具体实践都能够契合“一带一路”的机制建设需要,其开展将积极助推“一带一路”建设。首先,网状伙伴外交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伙伴关系基础。网状伙伴外交的开展建立在中国同他国建立的伙伴关系基础上,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和提升将促进伙伴外交的开展。伙伴外交的持续进行又可以反向作用于伙伴关系,并成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基础,由此形成一个积极循环,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其次,网状伙伴外交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机制选择。网状伙伴外交通过巩固既有机制和建立新机制的方式推动各国开展合作,*顾炜:《中俄网状伙伴外交的概念内涵和实现路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5期,第137~ 138页。其灵活性的特点使各种机制能够有机结合,为各国提供了形式多样的合作备选菜单,每个国家可以选择自己最需要的领域、最易参与的合作机制和最适宜的方式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再次,网状伙伴外交有助于巩固地区和次地区形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网状伙伴外交建立在伙伴关系基础上,通过外交活动的开展和合作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密切了各国之间的联系,加深了国家间的理解,有助于减少矛盾和摩擦,促进地区形势的巩固,并由此为“一带一路”提供良好的建设基础和建设条件。
(二)“一带一路”建设推动网状伙伴外交的开展
在网状伙伴外交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建设“一带一路”也能够对网状伙伴外交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第一,建设“一带一路”为各国带来实际收益,将巩固和提升伙伴关系,夯实网状伙伴外交的开展基础。中国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同有关国家在多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无论是在对象国建设高铁还是增加两国教育机构的互访等,都可以为相关国家带来诸如增加就业、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发展经济和促进社会进步等实际收益。这些收益会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巩固和提升双边伙伴关系水平。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经同蒙古(2014年8月)、澳大利亚(2014年11月)、新西兰(2014年11月)、埃及(2014年12月)、沙特阿拉伯(2016年1月)、波兰(2016年6月)、塞尔维亚(2016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2016年6月)等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些国家都位于“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的重要合作对象。在双边伙伴关系定位提升的同时,各国也同中国就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项目合作的相关问题达成一致。而每个国家都在各种领域参与了许多不同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具有多重国际身份,中国通过与这些国家提高双边伙伴关系水平并加强合作,也就使这些国家更愿意推动本国所在的地区和国际机制同中国深化合作。例如,波兰和塞尔维亚都是中东欧国家,在中国同波、塞两国分别提升双边伙伴关系定位的同时,两国也都分别表达了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意愿。这种带动效应有助于网状伙伴外交的开展。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的项目成果可以作为合作机制的基础,促进旧有机制的巩固与发展,推动新合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一带一路”建设是由众多项目组成的,这些项目涉及领域不同、参与国家数目有别、规模各异,但它们具有共同的影响作用。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相关的参加国能够增加相互了解,积累起合作经验,项目带来的成果也能够让各国提升继续合作的意愿,而继续合作可以通过拓展合作领域或建立合作机制等方式进行。例如,在东南亚,“一带一路”倡议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带来了新的契机;*卢光盛、金珍:《“一带一路”框架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升级版》,《国际展望》2015年第5期,第67~81页。在欧洲,匈塞铁路项目的推进将有助于中国同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机制的深化发展;中俄蒙经济走廊既是中俄蒙三国达成的具体合作项目,同时为推动该项目的建设,中俄蒙三国还在近年逐渐形成了三国元首会晤机制。由此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一带一路”框架内各种合作项目的开花结果,相关地区和次地区合作机制将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这也将不断推动网状伙伴外交的开展。
四、结 论
无论是俾斯麦为德国构筑的同盟体系,还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的同盟体系,都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无助于国家利益的持续实现和良好外交环境的营造。而中国提出并开展的网状伙伴外交则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不仅有助于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也能够为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机制支撑。开展网状伙伴外交和建设“一带一路”都将为中国塑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但必须认识到,两者都是长期性和系统性的工程,需要中国付出更多的耐心和持久的努力。
顾炜,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