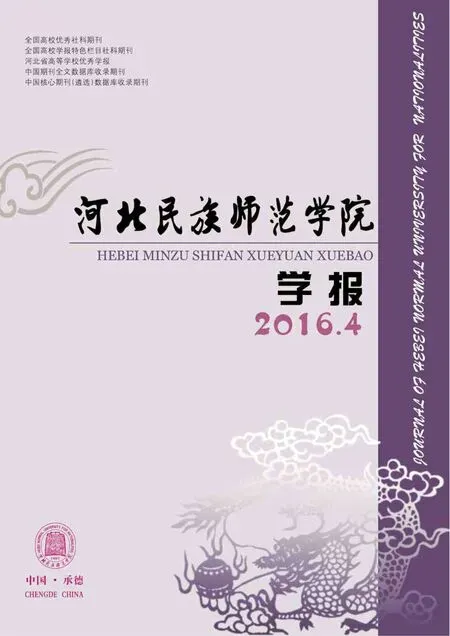语言游戏论及其译学价值分析
胡庭树
(淮阴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语言游戏论及其译学价值分析
胡庭树
(淮阴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语言游戏论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区别他前期哲学的重要标志。在语言游戏论中,维特根斯坦把语言视为生活形式的一部分,把语言的意义看作是语言的使用,将语言的使用(包括翻译活动)比喻为一种游戏,从而揭示出语言的复杂多样性、家族相似性以及遵守规则性等重要特征。然而,这些特征也同样体现于翻译的过程中,翻译不是隐藏其背后的意义实体的转换与对应,而是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与使用;翻译所体现的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相同的意义本质,而是二者之间相似的家族特征。
语言游戏论;译学价值;家族相似性;遵守规则
一、引言
分析哲学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中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导致了哲学的“语言转向”,这一转向也被称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从此分析哲学家对一切哲学问题的研究便归结为对语言的研究,因而分析哲学也被称为语言分析哲学。其中,作为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的维特根斯坦,既是实现当代哲学“语言转向”的第一人,也是完成这一转向的终结者。[1]264维特根斯坦前后发展了两种不同的哲学,前期以《逻辑哲学论》(1921)为代表,提出了关于命题和世界关系的“图像论”,探讨了弗雷格和罗素提出的逻辑分析问题,阐述了他自己在语言、逻辑以及语义学等方面的独特观点,对维也纳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期维特根斯坦转向对日常语言的研究,以《哲学研究》(1953)为代表,其中提出的“语言游戏论”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语言游戏论是对前期图像论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传统的意义指称论的批判。维氏强调在使用中把握语言的意义,并把语言的使用视为一种游戏,不同的语言游戏要遵守不同的语言规则,人们只能在游戏中感受它们之间的“家族相似性”,而不能去寻求语言背后一般的、本质的、不变的意义实体,因为世界万物是丰富多彩的,语言的使用也是千变万化的,根本没有适用于一切语言用法的共同的东西,因此,理想的人工语言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幻想。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将翻译活动也视为一种语言游戏。本文旨在通过对语言游戏论的释读来分析其对翻译学研究的启示与价值。
二、语言游戏论
语言游戏论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一个核心思想。维氏后期的意义理论其实就是意义的使用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语言游戏论也是意义使用论的形象说法。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探讨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提出的背景及其基本内涵。
(一)指称论的困境
指称论是传统意义理论中历史悠久、影响较大的一种理论。它的基本思想就是,名称或命题是通过指称外部世界中的事物或事实而具有意义的。换言之,一个名称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的对象,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的事实。这样,名称与对象,命题和事实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指称论在语言和实在的关系问题上建立了联系,但是没有将意义与指称区分开来,而且不能解释所有的语言现象,因而也招致了众多的批评和诘难。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的第一部分对语言的指称论进行了批判。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语词和对象之间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有些语词没有指称对象,而且语言除了指称功能还有许多其他功能;第二,有些语言看似发挥指称功能,其实不然,比如《哲学研究》中描写的建筑工和助手之间的语言交流便是很好的例证;第三,符号和命题之间的界线很难划清,有些符号既可以把它理解成语词,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语句(如独词句),这就要依语境而定,而且名称和对象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对应关系,指称常常具有不确定性,这一观点也类似于蒯因(W. V. Quine)所提出的“指称的不可测知性”,或者叫“本体论的相对性”;第四,指称论混淆了意义和意义的承担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词的意义未必就是它的承担者。[2]155-157后来弗雷格(G.Frege)对指称和意义进行了区分(如他的“晨星”和“暮星”的例子),明确指出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样,指称论的命运也就因为自身的缺陷而渐渐为其他的意义理论所取代。
(二)图像论的倒掉
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主要以图像论为代表,它描绘的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不是词汇组成的类聚物,而是由基本命题组成的。或者说,语言是命题的总和。世界是由事实组成的,但事实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而是存在于逻辑上的可能世界中。一个命题符号就是一个事实命题,命题和它所描述的事实之间具有共同的逻辑结构,命题是事实的逻辑图像。换言之,命题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是投影和被投影的关系。这样,语言便是世界的逻辑图像,通过分析语言最终能够揭示出世界的逻辑结构,这也是图像论所要表述的基本思想:语言和世界是一种对应和同构关系。
在图像论中,语言的使用严格遵守逻辑规则,因而语言的使用是唯一的、确定的,不存在任何歧义。前期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的基本单位是符号(或语词),而非命题(或句子),一个符号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的对象,而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它所描画的事实。可见,指称论和图像论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指称论是图像论的基础,图像论是指称论的发展,二者描画的都是语言和世界的一一对应关系。经过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猛烈攻击,指称论坍塌了,图像论也就随之倒掉了。
(三)游戏论的建立
早期的分析哲学家(包括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澄清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无论这种表达式是属于逻辑的语言还是属于日常的语言。但是,他们认为日常语言是存在种种缺陷的语言,哲学问题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人们误用日常语言所致。所以,应该建立一种理想的人工语言(或逻辑语言)来取代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这样便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哲学问题。然而,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思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否定存在一切命题所共有的逻辑形式,认为逻辑本身并不能完全解决语言的意义问题,而日常语言本身完全可以清楚地表达思想,主张从语言的实际使用出发来研究日常语言,强调对日常语言表达式的语法结构和使用规则的研究,等等。陈嘉映教授总结得好,“在图像理论里,语言从根本上是一种反映,而语言游戏则说,语言首先是一种活动,是和其他行为举止编织在一起的一种活动。”[3]8
“语言游戏”这个概念最初是在《蓝皮书》里提出来的,指的是“原始语言”或“语言的原始形式”。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也大量描述了语言游戏:下命令,服从命令;描述一个对象的外观,或给出对它的度量;报告一个事件;编故事,讲故事;演戏,猜谜;唱一段歌;解应用算术题;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4]17-18但是,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给语言游戏下过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对语言的本质进行界定过。在他看来,语言游戏本身无法定义,只能从不同的游戏中感悟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我们一旦给语言游戏下定义,就是人为地规定了被定义者的本质,而这正是两千年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错误所在,即对现象背后的本质、共相、一般的追求,从而使哲学家患上“哲学疾病”,陷入旷日持久的无谓的争论。事实上,世界万物是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是五颜六色的,语言的使用也是灵活多变的,早期分析哲学家所追求的那种理想的人工语言是不切实际的。人们现实生活中使用的自然语言是鲜活的、动态的、多变的,它与世界也并非是一种一一对应的静态关系,因此,语言也并非是世界的投影。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完全发展了与前期相对立的语言哲学观,在彻底批判图像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后期的语言游戏论,这一理论的基点是反本质主义的,即从根本上取消是否存在本质这类问题,旨在使哲学家从长期无法摆脱的困境中走出来。
三、译学价值分析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通过对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和意义观念论的批判,提出了意义的使用论,并把语言的使用比喻为一种游戏,即“语言游戏”。后期维特根斯坦“意义即使用”的理论也是语言游戏论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语言的功能并非仅仅在于指称或描述事物,语言只有在实际的使用中,才能赋予表达式以意义和生命;如果语言的功能仅仅停留在指称或描述事物,那么翻译固然会变得简单,但是人类的生活将会索然无味。维特根斯坦借助语言与游戏的对比,进而揭示出语言使用的多样性、相似性、规则性等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对于翻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价值。
(一)形式多样
在图像论中,语言的使用是按照严密的逻辑规则进行的,因而语言的意义是确定的、唯一的;而在语言游戏论中,语言的使用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语言的意义依语境而定,因而语言的意义是易变的、丰富的。将语言使用比喻成语言游戏非常形象、生动、贴切,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决定了语言使用的多样性,而语言游戏本身的内涵又超越了这一比喻意义。
语言游戏是多种多样的,把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活动也是形式多样的。传统的意义理论认为一个语句具有某种意义,另外一个语句如果与它具有相同的意义就是该语句的翻译。蒯因认为这是一种“语言的博物馆神话”,其中展品是意义,语词是标签,转换语言就是更换标签。[5]410-411根据语言的博物馆神话,语言中的语词和语句有其确定的意义。而蒯因通过彻底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的思想实验所要驳斥的正是语言的博物馆神话,思想实验的结果表明:翻译具有不确定性,即意义具有不确定性。这一论题不是说没有可以接受的翻译,更不是说翻译是不可能的,而是说可以存在多种多样的翻译。传统的翻译观把文本看作是封闭、自足的系统,意义是内在于系统并为系统所决定的,因而把追求确定的意义和对等的形式看作是翻译的最高目标。事实上,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翻译观,因为翻译是发生在“复数语言”之间的行为,如果世界上只存在唯一的“单数语言”(即上帝的语言),那么翻译就是不必要的,复数语言决定了翻译不可能是复制,而只能是以“差异”为特征的异化活动。例如,人类对于《圣经》的翻译可谓是历史悠久、工程浩大,但迄今为止,没有哪一部译本能够准确无误地传递神的话语,或者被称为是“最权威”的译本。即使是翻译成同一种语言的不同译本,也是各有千秋、相得益彰。翻译的不确定性或不唯一性决定了翻译的多样性以及重译的必要性。每一个译本都在不同程度上接近原文,但永远不能到达原文。换言之,原文/译文之间存在永远难以逾越的“/”。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堪称是翻译界的一场“哥白尼式革命”,从此“忠实”与“对等”已不再是衡量翻译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翻译已经不再局限于语言结构与形式的对等,而是源语和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对应。在德里达(J.Derrida)看来,翻译就是延异和播撒,文本没有终极意义,任何意义都是不确定的,寻求与原文“对等”的译文永远是一种奢想。斯坦纳(G.Steiner)则认为:“理解就是翻译,无论是同一语言之间还是不同语言之间,人的交往就等于翻译。”[6]490这种“理解即翻译”或“交往即翻译”的观点,赋予翻译以更宽泛的意义。可见,正如语言游戏一样,翻译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变动不居的,不存在唯一的翻译标准,更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译本。
(二)家族相似
追求精确性和唯一性以及现象背后永恒不变的“本质”一直是两千年来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彻底放弃了关于世界本质、语言本质的观点,用“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代之以“本质”的概念。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种游戏,也就存在着无数种语言的用法,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全体成员共同的东西,而只是有某种相似之处,有某种亲缘关系,或者说是一种错综复杂的、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网络。[4]47-48正如他本人所言,“我没有提出某种对于所有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东西为共同的东西,我说的是,这些现象中没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能够使我把同一个词用于全体,——但这些现象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彼此关联。而正是由于这种或这些关系,我们才把它们全称之为‘语言’。”[4]46因此,不同的语言也就组成了一个相似的大家族,它们之间既存在着某些共性,也存在着种种差异。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性的概念从根本上否定了本质主义语言观。在维氏看来,根本不存在“意义”这样确定的东西,也不存在任何抽象的,具有独立意义的语词和语句,一个语词或句子的意义就是它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游戏视为我们生活形式的一部分,语言游戏的家族相似性源于我们生活形式的相似性,反过来,我们的生活形式是我们进行游戏和使用语言的基础。正如他没有给出过语言游戏的定义一样,对于生活形式也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只是在《哲学研究》中多次提到这一概念。那么两者的关系应该如何表述呢?一般认为,“‘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即两者在涵盖的内容上有所不同——‘生活形式’包含了‘语言游戏’,又不限于‘语言游戏’,‘语言游戏’是人们生活形式的一部分,有时甚或是最重要的部分。”[7]20如果将两者割裂开来,语言也就失去了交流的意义,维特根斯坦因而纠正和批判了把语言从日常用法中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的错误。维氏把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翻译行为也视为语言游戏的一种,因而翻译行为也是我们生活形式的一部分。世界上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形成不同的生活形式,而语言又是人们生活形式的反映。我们之所以不理解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就是因为我们不理解说这种陌生语言的人的生活形式,但是不同民族的生活形式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因而不同的语言也应具有不同程度的可译性,这也是我们可以借助翻译手段来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基础,或者说“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是我们借以解释陌生语言的一个参照系”。[8]34既然从理论上来讲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似,那么原文和译文之间、不同语言的译文与译文之间、同一语言的不同译文之间也就存在着某种相似性,相似性程度的大小取决于目标语和源语之间的亲缘关系,当然在翻译实践中影响翻译的因素很多,这里仅是就家族相似性的角度来谈原文与译文,以及译文与译文之间的相似关系的。可见,生活形式或语言游戏的相似性决定人类翻译的可能性以及原文与译文、译文与译文之间的家族相似性。
(三)遵守规则
语言游戏必须遵守规则,没有规则,语言符号就失去了意义,语言游戏也就无法进行。因此,遵守规则也就成了语言游戏论的核心内容。规则具有约定性和相对稳定性,但也具有可变性。我们常常是“一边玩,一边制定规则”,“一边玩,一边改变规则”。一旦规则发生了改变,一个语词的意义或用法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但是,维特根斯坦指出,遵守规则存在这样的悖论:“没有什么行为方式能够由一条规则来决定,因为每一种行为方式都可以被搞得符合规则。”[4]121也就是说,人们的行为无法用规则来解释,但是人们的行为又必须符合规则。因此,我们要把遵守规则看成是一种“盲目的”的过程,看成是一种习惯。规则不是我们事先得到的东西,而是在游戏中向我们展现出来的东西,因为我们只有在游戏中才能感受到规则的存在,才能谈得上遵守规则。但是,在语言游戏与遵守规则之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我们是否遵守规则,只能在语言游戏中进行判断,我们如何遵守规则,仍然要以语言游戏为依归。
正如在语言游戏中我们总是习惯性地遵守规则一样,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游戏也有自身的规则,翻译中我们总是下意识地遵守这些规则。比如,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翻译要求,我们在翻译中只有遵守不同文体的各自规则才能将翻译进行下去,倘若将散文翻译成了戏剧,或者将小说翻译成为诗歌,这就违背了翻译的规则,因而也就很难达到正确传递信息和交流文化的目的。以色列翻译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吉迪恩·图里(G.Toury)在上个世纪提出了“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这个概念。所谓规范,“就是在特定文化和文本系统中,被优先而且反复采用的翻译策略。图里认为,在翻译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和以及翻译产品的各个层次,有关规范都在起作用。”[9]272这里,我们可以把翻译中的规范理解成语言游戏中的规则。这样,为了使翻译顺利进行,译者在翻译的每一个阶段总是要习惯性地遵守这些规范或规则。但是,即使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遵守了这些规则,也还是会出现“翻译悖论”的情况。具言之,我在翻译的过程中总是要面对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形式与内容、美丽与忠实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矛盾,这些矛盾永远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因为语言具有模糊性和多变性,对于不同的语义变量,我们很难对其作出精确的分析,这些话题争论了几千年结果仍然莫衷一是。在翻译实践中,如何恰当地处理上述几对二项式的关系,我们无法给出量的规定,而且在翻译实践中又无法回避。总之,在翻译中,我们总是习惯性地遵守规则,即使我们之前不知道这些规则。我们也并不是在学会了这些规则以后才开始翻译的,正如我们并不是在学会了游泳的规则以后才下水游泳一样,而是一边游泳,一边学习规则,但是在游泳的时候,一旦违背了规则,我们将会沉到水底,翻译的道理也是如此。
四、结 语
维特根斯坦通过对传统的指称论和观念论的反拨,提出了他的意义理论,即意义的使用论。从某种程度上讲,语言游戏论是意义使用论的形象说法,即把语言的使用比喻为语言的游戏,二者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语言游戏论不仅在哲学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给翻译学研究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可以说,翻译也是一种语言游戏,翻译的策略和标准是动态的、多变的,翻译现象的背后不存在确定不变的意义实体,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语言本质;翻译活动作为语言游戏的一种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生活形式的相似性决定了翻译的可能性,同时也决定了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家族相似性;语言游戏和遵守规则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样,翻译活动也是在遵守规则中进行的,如果违背规则,翻译活动也将无法进行。
[1]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单继刚.翻译的哲学方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陈维杭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陈波,韩林合主编.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6]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7]杨宁芳.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探析[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8-21.
[8]涂纪亮.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9]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Analysis of Language-Game Theory and its Value on Translation Studies
HU Ting-shu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an, Jiangsu 223001,China)
Language-game theory is a core content of Wittgenstein's later philosophy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ark which is distinct from his early philosophy. In the language-game theory, Wittgenstein regards language as one part of life and considers the meaning of language as a use of language. In addition, he compares the use of language (including translation action) to a game, thus revealing language's properties,such as variety, complexity, family resemblance and obeying-rule, which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is not the shift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e entity of meaning hidden behind languages, but the communication and use of different languages. Actually, the relation between source text and target text is not the same meaning as essence, but the “family resemblance” between them.
language-game theory; translation studies value; family resemblance; obeying-rule
B151; H059
A
2095-3763(2016)04-0120-05
2016-05-20
胡庭树(1977- ),男,江苏淮安人,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翻译与语言分析哲学。
2015年度淮阴工学院人文社科基金“唐诗形式英译的哲学语义学研究”(15HGS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