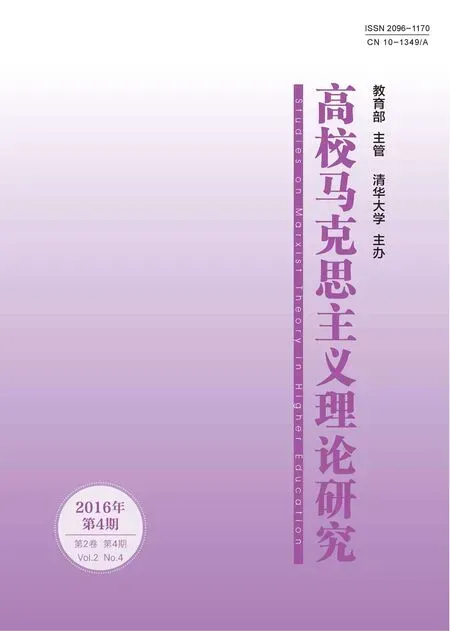1949—195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辨析
王 然
1949—195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辨析
王 然
编者按:自2002年以来,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举办的博士生学术论坛已先后举办17届,对于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的学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反响。第17届四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学术论坛于2016年6月在北京大学举行。为了进一步激发博士生的学术研究热情,本刊特选取在此次论坛上荣获一等奖的3篇博士生论文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与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设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职权差异较大,理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含义应立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同时,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可知,代行职权的范围包括立法权、选举权和决定权,代行职权的时间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开幕直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由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身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因而其不可能成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此时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仍能通过对中央人民政府具有约束力的决议。
政协全体会议;全国人大;中央人民政府;共同纲领;五四宪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选的条件还不具备等原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以下简称“政协全体会议”)被赋予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的职权,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以下简称《政协组织法》)等法律,并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有关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有三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首先,在政协全体会议职权与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五四宪法”)中的全国人大职权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是否仍然可以认为前者代行了后者职权?其次,如果前者确实代行了后者职权,代行职权的内容和时间如何确定?第三,如果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政协全体会议是否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种特殊的政治设计,严格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准确把握代行职权的含义,对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特点及演变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是进一步探究中共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团结民主党派、巩固自身执政地位的重要前提。本文拟采取规范分析的方法①这里的规范分析指从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出发探讨问题,根据法律规定确定全国人大、政协全体会议、中央人民政府的地位、性质、职权、作用,而非考察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相应机构实际发挥的作用。由于制度规定对现实政治运行的规制作用,从规范角度进行分析是理解现实历史进程的必要前提。,从这三个问题入手,对“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这一命题进行探讨。
一、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背景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政协全体会议根据《共同纲领》等文件的授权代行全国人大职权。这一独特制度设计是新中国建国程序调整的产物。
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即将到来,新中国的筹建工作逐渐被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1948年4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的《“五一”劳动节口号》[2][3]145,“其中经毛泽东亲自改写的第五条,正式向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由此揭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4]。这一口号表明,当时中共对新中国建国程序的设想是先召集政协会议,经由政协会议讨论并召集人大,然后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10月8日,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民主人士已到达哈尔滨,中共中央将《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发给在东北的高岗、李富春,要求他们就该文件中所提问题向民主人士征求意见。该文件第4条指出:“新政协所应讨论和实现的有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5]212对于后一问题则要求:“先行交换意见,以便提交新政协筹备会作初步讨论。”[5]212这份文件首次使用“共同纲领”一词[6],并且不再提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同时提出与民主人士就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方式交换意见。10月21日,高岗、李富春向中央汇报:“关于如何成立中央政府的问题。谭、王主张新政协后,限定时间召集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再产生临时中央政府。章、蔡主张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对内对外均需要,待全国统一后,再成立正式的。”[5]217②“谭”指谭平山,“王”指王绍鏊,“章”指章伯钧,“蔡”指蔡廷锴。这两份文件传达出三点重要信息。第一,中共此时已经考虑改变建国程序,暂不召开全国人大,而由政协会议直接成立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并就此与民主人士交换意见。第二,民主人士就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方式存在分歧,谭平山、王绍鏊主张先召开“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再由其产生临时中央政府;章伯钧、蔡廷锴则主张由新政协直接产生临时中央政府,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第三,章伯钧等民主人士认为,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要求尽早成立中央政府,这是促使建国程序转变的重要原因。11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高岗、李富春指出:“依据目前的形势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7]815明确表示了国内形势的发展促使中共中央意图改变建国程序,但此时中共仍准备就此问题与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11月25日,中共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进行协商时,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关于如何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即民主联合政府(即由新政协产生或由人民代表会议产生)问题及宪法草案问题,先行交换意见,留待筹备会讨论解决。”[3]214此时,中共虽已倾向于由人民政协直接产生临时中央政府,但仍在与民主人士交换意见,双方尚未达成一致。
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指出:“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8]234表明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在1949年召开政协会议,并由政协直接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变更了建国程序。3月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9]210-211由此批准了对建国程序的变更。3月25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10],“邀请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章伯钧等谈过几次,商讨新政协如何召开和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谈了开会的地点,参加的人数,会议的任务,以及其它一些问题”[11]109。经过不断协商,中共与民主人士就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方式达成了共识。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以下简称“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244这次会议通过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也将“提出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的中心任务之一,同时不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列为新政协的任务。[12]169至此,中共与民主党派均赞同由政协全体会议直接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不再召开全国代表会议。9月21日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三大文件,并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完成了由人民政协直接产生中央人民政府的建国程序,并规定在全国人大召开前由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
1948年到1949年,国内形势发展迅速,特别是解放战争的进程突飞猛进,使得中央对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时间的预计由5年缩短为1年。①1949年11月14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指出:“这样(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笔者注),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61.革命胜利的提前到来需要尽快成立中央政府,以应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局势。这大大缩短了中共筹建中央政府的时间,而召开全国人大又必须进行全民自下而上的普选,需要较长的准备时间。②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正式开始召开全国人大的准备工作。从这时起,直到1954年9月15日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共经历了1年零9个月的时间。参见: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308-342.考虑到全国尚未解放及战争条件下国内局势不稳等因素,要求在1949年召开全国人大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共改变了建国程序,暂不召开全国人大,而由政协会议直接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人大召开前代行其职权。①关于中共建国程序的转变及其原因可参见:[1]张皓.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机与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J].中共党史研究,2009(10):47-57;[2]杨火林.新中国建国程序的调整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过渡性特点[J].中共党史研究,2004(6):20-26;[3]李格.新中国成立前中央人民政府筹备述略[J].中共党史研究,1996(6):36-42;[4]李格.一届政协筹备问题的若干考察[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4):71-76.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政协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12]268这表明,人民政协所具有的“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使得它能够获得人民的拥护,从而可以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应当注意的是,只有全国人大才由人民普选产生,具有最充分的代表性,政协会议只能代行全国人大职权,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选举中央人民政府等人大职权。可见,国内局势对尽快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需求与短期内召开全国人大的困难产生了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必要性,而人民政协本身的广泛代表性又提供了代行职权的可能性。在这两方面条件下,中共与民主人士广泛交换意见,最终就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方式达成一致,决定由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在此基础上直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待条件成熟时再召开全国人大。
二、《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中全国人大职权的差异
根据“五四宪法”,全国人大拥有修宪权、立法权、任免权、决定权等多项重大权力,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13]526-527在此之前, 1949年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却将包括立法权、任免权、缔约权等重大权力在内的十项职权赋予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9]751-752这一规定似乎表明,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以前,由中央人民政府而非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从而与学界的普遍看法不一致。②学界通常认为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以前,由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例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认为:“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参见: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266.“到这时为止(1952年底——笔者注),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共同纲领》一直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参见: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308.“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7-8.“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尚不可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1949—1956)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27.
“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观点源于第一届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其第十三条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9]761由于《共同纲领》的临时宪法地位,这一规定自然是确定政协全体会议的性质和地位的重要依据。要正确理解这一规定,首先需要理清全国人大拥有哪些职权。
由《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中央国家机关的机构设置和权力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两份文件均设立了全国人大这一政权机关,然而赋予它的职权却有着重大不同。“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拥有“修改宪法”“制定法律”“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决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13]526-527等十四项职权,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构,并赋予其“解释法律”“制定法令”“决定同外国缔结条约的批准或废除”[13]528-529等十九项权力。可见,根据“五四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拥有立法、任免、决定等多项职权,是名副其实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政协组织法》构建的权力分配体系,并未明确列举全国人大的职权,却赋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广泛的职权。《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拥有“制定并解释国家的法律,颁布法令,并监督其执行”“批准或废除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和协定”“批准或修改国家的预算和决算”[9]751-752等十项权力,同时负责“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751-752。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职权基本涵盖了“五四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①由对比可知,“五四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职权未被包含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职权中的主要有四项,即修宪权、国家主席及副主席的选举权、国家主席等公职人员的罢免权和一些事项的决定权。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非普选产生,不具备与全国人大相同的代表性,加之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后的政体变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不可能拥有这些职权。,而由其组织的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又分别负责国家的政务、军事、审判、检察工作,这使得中央人民政府成为“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机关。与此同时,《共同纲领》仍然设立了全国人大,其第十二条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9]760-761。而《共同纲领》中有关全国人大职权的表述仅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②原文为“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61.即所列职权为政协全体会议代人大行使,故也可认为所列职权为人大所拥有。“人民政府委员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作报告”[9]760-761三段话。可见,由于中央人民政府是“议行合一”的政权机关,使得《共同纲领》不可能像“五四宪法”那样赋予全国人大广泛职权,其所拥有的职权只能通过《政协组织法》对于政协全体会议代行人大职权的规定加以确定。
在“五四宪法”中,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拥有包括立法权在内的广泛职权。而在《共同纲领》中,由于中央人民政府是“议行合一”的政权机关,拥有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等职权,全国人大仅被赋予了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等职权。在理解《共同纲领》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一规定时,必须注意到全国人大职权的这一转变,立足《共同纲领》对于全国人大职权的规定来考察政协全体会议是否代行全国人大职权,不能简单地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拥有“五四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职权,就认为是中央人民政府而非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
三、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范围和时间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是政协全体会议,而非政协的其他组织机构。根据《政协组织法》,政协会议分为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三个层次。[9]745-749其中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的名单由新政协筹备会确定,共六百六十二人[12]309,政协全国委员会由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由全国委员会选举[9]748。《共同纲领》《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均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大召开以前,由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9]747,750,761,政协的其他组织机构不具备这一职权。
对于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有观点认为,“(政协全体会议——笔者补充)在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后,就将国家最高权力移交给了后者”[1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虽然可以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其本身并非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选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后,即不再行使这一职权”[15],“在全国人大召开前,由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在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后,即将国家最高权力移交给后者”[16]。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仅限于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完成这两项职权后,即将国家最高权力移交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且不再代行全国人大职权。
为了从规范角度确定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内容和时间,应当基于《共同纲领》《政协组织法》等法律,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进行考察。《共同纲领》第十三条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9]761有观点据此认为政协全体会议代行人大职权是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17-18]。显然,这一判断的依据并不充分。从字面上看,用逗号隔开的内容之间难以断定有包含关系,故不能认为代行人大职权的内容就指后续三项内容。同时,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实际代行的职能已经超出了范围,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8]343。可见,《共同纲领》中的这段论述并未穷举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内容,以此来断定其范围是不可取的。
实际上,《政协组织法》对政协全体会议代行人大职权的范围有明确的表述,其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职权如下:……三、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甲、制定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乙、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丙、就有关全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或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决议案。”[9]747谭平山在《关于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报告》中将这三项权力概括为“立法权”(制定或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权”(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决议权”。[12]309
就立法权而言,政协全体会议不仅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而且还可以修改法律,这表明在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后,政协全体会议仍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否则就与其可以修改法律的规定不符。就选举权而言,政协全体会议赋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不同于有些观点认为的“国家权力”或“国家最高权力”[14-16],前者比后者更为具体。政协全体会议这一权力的行使仅意味着赋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具体的职权,并非概括性的“国家最高权力”。同时由于政协全体会议本身并不拥有这些职权,故不能理解为这些职权是政协全体会议“移交”给中央政府委员会的,更不能据此认为权力的“移交”导致政协全体会议不再代行国家最高权力。此外,政协全体会议除了上述两项权力还拥有“提出决议权”,更表明在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后其仍然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否则就无法对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决议。这三项权力均表明,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不仅限于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与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且在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后仍代行全国人大职权。
除此之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许多讲话以及中央文件也都涉及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时间。例如,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代表们作报告时说:“把普选由个别地方逐渐推广到全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才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9]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必须依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及时地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替现在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形式。”[20]可见,当时普遍认为,直到全国人大召开,政协全体会议始终代行全国人大职权。
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后没有再召开过政协全体会议,仅有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行了全国人大职能。然而不行使权力不等于不拥有权力,同时,以后续发生的历史事实来理解《共同纲领》等法律中对政协全体会议职能的规定也是不可取的。所以,虽然仅有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实际行使了全国人大职权,但仍然不能否认在法律规定上,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直至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
综上,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是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而非政协的其他组织机构。代行职权的内容包括立法权、选举权和提出决议权,而不限于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代行职权的时间为从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召开到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而非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后即不再代行。虽然历史上只有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实际行使了全国人大职权,但不能据此否定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在规范上始终代行全国人大职权。
四、政协全体会议并非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有观点认为,1949年9月,既然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么政协就应当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7]760将全国人大与中央人民政府规定为国家最高政权机关,而未赋予政协如此地位。其实,《政协组织法》对政协性质有明确表述,其第一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中国人民政协)为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7]745这表明,政协的性质仅仅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而不是国家机关。从两份文件的字面规定来看,只有全国人大和中央人民政府是国家最高政权机关,而政协仅仅是统一战线组织。
毫无疑问,由于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使其具有了统一战线组织和国家机关的二重性质①关于政协因其全体会议而具有的特殊性质,董必武曾论述道:“人民政协的职权,概括言之,可说是极大而且很特殊。说它的职权极大,因为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有等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表现在它可以制定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共同遵守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这一纲领有宪法的性质;它可以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它可以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说它特殊,因为它的全体会议在选出全国委员会后,它和国家政权机构就无直接关系。全国委员会是革命统一战线组织,不是国家政权的最高组织。它还要保证执行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决议及其自身的决议,这是中国革命条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的形式。”这段论述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政协所具有的双重性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202.,但并不能由此得出其是国家最高政权机关的结论。对此,董必武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起草提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发言中指出:“政协非人民代表会,不在国家体制中,其性质与地位,与新民主国家的祖国阵线等相同。政府在前台,它在幕后,是个不出名的参谋部。由它协定的东西,对政府有约束性,如像政府要按照共同纲领去施政一样,但最高政权机关不是政协,在目前是人民政府委员会,将来是人民代表会。”[21]可见,董必武认为政协本身不是国家机关,不在国家体制中,尽管在普选产生的全国人大未召开时它可代行全国人大职权,作出对中央人民政府有约束力的决议,但其本身并不能因此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此外,周恩来曾表示,“人民的机关包括两个:代表会和政府”[18],“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11]317。《共同纲领》也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8]760这均表明,仅有全国人大和人民政府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政协不是国家机关,不能因为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能就将其认定为最高国家政权机关。
在全国人大召开以前,中央人民政府是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8]760如前所述,虽然政协全体会议能够代行全国人大职权,但其本身并非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的召开并不等于人大的召开。所以,根据此条规定,直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中央人民政府一直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对此,董必武在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中说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虽然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出之后,后者即为行使全国最高政权的机关。”[22]周恩来也曾明确指出:“人民代表大会现在还没有开,只是有政治协商会议,由政治协商会议代行职权,所以它的全体会议开完了它就不存在了,只成立全国委员会,但是全国委员会不能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是由它选举出的中央人民政府行使这个政府的职权,它是最高机关。”[21]这表明,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看来,虽然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并且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但是后者一旦产生并被赋予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后,即成为最高国家政权机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央人民政府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但由于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其仍然可以通过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
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政协全体会议虽然代行全国人大职权,但政协本身并非国家机关,也就不可能成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同时,政协全体会议虽然代行全国人大职权,但政协不等于全国人大,政协全体会议的召开不等于全国人大的召开。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前,中央人民政府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尽管如此,由于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其仍然能够通过对中央人民政府具有约束力的决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1949—1956)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27.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06.
[3]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事暨资料选编[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4]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52.
[5]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6] 李格.新中国成立前中央人民政府筹备述略[J].中共党史研究,1996(6):34-40.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8] 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971.
[11] 石树光.迎来曙光的盛会——新政治协商会议亲历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12] 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上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65)(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4] 李格.关于1949—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的若干问题[J].党的文献,1996(4):77-82.
[15] 秦立海.1949—1954年第一届人民政协探析[J].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3(4):45-49.
[16] 史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基本特点[EB/ OL].(2009-08-19)[2016-09-23].http://www. hprc.org.cn/wxzl/tbtj/lctj/dandaizhg_1/.
[17] 李格.1949—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机构设置及其变化(上)[J].党的文献,2001(5):85-89.
[18] 李格.人民政协在全国人大召开前后组织和职能的变化[J].中共党史研究,2009(9):25-30.
[19]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7.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65)(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6.
[21] 马永顺.澄清对第一届人民政协代行人大职权的一些误解[J].党的文献,1992(6):89-90,14.
[22] 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50.
(编辑:李蕉)
王然,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