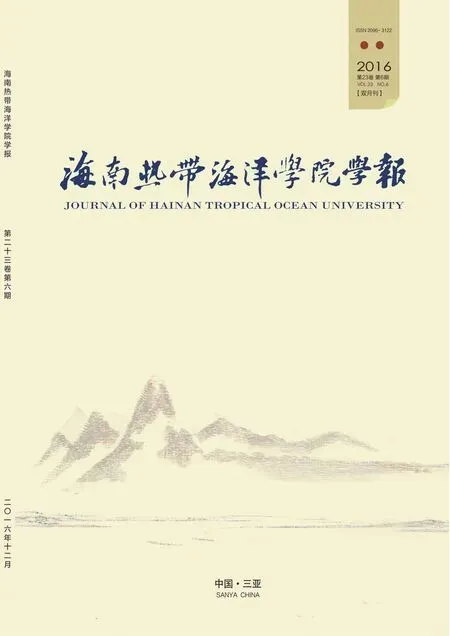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认同和游移
——论路遥对“新人”的塑造
刘立灿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口 571158)
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认同和游移
——论路遥对“新人”的塑造
刘立灿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口 571158)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社会环境中,路遥创作出高加林、孙少平等新的农村青年形象。因为接受了现代教育,他们的视野得到开阔,感到了命运的不公平并投入到改变命运的行动之中,但最终又回到出发的地方。路遥真诚地关切他们的遭际,期待着能够铲平城乡之间的沟堑,实现城乡两个世界的沟通。在艺术表达过程中,这一期待寄托在了社会与国家层面,“新人”本身则专注于自我的道德完善和对乡土的热忱。觉醒的个人尽管在与命运挣扎的过程中浮现了不顾一切的热情和自我苛求,但他们重新回到对时代的失语状态之中。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人”的塑造反映了路遥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意游移和无意识中的认同。
路遥;文学形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认同;游移
作为“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形象,梁生宝的命运是抛开有了进城心思的恋人改霞,转而全心投入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当中。而到了当下,方方笔下的涂自强成为农村青年的一个典型,他没有丝毫野心,一生一刻都没有松懈,却什么也都没有得到,是个十足的“落败者”。路遥小说中的主人公则是夹在这两类形象之间的“新人”,没有为了集体建设献身的豪情,但有着实现自己人生追求的野心,裹挟了孤独与骚动的时代气息。路遥对“新人”的塑造寄托了他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期待和反思。他有着借助文学关怀普通人的艺术构想,尽管这种构想只是一个轮廓,也足以报偿他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下进行“突围”的可贵努力。在进行“突围”过程中,他无意中仍受这一规范的潜在影响,这是一种无可奈何。
一、恰合时宜的“突围”
路遥是一个稳稳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时代鼓点上的作家,他的艺术创作成熟期在“天时、地利、人和”有利条件下到来。生长在城乡交叉地带的他,在自己努力进城和尽力活动帮家人进城的过程中,刻骨铭心地体验到了农村知识青年的真实命运。这些体验为他唤回“真实”提供了心理动机和真实细节。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环境的松动,书写“真实”有了充足的可能性。这些有利条件成就了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路遥。
路遥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青年命运的呈现及延伸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真实面貌,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现实主义一度在我国文学创作中占据权威地位,建国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犹是如此。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定义本身就存在着复杂的纠缠,在“写真实”原则艺术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政治倾向性之间难以找到平衡点。我国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接受之初就更偏重政治性这一方面,“可以说是一种更重视政治性或文学的政治功能的姿态‘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1]90。从1943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尽管期间偶有松动和讨论,但整体上对文学的政治教育功能的突出逐步强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性原则在中国找到了一个新的契合点,那就是对艺术的教育性、政治倾向性和阶级性的重新提出。”[1]2171943年以来,“文学事业是人民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应当为政治服务和为劳动人民服务,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事”[2]。 在政治标准第一的艺术规范下,社会主义社会是即将到来的现实图景。文学创作无法有效表现这一图景,因为作家对客观真实把握得不准确。因此,作家即使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发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表达。知识分子需要进行思想改造,把自己融入到阶级伦理之中,作为齿轮和螺丝钉发挥社会主义社会图景建设者的作用。浩然的《艳阳天》在自然灾害的惨烈背景下创作出萧长春这一工农英雄形象就是一个脱离“写真实”原则的例子。
随着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践的失败,改革开放开启了新的社会运作方式,中国融进了全球视野之中,面对更多的矛盾冲突。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很难再有一个权威性的规范。对现实主义作家来说,“文革”的结束为他们提供了“写真实”的良好契机,“在遵循文艺必须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这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每一个作家或艺术家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来从事创作,这是作家、艺术家的自由。”[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对松动的政治文化环境给了路遥书写自己真实人生经历、真实反映农村知识青年命运的契机。这个契机成就了路遥,把他从《惊心动魄的一幕》表现“文革”中英雄形象和《姐姐》《风雪腊梅》表现城市对乡村青年引诱和伤害主题的创作中突出出来。陈忠实认为《人生》的出现是很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他说:“《人生》一发表,我就感觉到了什么是表层的艺术,什么是深层的艺术,在这一点上我感觉路遥《人生》上的突破,不是路遥个人的突破,而是文学回归文学的本身,摆脱强加给文学要承载而承载不了的东西。”*转引自张艳茜《路遥与〈人生〉》,载《红豆》,2013年第2期。路遥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贡献了自己作为严肃作家的力量。
路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规范的“突围”集中表现在他对“写真实”原则的召回。这种召回首先通过他对“新人”真实命运的呈现得以完成。路遥把自己的视角放在自己最熟悉的城乡交叉地带,在交叉地带徘徊的“新人”高加林、孙少平是标准的农村知识青年。知识作为一种资本性的概念,带来了高加林个体意识的觉醒,使他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期待。知识资本的拥有衬托出“新人”们其他资本占有的匮乏。不仅如此,“新人”们首先必须应对社会资本的流失,应对不讲理也不要脸面的高明楼的盘剥。民办教师是高加林享有文化资本的底线,但这一底线在乡土人情秩序下的沦陷带给高加林深刻的孤立感。温柔美丽的巧珍对他痴情的爱更加深了他的孤独感,巧珍就是他在乡村世界里最美的收获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并且,巧珍将来除过是个优秀的农村家庭妇女,再也没什么发展了。城里姑娘黄亚萍带给他的才是对自己占有资本的有效确认,更是对自己个人觉醒之后需求的确认。但这种确认无法得到完成,最终高加林没有留在城市。知识这一资本性资源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路遥最痛心的地方。“大量有文化的人将限制在土地上,这是不平衡中的最大不平衡。”[4]高加林不会留在城市,还可以归结为他不光明的进城方式、始乱终弃的负心人“恶行”。身上没有任何负面因素的孙少平,最后也留在煤矿,和孤儿寡母作伴,“新人”的命运确实令人惋惜。孙少平身上拥有的高加林那样孤独、无助的气质已经得到了缓解,这个缓解证明了依靠知识这一资本进行“抗争”的无望;这个缓解部分来自于田晓霞的意外死亡,更是证实了依靠爱情进行主体确认的无望。城市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公平的社会体制保障,当然还有更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丰富的精神资源。但在严苛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下,高加林们只能在交叉地带绝望徘徊,这正是路遥内心深处的绝望之处,这份绝望正是他进行艺术创作的心理动机。
尽管路遥的“新人”没能成功进城让人觉得无限遗憾,但对于路遥来说,他的主人公们不能留在城市,而一定会回到乡村,恰恰因为他遵循了现实主义“写真实”的原则,描绘了“新人”们的真实处境。是谁让高加林们经历那么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个圆圈后不得不又回到起点?“是生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而不是路遥。”[5]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家,路遥有意识地把农村知识青年个人需求和社会发展提供的条件联系起来。路遥没有夸大高加林、孙少平对现实的掌控能力,并且没有向壁虚构出一个完满的结局。由于路遥对城市生活的隔膜、城市想象的贫乏,他小说中的城市停留在诱惑和陌生的阶段,城市无法成为“新人”生长之地。“孙少平最远只能走到煤矿,如果进了大城市我就管不住他了,因为路遥对大城市生活不特别熟悉。”[6]这表现出了路遥现实主义创作中严肃认真的态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中“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新观念的承载者不同,路遥的“新人”走在了社会理念之前,反而对社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指出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打开了用文学方式干预社会的途径,打破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固化模式。
除了表现“新人”的真实命运,路遥对“写真实”原则的遵循还表现在他对“新人”心理世界的关注。他致力于表现普通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并不把他们纯粹当作某种社会理念的代言人。对孙少平来说,他投身改变命运的行动之中,并不仅仅为了结束悲惨的生存现状,更为了生命的丰富,哪怕这种丰富仅仅由进过大城市、见过世面带来。孙少平敏感的精神末梢已经探出他狭窄的出身巷道,和广阔的“另一个世界”艰难沟通。他之所以最终“敢于”留在煤矿,正是因为他的有恃无恐。路遥极力表现的就是孙少平精神之丰富,他可以忍受各种境遇,并在其中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借以蔑视他面对的卑琐的现实世界。“新人”们的真实心理体验来自他们接受的教育和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思考,这种思考有着多种可能性,并且有着无限丰富和深刻的希望,像是关怀个人的萌芽,在合适的条件下就会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路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规范的“突围”集中更表现在他对自己艺术图景的勾描。他的艺术图景来源于他深沉的思考而不是政治规范的要求。对于路遥来说,他的关注点不是一两个农村知识青年的命运,也不是他们的心理世界,而是“社会”“历史”这样宏大的概念。对孤独的“新人”进城遭遇的深刻体验给了路遥关注国家层面问题的视野的契机,“一旦人类被迫注意到了人的孤独感,个人对社会的紧密性和复杂性就得到了更为详细的分析”[7]。路遥的“新人”不仅仅是纯粹的自我觉醒个体,更是深深镶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他们个体的关注最终指向对历史、对未来的关注。“路遥作品中同样潜隐着未来的因子,并由此渗溢出宏阔、深邃的历史意识。”[8]李云雷认为路遥的现实主义“不是批判现实主义,而是一种建构性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有方向、有理想的现实主义”[9]。我认为路遥的艺术理想在于用文学的方式打破城乡两个世界间厚重的壁垒,为知识青年尤其是农村知识青年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路遥的农村新人在和城里人发生冲突后发出的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10]88的声音。这种有着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的人物在“十七年文学”中是不会出现的。路遥从一种清醒的写真实的态度出发,意识到城乡二元体制给农村青年人生带来的阻碍,对这种阻碍真切的表现让人唏嘘不已。高加林的进城经历无疑是悲剧性的,即使孙少平可以进入黄原城,也只能作为最苦最累的打工者,无法获得真正的城里人身份。路遥的新人悲剧性遭遇在当下仍然有效,这些形象没有失去抚慰人心的力量。并且,路遥的“新人”并非自怨自艾的小人物,而是努力完成自己作为普通人的人生使命。他们对生活充满着期待,真诚地体验着人生的悲欢离合,并在人生经历中自我成长,收获了丰富的心理体验以应对人生的波折,他们是充满正能量的普通人。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法摆脱的“魅影”
路遥对“新人”的塑造并不仅仅有“写真实”这一个维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无意中的遵循几乎和他的“突围”一样明显。这种遵循一方面则来自他生活经历在艺术创作中不经意的投射,另一方面源自路遥艺术创作的“惯性”。总之,路遥是一位深深镶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环境中的作家。他的成就和局限都有着代表性,表现出艺术创作服从政治要求造成的悲剧并不会很快消弭。
在“十七年文学”的生长环境中,每个作家都无法避免“文学为政治服务”规范的整肃。它在无形中消磨着作家的艺术活力,导致个体和个性的压抑,就算是七十年代末崭露头角的路遥也不例外。1951年底到1953年,文学界曾有过由文联组织的学习活动,包括“文艺界整风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习”,目的在于调和文学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矛盾,整肃文学创作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引导文学更有效地为政治服务。用学习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显然比较简单粗暴,对艺术规律的忽视可见一斑。这正是我国利用政治手段整肃文学创作最典型的方式,并借助政治话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规约着作家、评论家甚至读者对文学的认识。路遥以个人深刻体验为视角切入文学创作,与这种规范当然格格不入。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走出这一阴影的覆盖。
尽管高加林的命运遭际反映着“写真实”的艺术原则,但路遥自身的生活经历投射到艺术创作中,他对社会的表现并没有完全超出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路遥对“新人”进行表现的过程中持着小心翼翼的心态。他精神紧张,觉得自己承受不住再一次的“失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路遥在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为弟弟安排工作时就密切关注着政治走向,“路遥在这封长信中,第二次提及当时的‘政治气候’,他对‘政治气候’过分敏感。”[4]以这种心态生活的路遥,是很难得到自由的艺术表达机会的。程光炜对路遥的判断非常有洞见性:“如果没有对‘十七年’和‘文革’文学营养的吸收、模仿,没有这种历史经验的沉淀,没有这种特殊的文学训练,是否会有路遥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不免存疑。”[11]1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政治对文学的“规约”与“十七年文学”时期相比,有着很大的继承和延续性。“人道主义”“主体性”等讨论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的机会。路遥在表现新人命运过程中指出社会现实对个人的限制,试图通过国家层面的政策关怀个体的命运问题,因而对社会机器的掌控者充满期待。这种心态无疑是缺乏作家作为个体的反思性的,他把个人命运的绳索绑在了社会历史的船舵上,恰恰是对“新人”主体性的一种消解。他的“新人”们放下对社会历史的反思而走上“知足常乐”的生活轨道,显示出路遥一厢情愿的安排,或者说他剥夺了他的主人公反思甚至进一步做出行动的可能性。他把“新人”进一步思考的可能性归为己有,化为小说中议论和说教的部分。路遥的这一姿态掩盖了他最可贵的试图沟通城乡两个世界的努力,使他的现实主义关怀缺乏可能达到的力度。
尽管路遥极力说明自己并不想做青年的“人生导师”,却时时流露出作为导师的姿态。路遥“继承”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中说教这种不高明形式,以达到教育读者的目的。这种方式往往会偏离“写真实”的艺术追求。当孙少安的砖厂遇到大危机的时候,路遥在“安慰”他的主人公之前先进行了议论:“而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在这条路上跌倒后,爬起来继续走下去?当然,我们毫不怀疑整个社会将愤然前行!”[12]149-150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路遥的小说中始终存在一个隐含的教育者,限制着典型人物展现的时代和个人的复杂性。路遥一再强调柳青对他的影响,把柳青式的写作和生活方式看作真诚的劳动,对柳青受到“十七年文学”规范整肃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在他看来,写作是回报社会、回报自己劳动的过程。作家要对读者“负责”,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避免高加林的悲剧。在伦理道德的外衣之下,规定高加林人生道路的,正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农村青年的角色定位。因为路遥小心的解释和剪裁,他的主人公们并没有超出这种定位之外的想法和行动,并且对这种定位进行了“极端化”的认同和个人努力。
路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持有遵循态度,导致他的“新人”经常在无意中超出“普通人”的规范。这种超出并不是来自主人公对当下社会的宏伟设想,而源自抽空了社会主义理想之后的躁动心态。“他尽量使他的心变得铁硬,并且咬牙切齿地警告自己:不要反顾!不要软弱!为了远大的前途,必须做出牺牲!”[10]128很难相信这是高加林在决定和恋人分手时的心理活动。这种强迫式心理的产生只是因为进城这件事而已。高加林给人留下的印象中,病态的挣扎和不顾一切的气质十分突出。不管高加林充满了多少活力,他都是卖了“良心”才回来的荡子,把他最终的回归乡土归结为生活对他的惩罚并不过分。尽管孙少平、孙少安在伦理道德上变得无法指责,但他们身上不顾一切的气质并没有得到缓解。当孙少平成为工人进入煤矿在体检环节遇到问题时,他找到负责体检的医生寻求帮助,因为自己有可能再次回到乡村他发出了一声“哈姆雷特式的悲怆的喊叫”“ ‘不!我不回去!’少平冲动地大声叫起来,眼里已经旋转着泪水”[12]18。与这种急切的心态相调和,“新人”们遇到的改革时代的问题、自身受到的伤害被他们携带的乡土世界的宽厚和温情所化解。他们成为了乡土伦理的代表,为了自我的道德完成进行自我压迫,用力过猛。“新人”没有了阶级代言人的身份,却有着革命时期青年身上的那种不顾一切的气质,有着潜在的破坏性。
路遥的小说主人公这种近乎病态的挣扎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性格并不是路遥的创造,而是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人物的设定有着某种悲剧性的关联。路遥清醒地了解极“左”时期文学的荒谬和“十七年文学”把个人作为阶级代言人的不妥,他有意识回避这些问题。但作为参加过文革、在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现实主义作家,有意识的回避也带来了无意识中的流露,急切的回避心态反而暴露了受其影响之深刻。他的“新人”们毫无道理的“自我压迫”与躁动的心态,恰恰是“无产阶级代言人”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的心理遭遇:他们致力于用劳动平衡内心的骚动,路遥则致力于呼唤一个伟大的时代,为他们带来光明的明天。
总之,路遥所处理的,依旧是“写真实”与他的艺术理念之间的缝隙,即如何让他的主人公们以“普通人”的姿态进入到自己的未来图景展示之中。他本想借助高加林们悲剧性的进城经历试图构建一个城乡两个世界相沟通的图景,表现一种有方向、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关怀。但由于路遥的生活经历、创作经历以及时代环境,他的艺术发展受到各种限制,路遥并不可能有所超脱。路遥极力表现的“普通人”在心态上缺乏自足性。他们的进城由自我意识的张扬滑落到自我道德的极力完成,进城中的悲剧性结局归结为社会制度应该反思的问题,这和路遥的初衷并不符合。赵树理曾极力迎合主流意识形态,他创造出“赵树理方向”。但仍然跟不上主流意识形态的脚步,反而不得不“进中南海庆云堂闭门学习毛泽东著作”[13]。相对于赵树理试图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而不得,路遥“挣脱”这一规范而不得更有深刻的悲剧性。
但对于路遥来说,“新人”的遭遇当然不是农村人或者城里人的过错,也不简单是社会制度的过错。城里人和农村人都有着各自的狭隘和活力,也都相互伤害,相互有着偏见,这并非阶级、阶层、城乡概念可以涵盖。据晓雷对路遥的回忆,“路遥笑了,接着他说这一次在延安害病一个月,使他的世界观变了,变宽容了”[14]。这份宽容也许是路遥对他笔下不平凡的平凡人的期许,消解着张克南母亲那样的偏见和高加林“我闻见你身上也有一股臭味!”[10]87的咒骂,也消解了高加林、孙少平“不堪贫穷而近乎病态的奋斗挣扎”[11]10。对这种“非常自私、功利和顽强的精神气质”[11]10进行稀释,正是现实主义作家路遥的艺术生长点。如果天假以年,他也许可以完成自己的“宽容”,这毕竟是后话,也是一种美好的期待。
三、余论:作为一个参照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
路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典型作家,他对现实主义“写真实”原则的遵循和遵循的限度并不难探索。综观对他的研究,他创作中的局限得到更多的阐释,原因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意中的继承表现比较突出,让研究者们耿耿于怀。他塑造的“新人”与其说是觉醒的个体,更像是变身后的“农民阶级代言人”,有着掩饰不住的阶级优越感以及优越感丧失之后的怨恨,可敬又可怕;他不厌其烦的说教给人的“反感”多于受到的启发。从这个角度看,路遥并不是一个招人喜爱的作家。如果一位作家没有托尔斯泰、高尔基那样的智慧和洞察力,我们又怎么会轻易接受他的说教?如果没有对“十七年文学”文学环境的了解,路遥可能更加难以在当下得到进一步的接受。
当然,文学要为读者提供认识世界的线索,带来“启示”,“写真实”的规范不会失效。因此,路遥仍然是很重要的作家。他创作的典型人物表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典型环境的部分真实。他的“新人”以实际行动试探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奋斗个人包容和限制的力度,揭示了城乡两个世界的隔膜,在这种揭示中不乏热情和温度,这正是路遥的可贵之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环境下的路遥,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的“逃离”愿望肯定多于认同的心态,但最终他逃离的努力和认同的不由自主一样突出。
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参照物观照路遥的价值是有效的。其有效性不仅出于路遥生活时代的考量,而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就是有着丰富内涵的标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果作为一种宽泛的关怀精神而存在,它所期待的“新人”有着各种可能性。不管是“十七年文学”还是路遥,都没有穷尽“新人”各种可能性,并且“新人”这个概念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衰落”渐渐被摒弃。正如刘诗宇指出:“主流文学界对于‘新人’形象的封锁或许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后来关于当下现实尝试存在的问题。”[15]因此,尽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统一的规范已经失效,它传达的关怀底层民众、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的理想并没有失效,反而在当下显得可贵。它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标尺存在,前提是它已经卸下党性原则的包袱,解除了长久以来的话语禁忌。总之,认识并表现生活的真实非常困难,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提供了“真实”的一部分标准或对“真实”的勇敢追求精神。以它为一个路标,最起码我们可以知道自己走出了多远,在行走过程中是否遗失了最初的真诚。
[1]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换[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217.
[2]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J].人民文学,1956(09):1-13.
[3]周扬. 周扬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78.
[4]梁向阳.新近发现的路遥1980年前后致谷溪的六封信[J].新文学史料,2013(03):140-150.
[5]路遥.路遥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2.
[6]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C]//李建军.路遥十五周年祭.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7:194 .
[7][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M].高原,董红钧,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96.
[8]王春云.宏阔、深邃的历史意识——论路遥的创作追求[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02):24-28.
[9]郝庆军,邵燕君,鲁太光,等.《平凡的世界》:历史与现实[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5):51-59.
[10]路遥.路遥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程光炜.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C]//程光炜,杨庆祥.重读路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2]路遥.路遥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3]魏巍.通过“柳青现象”反观“赵树理方向”[J].当代文坛, 2016(03):141-146.
[14]晓雷.故人长绝——路遥离去的时刻[C]//李建军.路遥十五年祭.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7:173.
[15]刘诗宇.“新人”形象涉及的问题与可能性—从严家炎与柳青关于梁生宝的争论说起[J].长城,2016(2):156-159.
(编校:王旭东)
Recognition and Wandering of Socialism and Realism—On Lu Yao’s Creation of “New Person”
LIU Li-c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hina)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the early 1980s, Lu Yao created the image of new rural youth such as Gao Jia-lin and Sun Shao-ping. Because of the acceptance of modern education, their vision are open, so they feel the unfair fate and take the action to change fate, but in the end return to the starting place. Lu Yao sincerely concerned about their fate, and looked forward to being able to tackle the deep ditch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achiev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worlds. In the proces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this expectation lies in the social and national level, and “new person” is focused on the moral improvement and the enthusiasm of the hometown. Awakened individuals, despite their desperate passion and self-demanding in their struggle with fate, return to the aphasia of the times. The shaping of the “new person” in the 1980s reflected Lu Yao's intentional wandering and unconscious recognition towards socialism and realism as a realistic writer.
Lu yao; literary image; socialism and realism; recognition; wandering
2016-11-21
刘立灿(1991-),女,河北邢台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G641
A
2096-3122(2016)06-0080-06
10.13307/j.issn.2096-3122.2016.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