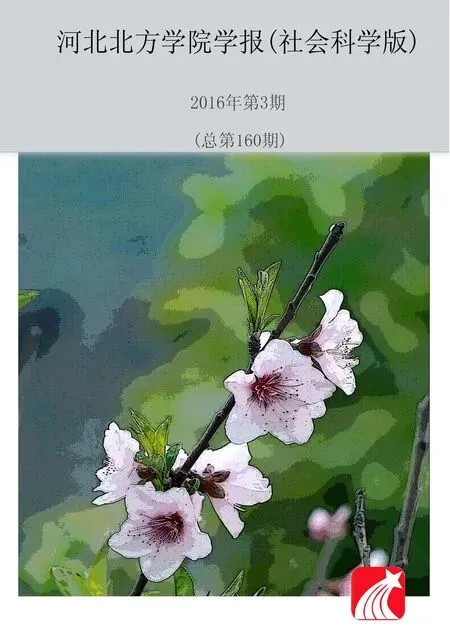论王安忆“乡村书写”的主题流变
尹 鑫 华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论王安忆“乡村书写”的主题流变
尹 鑫 华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都市作家王安忆对乡村的书写贯穿其创作的始终。其“乡村书写”大体经历了隔膜批判、温情礼赞、建构精神以及城乡相互改造的流变,但始终不变的是作家对底层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温暖而质朴的人文关怀。她以都市书写者的身份,在对乡民的生存境况、生活经验与情感方式的书写中超越了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并以美学的眼光发现了城乡间的共同点,这也正是王安忆书写乡村的独特之处。
关键词:王安忆;“乡村书写”;乡村;城市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60608.0911.034.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6-06-08 09:11
《长恨歌》发表后,王安忆逐渐被认定为都市作家和海派作家。而事实上,王安忆在其3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从未停止对乡村的关注和对乡土的思考。这些有关乡村的叙述或显现在引人注目的作品中(如《大刘庄》和《小鲍庄》),或隐藏在叙述城市作品的背后(如《富萍》),它们是理解作家创作必不可少的要素。因生活在都市,王安忆对乡土的书写必然不同于生长在乡村的作家。因此,研究王安忆的“乡村书写”,不仅要关注其作品本身,更要考察作家在不同时代际遇中对乡土的体验和感悟以及城市生活对流动乡民性格命运的描写。基于此,文章按照时代以及写作主题的变化,从3个阶段对王安忆的“乡村书写”进行梳理,以期探寻作家对该种题材创作的独特之处。
一、隔膜与批判:乡村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反面
以知青作家身份亮相的王安忆,凭借“雯雯系列”小说开启了文学征程和乡村之旅。与同时代的知青作家一样,她描写了知青在乡村的遭遇,即招工、求职、婚恋与升学上的坎坷。于此,乡村社会并不是温暖的家园,“雯雯一时间有些恍惚起来:她这是在哪里?这可是地狱?可是阴间?像于小蔓说的,像阿宝阿姨说的,在这里等着做猪做狗,等着轮到自己投人生,去做人”[1]184。在农村,她始终是外来者,这里带给她的只是青春的寂寞和无家可归的迷惘,“雯雯望着门外扯不断的雨,忽然意识到,那房子是不会盖起来了。她多么想有一间房子。有了房子,便有了自己的世界。有了自己的世界,便可以自己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而用不着像现在这样每时每刻都和贫下中农相结合”[1]171。对她来说,城市才意味着自由和安全。所以,她无时无刻不向往城市,无时无刻不想着逃离。小方的话道出了她的心声,“火车立刻就要带我离开这——我这么些年无时无刻不想着离开的地方;带我去那——我这么些年里无时无刻不想着要去的地方”[2]51。她只是乡村的“过客”,“火车”的隐喻传达出知青的无根感,这种漂泊体验来自作家的亲自体验——雯雯的原型就是作家本人。
1970年,王安忆赴安徽蚌埠五里河大刘庄插队落户。16岁的城市少女第一次独自出门,这个在家连手帕都不曾洗过的女孩同当地农民一样,在淮北农村贫瘠的土地上拉犁、挖河沟及收割庄稼……她在这里见证了农村的贫困与落后,内心无比怀念城市生活。正如作家所言:“我无法像很多人那样,怀着亲切的眷念去写插队生活。我离开插队的地方后,再没回去过。”[3]因此,“怀念城市”始终是她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
结束了“伤痕”时期带着控诉情绪对农村插队生活的悲怨描写,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王安忆的“乡村书写”转向冷静揭示乡村的封闭和乡民的愚昧,典型文本是《大刘庄》和《小鲍庄》。
大刘庄同当时中国的许多村庄一样封闭和愚昧。在当地,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仍是潜在的支配力量。小说中,迎春和小牛自由恋爱却遭到家族势力的阻挠,乡村政治力量的代表村支书却秉持旧观念站在家族势力的一边,这突出表现了以血缘为纽结的宗法制总是与显在的政权形式互为表里。乡村还存在根深蒂固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女性始终受男权与父权控制,幸福只能维系在婚姻上。未嫁的姐妹们恪守村里陈旧古板的规矩,在焦虑与期盼中苦熬。此外,百岁子离家出走和豁牙巴子强奸憨子等都体现了乡村的丑陋。作家往返于城乡之间,通过城乡生活状态的对比,展现了乡村生活的停滞与凝固以及村民内心的丑陋与愚昧,折射出作家对中国乡村文化的关注。更能凸现该时期乡土书写题旨的是《小鲍庄》。小说描绘了一个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仁义”村庄,民风淳朴且敬老爱幼。然而,“仁义”的村民却行着“不仁义”之事:鲍秉德的媳妇美丽贤惠,却因连生5个死胎而被丈夫和“舆论”逼疯;拾来和二婶相好,成了有4个孩子的寡妇的倒插门女婿,勤劳肯干却始终被村里人看不起;孩子捞渣背负着“仁义”,直至最后为救鲍五爷献出了生命……“仁义”固然可以维系朴素的人伦关系,但也是一张无形的网,束缚了人们。王安忆冷静地描绘乡村生活的平庸、卑微与沉重,揭示了乡村世界的封闭以及乡民精神的愚昧,于平淡而细致的笔调中隐含了文化批判的激情。
作为一个出身城市的现代青年,王安忆一直抗拒乡村文化并对其文化观点进行改变与塑造。在城乡对立中,她不自觉地站在了城市的位置。《大刘庄》存在两条叙事线索:一条在上海,一条在皖北农村大刘庄。作家通过城乡生活状态的对比,展示了农村生活的滞后与农民的愚昧。疯狂动荡的年代里,“城市青年琐细,互相磨灭和仇视,农村青年就是彻底愚昧了”[4]。作家将批判矛头指向乡村文明,城市与乡村这两个相互独立又有所联系的空间显现了某种失衡。然而,在《小鲍庄》中,城市与乡村关系又呈现出平衡。与《大刘庄》鲜明的城乡对比不同,《小鲍庄》采取了隐藏的两套话语系统的比较:一套是现代政治话语系统,另一套是小鲍庄独有的话语系统。由于作家的城市人身份,她在叙述乡村时必然带有一种“外在的眼光”,这种眼光隐藏在现代政治话语背后并打量着“小鲍庄”。为防止城乡关系再次“失衡”,王安忆创造了小鲍庄独有的“仁义”话语。“仁义”作为言语系统的中心解释了小鲍庄从前和正在发生的所有事件:鲍秉德疯了老婆,村民劝他离,“我不能这么不仁不义”;“打小仁义”的捞渣为了救“老绝户”鲍五爷失去了生命……正是在小鲍庄独特的“仁义”道德规则指导下,从城市等外在眼光中看上去愚昧、软弱甚至了无生趣的乡村生活才有其合理性。所以,“小鲍庄”是乡村叙事和城市目光的一个完美集合点。
王安忆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书写”经历了从对乡村生活的控诉到对乡村原初鄙陋文明与封闭文化批判的转变,小说的叙写对象也由插队知青过渡到本土乡民。此时,作者对乡村世界仍保持一段距离,对乡村文明仍持有一种拒斥和不认同的态度。因为,她的心紧密靠拢城市。同时,也正由于叙述人这种“不介入”的态度,使得她能够以一种超越愁苦的悲剧视角和田园牧歌的现代理性精神反观乡村世界,展现乡民的本真生活。
二、礼赞与审美:乡村作为一种现代性反思的参照
20世纪90年代,面对迅速变化的现代工业社会,王安忆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身感肝肠俱裂,心如刀绞的时候,那些洞察、超脱的哲学竟一点没有办法来拯救我,因而这些观念瞬息间粉碎了……我甚至觉得以后再不能写小说了……”[5]127-128因此,王安忆在这一时期重建笔下的乡村世界:一方面,面对世界化的潮流,乡村被城市置于孤立地位;另一方面,乡村作为独立于时代潮流之外的恒定空间,被看作是一种精神性存在并具有审美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与世界接轨的潮流,乡村文明在城市现代化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这样的情形表现在以下文本中:《悲恸之地》讲述了山东乡村青年刘德生进城卖姜,面对现代化大城市的诱惑以及城市人的鄙夷不断迷失,后受到惊吓而跳楼自杀的故事。作家选择主人公自杀作为现代城市危机的表征,透露出在现代化城市笼罩下,她对乡村社会的理解。刘德生作为来上海的农村青年代表,对吃喝、娱乐以及女人有着强烈的欲望,“他想:要是能到那上面去耍一耍,也就不枉来一遭上海了”[6]139。乡村质朴的价值观念起不到任何作用,乡村青年轻易地沦为城市的俘虏。由于固有的封闭与落后,他们所有的言行都近于笑话,并不断被鄙夷和嘲笑。最终,刘德生因与同伴失散迷路,仓皇中逃进高楼,在保安追赶下,恐惧至极而跳楼身亡。这个故事揭示了农业文明下的乡民迷失和毁灭在商业社会的凶险迷津中。《妙妙》讲述了一位想要成为“现代青年”却被时代潮流无情抛弃的乡村女孩的故事。妙妙的失败是宿命式的,正如作家所言“她大学上不成,生意做不了,只好将自己整个人生都赔进去。其实妙妙也很有女性意识,想改变默默无闻的人生,只是她除了身体之外手无寸铁”[4]34。这暗示出妙妙的自我城市化只能徒劳地在城市外围努力,她注定成为世界潮流下的牺牲品。妙妙和刘德生都是乡民的典型代表,他们展现了乡村青年在追求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失败,这也正是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乡土社会的价值判断。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面对日益商业化和平庸化的现代社会,以及大众对财富和欲望愈演愈烈的想象性满足,作家有意从都市书写中隐退,深情回望乡村,集中笔墨书写自己知青生活中的亲历往事。与“伤痕”时期的控诉不同,作家在质朴乡民身上发现了“美”的存在,“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太制度化与格式化,人变得概念而抽象,而农村的生活是感性的,更富有人性,更具有审美的性质”[7]118。作家通过创作《天仙配》《招工》《王汉芳》及《喜宴》等短篇小说和《文工团》《隐居的时代》与《姊妹们》等中篇小说,温情礼赞江淮儿女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并在这种乡村的记忆、回望及书写中寻找与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
乡村之所以值得礼赞源于其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最典型地体现在乡民对知青的态度上。《隐居的时代》中,质朴的乡民以包容的情怀接纳与对待下放的知青:对张医师持有敬重甚至把她的造访当作一种光荣;把于医师当作亲人,和她谈论家事及养儿育女的难处,对她的孩子也像对自己孩子一般;对黄医师则是又敬重又心疼,“因为朴实的村民有着天生的艺术气质,他们懂得欣赏那些和他们不一样的人”。
乡村世界还具有审美性,这种审美性突出表现为人性美。《王汉芳》中主人公从不显山露水,面对复杂的人事关系却应付自如,这种质朴和从容让人佩服。《喜宴》中新郎的学友会拉二胡会作曲,但因家庭成分不好,毕业后只能回乡务农。他虽然自己没有媳妇,可是对朋友的婚礼却开心从容地忙前忙后。《开会》中孙侠子把做饭这一平常的小事设计成艺术品。用料精细、过程设计合理且时间把控精准,显现了她对劳动的敬重。
对于人性美展现最突出的当属《姊妹们》。发表于1996年的《姊妹们》与作者在寻根时期发表的《大刘庄》有一致的人物和相似的情节,不同之处在于《大刘庄》书写了城市和乡村两条线索,而《姊妹们》则坚实地站在“我们庄”这片土地上。如果说作家在《大刘庄》中对于乡村更多地持审视批判的态度,到了《姊妹们》里则撩起乡村世界温馨美丽的面纱,歌颂人性的美丽,这美丽正是以“我们庄”的姊妹们为代表。“能使人们真心感受到我们庄的人性的,莫过于我们的姊妹们了……她们是我们庄人性的最自由和最美丽的表达。她们给风光枯乏的我们庄增添了一股妩媚的生气……这是我们庄的光辉,它照耀了我们庄平淡严谨的岁月。而我们庄也以悉心的关爱护卫着她们,这同样是以严格的规矩来表达的。她们羞怯、自爱、克己、友爱,真是我们庄人性的最好方面。”[8]在贫苦的生活里,姊妹们仍充满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刘平子时时处处忘不了打扮自己:用麦秸替自己编戒指和手镯;去地里干活手脖子上系块小手绢;衣服裁出腰身,裤腿要齐脚脖……姊妹们不仅对美有追求,生活上更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如小勉子,她遇事沉着、办事大方、有判断力且肯动脑子,是姊妹们的中心,她敢于冲破世俗,当嫁的年龄不嫁,遭到男方退婚时毅然为自己讨说法,婚姻终于随了自己的心愿。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民的愚昧偏见……“我们庄”的姊妹们就是这样自信而努力地生活着……
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的“乡村书写”,虽然在初期有对乡土社会面对现代工业化“永远也回不去”的描写,但中后期对温暖质朴人性美的赞扬却成为主旋律。作家正是通过对乡村人情美和人性美的歌颂,来抵抗城市中人们日益膨胀的物欲以及自身道德的沦丧。
三、互动与改造:乡村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迷惘
新世纪以来,王安忆的“乡村书写”呈现出不同样貌,即乡村与城市第一次以相互楔入的方式出现在文本中,两者相互开放与改造。当然,在这种城乡互动中,乡村不可避免地遭到扭曲和破坏:乡民从封闭的乡村走出去,必然受到物欲的影响。但作家笔下的乡民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永远回不去”的现代城市的外围者,而逐渐成为城市中乡土情谊和劳动精神的代表,他们是铸就城市发展内核的重要力量。
(一)过渡到城市
1996年夏,王安忆因病到绍兴华舍镇休养,在这里亲身体验了现代化和城市化给小镇的自然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带来的变化。于是,她写下了《上种红菱下种藕》这部描述在城市化进程中被不断改造甚至背弃的乡村的典型文本。
文章借助女童的视角,对沈溇、华舍、柯桥以及温州等地进行了描绘:沈溇大量的土地被征用修路建厂,青壮年外出打工做生意,村中留守的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村子渐渐变成空壳;华舍镇里工厂林立,市场经济已经在小镇中显露,由于小镇轻纺业缺乏必要的排污设备,使得乡民用水出现了困难……揭示了一幅幅现代化由城市向农村辐射及蔓延的时代图景。小说既描写了自然乡土面对工业化的重压濒临瓦解的现状,同时也表现了处于此时代中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
秧宝宝的爸爸夏介民为了给妻儿提供更好的生活,一步步向更大的地域迈进,挣了钱之后想犒劳家人,于是在柯桥最豪华的酒店订了房间。一家3口在宾馆里吃饭、K歌和看碟,“享受”了3天。但这样的“享受”丝毫没让3人感到快乐,有的只是空虚和孤独。可见,这就是挥霍性的消费主义的真相,它并不能提供实质性的身心满足。与此同时,传统的家庭聚居生活被打破,年轻人一个个离开,他们在实现个人发展愿景的同时,天伦之乐变得淡薄。就像老公公一样,3个儿子都走了,只有自己守着老房,实质上,他是在坚守诚实劳动带来的自尊与满足。然而,老公公毕竟是个老人,这样的品质以后还有谁来继承呢?
作家面对小镇充满了迷惘。工业文明确实改善了乡民的物质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利益至上的恶劣民风。作家在这里不是为了作出绝对的价值判断,更多的只是一种描写,展示在人口流动过程中,乡民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以及农村生存环境的变化。当然,还有一份忧思。
(二)城市里的乡村
随着乡民们不断涌入城市,他们逐渐在这里扎根并聚居,开始参与城市生活。与此同时,他们身上积极乐观的劳动精神也影响着城市。
《民工刘建华》中主人公的出现使农民被城市拒斥的命运有了戏剧性的转变。刘建华因自己的精明和勤恳获得了很好的生活,他是这个蓬勃群体的典型代表:勤恳善良且积极向上,聪明能干有心计,头脑灵活重情义。不同于父辈的农民,他们紧紧地楔入城市生活,其身上所具有的美好品质在城市生活中焕发出光芒。《骄傲的皮匠》中“小皮匠”被作者塑造成了“完美的劳动者”,他勤劳、质朴、温文尔雅又热爱读书。这种描写虽然显得有些“失真”,但却是作者刻意设计的。她希望通过对底层劳动者的“完美化”想象,支撑起对城市中整个社会的期待。
这些乡民除了自身具有“劳动的精神”外,他们之间还有割扯不断的乡土情谊,这些美好品质的最集中体现就是《富萍》。它讲述了一个扬州乡下姑娘富萍试图成为“上海人”的故事。本来到上海做短暂旅行的富萍,受上海的人和事的吸引,最终毁约逃婚,滞留上海不归。作家在叙述这个故事的同时,还以写实的手法对20世纪60年代初期上海的闸北棚户区作了细致的描绘。它处于这个繁华都市的底层,随处可见破败的房屋;这里的人们虽工作低微且生活贫困,却有着自足淳朴的劳动精神和不卑不亢的处世态度,“他们诚实地劳动,挣来衣食,没有一分钱不是用汗水换来的。所以,在这些芜杂琐碎的营生下面,掩着一股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9]186。由于居民多来自乡下,这里依旧保持部分乡村生活习惯、浓重的乡土观念和紧密的人际关系:舅舅家所在的闸北棚户区居民,“他们比村庄还抱团,还心齐,一家有事,百家帮忙”。正是因为这种团结,使得初次寻亲的富萍得以安全到达舅舅家;村民们是朴实的,大家最初觉得富萍悔婚不光彩,对她很冷淡,可是日子再往下过也就渐渐回到先前的样子,甚至有个糊涂的老婆婆来给舅妈提亲……这里的人简单且有包容心,这与现代人浮躁空虚的生活态度以及冷漠隔膜的人际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乡民们所具有的劳动精神与乡土情谊作为一种精神性力量,支撑着这个城市。
在新世纪的乡土书写中,王安忆开启了考察城乡关系的一种新的可能:两者不是作为独立或对立的个体存在,而是以相互楔入的方式彼此改造;乡村不断向城市迈进,而处于城市中的乡民又以流动的乡土情谊和劳动精神构成城市中最珍贵的品质。
王安忆的“乡村书写”贯穿了她漫长的创作生涯。知青文学时期,作家借助自身的真实体验和敏锐感触,提出了个人在异于自身的生活空间中如何实现价值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乡村的隔膜以及对城市的向往。寻根文学阶段,作家在理念上将城市空间和乡土空间并置,批判了乡村的封闭与愚昧。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家受现代化浪潮的强烈冲击,将乡土空间放置在世界潮流牺牲品的位置上,当城市进一步发展,变得令人窒息以后,作家回望乡村,找寻那些最朴实最本真的乡民。于是,乡土空间成为了一种寄托理想的审美形式。在新时期,作家看到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相互开启和塑造的可能。乡民们带着乡村质朴与本真的劳动精神走入城市,在建设城市的同时也改造着城市。在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王安忆不断追寻城市与乡村的变化,打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以一种新的眼光考察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没有将城市和乡村看成是相互对立的存在,也没有单纯描写一方而回避另一方,这正是她不同于莫言和贾平凹等生于乡村的作家的独特之处。她始终以都市书写者的身份努力寻找与发现乡村,呈现与叙写乡村。虽然对乡民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缺乏更为深刻的描写,更多的是把自己的主体意识强加在人物身上,显出了一定的理想化色彩,但也展现了王安忆作为都市书写者对乡村的情思、态度和人文关怀,以及知识分子强烈的责任心与忧患感。
参考文献:
[1]王安忆.69届初中生[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
[2]王安忆.雨,沙沙沙[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3]王安忆,郑逸文.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J]当代作家评论,2002,(5):154.
[4]王安忆.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叙述策略的转型——关于王安忆10年小说创作的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1991,(6):30.
[5]王安忆.独语[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6]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7]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8]王安忆.姊妹们[J].上海文学,1996,(4):14.
[9]王安忆.富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张盛男)
收稿日期:2015-12-01
作者简介:尹鑫华(1992-),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 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62X(2016)03-0026-05
Changing Trends of the Theme of“Country Writing”in Wang Anyi’s Works
YIN Xin-hua
(School of Literature,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0,China)
Abstract:Wang Anyi has written about the country life in her works though she is an urban writer.Her“country writing”has experienced a change of three periods:incomprehension and criticism,praise and appreciation,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nd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But the writer’s concern for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common people remains unchanged.As an urban writer who writes about the living situations,life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forms of country people,she does not follow the model of writing about the antagonism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Besides,she finds the common points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 through the aesthetic view,which is also Wang Anyi’s uniqueness compared with other writers’works with the country theme.
Key words:Wang Anyi;country writing;the country;the 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