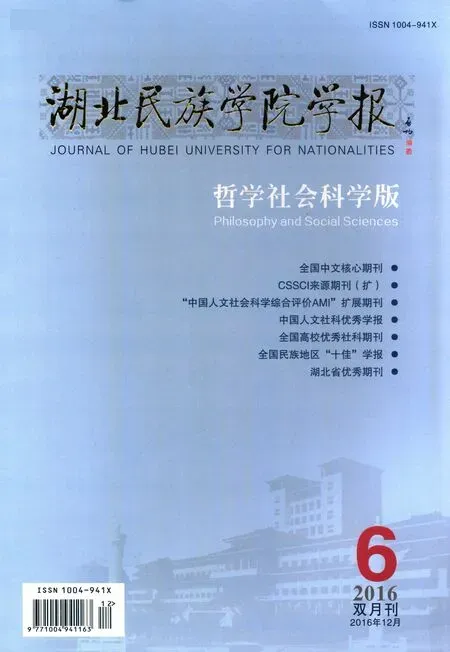湘西凤凰(沱江)方言词“担(tan55)”的语法化考察
向 亮,唐子婷
(1.湖北民族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2.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 400715:3.湖北民族学院 图书馆,湖北 恩施 445000)
湘西凤凰(沱江)方言词“担(tan55)”的语法化考察
向 亮1,2,唐子婷3
(1.湖北民族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2.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 400715:3.湖北民族学院 图书馆,湖北 恩施 445000)
湘西凤凰(沱江)方言中的“担(tan55)”是常用为动词、介词与助词的兼类词,具有明显的方言特色,其动词形式既有普通话动词“担(tan55)”的“承当”义,又有普通话动词“拿”的“握持”义,语法化为介词的模式也与普通话动词“拿”相一致。凤凰方言兼类词“担(tan55)”的动词、介词与助词形式之间存在演变的源流关系,而其发生语法化的关键因素就是语用环境的变化及句式中相关词语的语义制约。
凤凰方言;担(tan55);语法化
凤凰县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南角,县治沱江镇,是闻名全国的文化旅游名城。凤凰方言属西南官话怀靖片(鲍厚星2007),语音与自治州其它县市的西南官话相比,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可能是与凤凰县众多接壤之县市的复杂语言状况有关,凤凰方言在语音、词汇及语用方面都自成特色,特别是在一些常用词的特殊用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担(tan55)”在普通话中通常只作动词用,而未见其它的用法,可在凤凰方言中,却既可以作动词,又可以作介词和助词来使用,是一个身兼三职的兼类词,实际上这正好说明了一个汉语实词语法化的过程。刘坚、曹广顺等先生(1995)认为:“通常是某个实词或因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变化而造成词义演变,或因词义的变化而引起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改变,最终使之失去原来的词汇意义,在语句中只具有某种语法意义,变成了虚词。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语法化’。”[1]沈家煊先生(2001)则认为:“‘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是一种语言演变,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意义虚灵、表示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中国传统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2]26另解惠全(1987)、刘坚(1993)、洪波(1998)、江蓝生(1999)等均先后撰文对“实词虚化”[3]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解读,由此可见,“语法化”实质上是实词因句法位置或组合功能的变化而产生的“实词虚化”现象,同时,这种现象又包含一个语法嬗变的过程。以下就现存于湘西凤凰方言中的“担(tan55)”作为实例,来进一步探讨汉语方言中的语法化现象。
一、凤凰方言中的动词“担(tan55)”
“担(tan55)”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具有两个义项[4],一是“用肩膀挑”义,表示具象的动作行为,二是“担负;承当”义,表示抽象的动作行为和心理活动,在《汉语大字典》中有四个义项[5]:分别为①“肩挑、肩扛”;②“背负、负载”;③“承当”;④“举”义,而在《汉语大词典》中,除两项同用例外,“担(tan55)”有五个义项[6]921,前四项与《汉语大字典》同,第五个义项为“拿”,并标明该义为方言义。由此可见,一般的乃至于大型字词典对于“担(tan55)”的解释基本可归纳为“担负”义,是一个典型的实词,但有具象与抽象的双重涵义,其中“举”义与“拿”义相近,在普通话中虽未见用例,却多见于古代文学作品中,例如:
1.弯一枝窍蹬黄华弩,担柄簸箕来大开山板斧,是把桥将士孙飞虎。(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二)
例1中的“担”释为“举”义,其实释为“拿”义也通。特别是《汉语大词典》注明“拿”义用例仅见于方言中,例如:
2.那丫头自不来担,难道要老娘送进房去不成?(醒世恒言·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3.以后夫妻之情,看不过,只得又是一五一十担将出来,无过是买柴籴米之类。(警世通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
例2、例3中的“担”见于“醒世恒言”与“警世通言”故事中,这两个故事均发生于江浙某地,而“三言”的作者冯梦龙本人也是苏州人,说明至迟于明代之前,江浙一带的吴方言区已出现用动词“担(tan55)”来表达“拿”义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汉语方言大词典》中也有较为明确的说法,该词典认为“担”作为动词的第一个义项就是“拿,搬,持”,且在西南官话、徽语、吴语、粤语及闽语中均有使用,例如:
4.把那本书给我担过来 把那本书给我拿过来。(西南官话四川仁寿方言)
5.你去担支笔来 你去拿支笔来。(徽语安徽绩溪方言)
6.少张椅是我担来个 这张椅子是我搬来的!(闽语广东揭阳方言)[7]
无独有偶,现今西南官话的湖南凤凰方言中,动词“担(tan55)”最常用的意义就是“拿”,常用于“(主语)+担+NP”的句式中,如有必要,动词“担(tan55)”前还可用“把”字短语来引进对象,构成“(主语)+把+NP1+担+NP2”的格式,例如:
7.跟我担杯水来吃 给我拿杯水来喝。
8.帮我把□[ko42]本书担吧来 帮我把那本书拿过来。
9.好神担到,□[mao55]打落 好好拿着,别丢了!
10.我桌子上□[ko42]一百块钱你担了吗 我桌子上那一百块钱你拿了吗?
凤凰方言中的动词“担(tan55)”与“拿”在日常生活中共存通用,且具有同等的地位,例7-10中的“担”均可以换成“拿”,在意义表达上丝毫不会受到影响,相比而言,动词“担”更具地方色彩,且其“拿”义也极有可能是从“负载”义引申而来。不过在凤凰方言中,动词“担(tan55)”并无“肩挑”与“背负”义,除“拿”义之外就是“承当”义了,例如:
11.出了事你敢担担子吗 出了事你敢担负责任吗?
12.我怕担责任,管□[mao21]了 我怕担负责任,管不了。
例11的“担担子”与例12中的“担责任”意义完全一致,均为“承当责任”的意思,如果要描述具体的“肩挑”行为,只能用动词“挑”而非“担”,因而凤凰话的“挑水”绝不会说成“担水”,如果说“担水”,那一定是“拿水”的意思。但是,鉴于凤凰方言中存在“挑担子”和“担担子”在语义上各司其职的现象,我们推测,原本凤凰方言中的动词“担”既具有“肩挑”义,也具有“承当”义,后来更具口语特色的动词“挑”在“肩挑”义上完全取代了动词“担”,于是动词“担”在凤凰方言中除了方言义“拿”之外就是“承当”义了。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担担子”只是“肩挑”隐喻的说法,这与说话者的认知心理相关,即“肩挑重担”与“承担责任”具有一定的相似相关性,其实质为:“用一个相似的概念来表达另一个概念,动因是像似性(iconicity)和类推……语法化的早期阶段以隐喻为主。”[2]30而且,凤凰方言的“担担子”只用作比喻义,就是词语语法化的早期表现,可见,在这里动词“担(tan55)”实际上已经迈出了语法化的第一步。
二、凤凰方言中的介词“担(tan55)”
凤凰方言中的“担(tan55)”还经常作为介词来使用,句式的基本形式为:(主语)+担+NP+VP,这时,VP的焦点地位得以凸显,“担”则处于介引型的陪衬地位,例如:
14.你□[mao55]担我□□[y24mao21]咯 你别拿我开玩笑咯!
15.你担我和□[ki42]去(音[khi24])比啊 你拿我和他(去)比啊?
16.你担自家(音[ka33])和人家(音[ka33])去(音[khi24])比一下(音[ha33]) 你拿自己和人家去比一下!
例13-16中的介词“担”均与现代汉语的介词“拿”的语法功能相当,在凤凰方言中使用相当频繁。《现代汉语八百词》认为“拿”具有两种词性,即动词与介词,又认为“拿”作介词时具备两种基本用法:一是“把;对”,并指出“后面的动词限于‘当、没办法、怎么样、开心、开玩笑’等少数几个”,很显然例13与例14属于典型的此类用法;二是“拿+名+来(去)+动”,表示“从某个方面提出话题。动词限于‘说、讲、看’或‘比、比较、衡量、分析、观察、检验’等”[8],例15与例16的句法结构当属此类,只是凤凰方言的这种用法可加趋向动词,也可以不加。
石毓智(2006)指出:一个词的语法化发展须满足“合适的语义基础与适宜的句法环境”这两个条件,并认为“动词‘拿’具有‘握持’义,已具备向处置式标记发展的语义基础,同时动词‘拿’所带的宾语也是紧随其后的另一个动词的受事才行(例句: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来读)”[9]137-139。显然,动词“拿”的宾语“一本书”同时也可视为后一动词“读”的受事,正是这样的句法环境使得动词“拿”具备了处置的意味,例7中的动词“担(tan55)”也是如此。而“当谓语为充当、熟语、比较、方法时,‘拿’的语法化程度最高,已经失去了动词的主要特征”[9]152。这时的拿字结构已发展成为典型的处置式,凤凰方言中的动词“担(tan55)”也经历了类似的语法化过程,比如例13、14就属于熟语型处置结构,例15、16则为比较型处置结构。
而且,从凤凰方言“担”的动词及介词用法分析来看,可知其介词用法是由其动词用法虚化发展而来,这可从其近义词“拿”的语法化事实得到印证,何洪峰认为:“‘拿’字句的基本结构形式是:N1+拿+N2……在语义上,‘拿’字的功能义主要来自其[+握持]的语义特征。如果N2有[-可握持]义,‘拿’字就可能虚化”[10]。凤凰方言的动词“担”也一样,比如在例13-16中,“担”后面均为不可握持的人物,显然,这几例中的“担”都为引进对象的介词,但同时还含有一些处置的意味,即有“把……怎么样”的意思蕴含其中,其动词的主要特征已然丧失,获得了把字处置式及引起话题的功能。
如果“N1+担+N2”句式中的N2为可握持之物,则“担”的焦点地位又得以重新凸显,这时的“担”既可视为动词,也可视为介词,例如:
17.我担调羹吃饭 我用勺子吃饭。
18.担碗放到碗柜里去 把碗放到碗柜里去!
19.你担肉(去)喂狗啊 你拿肉(去)喂狗啊?
20.你担这张板板凳送爸爸坐 你把(拿)这张小板凳送给爸爸坐。
例17-20中的“担”视为动词的话,则有“握持、搬”等义,因为处于N2位置的“调羹”、“碗”、“肉”及“小板凳”均为可握持之物,这样就与其后的VP构成连动结构;如果视为介词,则有引进工具和强调对事物处置的意义,与其后的VP构成状中结构,但在实际运用中又不完全是这样,下面我们就这几例来进行具体分析:
例17中的“担”释为介词“用”最为恰当,表示吃饭所使用的工具为勺子,所以不再适合分析为连动结构,例18中的“担”仍为介词,表示对“碗”进行一种处置行为,相当于汉语的介词“把”,与例句17同为状中结构。可是,例19-20中的“担”则兼具两种情况,一是表示对“肉”、“ 小板凳”及要实施某种行为,即进行处置,因此与介词“把”的功能相当;二是“担”在这里仍为动词,具有“[+握持]”的语义特征,因此例句19-20又可理解为连动句,也就是说,相同的“N1+担+N2+VP”语法结构可以表示不同的语义内容,正如董学军(2003)所说:“具体结构的不平衡是引起具体词汇语法化的微观内因。”[11]
这种动词、介词两可的用例恰好体现了凤凰方言动词“担”向介词虚化的一种过渡形态,而这种过渡形式又印证了动词“担”在语义制约下逐步虚化的语法化过程。而且,凤凰方言中这种由“N1+担+N2+VP”结构所引发的动词“担(tan55)”的虚化现象,可视为一种“结构式语法化”模式,即“语法化过程涉及的并非单个词汇或语素,而是包含特定词汇或语素的整个结构式”[12]。正是这种“结构式语法化”模式为动词“担(tan55)”进一步虚化为介词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三、凤凰方言中的助词“担(tan55)”
除了动词与介词以外,凤凰方言中的“担(tan55)”作助词使用的情况也不乏见,句式的基本形式为:(主语)+担+VP,笔者通过调查分析后认为,其助词用法正是由其介词用法进一步虚化发展而来,例如:
21.肥坨子,(你)担压咯 胖子,(你)压咯。
22.□[mao55]光担讲咯,要做 不要光说,要做!
23.□[mao55]有钱,我担□□[thia21tsi21]搞 唉没有钱,我(应该)怎么办?
例21-24中的“担”后直接跟的是动词短语,如果把“担”去掉,根本不会影响全句意思的正确表达,因此“担”在这个语境中主要起的是加强语气和补足音节的作用,可以认定为助词。美国著名语言学家J.Hopper有一个关于词项语法化的“单向性假说(The hypothesis of unidirectionality)”,该假说认为一个词项的语法化过程具有单向性与渐变性的特点,且列如下文字图示说明这个过程:
lexical item used in specific linguistic contexts > syntax > morphology[13]100
这个图示告诉我们,使用于特定语言环境中的实义词项不仅有可能虚化为某种语法结构,还有可能继续虚化为某种词形结构。王寅(2005)也肯定了语法化这种单向性的存在:“词语等语言结构的语法化具有明显单向性(unidirectionality)。单向性包括以下三项内容:1)总是从独立实体向非独立实体演化,可能会成为不可独立运用的附着词缀形式;2)总是从复杂表达向简单表达方向演化;3)总是从较为具体的向较为抽象的、概括的方向演化”[14]。由此看来,凤凰方言中动词“担(tan55)”先虚化为介词,再进一步虚化为意义更虚的助词的过程充分验证了J.Hopper的这一假说,也符合王寅所说的独立性转向非独立性、具体变成抽象的单向性特点。
既然作为助词的“担”在上述例句中可以省略而不会导致听话人的误解,那么为何凤凰人平时在说话时还喜欢加上这么一个看似冗余的成分呢?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说话人的方言习惯问题,这还与助词“担”在句中所体现出的语用功能密切相关,这是因为由介词进一步虚化而来的助词“担”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介词的一些特性,尤其是在一些特定句式或表达一些特殊语气的语境中。因此,J.Hopper的“单向性假说”中还关注到了“layering(分层)”[13]124现象,即语法化后虽然产生了新的形式,但老的形式仍会保留一段很长的时间,其实上述四例中的“担”也可视为介词形式的变相保留。
譬如例21就是一个祈使句式,句中的“担压”就是“用身体压”的意思,是当地人常用于嘲弄身形肥胖者的揶揄之词,因此“担”在此处亦可理解为一个隐形的介宾结构“用(身体)”,但实际上其词汇意义已趋虚化。例22是一个表劝止的祈使句,句中的“担讲”实际可视为“担(用)嘴巴讲”的省略形式,含有责备轻蔑的意味,如果省去助词“担”,虽说在语义上表达一致,但这种情感色彩就会淡化许多。再如例23,其后一分句为带有强烈无可奈何情感的语气句,此句中助词“担”的存在无疑更加渲染与烘托了这种悲观的情绪。需注意的是,例23中的助词“担”虽然仍可理解为介宾结构“把、对(没有钱)这种情况”,但是这种介词的功能特性在该句中已消弭无几,如硬要附上则显牵强,可见此处的“担”已然演变为一个真正用于烘托语气的助词了。例24中的助词“担”后的动词短语是一个连谓结构,“这只鸡”为受事主语,“担”在此句中所起的主要作用有二:一是补足音节,略作停顿;二是强调“吃鸡”的方式。
由此可知,凤凰方言中助词“担”的位于句中,且用于动词短语之前,从其语法位置而言,正与介词相当,但不介引动作对象,也不带宾语,语法意义更虚,以至于去掉后都不会改变句子的原意。因此,类似于例21-23的句式均可视为“(主语)+担+NP+VP”省略介词宾语NP的经济模式,事实表明,一旦省略介词宾语,“担”就有可能进一步虚化为助词,这应该是语义环境制约的结果,也是话语经济表达的一种需要。其中,例21与例22中的“担”是介词向助词虚化的过渡形式,所存在着词性两解的可能。例23中的“担”则已基本丧失了介词的功能,是因为其后接的是“怎么办”一类的VP,却又省略了前面的介词宾语NP,就促使“担”在句中的语法功能由较实的引进对象类逐渐衰变为较虚的加强语气类。例24则更为特殊,是一个受事主语句,虽然在形式上仍为“(主语)+担+VP”的格式,在语义上却可理解为“担(把)这只鸡煮着吃”,但不必勉强将之视作介词宾语前置的句子,因为从功能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势必削弱句子的话题性,所以,例24中的“担”所起的语法作用就是强调与突出全句话题“这只鸡”后的述题“煮着吃”,显然已经彻底虚化为助词的用法了。
相比较而言,普通话中的介词“拿”在“(主语)+拿+NP+VP”的句式中,其介词宾语NP并无省略的情况出现,因而普通话中的“拿”也就始终未虚化为助词。可见,在此类句式中,介词宾语NP的有无是能否触发介词“担”进一步虚化为助词的关键诱因。正因为凤凰方言中的助词“担”是由介词虚化而来,故使得“担”成为语法位置在句中的语气助词。
四、凤凰方言动词“担(tan55)”的语法化过程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凤凰方言中的“担(tan55)”不仅身兼动词、介词和助词三种词性,而且这三种词性之间存在着演变的源流关系,即“担(tan55)”的第一词性应该为动词,它经历了从动词逐步虚化为介词,再由介词虚化为助词的语法化过程,这也是人类从具象到抽象的认知心理的真实反映。
凤凰方言中的动词“担(tan55)”无“肩挑”义,却有普通话动词“担(tan55)”的“承当”义,又有普通话动词“拿”的“握持”义,在“(主语)+担+NP”的句式中作谓语,表示“拿”,具有显著的地方词语特色。黄晓雪(2010)认为,诸如“持”“取”“捉”“将”“把”“拿”等“持拿”义动词都可以发展出用以构成处置式和引进工具语的用法。且认为“‘拿’引进工具语是普通话的常见用法,表处置的用法只保留在方言中”[15]。因此,凤凰方言中的动词“担(tan55)”在“(主语)+担+NP+VP”的句式中,由于VP焦点地位的凸显和NP语义的制约,从而发展为引进工具或表示处置的介词,应当是在情理之中的。
介词“担(tan55)”向助词发展的过程也是比较清晰的,由于语言经济原则的作用,省略了“(主语)+担+NP+VP”句式中的介词宾语NP,形成 “(主语)+担+VP”的新模式,或是在受事主语句中,由于话题的转换,且需要突出述题中的焦点,从而使“担”逐步丧失了介引或表处置的功能,导致其进一步虚化,最终语法化为位置在句中的语气助词。
正如刘坚、曹广顺、吴福祥先生(1995)所言:“如果某个动词不用于‘主-谓-宾’组合格式,不是一个句子中唯一的动词,并且不是句子的中心动词〔主要动词〕时(如在连动式中充当次要动词),该动词的动词性就会减弱。当一个功词经常在句子中充当次要动词,它的这种语法位置被固定下来之后,其词义就会慢慢抽象化、虚化,再发展下去,其语法功能就会发生变化:不再作为谓语的构成部分,而变成了谓语动词的修饰成分或补充成分,词义进一步虚化的结果便导致该动词的语法化:由词汇单位变成语法单位。”[1]
综上所述,凤凰方言动词“担(tan55)”在语法化为介词与助词的一系列过程中,除了人们的认知习惯以外,语用环境的变化及句式中相关词语的语义制约是其起变的关键因素,这是凤凰方言中词类引申的重要原因,也是促使人类语言的词汇系统持续产生新质,从而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
[1]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J].中国语文,1995(3).
[2] Paul J.Hopper,Elizabeth Closs Traugott.Grammaticalization[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3] 吴福祥.汉语语法化研究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5-168.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增补本)[G].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243.
[5]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G].武汉: 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1921.
[6]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第6卷)[G].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921.
[7] 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全五卷)[G].北京: 中华书局,1999:3210.
[8]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G].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93.
[9] 石毓智.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0] 何洪峰,苏俊波.“拿”字语法化的考察[J].语言研究,2005(4).
[11] 董学军.汉语词汇语法化原因探析[J].台州学院学报,2003(4).
[12] 吴福祥.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当前课题[J].语言科学,2005(2).
[13] Paul J.Hopper,Elizabeth Closs Traugott.Grammaticalization(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4] 王寅,严辰松. 语法化的特征、动因和机制——认知语言学视野中的语法化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4).
[15] 黄晓雪.“持拿”义动词的演变模式及认知解释[J].语文研究,2010(3).
责任编辑:王飞霞
2016-09-12
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土家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项目编号:14XYY015);2014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湘渝鄂边区土家语方言的类型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4YBA30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5M572425);2015年湖北民族学院博士启动基金项目(项目编号:MY2015B006)。
向亮(1975- ),男,土家族,湖南吉首市人,语言学博士,副教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及汉语方言。
H172.3
A
1004-941(2016)06-015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