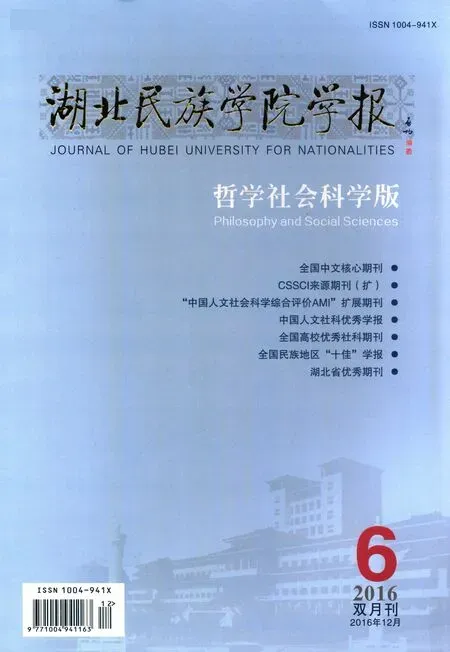空间与性别视域中的《梨花梦》研究
岳立松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空间与性别视域中的《梨花梦》研究
岳立松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清代安徽才女何珮珠所作《梨花梦》戏曲,藉剧中人物杜兰仙展现了女性对婚姻、身份的审视与思考。时空视阈与性别身份转换是作者赋予人物表述与传达意义的重要书写策略。戏曲在现实与梦境、仙界间转换,呈现出时空交错的特性,现实中的杜兰仙压抑与病态,而梦境之中却是感情外显、个性张扬,显示出其对现实的无奈与理想生活的追寻;藉由戏曲扮装,杜兰仙在男子、女子的性别身份中不断转换,隐含着自我欣赏与价值追寻;在红粉相伴“证同心”情感依恋,呈现出女子的情感诉求,可觇视清末才女的现实困境及情感追寻。
《梨花梦》;时空;性别身份;书写策略;情感追寻
《梨花梦》作者何珮珠,字芷香,号天都女史,清道光年间安徽歙县人,有诗作《津云小草》存世。珮珠出身于书香之家,父亲何秉棠,深于诗学;姊妹皆有诗名,二姐何珮芬,字吟香,著有《绿筠阁诗钞》;三姐何珮玉,字浣碧,著有《藕香馆诗钞》。《国朝闺秀正始续集》记:“秉棠,字子甘,深于诗学。诸女习闻庭训,各擅才名。方之张氏七女、袁家三妹,何多让焉。”[1]何珮珠深具家学渊源,具有明清女子的诗情才韵,其藉由戏曲《梨花梦》的主人公杜兰仙展现了才女对现实婚姻生活的压抑与不满。戏曲在现实与梦幻的时空之变、男装与女子的身份游移中显现出女子的内心世界与情感追求,从中可窥视清末女子的情感状态与两性观念。
一、时空之变:现实的无奈与追寻
《梨花梦》讲述女子杜兰仙随夫乘舟北上之时,忆想东邻女伴,情思难遣,遂戏为男装入梦相会梨花仙子,应仙子之请吟诗题咏。兰仙梦醒后追忆仙子不得,只得藉丹青写影以寄情怀。兰仙于悲秋之时复作一梦,梦入仙境,遇梨花仙子及藕花仙子,聚首同游后分离。戏曲所涉时间、空间不断地转换,其时间上自梨花绽放至深秋,其空间上则来往于现实、梦境与仙境,呈现出时空交错之特性。该剧以《梨花梦》为名,梨花是因杜兰仙梦遇梨花仙子,醒后又于梨花之下寻梦;梦是杜兰仙通往另一空间的途径,“梨花”与“梦”皆可视为时空转变之依托。
杜兰仙的出场场景是偕婿北上的旅途舟中。明清时期的女性并不完全束缚于闺阁之中,她们有机会随丈夫或父亲出游赴任,乘船就是旅途中必要的交通工具。女性走出闺阁,在开阔视野的同时,也放逐着女性的心灵。沿途的风景虽可赏览,但舟中长时的旅途也不免单调乏味,剧中人物杜兰仙不免困乏,遥想东邻女伴戏为男装后而入眠,进入到梦中虚拟的空间之中。
梦中杜兰仙遇到梨花仙子知音相惜,然而梦醒之后回到现实时却又令人黯然神伤,“(小生作醒介)原来一梦,回想先时光景好不凄楚人也(卷一赠花)”[2]。杜兰仙对梦中仙子难以释怀,只得步入园亭,试图寻觅昔日情景,“忆梦”中她又小步园亭,试图与仙子重逢,然而却未能相遇仙子,不禁感慨“梦少情偏逗,情悠恨更悠”,在无奈与伤感中,她生发出强烈的空间转换之愿,“愁凝黛,对了这溶溶月色,敲断瑶钗。断肠无益,只索归眠则个(卷二忆梦)”,她将孤寂的身躯寄于梦眠之中,希望再次进入梦中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深秋廖落、梧桐潇潇之时,杜兰仙因情而瘦弱成疾,在无奈的感伤中又试图努力将自己带入梦境,“良夜迢迢,美人何处,且转过这湖山倚栏小憩则个(卷四悲秋)”。当杜兰仙满腹别愁更为深至之时,便“作倦态入帏卧介,生巾服扮梦中兰仙上(卷五仙会)”,这是杜兰仙在屡次尝试入眠后,在强烈的心理暗示中,最终藉入梦的形式与梨花、藕花二仙子于仙境中“仙会”。
《梨花梦》着重书写了杜兰仙的“情思困人,且向纱帏小卧”、“归眠”、“小憩”、“倦态入帏卧”等动作,强调了入眠成梦的形式。在天上人间的转换中,入眠成梦成为空间转换的必要沟通渠道,也是其转入真实内心的一个行为策略。入眠是杜兰仙于现实中选择逃避的方式,这是一种刻意的追求,是对现实的不满及对美好心愿的追寻。梦成为摆脱现实的一种媒介,入眠成梦带有杜兰仙强烈的主观色彩。当兰仙于现实中得不到慰藉,即需要进入到一种虚幻而又理想的境界之中。“困”、“憩”、“倦”、“卧”等词既是杜兰仙在现实中的情态与动作,也是其现实生活倦怠心理情感的表露,表现出杜兰仙有意识的脱离现实空间,希冀进入另一重空间与情感世界的心态。
杜兰仙与梨花仙子的两次相遇虽都是在梦中,但所处空间却大不相同。初遇之时,梨花仙子移入人间,听闻舟中吟声清泠圆妙,左右顾盼时发现原来是“小谪人间,一向不晤”的兰香妹子,并主动请其赋诗题赠,赏其诗“清丽缠绵”,兰仙在此境中得以小露才情。而再次相遇之时,梦里空间则又转移至仙境。杜兰仙于天色大好之时,一路行来,步入仙境,登上仙山绝顶。此次与梨花仙子重逢,还得遇昔时仙界姊妹藕花仙子,三人携手同游后饮酒作别,此次仙会中兰仙才情得以显露和释放,将平生意气摹想一番,达至情感高峰。可惜正当叙会之时,杜兰仙却被晓钟惊醒,更有万端无奈,人生如梦之叹。人间与仙境的不同空间,展示出女子的不同的情志表达。
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舟中、梨花树下,还是梦境中的尘世、仙境,抑或是伤春、悲秋的时间触点,无不流露出杜兰仙的精神风貌与内在心理。现实中兰仙无以施展才华,只有于梦境中寻求认可与赏识。杜兰仙在梦境中遇到了知己、知音,遇到了才华展示、情感表达的对象,这也是她现实中潜隐的自我展现心理在梦中之实现。现实中的杜兰仙是无奈的、压抑的,而梦境之中的杜兰仙感情是外显的,内心激昂、笑傲洒脱,个性是张扬的。如此澎湃的心理情怀却压抑于现实生活的无奈之中,可以想见其对时空转换的渴望,她将理想寄寓于梦境、仙境,将一己情怀寄于空幻的仙乡世界。
戏曲在伤春与悲秋的情绪中演进,在现实与梦境、现实与理想中不断变换,在仙境与人间的相隔与聚首中展开。时间之变呈现出杜兰仙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命体验、无奈情怀;空间之变展演出杜兰仙不同的情感诉求及理想追寻。时空界域的转变中,正是作者人生体验之流露与展现。
二、身份转换:性别身份的游移
作者何珮珠藉由戏曲舞台的搬演特性,从容地将人物身份赋予性别的意义。杜兰仙的身份尤为值得关注,“赠花”中杜兰仙出场是“小生乌帽青衫”的装束,“忆梦”、“写影”、“悲秋”、“仙会”中皆是以“小生巾服”出场。这是一场女扮男装的“反串”表演,巾服男装是杜兰仙的出场形式、表演形式,而其实际的性别心理多重而复杂,藉由装扮,女性拥有自由的话语权利。戏曲角色在女性、男性间交错,性别身份的不断转换,显示出自我与情感的追寻是曲折的、多变的,两性关系的认知也是游移与暧昧的。
传统小说戏曲中女扮男装多为掩示女子身份,借男装而改变形象,虚拟男子身份以实现男性所带来的社会认同。如清代王筠《繁华梦》中的王梦麟就不满自我的女性身份而在梦中化身为男子王生,又如吴藻《乔影》中的谢絮才,也是“自惭巾帼,不爱铅华”[3]。《梨花梦》中杜兰仙虽是巾服形象,也有“奴家杜兰仙,厌为红粉,特换乌巾,敢夸名士风流,聊洗美人习气(卷二忆梦)”之语。但杜兰仙却对女子美貌大加赞许,带有赏悦之情,其自我描绘是:“粉香腮莲花一朵,兰珠凝眼角,梨玉削肩窝”。她初见手持梨花的仙子时,惊艳于仙子美貌,“猛见了三生窈窕姿,快活煞半晌凄凉我(卷一赠花)”。
无论是杜兰仙的自我形象,还是梨花仙子的艳影都呈现出典型的女子美态。初见梨花仙子因其美貌而引发的身心感受,使苦吟之中的兰仙极为振奋,这是感情的波动,是一种激荡人心的力量。兰仙梦醒时追怀梦中佳人再次得到触动与激发,产生“怎得化为年少乌纱,偕此明妆素艳”的才子佳人式的企盼,进而转变为一种情感追求。
现实生活中杜兰仙无从再遇梦中仙子,心中的怀想却愈为深挚,那么难以排遣的思念情怀如何抒发?杜兰仙遂将一番思念寄托于对梨花仙子的画影之中,用写影的方式试图将现实与梦幻相联通。写影是将梦中仙子留于人间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卷三写影:
我杜兰仙自与仙姊梦中叙会,兰心宛转,欲托三生。花信叮咛,难谋一面。叹丽人之遭际,感词客之辛酸。……握管伤心,妾尤薄命;停杯放眼,伊惯消魂。今日春去可怜,花娇不见,溶溶有泪,默默无言。(作悲介)不若画成小影,稍慰伤心。……你看骨洁肌清,好不精致神妙。
杜兰仙以写影的方式再塑仙子容颜,将之落实于可观可感的纸上,将梦境带入人间,不过这也只是暂时的慰藉,一厢情愿的寄托而已。
《牡丹亭》“写真”中杜丽娘是因情成疾,照见镜中消瘦的自我,遂想将美貌留于人间。“哎也!俺往日艳冶轻盈,奈何一瘦至此!若不趁此时自行描画,流在人间,一旦无常,谁知西蜀杜丽娘有如此之美貌乎!”[4]杜丽娘以丹青彩笔绘出自己的写真小影,并嘱托梅香将其葬于梅花树下。杜丽娘画的是自我憔悴容颜,展示出自我的怜爱之意,渴盼得到他人怜爱的感情。女子写真是一种自我发现与自我期待,是一种情感流露,期待自我的美貌永存,期待梦中才子能来至身边,这是女性以彩笔试图证明其存在,将其青春美貌与才华留于世间,是一种自我意识的突显及其对爱情的极度渴望。毛文芳指出“这点女性意识的浮现,预示了后来明清文学才女透过写作与绘画自我呈现的讯息”。[5]
杜兰仙写影描绘的是梦中梨花仙子,这是将理想佳人予以现实化。写影也将佳人难遇的伤情融注于笔墨之中,将虚幻的情境沉入到现实之中,使无以着落的感情有所寄托,正如兰仙所唱:“罗绮羞妆倾城貌,粉靥桃花咲。相思未易消,九曲回肠向卿低告,幽意托霜毫,写衷情,一例儿伤怀抱(卷三写影)。”写影图绘具有多重意指,既是对仙子的描摹,也是对兰仙自我的描绘。杜兰仙虽为梨花仙子写影,但也是她藉丹青之笔抒写自我期待的策略,是以图画形式表达的一种自我肯定与评价。杜兰仙不只是描摹仙子,而且还有意识模仿仙子神态,“不若闲步,一面将仙姊态度摹拟一番以消岑寂,有何不可,妙啊”,“我与你呵,一似形随影,怕秋风各自零(卷四悲秋)”。由此可见,杜兰仙对佳人的写影,未尝不是对自身美貌性情的一种描绘与肯定,融入了她对才女的认知,对女性理想的描画,带有对女子性别身份的推崇之感。
从杜兰仙的男装、女子的身份转变中可以看到她对自身性别身份的游移,既不舍女子形象,又不满女子身份束缚,显示出她对女子身份与两性情感的艰难思考与迂曲心路。我们从兰仙不断转换的身份中看到了一个内心炽烈的个体,追寻着自我的个体命运,“一个人感到唯有这样的生命热情的散发才让自己有美好地活过的感觉,才有自己身体的在世幸福,以至于非如此生活不可”[6],此时的兰仙才更具生命热情与真实自我。
三、情感寄托:“证同心”的知己情
《梨花梦》戏剧情节展开的前提是入梦,而入梦是因杜兰仙在现实之中忆及昔时女伴而情思困人:
(卷一赠花)(兹因偕婿北上,一路以来,路幌风帘,餐辛茹苦。回忆邗江与东邻女伴,斗草评花,修云醉月,曾有愿余为男子身,当作添香捧砚者。今日春色阑珊,余情缱绻,戏为男子装小坐。想当日呵)【锦搭絮】抵无限碧莲红豆种情窠,一味价似醉如痴望浣纱人。入梦多问东风心事知么。秦楼弄玉,月窟嫦娥,艳质芳姿,只落得睹晾闻声唤奈何。(情思困人,且向纱帷小卧则个。)
杜兰仙遥想少女时优游自在的生活。在这种追怀意识的心理激发下,使杜兰仙入梦后得遇梨花仙子、藕花仙子。戏曲预设三人本系同居仙境的姊妹,营造了梦中重会昔日友伴的情境,此设置照应了现实怀想中的东邻女伴,强调旧日相识的姊妹情谊。
戏曲所叙情景颇契合作者何珮珠之亲身经历。当时何珮珠与丈夫同舟北上津门,诗稿《津云小草》即吟咏此时生活。杜兰仙所忆东邻女伴自有昔时何珮珠少女生活的影子。《津云小草·舟中午日》“一钩新月淡穿波,比似娥眉丽若何,忆得扬州诸姊妹,杏衫应换雪香罗”[7]424。流露出何珮珠对昔日姐妹的留恋与不舍,这也是她对扬州美好生活的怀想,对少女情思的叹赏。
何珮珠所作《津云小草》诗集吟咏日常生活,诗歌婉转深挚、愁绪伤怀,可见其婚后家庭生活的辗转与艰辛,亦可从中窥见清代闺阁女子的生活及性情。二姐珮芬《津云诗草题辞》有句云:“一卷津云草,吟成亦可怜。为筹菽水计,典尽旧钗钿。来往京华路,奔驰为老亲。娇痴怜小妹,历尽万千辛。”王勋于《津云小草》题辞最可关注:
何芷香女史之诗足以见其性情之正,为可钦也。……虽然津云之作其在艰难险阻之日乎,观其篇中苦味谁谙透,低徊还自怜,胡为乎心伤一至此哉?然读至“换得莲花米,高堂好劝餐”又“姑意侬心会,何须问小姑”又“宛转订前承色笑,殷勤膝下废餐眠”则又不辞劳瘁,刻意承欢,可谓无怨无尤者矣。至“郎摊诗卷侬挑绣,鍼线都添翰墨香”则又安贫乐道,相敬如宾者矣。不谓以闺门之质而有贤豪之概,虽古之所称名媛淑女何以过此。[7]422
此语透露出作者日常生活之性情。可见,何珮珠在现实中是隐忍的,兰闺诗韵所呈现的诗情才韵逐渐被现实生活的艰辛所消磨,生活给其带来种种烦劳,但是她始终勉力承欢,处理好日常生活之事,与丈夫也是相敬如宾,体现出女贤之德。
何珮珠在生活中端庄贤淑、温和隐忍,她将自我感情埋藏起来,展示出一个社会所认可的、所彰显的女性形象,而其真正的内心世界与情感诉求只有寄托于翰墨之中,寄托于戏曲人物之中,借杜兰仙形象为自我抒怀。孙康宜曾指出:“明清时期的闺阁女诗人似乎寻得了一个受抑情感生活的抒泄管道。她们以浪漫爱情的方式在作品中陈述了女性之间彼此的友谊。在她们致献女性友人的词作中,经常可见‘相思’、‘断魂’、‘恋’等字眼。”[8]
古代女性生活范围狭小,较少有接触才子的机缘,故而昔时与姊妹、邻伴间知音相识的美好生活经历就成为才女理想和谐的生活体验,也成为才女印刻于心的人生怀想。一旦少女走入现实的婚姻生活,就担负了更多责任,失去了昔时的青春光景与少女情怀。若两性关系并不如意时,女子便会陷入对昔日光景的追忆之中。兰仙出场即表明心迹:“叹仙才如许却遭磨,粉香腮莲花一朵。……我杜兰仙,生成庄貌班才,带得仙风道骨,腰肢步处柳在灵和,气息吹来兰开澧水。十龄擅绣,七步成诗。可恼者鸾罔有偶,工画翠眉;雁塔无名,终残红粉(卷一赠花)。”她也常感叹:“欲觅一知音如梦中人者,正不易也”。当杜兰仙被梨花仙子所吸引,不由产生若为男子之身便可与美人相处之想,但是自己又很快否定了这种暂时的幻想,而且直指男女婚姻中少有和谐的悲剧现实。杜兰仙感叹:“想我杜兰仙纵有经天纬地之才,那有吐气扬眉之日,怎得化为年少乌纱,偕此明妆素艳?啐!我也呆了,见几个富贵人得偕佳偶者(卷二忆梦)。”杜兰仙戏为男装,男装不过是作者于现实生活中希冀摆脱男女之情的一种道具,也是她追怀女性情谊的一种外在掩示。何珮珠采有戏曲创作的形式,藉戏曲“反串”扮演来抒怀的原由,正如学者指出的:“以《梨花梦》为代表的‘效齐眉’之情感呈现与其执着于‘女同’,不如视为女扮男装之后特殊表演。”[9]
值得关注的是,杜兰仙并不希望寄怀于传统的男女两性之恋,她感受到现实中婚姻生活的优游和谐是很难实现的,这是对传统才子佳人观点予以否定,对传统的男女两性关系提出质疑。杜兰仙所构想的情感和谐图景并不源于传统两性关系,而是对此提出大胆的颠覆。她感叹“身世不谐,似闭樊笼病鹤,形骸束缚”,卷五“仙会”中杜兰仙更是直接点明心迹,唱出心声:
【北折桂令】似这证同心,拈花笑恋,煞强如效齐眉,孽债冤牵。为甚粉褪脂蔫,病怯愁淹?只怕梦儿中一幅红绡,写不尽腹儿中无限红绵。(卷五仙会)
举案齐眉的故事强调女子对丈夫之恭敬,丈夫自然也是相敬如宾,这是传统婚姻关系的典范,重在宣扬女子的辅助之德,这看似和谐的两性关系中,实际上是女子独立自我的缺失。传统两性关系中更强调女性贤德,而不是女子与丈夫真正的情感交流、心心相印与平等相处。杜兰仙并不推崇这种传统男女典范,她所憧憬的是逾越性别界限,追求“证同心”的知己之情。
杜兰仙的呼声极为大胆,对传统男女两性关系提出质疑。杜兰仙在男女身份间的游移与突破,正是基于自身身体感觉所带来的满足感,从而产生欲望的情愫。她以一种外在易装来对两性关系提出挑战,借此抒发对现实的无奈与不满,改变现实社会对女性的形塑。现实婚姻生活中女子难以寻求到和谐自由之路,但一腔情感又难以释放,便试图打破传统男女两性的关系之拘泥,探寻别样的生存方式与性别角色表现。秦楼弄玉终得有情之人的美好蓝图在男性伴侣中得不到满足时,便忆起昔时姊妹情谊,遂在女性中寄托爱恋情怀。
杜兰仙的情感处境染有作者何珮珠生活的影子。据同居扬州的王勋《津云小草》序:“张子,元配……张子为名进士孙,故风雅士。”[7]422何珮珠所作《随外子北上舟中杂咏》其一云:“茶具香奁共一舱,米家书画更同装。郎摊诗卷侬挑绣,鍼线都添翰墨香。”[7]424才子佳人共处舟中,“郎摊诗卷”、“挑绣鍼线”似是一幅温馨和谐之景,然而此景背后却是女子的付出。何珮珠虽嫁于风雅之士,但生活的重心仍是日常的生活料理及对丈夫的扶持,红袖添香中也隐含着妻子的无奈。作者通过兰仙之声传达了她对两性生活的失落,婚姻生活束缚了她的个性和才华,但现实的无奈并未羁绊其对感情的自由向往和追寻,她在心灵和笔笺中将一丝热血流洒。
杜兰仙流露出愿以红粉为伴的心理。忆梦之时,杜兰仙行入梨花树下,对花絮语低徊,“【前调】碧唾凝香袖,横波截月秋。你芳容合被烟光透,柔肠合被情丝扭,罗襟合佩鸳鸯扣。缘投争似两情投,怕今生情丝易尽情关陡(卷二忆梦)。”情丝扭、鸳鸯扣的意象带有爱恋的隐喻,透露出杜兰仙对梨花仙子的“两情投”的深切情谊,超越了一般的姊妹情谊。杜兰仙写影后,小鬟轻燕之语道出杜兰仙梦中相遇梨花仙子后的情态:“我想他二人的缠绵缱绻呵”(卷三写影),缠绵缱绻之情是杜兰仙对梨花仙子深厚不舍的情意表现,流露的是以红粉为伴的“证同心”的知己爱恋情谊。
杜兰仙执著于情,追求浪漫理想的情感,渴望建立“证同心”之理想的情感世界。杜兰仙把对女子的“证同心”的情感作为现实男女不和谐两性关系的释放,这种以红粉为伴的爱恋是在对传统男女两性关系的失望中所形成,是对现实的一种颠覆。作者大胆超越传统的男女两性爱情之限,表现出女子追求“至情”别样情感。
《梨花梦》中杜兰仙虽是男装出身,但在现实与梦境中她的性别角色是游移的,男子与女子视角不断转变,流露出内心的纠结与矛盾。杜兰仙以女性身份生活于世,才华不得舒展,个性不得张扬,她在现实中无疑是压抑的;若以男子身份,又感觉到才子佳人举案齐眉之不谐。无论是男性视角中的佳人形象抑或女性视角中的才子期待,都形塑于传统道德规范之中。杜兰仙的身份游移恰是体现出她对传统两性关系的质疑与挑战,表现出她对“情”的突破。杜兰仙有着强烈的自我欣赏与肯定,对感情也表现出热烈的追求,她对同性情谊的爱恋并不是意味着她对传统男女两性关系的否定,而是在现实的男女婚姻没有得到满足之下的心灵寄托与情感释放。
结语
无论是现实中的女儿身,抑或是梦境中的才子气;无论是现实的婚姻,抑或是梦中的情谊,杜兰仙的感情依然无所依恃,魂断梦空。学者研究“拟男”问题时曾指出:“主要在于女性无法情欲自主,既没有拒绝婚姻制度的权利,也没有保守同性之恋的现实空间。”[10]作者即使模糊了性别,现实依然未找寻到出路,对杜兰仙而言只是在梦中释放,而对作者何珮珠来说只能在作品中演绎和谐的情感世界,是一种借助戏剧的虚拟性来对现实人生作出的反驳与抗争。
藉由时空之变与身份转换的书写策略,我们从《梨花梦》中可窥视清代才女的情感世界,现实苦闷压抑使得她们以笔墨去书写人生,将一己情怀寄于空幻的仙乡世界。她们将人生的幸与不幸,将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感叹,对性别意识的觉醒都融于翰墨,以诗文词戏等各种艺术形式,去展现出一代才女的体验与感受,剖析出心灵的压抑与痛苦,追寻心中的理想与憧憬,也对传统社会性别角色提出挑战。尤为可贵的是,何珮珠对两性关系的思考挣脱了男权至上的桎梏,摆脱了传统的男性视角,传统的才子佳人之思,她的探索正是基于女性自身的思索与诠释,建立在女性自我意识的观点之上的。
[1] 恽珠.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卷10)[G].道光年间刻本.
[2] 何珮珠.梨花梦[M]//华玮.明清妇女戏曲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272.
[3] 吴藻.乔影[M]//华玮.明清妇女戏曲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251.
[4] 汤显祖.汤显祖戏曲集[M].钱南扬,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87.
[5] 毛文芳.物·性别·观看——明末清初文化书写新探[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 298.
[6]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28.
[7] 何珮珠.津云小草[M]//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18册).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8] (美)孙康宜.词与文类研究[M].李奭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88.
[9] 蒋小平.女性书写与情爱越界:戏曲史视野中的《梨花梦》解读[J].民族艺术,2013(4).
[10] 华玮.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141.
责任编辑:毕 曼
2016-08-2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世文学中的两性观念研究”(项目编号:10BZW069)。
岳立松(1979- ),女,文学博士,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与文化,园林文学。
I207.37
A
1004-941(2016)06-012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