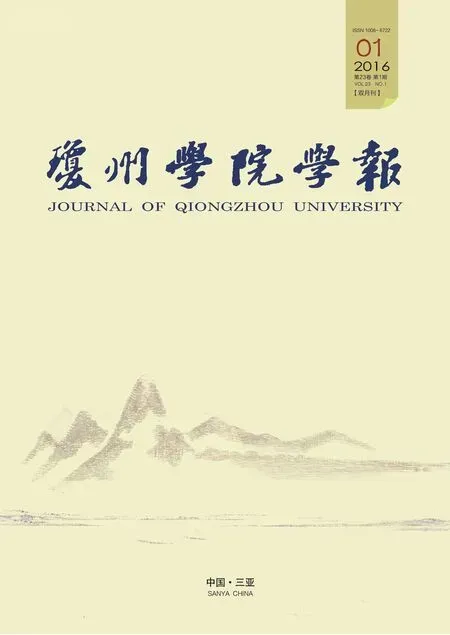苏轼的岭南贬谪生活与《和陶诗》的境界
郭世轩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0037)
苏轼的岭南贬谪生活与《和陶诗》的境界
郭世轩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0037)
考诸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过程,不难发现,苏轼被贬谪到岭南的惠州、儋州之后,《和陶诗》才开始大量出现。这充分说明了艰苦卓绝的岭南贬谪生活经历不仅是《和陶诗》创作动机的触媒和人生境界的转变,而且也是其人生体验的极致和审美体验的升华,同时还是其宦海生涯的反思与总结。而这一视角却少有论者涉及到。因此,研究苏轼之岭南贬谪生活体验与《和陶诗》之境界的关系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苏轼;贬谪生活;和陶诗;陶渊明;审美境界
考诸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过程,不难发现,苏轼被贬谪到岭南的惠州、儋州之后,《和陶诗》才开始大量出现。这就充分说明了艰苦卓绝的岭南贬谪生活经历不仅是《和陶诗》创作动机的触媒和人生境界的表征,而且也是其人生体验的极致和审美体验的升华,同时还是其宦海生涯的反思与总结。而这一视角却少有论者涉及到。这也恰恰是本文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本人不揣浅陋,将心得写出以就教于方家。
一、 岭南贬谪是古代士大夫人生痛苦经历的极限
“岭南”得名于由横跨于湘赣闽与两广的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等组成的“五岭”。“五岭”以南,故称之为岭南或南岭。南岭山脉东西错列,蔓延数千里,多为羊肠河道或崎岖山路,成为南北交通之障碍。毛泽东的《长征·七律》予以诗意化、浪漫化的改写:“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1]红军所履之处皆为艰难险阻,相比之下,五岭显得更加巍峨险峻和气势磅礴。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五岭成为古代政治经济和道德文化等方面极其愚昧落后、野蛮荒凉的象征。与之相对的“北岭”即秦岭则成为中国南北地理气候和长江黄河水系的分界线。“五岭”则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界线。作为唐代设置的“十道”之一,“岭南道”管辖着南岭以南的两广区域。迄今为止,“岭南”依然代表着这片土地并滋生出别具一格的岭南文化。
顾名思义,“五岭”不是山脉,因无统一的走向而成为一片“破碎的山地”。历史上的“五岭”具体方位是:大庾岭在今江西大庾县与广东南雄县接壤处,为粤赣之要道;都庞岭在今湖南永州市蓝山县与广东连州市接壤处,为湘粤之要道;骑田岭在今湖南郴州市区和宜章县之间,为湘粤通道;萌渚岭在今湖南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与广西贺州市八步区、钟山县毗邻处,为湘桂之要道;越城岭在今广西兴安县之北,为湘桂之要道。南岭山脉西起云南云岭,东入贵州为苗岭,中经两广和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边界而直达东海,其中大小山岭不计其数,史书单列这“五岭”大概与秦军的进军路线密切相关。*参见黄现璠、黄增庆《壮族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自先秦以来,岭南就是一个令人产生心理畏惧和情感恐惧的自然空间。先秦往往以百越、桂林郡、安南郡等称呼之。从政治空间来说,这是边缘地带,中原地区才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道德的核心与重镇,而中原之外的地方则显得较为次要和从属。
一般说来,在近代之前的中国历史上,黄河流域的文明在中华文明的成长与塑形的过程中始终起着支配和主导作用。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向周围辐射,主要表现为从北向南、自西向东推进。魏晋南北朝之后,岭南获得进一步的开发,如广州等地已发展成为较重要的城市,但相较于北方的长安、洛阳、开封等繁华之都还相差甚远。即使与长江流域的建康、江陵、九江、武昌、成都、姑苏、扬州、会稽等相比,尚有不小差距。即使到了宋代,文化和经济主要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主,而以珠江流域为主的岭南文化和辽河流域为主的东北文化仍显得极为荒凉与野蛮。相较而言,岭南文化又明显发达和优越于东北文化。这种文化上的优势在历代的科举考试中尤为突出。
秦代末年,赵佗进入岭南而建立越南,在陆贾看来这已是十分遥远的边鄙之地。他则代表汉王朝将先进文化和文明教化带到南越。即使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时代,长沙尚为不受欢迎之地,与帝都长安相比,仍比较落后和偏远。贾谊因受谗害而被流放至此,做长沙王的太子太傅,依然是悲悲戚戚、魂不守舍。这既是对汉皇室尤其是汉文帝的眷恋和思念,也是对荒蛮地域文化的极度不适应。在太子坠马惊吓而亡之际,惊魂未定的贾谊也随之英年早逝。在南朝宋代之际,一意孤行的谢灵运因不满刘宋王朝对自己家族的压制而任意妄为,最终被贬到广州做刺史,结果还是被诬为谋反而被腰斩。即使经过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朝近四百年的发展与开拓,长江流域的南端与南岭一带还是较为荒蛮偏僻的空间。初唐时期的沈佺期与宋之问相继被贬谪到岭南一带;中唐的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变法而在“甘露寺事变”中被一网打尽;“二王”(王叔文、王伾)和“八司马”(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一起被贬往江南和南岭一带*此处“二王”和“八司马”的经历,参见[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40页。。“二王”中的王伓被贬为开州(今重庆开县)司马后不久即病死,王叔文被贬为渝州(今重庆)司户的第二年即被赐死。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李纯即位,“八司马”中的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分别被贬到崖州(今海南三亚)、虔州(今江西赣州)、台州(今属浙江)、永州(今属湖南)、郎州(今湖南常德)、饶州(今江西上饶)、连州(今属广东)和郴州(今属湖南)做司马,长达十年之久。其中的崖州、连州、永州、柳州则属于五岭及岭南之地。元和十年,朝廷终于动了恻隐之心,将“八司马”召回京师,打算让他们在中直机关任职。其中刘、柳二人因在改革中极为激进而得罪了许多人,被视为“二王刘柳”而遭到朝臣的嫉恨。而此时的刘禹锡依然狂傲不已,因一首“玄都观”诗歌《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而再次引起非议,短短二十八个字再次为他“赢得”十四年的贬谪生涯,先后被贬到播州(今贵州遵义),后改为连州,夔州(今重庆奉节)与和州(今安徽和县)。而唐代古文运动的著名人物柳宗元也因此再次被贬到柳州,直至病死在柳州刺史任所。古文运动的另一个领军人物韩愈于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认为佛教于国无益有害而上书《谏迎佛骨表》,因触怒皇帝唐宪宗险被处死,后经裴度等人说情而被贬为潮州刺史,责令即日离京。*此处韩愈经历,参见[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60-2861页。韩愈仕宦半生蹉跎,因参与平淮五十岁才擢升刑部侍郎,两年后即遭此难,一时情绪异常低落,满心的委曲、愤慨、悲伤甚至绝望都灌注于《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潮州州治潮阳属于粤东,距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韩愈只身一人,仓促上路,行至蓝田关口之时,妻儿家眷尚未跟上,只有侄孙赶来送行。全诗充满了生命的绝望和赴死的悲壮:“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2]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潮州的艰难险阻和诗人的悲愤决绝,也间接透露出皇帝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愤恨——潮州是对政敌最好的惩处与流放之地。
而作为韩愈的敬仰者、文学上的追随者,苏轼则因对王安石变法所出现的弊端有所非议,而招致来自新党党羽持续不断的打击报复和拼死倾轧,另外还因不满于旧党全盘否定新法,而招致洛党门生故吏的打击报复。这样,心直口快、嫉恶如仇的苏轼及其门生被新旧党羽诬陷为川党党人而遭受接连不断的政治迫害。直至晚年被贬谪到岭南的珠江流域和南海昌化的儋州,政敌才拍手称快。“苏门四学士”是指北宋文学家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和张耒。继欧阳修之后,苏轼成为北宋文坛领袖,在当时的作家群体中享有很高声誉,一时门生、崇拜者众多,其中他最欣赏和重视这四个人。最先将四人并提并加以宣传、称赏的就是苏轼本人,《答李昭玘书》中道:“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3]145苏轼的推誉使之很快名满天下。“苏门四学士”最先见于《宋史·黄庭坚传》:“(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4]10204后来的贬谪可以见出,“苏门四学士”是荣辱与共的一个文学团体。“(元符三年)二月,先生以登基恩移廉州安置。同时化州别驾循州安置苏辙移永州,追官勒停人雷州编管秦观移英州,承让郎添差监复州在城烟酒税张耒通判黄州,承议郎监信州酒税晁补之佥书武宁军判官,涪州别驾戎州安置黄庭坚为宣议郎添差鄂州在城盐税。四月,先生以生皇子恩诏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又诏苏辙濠州团练副史移岳州,张耒与知州,晁补之与堂随通判,黄庭坚与奉议郎除佥判,秦观英州别驾移衢州,皆先生党人也。按,先生五月始被廉州之命。六月,发昌化,渡海,与秦少游别于海康,七月,至廉。八月,自廉历容、藤,与长子迈相期于广州,须骨肉至乃行。”[5]1708-1709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苏轼的人生之路愈走愈窄,其政治生涯则从山巅逐渐跌至谷底,从炼狱抵达地狱,但在精神之路上却是从炼狱逐渐升入天堂。可以说,流放到儋州,是新党政敌置之死地的结果,也是他苦难人生所可能抵达的极限。事实证明,大难不死,未必就有后福。如果不是热毒对身体的极度伤害,他北返至常州不会那么快就告别人世。
二、 岭南贬谪生活使他反思宦海生涯
苏轼终其一生经历了在宦海生涯中的大起大落,饱尝人世间惯常的人情冷暖和人心险恶。事实证明,在一生的“三起三落”中他依然故我,不改赤子本色,始终奉行的人生准则就是:坚持正义和真理,心直口快,以正为之。常言道,天妒英才。大凡有雄才大略之人都难免恃才傲物、恃才傲人,在桀骜不驯中彰显自己另类的言行,以显得落落寡合。正因为言语行为的出格与别致,所以在为人处世之时才在无形之中触犯了庸众和庸官的利益。在庸众和庸官占主流并掌权的现实语境里,占据要津的庸官自然就会在看不惯的幌子下假正义和大众之名,对英才实施残酷打击、恶意报复。
在宋代,苏轼是异常不幸的一位士大夫,他一生“三起三落”*从苏轼整个人生的政治生涯和挫折过程来看,笔者把这一经历简单地概括为“三起三落”。,“起”得惊人、幸运,“落”得吓人、厄运。这“三起三落”充分说明了苏东坡为人处世的不合时宜和对理想精神的执著不渝。具体说来,“三起”表现为步入仕途、东山再起和再回朝廷,“三落”表现为大难临头、知难而退和一贬再贬。“三起三落”从20岁之后就一直伴随着他,如影随形,直至他彻底离开这个世界。
第一“起”就是一鸣惊人,步入仕途。1057年,20岁的苏轼参加科考,一举成名天下知。在当年录取的388名进士中,他和弟弟苏辙分别以第二(主考官欧阳修误以为是曾巩的答卷,为避嫌而屈居第二)和第五的优异成绩高中。后来收入《古文观止》的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使他脱颖而出,名震京师。考中进士后的第一个职务是担任陕西风翔府判官,品级虽不高(从八品),但他扎扎实实干了近三年。被召回京后,又任职史馆(国家图书馆)博览群书。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他因对王安石新法有不同意见而遭受排挤和打击,先被下派到杭州做了两年零九个月的通判。后来担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太守(1074年)、徐州太守(1077年)、湖州太守(1079年)。步入仕途后的苏轼脚踏实地,逐步得到提拔重用。“一落”就是因“乌台诗案”而大难临头。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转知湖州。“乌台诗案”源于御史台的官员从中摘章寻句的设陷和污蔑(“乌台”得名于御史台院内乌鸦之栖息于柏树)。诗案起因于苏轼到湖州任所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其中对变法的几句牢骚话引起热衷改革之“新近”小人的强烈不满和仇恨。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人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第二个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二人实为新法的拥护者、攀龙附凤的新党红人和势力小人。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宋神宗只得降旨将苏轼交给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文字狱”阴谋便由此拉开序幕。同年7月28日,李定等人奉旨查办,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8月18日,苏轼被押解到京,被投进御史台监狱。御史台两个多月的“根勘”审理使他受尽非人折磨。苏轼被李定等人强加了“四大罪状”即将面临死刑。面对御史台的奏报,宋神宗左右为难。建隆三年(963年)宋太祖赵匡胤所立的不杀柴氏子孙和士大夫、违令者诛杀之的三条誓碑在无形中成为保护士大夫生命的护身符。李定等新党必欲置苏轼于死地的阴谋引起朝野上下的舆论哗然——认为苏轼罪不至死,新旧两派的正直之士纷纷出面营救。迫于各方舆论压力,宋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4]8644,从轻发落。苏轼被关在御史台审讯103天,直接导致他后半生的人生和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乌台诗案是新旧党争语境下产生的文字狱,苏轼不幸成为其中的“替罪羊”,宋神宗用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贬谪。当时属于下等州的黄州贫穷落后,被长江和巴河围得像一口井。苏轼毕竟是难得的人才,特别爱才的宋神宗不想太亏待他,只好在折衷中把他贬到离开封不太远的黄州,基本生活尚有保障。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大起大落,22-42岁之间的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个起落发生在48-54岁之间。1085年4月,神宗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由仁宗的皇后、英宗的皇太后高氏摄政,尽废王安石之新法,史称“元祜更化”。高氏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使得苏轼有机会东山再起,青云直上。苏轼任登州太守仅仅5天就被召回,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短短l7个月中,从戴罪之身的从八品升到正三品,苏东坡跃升12个官阶,创造了另一“奇迹”。但是,因看不惯高太后和司马光尽废新法之举,苏东坡再次坚持原则,反对全盘否定新法,最后因与太后和司马光等保守派的政见不合而主动请辞外放。1089年7月至1091年2月,他再次出任杭州太守。如果说第一个起落是身不由己的话,那么第二个起落则归因于保守派的复兴和他自己的古朴倔强、刚正不阿。
第三个起落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12年(1091年-1101年)。1091年3月,回朝之后的苏东坡当了7个月的吏部尚书,然后出任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扬州太守,再任兵部尚书1个月、礼部尚书9个月。从频繁的上下调动中,不难看出当时朝廷对他的极端矛盾心态。高太后对他极为赏识,希望他能成为制衡新党的中流砥柱,但“冥顽不化”的苏轼又使当政者(高太后和旧党)“恨铁不成钢”,对他的态度可谓爱恨交加、难以捉摸。1093年9月,高太后驾崩,18岁才得以亲政的哲宗心灵发生严重扭曲,从局外人变成了当权者,他刚一亲政就进行变本加厉的政治反扑,对元祜党人实行残酷打击和无情报复。针对苏轼的打击报复接踵而至:降为定州(今属河北)太守仅1个月,又被贬到遥远的英州、惠州,在惠州两年零六个月之后,又被新党顽固派章惇贬到更远的儋州(今属海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儋州是当时极其落后、没有开化的蛮荒之地,是对死刑犯之外犯人的最严厉惩罚。已到天涯海角就无处可贬,这就是苏东坡三起三落、跌宕起伏的人生。
乌台诗案前,苏轼作品的整体风格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发政治豪情。诗案之后的他虽短时官至翰林学士,但作品却少有“致君尧舜上”的豪放超逸,越来越转向大自然和人生体悟。至于晚年岭南流放、谪居惠州和儋州长达六年之久,作品中淡泊旷达的心境愈发明显,秉承黄州时期的风格,呈现豁达恬淡之境。乌台诗案使苏东坡的诗词作品发生明显的转变。在一如既往的“归去”情结背后,诗人的笔触由少年的无端喟叹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在“无端——无奈——无可”的转变过程中渐老渐熟,抵达平淡。题材上由前期“具体的政治忧患”转向后期“宽广的人生忧患”。黄州的贬谪生活使他由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逐渐转向光辉温暖、亲切宽和,变得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文化上,他也从前期的尚儒转为后期的道佛兼尚。前期儒家的社会责任使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和佛教慰藉,以期寻求宗教的解脱。“平常心是道”的佛教启迪使他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真正过上了农夫生活,并乐在其中。风格上也由前期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的大气磅礴、豪放奔腾,转向后期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的空灵隽永、朴质清淡。仕途上的“三起三落”实与他的性格气质和文化操守密切相关。他的红颜知己王朝云在他最困顿时,一直陪伴左右,因此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也最多。王朝云于惠州可能染上痢疾病逝后,苏轼“终生不复听此词(《蝶恋花》)”[6],一直鳏居。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其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为之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7]。这副挽联足以表现苏东坡的本真性格和文化信仰,那就是“不合时宜”的性格气质和“独弹古调”的文化追求。只有经过这几次大的打击和人生落差之后,苏轼才升华为淡泊名利的达人和境界极高的圣贤。在此基础之上,他才逐渐走近陶渊明,并视之为自己的知音。
可以说,在“不合时宜”和“独弹古调”这两点上,他确实与陶渊明找到了共同点。这样,在平淡自然、渐老渐熟的艺术修养中逐渐走进陶渊明的世界。相比较而言,“独谈古调”之“古调”表现在儒家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上。孔子关于政治之论,在他心中深深扎根。“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8]129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8]136从政的前提和动机必须做到身正和心正。因此,要正心诚意,才能修齐治平。少年时期对《范滂传》的认同和对范仲淹的向往,就已经在苏轼的心田播下求真务实的种子。他一生的“三起三落”皆源于求真务实、秉公持正,只有公敌而无私怨。对青苗法有异议,恰恰因为青苗法不利于百姓休养生息,却有利于奸商盘剥纳利;差役法不利百姓而募役法却利国利民,因此他坚决支持后者而反对前者。前者交恶于王安石的新党,后者得罪于元祐旧党。因为前者使他成为”乌台诗案“的替罪羊并饱受身心折磨和凌辱,后者使他成为自己阵营里不受欢迎的人、并被污蔑为川党的首领。哲宗亲政之后进行疯狂的政治反攻倒算,新党小人进行复辟,残酷打击、疯狂报复,他又首当其冲,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可以说,他的政治立场始终如一、从一而终,充满着正气与正义,绝非趋炎附势的小人。倒是新旧党中的许多所谓的正人君子却不乏口是心非、见利忘义、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之辈。
他的失败与悲剧恰恰在于不能“与时俱进”、随波逐流,唯有坚持真理与和正义才招致里外不受欢迎、敌友皆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后果。这也许就是他“常谈古调”的悲剧。正因为常谈古调,所以才如此地“不合时宜”。尽管被贬谪到岭南之后和王朝云皈依了佛教,修建了放生池,但赤子之心依然未改。可以说,他骨子里就是儒家的赤子。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语境之中,他是在持守儒家的教训踏踏实实地做人,而别人则是以儒家为借口实行法家之酷毒,或以儒家为中介践行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之小人勾当。因此,被流放到惠州和儋州之后,他产生闭门焚香思过、明哲自保之想法。这也许就是政敌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产生的“政治疗效”吧!被大赦之后,他请求北归家居颍昌(今河南许昌),不准而改居常州。可以说,岭南的贬谪经历既使他对宦海生涯产生哲学反思,也使他产生皈依田园之念。
三、 贬谪生活催生了苏轼的《和陶诗》
贬谪到岭南生活,不仅是对他政治热情的严重打击,也是对他理想主义的强大冲击。当然,有了黄州团练副使的跌落经历做铺垫,再多一次又如何?但毕竟是一次最大的打击,这对老年的苏轼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导致彻底的晚景凄凉。黄州贬谪恰逢人到中年,一些苦难和磨难尚可承受与抵御。被贬惠州时苏轼将近六十岁,由不惑之年进入耳顺之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历练。好在是耳顺之年,一切苦难和悲伤皆已饱尝,虽从政治巅峰突然跌落,但他早已做好心理准备。这种打击使他政治上万念俱灰,人生体验愈加丰富。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需求是丰富多样的、分层次的。从高到低依次为生存、安全、归属与尊重、爱、认识、审美和自我实现等七个层面的需求。*参见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8页。这些需且大致可分为物质与精神、生理与心理两大类型。相比较而言,对于随遇而安的苏轼来说,只要填饱肚子即可以乐而忘忧。而作为天生的乐天派,苏轼又特别善于营造生活趣味和人生格调,以做到苦中作乐、自得其乐。如同颜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8]59那样,苏轼留给后人的印象是大文学家、美食家和学问家,殊不知其美食家之名乃是苦难所逼迫、锤炼的结果。正因为流放地物质的极度匮乏才逼迫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调整心态、改善生活,营造平衡的心理世界。他所寓居的贬谪地皆是凄凉蛮荒之地,不仅物资极度匮乏而且文化也极其落后,但民风却极其淳朴。无论是黄州、惠州还是儋州皆是如此。
一般说来,人在物质层面的需求获得基本满足之后,精神需求显得极为重要。同时,一个人在遭遇到人事纠纷和权力倾轧之后,常常对现实世界充满着戒心和绝望,而将自己流放到大自然之中。相较于人事的功利倾轧、官场险恶和世故反覆而言,自然而又原始的生态环境使之倍感亲切,当地淳朴坚毅的民风可以给他带来一丝心理安慰。因此之故,他才想方设法,创造一切条件改变生活、改善心态、改变眼光,“东坡肉”“东坡肘子”等名吃才孕育而生,美食家的名声才得以流传。可以说,所谓的美食原料,在当时是极其平常、没有人待见的食物,经过他的加工才使之由“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寓居黄州,在城东荒坡之地开荒耕作以自给自足,将便宜而充足的猪肉买来烹调成美味可口的食物以犒劳自己和家人,“东坡肉”“东坡肘子”的美名由此得以传扬,更是苏轼在困苦生活环境中保持一颗童心和诗心发现美的结果。生活中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可以说,困境催生着作家的美名与境界,苦难孕育出成熟与成功,厄运并不能扼杀审美的眼睛和心灵。一旦生存问题解决之后,诗人就会产生归属感、尊严感,在爱心满足之后,获得对世人尤其是原住民的好感和喜爱。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他更加体认到世界的复杂性和人性的深不可测。岭南茂密的深林和原始生态颇类于家乡眉山的自然风光,淳朴的民风和远离官场污浊使之更加亲近百姓。博爱的心态、敏感的激情以及审美的眼光使诗人更加沉醉其中,忘却人世的苦难和政治的不幸,自得其乐、苦中作乐——劳动耕作、进出寺庙、拜访老友、结识新朋、游山玩水、亲近自然。面对淳朴无害的自然风光和自然人性,孤独苦闷的诗人找到最好的生存方式和体察视角。
相较而言,艺术家在世俗世界不被理解之时往往会倾向于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以寻求理解和深思。愈是孤独的艺术家愈是亲近自然、更易产生宇宙情怀和超越意识。相对于险恶的官场氛围,在美丽无害的山水陶冶下,心灵宁静,畅神怡性,更加热爱人生。迥异于西方个人本位的文化语境,中国文化则彰显出群体本位和集体情结。在西方,如贝多芬遭到来自生活、政治、人事和感情的打击之后,便会投身到荒蛮的森林和旷野以疗治受伤的心灵,使自己愈加孤独,在沉思世界和宇宙的同时愈加对人世失望和憎恨。因此,罗曼·罗兰才会感叹太热爱人类的人有时反而不被人类所理解*参见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121页。,甚至有更极端的哲人和诗人发出对人类的诅咒,如尼采等。而在中国,艾青则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9]。苏轼也不例外。他既不会对世人发出憎恶,也不会对世界绝望,更不会自杀。甚至对于政敌王安石,他还专门赴金陵拜访已遭贬谪的半山居士,长达月余之久。这在古代文人士大夫交往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有人说,中国诗人和艺术家很少自杀都是沉浸在其中并自得其乐的“逍遥”精神惹的祸,而缺少拯救情结和危机意识。*参见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5-56页。其实,这种观点大谬不然,这是西方中心话语的表现,体现了对西方个人本位观念的认同和追崇,也是对暴力美学的体入。*参见颜翔林《暴力美学的象征——以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为例》,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4期,第18-24页。动辄自杀,既无益于世界,也无益于人生,更有悖于上帝造物主的旨意。自杀并不能解决自杀者所迫切要求解决而又时刻困惑的问题,只能说明自杀者对世界的极度绝望和心灵的异常脆弱而已。大体说来,艺术家一旦遭到政治打击和人生苦难而处于绝望之时,常常会面向大自然,以宇宙自然为倾诉对象,将心中的苦闷和惆怅尽情诉说,心底无私天地宽,相互告慰见肝胆。因为大自然具有无限的包容力和亲和力,你会像对待最亲密的老友那样尽情倾诉,不用设防,从而找到归属感、皈依感。李白眼中的敬亭山、王羲之眼中的兰亭、陶渊明眼中的斜川与南山、孔子眼中的沂水莫不如此。贝多芬也在饱尝耳聋疾病侵袭难耐之时,投身于大自然之中。是大自然的森林拯救了他,使之放松身心、缓解紧张,变得身心和谐去迎接更大的创作激情和构思灵感。*参见[法]罗曼·罗兰《贝多芬传》,傅雷译,上海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84-186页。
饱受中国传统文化智慧滋养的苏轼在这方面更是左右逢源,在精神调适、心理愉悦等方面表现出极高的承受力和包容力。每当遇到难以忍受的苦难与打击之时,陶渊明如此,苏轼也是如此。在王朝云的爱情滋润和悉心陪护之下,他悉心向佛,在农耕和家务之余,潜心写作,《和陶诗》就是此时创作出来的。在惠州两年多,他悉心营造自己的“思无邪”斋。在诗文中所表现的知足感和幸福感引来上台新党的异常嫉妒恐慌,还有宰相章惇的疯狂报复,这帮新党小人在秘密捕杀苏轼门生故吏阴谋未能得逞之后,转而把苏轼流放到更远的天涯海角——儋州。再次地流放并未能摧毁苏轼的情志与激情,此时的苏轼在失去王朝云之后,在小儿子苏过的陪伴之下,在痛定思痛之后,在儋州开始真正的田居生活。惠州建房几乎用尽了他的所有积蓄,在海南等于白手起家。他在艰难困厄中另起炉灶,和农民充分融合在一起,体验农耕之乐。远离政治漩涡和官场邪恶之后,他真正地放松身心,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进一步抒写《和陶诗》,同时进行学术研究。
苏轼之所以引陶渊明为同调,是因为陶诗兼有向往归隐、赞美田园和关心现实的双重内涵。以“和陶诗”为中介,苏轼将陶诗风格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创造了新的审美意境。除了涵盖陶诗的题材外,《和陶诗》还书写了在贬所与朋友、田夫之谊,吟咏当地风物,表达了形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士大夫情怀等,有取法众人之长的倾向。*参见张强《从“和陶诗”看苏轼的心态变化与审美追求》,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0期,第126-134页。可以说,正是惠州、儋州的原始自然风景、淳朴民风和身体力行的农耕生活,使他充分体认到稼穑之艰难,在依然保持乐天的心态之下,“任命”思想有所抬升。作为岭南贬谪生活审美体验的升华之物,日积月累的《和陶诗》终于能够得以结集与传播。天涯海角的政治贬谪和谷底体验,使苏轼产生绝地领悟,真正地明心见性,真正地告别轻狂,真正地皈依淡泊,走向和平静谧之境。但由于出身地位、家庭教育、仕途阅历以及自我期许等方面的差异与悬殊,苏轼和陶渊明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尤其表现在审美境界和人生境界上。
四、 《和陶诗》与陶诗在境界上的距离
尽管苏轼、陶渊明两人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相通之处,如胸怀大志,关心黎民百姓,希望建功立业;感情丰富、注重情趣;在挫折中拥有达观的人生态度;真率自然、不拘一格之性情;共同的诗学观点等。但苏轼的《和陶诗》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模拟,其中既有对陶的认同,也有对自身精神的一种超越。*参见贾降龙《和陶诗流播不广原因初探》,载《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77-81页。而“和陶诗”乃是由苏轼首创的合拟古与和韵为一体的新诗体。和韵即以他人诗的韵字,按其原有顺序来做和诗;拟古就是模拟古人之作,重在神似,以期借他人之酒杯以浇胸中之块垒。
但苏轼的《和陶诗》却并非篇篇精品,而是瑕瑜互见、参差不一,自然赢得的评价也是褒贬难一。扬之者谓之“渊明之诗,春之兰,秋之菊,松上之风,涧下之水也。东坡以烹龙庖凤之手,而饮木兰之坠露,餐秋菊落英者也”[10]73。公断者以为“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至于其诗,极有区别:有作意效之,与陶一色者;有本不求合,适与陶相似者;有借韵为诗,置陶不问者;有毫不经意,信口改一韵者。若《饮酒》《海经》《拟古杂诗》,则篇幅太多,无此若干作意,势必杂取咏古纪游诸诗以足之。此虽和陶,而有与陶绝不相干者,盖未尝规规于学陶也”[11]。贬之者认为“渊明所以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费安排处。东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韵而和之,虽其高才,和凑得著,似不费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12]。相比较而言,陶渊明是以“和谐静穆、自然本色”[13]266的诗作而名世,当时是沉寂的,在宋代之前数百年里他留给后人的印象只是“孤生介立”[14]627的隐士和“文取指达”[14]627的文章。宋初诗人王禹偁、林逋等已在诗作中流露出慕陶、习陶之意向。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等则大力学陶。梅尧臣《答中道小疾见寄》云:“方闻理平淡,昏晓在渊明。”[15]王安石则在《寄虞氏兄弟》中传达出对陶渊明的仰慕:“久闻阳羡安家好,自度渊明与世疏。亦有未归沟壑日,会就相近置田庐。”[16]728欧、梅是苏轼敬重的恩师,王安石亦是苏的前辈,正是在时代风气与前人的感召下,苏轼对陶渊明才有了特殊的认知。青年时的苏轼春风得意,仕途畅通,22岁中进士获得文坛领袖和最高统治者的赞赏,名动京师。此时的他以儒家入世思想为主导,积极进取,因此在诗歌创作时,即便偶尔提及渊明,也只是为附庸风雅装点门面而已。据清人王文诰所辑录的《苏轼诗集》可知,“乌台诗案”之前的苏诗约1006首,与陶有关的有38首,仅占3.7%;在为官扬州时已创作了《和陶饮酒》20首;晚年贬至惠州、儋州后,才开始大量创作“和陶”诗。当“和陶”诗增至109首时,他亲自编集并嘱苏辙作《追和陶渊明诗引》(“引”即“序”,为避祖父苏序讳而致)。此后他又续写了15首。*此处及结语中的数字,为笔者统计,参见[宋]苏轼《苏轼诗集》,[清]王文诰辑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文不再出注。苏轼在《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中称:“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20首,今复为此,要尽和其诗乃已耳。”[3]72
早期得志的苏轼学李杜,诗之气象洪阔,一气呵成。谪居黄州的苏轼开始学陶,十分失意的他始生“归隐”之念。晚年贬谪岭南的生活环境、风土人情与陶诗中的南村较为相似,类似的情感体验便油然而生,诗风也向“平淡自然”靠拢,《和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即为佐证。他曾感叹道:“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10]30在对陶诗精准体认的同时,他也表达了深深的景仰之情。但苏轼《和陶诗》的最大价值是超越,即通过学习古人以达到对古人的超越和对自身的超越。苏辙认为“自其斥居东坡,其学日进,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诗比李太白、杜子美有余,遂与渊明比”[5]62。由此可见,苏轼和陶、学陶旨在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情以求有所超越。事实上,追和陶诗者多是“隐士、遗民、僧人、遭贬的或不得志的士人,身居要位的官僚则为数不多”[17]。“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诗作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18]他要学的是陶诗平淡自然、超然物外的真髓,从而参以已意,力图在文与质上有所超越。尤为可贵的是精神超越。
但这确实不易做到,比起诗艺的超越显得尤为艰难。“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10]33苏轼之所以极度称赏陶之“率真”,恰恰源于自身的率真。他在朝执政想谏就谏不畏霸权,迁徙各地欲行则行不畏人言,孤苦清贫随遇而安,超脱凡尘自然真切。陶渊明辞归里,苏轼却宦海沉浮,归意难足。胸中虽存归隐之意,未必如陶老死乡里,即便远在天涯亦可坦然面对、恬然自适。但毕竟在人生体验和自我期许等方面存在着界限,阻碍着苏轼与陶渊明在精神、境界上的无限接近。在和陶、学陶上有神似的一面,但更多地流于形似而显得“强和”“尽和”而不自然。每首必和,为和而和,就已经违背陶诗自然而然的创作动机,是“为文而造情”[19]538,已入于下流,只有“为情而造文”[19]538才显得真切而契合,更能体现出苏轼的艺术才华。宋人张表臣认为:“东坡称陶靖节诗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识此语之妙也。仆居中陶,稼穑是力,秋夏之交,稍旱得雨,雨余徐步,清风猎猎,禾黍竞秀,濯尘埃而泛新绿,乃悟渊明之句善体物也。”[16]279这就说明,陆游所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体认”与“躬行”确实是优秀诗人的真功夫。宋人周紫芝如此评价:“士大夫学渊明作诗,往往故为平淡之语而不知渊明制作之妙已在其中矣。”[20]201“故为平淡之语”恰恰是许多慕陶者的通病,大才如苏轼者亦不例外。宋人叶少蕴也认为:“渊明正以脱略世故,超然物外为意,顾区区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尝有意欲以诗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仿之。”[20]266陶渊明恰恰在自然而然中体现为人与为诗,毫不做作,更不作秀。这是那些“区区在位”的学陶者难以望其项背之处。陶渊明无意于文而文、无意于诗而诗、无意于佳乃佳,这是真潇洒和真自然,足以令那些仰慕者叹为观止。宋人葛立方说得更到位:“陶潜谢眺诗皆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刿目雕琢者所为也。”[20]298“平淡有思致”恰恰说明陶渊明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自然而然,一旦仰慕者“怵心刿目雕琢”皆入下流。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慕陶、和陶者之艺术创作与欣赏动机,多出自于“闲居”以“自娱”,是在借陶渊明之为人、为诗来陶写性情和自我宽慰,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当陶渊明以乘化委运来诠释自己的人生遭际之时,苏轼则吸取孟子的“养气”说之精髓,以“气”与“神”可永存天地间来彻底解构生死存亡之烦扰。“根据现实处境的需要对其(陶渊明)重新进行诠释和建构,在习陶、和陶的过程中,苏轼将自身旷达超脱的精神气质注入到陶诗冲淡平和的外壳中,体现了特有的直面命运和‘应物’的处穷哲理,并使其得以从中排遣情累,自我镇定,达到情感内在超越与净化。”[21]但其间的差距是难以忽视与弥补的,“东坡与陶,气质不类,故集中效陶,和陶诸作,真率处似之,冲漠处不及也。”[20]548胡云翼先生也认为苏陶二人天分不同,而东坡却偏要去追寻陶的藩篱,是“好卖弄天才的毛病”[22]。黄庭坚的《跋子瞻和陶诗》则认为:“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唊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23]二者之间仅仅存在着“风味”的“相似”而已。也就是说,二者仅仅存在着“真率”“坦诚”上的相同,却有着“天性”“个性”之差别:“冲漠”“淡泊”处是陶渊明“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之本然和必然,非恃才傲物、逞才扬己之苏轼所能及。因此之故,陶渊明是自愿退出官场以保全自己的清廉和清平,而苏轼则始终是与官场相沉浮,不愿在京城为官而自求外放而已。不管是京师内外,毕竟是官场。这说明他还是留恋官场、积极用世的。与陶渊明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诸葛亮《诫子书》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参见刘琦《历代小品文名篇赏析》,吉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88-89页。和自觉自愿尚有不小距离。
结 语
综上所述,晚年岭南贬谪生活的物质清贫和精神孤寂使苏轼饱受身心煎熬,在人生境界上进行新的超越。远徙之苦、丧亲之悲交相侵袭:爱妻王闰之、王朝云相继辞世,与朝云所生的第四子苏遁夭亡。接踵而至的苦难让晚年的苏轼对现实产生迷茫,快到生命的尽头他才自觉从陶渊明那里找到精神上急需的终极关怀,并大量创作《和陶诗》以求自我救赎。笔者据王文诰辑录的《苏轼诗集》统计,苏轼在岭南、海南共作诗410首,其中与陶相关的多达160首,占总数的39% ,绝大部分《和陶诗》就包含在其中。仅就这些《和陶诗》的内涵而言,苏轼在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上与陶渊明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和精神距离。“后来诗人苏东坡最爱陶,在性情与风趣上两人确有许多类似,但是苏爱逞巧智,缺乏洗练,在陶公面前终是小巫见大巫。”[13]266同时这也间接说明了一个文学基本原理:每一个优秀作家都有自己难以超越的特性,任何其他作家若想超越前人并完全取而代之是不可能的,哪怕你是最伟大的天才也做不到!这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经历、知识建构、人生体验、生命历练和审美世界等都是不可替代的。正因为如此,苏轼的《和陶诗》才进行了一次了不起的生命体验和审美实践。也许,苏轼的《和陶诗》之意义就在这里,至少它是苏轼岭南贬谪生活阅历的一次诗性见证和审美总结。刘中文曾撰文指出:“陶渊明,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正因为如此,其身后的中国士人无不对他膜拜有加。陶渊明因而成为一把可以打开中国士人心灵文化的锁钥。”[24]此论断在苏轼身上也是适合的。
[1]庆振轩,阎军.毛泽东诗词全集辑注[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59.
[2]钱仲联.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806-807.
[3][宋]苏轼.苏东坡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4.
[4][元]脱脱,阿鲁图.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苏轼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1994.
[6]林语堂.苏东坡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408.
[7]胡虎.苏轼与朝云[DB/OL].(2006-10-26)[2015-12-25].http://blog.sina.com.cn/u/1256844233.
[8]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文鹏,姜凌.中国现代名诗三百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170.
[10]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陶渊明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宋]苏轼.苏轼诗集[M].[清]王文诰,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2107.
[12][宋]朱熹.朱子全书[M].朱杰人,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755.
[1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14][南朝梁]萧统.文选[M].黄侃,平点.北京:中华书局,2006:627.
[15][宋]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94.
[16]李壁.王荆公诗注补笺[M].李之亮,补笺.成都:巴蜀书社,2002.
[17]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J].中国社会科学,2003(6):149-161.
[18][宋]苏辙.苏辙集[M].高秀芳,陈宏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1110.
[19]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38.
[20]何文焕,丁福保.历代诗话统编[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21]丁晓,沈松勤.北宋党争与苏轼的陶渊明情结[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111-119.
[22]胡云翼.胡云翼说诗[M].刘永翔,李露蕾,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72.
[23]任渊.黄庭坚诗集注[M].刘尚荣,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03:604.
[24]刘中文.周作人对陶渊明的文化定位[J].琼州学院学报,2014(6):13-17.
(编校:党 阳)
Su Shi’s Relegation Life in Lingnan and the Realm ofHeTaoPoetry
GUO Shi-xuan
( Literature School,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230037, China)
If we have investigated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Su Shi’sHeTaoPoetry, we can easily find out that after Su Shi’s relegation to Huizhou and Danzhou in Lingnan, a large amount ofHeTaoPoetrybegan to appear.This fully shows that Su Shi’s arduous life in Lingnan is his creation motiv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realm, the acme of his life experience and the sublimation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his reflection and summary of his official career.While this point is seldom studied. Therefore, researc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 Shi’s life experience in Lingnan and the realm ofHeTaoPoetry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Su Shi; relegation life;HeTaoPoetry; Tao Yuan-ming; aesthetic realm
2015-11-29
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AHSKF09-10D79)
郭世轩(1965-),男,安徽临泉人,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及中国文化诗学。
I207.22
A
1008-6722(2016) 01-0015-10
10.13307/j.issn.1008-6722.2016.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