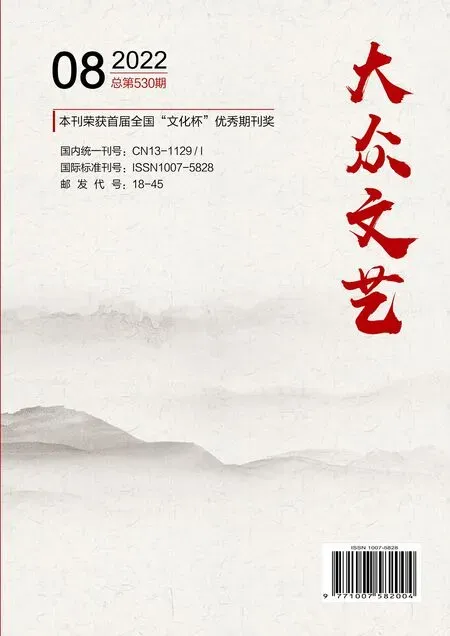浅析林白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以《一个人的战争》为例
胡叶飞 (广西大学 文学院 530004)
浅析林白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以《一个人的战争》为例
胡叶飞 (广西大学 文学院 530004)
作为女性作家,林白的写作既不是沉沦于男权话语的沼泽,不可自拔地为男性书写理想,也不是一位典型的“双性同体”1的作家,去书写“男女平等”的两性世界——而事实上,男女两性的世界从来就没有完全的平等过——林白也正是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林白的小说世界里,女人从来都是男权社会里的作为他者的男性的对象和牺牲。也因此,林白才“固执”地书写着女性自我的“一个人的战争”。本文试图用运女性主义理论,通过对林白的小说文本《一个人的战争》的分析,去探讨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以期能对这部惊世骇俗的作品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父权;两性;女性主义;性别意识
一、 巨大的阴影
在男权社会中,妇女的生存处境始终处于男性权威世界里的巨大阴影之中,林白也不能例外,在她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中,主人公多米正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作者不只一次的在这部作品中向读者暗示,书中的这位女孩,多米正是一个生活在巨大的男权世界的阴影之中的女性,多米的成长历程是林白的成长历程。在这一成长的历程中,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来自于家庭这个社会的几本单位中的“父亲”的形象已经模糊不清,甚至于对作者和文中的主人公多米来说,这一父亲的形象似乎是缺失的。同时,这一父亲的形象的缺失似乎为女性的成长和发展,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客观的环境和契机,但毫无疑问,伴随着她的成长中和成人之后的种种的来自社会的阻碍和拒绝,也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来自于男权社会,即那个无处不在的巨大的“父”的阴影。
1.父权的缺失
虽然林白一再提醒我们,文中的主人公正是作者自己,但我们还是愿意把文学的创作看作是作者虚构的艺术品——而不是一本个人的自传。就文本而言,毫无疑问,主人公多米正是出生于这样一个父权“缺失”的家庭之中。也因此,对于一位儿童而言,在她的童年经验之中,父亲角色的缺失,使得她一方面可以较早的摆脱来自于“家”的“父权”的深刻影响和巨大阴影,另一方面,也使得她得女性意识得以较早的清醒和确立。可以说,这一来自于童年的家庭条件是形成多米以后独立的女性意识和一个人的战争的前提。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将这本作品看作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那就是林白自己本人,作为一位女作家,之所以可以有这样清醒地女性主义倾向,也许一方面是来自于她曾经受过的教育阅读过的相关的女性主义的书籍,也许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对林白而言,她比别的作家甚至是女作家更具有这样的先天“优势”,而这一优势,似乎正是来自于她那独特的家——家的父权的缺失和独特的童年体验——孤独。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一个性别,在男性的眼中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她们只是男性的对象化的存在,是男性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的一个对象,女性永远是一个“他者”,是男性的“第二性”2,“是偶像,仆人,生命之本;又是魔鬼,阴谋家.搬弄是非之人,骗子。她是男人手中猎物,又是毁灭他的祸根。她意味着他不曾有但又特别渴望的一切,他的否定,他存在的理由。”3因此,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妻子除了是妻子之外,也是男性的对象化,某种意义上说,当一个家中“父”的形象已然缺失的情况下,传统的女性母亲已经不再是一个性别意义上的母亲了,她是男性的化身,是“父”的威严的化身,她在“家”对于儿女们所行使的权利已然已经是父亲的权利,她代替的是父亲的角色。在“家”的外部——即那个广阔的父的社会之中,她也同样是为父亲们代言的,她已然不再是一位性别意义上的“她”,而是男权社会中的男性的化身,她的语言、她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她的一系列行为准则已然是父亲的那一套。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多米的成长,虽已摆脱了那个家的父亲的巨大的影响,但同样有面对来自于她身旁的那位母亲的父权威胁的可能性。我们说多米的童年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正好为她提供了来自自身内部的性别意识的觉醒,是因为,虽然在那个家庭之中已然排出了来自于父亲的威胁,但至少多米的母亲,也没有给予多米以多大的影响——不管是出于女性本身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母爱或者是作为“父”的代言人的那种巨大的父权的阴影的影响,因为,作者林白早已向我们说明,这一对母女的关系很是疏远:多米的母亲由于忙于工作而很少顾及多米的生活和个人情感。对多米而言,她与自己的母亲并不“亲”,甚至还有点疏远,母亲于她而言,只是一个存在,这个存在与别的山、石、树、水的存在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同。
总之,在多米的童年之中,父亲的权威是缺失的,而同样作为父亲的权威的化身的来自于母亲的那种“父权”也是缺失的。这种双重的父权的缺失带给她的是孤独、自立和要强。同样,这种孤独有助于她的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5岁的小女孩,她甚至已经开始在那个孤独的封闭的小床上抚摸自己的身体;同样,这种自立和要强的性格也使得她在今后的成长中,在成人社会的拼搏挣扎中,面对强大的男权威严,敢于与之对抗,以至于对抗失败之后,只能走入“一个人的战争”,这是女性的一个人的清醒的“对抗”和“战争”。
2.男权的阴影
诚然,不论多米在她的童年时期如何“幸免于难”地躲过来自于“家”的双重的父权的压迫,但是,最终,等待她的,或者是她将要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强大的外在世界的“父权的威严”,这是她得宿命,她是无法逃掉的。只要她活着,这要她还得为了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去奋斗去追求,她就得面对这样一中现实——来自男性权利话语和秩序的挑战。而最终的结果是她被男权世界拒绝、排斥、中伤:她满怀着豪情走向社会,企图干一番大事业,但终究落得个下场是被欺骗、被强暴、被利用与被背叛,可以说,在她得种种人生经历中,在她与强大的男权世界的接触中,我们几乎处处可见的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拒绝和损害。正所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4,多米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来自父权的威胁。
3.沉沦
可一这样说,在多米被男性社会拒绝和损害的过程中,我么看到的是也是一部妇女在男权社会的沉沦史。这种沉沦可以是激烈的也可以是舒缓的。中国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女性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她们的历史是沉沦着的,是深潜在历史地表之下的。因为,这些深潜在历史地表之下的女性是无意识的,是没有女性自我意识的,因此,这种沉沦是舒缓的,甚至仿佛是女性的与生俱来的历史(如果说,在远古的男权社会之前的女权社会之中,女性是有自己的历史的话,那至少这种远古的女性历史是从来没有被保存下来的)。这样的女性的沉默的历史,一直到五四时期才开始被打破,一大批女性尤其是女作家们,冰心、卢隐、凌叔华等等才开始“浮出历史地表”5,开始书写女性自己的历史。但是,不行的是随着左翼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兴起和意识形态管控的加强,女性对自己书写的历史却不得不中断,甚至一直延续至当代,女性的独立的性别言说的历史已然没有传承下来。这也是一种女性的沉沦史,但这种沉沦是激烈的,就像多米的沉沦一样,这种沉沦来自于男权对女性的反扑——是对自觉拥有女性意识的一种女性的反扑。
仿佛是一个怪圈,一种轮回,男性从来就不想让女性与他们“并驾齐驱”。多米正是被迫的沉沦于这种激烈的男权的反扑之中的牺牲品。
二、个人的独语
我们之所以说,多米的这种沉沦是被迫的,而不像是千年以前的那群沉默的女性的沉沦是不自觉的不意识的,是因为,在面对自己的性别的时候,多米是清醒的。她不是男权社会的代言人,不是男性化了的女性。因此,她也不是几千年以来的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1.清醒地性别意识
多米以一位拥有着清醒地性别意识的女性。很小的时候,当她躲在自己的小床上抚摸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她就清醒地意识到,她是一个女人。她是一种不同于男性的存在,她也是一种性别,是另一种不同的性别。她的身体、她的感觉、她得欲望和快感,都是在她抚摸自己的时候开始产生并变得让她熟悉起来的。
很明显,如果说童年的对自己的认识只是一个萌芽,一个模糊的概念,那么,当她逐渐长大直到成人过程中,一次次来自外部男性世界拒绝和损害早已使她深深明白了自己的性别处境。这种对自己性别处境的认识,多半是与男权世界的两相比较而来的。如果说,童年对自己的认识只是局限于自身,对外界的男性世界还认识不清的话,那么当她成年以后,当她承受了来自男性世界的决绝、排斥、欺骗,经历了怀孕和男人的背叛之后,她早已深深意识到:作为女性,她不是生来“就是女性的,她是被变成的”6,她只是男人欲望和工具,是男人可以随意处置的“物”,作为一种“存在”,她不是构成男权世界的异己的“地狱”7,她还以一种“物”。这就是多米作为一位女性的性别处境,她自己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不利的处境的。
2.欲望的满足
然而,不管现实多么残酷,不管男权社会对女性构成的威胁是多么巨大,但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着清醒性别意识的女人,多米还是深切地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自己的欲望是什么的。作为一个人,她有着几本的生存需求,为此她不得不拥有自己的事业;作为一位女人,她拥有追求美好爱情的渴望,这不论是从心理还是生理上,对她都是一种满足,最为惊世骇俗的是作者林白也好不避讳的描述了多米的性的体验,毫无疑问这也是多米的欲望,是一位女性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多米的欲望。除此之外,多米还有很多的欲望,比如说:对成长、对成功、对获得社会的认可、对最终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等。
作者正是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位,有血有肉,丰满淋漓的女性,从而让我们(亦或是让男性?)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女性也是人,也有着她们的情感、理想、追求和欲望。她们是不同于男性的一个性别(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女性却一直是男性的对象,是“他者”),她们本应该与男性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享有平等的自由,这种平等不只是经济、政治地位上的平等,还应该是性别意识、话语言说方式等方面的平等。
但遗憾的是,从古至今,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似乎从来不曾出现过。现代社会中,当我们一味强调“男女都一样”的时候,实际上正是忽略了两性在性别上的差异和不平等,当我们把“男人和女人都当作是人”的时候,性别上的不平等就已经从在了。多米也一样,她正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女性,在这个看似性别平等的社会里(其实是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多才的多米雄赳赳气昂昂,满怀着期望和梦想,企图大展宏图,但经过一番在男性社会里的挣扎之后,她的一系列的欲望并没有得到满足,相反,她被伤得体无完肤,她只能遍体鳞伤的退缩到“一间自己的屋子”8,进行一场“一个人的战争”。
3.一个人的战争
多米这样一个女孩是值得我们同情的。首先,她是一位在父权的缺失下走出来的一位女性,正因为如此,她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女性性别身份,从这一点上说,她是一位女性的清醒者和孤独者。其次,在于男权社会的接触之中,在她追求自己的正当的权益和欲望的满足之中,她又受到了来自男性社会的种种拒绝和伤害,这一点上,她是痛苦的。可以说,她得痛苦是清醒地痛苦,是孤独者的痛苦,这就不能不令她的痛苦更痛苦。
可以想见,在强大的男性话语和男性秩序面前,作为一位孤独的清醒地女性,她又是无力改变自己的处境的,继续留在男性世界中的结局是只能让她更加痛苦。她也不能像她身边的别的女性那样自觉的继续臣服于男性世界之中,因为她毕竟比她们清醒。这样一来,对多米而言,她似乎只能躲在一个狭小的角落里,像童年时期的自己一样,再次回到那封闭的自我世界之中,来进行一场“一个人的战争”。既然男性已不可靠,既然爱情已不可得,既然事业上处处碰壁,已然男性们无法理解自己,那么,要找到一个依赖,缺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然这样,不如“自己嫁给自己”。
多米正是这样的一个值得同情的女孩。作为女性,林白不禁让我们想起了五四时期的鲁迅,她也是一位最先醒来的先驱,但她是一位女先驱。她想解放自己,解放女性,但终究鼓掌难鸣。
三、 独特的叙述风格
1.颠覆传统的叙事
作为一部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品,《一个人的战争》不仅是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尤其是在叙事方式上,也是对传统男性叙述方式的一种挑战。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贯穿全局。但作者又时而插入第三人称的观点,从侧面观察一位名叫多米的女子的命运和遭遇。“我”与主人公多米代表了林白的不同身分——过去与现在,虚构与现实,内里与外在,血肉与鬼魅,恋爱与被恋爱的身份。人物的主体因此分裂成多种不同可能,创造出极引人的叙述角度。除此,林白在叙事流程中插额外的情节副线;节外生枝,故事中有故事,想象与经验再难分清。像是她在西南边境鬼魅似的与“民国”女子相遇的一段,就是好例子。凡此都足以显示她对实验风格的好奇,而她曾从事电影编剧的经验,想来也给了她不少灵感。分裂的主题,流动的视角,多元的声音,《一个人的战争》俨然视作九十年代女性叙事的特征的蓝本。
2.细腻的感觉特色
除此之外,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林白对感觉世界尤其是女性感性体验的描摹也是入木三分的。她对意像的营造,比如“我说我想把玫瑰放进河里去。女人说:在你的意念中将玫瑰一朵一朵放进河里,意念要非常清晰,要一朵一朵地放,注意不要让他们倾斜、覆灭、沉到水里,要让它们浮在水面上,在意念中将玫瑰放满整条河,直到你闻到它们飘动的芬芳,这个仪式就完成了。”这样的语言,优美细腻,也许只有林白这样的女作家才能写出来吧,男性作家里总是少有的。
四、总结
伍尔夫说,女人要想写作,首先得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意思是说,女性要想解放自己,要想书写自己,首先就得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但是,毫无疑问,横隔在女性解放的道路上的不仅是属于女性自己的“一间屋子”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作为一位精致的女作家,林白始终在就像她作品中的那位多米一样,始终在努力经营着属于自己的一间屋子,同时她也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屋子里面挣扎着的多米。对于多米而言,也许经历了男性社会的拒绝排挤之后,她所拥有的也只有那所屋子了。幸好,在那所屋子里,她还在坚持,坚持着进行着“一个人的战争”。这是多米的命运,也是她得使命,但同时也是林白自己的使命。
注释:
1.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子[M].沈阳出版社 , 1999.08:120.
2.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西苑出版社 , 2004.05:23.
3.西蒙·波伏娃.女性的秘密[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1988.07:70-71.
4.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西苑出版社 , 2004.05:23.
5.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8-9.
6.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西苑出版社 , 2004.05:23.
7.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 , 1998.12:47.
8.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子[M].沈阳出版社 , 1999.08:2.
[1]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子[M].沈阳出版社,1999.08.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3]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西苑出版社,2004.05.
[4]西蒙·波伏娃.女性的秘密[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07.
[5]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2.
胡叶飞,广西大学文学院14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