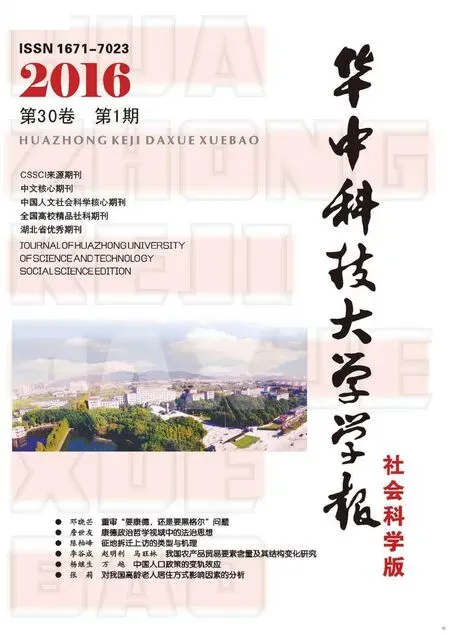国家治理中的国家伦理责任
——伦理本体中诚信底线上慎对亲属容隐和大义灭亲的对立
张国钧,
中国政法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088
国家治理中的国家伦理责任
——伦理本体中诚信底线上慎对亲属容隐和大义灭亲的对立
张国钧,
中国政法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088
摘要:国家治理离不开伦理本体、诚信底线。具体从天伦生诚信、诚信结人伦的伦理生态、诚信生态中,须以正式制度优先敦睦伦理尤其天伦,才从源头有诚信底线。亲属容隐就如此护持诚信底线,而须坚持完善;大义灭亲则反之,而须慎对,至少不支持不鼓励。慎对二者对立,慎重选择,就凸显国家伦理责任:以公道而系统化的正式制度,保障人们在常态中,自由地敦睦伦理;伦理和法律关系这一类两难中,行使优先权而敦睦伦理,从而从本根护持诚信底线;顾全法律关系乃至公序良俗美德;保障伦理永恒,因革传统中式信仰,永葆中华文明可久而可大。这是本体性的神圣责任。
关键词:伦理本体; 诚信底线; 国家治理; 国家伦理责任; 亲属容隐; 大义灭亲
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能力都离不开诚信底线。诚信底线则在伦理生态、诚信生态中,须生态化保障。伦理,在中国一脉千年,一如天伦、人伦、五伦、常伦、彝伦等范畴所蕴涵,是“正常永久……有宗教意味”[1]53,60的本体性关系,“千万年磨灭不得”[2]597;内生伦理永恒。因此,敦睦*敦睦,即制度安排和个人行为共生共荣,努力使伦理亲厚和睦。典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九族敦睦,百姓显明,万邦和睦,是安天下之当安者也。”(《尚书·尧典》)天伦和整个伦理,就是本体性的、神圣的伦理责任,分属、共属社会各界。落到国家,就是更重、更大、更关键的国家伦理责任:植根于伦理本体,以公道而系统化的正式制度,保障人们在常态中,悉心敦睦伦理;伦理和法律关系之类两难中,行使优先权而敦睦伦理,从而从本根解两难达两全甚至多全;始终护持诚信底线,保障伦理永恒和中华文明可久而可大。
国家伦理责任是神圣的本体性责任。其主体是国家,比政府更大、更稳定,不因政府更迭而变,对应着个人及其家庭、组织、社会;对象是伦理,对应经济关系、政治行政关系、法律关系等社会关系;内容是本体性责任,不同于德性、规范、应该等意义上的道德责任,包括名曰伦理责任实乃道德责任者,不同于马克斯·韦伯在准则意义上的责任伦理;范围是国内,对应国际,不是国际法针对国家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
诚信及其近义范畴信任、信用研究很多,没细化、深化到亲属容隐、大义灭亲。亲属容隐研究中,分歧在弥合,共识在发育,和大义灭亲有比较;没揭示彼此对立、利弊、取去,没细化、深化到诚信。国家责任研究没细化、深化到国家伦理责任,没涉及诚信或亲属容隐、大义灭亲。针对这些薄弱点,将其中的问题细分,本文从诚信的伦理本体尤其天伦源头,凸显亲属容隐、大义灭亲的对立、利弊、取去,聚焦并初探国家伦理责任,以期为细化、深化有关研究做准备,促进有关实践。
一、亲属容隐彰显国家伦理责任
诚信底线从伦理本体中,发自天伦。伦理从发生二分为:1)天伦,是天生的伦理,基于血缘因本能而天然生成、本然存在、自然演化,如亲子、兄弟、姐妹,同气分形,无穷绵亘;2)人伦,是人为建构的伦理,从血缘和天伦向外,为不同目的、视需要和可能,随时分形同气而建构甚至重构,从夫妻、收养、朋友到其他各种伦理。从中,天伦生诚信,是诚信源头,有天伦,才有、就有、必有诚信;诚信是天伦之果。诚信源于天伦,才广结各种人伦即所有正常社会关系,是人伦之因,有诚信,才有、就有、必有人伦;人伦是诚信之果——诚信兼为天伦之果、人伦之因,天伦、诚信、人伦天生、内生、自生、共生伦理生态、诚信生态;从中敦睦天伦,就自生诚信底线,才可能从根本上有人伦,有各种伦理[3]26。这是事实、常识、常态。中国史上从尾生抱柱、季札挂剑、孟母三迁、曾子杀猪到晋商徽商护持诚信而义不避死,此伦理生态、诚信生态生生不息。体现在现实中,恋爱、结婚、生育植根于伦理本体,则须有关各方天伦健全、家庭和睦;经济生活尤其现代市场基于诚信,其重要主体企业就始于诚信,成长于诚信,长青于诚信[4]86-87;传统国家若“深诚”(《贞观政要·卷2》《纳谏》)如一则长治久安,现代国家团结基于对“国王或政治上强有力者的忠诚”[5]28;法治国家“总统有权出于自己的信仰(persuasion)任命法官,前提是他们诚实、能干。”[6]185
亲属容隐从天伦、诚信、人伦的生态中,针对并解决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悉心敦睦天伦和亲密型人伦,坚守诚信底线。
亲属容隐针对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任何人违法犯罪则必究无疑,但其亲属(以下简称“该亲属”)若知情,法律上,固然有举证义务,但能否甚至应否履行?若强迫履行则后果如何?伦理上,应否履行、其后果更如何?会通伦理乃至社会,该亲属及其实体态伦理该如何对待,会如何对待?公权力和公众又该如何对待,会如何对待?进一步,该亲属对特定违法犯罪事实若不知情,法律上没举证义务;伦理上,对保护违法犯罪的亲人,有无义务(在其实体态伦理内),有无权利(从其实体态伦理向外,针对他人和社会国家)?若有,是什么权利?甚至违法犯罪嫌疑人在法律上,必依法追究;伦理中,还是否享有其伦理身分,此身分能否改变,能否剥夺?是否内生伦理权利?这些伦理义务和伦理权利、法律义务和法律权利彼此是什么关系?凡此都凸显为尖锐问题,在该亲属,伦理和法律关系交集,须同时维护而两难,其本人其伦理都陷入危境。从更大范围,因伦理作为社会本体普遍存在和起作用,并牵累有关当事人甚至社会、国家陷入两难,危及伦理、法律关系、公序良俗美德。
亲属容隐正视上述交集及其两难:上述交集中主体若不同,则各自履行其有关义务,承担有关责任。可问题是,一定伦理义务、法律义务同时逼临同一主体,须同时履行,但限于行为能力,不可能同时履行:若履行法律义务则势必牺牲伦理义务、破坏伦理;反之亦然。而如果牺牲伦理义务、破坏伦理,则其代价将无法以经济的或法律的尺度估量,更无法弥补。
亲属容隐求解该两难:对该亲属究竟有无该举证义务?若强求履行该举证义务,则对一定伦理和法律关系利弊如何?若不履行则后果如何?包括追究一定违法犯罪行为对一定伦理、法律关系甚至公序良俗美德有何复杂影响?对这些复杂问题仔细考量、慎重权衡孰重孰轻、孰优孰劣、利弊得失,既查清法律事实,依法惩治加害人及其违法犯罪(同时敦睦其实体态伦理,这一点在法律意义上同等重要,在伦理意义上则更重要),绝不默许更不助长犯罪;救济和补偿受害人权益,保护受害人及其实体态伦理,乃至整个伦理包括该亲属的实体态伦理,以尽可能减轻其因惩治加害人而受的不利影响,维护法律关系,保护法益,维护公共秩序;对该亲属豁免举证义务,保证其行使特殊优先权,悉心敦睦伦理,尽可能少损害甚至不损害伦理。其关键是,依法追究违法犯罪的同时,对该亲属,消极地,以正式制度豁免举证义务,不再有责任或服从义务,不举证甚至拒证没违法犯罪,不受法律惩戒;被豁免的举证义务责成公权力和有关知情人履行,以保证追究有关违法犯罪,从根本上维护法律关系,保证司法效率。积极地,有特殊优先权,全身心保护亲人、悉心敦睦伦理,包括保护涉嫌违法犯罪的亲属。
亲属容隐解难达全:会通并顾全伦理和法律关系乃至公序良俗美德,保证该亲属行使敦睦伦理的特殊优先权,使法律关系及其权利义务向伦理及其权利义务让步。于是,既因敦睦伦理而从本根维护法律关系,又在此前提下具体维护法律关系,合法更合情合理地解决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和有关两难,从而顾全伦理和法律关系及有关社会关系,防止牺牲伦理而维护法律关系,或强行维护法律关系却破坏伦理,或简单化地牺牲法律关系而敦睦伦理这一类极端倾向;顾全有关当事人及其私权利、国家及其公权力、违法犯罪嫌疑人和该亲属及其私权利、公众及其公权利等有关各方。
亲属容隐悉心敦睦伦理,从而护持诚信底线。诚信底线植根于伦理本体,源于天伦,存在于伦理生态、诚信生态,须有关必要条件甚至充分条件。该条件的满足须公道制度本乎伦理、出于人性、顺乎人之常情、保障人权。这是法律的重要使命。亲属容隐在中国历史上就以正式制度始于敦睦天伦,从本根、源头护持诚信;扩及从人伦中敦睦夫妻、朋友这一类亲密型人伦,制度化为法律规定,护持诚信,千年一脉。其中,发生中、本体上,敦睦天伦更本真、更本根。正如往圣先贤早就洞悉的,“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抚恤孤而民不倍”(《大学》章十),“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
亲属容隐虽增大司法成本,却悉心敦睦伦理,护持诚信底线,保长治久安,葆文明可久而可大,而利大于弊,须维护和重建。其中有国家伦理责任:健全和完善有关正式制度,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制度,如回避制度、容隐制度、拒证权制度等,以保障人们在常态中,行使言论自由、行为自由,悉心敦睦伦理,避开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从而内生诚信底线;两难中,行使特殊优先权,以敦睦伦理,以特殊方式从本根维护法律关系,辅之以有关各方同时维护法律关系,从而解决两难,达到两全甚至多全,护持诚信底线。
二、大义灭亲反衬国家伦理责任
任何违法犯罪固须惩罚。若在伦理中,惩罚者若是亲人,则彼此举证更遑论攻讦出卖,不论被迫还是自愿,即便举证属实、惩罚公道,都自我背叛甚至毁灭其婚姻、家庭、友谊,直接伤害一定实体态伦理,深层危及渗透态伦理乃至社会伦理,激化伦理和法律关系乃至社会秩序的两难,破坏诚信底线。若因拒证、保护违法犯罪的亲友而受罚,则加倍破坏一定实体态伦理及其至亲真情。凡此都或从源头破坏诚信,或直接击穿诚信底线,无论从伦理及其道德、法律关系及其法律、习俗、宗教上,其恶果比一般案件中因容隐而放过的犯罪更严重。惟其如此,“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尚书·康诰》):敦睦伦理尤其天伦,就有诚信底线,个人就从伦理中护持诚信,甚至一般性守法;破坏伦理本身就是大罪重罪,个人轻则为维护伦理而“违法犯罪”,重则陷入更大罪恶。
大义灭亲破坏伦理,而对诚信底线或从本体和源头破坏,或直接破坏。其一,天伦中,彼此举证,就从本体、源头破坏诚信底线,酿出诚信危机。孔子反对叶公主张的证父攘羊则直,实因那是破坏天伦,从源、从本破坏诚信底线;而诚信作为治国要件,“信则民任”(《论语·尧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不容破坏。其二,人伦中,尤其夫妻、朋友这一类亲密型人伦中,若彼此举证,则直接破坏诚信底线,酿成诚信危机,破坏正常社会关系。其三,有人被强迫、被利诱,为私欲甚至罪恶目的出卖亲人,破坏诚信底线,违法犯罪。无论天伦、人伦中,言论自由,保障人们出于人性、本着良心,坦陈真实意思并自主担责,才有诚信底线。然而大义灭亲强制下,有人竟违背人性、昧着良心而投机、谋利(经济利益、加官进爵或某种“荣誉”),助长虚伪、冷漠、残忍,甚至“忘亲遗义”(《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以直伤义”(《左传·昭公十四年》),而无异于“倡导背叛……不是在预防犯罪,相反,倒是在增加犯罪”[7]63,或蚕食或鲸吞伦理本体、诚信底线——对至亲都没诚信甚至出卖,会对谁有诚信而不出卖?甚至有人作恶,“杀亲益荣”(《左传·昭公十四年》)、卖友求荣,迫害无辜,为虎作伥,沦为工具、打手,“灭亲害义”*欧阳修语。欧阳修被贬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见朱熹编《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二之二),载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5页。。其四,击穿罪犯对其亲属、司法机关甚至全社会的特殊的诚信底线。那是改造罪犯的特殊的积极力量。罪犯如认为竟被至亲出卖甚至背叛,则其诚信底线、心理底线都被击穿,陷入绝望,改造减效,甚至铤而走险,重新犯罪甚至恶性犯罪。简言之,“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孝经·五刑》)。
大义灭亲违背人性,而破坏诚信底线。亲人在常态中彼此呵护;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中,彼此容隐,哪怕众叛,也不亲离。这都是人性的伦理层面。“父子之亲,夫妇之道, 天性也, 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 诚爱结于心, 仁厚之至也, 岂能违之哉!”(《汉书》(卷8)《宣帝纪》)“虽有罪,犹若其不欲服罪然”(《公羊传·文公十五年》),“父不可弃”(《左传·昭公二十年》)。对人性的这一类侧面,法律只有承认、尊重、保护,而面对常人及其行为能力,为常人立法,保护权利,设定义务,才有实效。“法律有关夫妻不得互相做证的规定,似乎就是对家庭完整性和例外性的最后的正式承认的情形之一”[8]325。如果违背人性、脱离现实、对公民拔高要求,甚至超现实超人性地硬框现实的人及其行为,强求亲属举证、参与亲自惩罚亲人,则一方面,从根本上、社会结构中,从人性深处,破坏力图维护的公共秩序;另一方面,强制人人须不利于亲属,从而须不利于自己。果若如此,则怎能成为法律!“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行为。……这真是一项罪恶的法律。它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却是风纪的泉源。”[9]176
大义灭亲强人所难,而破坏诚信底线。其要求超出行为能力,常人做不到,会尽可能规避。司法实践中,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甚至逃避作证的比较普遍,就是在抵制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亲属作证义务。高压下,被迫牺牲亲人亲情,消解诚信,也势必普遍违反,须大面积惩罚。但违者众多,罚不胜罚。于是,或者,有关要求自我否定,沦为废纸,毫无严肃性,更没尊严。或者“加大力度”甚至严刑峻法,强制遵守,则管理成本奇高,而被压垮;破坏伦理、破坏公共秩序、破坏诚信底线,这一类代价更难以估量,难以弥补。“驱之以法令者,法律积而民风哀。”(《汉书》(卷48)《贾谊传》)此风所至,“矜伪不长,盖虚不久”(《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运,就同一座直接横断河流的堤坝一样,或者被立即冲垮和淹没,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涡所侵蚀,并逐渐地溃灭。”[7]30此时要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国家安宁,则没基础,亦不可能。
大义灭亲虽会提高行政效率、司法效率,却破坏伦理本体,破坏诚信底线,丧失合法性合理性,凸显国家伦理责任:不能让其成为法律命题,甚至不能成为政策规定,充其量只是行政上偶尔应急以解特殊危机的权宜之计或特殊要求,不能制度化。若陷入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义无疑须坚决维护,但须始终围绕常人,基于常态,以常人之制规制有关行为,尽可能解难达全。对有关危机,须靠建立健全危机管理体制及其预警机制、应急机制,而不能靠强求有关当事人“大义灭亲”。即便有人自愿自决,无疑出于自由意志、崇高理想,是高尚行为,须肯定和保护,深层上却因破坏伦理、危及诚信底线,仍须审慎对待。
三、对极中敦睦伦理护持诚信
底线的国家伦理责任
亲属容隐敦睦伦理,护持诚信底线,合法性、合理性充足;大义灭亲则反之。正视此对立,以公道的正式制度,激活亲属容隐;慎对大义灭亲,至少不支持、不鼓励。从而悉心敦睦伦理、护持诚信底线,这是国家伦理责任,发自中国传统、满足现实需要。
最晚从春秋始,往圣先贤就疑大义灭亲、立亲属容隐[10],并逐渐培育出伦理豁免等制度,以保伦理本体、伦理永恒,从容应对各种考验,葆文明“恒于中国”(《穀梁传·哀公十四年》),千年一脉,独一无二,内生传统中式信仰。此进程中,周制礼作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使有恩以相洽,有义以相分,而国家之基定,争夺之祸泯焉”[11]475,兴盛700多年,并影响以后各主要朝代;秦等王朝强行大义灭亲,“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慎子》逸文),强大一时,却迅速覆没。其鲜明对比以宝贵经验、沉重代价一再昭示,悉心敦睦伦理,攸关长治久安,攸关文明常青。百年来,否定从亲属容隐到伦理豁免等传统,却肯定大义灭亲,于今尤烈。一沉一浮,形成破坏性合力,破坏伦理本体和彼此亲情,或间接或直接破坏诚信底线,破坏公共秩序,酿出伦理危机、诚信危机。要克服诚信危机,就须悉心敦睦伦理、培元固本;要克服伦理危机,就须完善有利于此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清除不利于此的制度和做法。惟其如此,慎对亲属容隐、大义灭亲及其对立,就从本体、源头上护持诚信底线,进而敦睦伦理、保护伦理永恒,因革传统中式信仰。国家于此有神圣的本体性责任。
现实中,发扬光大伟大传统,总结经验、汲取殷鉴,从影响甚至决定国家盛衰兴亡的生态化条件中,悉心敦睦伦理、出于人性、顺乎人之常情、受伦理制约,根治百年来战争、政治运动激化斗争之弊,根治近几十年来伦理分化、市场片面化发育之弊,根治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违法犯罪,根治对伦理本体的侵害甚至威胁,清除其危及国家稳定、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文明演进之害,因敦睦伦理、护持诚信底线而保障长治久安、社会良序、文明常青。凡此都攸关社会的、文明的、国家的命脉。国家于此有神圣的本体性责任。
国家伦理责任多是“消极”责任,常态中,受伦理制约,须维护伦理自治,而不能直入,更不能楔入或嵌入;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中,须积极作为,但不能轻易介入,同样宜从外部而须从外部提供制度保障。当且仅当伦理内讧且持续加剧、陷入危机,无力自调节时,需国家积极介入,但同样受伦理制约,须尊重伦理特点和伦理主体的意愿[3]29。这是伦理责任,也涉及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甚至经济责任;其圆满履行,个人有责,有关组织有责,全社会有责,国家更有责,并且如上所说是神圣的本体性责任。这是亲属容隐的意蕴所在,也是须慎对大义灭亲的意蕴所在。至于其他维度上,亲属容隐、大义灭亲是什么关系?和本文是否兼容?若是,怎么兼容?若否,则如何竞合或选择?凡此须另行细究、深研。
参考文献:
[1]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载《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2] 《朱子语类》(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 张国钧:《敦睦伦理以坚守诚信底线的国家责任——国家治理须应对伦理分化深层的天伦分化及其冲击》,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4] 张国钧:《诚信是企业生命力的必要因子——兼论晋商徽商诚信断裂的教训》,载《伦理学研究》2012年第4期。
[5]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 Ronald Dwokin.TakingRights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7.
[7]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8] (美)约翰·J.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9]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0]张国钧:《<春秋>怀疑大义灭亲而发育亲属容隐——从<春秋>记诛庆父及其微言大义切入》,载《孔子研究》2014年第2期。
[1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责任编辑吴兰丽
The State Ethical Responsibility in State Governance
ZHANG Guo-jun
(SchoolofBusiness,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Beijing100088,China)
Abstract:State governance, Commonly, depends on the ethical substance and based credibility, and specifically, has to harmonize ethical relation, especially Natural One (Tianlun) and holds based credibility by official system. So it is necessary to insist on and improve mutual-concealing among the relatives, and take carefully placing righteousness above family loyalty. In this way state ethical responsibility stands out.
Key words:ethical substance; based credibility; state governance; state ethical responsibility; mutual-concealing among the relatives; place righteousness above family loyalty
作者简介:张国钧,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伦理、管理伦理、法伦理。
收稿日期:2015-11-20
中图分类号:D03; 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6)01-01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