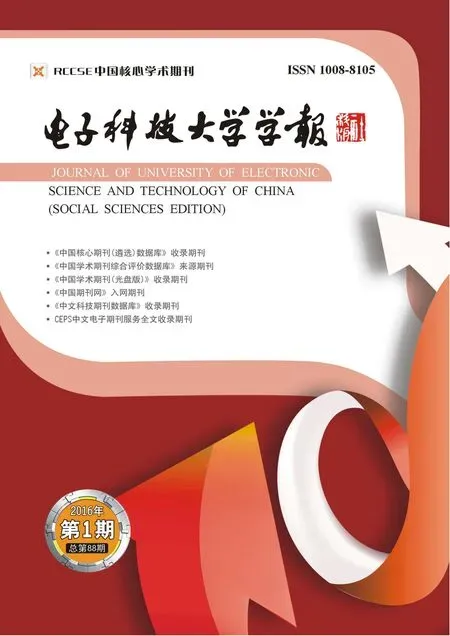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印度女性
——萨尔曼·拉什迪小说中的女性群像
□王 静石云龙[.苏州大学 苏州 5006;.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 006]
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印度女性
——萨尔曼·拉什迪小说中的女性群像
□王静1石云龙2
[1.苏州大学苏州215006;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210016]
[摘要]在塑造和表现权力关系时,性别往往成为后殖民作家们热衷描写的对象。在后殖民文学中,两性关系往往成为前殖民地与西方宗主国关系的隐喻。作为流散作家的拉什迪,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也采取了这一策略。在他的作品中,男性丧失了两性关系中的核心地位,从中心退缩到边缘,而女性则大多摆脱传统文学中被动、柔弱、依赖、失语的模式,从边缘走向中心。
[关键词]女性;边缘;中心;拉什迪
在塑造和表现权力关系时,性别往往成为后殖民作家们热衷描写的对象。女性与男性力量悬殊对立的状况最适合被用来呈现统治与被统治之间关系。在后殖民文学中,两性关系往往成为前殖民地与西方宗主国关系的隐喻。前殖民国家与女性一样出于边缘、弱势地位,而西方宗主国则像男性一样处于中心、强势地位。后殖民文学表述权力关系时,常指称西方为“他”,含男性阳刚意味,喻指其主体地位;东方则被冠之“她”的称谓,含女性柔弱、依附男性存在的意味,喻指边缘从属地位。传统西方文学在叙述时,常常以居高临下的男性视角遥望东方殖民地国家,以窥淫式好奇对东方女性的异国情调投以贪婪的目光。在不少东方游记中,东方女性成为白人男性幻想的对象:她们性感美丽却愚蠢野蛮,面对西方男性时温顺无比。这样的表述无疑更加激发殖民者高高在上的男性意识,强化自己的男性力量,为征服女性——落后的东方殖民地而编造借口。
流散的后殖民作家在创作时往往颠覆这一传统,通过解构西方作家笔下的东方女性形象来达到消解西方文化中心、从边缘地位突围的目的。作为流散作家的拉什迪,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也采取了这一策略。在他的作品中,男性丧失了两性关系中的核心地位,从中心退缩到边缘,而女性则大多摆脱传统文学中被动、柔弱、依赖、失语的模式,从边缘走向中心。在《午夜的孩子》中,原本为家中顶梁柱的父亲因中风而瘫倒在家,而原先一直照顾家庭的母亲则走向社会独立经营宝石店。小说中女性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意味着从边缘走向中心,而男性则从社会退隐至家庭,象征着从中心走向边缘,这一嬗变较为合理地解释了拉什迪笔下的两性关系。
一
拉什迪小说中出现一种独特的现象:主人公或叙述者均为男性,但小说潜在的叙述主体却是女性。在叙述两个家族之间恩怨的小说《羞耻》中,读者看到的是野心勃勃、权力争夺、背叛与复仇,分明是一部“几乎过度男性化的传奇”。然而,拉什迪却宣称,“这是一部关于苏菲亚·奇诺比亚的小说”[1]。女人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主角,作者认为女人从故事边缘走向中心,“接管了这部故事”,迫使他从“女性的棱镜”来观看被折射出的“男性情节”[1]。在《摩尔最后的叹息》中,拉什迪则更明确地让女性成为小说叙述的中心,声称“女人现在正在进入我的小舞台中心……她们,而不是那些男人,成为战争中真正的主角……”[2]。
印度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代表人物是《午夜的孩子》中的纳西姆。虽然整部小说围绕着萨里姆以及湿婆两位男性展开,但在故事的前半段中最为生动出彩的形象却是被称为“母亲大人”的纳西姆。她是富有的地主之女,成长在传统家庭,接受了传统宗教和文化教育。根据印度传统,姑娘的身体不能被陌生男人看到。她生病需要看医生时,竟然藏身床单之后,将需要检查的部位依次透过床单上的孔洞呈现给医生查看。纳西姆的形象因由众碎片拼凑而成而显得不完整。接受了西方教育、代表西方文明的阿齐兹,透过床单孔洞中显现的碎片化幻象,爱上了举止规矩、恪守传统、东方传统文化的代表纳西姆。这则事件实则象征了西方对东方异域文化的向往与倾慕。
传统东方女性与西方文化的男性代表的结合,是作者表现边缘与中心转换的极佳案例。纳西姆顺应父母之命嫁给阿齐兹后不久,传统东方与先进西方的冲突就开始爆发。拉什迪将他们婚后生活形容为“杀伤性极强的战场”。新婚第二夜,在阿齐兹看来合理的要求让保守传统的新娘感到羞辱而惊恐。她没有屈服,没有迎合丈夫,而是发出尖叫以表示抗议,结果,代表东方女性的她在这场冲突中取得了对代表西方男性的胜利。这场胜利意义重大,注定象征着阿齐兹永远无法获胜。拉什迪刻意选用了几个经典事件,强化了这种冲突后边缘与中心的转换。例如,印度妇女习惯用莎丽将身体严实包裹起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阿齐兹却要求妻子摘下面纱做现代人,恪守传统的纳西姆认为这无异于“光着身子在陌生男人面前走路”[3];阿齐兹请来摄影师为全家拍照,纳西姆则认为在外人面前抛头露面是奇耻大辱,更不用说将这耻辱记录下来。在子女是接受传统教育和宗教信仰还是学习外语和西方知识问题上,这种冲突自然更为激烈。纳西姆这位恪守传统信仰的典型印度女性,用自己的信仰构筑了一座堡垒,凭着自己异乎寻常的坚定抵御着西方文化的侵蚀。在这一系列东西方之争中,纳西姆代表的东方成为永远的胜利者,成功地抵御着西方文明在家庭内部的入侵,而阿齐兹代表的西方则无奈地甘拜下风。不仅如此,当阿齐兹将纳西姆为孩子请来的宗教导师赶走后,纳西姆决定对阿齐兹实施“饿饭”惩罚,迫使阿齐兹外出吃饭。“母亲大人”用她绝不退让的行为成功地实现了边缘与中心的转换,自己成为家庭的中心,而阿齐兹则处于家庭的边缘。
纳西姆这个恪守传统甚至有点顽固的印度女性,在拉什迪笔下闪烁着别样的光彩,这种光芒使得小说中其他男性人物在她面前黯然失色。她从小说的边缘走向中心,而将原本居于中心的丈夫驱赶到边缘,彻底告别了自己的“他者”处境,象征着东方殖民地在与西方宗主国的交锋中摆脱了“他者”地位,走向中心。
纳西姆首先作为一个由碎片拼凑的幻象呈现,吸引了代表西方文明的阿齐兹,却又完全异于其想象中充满异域风情的形象,告别了西方文化的“他者”想象。在西方人脑海中,对于穆斯林女性的印象最典型的就是以面纱遮面、包裹严实。她们是“被隔绝的”,只生活在“很狭小的生活范围中”。因此,许多西方人相信在伊斯兰教中,女性是“最典型的处于屈从地位的象征”[4]。她们通常在西方人笔下被描述为被迫的、屈从的、对丈夫有着极强依赖性。然而,拉什迪笔下的纳西姆却打破了这一“他者”想象。尽管有着戴面纱、与世隔绝的表象,纳西姆却与西方想象中的女性他者相差甚远。在与丈夫的斗争中,她一再固守传统,寸土不让地坚守家庭这一阵地,在代表西方文化的丈夫面前夺得主动权与控制权,彻底颠覆了被动、屈从的“他者”形象。
二
拉什迪笔下的女性除了在家庭这个小圈子里逐渐取代男性走向中心之外,还逐渐朝着政治这个向来由男性掌权的领域进军。这些女性一扫以往女性在政治上边缘化的形象,开始争夺并且掌握政治权力,在政治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羞耻》中,女人和政治结合在了一起:苏菲亚·奇诺比亚虽然是羞耻的化身,却成为印巴分治中千百万人的梦魇;她是印度政治中的核心人物,摆脱了女性在政治上的边缘地位。最能体现女性与政治力量结合的是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这位“立场坚定、政治方针强硬”的铁腕女领导人成为拉什迪笔下最热衷的描写对象。在印度历史上,英迪拉·甘地的追随者曾声称“印度就是英迪拉,英迪拉就是印度”。这位“铁娘子”一度被视为“印度一群老妪内阁中唯一的男子汉”[5]。拉什迪虽然在小说中讽刺地称甘地夫人为“寡妇”,批判她在紧急状态中犯下的错误,但这也无法掩盖甘地夫人作为一名女性,已从传统的相夫教子角色中转变,与政治结合成为力量的化身。
拉什迪文学世界中的女性群像,与西方文学中缺乏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女性有天壤之别。她们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新女性的代表,是英迪拉·甘地式反传统的新女性。《摩尔的最后叹息》中的奥罗拉就是这样一位女性的典型。她坚强、独立并且果断,没有把自己局囿于家庭,也并未把男性作为自己生活的依靠和中心,而是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寻找女性自我的地位和价值。西方文学中普遍呈现的印度女性的脆弱、优柔寡断、过份依赖男性的特点在她身上丝毫没有得到体现。奥罗拉自幼就流露出与印度传统女性相异的品质。奥罗拉年幼时爱憎分明,曾因母亲关系而冷酷旁观过患病倒地的奶奶。成年后的奥罗拉在1942年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曾一度被捕入狱,而这一经历使她成为民族运动英雄。现实生活中的奥罗拉独立自主意识极强,她一反女性不能选择结婚对象的传统印度文化习俗,克服一切阻力与年龄相差悬殊的亚伯拉罕结婚。婚后发现丈夫出轨后,奥罗拉并未因印度的一夫多妻习俗而隐忍,而是秉承自由平等的信念,以报复丈夫不忠的心态拥有数名情人,甚至曾传出与印度总理贾·尼赫鲁有染。众所周知,传统的印度女性是苦难和忍辱负重的代表,印度神话中有许多女神的忠贞故事,她们即使在遭到误解和抛弃时仍然深爱着丈夫,表现出顺从、隐忍的品质。然而,奥罗拉却无法忍受丈夫的不忠,并用以牙还牙的方式向丈夫发起报复,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意识。
三
在拉什迪笔下,男性从故事中心退居边缘,需要依赖女性的“棱镜”才得以叙述自己的故事。与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相反的是,男性逐渐趋向边缘化、去势化,表现为男子气概的丧失,流露出懦弱、无能的特征。
小说《羞耻》中,表面上的主人公奥马尔已沦为一个“边缘人”,一个甚至“站在自己生命侧边的观望者”[1]。拉什迪在描绘他的形象时全程使用灰色:灰色西装、灰色礼帽、灰色领带、灰绒面革皮鞋、灰丝绸内裤,为他的隐匿、边缘状态作出最好注脚;小说《午夜的孩子》中,“母亲大人”纳西姆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丈夫阿齐兹则黯淡地消失在小说的边缘地带,趋于沉默;小说《摩尔的最后叹息》中,与妻子奥罗拉相对的亚伯拉罕一反男性的阳刚形象,成为“忍辱负重”的化身。他因不忠而愧对妻子,认可妻子的报复,对妻子的不忠默默忍受,甚至对她的爱有增无减。正如印度传统文化中那些完美的女性形象,亚伯拉罕总是怀着崇敬的心理对待妻子,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完全颠覆了印度传统,丈夫从中心撤退到边缘,而妻子则走向中心。
拉什迪笔下去势化男性最具代表性的是《午夜的孩子》中的纳迪尔·汗。他是自由伊斯兰协会创始人米安·阿布杜拉的副官。后者遭暗杀后,他在逃亡中机缘巧合地躲进阿齐兹家,藏身阿齐兹的地下室,惶惶不可终日。暗杀事件过去很久后,纳迪尔依然每天被噩梦所纠缠,无法回到现实过安静的生活,竟然在阴暗的地下室过了三年寄生虫般的生活。拉什迪通过小说其他人物对这种男性进行了无情的评价:“连男人都算不上的胆小鬼”“傻里傻气的胆小的胖子”“耗子”和“蚯蚓”,清楚地表现出对这种去势男性的蔑视[3]。他还用纳迪尔与穆姆塔兹的婚后无性生活加强了这种态度。男性在此丧失了传统印度文化中勇敢无畏、刚毅不屈的男性气概,沦落为懦弱的胆小鬼。
西方传统文学中的男性常被描述成救世主,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起着将女性从苦海拯救出来的作用。然而,在拉什迪的小说中,这一英雄救美的模式被彻底颠覆,女性在关键时刻往往成为男性的依靠和支撑。在《羞耻》中,毕奎斯与海德的相遇一开始充满了传统的英雄主义气息。毕奎斯因父亲的戏院被宗教狂热分子炸毁而无家可归,她只裹着一条残缺不全的穆斯林纱布,几乎赤裸地开始了流亡生活,最后因受不了赤裸的耻辱而晕厥。上尉海德的及时救助,犹如童话中王子一吻将公主从咒语中拯救出来,英雄般地解除了毕奎斯的羞耻,使后者心存感激。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经历了丈夫情感上的背叛与政治上的政变后,毕奎斯意识到,女性在婚姻中不能完全依靠丈夫,丧失主体地位。在小说的结尾,海德政权被推翻。混乱中,毕奎斯让海德换上女人的面纱与黑色长袍,躲过反对者的袭击而逃生。如果说毕奎斯与海德的初次见面充满了童话色彩,落难无助的公主被王子拯救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小说的结局又彻底颠覆了这一传统,落魄的王子只有在公主的帮助下才得以逃脱危险。
结语
在拉什迪笔下,虽然偶尔也会流露出西方殖民者观看东方时的传奇色彩,但从整体上而言,他所刻画的女性形象仍然不同于西方文学中的东方女性。传统印度女性所必须的品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相当多的女性角色与传统文化中理想化的温顺、贤惠女性形成了强烈反差。传统的、边缘化的女性在独立后的印度社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女性不再是男性言说的对象,也不再是沉默失语的他者,而在果敢坚毅的女性形象的对照下,拉什迪笔下的男性们丧失了英雄气概,变得懦弱、犹豫和狭隘,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传统地位关系被彻底颠覆。拉什迪笔下的女性有别于西方作家笔下东方化的女性形象,摆脱了传统女性被动、阴柔、丧失话语权的形象模式,具有重塑印度的文化隐喻意义。正因如此,美国学者加亚特里·戈皮纳斯(Gayatri Gopinath)将拉什迪小说中女性的崛起以及“男性气概的丧失以及性无能”视为后殖民处境的鲜活隐喻[6]。拉什迪通过创造与东方主义文学中的女性完全不同的形象来颠覆传统思维习惯中“东方-女性,西方-男性”的二元对立,从而消解西方自以为是的中心地位并颠覆文化殖民霸权。
参考文献
[1]RUSHDIE S. Sham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3.
[2]RUSHDIE S. The moor’s last sigh[M]. London: Vintage Books, 1995.
[3]RUSHDIE S. Midnight’s children[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52.
[4]EL-SOLH C F, MABRO J. Muslim women’s choices: Religious belief and social reality[M]. Oxford: Berg Publishers, 1994: 187-188.
[5]DAVIS R H. Women and power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7: 20.
[6]DAIYA K. Violent belongings: Partition, gender, and national culture in postcolonial India[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编辑邓婧
Fromthe Peripherytothe Center——Women in Salman Rushdie’s Novels
WANG Jing1SHI Yun-long2
(1.Soochow University Soochow 215006 China; 2.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In shaping and representing power relations, gender has always been a favorite topic of postcolonial writers. In post colonial literatur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is often a metaphor of former colonies and western suzerains. Salman Rushdie, a diasporic writer, has also adopted this strategy in his novels. In his writing, the male characters lose the core position in sexual relations, retreating from the center to the edge while women, different from those passive, weak and dependent images in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literature, are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enter.
Key wordswomen; the periphery; the center; Salman Rushdie
[作者简介]王静(1985-)女,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石云龙(1955-)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英国移民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11WWB004).
[收稿日期]2015-01-11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DOI]10.14071/j.1008-8105(2016)01-01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