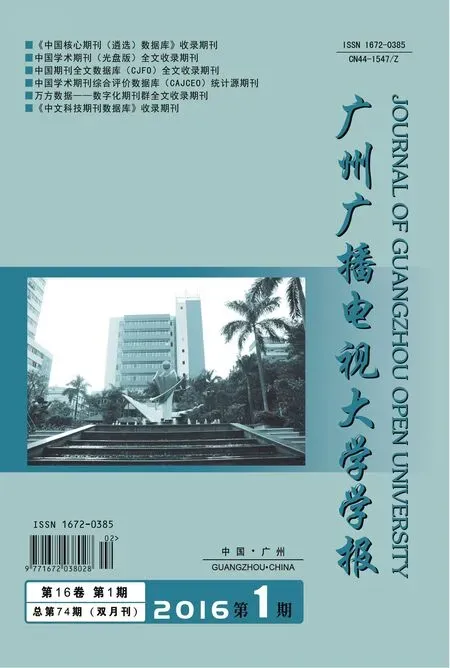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扩大适用成因及罪质
王 杰(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扩大适用成因及罪质
王 杰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摘 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本应行使保障公共安全的职能,但案情的错综复杂,法律关系的难以梳理使得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适用兜底。但是即使是罪名兜底化,也能够按照犯罪构成不法且有责的位阶顺序进行兜底原因的解析。防止罪名兜底化应使人身安全应当作为公共安全的核心与保护法益逻辑前提,并按照法条关系进行同类解释,并利用罪数原理妥善解决与相关犯罪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危险方法;公共安全;罪质
自2007年7月至2008年8月,被告人张玉军、张彦章为牟取非法利益,生产、销售含有属于化工产品三聚氰胺的蛋白粉,并将之分销到石家庄、唐山、邢台、张家口等地的奶厅(站),并被部分奶站添加到售与三鹿公司的原奶中,使之销售到全国,并造成众多婴幼儿患病、多名婴幼儿死亡和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等严重后果,其中,张玉军累计销售三无蛋白粉600余吨,销售金额6832120元,张彦章累计销售230余吨,销售金额3481840元。二人因涉嫌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刑事拘留,随后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罪”被公诉。经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二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分别判处死刑与无期徒刑。①
从行为方式上看,判定行为人在蛋白粉中添加三聚氰胺该当于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客观要件并不存在问题,而法院认为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核心根据在于,“二被告人均在明知生产、销售的“蛋白粉”的唯一用途,是给奶厅(站)往牛奶中添加,以增加原奶蛋白检测含量,会造成奶制品生产企业以被该物质污染的原奶为原料生产的奶制品被广大消费者所食用,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的情况下,置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而与之相近,2009年冬至2011年2月期间,被告人韩文斌等七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购买并销售瘦肉精给生猪经纪人与生猪养殖户,被一审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并为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②既然添加瘦肉精同样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从违法性层面相较两个案件并无二致,然而舍弃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非法经营罪乃至于罪名更为具体细致的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而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使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为较非法经营罪更为兜底的罪名,不得不令人深思。
近年来频发的驾驶机动车辆横冲直撞,③或是在公交车上与司机扭打的行为④,无不例外的被认定成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无论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张玉军三聚氰胺案,还是像早年肖永灵投放食品干燥剂这种客观上影响到社会管理秩序但无甚实害的闹剧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呈现出在各领域无所不包的扩张趋势。“然而,行为的翻新只是症候,并不是成为口袋罪的依据,而是口袋化的结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何成为口袋罪名,关键在于适用罪名的理由是法律的规范性至上还是规范的政策性至上。”[1]因此避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钳制公民自由的异变局面,必须对其泛刑化的原因加以剖析,并对其罪质加以释明。
二、问题的深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扩大适用的成因
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成立与否的唯一标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扩大适用,无论是政策导向的偏差或是强烈的当罚观念使得司法者将公众的求刑舆论作为裁判动机,归根结底在案件的具体认定上,都是犯罪构成遭到架空的结果——或是因为构成要件遭到形式上的解构,或是因为责任要件遭到有意无意的误用。
(一)刑法规范文义的偏离——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解构
“危险方法”与“公共安全”之称谓,已经天然带有社会防卫的意味。文义先天的不明确性使内涵在判断上极易偏离,构成要件的判断往往在不经意间滑出刑法本已设好的法域。对弹性的规范用语不加以限定,或将造成依据“罪状由描述的就该具备,没有描述的就不需要具备”这种形式上的理解的局面。
第一,规范文义的偏离首先体现于对于危险方法的相当性的忽视。按照同类解释的规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罪在刑法体系之中属于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的兜底,对其解释也就必须参照对于作限定列举的放火、决水等具有足以带来具体紧迫危险的罪行,换言之,此种危险方法必须是与法条中并行的放火、决水危险性相当的行为,能够在具体情况下被认定为“足以”造成诸如放火、决水、爆炸等难以挽回的火灾水险等严重的客观侵害程度。相当性的判断在构成要件该当性判断中被舍弃,作为对危险方法的实质限缩的要素被驱逐出犯罪构成之外,危险方法就有脱离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语义格局的趋势,而产生语义外延膨胀扩大趋势的危险。
第二,“传统观点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或者过失地实施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2]而所谓公共安全,亦本罪的保护法益,“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故而一旦行为形式上具有侵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之威胁,就符合了本罪的客观要件。诚然,对刑法条文解释的界限,与实质的正当性即处罚的必要性成正比关系,即越是值得处罚的行为,越有可能被解释为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3]但是公共安全的核心在于“不特定”与“多数”,换言之,对社会性的重视要求“如果是‘不特定的’,则意味着随时有向‘多数’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会使社会多数成员遭受危险和侵害”[4],而与之呼应,方法之危险性,应当具有延漫到多数人的属性,而非流于任何能够带来危险感的行为。
(二)间接故意归罪的泛化
“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是近代刑罚的一个基本原理。责任主义要求行为与责任同在亦即,行为人必须对可得谴责的违法事实负责。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责任的认定上,本应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入罪的思路在于,首先确定行为所随附的危险带有公共的属性,随之当然的认为将实施基本行为的被告人对公共危险加以放任,从而得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结论。这种为果索因的论证方式是“结果责任”的正名,颠覆了犯罪构成在罪名认定上的稳定与审慎,而其本质在于,犯罪间接故意的适用泛化。
间接故意和直接故意是刑法上的传统分类,所谓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且对之放任的心理,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统一。不能认为追求某一非法目的而形式上能够被判断成放任另一个侵害结果的行为都能确定行为人具有间接故意,否则按照这样的逻辑,在公开场合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之后为毁灭罪证、抗拒抓捕而使用的暴力的对象并不限于财产受害人,那么其暴力行为也具有危害不特定多数人安全的危险,根据公共安全的属性,也完全可以将刑法在转化型抢劫的规定理解为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再如,交通工具在现代社会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无论怎样便捷的交通工具都含有事故亦即社会危害的种子,但是不能说驾驶交通工具上路就是放任客观的危险,也不能说具有违反交通法规的认识就具备犯罪的故意。如果说在这样的程度上都被判定具有故意,这显然是将间接故意扩大化的不当结果。将行为随附风险所含的危险感予以全方位的打击,是强烈的当罚观念使得司法者突破了犯罪构成的冷静判断,而将求刑的欲望作为裁判的重要动机。
进而言之,以间接故意归罪实质是将行为人对危险的放任意志作为惩处的根据。但是“突出间接故意中的意志内容,乃是基于与直接故意相协调的考虑,以实现故意理论体系的内在一致性。”[5]以被放任的意志作为直接处罚根据,其首要的障碍在于对故意的认定上。充满任意性的故意的判断极度依赖于行为人对构成要件的认识,这将不当的强化口供在司法认定上的作用;在难以得到明确结果的情况下,而又不得不以行为人已经或者可能认识的内容推定其意志的形态。周光权教授认为对于间接故意中意志的判断应当结合三个层次的判断:其一,放任必须建立在对结果发生的“盖然性认识”基础之上;其二,行为人必然对结果有过“认真的”估算;其三,对结果采取“无所谓”态度。[6]在以间接故意的放任认定危害公共安全的犯意之时,法院的裁判文书对其中“认真的估算”并无详细的论证,而在确认行为人具有对构成要件的认识继之以对结果客观上的容认便得出具有放任的心态,这将使得在将公共危险扩大化的前提之下进一步造成公民自由与权利的严重压迫,将一些本不属于本罪涵摄的罪行甚至是一些应当无罪的行为归于本罪之中。
三、罪质的剖析:基于法益保护思想下的刑法解释
(一)人身安全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核心要素
危险方法的内容应当通过法条的规范内容进行限缩,而法条规范内容的确定,又取决于罪名所保护之法益的内容。刑法理论对于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安全作为公共安全的核心含义并不存在争议,将人身安全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的核心要素符合刑法保护生命的目的,坚持人身安全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罪法益的核心,符合法益保护的价值位阶原则。自由、财产等法益之保护发生冲突之时刑法仍会进行优位的衡量,“而生命法益则是采取绝对保护,不因为数量大小而发生为了多数人的生命之维护则可以牺牲少数人之生命的问题,也不发生因被害人之承诺而阻却行为人的杀人行为的违法性。”[7]对生命的绝对保护是对人的尊重,“公共”的核心亦在于“不特定”与“多数人”之利益,而其中最关键的莫过于生命的利益。将人身安全作为公共安全的核心,符合刑法的目的解释。
从罪刑相适应原则看,法定刑的轻重反映着立法者对于法益保护态度的强弱,罪刑相适应正是这种差别的本质体现。无论是放火、决水,亦或是破坏交通工具、易燃易爆设备等犯罪,均将死刑作为法定刑的顶点,古代曾强调同态复仇,为实现公平正义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中国人古老的正义观念中也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而与之相较,无论是故意毁损财产罪还是盗窃罪、诈骗罪,都没有将死刑作为其法定刑,即使是包含死刑的抢劫罪与绑架罪,也都是因为抢劫与绑架具有造成人身伤亡的高度盖然而使立法者不得不将死刑作为法定最高刑以警示罪犯劫财切勿害命,换言之,财产犯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力度之间的巨大差距,正是提请人身安全是危害公共安全罪核心要素的注意。
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人身危险,并不拘束于对孤立个体生命的威胁,相反,基于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保护,要求此种危险具有延漫的特点。危险得否扩散的考察必须考察具体个案的细节进而作出判断。日本刑法中将放火罪分为“向现住建筑物等放火罪”、“向非现住建筑物等放火罪”、“向自己所有的非现住建筑物等放火罪”、“向建筑物等之外之物放火罪”以及“向自己所有的建筑物等以外之物放火罪”,且“想现住建筑物等放火罪”之处罚根据在于“公共危险”以及“针对处于建筑物内部的人的危险”,如果不具有延烧的危险,即使危及了建筑物内部的人,也必须从向现住建筑物等放火罪的构成要件中剔除,进而以故意伤人罪或是故意伤害罪等侵犯孤立个体的生命、身体法益的犯罪论处。
(二)财产性利益损失应以人身安全作为前提
既然承认人身安全是公共危险的核心要素,那么纯粹的财产性利益究竟是否应当进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法益视野,或者说,对于刑法第115条中的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又应当如何将解释?论者认为,“重大财产必须是公众的财产,公共安全的范围限于公众的重大财产”[8]。然而如果人身安全是公共安全的核心要素,脱离人身安全的纯粹财产损失就没有独立存在于公共安全的价值。本文认为,公共危险是财产损失的前提,财产的危险并不是本罪本质的处罚根据,换言之,退一步讲,作为公共安全内容的公私财产应当仅限于“与人身安全密切攸关的公私财产”。[9]将纯粹的财产法益的损失作为公共安全的要素,不利于与刑法其他章节包含财产侵害的犯罪进行衔接。罪名之间最本质的区分在于保护法益之不同。如果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保护之法益中纯粹重大的财产损失具有独立的意义,那么在罪名选择上与故意毁损财产罪、非法经营罪等同样包含财产法益的罪名在构成要件层面难以甄别,换言之,构成要件类型化的功能将流于形式。
单纯毁坏了交通工具而根本未将危险延展至不特定多数人的情形下,由于没有延及人身安全,并不能因为毁损交通工具造成的客观损失而认为侵害了公共安全。重大财产损失的规范基础在于刑法第115条中的“重大公私财产损失”。为何有“公私财产损失”的立法要义,本文认为对其解释必须紧扣行为人之行为进行认定,客观行为的特殊性是我们追寻立法原意的根本之所在。[10]既然人身安全是公共安全的首要之义,便能够自然的认为,这种重大公私财产损失是危害公共安全时所带来的一种类型性的结果。换言之,重大公私财产损失其从属意义更强于其独立存在的实体意义。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矿山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电力设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亦或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重大事故或是严重后果的认定上,都是将造成伤亡结果作为第一位的判断内容,随之以重大的财产损失,亦即,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于重大财产损失的规定内容应作出以人身伤亡为前提的契机,换言之,公共安全视域下的财产损失并不纯粹。假如适法者拘文牵义,过于信奉文义解释,固执己见地将公共安全保护法益之通说奉若神明,将与人身安全毫无牵连的单纯财产安全罗列入公共安全范围之内,则必然直接和罪刑均衡原则背道而驰。[11]
(三)纯粹的公众生活的静谧不应当作为第一位阶的法益
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关于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应当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新法益内容,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以及对应的过失犯罪通常并不是直接侵害和威胁人的生命、身体而是扰乱公共生活的静谧。[12]从社会防卫的角度看,犯罪行为是对社会的敌视,任何犯罪都是对法益具有急迫侵害的类型都能造成人心上的不安生活上的不宁。公众生活的静谧,是危害公共安全类型犯罪所必然侵扰的对象,将之独立成为法益并不合适。
从刑法第114条、第115条所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之所以被界定为具体危险犯,就在于对其构成要件的判断上必须具体细致的判断出该当行为是否具有足以导致重大危险的产生。公共生活的静谧,在判断标准上原本就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如果认为单纯的公共生活的安宁平稳能够作为独立的法益存在,那么对于放火罪、决水罪等具体危险的犯罪而言,安宁和静谧之不明确内容并不能体现放火罪、决水罪的特质,对其认定并不能提供一个客观精确的标准。将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归属于公共安全的法益内容,笔者认为此种论断与其是对危害公共安全罪法益内容作归纳与阐释,不如说公众生活静谧是犯行必然招致的后果。静谧的生活遭受侵害,必然会造成社会成员的对于亲身生活的危险感,但是如果仅凭这种危险感就确定行为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不免将有将处罚根据从具体的危险转换成为抽象的危险之嫌疑。
即使是通常不认为具有侵害生命、身体相当性的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的行为,将其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根据依旧是人身安全,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可以看到,人身安全之侵害是由于设施被破坏之后的延误所造成,但既然将伤亡结果归结于延误,亦能确定破坏行为与伤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而确定破坏行为具有导致伤亡这一扩大解释也具有存在的空间。因此,公共安全罪质之顺位,处于第一顺位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安全,其次是依属于人身安全而判断的财产安全,即使将公共静谧作为法益,也不得凌驾于人身安全之上。
四、问题的破解
通过原因的分析剥开罪名的罪质,在于更好的保护法益,台湾学者林山田指出,“刑法之本质乃在于法益保护,故刑法实为一种法益保护法。刑法分则规定之每一个不法构成要件均为防止特定法益遭到特定行为模式之侵害所为之刑事立法设计。”[13]犯罪构成是一个先事实后价值、先客观后主观、先形式后实质的判断,结合分析得出的罪质,笔者坚持以下的判断逻辑:
(一)坚持同类解释的原则,危险方法需与放火决水具有相当的具体危险
规定在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构成要件解释上应当做出与放火、决水、爆炸等罪行程度相当的解释。放火、决水、爆炸等行为之共性,在于其结果实现之时的惨烈,如三国夷陵之战陆逊火烧连营大火七日七夜不灭,如关羽襄樊合战决水能淹七军。如果将此条文的兜底理解为章节的兜底,将使罪名之中的“危险方法”和“公共安全”二要素不当扩大,从而将轻微甚至没有危险的行为包含到构成要件判断之中。相当性的判断不仅要考察行为所发生的场所、作用对象、暴力程度进行考察,更重要的是,必须借助客观要素判断出行为是否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全。具体地说,会使社会的一般成员感觉到危险,客观上可能使更多的人(而非单纯的与人身安全无关的财产)遭受侵犯。因为惟其如此,方能体现出行为危害“公共”安全这一属性,也才可以说是“多数人”的安全。[14]相当性的贯彻不仅仅是构成要件行为具有相当的危险,而且在结果的判断上也必须一以贯之。作为处罚根据的危险是足以引起人身伤亡、公共财产损失等实害结果的危险,因而不能将只能引起恐慌的无物质结果危险作为处罚的根据。2001年肖永灵将食品干燥剂装入信封向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东方电视台陈某投递,被上海市二中院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是食品干燥剂不可能发生“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而后《刑法修正案(三)》增设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间接说明根本无法造成实害结果的行为,不应当作为刑法规制对象处理。
(二)对具有急迫严重危险的行为坚持具体危险犯的判断,划清与抽象危险犯之界限
刑法理论将危险犯分为具体的危险犯与抽象的危险犯,二者因不同的区分标准而有不同的分类。第一种观点认为,具体的危险犯与抽象的危险犯的区别在于,是否将危险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第二种观点认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虽然都将危险作为处罚根据,但前者需要司法上的具体认定而后者则是一种立法推定;第三种观点认为,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在于一种危险状态而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是行为本身的危险;而第四种观点认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的危险犯之间的区别在于危险程度的差异。[15]本文认为,第一种观点认为抽象的危险犯中危险不是构成要件要素,有违反责任主义之嫌疑;第三种观点并没有进行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的实质区分,具体的危险犯,也是由于其构成要件符合行为具有急迫的法益侵害;至于如果认为危险差异仅仅在于程度,则其判断没有明确性。本文认为危险实际是一种情势,第二种观点之所以有可取之处,在于具体的危险犯必须结合案件具体情状判断是否具有足以造成结果发生的情势,按照结果无价值的观点,作为结果的恶遭到否定而行为的恶则有较大的容忍性。诚然,刑法的归责原则终究是以结果犯与实害犯的犯罪构成要件架构为出发点的,抽象危险犯的处罚基础不以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结果为要件,而是从“行为无价值”的观点出发,将某种行为模式强硬评价为对法益具有典型侵害性与高度风险性。[16]但是抽象危险犯的设置意味着行为处罚根据的提前,意味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的行为圈被大大扩大,口袋罪之所以形成,最重要的手段则是通过强调结果的危险性,从而否定了行为的规范性。[17]而否定行为的规范性,又极易造成处罚的滥觞,如果将一旦发生冲动人心的案件,为朴素正义感所激愤的人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判断行为的性质,而是在法律框架之内寻找罪名处之而后快。因此,诸如欲公开抛洒上访材料而后欲自焚伸冤⑥、或者高空随手抛酒瓶砸死砸伤倒霉的过路行人⑦等案件,确实给公众的安全带来极大的危险感,但是“公共”的危险应当带有客观延漫的属性,将本罪从具体的危险犯偷置为抽象的危险犯,使一些本不属于本罪涵摄的行为强行涵摄,其归根结底,在于对处罚根据进行了错误的确认。
(三)以人身安全为核心利用罪数原理甄别相关犯罪,避免疑难案件间接故意的滥用
罪刑法定要求对行为的认定准确,但是公共安全保护客体可谓兼有人身与财产之双重利益,难以理清人身安全与财产利益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体系关系,既是本罪与刑法关于保护人身财产以及社会关系相关章节难以妥善衔接的根源所在,也是造成适用本罪之时频繁使用间接故意归罪的重要原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分则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犯罪诸多罪名联系千丝万缕,在行为不具有与放火决水等相当的具体危险时,能够判定为分则具体罪名的,就应当按照具体的罪名涵摄;带有延漫危险的行为侵犯了公共安全,同时亦侵犯了人身财产犯罪所保护的具体法益时,也可考虑罪名之间的想象竞合。换言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故意杀人罪、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等诸具体罪名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立场。恰当的进行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就能够将虽然客观方面稍带重合,但明确属于他罪的行为以其他具体罪名所评价。以间接故意入罪之论者往往主张,行为人虽然着手实行甲行为(即追求甲结果),但行为客观上放任了乙危险的发生。诚然,间接故意中放任的危险确是伴随实行行为产生,然而放任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行为人在明知行为性质的两重性、行为对象的多个性、行为结果的两可性基础上,应当承认他对行为的实施是有所选择的”[18],换言之,“没有选择,就不发生间接故意的问题,那只能是直接故意”[19]。因而,在危害结果实际上无处可选的情形下,不应当认为行为人的责任形式为间接故意,如行为人在公开场合自焚以维权的情况下,其所放弃或称之为侵害的法益仅仅为自己的身体与生命,并未与公共安全相涉,因而如果认为是客观上对公共安全有危险而主观上放任这种危险发生,则显得十分牵强。
五、结语
法益的概念在进行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上为不同犯罪勾勒出了独一的轮廓,为犯罪的类型化奠定了实证的基础,危害公共安全罪保护的是超个人法益,也因此当然地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但是对一个罪名的强调并不在于对之时时适用,罪名的设置、法定刑的构造已经反映出人们对罪名在抑制犯罪上的期待。然而对权益的关注容易演化成对罪名的热切,对罪名的热切将在不知不觉中演化成一种求刑的热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兜底化泛刑化似乎正是这种情绪呼之欲出的表达。虽然一个罪名在过渡膨胀之后能够运用规范的技术分析使得其回归到最初的质朴与平静,但一旦人心冲动之后将难以恢复以往的平静,希腊哲语有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样的河流”,正是警醒我们切勿使得求刑的冲动占据心思而造成难以挽回的错误。
注释:
①本案案件详情可见诸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石刑初字第353号刑事判决书、河北省高级
人民法院(2009)冀刑一终字第57号刑事裁定书与最高人民法院(2009)刑二复83394450号刑事裁定书。
②本案案件详情参见获嘉县(2011)获刑初字第121号刑事判决书,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人韩文斌等人非法经营一案的二审刑事裁定书”,http://www.110.com/panli/panli_28017466.html,访问时间2015年8月11日。
③参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巴中刑终字第51号刑事裁定书。
④参见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2014)闸刑初字第918号刑事判决书。
⑤具体案情可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1)沪二中刑初字第132号刑事判决书。
⑥参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沈中刑二终字第77号刑事裁定书。
⑦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刑一终字第23号刑事裁定书。
参考文献:
[1][17]孙万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何以成为口袋罪[J].现代法学,2010(5):72,78.
[2][4][12][15]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601,601-602,603,167.
[3]参见[日]前田雅英.现代社会与实质的犯罪论[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30.张明楷.论以危险方法杀人案件的性质[J].中国法学,1999(6):111.
[5]劳东燕.犯罪故意理论的反思与重构[J].政法论坛,2009(1):82.
[6]参见周光权.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65-167.
[7]陈志龙.法益与刑事立法[M].台湾:台湾林学丛书编辑委员会,1992:111.
[8]曲新久.论刑法中的“公共安全”[J].人民检察,2010(9):20.
[9][11]王立志.人身安全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必备要素——以刘襄瘦肉精案切入[J].政法论坛,2013(5):119,120.
[10]陈伟.论目的性限缩解释方法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为例的分析[J].法商研究,2012(6):69.
[13]林山田.刑法各罪论[M].台湾:台湾大学法学院图书部,1999:12.
[14]胡东飞.论刑法意义上的“公共安全”[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2):54.
[16]谢杰,王延祥.抽象危险犯的反思性审视与优化展望——基于风险社会的刑法保护[J].政治与法律,2011(2):79.
[18][19]杨兴培.犯罪构成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72.
中图分类号:D9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385(2016)01-0078-06
作者简介:王杰,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学。
收稿日期:2015-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