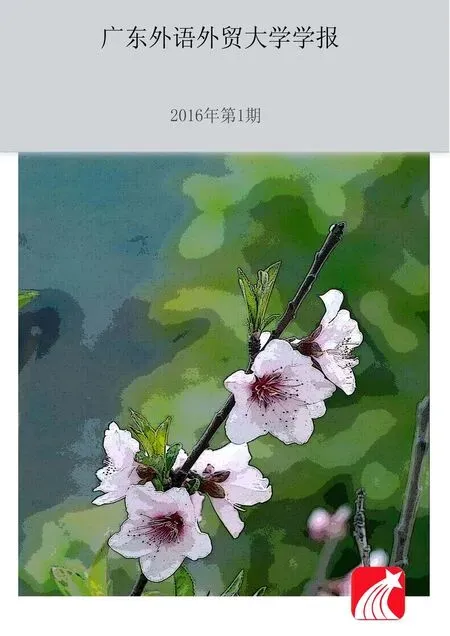神话重写与身份重构
——论海伦·邓莫尔《重获身体的三种方法》中的异伦理
付晶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广州 510420)
神话重写与身份重构
——论海伦·邓莫尔《重获身体的三种方法》中的异伦理
付晶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广州510420)
摘要:海伦·邓莫尔虽然被各类综述和专著介绍为当代杰出的英国女性诗人,然而中外学者对她诗歌的研究仍然是空白。邓莫尔代表性诗歌《重获身体的三种方法》,创造性地化用基督教神话中的女性符号——被贬低的夏娃和被尊崇的圣母,重新书写成一个关于女性“失去身份——嬗变与获取生命体验——重构身份”的神话。邓莫尔的诗歌具有独特的视角,通过建构新的“妻子的神话”呼应了克里斯蒂娃关于重新建构母性身份的异伦理学主张。
关键词:海伦·邓莫尔; 神话重写; 身份重构; 异伦理
一、引言
当现代心理学探索潜意识的同时,它亦赋予了神话新的认知。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展现了神话如何呈现认识与解释人类心理体验的过程。而荣格则用“原型”来解释集体无意识,并称之为“不断重复的人类经验的沉淀”(Sellers,2001:5)。这似乎意味着一旦人类经验发生变化,原型也可随之变化,并把这些变化带入到神话的叙述中。作为一位神话研究者,玛丽娜·沃纳(Marina Warner)看到了神话的开放性,认为它“具有编织新内涵和新形式的持续力量”(Sellers,2001:2)。这解释了为什么当代女性作家喜欢把传统神话放在当今生活经验和历史洪流中去审视,通过解构和重写神话向传统意识挑战,并结合文学、心理分析学、媒体等各个领域重新编织女性的生命体验。海伦·邓莫尔是英国当代诗坛杰出的女诗人代表,对她来说,女性生命体验存在着各种变化与不稳定性,诸如性、生产、衰老和死亡。然而这些独特的体验被象征压抑并零碎地散落在传统的宗教神话中,因此重写神话不仅仅是邓莫尔运用的艺术和叙述手法,还是她重新记录女性身份建构过程的方式。正如奥伯里恩评价道,“最好把她的诗看作是现实主义和难以形容的想象实践之间的桥梁”(O’Brien,1998:259)。
提到海伦·邓莫尔,读者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柑橘文学奖(Orange Prize for Fiction)获得者以及她的小说。直到2010年3月,邓莫尔以一首匿名参选的诗歌《胡说》(TheMalarkey)摘取了全英诗歌竞赛的桂冠,才让人们发现她的诗。至今为止,邓莫尔已经发表了9部诗集。即使如此,数据统计表明,①国内外学者至今没有关注邓莫尔的诗歌艺术。因此,本文以《重获身体的三种方法》这首诗为例,分析邓莫尔创造性地化用基督教神话中的女性符号——被贬低的夏娃和被尊崇的圣母,重新书写成一个关于女性“失去身份——嬗变与获取生命体验——重构身份”的神话。在这个新神话里,夏娃与圣母的身份并没有给女性带来认可与满足,反而是妻子的身份让她重获自我;女性也由一个单调的象征符号变成集合压抑、自虐、痛苦和快乐等丰富感官知觉的浑融体。这恰恰呼应了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关于重新建构母性身份的异伦理学主张。
二、陨落的女神——夏娃和圣母
人类对女性神祗的崇拜源于对生命和繁殖的尊崇,并认为女性身体变化的韵律犹如自然四季变化的律动;女性孕育生命就像大地对万物的滋养。从远古时代起女神就享有很高的地位,然而当父权制社会取代母系社会时,女神却从至高无上的位置被拉下来。缺乏女神崇拜传统的犹太教采取极端排斥和消灭的方式以期压抑女神所代表的繁殖力。然而,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却意识到女神崇拜的强大生命力,不得不选择性地接纳女神崇拜中不危及其正统信仰的成分,改造成圣母崇拜(顾蓓,2003:34)。《重获身体的三种方法》正是以失落的女神开篇,“早上我独自在床上偶然地/ 醒来发现我的身体不见了/它一直都在的啊”②。身体的消失突出了身体/思维的二元对立。麦卡菲提出形而上学是导致女性消失的原因。他认为笛卡尔的二元论崇尚思维,贬低物质,把思维看作是人的本质,男性思维由此被父权制推崇为理想。而女性由于历史原因被等同于身体,属于外延,因此被看作是没有本质的存在(beings without essence)(McAfee,2004:81)。基督教正是促使女性成为外延的父性话语,因为它把女性的身体归为原罪、性和死亡。诗歌第一节中对女性身体的肢解(截断的头发,松动的指甲,挂在脚跟的皮肤以及被人们渴求的耳朵)营造出对身体的心理排斥和抵制。消失是重构身份的前提,“我”也随之面临身份的分化,诗歌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写道,“首先我计划把自己偷回来。我是雾气/ 在腿间、腹部和臀部。我曾和很多男人睡过。”;“然后我决定化作贞女。没有了身体/ 编造一个新的故事轻而易举。”一边是代表夏娃的腿间、腹部和臀部,另一边则是代表圣母的耳朵、眼泪和胸脯。
凯莉·奥利弗认为象征秩序把母亲看作是神话和幻想——贞洁的母亲或毁誉的女人——以此来替代女性身体消失后的不确定的身份(Oliver,1993:80)。失落的女神获取的第一个身份是夏娃,伴随她的是卑贱、死亡和破坏。对头发和蚝肉般的肉体的描述带有性的隐喻:头发代表原始母亲生殖力(“我已把头发截成数段”),也暗示女性诱惑(“这样你们每位都有记忆的东西”);蚝肉是古希腊神话中爱神阿佛洛狄忒的食物,代表女性生殖和性爱欢愉。基督教话语把性和原罪、死亡联系,视之为对道德自我的威胁,因为“死亡来自夏娃,而生命来自玛利亚” (Kristeva,1987:239)。克里斯蒂娃(1987:234)把这种否定称作卑贱(abjection),是对原始母亲的生殖力和破坏力的原初恐惧(primal abhorrence)。被男性视作他者的女性是异己,一方面男性意识到对他者的欲望,另一方面作为异己的女性又不能享有和男性平等的地位和欲望,因此卑贱是男性“文化阉割”心理下产生的焦虑和反应。对女性形象的异化和歪曲、对性话语的禁忌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原初欲望的抵制,因此诗歌里作为原罪和原初欲望象征符号的夏娃形象被贬抑为道德败坏(“我曾和很多男人睡过”),是死亡的阴影(“我陪着你在灰烬弥漫的波兰车站,/ 我陪着你在柏林灰暗的广场”),被排斥在意识之外(“而你狼吞虎咽地啃下三个油饼,毫不停顿/ 只想着你自己”),是对自我的威胁(“很快我重获了我的双唇/ 在你刮胡子时我等在镜子后面/ 你撅着嘴。犹如刮蜡般,我刮下亲吻/ 它已不再有温润的触感。然后我飞走了。”)。最后,代表父系秩序的“你”和代表毁誉女人的“我”在镜子前后形成了二元对立。“我”的逆袭是失利女神的反击,虽然获得了嘴唇却没有得到声音;像蜡一样没有温存的吻,象征着死亡也见证了爱和原初欲望的终止。诗歌对暴力的渲染突出了男/女的决裂。
女神重获的第二个身份是贞女,暗示着圣母。“我”把圣母的身份戏谑成“没有了身体/ 编造一个新的故事轻而易举”。克里斯蒂娃(1987:235)在《圣母哀歌》中追溯了凡间女子玛利亚被尊崇为圣的历史过程,她写道,“圣母的人性并不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她通过和原罪脱离关系从而使自己脱离了人类”。教会通过四个世纪的禁欲主义把死亡和性联系,把代表至善的玛利亚和性分离并升华成圣母是基督教对异教改造的胜利。诗歌以隐喻的方式把这段历史隐晦地表现出来,“七年后/ 每一个无形的细胞将会复原/ 而没有任何一个曾经和你们任何一个接触过。”
诗歌同时借助浴水重生的古老神话来暗示女神的重生,“我浑身金色 沐浴在一皮夹水中。” 《希腊宗教概论》里提到,赫拉同宙斯的婚礼长达三百年,她每天在阿尔戈斯附近的卡纳索斯泉中沐浴后以恢复贞洁(王晓朝,1997:68)。然而具有浓厚男子中心主义色彩的基督教大力宣扬玛利亚的贞洁却非偶然。对于“Virgin”一词,克里斯蒂娃(1987:237)认为翻译成贞洁是一种误译,因为在犹太语中它指的是年轻未婚妇女的社会地位,而希腊语的翻译则注重生理和心理的状态,和“virginity”同义,“事实上西方的基督教策划了这个误译,并把自己的幻想投射进去,创造了一个文明史上最有力的想象结构”。所以当“他们沉迷于/ 对着我的童贞渴望地窃窃私语”时,“我”对崇拜充满蔑视。“皮夹”、“渴望”和“金钱”暗示着这种升华和崇拜背后的利益动机,因为“我真的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克里斯蒂娃(1987:259)认为圣母崇拜是父系社会向母系社会残余妥协的结果:虽然建立在交换和生产增长基础上的新社会需要超我和象征秩序的父性代理(the symbolic paternal agency),但是圣母是无意识中原初自恋(primary narcissism)的需要。把女性形象完美化,又通过圣母的形象疏离,从而在菲勒斯中心意识的框架下把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完成心理层面的换喻。只是女性形象虽然被升华、被崇拜,但也失去了浓郁的生命力,因为从此她被禁止了性和声音。圣母的形象被永远地定格在贞女这个象征符号上,她的女性欲望被废黜。如果女性的生理欲望等同于她的生育欲望,那么以圣母的身份为模范不仅是女性身份的一种自虐,也是为父系社会压抑女神生殖神性扫清了道路。诗歌里当女神的身体被废黜时,唯有代表倾听的耳朵被保留(“你们中有人恳求要我的耳朵/ 因为你们能够从那里听到大海”)。克里斯蒂娃(1987:248)指出,“我们唯一有权拥有的是圣母的耳朵,眼泪和胸脯。女性的性器官被转变成一个天真的贝壳、声音收集器”。对耳朵的接受既把原初欲望纳入菲勒斯-逻格斯框架中,又有助于父权对女性身份的定位:消失和非语言。最后,女神被奉上了神台(“很快他们给我奉上咖啡和香水”),却也高处不胜寒(“我去到一个冰冷的湖,一个铺满灰色地衣的岛屿”)。男/女的和谐以圣母的牺牲为基础。
三、“妻子”的神话和女性伦理
神话和宗教学家梅丽莎·拉斐尔(Melissa Raphael)从各地女神崇拜传统中总结出一个“三面女神”的形象:充满活力和诱惑力的白色少女神、象征生命力量和代表慷慨仁慈的红色母亲神,以及代表死亡、创造与再生的黑色老妇神(顾蓓,2003:37)。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神圣至尊的大女神被贬抑和改造,女儿性、妻性、母性浑然统一的形象不复存在。如同诗歌里,不管是夏娃还是圣母都无法呈现女性的多样性。为了寻找一个既满足又不自虐的身份,女神尝试了她的第三个身份——妻子(“第三次,我尝试和一个好丈夫结婚”)。这个身份的前提是“一个好丈夫”。当克里斯蒂娃讨论进入象征秩序的必要性时,她认为母性身体里包含着象征秩序,而圣母身份的嬗变也揭示了父性基督话语根基里含有母性特质。凯莉·奥利弗(1993:80)解释克里斯蒂娃的观点,认为女性不应该拒绝象征秩序或母性身份,应该认识并坚持象征秩序并非纯“阳性的”(phallic),而是“被冲突的异质过程不断改变的产物”。所以妻子/丈夫可以形成和谐的关系(“他知道我的过去但不介意”),取代了作为夏娃身份时的男/女二元对立,以及无“性”化的圣母。
克里斯蒂娃坚持从母性的话语中探索女性的意义,认为卑贱可以被想象父亲(the imaginary father)所包容。和拉康的“严厉父亲”相反,这是一位仁慈的父亲,是母亲和父亲的二重体。对父母二重体的认定是存在于自恋结构中(narcissistic structure)的原初认定,也是形成自我的过程中一系列认定的基础(Oliver,1998:65)。凯莉·奥利弗(1998:66-67)解释道,母亲的欲望包含她对父亲的欲望、她渴望满足的欲望和她对菲勒斯父名的渴望,所以父母二重体是母亲和母亲欲望的结合体。这种欲望只能在她结婚以后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诗歌里,作为妻子的女性身份与背负原罪的夏娃和远离人类本能的圣母不同,她既可以自信地宣称“我是世界上的一个女人”,也可以面对自己的欲望承认属于女性的愉悦(jouissance)(“只在她阴道的微笑中存在”)。诗歌的最后,“他轻抚着我可能存在的空气,/ 我转向镜子,看见雾气聚集/ 好像有人在玻璃里活了。”这面镜子和第二节中暗示对立和分离的镜子不同,它见证了爱与结合。随着“我”的呐喊,女性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身体。男/女的和谐以平等的欲望需求为基础。
诗歌对妻子身份的认同无疑呼应了克里斯蒂娃关于新的女性伦理的呼吁,因为它并不对立男/女、夫/妻、父/母,或者是思维/身体、语言/肉体。克里斯蒂娃把“hérétique”(异教的)和“éthique”(伦理)拼在一起合成了“héréthique”一词,字面意思为“异教伦理”,表达了她对传统伦理的颠覆(McAfee,2004:81)。而罗婷(2004:126)则把它解释为“Her-ethics”,亦即“她的伦理”,是女性的伦理。伦理讨论的是主体和他者的关系,尤其是主体对他者的责任。传统的伦理假设主体为独立的个体,“他”对“他者”的责任往往建立在“和我相同”(self-same)的意识上(Oliver,1993:1),如思维/身体,文化/本质,语言/肉体的二元对立都是基于形而上学对身份和异同的定义,即某一概念要基于它的对立面来产生意义。而克里斯蒂娃(1987:262)认为母性身份使母亲与婴儿模糊了主体/客体的划分,女性的母爱天性也演变成无条件的责任感,从而取消我/他对立。她随之以这种爱为模型提出了新的社会伦理,认为这是第三代女性主义运动的方向。异伦理学把主体对他者的责任等同于对自我的责任和对全人类的责任。这种伦理通过爱——而非法则——把主体和他者维系起来。在《妇女的时间》里,克里斯蒂娃(1995:223)写道,“籍此,他者对于‘我’不再是邪恶的、异族的,也不再诉诸外在因素如性别、阶级、种族或民族。‘我’成为攻击者时也将是受害者,相同的也是不同的,一致的也是异样的。”
诗歌拥护克里斯蒂娃的异伦理学,邓莫尔用“妻子”身份而非“母亲”身份是为了和圣母这个父权制的“母亲神话”有所区分,却又另具深意。“母亲”在女性主义诸多理论流派中是个争议性的话题。面对圣母这个母亲神话原型,西蒙·波伏娃认为在男权的主宰下,女性的最高价值是母亲身份的获得,因此母性是使妇女沦为奴隶的最技巧的方法,女性解放和母亲身份不可共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母性关怀被重新认识,认为女性解放和母性关怀可以交融,因为母性的爱与宽容是全人类人性的希望(王虹艳,2003:33)。然而女性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复杂性被割裂、对立的状态在文学创作中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其中妻性尤其被误解。如果女儿性是少女时代独有的纯净而自由的天性,母性是女人天性中具有的无私和宽容,那么妻性似乎就是因为婚姻而后天生成的,是对应丈夫的权威而生成的奴性。鲁迅曾写道,“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 (王虹艳,2003:34)事实上,女性身份是个复杂性的混溶体,女儿性、妻性、母性是女性生命阶段经历的各种不同过程,不应该孤立地抽离出来,更不能彼此对立。邓莫尔所塑造的妻子身份可以被看作是为妻性身份正名的新神话。诗歌里妻子的身份使女性的欲望成为被需求的,而不是被压抑或妖魔化的,而且女性可以和他者(男性)平等需求,他们的结合来自爱和信念(“我相信他的力量”,“他轻抚着我可能存在的空气”)。当女性的生理欲望被伦理道德所接受(“他知道我的过去但不介意”),她的身体将不再被等同于罪恶和死亡。诗歌中妻子的神话展现了克里斯蒂娃所倡导的母性法则,妻子比圣母更富于生命力在于她是一个拥有欲望并且得到承认和满足的健全的女人。
四、神话重写和异质性
重写是一种反思,而神话重写更是在历时态话语下对文化精神意义的反思。现代女性作家对神话的重写以女性价值为导引,不仅从形象系列更从话语形式上对神话这种特殊的文本进行重组。由于从女性独有的体验出发,神话重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意义增值的现象。对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来说,这种基于女性意识的意义增值有助于产生解构既有概念体系的多维认知,因而他鼓励多样化的书写形式和开放性的含义(Sellers,2001:25)。克里斯蒂娃更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建议作家要在书写中融入属于身体的记号话语,作为挑战菲勒斯-逻格斯中心体系的革命潜能(Sellers,2001:26)。记号话语是一种打破传统语义逻辑的异质性语言,它并不一定是专属女性的话语,而是代表非语言的原始驱动力,属于身体感官层面,例如声音、音调、韵律、颜色、气味等。象征秩序基于对记号秩序的压抑,在语言上建立了逻辑/非逻辑、神圣/卑贱、纯洁/不洁、有意义/无意义的二元对立,而诗歌语言则在表达机制上跨越了这个边界,因为宣泄情感的需要而具有许多“反常”的可能性。这种“反常”不仅是源自诗歌语言本身的异质性,也源自读者主体感受的需要。正如刘宏伟(2014:79)强调,依赖感受而非概念的“体验性语言”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意”是诗歌语言的独特表达,也是理解文学语言的心智活动的反映。
邓莫尔的神话重写也充斥着这种多样化和异质性,她的语言更诉诸感官层面而非叙述层面。首先,神话重写中,女神的形象更富于人性化而非刻板的象征符号。随着女神地位的沉落,男性主权简单地以“善”、“恶”来对她们进行分化。代表死亡与再生的黑色老妇神被重塑成夏娃,而女性也被简单地以“一条蛇和一个女人毁了上帝创造的完美”这样的方式一笔带过(顾蓓,2003:40-42)。即使基督教教会推崇圣母崇拜,也只是宣扬玛利亚的谦卑、顺服和贞洁。而邓莫尔笔下的女神更充满人类的情感,她会因为偶然发现失去身体而恐慌、会谋划“偷回”自己的身体、会感到愤怒并躲在镜子后报复、会用轻蔑的口吻调侃对她奉若神明的人们、会坦然地承认女性的欲望,所以神话重写还原了女性丰富的形象。女神拥有了主体地位,自由独立,不再像父系神话一样被降为男主神的附庸。同时,原本与女神主体形象密切相关的野性难驯、强烈的欲望、死亡与再生不再以偏狭的视角来呈现,超越了单一的好与坏的概念:她的野性难驯对应被误解与被排斥、她的欲望与对自己的他者(丈夫)的合理宣泄相对应、她的重生把毁灭与和谐相对应等。
其次,诗歌充斥着身体感官的隐喻。对于克里斯蒂娃来说,象征体系就像净化仪式把属于母性权力的古老经验归为污秽,从而建立了卑贱的逻辑(logic of abjection),形成清洁/肮脏、禁忌/原罪、道德/不道德的二分法(罗婷,2004:170-174)。邓莫尔的诗歌拥抱被视作卑贱的能指,用支离破碎的身体来展现身体的感官,如“我已把头发截成数段”、“我的指甲松动,脱离它们犹如/ 蚝肉般的床”、“有一晚我溜出我的皮。它慵懒地拖着/ 挂在我的脚跟,很疼”、“我是雾气/ 在腿间、腹部和臀部”、“我是世界上的一个女人/ 只在她阴道的微笑中存在”。头发、指甲、褪下的皮这种腐烂物、肢解的身体这些与肉体、尸体、杀戮相关的禁忌,以及与欲望、原罪相关的性禁忌被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打破菲勒斯中心意识下道德的捍卫。这些充满强烈记号语言色彩的隐喻,其意义不在于语言表达的层面或语义里,因为它超越了语言的逻辑而使语义模糊。然而从语言表达行为的主体的感官出发,松动的指甲从指床上脱离出来、褪下的皮肤犹拖曳在脚跟处,这是多么直观的疼痛体验。
再次,神话叙述中线性的故事过程被切断,呈现出跳跃性的理解断层、情节的断片和错综。邓莫尔的叙述并不是为了建构完整的故事,而是重塑女性经验,所以不受线性的时空限制。例如,女神身体的消失并不顺着头发、指甲、皮肤、大腿、腹部、臀部的时间顺序,而是通过身体的肢解来展现自虐、压抑的体验。又如,第二节中强烈突兀的场景变换不是为了叙述情节的必要,从灰烬弥漫的波兰车站跳跃到柏林灰暗的广场也并不是为了展现真实的场景,而是借助这些场景来唤起歧视、战争、死亡的联想。总之,邓莫尔的神话重写一方面颠覆和破坏传统叙述的话语形式,另一方面则建构女性独有的体验来纠正偏狭的男性审美。
五、结语
关于“母权制”这一术语,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在于它是指女性的政治权力还是母亲的法则。顾蓓(2003:38)在引述和评价艾娃·坎特瑞拉(Eva Cantarella)的观点时提出,“母权制”是对应“父权制”提出的,并按照“父权制”的思路把“母权制”看作是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的制度。这种站在男性立场上做的主观推断并没有坚实的证据,即便是在神话之中也找不到男性曾受到妇女歧视和不公待遇的迹象。相反,许多民族的神话里都保留着美好的“黄金年代”的回忆,“也许这些都并非无中生有,人类真的曾经经历过一个人与人之间(包括男女之间)和平共处、平等合作的阶段”。这么看来,邓莫尔对神话的重新书写就具有特殊意义,既追溯了父权话语对女神的假想以及女性形象被分化、贬抑的受虐体验,又复原了远古神话里关于两性间和谐的美好愿望,最重要的是以妻子的身份对女性欲望的挖掘使女性的形象更趋于完整,使女神回归人间性。而且妻子的身份既接受思维也不排斥身体,既拥有语言也不压抑肉体。在语言的表现上,诗歌丰富女性形象、打破逻辑化的叙述模式、侧重身体感官的隐喻,还原了女性体验的异质性和复杂性。
虽然20世纪以来女性作家往往对父权制传统和文化采取一种否定的互文方式来重构神话,但研究者一味强调女性屠龙者的形象就会抹杀神话隐喻意义的开放性。而基于克里斯蒂娃的异伦理学解读则具有内化对立的包容性,这对于探讨多元文化背景下女性主义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牛津英国文学指南》第六版 (Drabble, Margaret〈ed.〉.TheOxfordCompaniontoEnglishLiterature6th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在第308页有关于海伦·邓莫尔的词条,首先提到的是邓莫尔诗人的身份。Randall Stevenson撰写的《牛津英语文学史1960-2000》丛书第六卷——《英伦末日?》(Randall Stevenson.TheOxfordEnglishLiteraryHistory: 1960-2000Vol6. —TheLastof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一书亦肯定邓莫尔在诗歌领域的成就。而且国内关于当代女性诗人和当代英国诗歌的综述更是把邓莫尔援引为重要的诗人代表。然而笔者搜索了剑桥、Springer、Taylor和Francis、Jstor、中国知网、读秀等国内外知名期刊数据库,统计显示涉及海伦·邓莫尔的内容10条,其中2篇是研究邓莫尔小说的论文,1篇是研究邓莫尔小说翻译的硕士论文,1篇是邓莫尔的专访,其余6条均为介绍现代女性作家的综述和专著。由此可见,邓莫尔虽然被各类综述和专著引为重要的当代女性诗人,对她的诗歌的研究仍然是空白。
②《重获身体的三种方法》摘自Helen Dunmore. Recovering a Body. Newcastle: Bloodaxe Books Ltd., 1994: 10-11. 诗歌译文系本文作者翻译。在本文中出现的诗歌片段都加了引号或括号,后文不再一一注释。
参考文献:
顾蓓. 2003. 圣母崇拜的历史研究[D]. 张广智. 上海:复旦大学.
刘宏伟. 2014. 文学语言的意向性表达与感受意[J]. 外国语文(6):79-85.
罗婷. 2004. 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虹艳. 2003. 解构“母亲神话”与重建“母性关怀”——切入女性文本的一种视角[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33-37.
王晓朝. 1997. 希腊宗教概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DUNMORE H. 1994. Recovering a Body[M]. Newcastle: Bloodaxe Books Ltd..
KRISTEVA J. 1987. Tales of Love[M]. LEON S R(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RISTEVA J. 1995. New Maladies of the Soul[M]. ROSS GUBERMAN(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CAFEE N. 2004. Julia Kristeva[M].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O’BRIEN S. 1998. The Deregulated Muse—Essays on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Irish Poetry[M]. Newcastle: Boodaxe Books Ltd..
OLIVER K. 1993. Ethics, Politics, and Difference in Julia Kristeva’s Writing[M]. New York: Routledge.
OLIVER K. 1998. Subjectivity Without Subjects—From Abject Fathers to Desiring Mothers[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SELLERS S. 2001. Myth and Fairy Tale in Contemporary Women’s Fiction[M]. New York: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责任编辑:萧怡钦]
Myth Rewriting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Herethics Reflected in Helen Dunmore’s Three Ways of Recovering a Body
FU Jingjing
(SchoolofEnglishLanguageandCulture,GuangdongUniversityofForeignStudies,Guangzhou510420,China)
Abstract:Though introduced as an important English poet in different anthologies and overviews of modern women poets, Helen Dunmore has not received the deserved attention from the critics and researchers. This paper is to use Dunmore’s representative work Three Ways of Recovering a Body as a demonstration of her poetic charm. Innovatively reworking the feminine symbols in Christianity, the denigrated Eve and the respected Virgin Mary, Dunmore created a new myth of how a goddess loses her body, transforms herself and finds satisfaction in her new identity of being a wife. Dunmore’s perspective is unique and embraces Kristeva’s proposition of herethics.
Key words:Helen Dunmore; myth rewriting; identity; herethics
收稿日期:2015-03-31
作者简介:付晶晶(1979-),女,广东英德人,文学硕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20世纪英国文学、英国诗歌。
中图分类号:I561.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16)01-005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