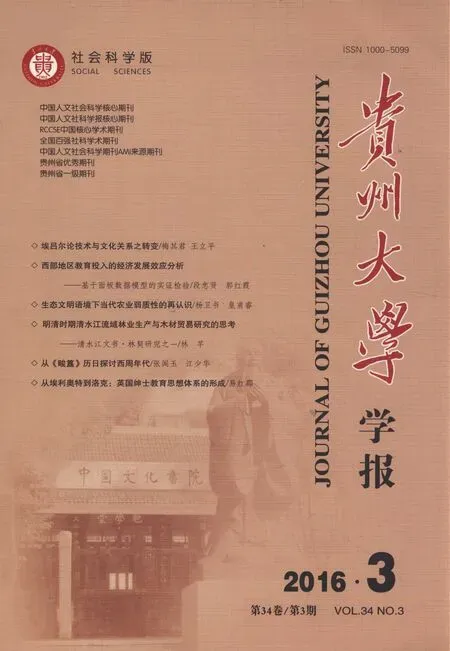酉水流域优质建材绝迹的社会历史原因探析
——兼论方志“物产志”的生态史料价值
彭 兵 杨庭硕
(1.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2.吉首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湖南 吉首 416000)
酉水流域优质建材绝迹的社会历史原因探析
——兼论方志“物产志”的生态史料价值
彭 兵 杨庭硕
(1.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2.吉首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优质建材大多产于特殊的自然与生态系统之中,而且需要经历数百年乃至千年以上的漫长生长岁月,以至于不少研究者习惯于认定过度地利用乃是优质建材绝迹的根本原因。然而,优质建材既然是一种可再生资源,那么在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大背景下,人类的活动肯定会对优质建材的形成产生各式各样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而这样的影响对优质建材的绝迹更具关键性。以酉水流域盛产的楠木为例,从宋代见诸汉文典籍以来,到明代后期,采伐量趋于鼎盛。入清以后,见诸记载者突然锐减;改土归流后,零星的采伐又频繁地见诸记载;等到了道光以后,各方志纷纷记载优质楠木的产出全面绝迹。这样的时间变化显然不符合楠木自然生长的规律,只能理解为相关的社会管护体制失灵所使然。
关键词:优质建材;可再生资源;管护体制;
楠木属于樟科楠木属乔木,在我国南方的低海拔山区本是一种极为习见的森林乔木。[1]但生长季超过数百年乃至千年以上的楠木,由于其质地坚韧,耐腐蚀,木质纹理致密,又易于加工,因而被视为优质建材。历代王朝的宫殿、陵墓、庙宇、祠堂都因由楠木建构,而备受世人的仰慕和赞誉。不过,优质楠木的产出都需要依托特殊的自然与生态背景,同时更需要借助规范有序的社会制度为支撑,因而极为难得,在我国南方,称得上楠木连片生长基地者为数不多。
除了酉水流域外,氵舞阳河流域、乌江下游和赤水河河谷各有一片大型的楠木生产基地,以至于到了今天,上述四地还保留着“楠木坪”、“楠木溪”、“楠木沟”一类的历史地名。①〔清〕乾隆十年《永顺县志》卷之一《地舆志·山川》。不过在今天象这样的地区,已经很难找到处于活态生长的楠木了。这里仅以酉水流域优质楠木产出的时间变化为例,略加分析,意在揭示社会管理体制的巨变才是优质建材绝迹的关键原因。
一、优质建材形成的自然原因
楠木本是我国南方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中的习见植物,通常都是与木兰科、木犀科、芸香科、桑科植物相伴生。[2]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要经受生物物种之间的生存竞争,楠木的植株数量虽然不少,但能够长成优质建材者却极其稀罕。原因全在于在自然生长状况下,虫害可以导致木材被蛀空,与其他乔木竞争时,楠木很难长成高大、挺拔、笔直的树干,因而也就很难产出优质的建材。其中在平旷区段长成的楠木,一方
杨庭硕(1942—),男,贵州贵阳人,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历史学、民族学研究。面,容易遭逢水淹,造成根系窒息,很难健康生长;另一方面,尽管楠木自身具有长成参天大树的禀赋,但若处在平旷地带,一旦比周边的乔木长得高,就很容易遭逢雷击,同样无法形成优质建材。
生长在山脊区段的楠木,在通常情况下也不可能长成优质的建材。因为在这样的生长区位,更容易遭逢雷击;加之土层极薄,营养物质的供给欠缺,还容易遭逢季节性的干旱,以至于尽管也可以自然长出楠木的幼苗,然而只能长成矮小弯曲的“老头树”。所谓的“老头树”尽管拥有数百年的树龄,但高度却不会超过三十米;在不可避免的雷击下,树干也不可能挺拔通直,而且木质纹理也必然疏密无序,达不到优质建材的标准。
历史上的楠木生长基地,通常被称为“楠木溪”,或者“楠木沟”。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分析思考的突破口,使我们有可能注意到,只有在深山窮谷之中,才能生长出优质的建材楠木来。①〔清〕乾隆二十八年《永顺府志》卷十《物产·楠木》。其自然原因在于,在深山窮谷之中,四周有高山屏蔽,楠木只要长出不超过山脊的高度,绝对不会遭逢雷击。更因为在深山窮谷之中,阳光直射的时间较短,光照不足,伴生的乔木都需要快速生长,争取阳光。而楠木由于其生物属性所使然,可以长到的生长高度比其它伴生乔木都要高的多。以至于在其幼年期,由于要与其它伴生植物争阳光,因而树干必然长得挺拔、通直。当其生长高度超过其它伴生乔木后,由于阳光充足,集材量可以猛增,因而可以迅速地屏蔽其它伴生乔木的生长,这样才能形成优质的建材。
除了阳光的因素外,立地条件的土质也至关重要。深谷底部边缘的山麓交错带,土质结构必然具有复合性,土壤结构的同质性较差,特别是这一区段的次生堆积,通常都是土石混合的复合体。其优势恰好在于在山麓的这种次生堆积地带,水分、肥料、透气性能都最适合高大乔木的生长,而且不会遭逢水淹,这才足以确保楠木的立地条件足以支撑它长成千年古树,形成稀罕的优质建材。
总而言之,在自然状况下,楠木仅是一种十分常见的乔木,但能够提供优质建材的楠木,则需要特殊的自然背景和生态背景,只有在深山窮谷之中才能长成优质建材,而且在其漫长的生长岁月中,还必须确保不会遭到人类活动的干扰,否则优质建材同样无法长成。因而,社会能够提供的制度保障,如果不能确保数百年乃至千年内稳定不变,优质建材还等不到达到高标准的要求,就可能被盗伐了,忽视社会制度保障显然无法正确理解优质楠木形成的充要条件。
二、优质建材产出的时间变化
具体到酉水流域而言,盛产楠木的记载首见于南宋人朱辅的《溪蛮丛笑》一书。该书载:“蛮地多楠,有极大者,刳以为船。”[3]这一记载中有三项内容值得细究。首先是,该书明确指出楠木是一种习见植物,但能够长成极大者却十分稀罕,这一认识与上文分析恰好可以相互印证。其次是,文中特意指出楠木产于宋人所认识的“蛮地”,也就是“五溪”的各民族地区,同时也是南宋汉人移民定居为数不多的地带,楠木的产出主要得利于当地居民的管护。最后是,文中明确指出最大的楠木,单凭一根树干就可以制成一条船。考虑到当时酉水流域通用的航船宽度都在数米,长度在10 ~20米左右。因而,能够像这样去使用的楠木,树干的直径至少应当在两米上下,长度应该能超过30米,其树龄至少在千年以上。文中言所未及者在于,如此巨大的原木应当如何采伐,如何搬运到水边制作成船,而这也是优质建材进入流通,实现其价值的关键所在。如果不解决集材运输问题,再解决如何采伐的问题,要将独木制成船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当代的田野调查结果显示,要整体搬运巨大的原木,关键是要开辟“洪道”,同时还需要完备成套的技术要领,才能有效地控制砍伐后原木的倒向,下一步的整体运输才成为可能。[4]所谓洪道,其实就是人工开辟一条运河,借助山涧的水流才能将原木漂浮到预先设定的码头,也就是集材场,原木的采伐才能顺利进行,采伐后的原木也才能到达原木的使用点。至于采伐的手段则需要严密的人员组织,在仔细观察树冠重心朝向的前提下,通过下斧的位置和力度,才能预先控制树木砍伐的倒向。
通检《溪蛮丛笑》一书后发现,该书对宋代各民族砍伐原木的工具有如下记载:
仡党:出入坐卧,必以刀自随,小者尤铦利,名“仡党”。[3]71
这里记载的是“五溪”地区各民族富于优秀历史传统的生产生活用具,统称为环首刀。这是一种长条形的单面道具。由于刀柄附有硕大的环形配饰,因而通称为环手刀。刀刃的长度为70~90公分,刀身的宽度仅4公分左右,刀剑呈圆形,之所以要配备大型的“环首”。目的是可以系上长条形的彩色纺织品,以便环首刀脱手落入草丛后,寻找时可以凭借环手和彩色的纺织品看准刀柄的位置,以免触及刀刃而误伤自己。关于这种刀具的制作和性能,该书“水秀铁”条有如下记载:
“铁之精英在水,数十年者,名水秀铁。”[3]107
这一记载说的是“湿法炼钢”。其原理是将融化的铁水,尽可能缓慢降温,使铁块表面生成厚壳。然后将这样的铁块埋藏在水中,特别是富含有机物的脏水中,经历十多年的光阴,让铁块表面的厚壳彻底锈蚀,未被锈蚀的部分就成了优质的钢材。[5]环首刀就是用这种所谓的“水秀铁”煅制而成,因而极为锋利、尖锐,能够成为砍伐优质木材的有效工具。
由于当时汉族地区的生产工具并未大量进入“五溪”地区,“五溪”各民族砍伐巨型楠木只能凭借环首刀去操作。粗略的计算,砍伐一株能制成独木船的楠木,需要数千个工时,耗时一年半以上才竣工。以此为例,不难推测,当时在酉水流域砍伐的楠木显然只能是那些个人或者数人能够搬运的,直径在30~40公分、长度在30米左右的小型建材,更大的建材当时根本无法外运。
《溪蛮丛笑》的上述记载根本没有涉及到优质楠木形成的自然背景和社会背景。原因全在于当时人们的认识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无法系统地剖析优质建材的自然背景,同时对人类社会提供的制度保障也不甚关注,但事实上要形成优质的建材,往往需要经历数百年的光阴。在这一漫长的岁月里,除了特殊的自然与生态背景外,人类社会所能提供的制度保障更是关键,要确保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受人类的扰动和砍伐,相应的社会制度保障至关重要,否则优质建材也无法形成。要获得优质建材,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的要素缺一不可。
酉水流域是土家族和苗族的杂居地,土家族形成地方性的行政体制为时较早。土家族中的彭氏、向氏、田氏三大家族,从五代十国起,在汉文典籍中就可以查到较为系统的文献记载。其中的彭氏家族在这一区域的政治地位,从10世纪起,一直延续到18世纪初,前后7经历了800余年的光阴。[6]因而,要探讨优质楠木长成的制度性支持,显然可以以彭氏家族为例。
永顺彭氏家族,从“五代”见诸史册记载以来,该家族一直是当地的世袭统治者,对上是朝廷的臣民,对下则是朝廷的代理人,雄踞一方。辖境内的一切事物都取准于该家族确立的规制,而且这样的规制与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治国理念相合拍。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7],在彭氏家族统治的800年间得到完整的体现。
13世纪以前,朝廷在这一地区执行的是“羁糜”制度。彭氏家族的嫡系后代照例都被朝廷委任为羁糜溪州刺史和“都事主”。[8]前一项官衔表明他们可以直接管辖整个溪州地区,也就是整个酉水流域的中下游;后一个官衔则是意味着他们可以召集土家族各部首领,传达朝廷的政令,并代表各部向朝廷作汇报。换句话说,整个溪州地区的军事、经济、政治、宗教,朝廷都是委托他们全权管理,他们只需要朝贡,不侵扰内地,就算圆满的完成了自己的职守。而内部事务则由他们自行管理,其中也就包括对整个辖境内生产生活的规划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对楠木生长基地的制度性管控,也就包括在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
元代以后,朝廷在这一地区推行了“土司制度”。彭氏家族也被委任为永顺土司,开始时仅充任安抚使,元明之交才升级委任为宣慰使,而且是并行建制了保靖、永顺两个宣慰司。两家土司的首领都出自彭氏家族,但领地则是将整个溪州地区一分为二,各掌一片。职位名称虽然有所改变,但其职权依然由彭氏家族世袭接管,使得朝廷对土司的管辖更其制度化和规范化。不仅土司要由朝廷亲自委任,土司衙门中还得设置朝廷流官充任的经理司,对土司的施政直接监控。但土司内部的后勤生产生活管理,依然由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全权统管。
除《溪蛮丛笑》外,宋元两代有关酉水流域优质木材外销的记载极为罕见。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当地没有优质建材产出,而是因为当时的运输条件欠缺,巨型的优质建材难以运往内地。与此同时,发达地区优质木材的供应可以就地解决,对酉水流域优质建材的依赖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但到了明代后,情况就大不一样,随着国内建材市场的扩大和运输技术的提升,酉水流域所产优质建材开始大量流入外地市场,因此而获得了可凭的记载。明代中期以前,由于这样的原木贸易,大多由民间操办,见诸文献记载者有限。但如下几段追据,有助于说明酉水流域所产建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市场流通。
据《辰州府志》云,(楠木)产于苗徼崇山广谷之中。又明时修辰州府署、辰州府学。永、保、酉阳诸司,皆献大楠木树百株。该府志又进而说明:明成化己丑,贵阳易天爵知府事,重建郡署,永顺、保靖、酉阳暨两江诸司,各以楠木百余章来助,皆以其材美也。①乾隆二十八年《永顺府志》卷十《物产》。
这一记载说明酉水流域所产优质楠木已经通过沅江水道销往数百里之外的辰州府,供官府修建衙署之用。不过,这样的优质木材流通,显然不是市场机制左右的产物,而是带有支持国家建设的性质。
到了明弘治年间,朝廷大兴土木,而南方大型木材欠缺,酉水流域所产楠木开始引起了朝廷的关注。当时在任的永顺宣慰使彭仕麒,开始主动向朝廷贡献优质楠木,相关内容,明人刘继先撰的《历代稽勋录》记载最为详实:
是年(正德任申七年,公元1512年),朝廷营建,父子(彭仕麒,彭明辅)自备帑金,采进合式大木七百余根奏献。
戊寅十三年(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春正月,公父子(彭仕麒,彭明辅)献大木之忱,各钦遵敕谕:加升公湖广都司指挥使,赐大红蟒衣三袭。
此同时,彭仕麒向朝廷申请退隐:乞修林下,建修颗砂行署。②〔明〕刘继先撰《历代稽勋录·忠毅公·稽勋》。所建别墅,显然是采用当地所产的优质楠木,楠木的消费既包括贡献,也包括自用在其中。
引文所涉内容在《明史·湖广土司传》,以及清代、民国所续的府县等志都有相应地佐证史料,《历代稽勋录》所涉内容的真实性就完全可以得到证实。不过各书所载进献大木的具体数量互有差别。其原因在于,彭仕麒所献大木并非一次性运达北京,而是多次抵达朝廷,验收时也是分批验收。而《明史》编撰者则是摘其重要者入史,自然会与《历代稽勋录》所载总数具有较大差异。而方志的编撰者有的是以《明史》或《明实录》为依据,有的则是以来自地方官的材料为依据。所以,记载上出现这样的差异不足为怪,但大批贡献楠木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通览上述记载,如下三方面的事实,对土司制度控制下的楠木生产最具代表性。
首先,采办楠木所经历的时间极为漫长,足证采办的难度极大。上述引文明确记载彭明辅在致仕退休后,从正德七年起就着手组织采伐,并集运楠木,一直到了正德十年,大批的楠木才运送至北京,并因此而获得了朝廷的奖励。其后,一直延伸到正德十三年,还有楠木陆续运抵北京,彭仕麒又再次受到重赏。光凭时间的延续看,运送如此数量的楠木抵达京城,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时间极为巨大,若不是土司遗力承担,加之沿途官员的支持,如此浩大的工程,要保证能够按期完成,几乎无法设想。诚如乾隆二十八年《永顺府志》卷十《物产》所言:
“(楠木)产于苗徼崇山广谷之中....伐置山谷间,俟山水发,始顺流下。然空灌蛀裂者多。”③乾隆二十八年《永顺府志》卷十《物产》。
单凭这一记载可知,采伐楠木需要专门安排运输渠道,其实质相当于为楠木运输专门修筑运河,而且还要确保发洪水时有足够的水量能够将巨型楠木冲到下游的集运场。即令如此,采伐到的楠木质量的差异也高低悬殊,优质楠木需要精心挑选才能达到朝廷的标准。仅此简短的说明,也足以看出采伐楠木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
其次,朝廷对土司的报偿是以荣誉为主,实物的奖励不足以报偿这笔巨大的投入。正德十年之际,彭仕麒已经致仕退休,其职位于正德五年,由他的儿子彭明辅继任,他自己则另建了颗砂行署,所用建材自然也是优质楠木。而朝廷恰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因为他献大楠木有功,而被破格任命为湖广都指挥使。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流官职衔,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司令,在明代的官阶属“正二品”,与他的土司职衔“从三品”,足足高了四级,这不得不说是极其优厚的破格任用。这样的荣誉赏赐与他所做的贡献十分相称。但朝廷赏给他的实物,仅止于“飞鱼服三袭”。在明代,这样的官服为高级贵族才能拥有,其级别与他所任的都指挥使相称。不过,这样的奖励很难与他为此支付的人力、财力、物力作比较。正德十三年,同样因为所献的大木运抵北京,彭仕麒再次被破格晋升为“正二品散官”、赐予“骠骑将军”衔。值得注意的是,这仅是一个荣誉,并没有实际的权利,但朝廷给予的颁赐,却到了朝廷的极限,连同他的妻子,一道获得了礼品诰命的封赏,还颁赐了大红蟒衣,赏赐规格已经与明代亲王相近。对退休土司而言,在整个明代无此先例,但赏赐的实物同样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最重要的实物赏赐乃是朝廷责令地方官为他所提供的“花币”,这样的实物相当于今天的纪念币,实际价值仅五十两白银而已,如此来看,实物赏赐与荣誉赏赐并不成比例。
最后,永顺土司大规模采伐楠木,决非有策略的邀功请赏。上述引文及《历代稽勋录》记载,准确反映出该土司的贡木是连续的过程,彭仕麒连同他的儿子彭明辅、孙子彭宗舜、重孙彭翼南都有大木进献朝廷,而且每次的进贡量大致相似,这都足以表明对楠木都是实施严格管制下的有计划的采伐,而不是一次性的投机行动。这从土司身份和心理也可以得到有利的旁证,彭氏土司乃至于整个酉水流域的土司,通过楠木采办而获得朝廷殊荣者甚多,而土司制度明确规定是世袭任职,其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并非个人的简单行为,而是关乎整个家族的兴旺。因而他们每次贡献的楠木虽然数量不少,但同时还必须关注到此后还能够均衡产出,保证后继者也能享受到同样的荣誉,以确保其家声的世代延续。由此看来,此前不少学人认为,这样的大规模砍伐,乃是楠木资源告罄的主因,显然有失偏颇。[6]土司的行为制度规定就得从家族荣耀考虑,能够获取荣耀的资源也是整个家族千秋万代的任职资本,因而任何一位土司都不可能光为自己个人谋利,而不顾及后世的发展。就这个意义而言,他们所采伐的楠木显然是规范经营的产品,而不是投机性的盗伐天然林。对此,以下各代土司的相关记载,更能提供有价值的佐证。
《历代稽勋录》“忠敬公”下又载:
乙亥十年(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恭遇朝廷营建宫室,公父子(彭仕麒,彭明辅)各备帑金,采大木进献。丙子十一年(公元1516年),钦奉奖励。
戊寅十三年春(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荷朝廷軫念远臣,父子(彭仕麒,彭明辅)树立功绩,各有进献大木之忱。是年秋,各钦奉敕谕奖励,加升公正二品散官、骠骑将军,赐大红飞鱼服三袭。①〔明〕刘继先撰《历代稽勋录·忠敬公·稽勋》。
朝廷给彭明辅的这次奖励是与其父彭仕麒分别奉献大楠木所获得的殊荣,而授奖的等次则低于其父,这显然是按照资历授奖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父子两人的大木进献是分别执行的,因而也就是有规制常规采伐的具体表现。考虑到他们分别进献的楠木数量大致相等,而达到这一规格的优质楠木,其树冠的地域覆盖面积超过一亩,因而两人进献的大木将涉及到一千多亩的范围。如果不是按照既定的规划,分别展开如此大规模的采伐,最多都会表现为在以后的进献的楠木都不可能达到此前的规格和等次。然而彭明辅后续贡献的大楠木,其规格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明显地提升。这就足以表明在土司制度的规约下,其楠木的管护和经营,绝非放任自流的直接采自天然林。对此,请看该书的如下记载:
甲子四十三年(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春三月,公(彭明辅)进献木植,本省抚云及祖孙采金大木,忠勤素著,移资兵部杨尚书题,奉圣旨:“是彭明辅采进大木同效忠勤,准照例升赏,写勅奖励,备资到公。”②〔明〕刘继先撰《历代稽勋录·忠敬公·稽勋》。
这次因大木授奖,其间相隔大致是半个世纪,而获奖的等次与前次相当,足以佐证其贡献楠木的数量大致相同,这就表明优质楠木的产出,事实上是按计划抚育的结果,每次采伐后的幼龄楠木在经历一段时间内的管护后,同样规格数量的楠木又可以抚育成才,达到进献的标准。考虑到优质楠木产出的自然背景极为苛刻,并非均衡的分布于整个土司的领地范围之内,而只能分布在十分特殊的山谷地带,楠木还需要植根于山麓的次生堆积层上。因而有理由相信,各楠木的产出地,其地域范围相对集中,具体而言,就是集中分布于今永顺境内的小溪山谷之中,在这样的领域中,只要实施有计划地采伐,楠木资源就可以得到永续性的育成。
然而,彭明辅的儿子和孙子却不如彭明辅那样有幸能够活到高寿,由于常年的外出征战和感染疾病,彭明辅的儿孙两代都没有机会超过四十岁,但奇怪的是彭明辅的儿子和孙子同样是遵循计划地培育楠木的惯例,向朝廷继续均衡贡献大楠木,并不断地获得殊荣。《历代稽勋录》对彭宗舜的贡木作了如下记载:
(彭宗舜忠庄公)癸卯二十二年春(公元1543年),遇朝议建庙,公(彭宗舜)进献大木二十根.......会部院题,奉圣旨:“是彭宗瞬采木合式,准于原职上加级服色一阶,授昭勇将军。”①〔明〕刘继先撰《历代稽勋录·忠庄公·稽勋》。
这一记载的内容是在彭宗舜继任土司以后所为,但这次进献大木与其父的行动不是一体,而是以自己现任土司的名义进献大木,其大木的数量虽然有限,但却足以表明,当地楠木资源的储备量相当丰富,并没有因为历年的密集采伐而告罄,因而可以做到一旦朝廷需要,就能按照要求及时上供楠木。当然也因为进贡楠木不多,因而所获的赏赐也等而下之,仅是在他的“从三品”土司的规格之上加授一级,并授予“昭勇将军”职衔,也就是享受“正三品”的任职待遇。也因为他英年早逝,所以以后的规模性献木他没有机会参与其间。
彭明辅的孙子彭翼南正式出任土司后,除了因平倭之功而备受封奖外,同样参与了大规模的供楠木活动,也获得了超乎寻常的褒奖。该书载:
(彭翼南忠贵公)丁巳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秋七月,恭遇朝廷修建殿宇。会湖广主抚臣檄公,为钦奉大木事。公乃率众进山,采取合式楠木板枋二千七百余根进献。公祖孙又共采大木六十余根进献。……己未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秋七月,公采楠木进献,有湖广赵抚臣奖云:“彭明辅素称道义,久效忠勤。其孙彭翼南克承祖职,益振家声。往年,著绩浙江,近者各道回省。共称祖孙效忠济美之实。本院深嘉叹赏。今据采报木数,及欲各自进献,俱见忠义之素。仰守巡道动支内银二十两,造办银牌、金币,赉送奖劳。”②〔明〕刘继先撰《历代稽勋录·忠贵公·稽勋》。
甲子四十三年春三月(公元1564年),公以进木之忱(彭翼南忠贵公),湖广徐抚臣准兵部咨。奉圣旨:“彭明辅、彭翼南采进大木,用效忠勤,准照例升赏.。写勅二道奖励,加升公湖南都司都指挥使,赐大红蟒衣三袭。加升公云南右布政使,赐大红飞鱼服三袭。③同2。
凭借这一记载不难发现,彭氏家族四代土司,持续仅供大楠木的数量不减反升,增加的数额数倍于此前的进贡数量,如果不是有计划地抚育采伐,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而彭翼南所受到的褒奖,除了与其祖父、曾祖父相同外,还被委任为云南右布政使,这表示着他是在在土司任内直接出任流官。对于土司制度规制而言,这显然是一种特殊的破例。但对土司而言,他们关注的重心理应是关乎整个家族的兴旺,而不是个人的邀功行赏,因而此次彭翼男大规模进贡楠木,决非竭泽而渔,而依然是一次规范的有计划采伐。对此,其后继者的贡木同样可以提供可凭的佐证。
彭翼南英年早逝,其后继者彭永年即位的年纪和任职期限都较短,但其孙子彭元锦却有幸多年任职,因而进献楠木在其孙彭元锦又有突出的表现:
万历十五年即任......先是。公采献大木奏修清宁宫。蒙工部题准照例加升给与应德诰命。奉勅加飞鱼服一袭,升授湖广都指挥史……。④〔明〕刘继先撰《历代稽勋录·元锦公·稽勋》。
该书的上述记载虽然没有直接记载大木的数量,但所获的奖励包括诰命委任为都指挥使,赐飞鱼服都与其先辈获得的殊荣大致相近,足以表明其贡献大木的数量应当大致与其祖父和高祖父相当,也就是楠木的产出依然是有计划的活动,并未表现出资源的告罄。
综上所述,永顺土司向外界提供优质楠木,时间累计从成化年间起到彭元锦贡献大木为止,时间跨度超过了一个半世纪。以楠木的育成周期而言,第一次采伐时,达不到采伐要求的幼树事实上已经长成了符合规格的优质楠木了,而历次贡木数量却基本呈现为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只能解释为,这是有计划抚育、适度采伐的结果。而从土司制度下再任土司的主观意愿而言,他们追求的是家族的永续兴旺和荣誉,而不是一味的追求个人的升官发财,这从上述记载中很多贡献大木都是父子,甚至是祖父孙三代协同参与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换句话说他们的主观意愿也是要保持楠木资源的可持续的高规格产出,以确保整个家族都能够获得朝廷的褒奖,从而巩固该家族在其领地内的世袭特权。这同样表明,他们的楠木采伐对象绝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天然林,如果不经过人工的有效管护,及时淘汰不合规的楠木,高规格的楠木产出也不可能做到。因此,把数百年后酉水流域楠木资源的濒临灭绝,归结为历年皇木采伐的过度利用,显然有违文献所提供的上述史实。要知道文献所能提供的资料仅仅是他们楠木采伐中的有限构成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土司家族本身也需要消费楠木,以显示其家声,他们在贡献皇木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民间渠道提供等而下之的楠木,以获取巨额的利润,要知道这样的收入也是维持其在土司统治期的经济支柱之一。就上述意义而言,土司制度既然明确规定土司领地内的一切资源都交由土司全权掌管,那么为个人的意图而过分的采伐木材,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维护家族的世代荣耀都会很自然的使他们的采伐行动不能不是一种有计划的理性行为。至于清中叶以后,当地的优质楠木资源告罄显然另有其社会原因。
三、酉水流域优质建材的濒临灭绝
据《永顺府志》记载,彭元锦任职的晚年,国内政局遭逢了巨变,朝廷自顾不暇,大规模的营建也因此而停顿下来。崇祯四年(公元1641年),彭元锦去世,其后继人随即引发为家族内部的争斗。但土司对楠木基地的掌控由于有土司制度相关规制做保证,并没有受到重大的冲击。按照土司制度的定规,所谓“蛮不出洞,汉不入境”。因而在朝廷营建战亭的期间内 ,楠木的私自伐卖并不会爆发式的出现。加之,明亡以后,清廷虽然接管了政权,但酉水流域所处的中国南方地区政治动荡事实上前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直到清康熙二三十年间,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叛结束,南方的社会规序才趋于稳定,而继任的永顺土司彭洪海也在康熙的后期趋于鼎盛,至今保存完好的《德政碑》可以为此佐证。
鉴于社会背景的持久动荡,不仅是民间,就是宫廷的营建也未曾规模性的倡导过楠木采伐,因此有理由认定酉水流域土司统治区的楠木储备,并不会因动荡而蒙受巨大损失。但令人费解的是,自从雍正朝对永顺土司实施改土归流后,短短数十年间,乾隆朝编纂的永顺府、县两志都明确记载当地的优质楠木储备已经彻底告罄。细究其间的差异,仅仅表现为土司的被罢废。除此之外,自然生态背景与国内市场对楠木的需求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就足以表明失去了土司的有效管辖和有计划采伐,才应当是楠木资源告罄的主因。
乾隆二十八年编纂的《永顺府志》明确记载:“……(楠木在)今府蜀稀有,积岁砍伐,良材尽矣。”①乾隆二十八年《永顺府志》卷十《物产》。这一记载并没有明确指出,所谓“积岁砍伐”是从何年开始,但若考虑到在改土归流前,在土司的管辖的下,出于家族获取褒奖的楠木,既然能做到有序的管控,当然不可能听任楠木资源会因“积年砍伐”而告罄。因而有理由相信,此处所称的“积年砍伐”只能是指从改土归流到府志编成的三十多年间才发生的事情。而砍伐的方式和渠道,显然是民间的个人行为,而不是土司砍伐。又据同治十三年《永顺县志》卷六《风土志·物产》:“楠木,有白楠,有香楠”。《明史》:“永顺各宣慰历此贡木即此。今积年砍伐,良材几尽”。这一记载的所涉内容与《永顺府志》所载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但直接点明楠木仅是“良材几尽”,而未排除楠木幼树的客观存在,其表达方式更贴近实物发展的实情。
民国十九年《永顺县志》载:
“光绪十九年修县书院,其讲堂三间栋梁栌栭均系大楠木造成,自是,而官山楠木无遗种矣。”②民国十九年,胡履新、张孔修纂《永顺县志》。
这一记载最值得注意之处有三:
其一,直到光绪十九年修建永顺县书院,当地还能提供有限的楠木,这足以证明楠木资源的告罄,事实上经历了极为漫长的一百多年的时间跨度,这与楠木长成的自然规律基本相符。
其二,在这段文书中明确提及“官山”字样,而此处所称的“官山”,显然是指此前直接由土司管辖经营的用材林生产基地,而绝不是民间土地天然林的产出。单凭这一提法就足以证明:在土司管辖的时代能够提供给朝廷的优质楠木,在产权归属上极为明确,都是土司直接经管的私产。这正好可以作为土司时代的楠木采伐是有计划采伐的林木,而不是归属无人经管的天然林的有力证据。
其三,上述引文又明确指出,此前楠木生产基地已经到了“无遗种矣”的地步,换句话说,不仅成才的优质楠木已经告罄,就连处于幼林期的楠木也不复存在了,而提供的这一信息显然与楠木的自然生长状况根本不相吻合。不管是出自天然林,还是人工管控的用材林,不同树林的楠木都应当同时并存而且能够有批次的计量砍伐。既然此前楠木生产基地的楠木连幼树也不存在,其造成破坏的社会原因显然不仅仅是采伐本身所使然,而应当是原先的楠木生长用地改做他用,被置换为种植其他物种,或者置换为农田,才可能出现如此与楠木自然生长规律不相吻合的现象。对其间的社会成因,只能与土司管理体制的不复存在直接关联,而且这一认识在相应的地方志却可以提供间接的证据。
乾隆二十八年《永顺府志》卷之十一《檄示·掘壕种树示》有如下记载:
“照得永属地方,山多荒土,仅可种植树木。已奉督意,檄行示谕在案。查民间山土,原须广种杂粮,为每年食用。岂知种树之利,数年以后即可致富。尔等须于近溪河者种杉树,背阴者种蜡树,坪坦者种桐油树,多砂石者种花椒树,园角墙边或种桑养蚕,或种麻纺织。长成之后,无须人力薅锄,年年可收利息。然亦有明知其利而不肯种植者。本府因公下乡,询之士庶,俱称“偷窃践踏之故”。查长沙各县,凡蓄禁树木之家,俱于本人地界,掘壕筑墙,牛马不得践踏,邻人不得偷砍,立法最为妥当。尔等若愿种树,应照长沙式样,于周围地界挖深土壕,筑墙三四尺高,则树木便可蓄禁。即或人力不多,不妨随时筑土,一二年间,土墙成,而树木长,利息亦自此渐大,是又何憚而不为之。合再出示劝谕。凡于种植杂粮之外,所余山地及墙边圆角,俱须相度地利,广种树木。或恐偷砍践踏,即需筑墙蓄禁,如有纵放牛马践食,以及进界偷砍者,许即报明该县,除重责外立着赔偿,断不估宽。尔等切勿偷安怠惰,坐式地利,且掘壕年久,豪强不得兼并于尔等,甚有后效。慎勿怠慢观望,至十余年后,始信本府之言为大有益也。①乾隆二十八年,李静《永顺府志》刻本,卷之十一《檄示·掘壕种树示》。
仔细玩味这篇告示,一方面由衷的感佩张天如知府能如此关切黎民生计,实属难能可贵。另一方面又觉得这篇告示所涉内容确实有些令人大感意外。如下四方面的内容确有深究的必要。首先,这位知府号召乡民改种树木的土地资源,在此前是长期沿用的杂粮种植地,而这些杂粮种植地,如果没有宽裕,这位知府断然不可能号召乡民改种林木获利。然而,在改土归流前,土司对领地内的土地资源肯定是实施了严格的规划,而土司对朝廷的纳粮任务极为宽减,因而当时的农地主要用于乡民的自食,不许外卖,无需承担朝廷的税务。在当时的背景下,扩大粮食的种植,开荒建构农田,完全没有必要。在“溪洞”组织的规约下,规模性的粮食储备,其必要性并不大。因而农地资源的利用,从来都不追求个人占有的宽裕。可是改土归流后,朝廷一再的鼓励内地的汉族居民移民的领地内开荒,以此提高官府的税收收入和粮食储备。在人口突然增加的背景下,还能表现出土地资源的宽裕,完全可以从一个侧面表明,这些赋予的杂粮种植地在土司统治时期肯定不是现成的农用地,而是来自土司直接管辖的林地和牧场。因而在接纳移民后,才能拥有土地上的宽裕。其背后隐含的事实,至少包括有相当一部分杂粮种植用地,在此前肯定是土司管辖下的山林领地,特别是土司视为珍宝严密管控的楠木生产基地,肯定包括在其中。换句话说,这些暂时宽裕的杂粮用地,在改土归流前,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土司的楠木生产基地,也就是上文提及的“官山”。
其次,如告示所言,乡民不敢于改做经济林木的原因,是“恐惧被偷盗”。这就足以表明,这些此前准备种植林木的宜林地,因为相应的制度规范并未形成,乡民才会有这样的顾虑,官府也才会向乡民献计,要他们挖壕沟、建高墙,以应对制度不健全所引发的林木偷盗问题,而这样的情况在土司统治时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考虑到种植楠木需要数百年才成材,而土司统治时代可以完全确保楠木的用地不会被挤占,足见其制度保证的可靠。而今,种植一般性的低价经济林木还惧怕偷盗,这与土司制度下的严密监控,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足以证明,官府号召植树的对象显然是改土归流后才定居当地的移民,而不是改土归流后尚处于溪洞统辖之下的土家族居民。植树涉及到的林地,也不是改土归流前早已稳定的传统农田。
再次,告示中号召乡民种植的树木是杉树和油桐,这是短时间即可成材的廉价林木,而不是珍稀的优质建材。这一种植树种的变化同样足以佐证改土归流后的官府没有管护楠木林的职责,也没有能力实现对优质楠木基地有效的管护。因而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号召乡民种植廉价的树种,这同样是制度体制改变后才需要实施的树种置换需要。
最后是,告示中还明确告诫乡民,如果有人偷盗,可以报官,官府可以为他们做主。然而结合当时的官府人员配置,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空头喜宴。零星的林木盗伐真要报官审理,不管是取证,还是审理,在事实上都很难及时得到公平的裁断。而且林木的生长期至少需要几十年,而官府的首脑三五年一换,要认真的审理,其客观的困难也是官府首脑无法克服的制度性障碍。因而这样的告示就实质而论,还不足以发挥消除乡民顾虑的作用。因而这样的告示,获取政绩容易,真正落到实处难度极大。但通观整篇告示,最关键的史料价值却在于,就上述四个方面而论,确实可以告诉我们改土归流后,原先的土地资源利用方式肯定发生了巨变,其中肯定包括对原先的“官山”楠木生产基地被改做它用的不争事实。否则的话,上文提及的“官山楠木无遗种矣”就很难获得正确的理解了。
立足于《历代稽勋录》有关楠木进贡的记载,不难发现,在土司统治时代,楠木的砍伐是在土司严密的管控下执行的,优质楠木的长成也必然是在严密的管控之下长成的。但改土归流后,楠木的砍伐和出卖,就会成为寻常的市场性活动,谁掌控了楠木就可以自由买卖,管控的失效也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如下一则实例可以视为对上述理解一个有力的旁证。民国十九年《永顺县志》载:
“柏,惟旧司有二株最古,约有三围餘。咸丰间,有武陵贾人以百金购之,不可得。”①民国十九年,胡履新、张孔修纂《永顺县志》卷十一《食货一·物产》。
文中提及的柏树虽然在当时没有出售,后来则肯定被出售。考虑柏树在永顺地区并不是土生物种,而是由西北相对干冷的地区引种的树种,这样的树又在土司衙门前定植了数百年,这显然是作为风景树去加以种植。况且改土归流后末代土司彭肇槐及其后裔被清廷封为伯爵,并可以世袭参将,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永顺地区的历任地方官都对该土司的遗址,遗迹下令认真保护,不许任意毁损。衙门前的风景树尚且有奸商打起了主意,那么土司官山内原先监管的大片楠木到改土归流后,会变成私自盗卖的对象也就不难理解了。[9]因而仅就这一实例就表明,楠木资源的告罄显然不是有计划砍伐所使然,改土归流后管控失灵被私人盗伐盗卖才是告罄的主因,而倒卖以后,原先的楠木生长用地如果再种植楠木,不可能确保以后的收获规制保持稳定,而改做农田用地,也就成了情理中的事情。由此可见,导致楠木资源告罄的社会原因和其间的演变过程,应当理解为如下三个方面的必然结果:
其一,产出优质建材需要持续数百年的的行政权力监管,而改土归流后这样的土司政治势力被摧毁,国家设置的府、州、县地方官员,其施政规范与内地各府县相同,主要是监管常规的农业生产。但要维护好楠木生产基地,既需要特殊的自然环境,又需要特殊的监管方式,还需要特殊的管理政策。但这些内容在常规的府县掌管职权范围内都不能包括在其中,这将意味着改土归流的实施,事实上在无意中摧毁了楠木生产的必须匹配的社会文化背景,从而导致了楠木资源的枯竭。
其二,改土归流前,朝廷对土司地区的管辖始终坚持“汉不入境,蛮不出洞”的规范,因而在改土归流前,楠木的出境都得在土司的全权监管下完成。而改土归流后,随着大量汉族木商的涌入,盗卖珍稀楠木成为政策监管的盲区,残存的楠木肯定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了致命性的摧残。因而残存楠木的盗卖,地方官不是不知道,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职责,因而他们只能是听之任之,或者是插手其中,从中获取额外的灰色收入,而这正是残存楠木资源绝迹的直接原因。
其三,改土归流后,地方官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都是致力于鼓励各族居民,特别是迁入的汉族居民实施大规模的开林种地。而他们必然要占用的土地资源,就必然包括原先的楠木生产基地,这种可积累的持续推进,最终会将此前楠木的生产基地,蚕食殆尽,以至于重新长出楠木都将成为不可能。上述引文提及的“楠木无遗种矣”都是由于无序开垦,才会弄到这样的地步。
总之,方志记载的楠木资源告罄只是一个结果,其具体过程则表现为无人监管、盗伐猖獗、林地被改做农田使用3个主要方面。到清代末年,永顺地区不仅楠木资源告罄,就连其它低档次的建材也极度萎缩。随着生态的破坏,当地各族居民陷入了贫困,一些有作为的地方官不得不出面号召各族乡民植树造林,改造生态环境。但这样的行动显然是一种亡羊补牢的被动做法,这样的做法也肯定无法推动楠木林的恢复。即令政策落到实处,也必然无法产出优质楠木,最多只能产出一般性的经济林产品。因而酉水流域楠木资源的告罄与自然环境无关,与种植技术的失落也无关,而是与行政管理体质的转型,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其他社会问题直接关联,是社会环境的变迁和纯粹的社会原因摧毁了当地的楠木生产传统。
四、结论
此前,不少学界专家总是习惯于将生态的退变简单的理解为因个人追求私利而破坏的结果,或者理解为是人口过多、耕地短缺而必然派生的无意识结果。但若与酉水流域优质建材资源的枯竭为例,却不难看出,真正造成破坏的直接原因却出在政治和政策上,即令改土归流事出有因,处置得当,在政策上可以不负责任,但在无意中派生的生态破坏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优质建材的生产需要高度稳定的、超长时段的严密监控与管护,又需要特殊的生存环境,因而维护楠木生产的制度保障系统必不可少。土司制度下土司所承担的这一职责在改土归流后没有出现相应的替代政策出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策断裂和需要认真吸取的失策教训,而历代方志所反映的内容就是这一失策的最终结果,因而这是一项来自历史的教训。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不认真考察当地的文化生态背景,不将生态维护的责任落实到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生态环境的灾变其实是在眼皮底下悄然发生的,不注意这样的变化,终将铸成不可挽回的生态罪责。
参考文献:
[1]蓝勇.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4):19.
[2]卢扬煦,等.楠木人工林林下植物物种多样性研究[J].浙江林业科技,2012(1):13-15.
[3]符太浩.溪蛮丛笑研究[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175.
[4]石开忠.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林业开发及对当地侗族、苗族社会的影响[J].民族研究,1996(4).
[5]〔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6]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西汉〕戴圣.礼记·王制[M].刘小沙,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1.
[8]龚荫.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纲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
[9]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J].历史研究,1994(6):94-97.
(责任编辑 杨军昌)
中图分类号:C9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6)03-0071-10
DOI编码:国际10.15958/j.cnki.gdxbshb.2016.03.012
收稿日期:2016-04-20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以来农作物引种对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影响研究”(15CNZ044);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物产志在探析武陵山区生态变迁史中的价值研究”(CX2015B556);国家民委生态民族学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项目“从地方志物产志看武陵山区生态变迁的机制与过程”(15jdzb09)。
作者简介:彭 兵(1993—),男,湖南永顺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态民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