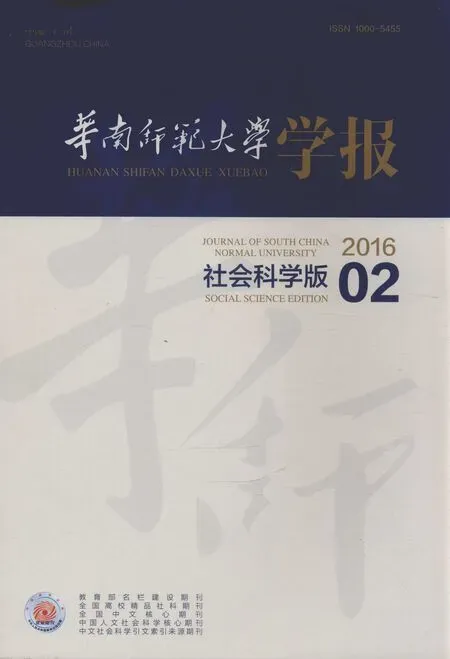公共性:唐代女性诗歌的别样视角
赵 小 华
公共性:唐代女性诗歌的别样视角
赵 小 华
【摘要】中国文学批评史对女性诗歌的评价历来不高。究其原因,许多评论忽视了女性诗歌突破私人视角、记录社会变化、书写公共事件、进入公共生活的努力。唐代女性诗歌除了表达自我情感、记录生命历程的私人视角外,也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对唐代女性诗歌公共性的探讨,是回应“绣余”“爨余”“狭隘”“单调”等批评论调的必然。
【关键词】女性诗歌唐代公共性
从《诗经》到当代,女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用笔记录社会变动、抒发人生感慨、描写心路历程和思想变化。
当唐诗以其所达到的高峰成为时代文学的代表时,唐代也是女性诗歌写作从沉寂走向迅速发展的重要转折期。不少唐代女性拿起笔,记录了那个大繁荣、大精彩与大破坏前后相继的时代,记录了她们精彩跌宕、悲欢离合的一生。尽管仍然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但唐代女性却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书写的形式表达她们真实的经验。仅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而论,其所录女诗人有168人,遍涉各阶层,构成了对当时诗坛有一定影响的女诗人群体,不仅为明清女性文学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唐代女性生活和情感的真实信息。*周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据季振宜《全唐诗》所录诗人1 895人中,女诗人有124人,占总数的6.5%。从数量上来看,唐代女诗人数量及诗歌创作量远远低于男性诗人及其诗歌创作量。然而,就文学发展历史而言,《全唐诗》卷5、卷7、卷9收录妃嫔公主的诗歌53首,卷797至卷850收名媛诗歌107家、诗535首,这几乎是先秦魏晋南北朝两千年历史时期现存所有女性作品总和的7倍,不能不算是女性文学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在《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诗文评类共712部作品中有45部作品里收集了唐女诗人的诗歌,占整个作品集的6%。*具体分析见郭海文:《唐五代女性诗歌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对于古代文学中的女性书写,历来有比较大的争议。
与男性作品评判的标准不同,女性书写首先面对的不是作品艺术品位、审美风尚的评判,而是创作者之妇道的评价。从唐朝最为著名的女诗人薛涛、李冶和鱼玄机所受到的批评便可知,这种意识已是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孙光宪认为鱼玄机“自是纵怀,乃娼妇也”*(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九,第194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计有功称李冶为“失行妇”*(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十八,第11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并将女冠称为娼妓;陈振孙评价鱼玄机:“妇女从释入道,有司不禁,乱礼法,败风俗之尤者。”*(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第5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明代胡震亨也认为:“鱼最淫荡,诗体亦靡弱。”*(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第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直到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生活》(1984年改名为《中国女性文学史话》)、陈文华的《唐代女诗人考略》等著作,依然沿袭旧说,称呼她们为“倡优”“倡妓”,批评她们“纵情”“行止最不检”*陈文华:《唐代女诗人考略》,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l期。。
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学者对中国传统的女性书写也有过极为辛辣的批评。在《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闺秀艺文略〉序》中,胡适认为女作家的“成绩都实在可怜得很。她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这近三千种女子作品之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是诗词,是‘绣余’‘爨余’‘纺余’‘黹余’的诗词”,她们“决不敢说实话,写真实的感情,诉真实的苦痛,大多只是连篇累幅的不痛不痒的诗词而已。既可夸耀于人,又没有出乖露丑的危险,我想一部分闺秀诗词的刻本都是这样来的罢……真正有文学价值的诗词,如纪映淮、王采薇之流,在这三千种书目里,只占得绝少数而已”*欧阳哲生:《胡适文集 4》,见《胡适文存三集》,第5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此言,既犀利无情,也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因为这本来就代表了大多数人对女性写作的看法。诚如谭正璧先生所言,不少批评家秉持着这样一种思路:“有唐一代女诗人,都因生活的狭隘,情感的单调,都没有什么特别成绩。”*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 第20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从两性的发展来看,男性的生命历程,大多活跃在公共空间,以建功立业、实现政治理想为人生基本抱负,其诗歌创作更多与时代、社会、政治等宏大叙事紧密结合。*不排除男性诗人也关注家庭书写,如唐诗中有不少写给家中幼子的诗。见赵小华:《父亲的记录:唐诗中的儿童书写》,载《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女性生活的绝大部分空间是家庭,其创作中落笔家庭、抒写自我心境实属必然。对拘囿于家庭生活的女性来说,自我婚姻与爱情确实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女性对于自身之生命体验、心灵感受、情感变化的体验较男性更为细腻和深邃,其描写也更加细致入微。相应地,女性诗歌更关注自我独特而私人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抒发,风格柔婉缠绵,具有书写个人历程、表达自我感情的私人特质。由此,道德评判者关注作者身份,现代批评家则冠之以“狭隘”“单调”等特点。其共同的缺失在于,忽视了女性诗歌突破私人视角、记录社会变化、书写公共事件、进入公共生活的努力。本文把女性诗歌在这方面的特色称之为公共性。对唐代女性诗歌公共性的探讨,是回应“绣余”“爨余”“狭隘”“单调”等批评论调的必然。
一、突破:私人视角的扩展
唐代士人以考取功名、求得仕宦作为读书的最终目标。无数士人奔走在宦途,却也有很多人因种种原因而面临官职的变动,甚至因意外之祸而遭贬谪。一旦面临被贬,士人往往下笔成诗,一抒胸中之块垒。这使得贬谪诗歌在唐诗中占有很大分量,也引起了当代学者的注意。贬谪与文学的关系成为诸多专著持续讨论的问题。
男性士人一旦遭贬,要承担此后果的其实并非他一人。其年迈的高堂、结发的妻子以及年幼的儿女都将共同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这其中,女性对贬谪一事的态度和感受,在以往的诗歌研究中少有得到关注。出自女性之手的相关诗歌,则为我们提供了最直接的素材。
《旧唐书》卷一四六《薛播传》记:“初,播伯父元暧终于隰城丞,其妻济南林氏,丹阳太守洋之妹,有母仪令德,博涉五经,善属文,所为篇章,时人多讽咏之。元暧卒后,其子彦辅、彦国、彦伟、彦云及播兄据、总,并早孤幼,悉为林氏所训导,以至成立,咸至文学之名。开元、天宝中二十年间,彦辅、据等七人并举进士,连中科名,衣冠荣之。”《新唐书》也有类似的记载。这位培养了七位进士的林氏,在自己的儿子被贬谪时,表现出惊人的坚毅和自信,相信自己培养出来的后代清白正直,所遭遇的不公平只是暂时的,给被贬的儿子以力量和温暖。
开元天宝年间,林氏之子薛彦辅因事左贬,林氏以诗《送男左贬诗》*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卷七九四,第五册,第328—32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下引诗歌只注篇名。送之:
他日初投杼,勤王在饮冰。有辞期不罚,积毁竟相仍。谪宦今何在,衔冤犹未胜。天涯分越徼,驿骑速毗陵。肠断腹非苦,书传写岂能。泪添江水远,心剧海云蒸。明月珠难识,甘泉赋可称。但将忠报主,何惧点青蝇。
诗歌两用典故,标明儿子忠心为政却遭诽谤的冤屈,字里行间既流露出对自我清白的坚持,又控诉迁谪之不合理,表达无端被陷害的愤慨。后面由贬谪地点之远、悲愁之重极尽夸张抒写母子间的骨肉情深;最后两句峰回路转,强忍悲痛,特别突出表现对儿子的信任和鼓励,给后者以坚持的力量。同时,也对那些谄媚小人的可耻行径表示了极大的轻蔑与痛恨。
唐代男性遭遇贬谪之不幸在诗歌中有大量抒发,而这种不幸有时也会落到一些女性头上,成为她们生命中难以忘怀之痛。
中唐女诗人薛涛,文采风流,多才多艺,不仅工为诗,还精翰墨、通音律,更创制了风行一时、流传千古的薛涛笺。出众的才情使薛涛闻名遐迩,蜚声蜀中。然而薛涛一生多次遭贬,备尝人间艰辛。
据后蜀何光远《鉴诫录》卷十记载:“涛每承连帅宠念,或相唱和,出入车舆,诗达四方。中朝一应,衔命使车,每届蜀,求见涛者甚众,而涛性亦狂逸,所有见遗金帛,往往上纳。韦公既知且怒,于是不许从官,涛献《十离诗》,诗意感人,遂复宠召,当时见重如此。”由此可知,薛涛虽身在乐籍,却是因诗才而闻名,并进而得韦皋看重;因收金帛事,被韦皋疏离,乃作《十离诗》以明志。张篷舟先生也认为《十离诗》应为献韦皋之作。*张篷舟笺、张正则等续笺:《薛涛诗笺(修订版)》,第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十离诗》借物陈情,以表达自己内心的苦衷和愤愤不平。作为组诗,且每首都有“离”字,故称《十离诗》。诗歌以十组生活中常见的、既联系又相对的事物作为对比意象,赋予犬、笔、马、鹦鹉、燕、珠、鱼、鹰、竹与镜以被动弱势的意义,俨然象征着女诗人自己;而与之相对的主、手、厩、笼、巢、掌、池、鞲、亭与台在诗中则主动强势,让人想到强大的男性及男权社会。每一组意象中的“离”,文字表达上看似主动,而实际都是“被离”。部分学者认为该诗雅道不继、毫无气节,因此大加贬斥;或谓“作者不得不贬损自己的人格来求得主人们的同情和宽恕,诗的风格不免失之卑下”*江民繁、王瑞芳:《中国历代才女小传》,第133页,浙江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然而,如果从薛涛以一介女子置身男权社会、个人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人手中的背景来加以解读,则知《十离诗》之创作,意在反躬自省、绝望哀求,由此不得不低声下气、屈己扬人。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名获罪被遣的乐籍女子,薛涛在诗中力图突破个人命运的不幸,追问原因、表达控诉、直抒心曲。这使得《十离诗》内蕴着女性对于自我遭遇不幸的真实记录和深刻反思,表现出对私人视角的突破和扩展。
从字面分析,组诗每一首的第三句都是表达具体的离/被离的原因。而对这些原因的叙述,却有细微区别。如“近缘咬着亲知客”与“都缘用久锋头尽”就有意气之不同:“咬着亲知客”是作者因错被离的原因;而“用久锋头尽”却是会发生的事实,是一种客观现象,以此而见疏被离,难免有意气不平之感。他如“只缘一点玷相秽”“无端摆断芙蓉朵”“无端窜向青云外”等语句,都可洞见作者于其中内蕴的愤懑意味。只缘,说明并非严重的问题;无端,则明白干脆地表示自己本无过错。以此而见疏,足见作者对自己遭受不白的愤怒控诉。“出入朱门四五年”“陇西独自一孤身”等句,寓身世于笔端、曲笔倾诉;“平原捉兔称高情”“追风曾到日东西”等句,表达了自视甚高、不肯将息的高远志向。总之,“《十离诗》感物伤情,直抒胸臆,不失为一组反映中唐社会人情世态以及女诗人身遭不幸的真情实感之作……绝不能把《十离诗》全看作是薛涛对权贵的乞求、哀恳、屈服,而应看到这组诗在思想内容中的积极因素以及作者对统治者的抨击和抗争”*天问:《薛涛简论(上)》,载《成都大学学报(杜科版)》1988年第3期。。
薛涛集中还有《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二首云:
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却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
黠虏犹违命,烽烟直北愁。却教严谴妾,不敢向松州。
诗歌中既有对边城苦寒战乱的白描,有对以往生活的深刻反思,也有心怀不满的曲折讽喻,想要回到成都的愿望的表达却是十分委婉。
从生命历程来说,女性也有追求自我生命、向往自由的本质需求,诚如涛诗所言:“追风曾到日东西”“常将劲节负秋霜”;然而,这样的追求往往得不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的许可和支持。如果女性的追求超越了男性所规定的范围,便会面临被“离”的命运。*薛涛集中另有《罚赴边上武相公》(二首),为上武元衡之作。则薛涛被罚边,不止一次。因得罪而被罚边,对于一个弱女子来说,其所承受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都是巨大的。
二、记录:社会变化及公共事件
仔细解读女性创作的作品,能发现不少与现实密切相关、有感而发的作品。它们充分展示了女性被拘囿在狭小的生活天地中仍然关心国家大事、感悟重大历史事件、心系国家政治的现实情怀。如《诗经·鄘风》里的《载驰》是现存最早的女诗人作品,其作者许穆夫人在卫国为狄所破时,请救于许国而不得,失望之余,发而为叹,体现出女性百折不挠决心恢复卫国的愿望与努力。东汉蔡琰的《悲愤诗》立足于个体生命的哀叹,将个人生命的重大变化放在社会重大历史事件中进行书写,读来令人涕下。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唐代。
唐代由于国力强盛,在国家礼乐制度方面不断发展完善。祭祀大典作为整个社会最盛大最隆重的事件,在唐诗中时有记载。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在国家大典里从来不得抛头露面。然而,时至武则天时期,她的众多改革方案极大地提高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甚至使得妇女在国家大典的祭祀中也开始崭露头角。武则天本人参加过封禅,主持过多项祭祀。这些都在她的祭祀大乐中得到了记载。武则天的诗歌现存于《全唐诗》47首,大多数涉及祭祀拜神、礼乐仪式等内容。武则天的祭祀诗,往往采用古朴的诗经体来写作,文辞典雅,风格古质,是她走上政坛的宣言。如《曳鼎歌》云:“羲农首出。轩昊膺期。唐虞继踵。汤禹乘时。天下光宅,海内雍熙。上玄降鉴。方建隆基。”这首诗很有《诗经》中“颂”的风采。光从形式来看,这种四言诗的形式,在唐五代女性诗歌中除武则天、韦氏用过外,其他人几乎无一涉足。而武则天的诗歌中,这种四言诗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内容也多展示皇家祭祀盛典。如《唐明堂乐章》12首,分为《外办将出皇帝行》《皇嗣出入升降》《迎送王公》《登歌》《配飨》《宫音》《角音》《徽音》《商音》《羽音》等,其词藻华丽,内容多歌颂祖先、祈求福社。武则天这类诗歌还有很多,如《大享拜洛乐章》15首、《唐李吴天乐》12首等。这些以“颂”为主要形式和内容的诗歌,既继承了《诗经》中“颂”的传统,又以其宏大气势对唐诗从初唐到盛唐的转变起到了引导性作用,更昭示了武则天在政治上的成功。
宫廷中其他有才华的女性也用诗歌记录了她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其中,宫廷应制赋诗是最常见的活动。太宗朝以《谏太宗息兵罢役疏》备受史家赞颂的徐惠,现存《奉和御制小山赋》《赋得北方有佳人》《秋风函谷应诏》等诗,表明她经常在太宗宫廷应制赋诗。*此可补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之缺。该书第一章详细考述了贞观宫廷诗人群唱和活动,考得太宗群臣唱和诗二百一十四首又二断句,文赋十三首,预唱诗人四十五人。不论是诗文还是作者的统计,都没有将徐惠计算在内。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第12—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秋风函谷应诏》起首即云:“秋风起函谷,朔气动山河。偃松千岭上,杂雨二陵间。”写得意境壮阔,一扫应制诗之因袭旧言。上官婉儿极富才华,《旧唐书·后妃传》记:“婉儿每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数首并作,词甚绮丽,时人咸讽颂之。”*《旧唐书·后妃传》卷五一,第217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她的不少应制诗既记录宫廷大事,又一洗应制体一味颂美的沉闷风气,表现出难得的清新俊美。《驾幸三会寺应制》以“四山缘塞合,二水夹城流”的动词连用,描绘出风景如画的自然胜景,更有恢弘徐远的气象内蕴其中。《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之一云:“三冬季月景龙年,万乘观风出霸川。遥看电跃龙为马,回瞩霜原玉作田。”本是写皇帝出游的歌颂之词,却通过马队快速如龙腾、原野覆霜似白玉的景物转换来抒发皇家气派和盛世豪情,非胸中有丘壑者不能为之。所以有学者评价,上官婉儿的应制诗“极富生气,不但写得清新,而且写得大气,一洗委靡之风”*王卢生注译:《大唐才女上官婉儿诗集》,第1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唐代边事不宁、战事频繁,边塞诗派的兴起有其现实基础。历来讲唐代边塞诗人,大都关注高适、岑参等诗人。唐代妇女在边塞诗中往往成为男性诗人笔下的思妇符号,缺乏生动的感情和具体的活动。而女诗人自己拿起笔创作的边塞诗中,情形便大不相同了。鲍君徽的边塞诗《关山月》云:“高高秋月明,北照辽阳城。塞迥光初满,风多晕更生。征人望乡思,战马闻鼙惊。朔风悲边草,胡沙暗虏营。霜凝匣中剑,风惫原上旌。早晚谒金阙,不闻刁斗声。”描写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征人艰苦的生活环境,兵士久戍不归的凄苦和渴望结束战争的心情跃然纸上。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唐代边塞诗是一个包容内容很广的概念,不仅描写边塞战争场面、边塞风光、民族交往以及将士情感的诗算作边塞诗,反映边塞将士家中思妇生活和情感的诗也应算作边塞诗。”*任文京:《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第186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裴羽仙有《寄夫征衣》:“愁捻银针信手缝,惆怅无人试宽窄。”侯氏有《绣龟形诗》:“闻雁几回修尺素,见霜先为制衣裳。”末云“绣作龟形献天子,愿教征容早还乡。”龟,用谐音“归”也,饱含了希望丈夫早日归来之意。据说这首诗情真意切,打动了唐武宗,不仅赏赐侯氏,也如其所愿让她丈夫归乡。陈玉兰《寄夫》更写得情真意切:“夫戍萧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这种绝望的追问、从女性角度选取最关冷暖的关心,令人对于边塞征战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说到和亲,人们经常感叹的是“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王昭君,其中包含了对女性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国运的思考。在强盛的唐代,和亲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唐会要》卷六“和蕃公主”一节,列许多和亲公主在其中,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等。名列其中的宜芳公主也很有名,这不仅来自她的和亲,更来自她所作的诗。《虚池驿题屏风》云:“出嫁辞乡国,由来此别难。圣恩愁远道,行路泣相看。沙塞容颜尽,边隅粉黛残。妾心何所断,他日望长安。”唐代关于和亲的诗歌有不少,但大多都是男性诗人的有感而发。和亲牺牲的是女性的终身幸福,女性诗人对此的感慨也许都被淹没在历史的风沙中了。作为亲历者的宜芳公主所留下来的诗,就更加弥足珍贵了。诗歌对于自己辞亲离乡、去国千里、杳无归期、任如花的容颜在漫天风沙中凋零的悲惨命运进行了勾画。此诗写得虽然含蓄,但由于是在交道要道的驿站屏风所题,仍然显示出很强的控诉味道。
三、对话:进入公共生活的努力
从对话角度切入研究女性作品,可以蔡瑜为例。她认为唐代女性诗作在形构上具有两个特点:“首先是,作品多采用问话或预设倾诉对象的话语姿态,其次是,为数众多的作品为四句或八句的短诗。”男性诗人之诗中的问句形式,常常是自问自答或采自我辩解的姿态,是一种“独自式的对话”;而唐代女性诗作中的“对话”表现,同时存在“倾诉”与“倾听”的特质,“处处显示出不以自我陈述为满足,而是期待回音、谛听变化、准备再度反应的流动性。因而,诗的叩问语气预留了响应的空间,简短的形式显示出倾听与倾诉同样热切的心理倾向”*蔡瑜:《从对话功能论唐代女性诗作的书写特质》,见张宏生编:《古代女诗人研究》,第145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由此,文章透过对话、情境、关系的交互作用来谈唐代女性诗作在特定关系、具体情境下的对话;并具体分析语言、现身、对象诸因素在女性诗作中的交织。由此,作者希望重读唐代女性诗作,寻找出女性书写与男性书写可能的分离点。
受此启发,俞世芬在分析唐代女性创作时也提出了对话的问题,认为对话作为非常有效的抒情策略,承担了女性突破沉默、确认自我的性别反抗。
对话体现了诗人借助诗寻求与说话对象的交流、期待与男性社会互动沟通的目的……唐代女性诗歌中的对白,不是通常意义上文本的对白形式。它实际是指诗人的写作态度提供给作品的一种对话性:叙述人或抒情者期待来自对象的倾听与应答,从而使自身参与到多元的社会生活与感情世界中去。以数量众多的爱情诗为例,希望得到倾听,获得情感上的认同与体贴,从而实现情感的沟通和生命的交流,是女诗人自觉的创作目的。*俞世芬:《边缘抒情:论唐代女性诗歌的“复调性”》,载《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5期。
无疑,对话视角的分析有一定可行性,对于揭示女性创作时的心理活动、写作意图等都有一定作用。然而,即便女性在写作中倾注了满满的对话意图,其愿望往往还是会落空。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哪怕采用了强烈的质问,大多数还是得不到平等对话的机会。
由此,女性创作中充满了无法回答、无人回答的“对话”。如程长文《春闺怨》的“良人何处事功名,十载相思不相见”,问语中充满十年的思念和心酸,何其沉重!鱼玄机“书信茫茫何处问?持竿尽日碧江空”(《情书寄李子安》)一联写尽了问而无答的尴尬;“水柔逐器知难定,云出无心肯再归?”(《送别》)明知男子如水云般朝三暮四、用情不专,所问也是徒劳无益。薛涛《十离诗》之《鱼离池》《鹰离鞲》有“无端摆断芙蓉朵”“无端窜向青云外”句,表明被离的原因。两个“无端”的连续使用,首先从语气上界定了被离之因不可成立、所遭乃飞来横祸,从意思上也明白地传达了作者本无过错却要承担严峻后果的愤懑不平之气,试图展开对话、获知答案的心绪一览无遗。其声气之激越,与《十离诗》中其他诗歌的反躬自省、屈己扬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赵小华:《女性生存困境与诗歌风格之形成——以薛涛其诗其人为例》,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3期。
薛涛的过人才华和特殊身份使得她有不同于一般闺阁女子的广泛社会交往,诗歌内容也多为与当时名公文士的酬赠唱答。*据张篷舟先生考证,和薛涛唱和的,除了韦皋、高崇文、武元衡、王播、段文昌、李德裕等六届镇帅外,还有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严绶、张籍、王建、杜牧、刘禹锡、吴武陵、僧广宣、韦正贯、萧祜、卢士玫、李程、张元夫、段成式等文坛名士、仕宦名流;只有姓氏、官衔或排行,现尚未知名字者,共有十六人。此外,虽无姓氏、官衔或排行,但涛诗确为与人唱和者,亦有四首。见张篷舟笺、张正则等续笺:《薛涛诗笺(修订版)》,第98页。由此,薛涛诗多呈现出一种对话态势。
蜀地历经战乱、百业荒废,这使得在高崇文平乱之后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武元衡连连感叹:
悠悠风旆绕山川,山驿空濛雨似烟。
路半嘉陵头已白,蜀门西更上青天。
薛涛有《续嘉陵驿诗献武相公》与之展开对话,接续原诗“蜀门西更上青天”,却翻出新意:
蜀门西更上青天,强为公歌蜀国弦。
卓氏长卿称士女,锦江玉垒献山川。
身为蜀人,历蜀地多年战乱,薛涛对于镇蜀难深有体会,因此能认同武元衡的观点;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历经战乱,现在的蜀中人民更有着对和平生活的强烈渴望,杰出的蜀中人物与秀丽的蜀中山川亟待呈现其美好的一面,期待新川主能够带来新的变化。短短四句诗,展示了人杰地灵的川蜀之地。因其强烈的对话性,既以历史和事实来宽慰新主,又充满热情和期待,给来者以温暖和力量。
薛涛之诗,常以对话为方式,表达其关心现实、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如《贼平后上高相公》云:“惊看天地白荒荒,瞥见青山旧夕阳。始信大威能照映,由来日月借生光。”高相公,指高崇文。永贞元年,刘辟据蜀,朝议讨伐。元和元年九月,高崇文平刘辟之乱,薛涛作此诗以上。诗以叛军造成西蜀大地生灵涂炭引起,内蕴对民众疾苦的关怀;以青山映照旧夕阳来表达贼平后人民生活恢复正常的欣慰,反映出对朝廷的充分信任和对平定叛乱军队的高度赞扬。这类尝试对话、直抒心意、关注政治局势和民生疾苦的诗歌,薛涛还写了不少。如她最有代表性的《筹边楼》诗云:
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
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
筹边楼,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后所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新唐书·李德裕传》记,筹边楼建好之后,李德裕命人在四壁绘蛮夷险要,观察西南两面的山川形势、召集将士商量筹划,这些活动都是在筹边楼上进行的。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危机是内外交困。由于纪律涣散、藩镇统领无绪、贪得无厌,经常发生抢夺周边地区少数民族财物牲畜的现象,扰乱了边民的和平生活。是以,涛诗直接与这些将士对话,以“诸将莫贪羌族马”之语直斥唐军扰民,表现出超凡的勇气和胆魄。难怪《名媛诗归》评此诗说:“教戒诸将,何等心眼!洪度岂直女子哉,固一代之雄也。”*(明)钟惺:《名媛诗归》,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三三九册,第153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应该说,“教戒诸将”的评语直接抓住了薛涛诗歌的对话性本质。
由于传统文化的偏见,古代女性的文学书写更容易被进行道德评判而非艺术品味;由于个体生活空间的不同,古代女性的文学书写更容易被冠以狭隘单调之名。传统文学批评史往往忽视女性诗歌在突破私人视角、记录社会变化、书写公共事件、进入公共生活等公共性方面的努力。作为社会的存在和在社会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群体,唐代女性在诗歌中除了表达自我情感、记录生命历程的私人视角外,也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这方面的探讨和研究,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
【责任编辑:肖时花】
(作者简介:赵小华,四川宜宾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政治与行政学院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6)02-0145-06
【收稿日期】2015-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