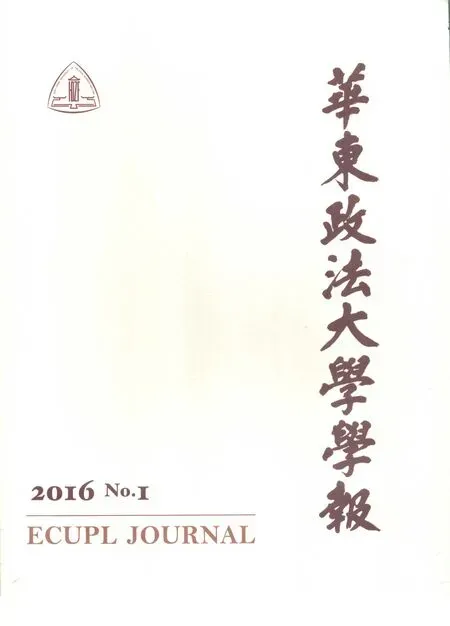网络著作权侵权中“直接侵权主体”判断的规范构成
——以“私人复制例外”的合法范围确定为中心
张 鹏
网络著作权侵权中“直接侵权主体”判断的规范构成
——以“私人复制例外”的合法范围确定为中心
张鹏*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直接行为主体”判断问题上“从属说”适用难题的克服
三、“私人复制例外”的合法范围与“直接行为主体”判断
四、我国著作权法上“直接侵权主体”判断的模式选择
五、结语
著作权法上普遍认为应该依据“从属说”处理直接行为与间接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一观念将导致直接行为构成“私人复制例外”时,无法追究间接行为人的侵权责任。面对这一难题,比较法上一般通过扩大拟制“直接行为主体”解决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责任追及问题。对此,应从导致“直接行为”非侵权构成的宗旨与构造出发,对于“直接行为主体”支付过对价且在权利人预期之内的作品利用行为,不应因服务提供商在技术上较为深入地参与这一过程而将其拟制为“直接侵权主体”;相反在不满足上述条件时则可通过“直接行为主体”的拟制,解决“从属说”下服务提供商责任追及难题。我国著作权法修改中体现的逐步缩小“私人复制例外”的做法,应受到批评,以期找到平衡著作权人利益与公众享受技术进步便利的接点。
直接侵权主体间接侵权主体从属说 私人复制例外向公众传播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
在著作权法理论中,始终存在着“直接侵权行为”与“间接侵权行为”的划分,而这种划分就根源于著作权侵权构成的特殊构造之上,即著作权法并不是对于作品的一切利用行为赋予排他权,而仅仅针对法定的某些利用行为设置了“专属领地”,只有未经许可实施这些法定利用行为,并在缺乏法律上免责事由的情况下,才构成著作权“直接侵权”。〔1〕王迁:《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页。一般来说这种“直接侵权”的构成是围绕“复制权”与“向公众传播权”两大支柱建立的。〔2〕参见郑成思:《版权法》(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第三人对于这两大权项侵权行为的教唆帮助及参与支持,除非在一国著作权法中存在对此规制的明文规定,否则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民法上的共同侵权行为或规制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予以解决。〔3〕参见崔国斌:《网络服务商共同侵权制度之重塑》,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如果依据民法规则处理“间接行为”侵权构成的话,与专利法上处理“直接”侵权行为与“间接”侵权行为关系问题上可能存在的“独立说”构成不同,普遍认为应该依据“从属说”处理直接侵权行为与间接侵权行为之间的关系。〔4〕王迁:《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即在专利法上处理专利零部件提供商间接侵权责任时,通过施加“专门用于侵权用途”要件,就可以起到脱离“直接”侵权行为独立追究间接行为人责任的救济实效性;而“专门用于侵权用途”这一要件在著作权间接侵权责任追及过程中几乎难以起到任何规范作用,因为几乎没有哪种供作品利用者使用的设施或服务是不具备实质非侵权用途的,故而著作权间接行为的违法性基础只能来源于间接行为人对于直接行为违法性的主观认识。如果脱离了直接侵权行为的违法性而追究间接行为侵权构成的话,将会突破著作权法上以法定利用行为作为侵权要件的构造,使得第三人丧失对于自身行为违法与否的可预见性,进而阻碍促进作品复制与流通的创新性活动的开展。〔5〕田村善之:《著作権の间接侵害》,载《著作権法の新论点》,商事法务2008年版,第259-306页。
上述处理“直接行为”与“间接行为”关系上的“从属说”构成在法律效果上主要体现在“间接行为”两种不同类型的侵权判定上。其一是间接行为是诱发“直接侵权行为”大量发生的中介;其二是“间接行为”仅仅扩大了私人用户合法利用作品行为的范围。前者的典型就是P2P软件提供商对于最终用户违法上传作品所承担的帮助侵权责任;〔6〕典型的有A&M Records, Inc.v. Napster,Inc.,114 F. Supp. 2d 896(N. D. Cal. 2000);In re Aimster Copyright Litiation, 334 F. 3d 643(7th Cir. 2003);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v. Grokster, 125 S. Ct. 2764(2005)等。参见熊琦:《著作权间接责任制度的扩张与限制——美国判例的启示》,载《知识产权》2009年第6期。后者的典型就是为私人提供云储藏服务、〔7〕如美国关于云储存服务(locker storage)的Capitol Records, Inc. v. MP3tunes, LLC, 821 F. Supp. 2d 627 (S.D.N.Y. 2011) 案。提供跨区域视频传输服务〔8〕如美国关于网络电视传输服务的Cartoon Network v. CSC Holdings, 536 F.3d 121 (2008);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ies v. Aereo, 134 S.Ct.2498(2014)案。以及提供书籍电子化服务〔9〕如日本关于书籍代理电子化服务的東京地判平成25.10.30平成24(ワ)33533 [ユープランニング]; 東京地判平成25.9.30平成24(ワ)33525 [自炊代行訴訟]案。等服务提供商的侵权判断问题。对于前者由于总能找到可资评价违法性的直接侵权行为,因此在“从属说”构成下并不存在突出的问题;而对于后者正是因为“从属说”的存在,导致在“直接行为”构成“私人复制例外”的情况下,由于“直接行为”不构成“直接侵权行为”,故而无法追究“间接行为”的侵权责任。特别是对于将商业模式建构在“私人复制例外”这一“直接行为”免责之上的服务提供商来说,其服务内容本身就是针对最终用户的合法行为提供技术支持或设备便利,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权利人追究服务提供商间接侵权责任时,很难寻找到直接侵权行为。对此,通过区分“直接”与“间接”行为,在承认直接行为不构成侵权的基础上,针对间接行为所涉及的设备征收补偿金的做法,在前数字时代被普遍认为是较为妥当的保护模式。〔10〕其典型就是发生在前数字网络时代的美国索尼案(University City Studios, Inc. v. Sony corp. of Am, 464 U.S. 417(1984)),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索尼公司提供录像设备的行为非以侵害著作权为主要用途,无需承担间接侵权责任。诚然,单个最终用户家庭内私人复制行为由于对著作权人造成的损害轻微,且考虑到权利行使成本高昂等市场失败现象,一般均承认个人用户在私人领域复制的自由,但是由于索尼公司录像设备的提供导致了单个私人复制造成的轻微损害的聚积,对于权利人来说,出于“一网打尽”目的摧毁其商业模式正当性也难以否定。正因为如此,在索尼案败诉后,通过家庭内录音法(AHRA)的立法,对于消费者非商业目的使用的录音录像设备、录音录像载体导入了补偿金制度(第1008条)。同样的实践也见诸于大陆法系国家,只不过由于理念的不同,在私人复制补偿金的认识上体现出了两种典型差异,即“作为政策实现手段的补偿金制度”与“作为权利实现手段的补偿金制度”的对立(上野達弘:《私的録音録画補償金制度をめぐる課題と展望》,载《ジュリスト》2014年第1463号,第29页)。
而伴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对于作品的复制行为更加简便,多功能数字载体的普及也使得均还原成二进制数字代码的复制品与原件在质量上几乎不存在任何差距,复制成本更加微乎其微,加之互联网技术的勃兴,使得在前数字时代不可想象的跨越“时间”、“地点”与“载体”的作品利用行为成为现实。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包含了服务提供商的贡献,并体现出了难以清晰区分最终用户“直接行为”与服务商“间接行为”界限的商业模式。如果放任此种服务的存在将导致权利人通过排他权设置价格差别〔11〕Wendy J. Gord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Price Discrimination: Implications for Contract”, 73 Chi.-Kent. L. Rev. 1367(1998).的手段难以奏效,因此比较法上也存在将服务提供商拟制为“直接行为主体”,使得其无法适用“私人复制例外”。但是此种做法旨在阻止为最终用户提供技术便利与网络服务的商业活动,最终也将导致利用者本应享受的作品效率性地跨越“时际”、“区际”与“载体”的利用活动难以实现。因此如何处理此种服务提供商的责任构成问题已成为数字网络时代著作权侵权判断领域“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
对此问题,我国学说与实践体现出了两种倾向。其一是由于《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1款作为规定网络服务商承担侵权责任的一般性规定,直接指出了网络服务商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时应承担民事责任。而此处的“权益”不限于著作权法明文规定的构成法定利用行为的侵害,因此脱离直接行为的违法性判断,“独立”地评价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责任是有存在空间的。特别是《侵权责任法》在责任承担方式上较大陆法系诸国更趋于多元化,〔12〕魏振瀛:《论请求权的性质与体系——未来我国民法典中的请求权》,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4期,第399-403页。并以侵权责任来统合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和返还原物等责任承担形式,因此通过《著作权法》中的特别立法规制间接侵权行为与利用《侵权责任法》中一般性规定在效果上并不存在本质区别,这也导致我国司法实践倾向于直接衡量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责任构成。但是由于《侵权责任法》中的规定过于抽象,并未具体到针对哪种服务提供行为可以行使停止侵害请求。如果仅仅依据服务提供商的主观违法性进行判断的话,可能会将技术性辅助最终用户合法作品利用性质的中介服务也纳入规制范围,造成停止侵害请求谦抑性的丧失。其二是通过限制“私人复制例外”的适用范围,使得大量最终用户所从事的“直接行为”构成“直接侵权行为”。从规范层面看,《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规定了 “个人使用例外”,但与比较法上的“私人复制例外”条款相比在适用范围上仅限于个人,即强调该款所指的是个人使用,而不是私人使用。〔13〕例如日本著作权法中的私人复制例外的适用范围包括个人、家庭及类似范围之使用(第30条)。个人使用意味着只允许复制一份,而私人复制则可以制作多份复制品。〔14〕韦之:《著作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最新《著作权法修改草案》〔15〕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来源:http://www. 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406/20140600396188.shtml,2015年4月1日访问。中,将该款规定修改为“为个人学习、研究,复制他人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的片段”,这使得“个人使用例外”的适用范围再次受到极大地缩减。从效果上看,这一规定可能直接导致了绝大多数利用者在私人范围内的作品利用活动构成侵权状态的持续。举例来说,对于云储存服务,个人以文件备份等为目的将文字、视频等作品上传网络云端并供自身下载的行为由于不构成文字作品的片断,因此构成著作权直接侵权,而提供云储存服务行为的主体则有可能通过间接侵权被追究责任。
我国的上述实践对于诱发“直接侵权行为”大量发生的中介服务提供商的责任追及不会出现显著偏差,但是对于仅仅扩大了私人用户合法利用作品行为范围的服务提供商的责任追及则可能带来扩大性效果,进而不当地阻止该类服务的开展。事实上,第二类间接行为的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服务中有一大部分正是因为“私人复制例外”存在的合理性而应予免责的服务类型。此外,限缩“私人复制例外”的适用范围,尽管可以使得“直接侵权主体”的判断不存在疑义,但是会极大地限制私人空间内活动的自由,并使绝大多数日常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作品利用行为沦为违法状态,为公权力介入私人自由空间创造便利,因此也应思考“直接行为主体”判断与“私人复制例外”合法范围的关联,以期在排除间接行为诱发私人违法复制的积聚效果的同时,扩大用户私人复制内的自由空间。
因此,本文将以网络著作权侵权判断中的“直接行为主体”为切入点,探讨其认定上的规范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求我国著作权侵权判断中“直接行为主体”的规范涵义。笔者希望阐明的是:应从导致“直接行为”非侵权构成的“私人复制例外”的宗旨与构造出发,对于直接行为主体支付过对价之后,并在权利人预想范围内进行的作品利用行为,不应因服务提供商在技术上较为深入地参与这一过程而将其拟制为直接侵权主体。我国著作权法中体现的逐步缩小“私人复制例外”的做法特别应该予以批判,这样才有利于找到平衡著作权人利益与公众享受技术进步便利的接点。
二、“直接行为主体”判断问题上“从属说”适用难题的克服
区别于诱发“直接侵权行为”大量发生的中介服务,扩张私人对于作品利用范围的服务模式主要集中在“时际”、“区际”以及“载体”转移之上,对于上述以“私人复制例外”为基础建构的商业模式,如何追及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责任成为了问题的焦点。如果直接利用者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行为,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既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也不构成独立的侵权行为,因而必须寻求其他解决之道。〔16〕参见李扬:《日本著作权间接侵害的典型案例、学说及其评析》,载《法学家》2010年第6期。从既有学说角度看,〔17〕参见郑重:《数字版权法视野下的个人使用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具体方案不外乎三种:其一是针对各类型商业模式通过立法作出特别规定,将其视为独立的著作权侵权行为;〔18〕这一方案不失为釜底抽薪的良策,但是难点就在于面对纷繁的服务提供类型,究竟应将何种类型纳入规制范畴,以及通过何种要件明确地划定边界。此外该种模式也可能因为技术的迅速发展而丧失规制的实效性。其二是要求提供具备实质非侵权用途的数字复制载体的生产者或者提供者向著作权人或者邻接权人支付适当复制补偿金;〔19〕这一方案,普遍认为嚆矢于1965年西德著作权法的私人复制补偿金制度。尽管在前数字时代有效地解决了利益平衡问题,但是在数字时代各国反而都在思考如何限缩其在多功能数字设备上的适用空间。在前数字时代的补偿金设置上,可以通过空白磁带的补偿金征收,实现复制频率较多的复制者与复制频率较少的复制者在征收补偿金上的自然差别。而对于多功能数字载体征收补偿金的话将无法产生自然区别,因此交叉补贴现象明显;此外,不仅在利用人间交叉补贴现象广为存在,在权利人间也存在着这一现象,由于征收上来的补偿金与应该取得补偿金的权利人间难以产生准确的分配,故而造成某一著作权人对于其他著作权人的补贴(Jeremy F. DeBeer, Locks & Levies, 84 Denv. U.L. Rev. 168(2006))。而有学者主张的对于非营利性P2P文件传送行为一律设置著作权限制规定,并对网络接续控制上征收补偿金的观点(William W. Fisher, Promises to Keep: Technology, Law, and the Future of Entertain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仍旧难以避免交叉补贴现象的发生。此外在技术措施与数字许可较为普遍的时代,仍旧征收补偿金,相当于对消费者二重收费,增加了利用作品的成本 。总而言之,对于数字载体征收私人复制补偿金的实践,各国都在踟蹰中盘旋,很难做出划一的决定(参见小嶋崇弘:《欧州における私的複製補償金制度を巡る近時の動向》,载《A.I.P.P.I.》2014年第59卷第1期)。其三是将服务提供商拟制为“直接行为主体”,进而免于著作权限制规定的适用。
其中第三种方案,直接涉及“直接行为主体”的判断问题。各国司法实践也较为积极地采取了此种模式。即由于服务提供商在商业实践中深度参与了“直接行为人”的复制行为,因此在满足一定要件的前提下,通过扩张解释“直接行为主体”的范围,将物理意义上“直接行为主体”判断,即何者在物理意义上亲自实施了作品的复制,扩张到经济价值或社会通识意义上的判断,即何者可以拟制为直接行为人。举例来说,一般私人复制例外允许作品在家庭及类似范围内共享,但是如果法人面向超出家庭范围内的群体共享复制品的话,则超出了私人复制例外的范围,构成复制权的直接侵权。因此将物理意义上或自然属性上非直接行为主体的间接行为人拟制为直接行为主体,可以避免由于物理意义上的直接行为主体构成私人复制例外免责的困境。
对于“直接行为主体”进行扩大性拟制的手法是解决上述问题的较为朴素的想法,而且也在比较法上被普遍使用,区别只在于拟制的程度上。其中日本通过“卡拉OK”法理的运用全面地拟制性判断“直接侵权主体”,〔20〕参见李扬:《日本著作权间接侵害的典型案例、学说及其评析》,载《法学家》2010年第6期。而德国则是在维持以物理意义判断“直接行为主体”的原则下,例外性质地拟制了“直接行为主体”。〔21〕横山久芳:《ドイツ著作権法における間接侵害の規律のあり方》,载高林龍:《知的財産法の国際交错》,日本評論社2012年版,第135页。但是事实上这一模式的最大弊端就在于“拟制”的扩大倾向导致的可预见性降低,进而对于新技术下商业模式的创新带来抑制效果。以日本“MYUTA”案所代表的“载体”转移商业模式为例,〔22〕東京地判平成19.5.25平成18(ワ)10166。伴随着技术环境的变化,如果最终用户可以轻易地从市场购得将CD音源载体转移到移动手机的软件的话,可以预料在将来这一时点,对于此种软件的生产与销售行为将不会被视为侵权行为,因为最终用户可以在私人范围内通过一般软件进行这一技术操作,而不需再借助服务提供商的技术支持。对于将来某一时点随着技术普及而合法的行为,如果在现在这一时点因为技术尚未普及而被判定为侵权的话,到底在哪个技术成熟时点,违法行为将转化为合法行为的判断将会模糊不清,更重要的是对于新技术的普及也将产生过度抑制的效果。也就是说现在这一时点此种服务的实践均因侵权而被迫停止,只有在该技术成熟到一般性普及于最终用户时才可以在市场上合法化流通。这样的话,最终用户享受新技术的步伐将被大为延迟。〔23〕田村善之:《日本の著作権法のリフォーム論》,载《知的財産法政策学研究》2014年第44号,第40页。另一方面,从著作权人的角度看,本来已经赋予其通过自身研发阻止他人将CD音源载体转换到移动终端的技术保护措施防止此种商业模式的诞生,而这一措施也受到著作权法的保障。由于其并未开发与实施该技术措施,而是寄希望于通过技术障碍阻止最终用户的行为。此时,著作权人就应该意识到随着技术的进步,市场上将诞生针对技术屏障而提供的服务,因此并不需要为了著作权人利益的保护而阻碍新型技术下建构的商业模式。〔24〕参见王迁:《“技术措施”概念四辨》,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再以纸质图书的电子化为例,〔25〕以日本司法实践为例,由于《日本著作权法》在“私人复制例外”适用的行为手段上排除了利用人以供公众使用的自动复制设备进行复制的行为。同时在1984年日本著作权法修改中针对“自动复制设备”在附则中进行了限缩性解释,即认为“自动复制设备”不包括专供文书或图画复印的设备。所以如果店内提供的设备构成专供文书或图画复印的设备时,满足“私人使用例外”;而对于店内提供的供个人复制录音录像制品的设备,则排除在私人使用的行为手段之外。从更加实质的角度来看,对于此种服务的提供,并不在于实际操作复制技术全过程的主体是否为个人,而在于复制的内容是由哪一主体决定的。尽管最终的复制行为形式上是由个人完成的,但是实质上书籍选择范围经过了店家的筛选,通过拟制复制行为的规范主体是营业性扫描复印店可以认定其构成复制权侵害,从而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服务商为携带书籍到店内的个人用户复制书籍(東京地判平成25.10.30平成24(ワ)33533 [ユープランニング])或个人用户将书籍邮送至服务商,由服务商扫描后将电子文本传送给用户(東京地判平成25.9.30平成24(ワ)33525 [自炊代行訴訟])的情况,其共性特征在于所复制书籍的内容及种类均由个人用户选择,而物理上的复制行为由经营者操作。而日本法院在实践中判决两种商业模式均不构成个人用户的私人复制例外,而应视作经营者的复制行为,从而实现了权利人的侵权责任追及。田村善之:《日本の著作権法のリフォーム論》,载《知的財産法政策学研究》2014年第44号,第40页。对于日本司法实践中认定的服务提供商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的判断,学说上提出了许多质疑,其中有观点认为,委托他人复制的行为,只要满足了以下三个要件,即应认定用户构成“直接行为主体”:用户与服务提供者间存在就复制书籍的委托合同,并支付服务报酬;服务提供者依用户的指示从事物理性复印活动;复印的全部复印件由用户受领。而允许此种商业模式存在的实质理由则在于促进出版社低价提供电子版书籍。事实上现实中尚未罹于著作权保护期限的书籍大量存在,而真正出版的电子书籍只占很小一部分。其中,还包括许多认为没有必要禁止私人复制活动或是孤儿作品的著作权人,因此如果否定私人复制者委托他人从事纸质书籍电子化活动的话,将会使得通过书籍的电子化方便阅读和储存的技术便利消失。因此只要是用户并未利用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书籍,而是自行购买并携带书籍委托服务提供者复制的,应该构成“直接行为主体”。而著作权人如果认为正是由于电子化图书大量生产导致了市场上未经授权的盗版图书在数字网络环境下更容易流通的话,就应该积极地将电子书籍的价格降低到私人电子化书籍成本以下的价格销售,从而通过市场竞争排除此种行为的存在,〔26〕田村善之:《日本の著作権法のリフォーム論》,载《知的財産法政策学研究》2014年第44号,第95页。而不应该一概排除服务提供商的服务提供行为。
对于跨地域作品传输中“直接侵权主体”的认定,从日本司法实践可以看出,除了个别下级法院较为谦抑地认定最终用户为“直接行为主体”外,几乎所有判决都扩张解释了“直接行为主体”,将服务提供商拟制为直接行为主体,进而追究其直接侵权责任。〔27〕大阪地判平成17.10.24判時1911号65页(“選撮见録”案);知財高決平成17.11.15平成17(ラ)10007(“录像网络”案);最判平成23.1.20民集65巻1号399页(ロクラク案)。这一做法从效果上直接阻碍了新型商业模式的发展,而最终用户也不能够享受因技术进步带来的作品利用上的便利。试想在前数字网络时代用户家庭内定时录像、多频道选择录像属于“时际”转移,构成合理使用。但是由于技术限制,除非用户身赴外国否则无法实现“区际”转移。在数字网络时代,用户亲自购买作为市场上一般流通的复制设备,并将其置于外国某一服务提供商处,通过网络选择欲录制内容,并与服务提供商形成一对一的传输关系,从而实现了跨地域的节目欣赏。〔28〕美国近期的Aereo案实际上也是此种商业模式。同样是私人范围内的复制行为,仅因为服务提供商相比于“时际”转移服务更多地介入了复制与传输的技术过程就产生合法行为违法化的转变效果,不禁令人质疑其拟制“直接行为主体”的正当性。从这类案件的本质看,更多地体现了对于某一行业垄断利益的维护。以日本“ロクラク”案为例,原告就是各地电视台,他们为了维护事实上的地域垄断,即日本实行电视台地域牌照制度,维护各地方电视台在其地域内的垄断,限制其他地域内电视台节目在本地域内的流通。而被告服务不仅针对身处海外的希望收看日本电视节目的用户,而且某一地域外希望收看其他地域电视节目的用户同样可以享受这一服务。因此,法律上的垄断因为技术上的突破而形同虚设,故而各电视台极力封杀这一服务模式。事实上与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服务相比,只要各电视台根据市场的需求创设跨地域电视节目转播服务的话,将是极其具有竞争优势的,因为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商业模式为了规避著作权侵权风险,往往是非效率性的。但是,他们拒绝改变商业模式,而一味封杀他人新型商业模式,这一做法从竞争政策上看也是颇受质疑的。〔29〕田村善之:《日本の著作権法のリフォーム論》,载《知的財産法政策学研究》2014年第44号,第44页。
综上所述,扩大性拟制“直接行为主体”的实质在于:某一行为由于行为主体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侵权判断上的本质差异。既有认定“直接行为主体”的方案不管是依据物理意义标准还是实质参与性标准,都忽略了“直接行为主体”认定与著作权限制规定的实质性关联。它们均以“私人复制例外”作为判断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认为对于私人范围内的复制行为如果认定私人为“直接复制主体”的话,就不存在间接侵权存在的可能性,故而需要拟制“直接行为主体”为服务提供商。事实上,脱离“私人复制例外”这一免责规定存在合理性基础的拷问以及合法范围的探寻是无法真正理清“直接行为主体”判断的规范涵义的,因此本文进而提出对于扩张私人复制范围的服务提供行为只有在“私人复制例外”判断中才能准确定位“直接行为主体”的认定,以下将详细介绍“私人复制例外”的合法范围与“直接行为主体”判断构成。
三、“私人复制例外”的合法范围与“直接行为主体”判断
传统上对于“私人复制例外”的理解存在两种不同的合理化基础。一种是认为在个人、家庭以及类似闭锁范围内微量作品利用行为应予免责。〔30〕加戸守行著:《著作権法逐条講義》,著作権情報センター2006年版,第225页。也就是说本来私人复制行为也应纳入著作权人排他权范围之内,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利用行为也构成侵权行为。但是,考虑到权利行使成本过高等市场失败现象,〔31〕Wendy J. Gordon, “Fair Use as Market Failure: A Structur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Betamax Case and Its Predecessors”, 82 Colum. L. Rev.1600(1982).而通过立法放弃对此领域的规制。另一种是认为对于利用者已经支付过对价的作品为确保其后续私人范围内利用自由。也就是说私人复制行为本身并不是违法行为,而是维护私人自由活动空间的体现,即使由于损害的积聚或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私人复制可以为排他权控制的情况下,也应在一定范围内维持其存在。
两种理由在处理建立在“私人复制例外”基础之上的服务提供商侵权责任判定上也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如果认为“私人复制例外”的理论基础是在于轻微损害与交易成本过高的话,间接性服务提供商的服务提供使得个别性轻微损害易于产生积聚效果,此时私人复制行为对于权利人造成的损害不再是轻微程度,而且通过对于服务提供商的“一网打尽”就可以避免因对于各个私人复制主体行使权利的交易成本过高问题,因此通过限缩“私人复制例外”的范围,使得权利人容易找到直接侵权主体,进而根据间接侵权判定规则〔32〕学说上多主张使用民法上的共同侵权责任,参见崔国斌:《网络服务商共同侵权制度之重塑》,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追究服务商的责任或者通过将数字网络服务商拟制为直接行为主体,就可以避免在数字时代对于“私人复制例外”的继续维持;如果认为“私人复制例外”的理论基础在于维护使用者对于已经支付过对价的私人空间作品利用自由的话,问题的关键就集中在利用者是否实际对于其所利用的作品支付过对价以及利用者是否自主地决定所利用作品的范围与内容,并且此种利用行为也在权利人预想范围之内,而对于服务提供商的行为,也因为不存在直接侵权行为,而无法进行间接侵权责任追及。
采用第一种正当化理由背后主要是认识到数字时代“私人复制例外”对于著作权人可能带来更大的损害,因此应通过维护作为价格差别工具的著作权保护体系,〔33〕Wendy J. Gord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Price Discrimination: Implications for Contract”, 73 Chi.-Kent. L. Rev. 1367(1998).限缩性适用“私人复制例外”。〔34〕而其理论嚆矢于1996年美国联邦第7巡回法院在ProCD案(ProCD, Inc. v. Zeidenberg, 86 F. 3d 1447(7th Cir. 1996)中所持见解。该案主审法官Easterbrook根据价格歧视理论承认了拆封合同的有效性,排除了著作权权利用尽作为强制性规范的适用。而一般认为其理论依据就是价格差别理论,即通过合同条款的约定,使得根据不同用户需求设定不同价格成为可能,这样不仅使得有意愿以较高价格享受作品的用户需求得以满足,也使得在统一制定价格条件下无法负担该价格的用户,得以以较低价格同样享受作品带来的福利。由此使得无谓损失减少,经济效率性提高。而为了维持此种价格歧视,就需要防止以较高价格享受作品的用户与以较低价格享受作品的用户之间的套利行为的发生。因此通过合同约定排除著作权法上的权利用尽的适用,可以禁止以较低价格享受作品的用户向其他用户转售作品的载体。著作权法中事实上存在着诸多以较低价格向某些支付能力较低的用户提供作品的机制,诸如思想表现二分法等,这些规定可依合同予以变更,因此仅仅是预设规则的集合,而不属于不可通过合同僭越的强制性规则。同理,各种排除用户复制及接触的技术措施,也可以视作通过合同约定维持价格差别的工具,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予以保障。数字时代使得作品的交易成本显著降低,因此应创设价格差别的实现条件,即市场是独占性的,著作权人享有法定的独占权,并可以控制价格;市场的消费者间存在有不同高低的信息费用;禁止不同价格意愿和能力的消费者间的套利行为,进而实现效率性。
但是,自从作为价格差别的著作权理论诞生之后,对其质疑之声不断。〔35〕通过合同排除著作权权利用尽以及著作权权利限制等的适用的观点可能打破著作权法上原有的价格差别工具。具体来说,传统著作权法上本来就存在着让低支付能力的消费者享受作品的机制,而承认合同价格歧视的有效性恰恰是排除了著作权法上的固有价格差别,因此在理论构成上出现了承认合同价格差别的同时,排除固有价格差别的矛盾现象(J. Cohen, Copyright and the Perfect Curve, 53 Vanderbilt Law Review 1799(2000))。特别是对于价格差别性设定下著作权人获得的消费者剩余来说,其中不仅包含了对著作权人创作的激励效用,还包含了对于作品具有较高价格支付能力的消费者通过作品演绎利用的再生产效用,以及通过二手市场与私人复制领域的例外规定,低收入消费者与对作品价格低支付能力的消费者由于得以接触到作品,从而可能转变成新的作者的效用。如果承认著作权人通过价格差别战略获取消费者剩余的话,损害的将是分散化主体分享作品效用下新作品创造的激励。〔36〕田村善之:《効率性•多様性•自由─インターネット時代の著作権制度のあり方─》,载《北大法学論集》2002年第53巻第4号,第42-61页。因此与上述价格差别理论相反,第二种正当化理由则认为相比于著作权人中央集权式的价格差别战略行使,保留较为广泛的权利限制与例外,从而允许消费者间私人领域自生地作品共享机制,将更具有效率性。〔37〕Michael J. Meurer,“Copyright Law and Price Discrimination”, 23 Cardozo L. Rev. 55(2001).也就是对于利用者已经支付过对价的作品,确保其在后续私人范围内利用的自由。著作权人仅对作品首次使用行为中的复制、传播等法定利用行为实施排他权,并取得相应对价,而对后续其交易时可预想的私人复制行为不再控制。举例来说书籍贩卖过程中著作权人通过复制权与发行权实现了对价的获取,而消费者获得书籍后的阅读、私人复制、亲友间共享、二手销售等行为则不在排他权范围之内。
在“私人复制例外”的第二种正当化理由的构造下,“直接行为主体”认定上首要标准是就复制作品范围由何者决定且是否支付过一次对价后行使权利人预想范围的作品利用行为。〔38〕前田健:《著作権の間接侵害論と私的な利用に関する権利制限の意義についての考察》,载《知的財産法政策学研究》2012年第40号,第177-212页。只有支付了对价并决定作品种类的利用者才可以被评价为不必再度支付对价而在私人领域内行使法定利用行为的主体。例如帮助用户将已经购买的CD音源通过云端储存并同步的服务提供者,仅仅进行了技术上的辅助行为,而复制与传播的内容已经经由用户支付了对价并自主决定了作品的内容与种类。在实质上服务提供商的行为相当于对于纸质图书的搬运行为,而最终用户应被认定为“直接行为主体”。
有关作品利用的不同商业模式下,“直接行为主体”判断是否满足首要标准的判断也会有所不同。对于书籍与音乐等一次性销售的商品,只要利用者购买该类商品,对其后续的私人范围内的“时际”、“区际”以及“载体”转移行为应该认定其构成“直接行为主体”,而在复制以及电子化的标的是由服务提供商自行购买并提供给用户的话,即使物理上、技术上是由最终用户亲自操作的,也应将服务提供商认定为“直接行为主体”。较为复杂的是对于电视节目等商业模式是建立在通过广告的重复播放分次取得对价的处理,其不是对于作品的一次性对价取得,而是通过广告的播放实现多次收益。对于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电视节目跨地域复制及传送服务,到底是将其视为用户已经支付了对价并在其指示下进行复制与传送;还是将其视为服务提供商自己复制了节目并向用户兜售,两种认识将产生质的区别,即前者用户将被评价为“直接行为主体”,后者服务提供商将被评价为“直接行为主体”。从日本既有的行政规制角度看,对于地域外电视节目的“区际”转移服务并不在权利人所预想的作品流通范围之内,理应使得权利人再一次就地域外作品的复制与传播行为征收对价,而服务提供商的行为导致此种对价征收活动难以达成,因此将服务提供商评价为“直接行为主体”更符合日本的情况。对于实质上的“时际”转移性服务提供,将用户认定为“直接行为主体”则更加恰当。〔39〕前田健:《著作権の間接侵害論と私的な利用に関する権利制限の意義についての考察》,载《知的財産法政策学研究》2012年第40号,第177-212页。
总之,对于“直接行为主体”的认定不应脱离“私人复制例外”这一免责规定的宗旨,只有这样才能对物理意义上的“直接行为主体”与社会通识意义上的“直接行为主体”进行有意义的区分,进而拟制的“直接行为主体”不会因为缺乏预见可能性而阻碍新型商业模式的发展。
四、我国著作权法上“直接侵权主体”判断的模式选择
如果认为我国著作权侵权判断构造上满足法定利用行为要求与否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基本架构,〔40〕王迁:《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进而将“间接”行为的侵权追及诉诸“从属说”也是普遍的共识。〔41〕例如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试行)》(京高法发[2010]166号)第15条中认为:“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P2P(点对点)等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构成侵权应当以他人实施了直接侵权行为为前提条件,即第三人利用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P2P(点对点)等服务传播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系侵犯他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学说上的详细介绍参见王迁:《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在此基础上寻找“直接侵权主体”成为了追究间接行为主体的必要步骤。而此点常常为司法实践所忽视,即从当前已有网络侵权的司法案例来看,我国法院无一例外地回避了这一问题,默认了个人用户的下载行为属于直接侵权行为。〔42〕陈明涛:《网络服务提供商版权责任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而这又与我国著作权法上限制“私人复制例外”范围的实践相关联。事实上从规范层面上看,我国“个人使用例外” 存在诸多自相矛盾的内容,也就是说限缩“私人复制例外”适用的模式〔43〕例如在适用范围上仅限于个人,即强调该款所指的是个人使用,而不是私人使用(例如日本著作权法中的私人复制例外的适用范围包括个人、家庭及类似范围之使用(第30条));在行为客体上仅限于他人已公开发表之作品(黄玉烨:《著作权合理使用具体情形立法完善之探讨》,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4期);限制使用目的为学习、研究以及欣赏,而不是以营利与非营利与否进行区分。与扩大“私人复制例外”适用的模式〔44〕例如在行为手段上不限于复制,而是作品的“使用”行为(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曾采用了作品的“使用权”概念(1990年《著作权法》第10条),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则取消了抽象的“使用权”,代之以具体的控制作品使用的权利,包括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等权利。作品的使用权被隐去,复制成为作品使用的一种方式。不过,不管是否采用“使用”这一词语,均改变不了著作权法调整作品使用的特性(高富平:《数字时代的作品使用秩序——著作权法中”复制”的含义和作用》,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共存于我国“个人使用例外”的要件构成之上,因此对于该条规定的立法意图评价是十分困难的。〔45〕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个人使用例外”在1990年著作权法制定之际就已存在,但是立法理由中并未言明其宗旨与适用范围。仅存在有关著作权法上合理使用相关规定的笼统解释原则,即“著作权法的制定要考虑作者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合理使用范围应当比西方国家宽,要有利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敌我斗争”(1990年8月30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棼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汇报)。如果过度限缩“私人复制例外”的范围,的确可以轻易地寻找到可资评价的直接侵权行为,进而圆满地解决“从属说”对于间接行为者的责任追及问题。这样的话,刻意进行“直接行为主体”的规范性认定也是多余的。例如在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与北京优朋普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46〕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高民终字第2581号。中,被告作为网络电视生产销售商对于其提供的供用户下载及同步观看网络视频设备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而这一责任取决于其客观行为表现的主观过错。〔47〕王迁:《超越“红旗标准”——评首例互联网电视著作权侵权案(优朋普乐公司诉 TCL 集团和迅雷公司案)》,载《中国版权》2011年第6期。由于法院没有认定最终用户进行的作品下载行为与同步观看行为的违法性,因此其可能默认最终用户对于违法作品的下载行为构成“直接侵权行为”,〔48〕对于行为客体是否限制为合法作品,我国著作权法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6条中,并没有为网络环境下的“个人使用”设定权利限制与例外 。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立法者对于网络环境中个人下载违法作品的法律定性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从比较法上看,近期修改的英国版权法第28B条中对于私人复制目的仅限于备份、载体转移以及仅个人接触可能的储存三种目的;而对于私人复制的适用范围则严格限制了个人对于合法持有的作品载体才可以进行复制,因此极其强调用户至少支付过一次对价,而对其后的私人范围内个人使用行为予以免责。在2012年日本著作权修改(平成24年法律第43号)中将明知是他人违法上传的有偿音乐及电影作品而以个人使用为目的的复制行为纳入了刑罚规制范围(张鹏:《日本著作权法修改中违法下载行为刑罚化规定评介》,载《中国版权》2013年第2期)。故而被告的行为构成对于违法行为的诱发与积聚,因此具有可罚性。但是假设被告提供的设备仅仅是促进三网融合过程中不同载体间用户私人复制范围内的作品利用活动的“载体”转移的话,如果不分析“直接行为主体”的侵权构成,而直接判断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责任就会造成扩大规制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对于侵权来源的作品能否适用“私人复制例外”的问题,《德国著作权法》第53条第1款就要求只有数字私人复制的作品来源于合法取得的原件时才可以满足私人复制例外的要求。当某一作品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进行流通的话,显然不构成对该作品的“正常使用”,因此对其进一步的复制也是非法的。这一观点背后的逻辑体现了罗马谚语“欺诈使一切变得无效”(fraus omnia corrumpit),即“私人复制例外”的正当性由于作品出自非法来源而消失。在数字时代的典型情形就是最终私人用户通过P2P文件共享软件下载或在私人范围内传播非法来源作品。在欧盟成员国司法实践中对于作品的违法来源与私人复制例外的适用与否问题存在两种态度,其中在法国法上,尽管没有明确立法规定满足私人复制例外的作品范围必须限于合法来源的作品,但是司法实践普遍认为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49〕法国司法实践的具体介绍,参见Stavroula Karapapa,Private copying, Routledge, 2012,p.111.而在荷兰的司法实践中则明确表明作品的来源合法与否与是否可以适用私人复制例外并无实质性关系,从而否定了违法来源的作品复制件进行复制不能构成私人复制例外的观点。〔50〕荷兰司法实践的具体介绍,参见Stavroula Karapapa,Private copying, Routledge, 2012,p.111.对此有学者认为如果最终用户在主张私人复制例外时都必须举证证明其作品来源于合法渠道的话,那么私人复制例外的适用将会被大大限制。〔51〕Christophe Geiger,“Legal or Illegal–That is the Question! Private Copying and Downloading on the Internet”,39 (5) IIC 597-603(2008).更重要的是私人复制的作品来源于违法复制件的行为仅仅是证明对于“三步检验标准”第二步骤“与作品正常使用相冲突”的指示性条件(indicative),而不是决定性条件(decisive)。其理由在于根据“正常使用”的规范性解释,仅仅证明了最终用户复制所使用的作品不是其购买的,或者不是通过合法渠道获得的,并不能证明著作权人丧失了对作品使用所享有的市场。因此单纯强调最终用户在适用私人复制例外时必须合法取得作品的做法并不是“三步检验标准”所强制要求的要件,不区分合法与非法来源作品一概适用与私人复制例外的做法并不与“三步检验标准”相冲突。而解决P2P软件上违法作品泛滥并极大损害权利人利益的更加有效的方法是对向公众上传作品的传播者进行有效规制,同时对于为上述行为提供场所、道具以及系统的第三人,应在间接侵权独立说的模式下追究诱发私人复制广泛发生行为的侵权构成。
因此从结论上看,应强调对于服务提供商侵权判断的两步法:第一步是对于“私人复制例外”的范围,判断何者为“直接行为主体”,这一过程中主要强调利用人至少进行一次对价支付,而对于违法作品的私人复制应持否定性见解。而在此基础上第二步则是对于间接行为者的责任追及,即对于由最终用户支付过对价并自主决定复制作品的内容与种类的行为,即使服务提供商在技术上较高程度地参与了复制与传播的过程,也应该维护最终用户在私人范围内的行动自由;而对于不满足“私人复制例外”的“直接侵权行为”的诱发与帮助性间接行为则应根据“间接侵权”的规则予以判定。〔52〕在殷志强与金陵图书馆著作权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苏民三终字第0096号)中,尽管从形式上看打印行为是由金陵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操作的,但因该打印行为是应读者殷志强的要求进行的,因此不应该将金陵图书馆评价为复制权侵权的直接行为主体。参见吴伟光:《著作权法研究——国际条约、中国立法与司法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页。
五、结 语
伴随着数字化与网络化技术的进步,作品的复制与传播行为日趋简便,使得前数字时代不可想象的跨越“时际”、“区际”与“载体”的作品利用行为成为了可能。在利用者享受技术进步恩惠的同时,不可否认著作权人的利益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侵害之虞。在这一背景下,权利人试图通过追究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责任而“一网打尽”地封杀个人用户在私人范围内对于作品的复制与传播行为。由于服务提供商间接行为评价上的“从属说”的存在,导致“直接行为主体”构成私人复制的情况下,无法顺利实现对于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追及。因此,各国司法实践通过将服务提供商拟制为“直接行为主体”实现了这一目的。这一做法可能造成对于新技术环境下商业模式的封杀,令用户无法享受因技术进步带来的作品效率性利用。对此,本文提出应该结合私人复制例外的宗旨与适用范围探讨“直接行为主体”的判断问题。对作品初次支付过对价并自主决定所要复制及传播的作品内容和种类的情况,不应将深度参与技术性辅助的服务提供商拟制为“直接行为主体”。对于我国在立法论上限缩“私人复制例外”范围的做法应予警惕。因此,从维护私人领域行动自由的宗旨出发,对于我国法上的个人使用例外应扩大解释,以期从解释论上一以贯之地促进私人作品共享的宗旨。〔53〕更为详尽的介绍参见张鹏:《我国著作权法上“个人使用例外”的法解释学论纲》,载《民商法论丛》2015年第58卷。同时应发挥“直接行为主体”判断在区分“为私人合法行为提供技术性便利”与“助长盗版行为泛滥”两种间接行为上的规范功能,这样才有利于找到平衡著作权人利益与公众享受技术进步便利的接点。
(责任编辑:吴一鸣)
* 张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解释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