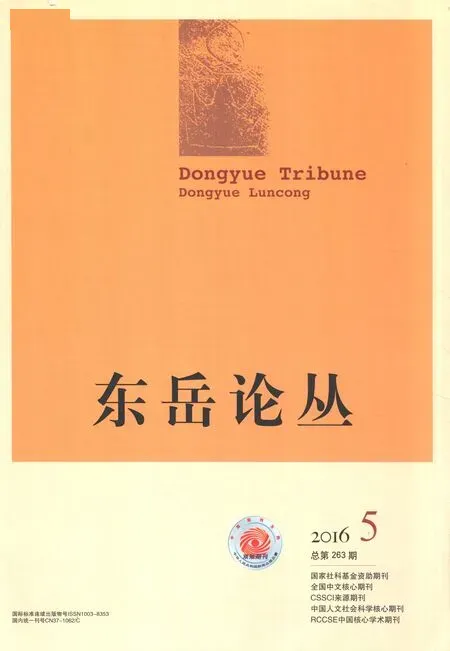论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始造型艺术研究
董龙昌,刘 静
(1.山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2.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0)
美学研究
论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始造型艺术研究
董龙昌1,刘静2
(1.山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2.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0)
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始造型艺术研究可以分为从艺术内看艺术和从艺术外看艺术两个层次:从艺术内看艺术是列维-斯特劳斯通过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原始艺术造型特征的分析;从艺术外看艺术则是从文化角度对原始造型艺术意蕴的深度发掘。这种二层次分析法在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造型艺术的“裂分表现”法及面具艺术研究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列维-斯特劳斯原始造型艺术研究的主要价值包括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立场;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整体性、关系性和比较性的学术视野;理论阐发与现实观照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但同时也存在审美/艺术维度的缺失、研究对象“结构”剖析上的随意性和田野调查力度不够等局限。
列维-斯特劳斯;原始造型艺术;结构主义;艺术人类学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田野调查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原始土著民族形形色色的艺术样式,如南美卡都卫欧人的图画艺术、北美西北太平洋沿岸民族的面具艺术等。列维-斯特劳斯对这些原始造型艺术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并投入了大量精力对它们加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列维-斯特劳斯加深了对这些原始艺术价值的认同与热爱。
一、原始造型艺术中的“裂分表现”法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人类学研究过程中广泛接触到大量和原始艺术相关的民族志材料,通过对这些民族志材料的梳理,他发现一些不同时代或相距遥远的地区虽然不存在相互接触、影响之可能,但是这些地区的艺术无论在造型风格还是表现手法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给人印象深刻,这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这些不同地区的艺术涉及北美西北海岸地区艺术、古代中国艺术、南美卡都卫欧印第安人艺术和新西兰毛利人与瓜依库鲁人的艺术。
在对北美西北海岸地区艺术造型特点的研究上,列维-斯特劳斯认同人类学家博厄斯的看法,认为该地区艺术在造型上总体上呈现出“裂分表现”(split representation)的特色:当地土著在对动物的刻画上倾向于将它们从头至尾切分成两半,然后将这两个半部并置在一起,这样他们就用两个侧面形象达到对该动物的正面形象加以表现的目的。在这种表现中,被切割的部分各自脱离了它们原来的位置,两个侧面形象在口鼻处对接,头的前部是连贯的,眼睛及下额的两半则是互不接触的。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这种“裂分表现”的艺术手法并不为北美西北海岸地区所独有,在中国上古艺术里同样存在。以中国安阳出土的饕餮纹饰青铜器为例,其正面刻画的饕餮纹饰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中间部分为一个一分为二的无下颌的饕餮面具;上半部分为由饕餮的两只耳朵构成的龙形面具,两条小龙双面相向,分别以侧面形象的方式得以展现;下半部分也可作类似的解释*③④[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页,第270页,第263页。。学者顾里雅(H.G.Creel)的研究成果为列维-斯特劳斯的上述解释提供了理论支撑。他在研究中国商代的装饰艺术时认为这一艺术门类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把动物表现为平面或圆形层面。这就好像是拿起动物,从尾巴尖开始将其纵向剖开,一刀剖至鼻尖,但并不豁开。然后将两个半扇摊开,再把这一分为二的动物平铺在器物表面上。两个半身仅在鼻尖处连接。”*转引自[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顾里雅的叙述同前述北美西北海岸地区艺术的造型特点极为相似,这里所谓“特别的方法”实际上指的就是“裂分表现”法。
列维-斯特劳斯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在南美卡都卫欧印第安人的艺术中同样可以发现这种“裂分表现”法。在一位卡都卫欧妇女手绘的文面人物形象中,人物的造型沿水平和垂直两条轴线对称分布,水平轴线沿着眼孔将整个脸部分为上下两部分,垂直轴线则从脸的正中间穿过,两只眼睛分别是前额左侧和右脸颊上两个螺旋纹饰的起点,这两个螺旋纹的旋转方向相反。画中人物的上嘴唇用弓形图案加以复合表现,同时以一种缠结纹加以装饰。表面看来,这幅图画的造型是不对称的,“然而这种不对称性掩盖着一种复杂而真实的对称性”③。这种对称性表现在相交于鼻子上端的轴线实际上把整个面部划分成了四个三角区域,即左前额、鼻右侧和右脸颊、右前额、鼻左侧和左脸颊。前两项和后两项内部之间无论在造型还是在纹饰图案上均体现出一种对称关系。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这一绘画图案实际上是画家使用“裂分表现”法完成的,因为文面人物的脸孔由两个并排在一起的侧面构成,正因如此,整个脸部图案轮廓才会显得宽阔异常。
同卡都卫欧印第安人一样,列维-斯特劳斯发现,新西兰的毛利人与瓜依库鲁人对艺术的表现也采取“裂分表现”的形式。在他们最为发达的文身艺术里,我们再次见到了一分为二并置在一起额头、脸部及鼻子,嘴同样也是对半拼起来的。这一切无不同前面已经介绍的艺术样式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综合来看,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北美西北海岸地区艺术、古代中国艺术、南美卡都卫欧印第安人艺术和新西兰毛利人与瓜依库鲁人的艺术的比较研究,所发现的关于原始造型艺术的“裂分表现”法确实是普遍存在的,它可以被恰当地概括为一种通过将表现对象一分为二的切分并置达到用两个侧面形象表现正面形象的目的的一种艺术造型方法,它普遍存在于原始人的绘画、面具等艺术门类中。
在关于为什么原始造型艺术中会普遍存在这种“裂分表现”法的解释上,列维-斯特劳斯并不同意文化传播学派的观点。该学派倾向于从文化间相互接触、影响的角度看待艺术的“裂分表现”问题,将艺术的“裂分表现”视为一个地区文化对另一个地区文化施加影响的结果。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当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的关系客观存在时,以文化传播论的视点看待艺术问题是有道理的。然而当这种关系在客观上并不存在时,如果依然固守文化传播论的观点,那么只会误入歧途。事实上,这后一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一个装饰性细节,一个特别的图形只需来自世界上的两个不同地区,就会有热心人不顾两种之间通常十分明显的地理距离和历史间隔,立即宣布这两种其实舍此绝不可比之处的文化起源相同,有着无可置疑的史前联系”④,这种不顾一切地寻找相似性的做法是罔顾历史的表现,无疑是极为武断的。就原始造型艺术的“裂分表现”法而言,北美西北海岸地区艺术、古代中国艺术、南美卡都卫欧印第安人艺术和新西兰毛利人与瓜依库鲁人的艺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不存在相互接触之可能,因此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用文化传播论的观点解释这一问题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列维-斯特劳斯同样不满意博厄斯在研究北美西北海岸地区艺术时对“裂分表现”法所作的解释。博厄斯将该地区造型艺术中存在的“裂分表现”法归因于所表现对象由三维到二维的转化。他指出,众所周知,在一个二维平面上依原样描绘一个三维立体的客体事实上是不太可能做到的,这就要求艺术家作一定的转化处理。例如如果要将一个动物形象完整地绘于方形盒子上就必须改变它的原有面貌使之发生某种程度的错位变形,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契合于方形盒子的造型特点,艺术家在这一过程中所使用的表现方法就是“裂分表现”法。列维-斯特劳斯并不认同博厄斯的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虽然博厄斯这位现代人类学大师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显得优雅而简洁,然而这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幻象,它并不符合原始人的艺术现实。因为大量民族志材料表明,在许多不同地区文化中用于装饰的盒子上所绘的动物或人的形象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形或错位,这些客观存在的人类学事实是对博厄斯观点的有力反驳。
当用文化传播论的理论及博厄斯的观点解释原始艺术中普遍存在的“裂分表现”法行不通的时候,列维-斯特劳斯建议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如果我们不懈地向历史求助(首先就应当求助于它),而历史告诉我们‘此路不通’,那么就让我们转而求助于心理学或者对形式的结构分析吧。让我们试问,本属心理或逻辑性质的内在关联是否有助于理解那些同时发生的反复出现的现象,这些现象的频率和凝聚力都不可能出自一场概率游戏。”*②③[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第278页,第276页。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通过“裂分表现”法得以展现的北美西北海岸地区艺术、古代中国艺术、南美卡都卫欧印第安人艺术和新西兰毛利人与瓜依库鲁人的艺术,实际上反映的是艺术的造型成分与图解成分之间的二元关系,也就是结构与图案之间的二元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对立的又是功能性的。一方面,图案本身的要求施加于结构之上产生了裂分和错位,对立关系因此产生;另一方面,由于原始人总是同时从造型和图解两个方面对艺术对象加以想象性创造,因此,这种二元关系又是一种功能性关系。“一只瓶子,一只箱子,一堵墙,都不是一些预先已经存在、只需加以装饰的独立的物体。它们在整合了装饰和实用功效之后才获得了确定的存在。”②例如在原始人看来,用动物装饰的一个箱子并不仅仅是用来盛放东西的容器,它甚至就是动物本身,是它守护着人们的物质财富。
就艺术的造型特点而言,“裂分表现”法反映的是结构与图案之间的二元关系,这是列维-斯特劳斯诠释“裂分表现”法的第一个层面,也是较为浅显的层面。从另一个层面看,“裂分表现”法实际上反映的是艺术与社会的深层次关联,这是列维-斯特劳斯原始造型艺术研究人类学旨趣之体现。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原始造型艺术的“裂分表现”法既反映出人类由自然向文明的过渡,又同特定社会的等级制度密切相关,它构成了特定文明的功能性表达。一方面,在原始人的思想深处,图画同脸孔之间具有一种对等的关系,因而他们通过“裂分表现”法的形式所创作出来的绘画便使人具有了人的尊严,这保证了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由自然到文化的过渡;另一方面,不同图画的图案设计与风格又与特定的阶级旨趣和社会地位紧密相连,因此,通过“裂分表现”法展现的原始造型艺术实际上又象征了个人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分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裂分表现法与一部关于人格分裂的社会学理论有关。”③
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以卡都卫欧艺术为例,进一步论述了透过原始造型艺术的“裂分表现”法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卡都卫欧人是姆巴雅-该库鲁(Mbaya-Guaicuru)印第安人在巴西的代表,他们的社会结构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一般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它们呈金字塔形分布,在最上层的是贵族,贵族之下是武士,居于最低等级的是奴隶。这三个等级之间的界限森严,严禁互相通婚,这就使得其中的每一个阶级倾向于自我封闭,这显然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团结和稳固。与社会分层相应的是他们在艺术上极为重视对身体上尤其是脸上的绘画,不同等级的脸上绘画在图案、范围上也有着严格区分。
位于巴拉圭的瓜那族和马托格洛索的博罗罗族在社会组织上同卡都卫欧人一样也存在相近的三个等级,然而他们的社会同时又划分为两个互婚亚族,这样由三阶级划分造成的社会不均衡在某种程度上就被互婚亚族的二分法所平衡,因此,他们的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就显得相对较低。
尽管卡都卫欧人在社会组织上没有采取瓜那人和博罗罗人相同的结构形式,因而其社会发展面临相当大的风险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此视若无睹。他们将这种关切转移到了艺术上。在他们的图画艺术中能够发现同瓜那人和博罗罗人的社会组织原则相似的结构性特征。卡都卫欧人通过“裂分表现”法在其图画艺术中表现出来的既对称又不对称原则实际上是对其社会分层矛盾在艺术上的想象性调解。因此,正如梅吉奥所言,卡都卫欧人的图画艺术“已不仅仅是经验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工具,它还是超越社会生活的一种意象;它是描绘它赖以产生的那个社会的乌托邦形式的一种隐喻。”*[法]若斯·吉莱姆·梅吉奥:《列维-斯特劳斯的美学观》,怀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二、“面具之道”
面具是普遍存在于世界范围的文化现象,其历史久远,可追溯至人类诞生之初。它既是物质性的器具,又具备精神性的效力,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结合的产物。面具有着非常实用的功能,广泛应用于原始人的狩猎、战争、祭祖等活动。而作为精神文化产品,它是一种具有特殊表意性质的象征符号,具有沟通天地鬼神的作用。因此,面具在初民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面具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历史积淀决定了它不仅具有雕刻、绘画等方面的艺术价值,更具有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文化价值*参见顾朴光:《面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诚如有的研究者所言:“面具并不仅仅是娱乐或表演的道具,甚至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品,它更应该被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文化的产物,是神灵、权力、地位的象征,它为我们研究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综合学科提供了广阔的领域。”*沈福馨:《人类宗教文化的综合载体——面具》,载沈福馨、周林生编:《世界面具艺术》,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由前文论述可以看出,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造型艺术中“裂分表现”法的研究实际同其对面具艺术及面具文化的重视密不可分,他所研究的北美西北海岸地区艺术、古代中国艺术、南美卡都卫欧印第安人艺术和新西兰毛利人与瓜依库鲁人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变形的面具艺术。对此,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裂分表现”法的论述中有着明确说明,他讲:“对于我们来说,裂分表现法不仅是面具的一种图解表象,而且是一种特定的文明的功能性表达方式。”*[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列维-斯特劳斯在这里将“裂分表现”法同面具的图解表象联系在一起,意味着他实际是将上述四个地区的原始艺术视为面具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的,这四个地区艺术的造型表达方式是列维-斯特劳斯的主要着眼点。
当列维-斯特劳斯将研究重心放在面具艺术上时,他的着眼点变得更加综合化、多样化。因为在他眼中,面具是一个综合性、多样性的领域,它把神话、社会与宗教功能、造型艺术表达方式有机地融为了一体*参见[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家身份决定了在其对面具艺术所采取的综合化、多样化的研究中,人类学旨趣最为突显。事实上,这也是每一位涉足面具艺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主要目的之一。与其他人类学家相较,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意识,构成了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因此,人类学旨趣及结构主义方法也就成为列维-斯特劳斯面具艺术研究的两个最突出特点。
在流亡美国期间(1941—1947),列维-斯特劳斯与以布勒东等人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共同发现了西北太平洋海岸英属哥伦比亚地区的印第安人艺术。这一地区印第安人艺术的高超成就让列维-斯特劳斯惊叹不已,在他看来,这些艺术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居住在北部的特林吉特人让我们领略到源于诗意的精妙想象力的雕塑和珍贵的装饰品;随后是偏南部的海达人,他们的作品雄浑阔大,力量勃发;钦西安人与之相仿,也许带有更富有人情味的敏感;贝拉库拉人的面具风格华丽,以深蓝色为主调;夸扣特尔人的想象力纵横恣肆,他们创作的舞蹈面具具有令人惊讶的火焰样式和色彩;努特卡人则更多地受到某种写实主义的制约;最后,居住在最南端的萨利希人的风格极为洗练,多棱角并图式化,而且丝毫不见北方的影响。”*[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在这一地区的诸多印第安人艺术中,列维-斯特劳斯对面具艺术情有独钟,并进行了专门研究。尽管他意识到面具艺术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他的研究重心却并不在此,通过分析面具的造型艺术特点透视沉潜在面具背后的深沉的文化意蕴才是其研究的真正旨趣。换句话说,充分发掘面具的人类学价值才是列维-斯特劳斯面具艺术研究的真正目标和重心。这由其对面具艺术研究专著《面具之道》(TheWayoftheMasks)的命名可见一斑。按照张祖建先生的说法,“面具之道”所用的法语“道路”(la voie)一词与“声音”(la voix)一词谐音,列维-斯特劳斯以此命名,其言外之意在于告诉读者面具是发声的,我们不能仅仅将它们视为静止的审美对象,我们还要学着倾听它们“说话”*参见张祖建:《面具之道·译者序》,载[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面具所说的内容即为其人类学价值之显现。
列维-斯特劳斯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萨利希语族的斯瓦赫威面具、努特卡人和夸扣特尔人的赫威赫威面具及夸扣特尔人的皂诺克瓦面具三种面具形式。
斯瓦赫威面具主要出现在萨利希语族,这一部族主要分布在北美弗雷泽河入海口的南北两侧以及温哥华岛的东部。斯瓦赫威面具有着鲜明的艺术造型特征:突起的眼珠、向外吊垂的舌头、在面具上端及鼻子上安装的鸟头以及与此配套的用天鹅翎和绒毛做成的供披戴面具的人穿着的白色礼服。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只有贵胄世家才拥有斯瓦赫威面具,其传承只能通过继承和姻亲两种途径。他们认为拥有这种面具或者得到面具帮助的人将有好运降临,有助于他们获得财富。斯瓦赫威面具有其特定的应用场合,它主要出现在波特拉赤(Potlatch,即夸富宴)及其他世俗性仪典中,不应用于冬季祭神仪式。从语义角度看,通过对与此有关的起源神话研究表明,该面具具有双重类比性:与鱼类比、与铜类比*参见[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赫威赫威面具主要出现在努特卡人和夸扣特尔人两个部族中。其中以夸扣特尔人的最具有代表性,主要分布在温哥华岛的北部。在造型特征上,赫威赫威面具与斯瓦赫威面具相类似,且更具有现实主义风格,其突出特征是:暴突的眼珠、探出的舌头、鸟头形的附加物以及野鹅毛的装饰物。与斯瓦赫威面具相较,赫威赫威面具的风格更加率性、奔放。从社会学角度看,夸扣特尔人认为,赫威赫威面具和地震相关联,带着它舞蹈能够引发地震。它同斯瓦赫威面具一样具有特定的应用场合,禁止在冬季祭神仪式中使用。从语义角度看,与赫威赫威面具相关的起源神话同样表明,该面具具有可与鱼、铜类比的双重类比性。不过赫威赫威面具的类比是反向类比,它象征着性情悭吝,与财富不可兼容。
皂诺克瓦面具主要出现在夸扣特尔人部落中,同样分布在温哥华岛的北部。在造型特征上,它同斯瓦赫威面具完全相反,其主要特征是:深凹或半睁半闭的眼窝、向前撅起的嘴巴和与以黑色为主的以皮毛为装饰物的礼服。从社会学角度看,皂诺克瓦面具不归贵族世胄专享。在波特拉赤仪典中,佩戴皂诺克瓦面具的表演者需要背负一个背篓,里面盛着象征财富的铜,将铜分与观众。与赫皂诺克瓦面具相关的起源神话表明,与斯瓦赫威面具一样,皂诺克瓦面具也是财富的象征,同财富的聚散密切关联。
由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斯瓦赫威面具、赫威赫威面具和皂诺克瓦面具之间存在着既相似又对立的关系。在造型上,赫威赫威面具和斯瓦赫威面具具有相似性,然而在所行使的社会功能上,二者却是截然对立的:斯瓦赫威面具象征着慷慨,拥有者乐善好施;赫威赫威面具象征着吝啬,与财富的拥有不相容。皂诺克瓦面具与斯瓦赫威面具虽在造型特征上完全相反,然而二者却有着相同的社会功能,即扮演了财富的慷慨分与者的角色。
在对以上三种面具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当同一信息由一个族群传递到另一个族群时,会产生两种颠倒情况:第一,当所传达的信息不变时,那么该信息的元素会在造型上发生完全颠倒(如赫威赫威面具之于斯瓦赫威面具);第二,如果所传达信息的造型元素不变,那么所传达信息的语义会产生完全的颠倒(如皂诺克瓦面具之于斯瓦赫威面具)。列维-斯特劳斯对这种二元转换关系进行了非常经典的表述:“从一个族群到另一个族群之间,当造型样式维持不变时,语义功能会发生颠倒。反之,当语义功能维持不变时,造型样式会颠倒。”*[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由以上研究过程及结论可知,列维-斯特劳斯对面具艺术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方法依然是结构主义的。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列维-斯特劳斯对面具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该艺术的几个主要造型特点切入的,如眼睛的突起与否、舌头的吊垂与否等,这些造型要素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其在神话研究过程中的所使用的“神话素”概念*参见乔晶晶:《斯特劳斯的启发》,《世界美术》,2002年第3期。。列维-斯特劳斯在面具艺术中所采用的结构主义方法可视为其神话研究的自然延伸,他将在神话研究中已经获得验证的方法扩大到造型艺术的领域,并做了较为成功的尝试。
众所周知,在神话研究中,同语言类比是列维-斯特劳斯习惯采取的方式,在对以面具为代表的造型艺术上,他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他认为,“跟语言中的词语一样,每一副面具本身并不具备其全部意指。意指既来自于被选用的义项本身的意义,也来自于被这一取舍所排除的所有可能替换它的其他义项的意义。”*[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46页。很显然,列维-斯特劳斯是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观照面具的。在他看来,单个面具并不具备固有的意指,因此是无意义的。只有把它置于各种变异的意义组合体中,从整体性、比较性的视野出发,通过对不同类型的面具进行比较,我们才能获知一个完整的语义场,从而获得对面具艺术的科学认识。这是列维-斯特劳斯以结构主义方法研究面具艺术的精髓之所在。
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主要是从纯形式的角度对以上三种面具艺术进行的结构分析,那么在完成这种分析以后,他便把分析的视角转向了形式背后的更为广袤的文化土壤。列维-斯特劳斯依据面具的造型特征及相关的起源神话,追根溯源,寻找到了面具背后所折射出的共同的经济基础——与“铜”相关的社会生活。通过对“铜”的研究,列维-斯特劳斯找到了能把斯瓦赫威面具、赫威赫威面具和皂诺克瓦面具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媒介与途径。
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斯瓦赫威面具传入夸扣特尔人部落的过程存在着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观念的传播,即斯瓦赫威面具是作为财富、地位的象征这一观念的传播。其结果是,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夸扣特尔人制造了“铜”(斯瓦赫威面具与“铜”的类同性体现在面具突起的眼睛所代表的无限目力宛如铜散发出来的光芒)。由于夸扣特尔人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拥有了“铜”,那么其作为财富象征的意义便会减弱、消失,乃至逆转。反映在面具上,赫威赫威面具在造型上虽与斯瓦赫威面具有相似之处,但其承担与财富相关的功能却相反。第二阶段,夸扣特尔人以其特有的方式改造与皂诺克瓦面具相关的神话。尽管皂诺克瓦面具仍与慷慨给予财富相关,但是“铜”已经替代了斯瓦赫威面具所具有的象征财富、地位的观念。因此,夸扣特尔人便颠倒了斯瓦赫威面具的造型特征,并将之体现在了皂诺克瓦面具上。这便是萨利希语族的斯瓦赫威面具向夸扣特尔人的赫威赫威面具及皂诺克瓦面具的总体演变过程。由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这一过程中,“铜”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三、列维-斯特劳斯原始造型艺术研究的价值与局限
总体来看,结构主义方法和鲜明的人类学旨趣是列维-斯特劳斯原始造型艺术研究的突出特点。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始造型艺术研究可以分为从艺术内看艺术和从艺术外看艺术两个层次。用结构主义的方法从纯形式的角度分析原始艺术的“裂分表现”法及斯瓦赫威面具、赫威赫威面具和皂诺克瓦面具之间的造型特点,是列维-斯特劳斯站在艺术内看艺术立场的反映;在形式分析的基础上,列维-斯特劳斯透过原始造型艺术“裂分表现”法的表层对艺术与社会之关系的阐释、对面具艺术背后的经济、文化因素的找寻,则是其从艺术外看艺术立场之体现。
我们认为上述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始造型艺术研究之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原始造型艺术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立场,不仅顺应了世界学术的发展潮流,而且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众所周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无论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均呈现出两种发展态势。一方面,各学科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精细,学科不断走向精细性分化;另一方面,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及混沌学等理论的兴起及广泛传播,各学科之间又出现交叉、融合迹象,跨学科研究随之成为一种新趋势,这催生出一批新的学科增长点,作为一门学科的艺术人类学的产生正是美学/艺术学同人类学交叉融合的产物。列维-斯特劳斯在其艺术人类学研究过程中依据其特有的运思方式将不同地域文化的原始造型艺术现象放在一起加以综合关照,同时又广泛借鉴了哲学、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数学、逻辑学及生物学等学科知识,正是在这种多文化的交流沟通及多学科的互动协作中,列维-斯特劳斯实现了他对原始造型艺术的精彩解读,这在他对印第安人面具艺术的解读过程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他在原始造型艺术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跨文化、跨学科立场为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二)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原始造型艺术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为美学、艺术学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
列维-斯特劳斯不仅将源于现代语言学的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人类学研究中,而且还有意识地将其进一步扩展到原始造型艺术研究中,表现出一种自觉的方法论意识。通览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历程可以发现,他首先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的是亲属关系,然后又在神话、诗歌、音乐及原始造型艺术等领域中加以进一步验证、深化和拓展。如他在对俄狄浦斯神话的解读过程中就表明了这一研究意图,在他看来,他对俄狄浦斯神话的解读与其说是为了寻找一个被专家学者普遍认可的观点,不如说是为了说明一种技术,是为了验证结构方法在神话研究中的效力*参见[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他在对美洲西北海岸印第安人原始艺术的“裂分表现”法的研究过程中同样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他的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当用文化传播论的观点研究不同地区艺术所共同存在的“裂分表现”法行不通时,列维-斯特劳斯明确表示可以通过对原始造型艺术形式的结构分析解决问题*[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通过对结构方法的广泛运用,列维-斯特劳斯获得了变混乱为明晰的本领。埃德蒙·利奇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真正有价值的贡献不是对对立的双方及它们相互间多样的排列组合的形式主义的探讨,而毋宁是他在分析过程中运用的真正具有诗意的联想方式:在列维-斯特劳斯手中,再复杂的事物也会马上由混乱变得清晰明了。”*[英]埃德蒙·利奇:《列维-斯特劳斯》,吴琼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在笔者看来,列维-斯特劳斯所具有的“诗意的联想方式”是同其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密不可分的。他的这种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不仅可以为美学、艺术学研究提供理论武器,而且提供了文本解读上的具体范例,这对于增强美学、艺术学批评的具体可操作性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三)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原始造型艺术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整体性、关系性和比较性的学术视野,对于拓展我们的思维方式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出于对结构主义方法的偏好,列维-斯特劳斯在对原始造型艺术的研究过程中首先持有的是一种整体性的学术视野。他对艺术的研究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是从研究对象的结构性特征入手对它们加以宏观把握。在他的学术视域中,既可以将14至18世纪新西兰毛利人的文面艺术同中国商代的青铜器艺术放在一起加以研究,又可以将美洲的神话同欧洲的民间传说甚至日本的神话故事放在一起加以研究,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这些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艺术无论在社会组织、宗教生活还是在审美习惯、艺术造型等方面均呈现出一种整体结构上的相似性。“如果说结构主义曾经怀有席卷天下的抱负,那不是因为它是一种手段,而是因为它研究的对象本身是一个整体。”*[法]德尼·贝多莱:《列维-斯特劳斯传》,于秀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7页。法国学者德尼·贝多莱的这句话可看作是对列维-斯特劳斯原始造型艺术研究坚持整体性学术立场的很好的说明。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原始造型艺术研究过程中还坚持关系性的思维方式,这同样是由其对结构主义方法的迷恋决定的。在结构方法的指引下,列维-斯特劳斯并不从孤立的角度看待某个艺术问题,而是将其放在由艺术对象与艺术对象组成的系统中加以考量,例如列维-斯特劳斯对美洲萨利希语族的斯瓦赫威面具、努特卡人和夸扣特尔人的赫威赫威面具及夸扣特尔人的皂诺克瓦面具这三种面具形式的研究,他坚持将这三种面具形式纳入到一个系统中,从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研究面具艺术问题,最终得出这一结论:当一个面具形式由一个族群向另一个族群流传时,如果它的造型样式保持不变,那么它所承担的社会文化职能则会发生完全颠倒,反之亦然。即使是对单个艺术对象的把握列维-斯特劳斯同样坚持从要素与要素组成的关系系统出发,例如他在神话研究过程中对“神话素”这一概念的使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这种关系性思维方式是对传统主客对立思维方式的反拨,其中所传达的反主体中心主义色彩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详见高宣扬:《列维-斯特劳斯及其结构主义的历史地位》,高宣扬主编:《法兰西思想评论》(第五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页。。
与关系性思维方式相联系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在原始造型艺术研究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比较性视野。一般的比较研究多强调所研究对象在事实上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列维-斯特劳斯比较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主要从结构相似性的角度出发看待艺术问题,他对原始造型艺术中的“裂分表现”法的研究是这一学术视野的集中体现。在他看来,虽然北美西北海岸地区艺术、古代中国艺术、南美卡都卫欧印第安人艺术和新西兰毛利人的艺术并不存在相互交往、影响之可能,但是这并不妨碍对这四个地区艺术的比较研究,因为这些不同的艺术形式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即在造型上共同遵循“裂分表现”法的规则。
列维-斯特劳斯在原始造型艺术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整体性、关系性和比较性的学术视野,顺应了人类思维方式由主客对立的实体性思维向多元共生的关系性思维革新的现代要求,对于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拓展我们的思维方式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世界是一个关系的世界,人的思维同样应是一种关系性的思维。
(四)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原始造型艺术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理论阐发与现实观照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为文艺学、美学的发展及艺术学研究范式的革新提供了参照。
这里所谓列维-斯特劳斯原始造型艺术研究之理论阐发与现实观照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两层意思:第一,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造型艺术的研究大多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田野现实是其理论阐发的前提条件。虽然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历程中,他进行田野调查的时间比较短,他也因此饱受人类学界同行的批评,但是即使是在其有限的田野调查经历中,他也对艺术给予了一定关注,例如在巴西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列维-斯特劳斯对卡都卫欧人的图画艺术进行了相当细致的了解,这为后来他对这一艺术样式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第二,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原始造型艺术的具体理论阐发过程中,并没有忘记现实之维、文化之维。在用结构主义方法进行艺术研究的同时,列维-斯特劳斯极为重视现实经验维度,他注重从现实的、文化的角度对其理论观点加以验证或修正。例如对印第安人面具艺术的研究过程中,一方面,他充分运用结构主义方法通过寻找文本中的一系列二元对立来对不同地区的面具艺术进行细致解读;另一方面,他又从地理、经济—技术、社会学等层面对其结构分析加以验证。
列维-斯特劳斯原始造型艺术研究之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为文艺学、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启示。当前文艺学、美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瓶颈之一就是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学者们拘囿于概念术语的玄思游戏,对现实生活中兴起的各种文学、艺术现象却不能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学术研究的现实根基日渐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回归现实、还文艺学、美学研究以感性存在的本来面目的呼声日渐高涨*参见王杰,海力波:《列维-斯特劳斯与审美人类学》,《东方丛刊》,2001年第2辑。,列维-斯特劳斯原始造型艺术研究对现实维度的重视无疑是文艺学、美学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
列维-斯特劳斯原始造型艺术研究之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注重从文化的维度看待艺术问题,这对当前的艺术研究同样具有启示意义。从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的观点看,艺术研究不应仅仅关注艺术作品的形式特征,而且还应重视对形式背后的文化意蕴的发掘,唯其如此,当我们面对一件艺术作品时才能充分感受到其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深刻内涵,而这恰是人类学的视界,易言以明之,未来的艺术研究不仅应是“艺术的”,而且还是“人类学的”,这是列维-斯特劳斯原始造型艺术研究给予未来艺术研究的重要启示。
尽管上文我们对列维-斯特劳斯原始造型艺术研究的价值多有肯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局限性。在笔者看来,列维-斯特劳斯原始造型艺术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始造型艺术研究存在研究对象艺术性/审美性的缺失问题。尽管列维-斯特劳斯对以印第安人面具艺术为代表的原始造型艺术的美学价值推崇备至,但人类学家的身份决定了列维-斯特劳斯在看待艺术问题时更多地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的,这是其艺术研究的优势所在。然而,在学术研究中如果仅仅拘泥于这一立场而对原始造型艺术的美学价值主动回避恐怕也不是艺术研究的正途,毕竟艺术之为艺术总是与其审美性、情感性及愉悦性分不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幼蒸先生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学研究和神话研究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文学和神话学,尽管功力深厚,运思博大精深,却基本上是对文学现象进行一种‘科学式扫描’,其文学价值观是基本固定的。”*李幼蒸:《列维-斯特劳斯对中国社会科学启示之我见》,《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就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始造型艺术研究而言,李先生的这一断语无疑也是适用的。
(二)列维-斯特劳斯对结构方法的运用有时过于主观随意,其对具体研究对象“结构”的剖析充满了先验性,具有极强的演绎色彩。通过结构方法的运用,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学术研究过程中收获了明晰性,任何复杂的文学、艺术现象到了他的手里一经结构分析立即变得简单起来,这是列维-斯特劳斯的非凡之处。然而,其结构方法在具体应用过程中究竟是否科学却是值得推敲的。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结构方法(以二元对立为主要标志)充满了主观随意性。程代熙先生认为:“列维-斯特劳斯把‘二元对立’当作一个框架,把他所需要的东西往框架里一放,并根据自己的心愿来加以解释。因此,他的‘二元对立’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武断色彩。”*程代熙:《列维-斯特劳斯和他的结构主义》,《文艺争鸣》,1986年第1期。这一判断大抵是正确的。
(三)田野调查的力度不够。尽管我们在上文谈及列维-斯特劳斯原始造型艺术研究的价值时曾肯定其对田野调查的重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在其一生当中进行田野调查次数确实极为有限,而且每次调查的时间都相当短暂,这也是他的学术研究被人类学界称之为“理论人类学”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原始造型艺术就其产生而言,多与其所根生的文化土壤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研究者田野调查力度的大小直接关系着其结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始造型艺术研究无疑存在这一问题。列维-斯特劳斯原始造型艺术研究田野调查力度的不够使得其学术成果饱受争议,其在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浓郁的理论思辨色彩及文风的晦涩更加妨碍了人们对其学术思想的理解和接受。
[责任编辑:王源]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与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研究》(15YJC760019)、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现状研究》(2014015)、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董龙昌(1985-),男,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刘静(1981-),女,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山东大学出版社编辑。
B83
A
1003-8353(2016)05-01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