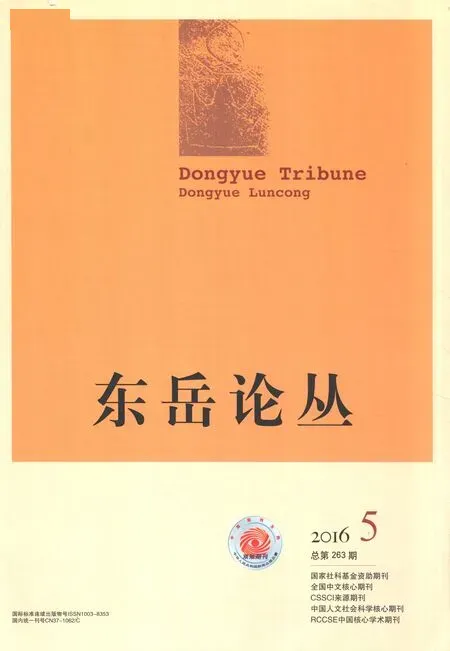城市在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中的地位
胡大平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本刊特稿
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空间
城市在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中的地位
胡大平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在直接的意义上,马克思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特别借助于列斐伏尔等哲学家、哈维等地理学家、卡斯特等社会学家重新“发现”和解释的。更确切地说,在城市成为社会斗争基本舞台的背景下,人们试图从空间变迁机制角度阐明当代城市的性质及其意义时,马克思主义之理论价值得到了再度阐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科学分析的政治经济学,迄今为止,仍然是最具竞争力的历史叙事以及任何现代性自我理解都无法绕开的思想资源。
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在相关领域取得重大进展,这是值得欣喜的事,但同时亦是需要警觉的现象。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学术和理论中的这一胜利,潜在地包含着一些重大的代价,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划之意义被压抑,在多数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成为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或其他后现代立场的注脚,成为这些立场政治化的手段。在其中,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之当代有效性的元理论问题是,马克思是否存在着时间压倒空间的历史叙事偏好,从而不足以胜任今天的城市分析?该问题既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时空观,又涉及城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地位。问题是由一些法国思想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来的,无论是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现代知识型加以批评的福柯,还是努力将之升级为“空间生产知识”的列斐伏尔,都认为马克思过度依赖历史时间而在空间研究上有所欠缺。
在马克思那里,情况是否如此?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法国的思想家们会比较集中地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的回应从这两个问题进行。
就第一个问题来讲,首先从相对简单的层次入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忽略了城市?答案是否定的。虽然马克思没有言明自己的分析以为城市为直接背景的,但在其理论前提上却蕴含了这样的基本假设:城市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维系和扩大的理想环境。在代表着其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草稿)述中,马克思恩格斯从欧洲城乡分工这个背景出发基于分工视角勾勒出现代资本主义的成长轨迹,他们强调,“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在中世纪,“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生产方式内部兴起的堡垒。在这些城市中,通过商业,“自然形成的资本”产生了,城市之间的分工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产生,这又进步推动了封建制从内部的瓦解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创造了全部条件*参阅《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115页。。简言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直接与城市高度相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强调,“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115页。。这也清晰地表明,马克思所言的资产阶级社会就是城市世界*不过,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眼中的“城市世界”并非乡村倾向于消失的现实世界,而是一种分析上的理想类型,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建立在其上并最终推动形成的理想的人群聚落条件。后来,马克斯·韦伯的形式社会学专门强调了理想类型在分析中的独特作用,而其对城市的定义亦采取了理想类型。其在城市定义上与马克思亲和性,亦源于此。必须同时指出的是:构成马克思分析背景的城市世界,作为一个理想类型,它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城市主宰乡村的状态,但就其现实性来说,乡村不仅存在,而且会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的需要继续发展并扮演其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换句话来说,在现代性社会结构中,乡村是由城市座架并按其需要发展的。这一点异常重要,它是理解今天城乡关系的关键。由其观之,城市化之概念(用辩证法的语言说,“反思的”)规定性在于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其上的生活方式的全面工业化、商品化和资本化,而非乡村人口和景观的消失。正是这一原因,马克思恩格斯把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理想人群聚落形态。这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把城市化简单地理解为城市消灭乡村的过程,这是极端错误的。因为,这种情况正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对立造成的畸形社会发展。。这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调。我们看到,虽然马克思并没有言必称城市,但其分析恰恰是以城市对乡村的统治为前提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城市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承担者以及表象,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前提之一。也因此,正如哈维论证的那样,城乡对立、劳动地域性分工的重要性、生产力在城市群中的集中、劳动力价值甚至价值规律的作用都呈现出空间的细分、通过交通和通讯技术创新克服空间障碍的重要性,这些对于当代来说至关重要的论题马克思皆有涉及*David Harvey,Spaces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1,pp.325-327.。简言之,从马克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过渡到城市研究,或者在城市研究援引马克思,绝非生搬硬套。甚至,由此出发,建构某种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并非难事。所以,当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等人打开马克思主义城市分析的阀门,它便以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方式散布到流行研究中,以至于在今天有关城市的诸研究中(从空间理论的形而上学讨论到城市规划这样的实践科学)不谈及马克思倒是一种反常。
现在,我们来看列斐伏尔,他强调,“对于马克思来说,空间似乎仅仅是生产场所的总和,是各种各样市场的领域。除了住房问题外,城市也没有产生大的问题”*Henri Lefebvre,State,Space,World:Selected Essay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9,p.211.。因此,当城市成为斗争的焦点,他要求马克思主义在空间分析上有更大的理论作为,提出了升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空间生产知识”计划。当然,列斐伏尔并非告别马克思主义,他清晰地强调自己的城市分析乃是由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个传统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重视的问题生发出来的,而其“空间生产”观点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并回溯性占据元理论位置,乃是由因为他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空间中的商品生产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正是后者构成今天生产关系再生产之神秘化的方面。列斐伏尔实际所做是借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形式语言来分析当代日常生活经验的复杂性,为突出后者的重要性,他不恰当地夸大了马克思主义之空间分析的不足,这导致受其影响的多数研究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错误拒斥。列斐伏尔没有言明的地方,他的欠缺,后来的哈维极大的纠正了。哈维也强调必须把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突出城市、地理和空间在当代的意义,但他的做法是从使用价值和固定资本角度重构《资本论》并由此阐明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化机制、特点及其后果*David 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Oxford:Blackwell,1982.。这是几乎所有公开表明自己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理论家都必须做出的回应,亦是所有试图揭示当代空间生产性质和矛盾的研究都不能简单回避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斯瑞夫特那样的地理学家和沃勒斯坦那样的社会家那里清晰地观察到,前者从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入手试图以地理作为入口为主体与结构之间关系提供一种解释*Thrift.Spatial Formations.London:Sage,1996.,后者则基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与日常生活用品的长距离贸易关系发展出世界体系理论,从而都在城市、地理和空间问题上形成了有影响力的理论创新。
如果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不存在城市分析的缺失,而且实际上是以城市为中轴展开的,只是他本人并没有按照我们在巨大的城市压力下直接把城市作为叙述对象,那么他的分析是否存在着对历史时间的过度依赖呢?即在元理论层次存在着时间压倒空间的偏好呢?也不存在。首先,如果时间描述的是人类发展的一般过程或抽象的变化特征而空间则突出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那么这对于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作为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论的马克思来说,那种倾向是不可想象的。从《大纲》到《资本论》,我们都能够在诸如货币—资本、生产力、阶级这些核心问题的分析上看到马克思真正的关注乃是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历史表现而非其抽象的特点,后者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其次,更重要的是,在唯物辩证法视域中,时间空间不仅是一般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且是人之存在的基本形式。马克思强调,“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32页。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时空是由社会历史决定的,这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的基本前提,正是通过这个前提,马克思把人之生存、发展和自由视为特定条件决定的客观事实,而非抽象的伦理或价值要求。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清晰地表达了空间乃是社会历史产物之一思想,虽然他并没有像列斐伏尔那样直接概括出这个命题。对于辩证法来说,脱离时间的空间与脱离空间的时间,都是不可想象的。《资本论》的一些有关时空关系的重要观点,如关于自然节律和时间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调节,资本主义倾向于以时间来消灭空间,我们都十分清楚,在有关当代研究中也反复再现。而我们反过来说马克思存在着时间压倒空间的叙事偏好,这将是奇怪的。
简单言之,马克思既没有忽视城市,也不存在历史叙事的时间优先性假设,那么,即便是列斐伏尔、哈维这样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为什么仍然谈论马克思分析的空间之维的缺失,这到底是何用意呢?
首先,我们从那些最终告别马克思主义或者对其进行批评的那些理论入手,他们或者认为从马克思无法过渡到当代,这意味着马克思永远停留在19世纪了,或者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存在着原始的缺陷或错误。例如,在许多作者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主要涉及的资本生产,而将劳动力仅仅视为资本生产过程的前提。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展开对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之生产过程的分析。也正是这一原因,当代社会理论突出劳动分工与劳动力的生产、阶级形成之经济过程之外的社会进程影响。在这一类理论家中,吉登斯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提出了替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化理论。在总体上,吉登斯认为,“无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存在着多少极深蒂固的缺陷,它仍然是任何讨论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中的‘地位’的出发点”*[英]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不过,作为其核心的关于生产力(即历史发展原动力)、阶级斗争(即社会变迁机制)和世界历史分期(即社会演化)思想,特别是关于它们的简化表述,一直存在着争论。在此背景中,受结构主义之反本质主义影响,他试图抛弃既往历史叙事之目的论、功能主义和进化论等几种重大假设重建一种能够对当代社会进行总体性批判的社会学框架。这种框架核心假设是:人类社会是作为一种权力结构(即支配性结构,用马克思的话来讲,某种要素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结构)而演化(生产和再生产)的。为说明这种结构的变迁(即结构化),吉登斯引入“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概念,以说明特定的社会(即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与其支配性结构之间的关系,或更准确地说,特定的支配性结构是如何通过对空间和时间的定义形成具体的社会系统的。由此,时间、结构和空间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情境下的特定社会实践是如何展开的,便成了结构化理论的内容。归根结底,吉登斯实际上是以许多复杂的理论概念展开了马克思关于人们在不能选择的条件下不断创造他们的历史这个观点,并对现代社会特点进行了解释。这一类例子表明,把马克思主义空间化的动态,在积极的意义上,是试图把马克思带入当代社会历史情境又而回避教条主义传统的一种努力。因此,严格地讲,当代理论谈论的马克思之“缺失”,不是马克思的缺失,而是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缺失,特别是教条主义,它确实过度依赖了抽象的历史规律或以时间为底蕴的历史目的论假设,从而在当代资本主义变迁回应方面表现出无能。
正是像列斐伏尔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教条主义理论之痛,从而强烈要求把分析的焦点置于当代而不是留恋于一般历史规律的重复,在此过程中,为阻断教条主义的前提,不惜割股断腕,指认马克思本人的含糊或缺失。他认为,在今天,空间矛盾,“不再是马克思在黑格尔之后所分析的那种历史时间的矛盾*[法]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对那种矛盾的分析,依赖于“正-反-合”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的时间机制,而在今天,主要问题,则表现“经济增长”、衰退、恶化和犯罪、日常生活、都市这样的共同时性空间领域*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 of Production.Translated by Frank Bryant.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78,p.14.。所以,他主张以比马克思时代更高水平的辩证综合、发展马克思的概念,创新推动日常生活革命的“空间生产的知识”。当然,在更大的理论范围中,多数试图以“马克思具有时间压抑空间的理论偏好”为缘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社会理论动向,都直接地受福柯影响。在福柯看来,17世纪以后,空间逐步成为权力的手段,而批判理论并没有做出一致的回应,而停留在历史规律依赖上。福柯或许是正确的,但这一点并不适用于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灭亡都是像自然规律那样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时,并非像康德那样诉诸线性时间支撑的世界历史,而是源自对其内在矛盾运动的分析。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结构主义能够普遍地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那里获得共鸣。甚至,整个结构主义思潮,从列维—斯特劳斯开始,它的发展始终受惠于马克思。这个事实表明的,我们无法轻言马克思主义之空间和共时性形式分析的缺失。在直接意义上,指认马克思的分析存在时间压倒空间偏好的缺失,只不过是强调相反路线的一种学术策略罢了。这种策略恰恰是68法国革命失败之后人们寻求新的激进表达之选择。这一点戴维·哈维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在戴维·哈维看来,与后来的马歇尔、韦伯和涂尔干一样,在马克思那里,时间和历史优先于空间和地理,他把后者作为是历史行动的稳定背景或场所。不过,哈维并不认为,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并非必然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他本人也亦试图改变那种偏好而突出空间问题呢?在哈维看来,必须肯定资本主义对空间进行重组的可能性。这是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正的前提,因此亦是实现改造世界的前提。客观上,这是当前左派面临的重要任务: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并没有直接带来对它的当代结构的颠覆性见解,相反由于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变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理论前提空前地暧昧起来。造成这一困境的理论上原因是:在研究资本主义时,多数左派理论家忽视了空间问题,即只关注空间中的资本主义,而没有考虑到空间是如何生产的,以及空间生产的过程如何融入了资本主义的动态及其矛盾。与之相对,哈维试图回答“资本主义是如何生产它自己的地理的”这个问题,并且由此在理论上直接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一种“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Harvey,D.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Baltimore:the Johns Hops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p.xii.就哈维的实际理论成就来看,这两点是显著的:一是通过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重构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空间关系和地理发展的一般理论;其二是在此基础上回应了新自由主义或新帝国主义问题。通过他的例子,我们可以说,谈论马克思主义具有时间或空间偏好是没有多大理论价值的。强调空间问题在当代的重要性,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为了解决这个长期面临的难题:资本主义是否通过地理扩张和重组来摆脱其内在的矛盾。第二国际以来,卢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论,以及源自拉美经验的帝国主义与依附理论,直到今天各种新帝国主义或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理论,都在回应这个问题。哈维抓住了这个问题,即资本主义克服马克思所称的空间障碍或界限乃是一个空间重组的过程*David Harvey.“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in Spaces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1,pp.312-244.,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当代资本主义分析。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例子也激发了人们对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史资源的兴趣。
对马克思分析之空间视角缺失的评价,还涉及问题的另一个层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趋于成熟之际,为这种生产方式的科学叙述提供了一种理想类型,即对资本生产一般的抽象概括,也就是我们今天泛称的“资本逻辑”之一般分析。实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类型分析向今天资本主义现实批判的过渡,是我们而非马克思本人的任务。在完成这个任务过程中,我们提出城市、新阶级、生态或其他什么视角,其现实合理性乃在于这些领域和问题在当代的重要性,但不能由此断言,城市、性别、种族以及生态等视角在马克思那里的缺失是一种遗憾。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期待投射到马克思身上,那意味着解除我们自身的理论义务,它正是教条主义思维的深层逻辑。在这一点上,不只是正统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且多数对其进行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分享了同一逻辑。因此,肖特的这个强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城市不是独立于广阔社会之外的另一个东西,并不存在能从社会反思中抽象出来的独立的‘城市’话语。‘城市’危机、“、‘城市’问题就是社会危机、社会问题,前者不能被简化为地理解释”。*[美]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郑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3页。可以说,这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不能把当代各领域的突出问题简化为某种突出空间重要性的地理解释,而必须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历史进程中来把握它们的性质和表现。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089)。
胡大平(1969-),男,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马克思与城市(笔谈)
B03
A
1003-8353(2016)05-0005-11
【编者按】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城市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城市社会学、地理学以及都市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一,甚至在建筑和城市规划等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如何通过与城市研究联姻,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并且回应西方研究提出的有关马克思的重要误解,从而更好地服务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构成我们的重大课题。本刊就此问题刊发一组讨论,希望能推动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