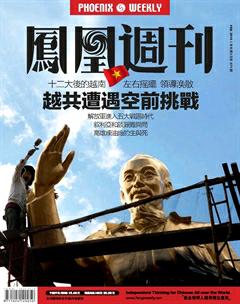前证监会官员谈金融反腐
张弛
持续股灾令中国金融、证券管理部门备受质疑与指责,从去年底至今,中央纪委和相关执法机构已对数十名金融业高官和企业高管进行调查。
金融反腐能否拯救内地股市?2016年伊始,《凤凰周刊》专访了曾任职于中国证监会的资深证券专家何晓宇教授。
不能说“反腐就是权力斗争”
记者:你怎么看待当前中国大陆的金融领域反腐行动?你和金融界一些人士,会更多从专业角度分析,还是会与政治问题挂钩?
何晓宇:目前大陆不止是金融领域在反腐,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在反腐。我个人理解,作为发展中国家,而且是在封建国家的基础上演变过来,腐败的问题会尤其严重。制度不完善,民众监督政府的意识也比较欠缺。十八大以来,中央将反腐这件事情提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而之前没有这么明确强调。我并不认同“反腐只是借反腐干掉对手”的观点。
记者:所以你认为是必须要反的问题?
何晓宇:必须得反,这牵涉金融风险防范问题。作为垄断行业,国民经济命脉,如果腐败丛生,会给整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带来风险。比如说中国证监会,公司上市明码标价,你要上市就要给多少钱。还有邮储银行行长陶礼明,给高速公路项目贷款,回扣明着要。金融领域的腐败,对经济的危害,对民心的侵害,比起其他行业更甚。其他行业都在反腐,为什么要包庇这些金融腐败分子呢?我个人的理解,股灾是一个契机,令金融反腐深化。但这个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姚刚已经是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了,但他一定不会是最后一个。
记者:但也有人觉得,不应该把股灾以及金融系统的问题归咎于几个人。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带领的一个小组出具的一份报告称,中国股市不完善的市场机制、狂热的投资者以及部分媒体的偏颇报道等多重原因导致了股市异常波动,而不是某些具体的“坏人”,引发了股灾。
何晓宇:归根结底还是体制问题。比如姚刚,被称为“发审皇帝”,个人的权力非常大。当个人的权力太大,很多制度基本就形同虚设了。比如我是银行行长,虽然我们也声称是集体领导并建立了集体决策制度,但副行长其实是要看我脸色的。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制度性的建设,包括中国的金融法律一直在完善。有的是市场化的修修补补,像银行业,还有的是彻底翻盘,就像这次中证监的注册制。但问题是,法律摆在那儿,制度摆在那儿,就可以得到执行吗?举个例子,北京不允许随便停车,这是制度,但车子照样到处乱停。再比如注册制,是颠覆性的制度改变,但这就一定能杜绝腐败吗?第一,完善是否到位。第二,即便已经很完善,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很快便会衍生出新的玩法。现在腐败都是团伙化的,监督机构的人也可以被同化,有关方会迅速结成新的利益联盟,大家心照不宣。
制度与执行的悖论
记者:中国大陆也是有制度的,但为什么执行不下去?
何晓宇:是的。不是没有制度,关键是执行不到位,打击力度不够。运动式反腐有积极意义,事后监管和处理也有震慑作用,但运动式反腐有一个问题,不可长时间持续。
总的来说,财产是公有的或者说是国家的,谁该对公有财产负责?如果是人民,究竟谁是人民?金融业,包括央企比如华润,出现腐败问题都是这个原因。你是监事会主席,我是董事长,我是受国家委派管理国家资产的,你是来监督我的,但我们可以勾结在一起,瓜分一点国家资产。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要保卫公有制。要形成一个制度,但这个制度很难完全到位,那怎么才能当好公有制财产的“看家狗”?只能从上往下压,直接从中央层面往下压。金融反腐为什么自上而下,就是这个原因。
记者:不可能有从下往上这种自觉的动力吗?
何晓宇:第一,没有动力;第二,政府没有给予人民这个权力。举个例子,银行最大的客户是谁?存款者。证券业最大的参与者是谁?投资者。都不是国家的钱,是客户的钱。但中国的制度设计,客户是没有权力管理这些钱的。要真正履行对银行、对证券市场、对证监会的监督,应该有一个机构,一个真正代表投资者的机构,而不是政府任命。
记者:怎样让投资者真正做主?
何晓宇:既然政府不能够代表投资者权利,投资者就要推举自己的代表出来。采取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思路就不对。这届政府很有魄力,倡导依法治国,习近平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了三个必胜,“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他喊出了“人民”。这些进步我们都看得到。作为人民,不能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必须有能够行使自己权利的代言人,这就是监督。为什么制度执行不下去,甚至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运动式的反腐搞了一批又一批人,其实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执政党要真正体现人民的呼声。反腐当然会遇到阻力,特别是一些利益集团,但再强大的利益集团,如果这批人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就要坚决打击。不要有顾虑,不要怕被抹黑。
“经济政策政治化”倾向
记者:金融监管部门出台的一些政策,包括救市的措施,有一种“经济政策政治化”的倾向。作为专业人士,你怎么看待类似这些政策?
何晓宇:我个人认为,这届政府有些方面做得很不错,比如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加自信,做工作也很扎实。但在前段时间,整个社会舆论有一种保守思潮,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有所体现。包括反腐,反到连职工的福利待遇都没有了,矫枉过正。当然现在政府已经在微调。
内忧外患,国家面临的形势比较严峻,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执政党的确会格外警惕。大环境如此,加上中国人又喜欢察言观色,有点什么苗头就开始猜。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乱象可以理解,而这种东西也会渗透至金融领域。在这方面,政府做得还是很到位,一直在微调。
记者:金融领域的种种表现,其实也是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大环境的一个缩影?
何晓宇:是的。这些也会渗透到金融和经济领域,这是由思维模式决定的。比如政府定了,就这么干,这是否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肯定是违背,我总体上也比较不认同这种做法。但是,在极个别特定情况下,就像“股灾”,除了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也没必要完全排斥行政手段。
我个人认为一些思潮应该警惕,但事实上会很难。对于很多人而言,包括监管部门还有学者,会宁肯保守一点,这样不会犯错误,能保住“乌纱帽”。大家都希望明哲保身,不会发表任何逾越底线的言论。这些我可以理解,但这对国家、对民族,还有对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历史会证明这一点。
“不作为”也是一种腐败
记者:你认为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何晓宇: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中国经济要崩溃,也不是要亡党亡国。我相信共产党的执政能力,1976年经济那么困难,现在也是世界第二了,将来还可能是老大。最大的问题,是人们精神上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反腐败也没多少价值。
记者:你的意思是需要重建人的精神信仰?
何晓宇:整个社会很多人已经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了。比如,很多人觉得说实话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不仅可能犯错误,也得不到什么实际利益。而这种文化,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如果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怎么办?就像我是教授,就考虑怎么让自己更有名,捞到更多的钱,不这样想的话,别人反而觉得你不正常。这种“不作为”,其实也是一种腐败。
今天谈的话题是金融反腐,实际深入谈下去,是人人都在想如何让自己利益最大化。有些人政治立场忽左忽右,其实是在察言观色,看能不能捞到好处,并不是内心真正的想法。金融反腐的关键在哪儿,是要治病。所谓制度、规则从来都不是关键,那只是操作层面的技术问题。重点是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不然,运动式反腐过后,还是会死灰复燃。
记者:所以主要还是人的问题?
何晓宇:这么高层次、大面积的腐败,尤其是金融领域,那些腐败分子,都曾经是国家的精英人才。
专业精英人才,然后全部毁掉了。随便说两个,一个姚刚,一个张育军,都是平时低调、勤奋又有才华的人,现在都身陷囹圄。党培养他们多年,如今走上犯罪道路,难道完全是个人责任吗?没有大环境,他们能腐败得了吗?我要说的是,我们要总结教训,不是把腐败分子打掉就完事了。
记者:对于这一轮金融反腐的前景你怎么看?如何往下推进,有没有一个预测?
何晓宇:整体的反腐行动,中央是肯定不会收兵的。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包括王岐山,他们真的想做事,不是要建立什么丰功伟绩,捞个人利益。这轮反腐是史上规模、范围、力度最大的,对于前景,我还是非常看好。不过,所谓的看好,只是说在这种强力高压下,会有一批人有点不敢腐败了,但下一步要做的,应该是让这些人彻底不去想腐败这件事。就这点而言,还是没有彻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