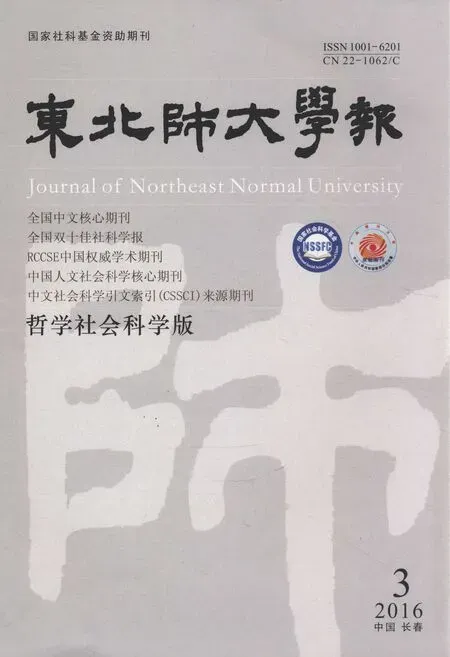语言与再生产
——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探微
周 旻,侯怀银
(1.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2.山西医科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1;3.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语言与再生产
——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探微
周旻1,2,侯怀银3
(1.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2.山西医科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1;3.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伯恩斯坦是“再生产”理论的创始人,他的研究受到了欧洲结构主义、古典社会学的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共同影响,最终形成独特的符码理论。他的理论从语言符号学入手,逐步渗透到社会权力控制的核心,指出:语言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和文化再生产的工具。学校教育由于受到中、上层阶级的掌控,无论在教学还是评价方面,都使用中、上层阶级的语言进行传递和沟通,因此相较于工薪阶层的儿童,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更容易取得学业及社会适应方面的成功,进而步入上层社会,实现阶级的再制。看似平等的学校教育,其实质是带有不公平性的。
[关键词]伯恩斯坦;符码理论;再生产;教育社会学
伯恩斯坦是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教育社会学家,是新教育社会学派的奠基人。他的理论中充斥着语言、符号、权力、文化、意识形态、阶级、再生产等晦涩繁冗的概念,思想足迹遍布语言、心理、教育、社会、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其符码理论既是他学术思想的集结,也是其毕生研究的重点。这一理论,以语言学为切入点,经过社会学和教育学的实践检验,最终落脚到哲学的高度,为我们揭示了隐藏在学校教育背后的不平等,以及教育的文化和阶级再生产本性。纵观我国学者之前的研究,对于伯恩斯坦的研究少之又少,究其原因在于以下两点:首先,伯恩斯坦的思想横跨了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其涉猎之广、思维之繁很难单纯地从一个学科的角度去加以解读;其次,关于伯恩斯坦理论的来源,至今未有定论,多数学者将其归为“涂尔干主义”者,也有学者认为他的思考秉承了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还有学者认为他的思想是英国新教育社会学的一部分。但是这些都没有得到他本人的认可,英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Douglas,M)也因此戏称:伯恩斯坦是一只“非鱼、非兽、非禽”的怪物。本文,从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入手,着重从文献的角度梳理伯恩斯坦思想的理论渊源,并探究其理论中关于学校教育的再生产本性研究。
一、符码与符码理论
(一)符码
1.符码:符号传递“意识”的衍生物
符号的本意指具有某种指代意义的标识。它可以指代一个对象、一种特性,或者一个事件。但是,无论是索绪尔的传统符号语言学思想,还是卡西尔的文化符号论,抑或是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最终都将符号学的研究指引向人与社会的范畴。当符号的指代客体变为某主体的观念、思想、意识时,符号就从一种单纯传播讯息的载体,变为偏向主体表达习惯的专属介质,符号也就从原本的客观指代,完成了其社会化的过程。这种社会化的符号和符号的社会化过程,就是符号的编码,简称符码。
人类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就是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和人的存在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1]30,它们之间形成一一对应的指代关系。在表达“意识”时所指涉的就是符码操作的一整套东西,包括主体、各种生产关系以及之间的联结方式,因此控制“意识”也就成为统治阶级确立自身统治地位的命脉。父母、教师、神父等责无旁贷地成为传递意识的主体,他们所运用的语言,所讲授的知识,所认同的习俗,所传递的观念,经过与客观指代的符号相整合,就自然地成为意识传递的载体,成为了载有一定意识的符码。
2.符码:符号组成方式背后的文化
符码与符号不同,它强调的是建构文本系统的材料,也暗含了一种破译文本意义的规则。最初,索绪尔在《语言学教程》中提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如果我们能够在各门科学中第一次为语言学指定一个地位,那是因为我们已把他归属于符号学[2]38。在此基础上,索绪尔将符号分成“所指”和“能指”两个部分,来对应生活中的“概念”和“声音的心理印迹,或音响形象”。与之相比,卡西尔则从文化的角度,为符号赋予新意。在《人论》中,他说: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3]33。这样的论述,超越了符号的普遍意义,既表明用于大众交流和沟通的工具的符号,也突出了符号的感性之处——当符号通过一定的编排方式,构成一种稳定的符码,在大众间传播的时候,其本身会不自觉地携带使用主体思想所特有的意义,以区分主体存在的文化背景。
语言原本是一种单纯的表述符号,但是不同的主体有其不同的语言组织习惯和规则,当语言在组织和使用方式上带有了主体的独立思考和个性习惯时,语言本身就成了一种最基本、最常见、最通俗的符码。
(二)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
伯恩斯坦在1960年进入英国伦敦大学语音学系担任助教,基于对犹太家庭孩子和贵族家庭孩子在入校初就表现出学习方面的各种差异,他大胆地假设“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孩子的语言使用习惯是造成他们之间学业差距的主要原因”,此后他立足这一论点,探索语言符号的功能在社会建构时的重要作用,进而确立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儿童的交际代码中确实存在社会阶级差异[4]137-149。
1962年,受到卡西尔文化符号学的影响,伯恩斯坦第一次在文章中使用了“符码”(code)一词[5]221-240。他认为自己的思考突破了结构主义中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更多探讨的是不同文化背景阶层的语言构成习惯与使用规则,即语言与社会构建的相互关系;因此,他选择“符码”一词,着力将研究提升到传递阶级文化的手段这一高度。伯恩斯坦指出:劳动阶级所使用的限制型符码(restricted code),其组成多选择简单而受限的语言方式,其理解也必然依赖于特定社会脉络的语境,具有一定的特指性。在使用过程中,劳动阶级更遵从共同的背景预设,每次交流都可以看作是对社会秩序和权力的重复强化;使用精致型符码(elaborated code)的中产阶级则不然,精致型符码本身就是由复杂的语言方式构成,并包含完整的语义,这类语言更重视个人思想的表达,其理解也并不一定要依附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使用精致型符码的中产阶级更注重个人知觉的表达,同时也更乐意接受不同的背景预设。
经过调查,伯恩斯坦发现在资本主义学校中,教育者更偏爱用精致型符码传递知识,相较于劳动阶级而言,中产阶级的子女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学校的这种知识传递方式,因此在学校教育中获得了更高的参与度和认可度。可见,语言其实是一种切实存在的权力的延伸,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先锋。
二、符码理论的学术渊源
对于符码理论的解读,既不能单纯地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也不能仅仅从教育学的角度来分析,究其根本,我认为伯恩斯坦符码理论的构建来自于以下三方面的启示:
(一)以欧洲结构主义为思维框架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目的是描写一个理想化的、内部具有一致性的语言系统[6]174-178。在伯恩斯坦的研究中,广泛地关注了语言、课程、教学等概念,并将其根植于家庭、阶级、学校等社会结构中,深化为意义、意识、文化等哲学话语,并赋予自己独特的解释——符码、分类与架构。因此,吉布森(Rex Gibson)在其《结构主义与教育》(《Structuralism and Education》)一书中,曾明确地指出伯恩斯坦是一个“具有欧洲结构主义所有特征的结构主义者”[7]175,并且将“伯恩斯坦”独立成章命名为“伯恩斯坦的结构主义”。
1958年,伯恩斯坦发表的第一篇文章《Some soc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perception: an enquiry into sub-cultural differences》中指出:中产阶级的儿童有能力回答、掌握和理解语言……这是一种阶级环境的结果,由于工人阶级环境的不同,工人阶级的儿童……在表达符号和公共语言上是受限的。1962年,他又说:“社会学家研究的任务之一是寻求特殊语言形式的社会根源……社会结构将语言的可能性转化成一种特殊的符码。”1971年,“精致型符码和限制型符码,是由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产生的,实际上,它们很可能是不同社会结构的一种表现。”直到1982年,他还不断地提出:阶级关系受产生、分析、复制不同的沟通形式并使之合法化,它传递支配和受支配的符码……在文化上决定了这些符码定位的方法。在他思考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能发现其思维中结构主义的影子,“社会经验是由社会阶级结构所控制的”这一论断,更是贯穿其思想始终。这也使得他的结构主义,被公认为与英国和美国教育社会学主流相关联[7]178。伯恩斯坦的研究关注的是关系,而并非语言或环境,这是典型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
(二)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批判继承
伯恩斯坦自己曾坦言:在宏观层面我运用涂尔干和马克思思想[8]37。如果说欧洲的传统结构主义是其思维的主要架构方式,那么涂尔干的社会劳动力分工理论和马克思的阶级思想就可以作为他分析社会结构的客观基础[8]34。因此,在伯恩斯坦的理论中到处充斥着对“生产”、“阶级”、“分工”等概念的论述和拓展,在他诸多论文的参考文献中,也随处可见对马克思、涂尔干等人的学术论著的引用。
伯恩斯坦说:马克思开启了意识的阶级分化的问题,及其与社会分工和生产的社会关系之关系[9]140。因此,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他采用了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分层方式,以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为研究对象,但是,他又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方面的矛盾,具体的说是指经济领域的生产关系及工具控制决定阶级的位置与关系[8]60,而伯恩斯坦和他的符码理论所关注的是文化再生产的问题,因此,对于马克思经典论断“阶级之间的区别在于控制‘物’(the ‘object’of control)或权力关系的‘基础’(the ‘basis’ of relations of power)”[10]59-82,这一观点中的“物”或“权力关系基础”伯恩斯坦都转换为一种“文化的特质”。
与马克思不同,涂尔干在研究社会分层,谈论“不平等”问题的时候,把社会的不平等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个人的出身背景不同而导致的不平等;另一种是由个人能力而导致的不平等,即外在不平等和内在不平等。伯恩斯坦早期所做的智力和词汇测验都是将被试按照出身背景进行分组的。因此,布列克里局·杭特等人直接将伯恩斯坦归为“涂尔干学派”,以此来表示他受涂尔干思想的影响之深。伯恩斯坦自己也说:精致型符码理论的研究为解释教育论述的社会结构及其不同实践的塑造,成为一个社会权力分配和控制原则的载体,就此而言,似乎可以说它回到了涂尔干思想的源头[9]142。
(三)与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互动
新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学,这一群体的共同观点是反对马克思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更加强调思想、文化、文学等上层建筑在构成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伯恩斯坦梳理了经济与文化的主要观念之后,提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在“五十年代后期受到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人的修正,他们对于公民社会、霸权、知识分子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和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尔都塞更是大量借用葛兰西的观点来分析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11]150,并笑谈:“在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我发现和我阐述的问题产生共鸣且最契合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阿尔都塞(Althusser)的意识形态理论:想象的主体。”[9]195
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指出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阶级实践考虑而构成的;在他看来,外表中立的教育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本质同教会、传媒是一样的,学校可以算是意识形态的大本营[12]224。
伯恩斯坦受到阿尔都塞思想的启发,在1990年出版的专著《阶级、符码与控制(第四卷)——教育论述之结构化》中,他阐明:一种社会类别的话语,是由规约并合法化的沟通形式及专门化的论述规则构成的[11]25。这种“合法化”和“专门化”的话语方式既是统治阶级实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载体,更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不仅稳固了统治地位,同时也完成了阶级的复制。
三、再生产:符码理论的教育控制逻辑及实践结果
伯恩斯坦强调:“符码,是支撑语言形式和社会形势,及其变化和再生产的结构化的原则”[13]66。因此,19世纪70年代后期,他开始以符码理论为工具,从结构主义的视角,不断地分析教育实践在文化和权力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一)符码理论的学校教育控制机制
1.学校课程的符码式分解:聚合型符码和统整型符码
课程是学校传递知识的具体形式。伯恩斯坦在谈论课程的时候,并不是着眼于课程的内容或课程的编排,而是以一个非常抽象的方式谈论课程。他发现有些课程在安排时间上有多寡之分,从课程性质的角度来说,又有选修与必修之分。伯恩斯坦认为这两个方面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课程内容的相对地位。而课程与课程内容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又可以表明课程内容之间的关系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
通过研究,他发现在高地位的课程之间,往往保持着一种相对封闭的关系,伯恩斯坦将这样的课程称为聚合型课程(a collection type),这种课程各个内容之间相对独立,界定清晰,学习者必须掌握大量的有效内容,才能符合评价的标准。在教学方面,这种课程注重知识的陈述式获得,因此更强调教师的教导,学生的自主权相对较小,其结果的可测评性较高;而那些相对开放的课程,被称为统整型课程(an integrated type),这种课程的教学内容之间相互融合,它们原本就是贯穿于一个普遍性的观念之中的,这种观念的变动也是未尝可知的,因此其指导下的课程也趋向一种同质化。在教学方面,则更重视知识的自主获得,学生自主权相对提高,自我调控的程度更高,其结果的可测评性较低。
伯恩斯坦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的课程是以聚集性课程为主的,这样学校就可以通过考试,轻松地将学生分为“有文化”、“无文化”或“好学生”、“坏学生”等几类,由此达到控制学生等级的目的。
2.教学符码的实践形式:分类与构架
分类(classify)与构架(framing)是伯恩斯坦提出,用以分析课程、教学和评价这三种信息系统的内在结构的一组概念。伯恩斯坦的分类并不是涉及内容的分类,而是指针对内容之间的联系的一种分类。在知识与知识之间,有些通过清晰明确的界限划分,而显得泾渭分明,这样的知识之间具有较强的隔阂,我们将其称为强分类;而另一些知识内容之间的界限模糊,其独立性也较弱,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更为融合,我们将其称为弱分类。因此,分类关注的是内容之间的界限的清晰程度,我们可以此作为教育知识的劳动分工的依据。
构架这一概念同样不涉及教学知识的内容,它所关涉的是传递和接受知识背景的形态,以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构架强的场域,可传递的知识与不可传递的知识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在构架弱的场域,则界限模糊。这种界限其本质左右着教学关系中知识传递的形态。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对于教学内容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选择的权力。在构架强的场域中,教育主体可突破的范围较小,可选择的余地也相应较小;而构架弱的场域,则意味着教师和学生拥有较宽泛的选择余地。简而言之,构架的强弱决定了教学关系主体对于教学活动的控制程度。
在当时,英国的学校教育以精致型符码的传播为主,属于弱分类弱架构的言说结构系统,此种情况使中、上阶层学生能够快速进入学校场域的知识结构和师生的权力关系网络,他们能有更好的学习表现;而劳动阶级的子女多使用的限制性符码属于强分类强架构的组合,与学校场域内的知识结构并不相符,因此难以获得成功[14]13-33。
(二)符码理论的文化和阶级再生产实践结果
伯恩斯坦曾直接地指出:知识就是一种高质权力,一个社会如何选择、分类、分配、传递和评价它认为具有公共性的知识,反映了权力的分配和社会控制的原则[15]61。
通过分类与构架,教育的权力再生产实质呼之欲出。伯恩斯坦认为生产方式和教育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最后的输出方式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但是他敏锐地指出这两种输出方式均暗含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因此在社会基础在结构上是相似的。不同分工的社会实践受社会分工的原则及其内在的社会关系所约束,而社会实践是社会分工的表现形式,一旦社会分工形成,每个阶层便会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来夯实这种分工的结构,伯恩斯坦将这种实践的方式称为“专门化”[11]25。与此同时,专门化的类别,一定会带来专门化的“语言/声音”,这种语言是这一类别专门化的媒介,米德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社会组织原则,社会成员正是通过语言(符码)的互动来学习自己所属的角色及应有的行为。这种带有合法化和专门化的语言无形中传递了属于自我阶层的特定的认同和界限;因此,语言的使用已经不再是个人习惯,而是个人社会化习得、社会关系形态及社会认同的反应[16]68-72。
在教育活动中,同样遵循这样的符号体系,社会权力通过一种隐匿的控制力来左右学校的教育实践活动。不同的社会关系使用不同的符码规则,不同的符码规则又进一步拉大了不同社会关系间的分歧。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权力阶层制定的文化,因而更容易在成绩和职业选择中胜出,进而重复地去推行上层阶级所认同的文化,从而实现了权力阶级身份的代际延续。至此,教育实践的文化、阶级再生产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是他毕生研究的思想结晶,这一理论既是其早期理论研究的终极成果,同时也是他后期实践研究的立足点。梳理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有利于我们跳出教育社会学,甚至是教育学的圈子,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围解析教育公平的问题,探讨教育在文化生产中的作用,揭示教育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力量,了解教育在意识形态控制中的作用,从而提升教育研究的层次,拓宽教育研究的视野。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岑麒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4] 阿兰·R·萨多夫尼克.著名教育思想家巴兹尔伯恩斯坦(1924—2000)[J].教育展望,2002(4).
[5] Bernstein·Bernstein. Social class, linguistic codes and grammatical elements [J]. Language and Speech, 1962(5).
[6] 王萌萌.乔姆斯基内化语言理论的解读及反思——纪念《语言知识:其性质来源及使用》出版30周年[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7] 吉布森.结构主义与教育[M].石伟平,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民84).
[8] 苏峰山.意识权力与教育——教育社会学理论导读(2版)[M].高雄: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5(民94).
[9] Basil·Bernstein.教育、象征控制与认同——理论、研究与批判[M].王瑞贤,译.台北: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民94).
[10] Apple·M. Education, culture and class power: Basil Bernstein and Neo-Marxist sociology of education. Knowledge and pedagogy: the sociology of Basil Bernstein[M]. Norwood, N. J.: As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95.
[11] Basil·Bernstein.阶级、符码与控制(第四卷)——教育论述之结构化[M].王瑞贤,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6(民95).
[12] 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13] Atkinson·Paul. Language, Structure and Reprodu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Basil Bernstein [M]. London: Methuen, 1985.
[14] Bernstein, B.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vol.4: The Structuring of Pedagogic Discourse [M]. London: Routledge,1990.
[15] 麦克·F·D·扬.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M].谢维和,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6] 周利敏.从“权力再制”到“文化再制”:教育实践中的符码逻辑[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4).
[责任编辑:何宏俭]
Language and Reproduction: Bernstein’s Code Theory
ZHOU Min1,2,HOU Huai-yin3
(1.Marxist Philosophy Institute,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2.School of Humanities,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Taiyuan 030001,China;3.School of Education,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Bernstein is the founder of reproduction.His study from the structuralism,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ies, and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Neo-Marxist, eventually create a unique theory of code.His code theory learns Semiotics of language,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the core of the social power control. He points out that codes is a habit, when somebody edits and organization language, they must comply with their respective classes. And then he found that the middle-class make good use of elaborated codes, and the working-class tend to use restricted codes. The school education is controlled by middle-class,it always followed the elaborated coding that conventions of power elite. So compared to working-class children, the children of the middle-class were easier to adapt and integration into this education, and more likely to succeed. When they into the upper classes of society,the purpose of reproduction is reached.
Key words:Bernstein; Code Theory; Reproducti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收稿日期]2015-07-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一般课题(BAA140015);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4228)。
[作者简介]周旻(1982-),女,山西太原人,山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侯怀银(1963-),男,山西平遥人,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6)03-0235-05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3.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