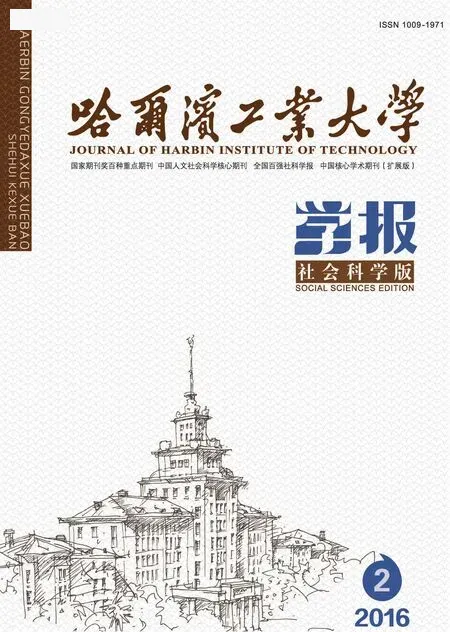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的路径选择
江 卓(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的路径选择
江 卓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
摘 要:20世纪后半叶,西方民主遇到了危机,民众参与政治乏力,政治合法性危机涌现。在此背景下,协商民主在西方逐渐兴起,尽管西方政治实践中一直就有协商的传统,但其协商民主并非是在总结政治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在对选举民主的批判基础上产生的。在中国,协商民主却是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人批评中国是威权国家,不具备相应的民主政治生态。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备政治合法性、逻辑正当性与制度优越性。它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倾轧和竞争基础上的两党制、多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运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推进协商民主建设,并把好的实践制度化,可以彰显中国民主建设的成就和进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国家治理的必然路径选择。
关键词: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国家治理;政治实践
一、西方协商民主的产生与发展:理论、实践与实验
古希腊时代的民主城邦由于疆域狭小,社会生活相对比较简单,公民之间同质性较强,于是他们发明了直接参与式的民主。“民主是一种既区别于君主制、又区别于贵族制的政府形式,在这种政府形式中,人民实行统治。”[1]1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人口、疆域大幅扩展,使公民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变得非常困难,精英治理成为不二选择,同时由于很多理论家认为直接民主容易导致多数暴政、非理性政治、激情政治和群氓政治等劣质政治现象,于是就出现了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即公民自己选举代理人进行统治与治理。它普遍兴起以后,选举变成了民主的基本标志。
二战后,美国学者熊彼特将代议制民主进一步发展为“精英民主”,指出民主并不是人民自己“当家做主”,而是为了达到政治决定而采用的一种方法和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下,想获得决策权的人要在人民的选举中通过竞争而产生”[2]。不同于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精英民主直接否认民主是人民的统治。精英民主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人民的统治,民主只是一种精英产生的程序。当今欧美国家的制度安排被看作是这种民主形式的典型体现。综观美国的总统制、欧洲的议会制,民主主要体现为公民通过总统选举或议会选举,选择政治精英去制定公共政策,管理国家事务。
民主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大众和精英的权力关系:究竟是大众还是精英掌握权力。现代民主并不反对精英的领导,但是反对精英对权力的垄断。民主就是要“让精英团队保持领导力,让平民团队保持影响力”[3],就是要保持精英和大众的一种平衡。
然而,伴随着民主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胜利的却是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在雅典的直接民主体制中,一方面,公民能够直接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过程当中,另一方面,公民参与并不受到等级、社会地位和财富的限制,穷人和富人在治理国家当中的地位是相同的[4]。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中,公民不再亲自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而是选择自己的代理人进行管理和决策。在精英民主看来,民主仅仅是一种产生领袖并使之合法化的制度安排,精英是政治过程的核心,而不是民众。
民主理想和民主实践之间的落差愈演愈烈,许多民主国家的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兴趣匮乏,伴随投票权扩大的却是投票率的不断下降,政治冷漠大行其道。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实践中的问题层出不穷:金钱左右选举,筹款越多,竞选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媒体左右选举,选举变成了选秀,选举候选人“多少有点像我们挑选清洁剂一样”[1]269;政治过程演变为政治精英间的竞合游戏,“谁来统治”变成“选谁来统治”,公民与政治渐行渐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方学界开始反思以代议制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理论。以佩特曼为代表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家们认为,政治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和政治冷漠必须通过政治参与来解决,主张扩大民主参与的层次和方式。协商民主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西方学界兴起。1980年,美国学者约瑟夫·毕赛特在其博士论文《国会中的协商:一项初步的研究》中,最早阐释了协商民主的概念。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尤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等也加入了协商民主的研究和讨论中,被公认为协商民主的理论大师。他们使协商民主理论成为西方民主理论讨论中的重要一派。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以公民参与协商提高公民的公共理性,以协商程序来体现人民主权,借此重新提振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协商民主所关注的不是领导人的选举,而是决策的民意性。协商民主是对自由民主的补充完善,还是对自由民主取而代之的新型政治模式?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协商民主的两个主要流派。一是自由主义协商民主理论,认为协商民主绝不是对自由民主的替代,而是自由民主的一种补充,协商民主各种制度和途径的运用目的在于提升选举民主的质量或者激活选举制度,使其真正对普通公民有利。二是协商民主替代理论,认为民主的本质是协商,而不是投票,理想协商是不需要投票就能够达成共识,如果把协商民主置于自由民主的框架之下,就会限制和扼杀协商民主的创造性和发展空间。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西方大多数协商民主理论家认为协商民主的产生是为了弥补选举民主的缺陷,是自由民主的有益补充。
尽管西方政治实践中一直就有协商的传统,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协商民主理论并非在总结政治实践的基础上产生,而是在对选举民主论的批判基础上产生的。可以说,西方协商民主是从理论到实践的。协商民主主义者是在反思过去民主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协商民主理论,然后用这个理论去指导协商民主实践和实验。后者包括诸多形式,相对常见的形式是公民共识会议和协商民意测验。
其一,公民共识会议。主要是在政策做出之前,在专家的指导下,邀请公民参与对话和讨论,最后形成讨论的意见和建议,以供决策机构参考。一方面,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倾听和尊重了公民的意见;另一方面,公民也在对话协商和讨论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并直接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其二,协商民意测验。协商民意测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协商民主研究中心主任菲斯金开创的一种协商民主实验。菲斯金先后在20多个国家或地区尝试了协商民意测验方法。协商民意测验的关键点是在协商讨论前后进行两次民意测验,主要就是观察经过协商和讨论之后,民意是否发生了改变,以此来说明协商和讨论对于真实民意的重要价值和意义。通过实验发现,对话、讨论和协商确实对改变和塑造民意有着显著的作用,还可以激发普通民众了解、学习和参与国家事务的积极性,促进沟通,从而增加社会资本。
上述协商民主形式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由于参与人数较多,组织起来更为困难,成本巨大;其次,这些形式在很多地方只是专家和学者的实验,缺乏连续性和制度化;再次,并不是每一个想参加的人都能参与,对于那些没有参与的人来说,这种会议是否就具有正当性,同样存在疑问。
二、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的逻辑路径和政策支持
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特征;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线,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其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始终以实现人民民主为己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各种形式推动党派联合,充分利用和发挥革命统一战线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整合了社会各革命力量,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协商方式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也把民主列为主要的国家层面的价值。
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两种形式:“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这样的划分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首先表明中国的政治形态毫无疑问体现了民主政治的精神,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世界民主政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表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区别于西方,中国的民主政治不是简单照搬照抄别国的政治模式,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特定发展阶段出发,发展出的一套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的人民民主制度。区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并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既是对过去民主政治探索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今后民主政治发展的前瞻性指引。
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在反思以代议制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主要是思想家为了弥补选举民主的缺陷而设计出来的一种民主形式,在实践中主要是思想家的思想实验。在中国,协商民主却是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不管是中央层面的政治协商会议还是基层的民主恳谈,都是具体的政治实践。在中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中,一直就有协商民主的传统。当然,实践中的这些协商民主既有成功的经验需要总结和推广,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
中国协商民主实践开始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和完善。协商民主制度是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实践共同成长的,不仅成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也成就了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和实践。在实践层面,协商的范围由党派到国家再扩展到社会领域。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认识到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必要性,第一次国共合作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党派协商实践。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政。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更加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政权,可谓协商民主在政权建设中的第一次伟大尝试。解放战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顺利实现协商建国,协商民主开始在国家层面全面展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政党制度正式确立。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之后,毛泽东指出“通过政协容纳许多人来商量事情很重要”,明确了人民政协继续存在的必要性。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被明确写入宪法。在国家层面协商民主快速制度化的同时,中央适时提出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任务,标志着协商民主向社会层面扩展的开始,权力机关的立法听证和政府机关的政策听证发展迅速。在党和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下,基层协商在乡村和城市行业间迅速发展起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国家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进,政府与社会间的网络协商也在地方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政治协商制度、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和基层协商制度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中国协商民主一直就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实践。中国开展的这一系列的协商民主制度和机制促进了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为缓解社会矛盾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与前苏联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中国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是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有国外学者批评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认为中国的发展不可持续,会陷入“局部改革陷阱”。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治领域所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得以推进,恰恰是以政治改革和进步为前提的;很难想象在没有政治改革的前提下,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中国具有悠久的民主协商传统,中国共产党建政和建国的历史中蕴含了大量的民主协商的政治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协商民主从上到下更是蓬勃发展。研究中国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的多层次制度化发展,是彰显中国式民主的重要方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套规范的制度和程序。这些规范的制度和程序既有根本大法宪法的保证,又有具体规章制度的详细规定。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就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12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从制度上、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人民政协的性质被定义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各人民团体共同参与和协商合作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被明确写入宪法。2006年《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首先提出了“把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的命题。中共十七大报告再次鲜明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2007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指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中共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的发展被提到新的高度。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协商民主第一次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5]。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系统阐述了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协商民主规定,指出了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来源、意义以及如何推进协商民主等。2014年10月27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2014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该文件于2015年2月9日由中央办公厅下发。该文件对协商民主的描述是:“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
三、比较视野下协商民主的发展空间:中国国家治理的必然路径选择
尽管中西方协商民主差异很大,协商民主也有许多研究流派,研究者目前还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在协商民主的本质和内涵上,也有一些清晰可辨的共同特征。
第一,协商民主主要是一种决策过程中的民主机制,其强调要通过制度、机制、程序和技术让公民参与到决策过程当中,以此来激发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进而改善和提高民主的质量。从西方协商民主的实践和实验来看,决策过程中的协商和讨论主要发挥的是咨询和测验民意的作用。戴维·米勒认为:“当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过程而达成,其中所有参与者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并愿意平等听取和考虑不同意见时,这个民主体制就是协商性质的。”[6]
第二,协商民主强调大众要理性参与政治。协商民主的支持者强调公共事务要公共协商和公共讨论。民主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公民要参与政治。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参与都是各国普遍认可的民主原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民直接参与管理和决策,也不意味着把政治参与仅仅看成投票活动。协商民主强调公民要参与到决策过程中,但只是公民的参与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而非公民个体或团体亲自作出决策。从这个意义看,协商民主与代议制和精英统治是并行的,目的是在精英占据政治主导地位的当下,让普通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从而在精英和民众之间达成一种平衡。
第三,协商民主强调对话和讨论。协商民主支持者认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是对话和讨论,通过对话和讨论,提高公民的理性和政治辨别力,以此反映真实的民意。
中西方协商民主尽管存在以上共性,但差异之大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想从逻辑上确定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发展空间,需要从比较视野出发进行观察:
第一,中西方协商民主发展的逻辑路径不同。西方的协商民主发展过程是从理论到实验,主要是思想家为了弥补选举民主的缺陷而设计出来的一种民主形式,在实践中主要是思想家的思想实验。中国的协商民主发展过程是从实践到理论,不管是中央层面的政治协商会议还是基层的民主恳谈,都是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在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的。尽管西方政治实践中一直就有协商的传统,甚至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公民街头的政治辩论,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协商民主理论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在总结政治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在对选举民主论的批判基础上产生的。思想家为了弥补选举民主的缺陷而设计的一种民主形式,在实践中主要是思想家的思想实验。协商民主比较关键的内容是谁来发起和组织协商,谁来参与协商,西方协商民主的实验更多是研究者推动的,因此,组织者很多是学者和学者依托的研究机构。学者推动的协商民主实验往往设计比较周密,程序比较完善,但往往只是思想家进行的学术实验,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有限,而且成本高昂,持续性和制度性较差。中国协商民主却是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不管是中央层面的政治协商会议还是基层的民主恳谈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协商民主实践,都是具体的政治实践。在中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中,一直就有协商民主的传统。在基层,协商民主试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基层治理问题的,如解决了基层政府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基层民众的政治冷漠难以形成基层自治、基层政企和社会间资源难以有效整合等问题。
第二,中西方协商民主在实践中的发展空间差异很大。西方选举民主制度化程度较高,相对比较成熟,因此,协商民主在实践中事实上空间并不是很大,在实践中大多数是思想家的政治实验,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事实上仅仅处于边缘地位。中国的协商民主本身就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当协商民主这一概念和理论传入中国之后,尽管该理论与中国的政治实践特别是中央层面的政治协商相去甚远,但是仍然在中国引起了学者和政治家的广泛积极回应。由于西方选举民主制度化程度较高,相对比较成熟,协商民主在实践中事实上空间并不是很大,目前参与协商实验和实践的还是少数公民,还没有影响到广大普通民众,因此还没有形成一种影响民众思维和日常生活的民主模式。学者推动的协商民主实验往往采取的是抽样的办法选取参与者,这种办法确实能够保证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但是,参与对象缺少利益相关性,往往参与热情难以持续。此外,协商民主实验的参与人数毕竟有限,对于那些大多数没有参与过协商民主的人来说,一方面协商民主的正当性值得思考,另一方面也难以对他们产生直接影响。在理论上,虽然协商民主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研究协商民主的队伍仍不够庞大,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事实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因此,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西方协商民主事实上与理想的状况差距仍然很大。恰恰相反,在中国政治实践当中,当选举民主遇到发展瓶颈的时候,协商民主在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来。协商民主理论出现后,中国很快就引入了这一概念,希望通过这一概念对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进行解释和总结,并进一步指导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使其制度化和规范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以应对民主化与政治合法性的压力。进而言之,由于中西方协商民主发展的路径不同,中西方运用协商民主理论的目的也不同,因此,尽管中西方协商民主理论都强调要让民众参与到政治决策和管理过程当中,而不仅仅是投票和选举,但是中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内涵不同是很正常的。那种认为中国政治实践中不存在西方式的协商民主,从而贬低甚至否定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的做法是错误的。事实上,把西方的这一民主理论翻译为适合中国话语体系的协商民主,对于促进中国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的发展意义非常重大,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创新。唯有以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创新特别是基层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创新为基础,正视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差异,并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制度和程序设计,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而这种理论和实践创新,才是中西方对话的基础。
第三,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不同。中国的协商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在推进和完善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目标是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入新的活力。加强协商民主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有组织、有重点、分层次积极稳妥推进各方面协商。”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主导了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不管是中央层面的政治协商还是基层的协商民主,都是在各级党组织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协商民主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和改革时期,探索新的执政合法性来源,所以,协商民主对于巩固和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协商民主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途径。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方面经验,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价值需要有具体的民主制度、程序和技术来实现,中国目前大力发展协商民主的目的就是在具体制度、程序和技术上让人民当家做主有实现的依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和民主建设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要用民主来实现国家认同,用法治来构建国家秩序。因此,协商民主要保持健康、稳定、有序发展,必须在实践中坚持和运用法治原则。
参考文献:
[1][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绛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37.
[3]燕继荣.“草根”与“精英”冲突的思想根源[J].同舟共济,2011,(6).
[4][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比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47.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9-30.
[6]何包钢.协商民主:理论、方法和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8.
[责任编辑:张莲英]
·政治文明与法律发展·
Deliberative Democrac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ecessary Route for State Governance
JIANG Zhuo
(School of Govern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western democracy encountered crisis:weakness happened in public participation,democratic state got faced with crisi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Under this background,deliberative democracy rises gradually.It does not arise on the basis of long-term practice,but of Criticism of Election democracy.Criticism comes that China is an authoritarian nation,one-party system state rather than democracy.To the opposite,in fact,the Party-leading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system is the basic political system to promote Chines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cause'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t owns political legitimacy,logic justification and system superiority.This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s suitable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It is different either from the western multi-party system or from the one-party system in some socialist countrie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ecessary route for State Governance.To realize people as masters depends on institution,procedure and technique,and this needs to develop deliberative democracy.To change practice into institution,deliberative democrac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ecessary route for State Governance.
Key words:Chinese characteristics;deliberative democracy;state governance;public participation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6)02-0026-06
收稿日期:2015-10-22
作者简介:江卓(1985—),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