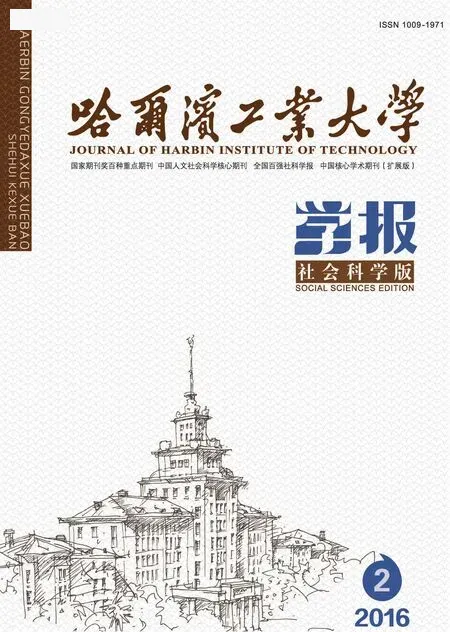“环境悬崖”与“麦金太尔之问”
——兼论儒家“分—和”理论的现代意义
宋君修(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阳550025)
“环境悬崖”与“麦金太尔之问”
——兼论儒家“分—和”理论的现代意义
宋君修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阳550025)
摘 要:美国“财政悬崖”的现象点燃了“悬崖”的概念词语范式。“悬崖”以学术时尚的方式成为一种“形式观念”。虽然在“环境悬崖”中,“悬崖”仅仅是一种形式,但是其本质则是一种谈判行动机制。但是“环境悬崖”毕竟涉及不同的伦理主体,因此必须进行“麦金太尔之问”,以批判地拷问在问题解决中的公正平衡。此外,“麦金太尔之问”表明,这一机制内在地要求一种古老的儒家道德哲学智慧,即在《荀子·王制》中具体阐释的“义”以“分—和”的智慧。这要求在“环境悬崖”中,在合于时代条件的“义”之框架下,达到有效的“分—和”,以差等而统筹的方式有所实际地解决公共而共同的环境危机问题。因此必须进行的“麦金太尔之问”建设性地要求明确,在环境危机问题的实际解决中,这些伦理主体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义”之框架下,以什么样的差等而统筹的“分—和”方式与“环境悬崖”相关,并明确各自的责任和行动,从而在“环境悬崖”中维护尽可能的公正伦理平衡,聚合出尽可能广泛的“现代人类”的伦理力量。
关键词:财政悬崖;环境悬崖;麦金太尔之问;分—和理论
引 言
历史的发展与比较以及学者们的反思和大众的直接感受表明,现代文明是一种所谓“祛魅”的文明。这典型地体现在现代人的意义流失或丧失的体验上。所谓的后现代文明,从其目前的表现来说,也只不过是对这种意义流失或丧失的非建设性的反动或反应/映。
从现代文明发生以来,以欧洲人为主导的现代人发现了并试图走一条不同于传统的神(以宗教为典型体现)文明的欲望(以资本为典型体现)文明的道路。欲望文明的特点是为了欲望而欲望,尽管其曾经成功地高举“为了人类的发展和进步”的旗帜,并且这是在全球范围内的,但是特别是近几年在这种文明的主要引领地区即欧美的种种现象表明,并且那里的学者们的反思更表明,这种进步只不过是一种神化,就像广为人知和越来越被认同的科学是一种神化一样——实际上,这是不够的,因为在本文看来,这种进步的神化只不过是科学之神化的神化。
实际上,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在这种欲望文明的神化迷梦破灭以来,已经事实上体验并反思到,这两种文明实际上是两种意义体系,并且在旧有的意义体系越来越消淡于历史背景之中的同时,新兴的意义体系到目前为止总是摇摇晃晃于一种普遍纠结的现状。
文化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曾经把这种起始于欧洲人的现代文明的致命性特征归结解释为基于死亡的生存竞争[1]。表现在文明现象上,这即是如何有效地终结生命的军备竞赛和战争。更加有效地终结生命的现代文明在两次世界大战那里拉开了地狱史诗般的序幕。从此以后,军事科技牢牢地控制着现代文明的欲望步伐。与此相伴的是科学技术、社会生产与活动等的“链条”化和“线条”化。如果说以前人们还更多地把审美目光投向自然本身,那么现在这种目光更多地投向了这种“链条”和“线条”。但是人们似乎忘却了,对这种“链条”和“线条”的审美是以对自然本身的审美为前提和条件或基础的。当这二者之间失去了应有的平衡之后,聚向于我们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生存质量的“悬崖”审美也就被迫发生、产生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与生态的问题以一系列的个案“悬崖”终于向我们人类提出了诉讼并得到了立案,并由此而形成了一个普遍性的“悬崖”意识,即危机意识。但是,“环境悬崖”这个词语却另有其有意思的缘起。这就是近年来的美国“财政悬崖”这一政治—经济的问题与现象背景。此外,再加上曾经热议过的“道德困境”,我们应该有理由认为,事实上从现代文明发展的巅峰开始,我们的现代世界就已经处在了各种各样的和程度不等的“悬崖”上,一直到美国“财政悬崖”这个有意思的现象点燃了“悬崖”的概念词语范式。
一、“悬崖”的理论背景
“悬崖”这个词语的基本含义通常是指一种众所周知的地貌,正像在“悬崖峭壁”这个成语中所描述的那样,即一块陆地远远地高出于另一块陆地之上,并且形成极为陡峭的夹角形状关系。按照美国“财政悬崖”的时事新闻报道,我们知道在“财政悬崖”这个词语中的“悬崖”与“悬崖峭壁”中的这个众所周知的作为一种地貌的“悬崖”没有“质料”(亚里士多德)上的关系,而只有“形式”(亚里士多德)上的关系,即只有“陡峭的夹角形状关系”这一形式上的关系。
根据新闻报道,“财政悬崖”这个词语只是用来描述美国政府财政状况的曲线图中的突变部分的“悬崖”样的曲线形状。但是,不论是“质料”(亚里士多德)的还是“形式”(亚里士多德)的“悬崖”,在我们的认知上都会产生一种相应的体验,例如恐惧感,并且这是人性的必然的,因为按照休谟的观念与印象的双重关系的知觉理论[2],只要我们具有了某种事物和现象的印象之后,相关该印象的观念一经刺激起来,就会自然地刺激起与该印象紧密相关的情感体验。
此外,从心理学上著名的“视觉悬崖”实验[3]来看,我们应该有足够理由推测,我们人类面临“悬崖”情境的时候,会程度不等地产生相应的情感体验。该实验的基本构思是:以各种方格图案创设视觉的“悬崖”错觉情境,并在图案上方搭一个架子,铺上玻璃板,然后放置不同年龄的幼儿于玻璃板上,具体位置是在相对于视觉错觉情境下形成“悬崖”的玻璃板那一部分的对面部分,并让孩子的妈妈在玻璃板的“悬崖”那边召唤幼儿,看幼儿会如何反应和选择。这种实验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恐高”情境:人站在高处安全处,理智上知道身处安全处,但是对视觉中看到的高处情境却身不由己地产生程度不等的恐惧害怕的感觉。尽管我们不能描述说该实验中的幼儿产生了某种恐惧害怕的感觉体验,但是实验中大多数幼儿的行为选择,即避开深度的“视觉悬崖”区域而爬向正在召唤他们的妈妈的行为选择,却不能不让我们推测,“视觉悬崖”客观上还是对幼儿发生了一定的刺激性影响,从而改变了幼儿通常在妈妈的召唤下会直接爬向妈妈的行为倾向。那么,当据此而来分析成年人的时候,我们岂不是有更多的支持和理由来解释说,成年人在“悬崖”情境中不可能不产生相应的害怕等情感体验,因为休谟的知觉理论很自然地说明了成年人面临“悬崖”情境时,会使用其知识和印象的储备来解释所处的情景。
因此,“悬崖”的知觉经验内容及其形式对我们人类具有重要的刺激作用,而作为知觉经验形式的“悬崖”观念和语言不可能不具有极为容易传播的刺激性警戒意义,并且这种意义的现实体现更在于以不自觉的或者无意识的方式促使人们对相关的事情和问题达成求同存异的公共意向或共同意向。这就是“财政悬崖”这个热词之所以如此受人们追捧的原理性理由。或者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来解释,由“悬崖”的“质料”而来的“悬崖”的“形式”,或者用休谟的术语来解释,由“悬崖”的“印象”而来的“悬崖”的“观念”,当这二者相结合的时候,被我们所把握的“悬崖”的“形式观念”,也就水到渠成了。
这样,“悬崖”这一“形式观念”一旦作为一个一般概念来使用,其本身也就立即具有了自身的双重含义:意指一种危险形势,并且意向着相应的应对举措。这正是“财政悬崖”所唤起的“……悬崖”这种语言表述方式的语言学内涵,尽管类似的语言表述古已有之,但是以往从未像现在这样形成一种语言表述上的“形式观念”及其概念趋向。①对这种语言表述的“形式观念”的学术关注,已经逐渐开始发生,例如《从语言学角度解读“X+悬崖”复合词》(于璐、刘锦明,载《长春大学学报》2014年第11期),以及《框架视域下隐喻的话语功能建构与翻译策略——基于美国财政悬崖报道的批评性分析》(韦忠生,载《当代外语研究》2014年第4期)。很显然,“悬崖”这一“形式观念”很有效并且很形象地引起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整体理解,并且在这种整体理解之下同样地被暗示相应于这种整体理解的问题解。
二、“环境悬崖”的哲学本质
尽管我们可以对“悬崖”这一“形式观念”进行上述的分析,但是这还仅仅是“悬崖”这一“形式观念”在语言表述上的一般理解,因为以美国的“财政悬崖”为典型例子,我们有理由认为,“悬崖”的“形式观念”仅仅构成为一种形式,但是却与前述的双重含义无关。这正是《美财政悬崖:真危机还是伪问题》一文的基本结论所给我们的启示,因为该文的基本结论是:“‘财政悬崖’反映了代表自由派的奥巴马行政当局和代表保守派的国会共和党人,在宏观治理上存在的哲学分歧,也是两派立场及其支持者势均力敌的结果。但‘悬崖’本身其实是人为设置的谈判机制。”[4]
不论在其他问题领域中,美国“财政悬崖”这一表述有何特定含义,至少根据《美财政悬崖:真危机还是伪问题》这篇文章所给出的论据及其论证,在美国“财政悬崖”这一表述中所本质上指向的现实含义必然要包括“设置谈判机制”这个核心内涵,因为这是由美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美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仍然是20世纪冷战时代的,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对美国公民的社会福利承诺越来越多,导致美国政府财政负担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美国人口寿命越来越长,这就使得基于半个多世纪前的人口寿命而设计的福利体系因为未能与时俱进而遭遇到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此外,冷战结束后,西方发达经济体在资本本性的推动下把整个世界都席卷进经济全球化,这使得西方发达经济体与此前冷战时代的状况相比,显得单薄了很多,这种状况对美国国内中产阶级产生了普遍的焦虑压力,并且与此一道的还有贫富差距的扩大趋势,这种情况使得美国政府在经济增长、公民福利、财政额度、财政渠道即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等问题之间,陷入一种正好与美国政府大选好戏连台的游戏状况,因为美国两党的保守派倾向于要保护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干预社会,而自由派则倾向于要反对财富过于集中而稳定中产阶级并保持社会向上的流动性。从美国的实际时事来看,这一游戏状况很好地满足了美国公民的审美需要,让美国政府借此很好地完成了大选,并且在游戏的“好莱坞最后时刻”,让“谈判机制”准确地激发并解决了旨在游戏情境的“两难选择”,“拯救”了美国而免于“财政”的“悬崖”,从而达到了对于相关各方都利好的局面。
因此,在“悬崖”这一“形式观念”的一般理解之外,我们需要强调另外的一个理解,即在危险形势和相应的应对举措意向的双重含义之外,并于此相关,强调作为“游戏”规则的“谈判机制”的“设置”倾向这一含义。实际上,在这一含义之下,“悬崖”这个词语仅仅成了一种符号象征,其本质则指向两害相权和两利相权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在利害相权的相关方之间,发生一种“推人出圈”的游戏,但是问题在于游戏双方都不想出圈,而都想继续游戏,因此双方默契地都需要一个不推出圈而继续游戏下去的游戏规则的商谈,但是具体的商谈细节则是看情况而定的。这样,“悬崖”这个词语也就仅仅表达了一种游戏商谈的意向敦促,但是这种意向敦促又不是完全虚构的,同样也不是完全真实的。换言之,“悬崖”这种意向敦促仅仅表达了游戏者彼此之间的相互制约以及共同的游戏目标和意愿,仅此而已。
很显然,在前述的分析讨论下,对“环境悬崖”我们可以有如下的理解:一是环境的危险形势,即“环境危机”;二是与环境的危险形势相应的一般应对举措及其意向;三是环境危险形势中的相关人类群体相互之间的旨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地解决环境问题而共同生存下去的具体谈判和敦促。如果借鉴美国“财政悬崖”的“游戏规则”,那么这种具体谈判和敦促更可以表达为:设置一个促发“环境悬崖”的临界点,当该临界点被促发后,按照设置好的应对措施和意向自动地执行。但是,对此而言,前提条件是相关于“环境悬崖”的群体事先达成各自能够接受和执行的举措。最后,这个前提条件的整体性前提则是:相关于“环境悬崖”的群体之间具有无可推卸和规避的严肃的利益关系,构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利益整体,如此才能保证“环境悬崖”的理念机制或概念机制能够形成。
这样看来,“环境悬崖”以时尚的概念语词方式,更为形象而富有激发意义地表达了以前的“环境危机”所要描述的内容,此外更加呼吁促成实际问题解决的谈判。或者说,与“环境危机”相比,“环境悬崖”以更加富有整体性问题指向的诗意意象的方式,更为有效而形象地表达了已经达到了临界点的20世纪以来的环境、资源、生态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所描述的我们“现代人类”的生存发展的时代问题。
然而,正如本文开篇所讨论的那样,我们“现代人类”的生存发展的时代问题,尽管以“环境悬崖”的时尚方式呈现,但是这个问题却是以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生存发展的深层的理念结构为基础的。至少艾斯勒所分析的欧洲人的生存发展的理念,即基于死亡的生存发展理念,让我们有理由认为,欧洲人所开启的“现代文明”正如欧洲神话中所说的那样,这实际上是开启了那个“潘多拉魔盒”,而其结果正是“现代人类”的欲望被赋予了更为有效的“身体”即“现代资本”。这样,“现代人类”的“现代”“欲望”凭借这种无所不在的、无坚不摧的、无柔不化的“现代资本”的“身体”,迅速让“现代人类”以全球化的方式陷入了一种有意无意的人为主导的“激进游戏”的状况。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潘多拉魔盒”是“现代西方人”打开的,他们享有了前半期的收获,却在后半期消极地应付因此而来的后果影响,试图在本性上整体相关的环境中尽可能割裂出其本国领土所在的环境而予以尽可能最大的保护、恢复和维持。但是对这种整体相关的环境中的他国、尤其是发展落后的国度的环境问题,他们则以转嫁代价的方式,消极作秀地来对待。这实际上是一种生存发展上的先发优势及其思维方式。但是问题在于,地球上的环境是本性上整体相关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把其领土上的环境完全割裂孤立出来。在“现代人类”还没有找到其他可供生存发展的星球环境之前,除非哪个势力集团的领导人物发疯了,否则目前生存发展方式下的本性上整体相关的环境问题,就是其无法忽视的。这是因为,在地球的资源和环境彻底消耗殆尽之前,以及在“现代人类”找到新的其他星球环境并能够实现比较安全的太空运输之前,“现代人类”将面对的地球岁月仍然是足够长的,从而除了发疯的人之外的任何一个“现代人类”都不可能不为其血脉种族的延续而关注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因此,对我们地球人来说,环境问题本性上是一个整体相关的问题。换言之,环境是本性上超越国界和民族的,是不可能根本上被“私有”的。但是,地球人的自私又的确是其本性,也就是说无法排除某些“现代人类”在等待因为资源和环境耗尽时,抱着能够享受最后自家剩下的良好环境的想法,消极地对待目前的整体相关的环境问题。此外,地球人目前又的确是国家和民族林立,而不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换言之,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和环境问题的整体相关本性相应的利益紧密相关的地球人的或者“现代人类”的整体。那么,应该如何协调这种问题境遇以最终达成“环境悬崖”呢?
三、“环境悬崖”:“麦金太尔之问”的拷问
很显然,这种问题境遇的“环境悬崖”,事实上正符合了人类的实际生存发展模式,即任何生存发展都是非常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这也就是说,不论是自由意志文化下的人们,还是血缘情感文化下的人们,他们都是以具体的个人按照各自的原则组成一个个非常具体的社会单位,以作为人类的实际生存发展模块。但是不论所组成的是什么样的单位或模块,它们都终极地落实到单个的人类个体身上。这也就是“环境悬崖”的这种问题境遇何以如此的解释,同时这也是这种问题境遇的正解之所在,即由一个终极个人点和一个单位或模块体之间构成的一个具有一定弹性的“谁”之问题所向。
对这种问题境遇的“环境悬崖”,一个兼具批判性和建设性的伦理思维方式,就在等待着“现代人类”去达成共识了。这就是麦金太尔在其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以独特的题名而提出的那种伦理思维方式[5]:作为伦理主体的“谁”的问题是任何伦理问题中都不应该忽视的,这也就是说,面对任何一个伦理问题,都应该如此追问:那是与“谁”即哪个伦理主体相关的?①需要澄清的是,在此只是援引麦金太尔的这种追问方式,而非其理论思想。换言之,不论麦金太尔是社群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这都与本文的探讨无关,而有关的仅仅是这种极具理论冲击力和张力的“追问方式”。在本文看来,这种追问方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其突破了某种理论盲区,而这一理论盲区对研究和解决各种广义伦理问题和现象,例如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具有很好的建设性导向矫正作用。“麦金太尔之问”本身实际上成为广义伦理问题和现象研究的试金石,可以让研究者们、各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们、普通的人们尽可能规避误区,避免谬误。我们可以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之为“麦金太尔之问”,以突出这种伦理思维方式在“呐喊”(鲁迅)中所警惕人们不应该忽略的重要问题之所向。
实际上,“麦金太尔之问”表明,伦理问题不可能不涉及利害相关的伦理主体。在“麦金太尔之问”下,任何类似正义与合理性等的问题,都是前伦理的,即都是抽象的。当这样说的时候,所要强调的是,一种抽象的伦理观念只能落实到相应的利害相关的伦理主体上,那才能够真正地实现。因此,在“麦金太尔之问”的追问下,面对“环境悬崖”,我们应该要追问的是:“谁”之“环境”?何种“悬崖”?这一追问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伦理问题只能够现实由一定伦理主体去具体实施解决方案。如果在伦理主体不明确的情况下,伦理问题就只能够是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仅仅处在人们的头脑意识与观念之中,不论该问题是多么现实紧迫的。
很显然,哪怕是“麦金太尔之问”也无疑是一种极为“现代”的西方式理论理解。尽管“麦金太尔之问”可以很好地解释人类社会的伦理分工与合作,但是事实上,正如黑格尔向我们所描述的那样,这种伦理分工与合作的现实基础是市民社会,因为市民社会是天然的紧密的利害相关整体,并且市民社会是非血缘的底层理念结构的[6]。换言之,“麦金太尔之问”所要追问的那个“谁”之问题所要指向的并非是血缘层面的人,而是像黑格尔所描述的那样的遵循自由意志的法的原则而形成的人。这样看来,“麦金太尔之问”本质上要指向的不是“谁”,而是“谁”之自由意志。这也就是说,在“麦金太尔之问”看来,人类社会的伦理问题的关键点在于,相关的伦理理念和问题所出发的自由意志具体之所瞩何在?因为,毕竟任何一种正义、合理性等伦理理念,都是真正地对某种具体所瞩的自由意志而言是真实无妄的、有效的。
但是,尽管自由意志也是一种人类的普遍价值与原则,然而另一种人类的普遍价值与原则也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非常古老的血缘这一普遍的价值与原则。如果自由意志是抽象先验的,那么血缘则是具体先验的,并且比前者更加古老和自然。血缘所造就的民族和文化自然地以家族或者家庭为社会的基本有机单位,而自由意志所造就的民族和文化则自然地以生物学上的人类的个体为社会的基本有机单位。如果后者主要以理性为其信息运算规则,那么前者主要以情感为其信息运算规则。这种血缘情感的信息运算规则典型地体现在兼容并蓄的儒家文化及其所支撑的生活方式上。对这种血缘情感文化来说,“麦金太尔之问”确确实实地要直接指向一个具体的“谁”,而不是通过一个抽象的自由意志再指向一个具体的“谁”。这种直接指向的“谁”表现为一个个具体的血缘簇群或者血缘族群,并且它们表征为具有具体的社会历史内涵的姓氏。在这种文化之下,如果一个问题只得到了理性上的解决,而没有得到情感上的解决,那么一种口服心不服的消极应对行为和活动将是难以避免的,反之,如果一个问题首先得到了情感上的解决,哪怕是在理性上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其结果往往很可能是万众一心地积极行动和活动起来,齐心协力地去解决问题。
虽然看起来,这是两种对立的普遍价值和原则,对立的信息运算方式,但是就其本质来看,它们是殊途同归的。其实,它们都各以自己的方式,非常在乎“麦金太尔之问”的问题之所问和所以问。对血缘情感文化来说,以情感为信息计算的优先规则,可以在对问题只具备有限理性处理之时,人们就非常高效地进入行为和活动的准备、甚至执行——尽管这时难免有一种盲目状况的出现——此外更能够积极主动地介入对问题的理性处理。这是因为血缘情感文化下的伦理主体,在这一过程中,感知到了其主体地位的价值、意义和尊重。相比较起来,对自由意志文化来说,以理性为信息计算的优先规则,可以在对问题达到了条件范围内最大的理性处理之后,人们才非常高效地进入行为和活动的准备或者执行,但是这却减少了盲目状况出现的几率,并且人们会更积极主动地严格按照理性处理的结果来行为和活动。这是因为一开始个体的人们就以自由意志的伦理主体的正面方式进入对问题的理性处理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自始至终有着完全的自由意志的自觉和意识。如果说自由意志文化是一种偏主动型文化,那么血缘情感文化就是一种偏被动型文化,相应地,二者的伦理主体一种是偏主动型的伦理主体,另一种是偏被动型的伦理主体。
四、“环境悬崖”与儒家“分—和”理论
这样,“麦金太尔之问”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就是:不同类型的伦理文化和伦理主体,以及同一伦理文化下的不同伦理主体。尽管这些伦理主体各有差异,但是在同一个“环境悬崖”的问题下,它们又不得不以各自的方式存异求同地面向问题,并且在时间、范围和程度等具体问题上更是差异纷繁。实际上,这种问题方式的本质在一千多年前著名的儒家“分—和”理论那里早已经被阐述得极为清晰明确,并且被连续不断地付诸实践了一千多年了,虽然这个问题在现在被西方人以非综合的分科分析的方式更有效地表达为分工合作的理论。儒家的这种“分—和”理论的经典阐释如下:“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
根据荀子的这一阐释,人类正是因为以这种根据“义”而来的“分”与“和”为原理才达到了“群”的“胜物”状况的。在这种以“义”而“分—和”的原理下,人类的这种“群”显然不可能是动物般的群落那么自然而简单,而是霍布斯的“利维坦”那样的,构成一个远远高于动物的自然群落的伦理整体,具有构成整体的所有成员公共的以及共同的意识、意志、精神,从而成为一个伦理主体。这种“群”的伦理整体与伦理主体,一般被称作社会、民族、国家。它可以根据以“义”而“分—和”的原理,在自身内部又适当地分为更小的“群”。正是在“义”以“分—和”的原理下,通过“群”的方式,人类的个体才现实地组成大大小小不同的伦理簇群和族群,并且以这种伦理整体为生存发展的方式,即相应的伦理整体的生存发展同时内含着或者蕴含着其中的人类个体的生存发展,并且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尽管个体和伦理整体具有共同的生存发展方向,但是这种生存发展方向在个体和伦理整体上的具体展现毕竟是不同的。因此,如何恰当而有效地“义”以“分”,这就构成这个棘手问题的解决关键,因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和”以生存发展。这一“分—和”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何以古代中国可以历经两千多年而始终不曾改变其基本的文明模式,并且在“现代”仍然坚韧地在这种文明模式的遗传印记上凭借全新的资源和条件继续发展。
前述解释的那种问题境遇的“环境悬崖”,事实上的确存在着在“麦金太尔之问”下的诸多不公正的现象和问题,然而“环境悬崖”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性问题。纵观人类的发展史,那种企图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做法,很少有行得通的,但是从整体性问题出发,参照不同的伦理簇群和族群与这种整体性问题的关系程度,以有所差异和差距的现实方式,反而更能够共同趋向整体性问题的实际的而非观念理想的解决。这是我们中国古老的儒家“分—和”理论的永恒作用,因为我们人类之生命本性上是以这一理论为深层机制而远远高于动物地生存发展的。“麦金太尔之问”这种从西方新兴的美德伦理发出的追问和“呐喊”(鲁迅),只不过是管中窥豹的方式,对“环境悬崖”这样的问题作出了一点回响,以与千余年前发出的“分—和”声响呼应。
“麦金太尔之问”的意义不在于“环境悬崖”能够达成什么理想结果,而在于实际地能达成什么。“麦金太尔之问”只是以拷问的方式提请人们思考不可能理想地处理的环境问题的现实纷争的状况和条件,提请人们注意一种伦理努力必须根由于一定的伦理主体们的伦理“分—和”的“和声合作”。但是,尽管如此,“麦金太尔之问”仍然不失其对现实纷争的状况和条件的批判性,而不会默认而容忍不公正的现象和问题。这也就是说,前述的问题境遇实际上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原罪”,而在只能够分析却无法解决这种“原罪”的条件下,我们“现代人类”有义务以“麦金太尔之问”去分析直面这种“原罪”,并且背负着这种“原罪”而按照古老的“分—和”理论的本质算法来追求实际而确实地达到一定的“环境悬崖”状况,促成指向有效行动的环境问题的整体性谈判机制的形成。这既让各伦理主体达成环境问题之严重性的公共而共同的肯认,又让它们实际地进入“环境悬崖”——要么,它们主动地如此;要么,它们在来自不同伦理主体的公众压力下,被动地如此。
结 语
这是可能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环境悬崖”的哲学解释。不同于“环境危机”的问题警告,“环境悬崖”在问题警告之余,更实际地成为一种应对危机的态度与行动的机制。这种“环境悬崖”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广义伦理的机制,因此必须以“麦金太尔之问”来作为达到有效的“分—和”的“义”之框架的保证。很显然,“麦金太尔之问”的画外音是:要么能够彻底摧毁对方的伦理主体,否则的话,就要公共而共同地生存发展下去,这就要在相应于时代条件的“义”之框架下进行有效的“分—和”,以促成“环境悬崖”机制的达成。根本地来说,上述“环境悬崖”的解释只能指向这样一种本质:生命,特别是人之生命,或者人—类(这种类毋宁恰恰是各种各样的伦理之类)之生命,只能是整体关联的,可以在内部无休止地争斗,但是不可以置威胁整个生命的危机问题于不顾,因而必须进行“麦金太尔之问”。
参考文献:
[1][美]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M].程志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2][英]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3-18.
[3]熊哲宏.你不知晓的20世纪最杰出的心理学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张晶.美财政悬崖:真危机还是伪问题[J].南风窗,2013,(2):71-73.
[5][美]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M].万俊人,等,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责任编辑:王 春]
·经济理论与经济建设·
On“Environment Cliff”and“the Question of MacIntyre”
—Concurrently on the Modern Meaning of the Confucian“Divde⁃Harmonious”Theory
SONG Jun-xiu
(School of Humanities,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The phenomenon of American“Fiscal Cliff”has the kindling effect to the conceptual phraseology paradigm of“cliff”.“Cliff”forms a kind of“form-idea”in the way of scholastic fashion. Though in the phenomenon of“Environment Cliff”,“cliff”is just a form,its essence is a kind of negotiation-action mechanism. However,in the final analysis,“Environment Cliff”involves different ethical subjects,so“the Question of MacIntyre”has to be carried out so as to make a critical torture-questioning to the balance of justness in the solving of such question. Besides,“the Question of MacIntyre”shows that such mechanism asks in inner a kind of ancient wisdom of Confucian moral philosophy,which is the wisdom of“Divide-Harmonious”by“YI”explained specifically in the literary piece of“Wang Zhi”in<XUN ZI>. What is asked here is that,in“Environment Cliff”and under the framework of“YI”that is propitious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time,an effective “Divide-Harmonious”is to be achieved so as to solve really some public or common environmental crisis problems by the way of plan as a whole with difference of distinction. So,“the Question of MacIntyre”carried out necessarily asks constructively that such questions as below should be clear:in solving really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problems,under what kind of framework of“YI”should these ethical subjects actually be,by what kind of method of plan as a whole with difference of distinction should these ethical subjects be related to“Environment Cliff”and make clear their own responsibilities and actions so as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just ethic as far as possible and get together the ethical power of“modern humans”as wide as possible.
Key words:“Fiscal Cliff”;“Environment Cliff”;“the Question of MacIntyre”;the theory of“Divide-Harmonious”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6)02-0120-07
收稿日期:2015-10-10
作者简介:宋君修(1976—),男,山东莱阳人,讲师,伦理学博士生,从事中西道德哲学与中国语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