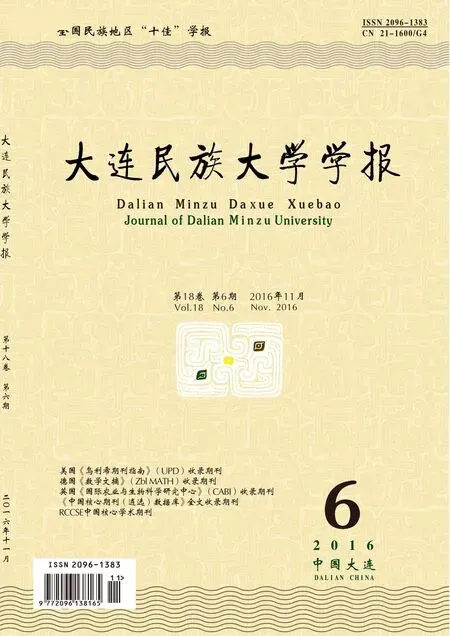兄弟分离与马龙成骢:北方游牧族群聚分融合的神话表述
南文渊
(大连民族大学 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05)
兄弟分离与马龙成骢:北方游牧族群聚分融合的神话表述
南文渊
(大连民族大学 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05)
兄弟分离与马龙成骢的故事是北方游牧族群聚分融合的一种神话建构。无论是历史史实的描述还是神话的建构,表达的观念是共同的,即游牧族群的分离与融合都是游牧族群生存的必然法则,是一个族群为适应生态环境变迁而进行的一种族群重建和文化创新的壮举。
游牧民族; 迁徙;神话建构
北方草原区域一般是指青藏高原西北部、天山南北、蒙古高原及黄土高原西北部。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区域创建了不同时期的游牧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公元13世纪前后,北方草原盆地先后出现了猃狁、赤狄、白狄、长狄,胡、匈奴、乌孙、月氏、昆夷、突厥、室韦、蒙古诸等西域诸族;在青藏高原东部、黄土高原西部出现了戎、氐、羌、党项等等;东北部森林草原地带出现了肃慎、貊、貉、山戎、东胡、鲜卑、女真、满等民族,这些族体大多是森林狩猎族群或者草原游牧族群。族群分离与融合的神话传说往往发生在这些族群系统之间。
一般人的印象中从蒙古高原到青藏高原是一片封闭的内陆沙漠荒原,限制了文明的繁衍;但是实际上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蒙古高原西部到青藏高原的北部的河西走廊、昆仑盆地、祁连山-青海湖盆地到南方的羌塘草原、阿里盆地一直是游牧族群来回迁徙游牧的草原走廊,也是北方各个族群文化交流的通道。游牧族群是为自由游牧而生存。不同游牧族群神话与历史记载中,都有一个中心思想:祖先奉天命降生后,原先居住的地域过于狭小,限制了游牧的发展。于是通过克服重重困难,迁移到更加广阔的草原上再行扩展。从游牧人的草地生态环境观念看,草原、天气、畜群的相互和谐是游牧民族生存发展的保障,而实现这三者之间和谐的最好方法就是迁徙、游动、寻找新草地。游牧人离不开草原但又不能不流动,于是只有周期性地扩展草原,每隔一段时间旧的草地不够用,便占领新的草地。所以草原游牧人始终处于游动之中,游动便是他们的生活之道,游动才有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如果停止下来,定居不动了,游牧人的生命也完结了。
有关游牧民族迁徙的文本,一种是历史事件的描述,另外一种是神话的构想。前者被认为是真实的,后者是虚构的。但是无论是历史史实描述还是神话建构,表达的观念是共同的,即游牧族群的分离与融合都是游牧族群生存的必然法则,是一个族群为适应生态环境变迁而进行的一种族群重建和文化创新的壮举。
一、“兄弟分马”:人口增加与资源短缺而引起族群分离的表述
草原游牧民族的神话大多是与草原资源的分配相关。人口增加引起草原资源短缺的矛盾表现在北方游牧族群迁徙的真实历史事件之中。
1.三马分离:羌塘-青海湖游牧族群因草原资源匮乏而分裂变异
英籍藏学家托马斯根据敦煌吐蕃文献编写《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一书,反映了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和族群生存方式变迁过程。高原的生存区域生态环境从森林退化为草原,再从草原退化为荒漠。较为温暖潮湿的地方被高原人开垦为农田,草原动物被驯化,饲养的动物也在变异。神圣的动物逐渐剥去神秘的外衣,成为被人驱逐、驯化、使用的家畜。其中提到生存在藏北羌塘草原和三江源地区的游牧族群的变迁。
羌塘草原和三江源地区的游牧族群在《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中称为“南木国”。它可能是包括以“纳木措”为中心的藏北羌塘草原和长江上游(在青海玉树西部),是高原草原游牧区域[1]。作为游牧族群的南木巴(Nam-pa)最初的游牧范围在羌塘草原,以牦牛为图腾。但是后来由于“没有足够的草吃,没有足够的水喝。”他们中一部分人到东北藏地区半农半牧的河谷。文献中提到南木巴族群的南夫人的宠爱的是杂交奶牛,即犏牛。表明这是一个以母黄牛与公牦牛的杂交的的后代即犏牛为图腾的部族,它的主人显然是河湟河谷地区半农半牧的族群——嘉西番。嘉西番这个名称是汉藏两种语言的结合,嘉,藏语意义为汉人,称嘉什干。西番,是汉语对藏人的称呼。嘉西番即汉化藏人,他们大多居住于黄河,湟水流域的农业区,一般操藏汉两种语言。《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中的“马匹的故事” 讲:马的祖先最初在天界,由于“没有足够的草吃,没有足够的水喝”,于是马匹三兄弟下界去寻找水草丰美的草原。三兄弟分别为长马、次马和三马。其中长马最强壮,也最富于冒险精神,它只身前往陌生的北方牦牛领地,要求牦牛重新分配草原资源:让马先吃草,让牦牛后吃草;马食草量大,牦牛没的吃。牦牛认为这是抢夺草原资源的来犯之敌,于是与长马发生角斗。结果长马被牦牛所杀害。长马被害,意味着神马已经失去了神圣地位。长马死去了,次马与三马商量今后如何生存。次马主张去其卓登松这个草原去,那里“有足够的草吃,有足够的水喝”。但是三马此时已经灰心丧气,它觉得还是留在人类居住的地方好,没有风险,还有吃喝。次马警告三马,如果到人类的地方,你将会“戴上嚼子,驮上鞍子”,失去自由,供人驱使。但三马认为只要生存,虽然受人奴役也心甘情愿。俩兄弟因意见不和,只好分道扬镳。次马仍坚持它的野生生存方式,留在了草原。三马只身来到了金王国,与人类交上了朋友,成为驯服的家马,并从此成了人的坐骑[2]。这个故事建构了神圣骏马的变异过程:神马变成野马,野马变成家马。神圣牦牛的变异过程是:神圣的牦牛变为野牦牛,野牦牛变为家牦牛,家牦牛与黄牛交配再变为犏牛,而犏牛的牛犊不能够再生育。于是便断子绝孙了。这个寓言般的历史故事明确告诉了自然环境的退化导致人类族群的变异,整个草原被瓜分、被开垦的趋势下,马族与牦牛族的争斗挣扎是徒劳无益的*无独有偶,这个寓言般的历史故事出现在唐代诗人杜甫的诗集中,他写道:青草萋萋尽枯死,天马趾足随牦牛;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
2.兄弟分马:吐谷浑的西迁
马是骑马民族的标志。一匹马,一杆枪,一壶酒,驰骋万里草原,纵横高山大河。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千年历史。他们喜爱自己的骏马,进而作为神马崇拜它,形成了崇拜骏马的民族群体。马的驯化和使用是北方游牧族群长距离迁徙的关键。骑马族群,它大致起源于铜器时代,发展于漫长的铁器时代。从东亚向西经中亚、西亚,南至青藏高原的广阔草原地带是骑马族群的活动区。骑马族群骁勇骠悍、进攻性强;但是天气的变化和草原资源的短缺常常引起骑马游牧族周期性的分裂迁徙。
“兄弟分马”是一种族群分离模式:原族群由于资源分配不均或者利益冲突发生分裂,部分成员远走他方另组族群,从而导致母体族群的分离和人口的流失。据说吐谷浑率部到青海是他的骏马按照天的旨意引部族而来的。《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慕容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户以隶之。”慕容是涉归的嫡次子。他们游牧于今辽西北和内蒙古东部广阔草原上。公元283年,涉归死后,部众拥立慕容为可汗。此后不久发生了马斗事件——吐谷浑和慕容两部的马在一处草场上嘶咬,慕容恼怒,指责其长兄部下与之争夺草原,引起马匹相互斗悪;吐谷浑则慷慨悲壮地回答说:“马的相互嘶咬争斗是其天性,为何要迁怒于人呢?既然你要我走,我便去一个万里之外的地方吧。”于是决定远离故乡。并对劝阻者表示,应以天的旨意决定去向:“请君试驱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随去。”马群被向东驱赶了十几次,又全都嘶鸣着掉头返回。(辽东是森林地带,辽西是草原,马作为草原动物,当然不肯向森林方向去的。)于是吐谷浑与1700户部众驱赶牛羊走上西迁之路。他们由老哈河至阴山,再经陇山至大草滩,最后到达青海湖盆地,而慕容思念长兄,作《阿干之歌》表示悔恨自己*《宋书》《魏书》《北史》等亦记此事,但文字并无多少出入。《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发表了阿尔丁夫的文章:《关于慕容鲜卑〈阿干之歌〉的真伪及其它》,披露了只知有其名、而不见其文的《阿干之歌》,其歌云:“阿干西,我心悲,阿干欲归马不归。为我谓马何太苦,我阿干为阿干西;阿干身苦寒,辞我士棘位白兰。我见落日不见阿干,蹉,蹉!人生能有几阿干。”。
草原时代的鲜卑拓跋氏是父系社会,辽东草原人口增加,而草原区域狭小,因此部落之间发生争夺草原资源的斗争。
3.兄弟分马:和硕特蒙古的西迁开辟了青藏高原游牧王国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后,给二弟哈撒儿分配额尔古纳河和海剌尔河附近的封地。大多数哈撒儿后裔均游牧于今天的内蒙古东北部和东北三省一带。哈撒儿家族传至七世阿克萨噶勒代,其长子阿鲁克特穆尔,于公元1425年登上蒙古大汗之位,即阿岱汗。他将哈撒儿家族的势力扩展到兴安岭以南的兀良哈三卫之地。公元1430年左右,阿鲁克特穆尔与兄弟乌鲁克特穆尔因为草原划分、属民归属问题发生纠纷,弟弟乌鲁克特穆尔一怒之下率福余卫乌济叶特人为主的部分属民离开呼伦贝尔草原向太阳落山的方向西迁,后成为卫拉特蒙古之组成部分——和硕特部,在天山南北游牧。这又是一例兄弟不和分离的事件,但它对草原文明创新带来了巨大影响。从16世纪初起,土默特、鄂尔多斯、喀尔喀蒙古部相继进入青海草原。1640年乌鲁克特穆尔之重孙固始汗率领和硕特部蒙古骑兵进入青藏高原,占领拉萨。和硕特蒙古联合西藏格鲁派上层,顺利地建立了青藏高原的和硕特汗廷。他的子孙占据藏北草原与青海湖草原长达300年,建立了青藏高原和硕特部蒙古的游牧王国,传播了藏传佛教文化。在1640-1720年近80年间,青藏高原上的蒙古至少有20万人。和硕特部蒙古适应高原环境,与吐蕃文明相互交流,保留了古老的“德都”蒙古文化,创造了高原游牧文明。
二、龙马成骢:高原西北游牧族群的融合神话
分离的族群在迁徙的旅程会寻找到新的归宿处,他们与当地土著族群相会,建立了新的族群关系,在长期的共同生存中融合成为新的族群。这样产生了族群融合的神话传说。
1.汗血白马与青海青龙结合的青海骢——构建吐谷浑的神话演绎
公元3世纪,吐谷浑率部到青海湖盆地,建立了土谷浑国,其中心可能就在青海湖。他们以青海骏为荣耀。
《隋书·吐谷浑传》中明确提到龙与“波斯草马”相匹配的一说:
“青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牡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因名其马曰龙驹。”
《新唐书·吐谷浑传》云:“有青海者,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须冰合,游牡马其上。明年生驹,号龙种。尝得波斯马,牧于海,生聪驹,日步千里,故世称青海骢。”
青海骢是毛色以青色和白色相间的马。一般在浅蓝或浅灰色中有白色圆斑点的马多见。黑色马与白色马交配后易产出此种色彩。实际上吐谷浑部以辽东鲜卑之马(蒙古马)与高原的波斯马交配,产生适应高原环境的新一代马;从中挑选色彩特异者——青海骢作为自己的族群标志,并将其神化为龙驹,以示族群的不平凡。得杂交的优势,日步千里,说明此种马的善走。民间也有相同的传说(杨应琚《西宁府新志》,38卷,第6页),这种传说从吐谷浑开始流传。
《乐府诗集》对吐谷浑马有这样的赞美: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相波。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
西方来的“波斯草马”与东北游牧民族的马在青海湖草原的结合,是说明青海湖游牧民族的来源的一条很重要的线索。汉代的汉武帝通西域,曾多次从乌孙(当时在今新疆伊犁境内)和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一带)引进良种马以改进马政,充实骑兵。乌孙马称为大宛马,产于土库曼斯坦。到隋唐时,又大量引进波斯马,唐太宗昭陵六骏之一的什伐赤,相传即是波斯骏马。汉、唐两代,都在河西与青海设养马苑,大量繁殖适于在高寒地带作战的军马;今天在西北地区的蒙古、哈萨克、藏族牧民中饲养有伊犁马、浩门马、祁连马和刚察马等。这种马性耐寒,轻捷善走。神话中的白色的汗血宝马在青海湖岛与青色的龙相结合而产生的青海骢。实际上吐谷浑部以来自波斯的汗血宝马与高原的蒙古马交配,产生适应高原环境的新一代马;日步千里,说明此种马是适应高原环境的良驹,这标志着游牧的北方族群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适应:已经成为青藏高原的游牧族群。其后代将青海骢作为自己的族群标志。青海骢象征着北方游牧民族与青海湖盆地的戎族群的结合。
2.马身而龙首:冉駹羌的图腾
在古代羌、戎神话中,青龙是青藏高原东部河谷戎族群的象征,白马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象征。它们的结合便是古代高原游牧族群构成。这个游牧族群在吐蕃之前是羌,吐蕃时期之后是卓巴。
今天的甘肃西部、青海东部地区是龙马族群的生存地。《山海经》上说:“凡岷山之首,自女儿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这是最早的龙马族群的主神神话传说记载。 “马身而龙首”者,可能就是冉驡族。秦汉时期的冉驡,以岷江上游为中心。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莋都国东北有冉駹国,或土著,或随畜迁徙。自冉駹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此三国亦有君长。駹:(mang)《尔雅·释畜》:深色毛而脸面有白色的马。而《汉书·匈奴传》解释为青色的马。不过《辞海》称冉駹夷在四川茂县,崇拜牦牛。(《辞海》,第1381页)如果冉駹是青色的马。那么应该崇拜的是马,而不是牦牛。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冉駹是山羊:如有人考证冉駹是羌语,“冉”古羌语为山羊的意思,冉駹就是山羊多之意。其族群是后来的嘉良夷,现在的嘉绒藏人。根据《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汉时期的冉駹羌分布在河谷,分散居住,各有部落;分为游牧部与畜牧农耕结合两种类型:“或土著,或随畜迁徙”;贵妇人,党母族;居河谷石碉房,依山居止,累石为室,游牧者拥有帐篷。
3.牛形而象齿的兹白牛:大夏族群图腾
《逸周书·王会解》中例举的是北方族群的图腾,依次是:“禺氏騊駼;大夏兹白牛,兹白牛野兽也,牛形而象齿。 ”*《逸周书·王会》:禺氏 騊駼。尹知章注:禺氏 ,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孔晁注:騊駼,马之属也。《尔雅·释畜》:騊駼,马;郭璞注引《山海经》:北海内有兽,状如马,名騊駼,色青。见《逸周书》第3册,孔晁注,中华书局,1985年。禺氏是指月氏,騊駼是青色的马;大夏茲白牛,牛形而象齿,表明是牛与大象的结合。《山海经·海内东经》提到:“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又说:“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吕氏春秋·古乐篇》:“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史记》谓葱岭西自古著名之国曰大夏,立国当在黄帝以前,周穆天子西行时,其国尚存。
有人认为大夏是指公元前15-前10世纪的轩辕之国。大夏坐落在古昆仑,为黄帝下宫。《山海经·西次三经》中“崇吾之山—轩辕之丘”间的山系,大部在今新疆延伸到今西亚一带。大夏茲白牛的图腾可能标志着南亚族群与西亚族群在中亚的融合。
4.昆仑熊神与红山龙神:黄帝族群的图腾形象演变
史称黄帝为有熊氏,《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教熊、罴、貔、貅、豹、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此六野兽都具有北方民族的图腾色彩。其中熊氏族居六氏族之首,故黄帝族群的图腾最初可能是熊。黄帝族“迁徙往来无常处”。作为游牧族群,他们从西北高原昆仑区向东方迁徙,其中一支到了华北北部及东北地区,在那里创造了红山文化。开始以“云”纪事名官,可能改以“云”作为族群神灵,而“云”是龙神的别称。红山玉龙以前人们称之为玉猪龙,但是也可以看作是玉熊龙。玉熊龙与神话中熊神与龙神的结合相吻合*苏秉琦提出:“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只有黄帝时期与之相符。”他认为红山文化的时代相当与五帝时代的前期。。
5.白狼与白鹿图腾是森林族群的结合
狼和鹿是古代北方各游牧族群中主要图腾形象。《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人名曰犬戎,是为白犬,肉食。犬戎者西周时期时居地在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古地区。《国语》云:“穆王将伐犬戎,祭公父谏曰:‘不可’,王不听,逐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说明犬戎是崇拜白狼、白鹿的森林-草原游牧狩猎民族。“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可能是指擒获以白狼白鹿为图腾的族群首领而归。在历史时期的蒙古、有狼族和鹿族结合而形成蒙古族的神话;古突厥人以狼作为他们的祖先,塞人以鹿作为自己的图腾象征。
6.人身马蹄的图腾是丁零族的象征
《山海经·海内经》:“北海之内,……有钉灵之国。其民从膝以下有毛,马蹄,善走。”又《三国志》注引《魏略》云:“乌孙长老言:北丁令有马胫国,其人声似雁鹜,从膝以上身头,人也,膝以下生毛,马胫马蹄……”人身马蹄表示草原族群丁零族的祖先神或者图腾形象。同时,《山海经·西次二经》提到,西北地区自铃山至于菜山,凡十七山中“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马身,其七神皆人面而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为飞兽之神。”表明西北昆仑区域族群大多崇拜马和牛图腾的族群的融合。
7.青牛和白马是构成契丹族的图腾
契丹部传说最初只有青牛和白马两部,即以青牛和白马为图腾的两个原始氏族。后来由这两个原始氏族又繁衍了许多亚氏族。青牛部和白马部便成为一个共同体族群,表明青牛和白马也由氏族图腾演变为族群图腾。
三、神话表达游牧民族分离与迁徙的文化意义
游牧族群在北方草原中部和西部迁移。其中有南来北往的,也有东西互迁的。这种迁徙固然与气候的变化密不可分,但是或许有另外一种原因,那是精神上的一种需求。这是一种定向的自觉自愿的迁徙,其目的是为了寻找生存的意义,寻找生命的归宿。
1.族群的新生:迁徙中实现族群的融合与重组
游牧族群的迁徙,不仅是气候、环境这些外在的原因,其实对族群自身的更新、发展也是必要的,游牧族群是在迁徙的进程中形成,在流动的进程中发展壮大的。当一个族群静止地死守一份区域,不交流、不流动,那么她很快会退化衰落。而长距离的大规模的迁徙,会促使族群成员在迁徙流动中焕发生机,寻找生命的活力,人生的意义,而且迁徙会使族群得到更新的机会:迁徙到新的区域,与新的族群发生结合,通过双方成员的广泛接触,建立族群成员之间的婚姻联系,最终导致族群文化的变革更新,或者新的族群诞生;而新族群往往是朝气蓬勃、富有活力的。一江两河流域的外来的猕猴为象征的族群与岩魔女为象征的当地族群的结合,导致吐蕃族群的诞生;青海湖的羌人与东北草原鲜卑族的结合导致青海湖草原吐谷浑的诞生;山南一个部族迁徙到三江源草原,与当地藏族结合,产生了果洛藏族。河湟地区羌人、汉人的相互迁徙融合,导致羌汉融合,产生河湟藏族。唃厮啰政权灭亡后,其部众与汉人、党项人杂居于河湟。他们长期共同生活,相互交往、通婚的现象均较为普遍,呈现出民族更新发展的特征。族群流动交往强化了民族认同。不同族群正是在区域迁徙、社会互动、相互比较中产生更强烈的族群认同感;而在完全统一、静止不动的社会无所谓民族认同。
2.寻根问祖、追寻精神圣地
距今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西部高山盆地的族群逐步从西部高山走向东部河谷,然后从高原东部河谷走向黄土高原和中原大地。传说中的华夏民族的首领炎帝黄帝也是在这一时期从高原东缘走向黄河中游地区。从高原西部迁徙到东部河谷盆地的原因可能与气候变迁相关,常年的寒冷气候迫使高原西部湖泊盆地的人类不得不迁徙到东部温暖的河谷。但是回归到原生地的内心意识使他们不断返回河流源头寻找祖先之根。人们在不断的迁徙中坚定了一个信念:死去的先祖神灵均居住在河流源头的高山之上。而天神也是居住在高山大岳之上。回归高山是回归祖先的灵魂,祖先的灵魂是自己的血脉源泉。回归祖先出生源地,是从中吸取祖先的灵气,保持祖先的血脉,传承祖先的精神。
藏北的冈底斯山是四河的发源地,也成为四河下游流域的不同种族、不同族群、不同宗教徒的精神故园。从远古到今天,各地一直有源源不断的人群溯河而上,来到冈底斯山朝拜神山。昆仑山成为华夏诸族群的祖先之山,精神故地。历史不同时期中原华夏民族中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不断地前往西方,寻找昆仑圣地,寻找黄河源头,寻找黄帝故地,寻找女娲和西王母;而蒙古高原乃至东北亚的游牧族群不断地来到青海湖湖畔、祁连大草滩、柴达木盆地、藏北羌塘,是寻找熟悉的生存环境,良好的生态景观,也是为了追寻精神家园。
12-14世纪出身于黄金家族的蒙古人的故乡是在肯特山下的三江源草原。这里分布有日月山、青海湖。成吉思汗在这里汇集了各个部落的蒙古人,建立了蒙古国。然后走向世界,走向辽阔的草原,形成了蒙古人治理的欧亚五大汗国。14世纪以后,分散在各地的蒙古人依然念念不忘自己追求的故乡,他们在各地的草原寻觅与故乡草原相似的地方,例如来到青藏高原的俺答汗将青海湖称之为青海,湖畔山峰称之为日月山。认定这是故乡肯特山草原相似的草原,是自己可以长期生存的家乡。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人生意义,到新的环境去探寻是游牧人后代的天性,是他们遗传的基因。这与宗教徒对来世的追求有共同之处,现实世界寻找不到有意义的生活,人们寄希望于来世或者彼岸世界。所以历史上的人们来来往往的大迁徙不一定完全为了物质利益,从古到今总有一些人是为了理想、梦想而寻找,而且要把探寻的梦想付诸于实践。
[1] 吴均.论夏嘉同音与羌藏同源[J].中国藏学,2006(2):111-119.
[2] F·W·托马斯.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M].李有义,王青山,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20-34.
(责任编辑 王莉)
Separation of Brothers and the Horse-dragon-bred Congs: The mythical expression of the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northern nomadic ethnic groups
NAN Wen-yu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Northeast Minorities, Dalian Liaoning 116605, China)
Stories about the separation of brothers and horse-dragon-bred Congs are myth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northern nomadic ethnic groups. The description of historical fac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yth convey the same idea that the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northern nomadic ethnic groups is inevitable for their survival and a magnificent feat for ethnic groups to reconstruct their groups and innovate their cultures for the sake of adapting to the chang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nomadic people; migration; myth construction
2016-09-09;最后
2016-09-19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3MZB052)。
南文渊(1952-) ,男,蒙古族,青海湟源人,教授,主要从事民族生态文化研究。
2096-1383(2016)06-0533-06
C9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