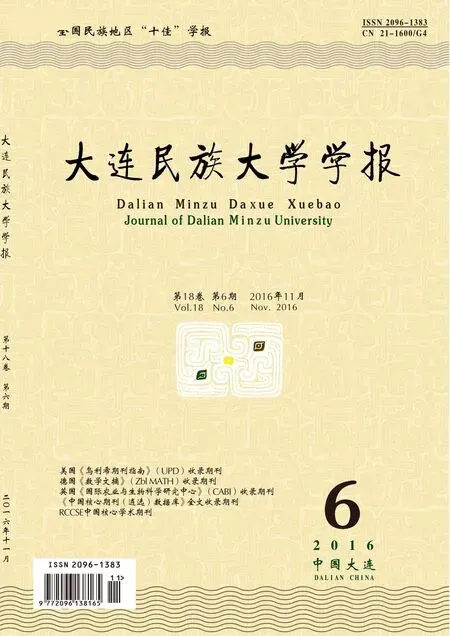论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两种方式
孙 岿
(大连民族大学 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05)
论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两种方式
孙 岿
(大连民族大学 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05)
当今世界范围解决民族问题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类是把民族问题作为文化问题来解决,另一类是当做社会问题来处理。前者基于争取身份承认的政治诉求,后者基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制度诉求,通过比较两种民族政策的历史过程,阐述政治经济诉求与文化诉求之间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澄清民族问题的本质。
民族问题;政治经济诉求;文化诉求
当今世界范围解决民族问题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类是把民族问题作为文化问题来解决,另一类是当做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来处理。前者基于争取身份承认的政治诉求,后者基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制度诉求,这两种方式决定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族政策。近年来,中国学者对两种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进行了比较[1],阐述了多元文化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论起源、主张和实践[2],深化了这方面的研究。那么,这两种方式有什么联系呢?本文通过比较两种民族政策的历史过程,阐述政治经济诉求与文化诉求之间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澄清民族问题的本质。
一、从文化视角处理民族问题
1.文化承认源于殖民地的种族主义制度
西方国家一般把民族问题作为文化问题来处理,这与西方社会区分不同种族的历史相联系。西方社会区分不一样的人都喜欢用Race这个概念,Race不仅是Kind的意思,包括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他们在区分Race的时候非常随意、武断,可以根据皮肤颜色、来自的地区、信仰的宗教等来划分[3]。例如,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最早卷入奴隶贸易。黑人被贩卖过来作为奴隶,自然而然在种族上形成梯级结构。美国早年的种族分类沿用了欧洲的布鲁门巴哈的分类体系,即全世界人类可分为五大人种,高加索人种(白色人种)、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马来亚人种(棕色人种)、尼格罗人种(黑色人种)和阿美利加人种(红色人种)。在美国历史上,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WASP)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而少数族群则处于遭受压迫的从属地位[4]。白人中心主义崇尚与“白色”相关人种特征的各种规范构建了权威结构,主流白人将有色人种标识为“黑色”“棕色”和“黄色”,赋予种族特殊的含义。媒体将有色人种描述为罪恶的、野蛮的、原始的、愚昧的,日常生活中对他们进行暴力侵犯、骚扰和歧视,把他们排除在公共领域和协商机构之外或被边缘化,剥夺了他们的合法权利和法律保护。正是建立在人类生物学基础上的种族理论,使白色人种掌握着话语权和支配权,堂而皇之地排斥和压迫着有色人种。
“争取承认的斗争”在20世纪末迅速成为政治冲突的主要形式,“差异承认”的诉求激发了各类群体的斗争,斗争首先在民族、种族、“族裔”的旗帜下动员起来。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20世纪60年代美国种族隔离制度最终取消,种族这个词逐渐从美国社会淡出。随着种族主义被取消,西方社会更多地用文化(Culture)和文化多样性,来替代种族(Race)差异。在理论上,就是以相对主义的文化多元论为基础,以强调文化价值“差别权”的方式提倡尊重民族文化,反对欧美文化中心主义。因此,西方主流社会认为,只要矫正错误的文化评价体系,给予受贬低群体文化特殊性赋予肯定的承认,就能解决族裔之间不平等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南茜·弗雷泽所讲:“其成员所经受的任何结构性不公正都将最终追溯到文化评价结构上。这种不公正的根源以及其核心,将是文化上的错误承认,而任何与之伴随的经济不公正都将最终来自文化根源。”[5] 20
2.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片面性
为了矫正以往错误的文化评价体系,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即在自由宪政民主政治的原则之下,赋予少数民族文化群体一定的差异或者集体政治权利,通过承认与尊重社会不同族群成员间的文化差异,构建一种和谐的族群关系与文化共存。例如,加拿大政府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针对少数民族的不公正待遇表示道歉并给予补偿。官方不再用具有歧视性的称呼,规定每年一度举行“多元文化节”,支持各族群使用自己的语言与文字。在因纽特人居住地设立自治区,保障各族群拥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利等。公共救助计划向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少数民族提供需要审核的“有计划的”援助,教育界中以降低分数录取有色人种学生比例等等[6]。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改变了错误文化评价模式无疑是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但由于不触及政治经济体制族裔化的深层结构,就预示了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一是市场竞争自然构建了族群劳动分工的差异性。大部分有色人种从事低报酬、低地位、肮脏的工作,而大部分“白人”从事高报酬、高地位的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这就造成大部分有色人种成为“剩余劳动力”,甚至成为不值得剥削、完全被排除在生产体系之外的群体,它仍延续剥削、边缘化和剥夺的特殊“种族”模式。二是加剧了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的隔离。加拿大印第安人保留地位于偏远地区,长期与主流社会相隔离,只有三分之一人口愿意和能够外出工作,绝大多数人只能待在部落等待政府施予救济。2016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的阿塔瓦皮斯卡特原住民社区共有2 000人,其中有101人企图自寻短见,其中有1人死亡,原因是生活水平相对低下、暴力犯罪、吸毒和入狱等问题突出[7]。三是主流社会以救世主姿态对待少数族裔群体,起到了扩大文化差异的反作用。主流社会把处境最恶劣的群体污名为一群“天生有缺陷又不满足的受特别恩惠和施舍”的群体,最终造成经济与文化从属地位的恶性循环。正是因为多元文化主义存在夸大各种文化的相对性而否认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的弊病,使得很多西方国家领导人公开表示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
综上,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超越白人主流构建的话语体系和支配体系。它以表面上的文化承认替代种族压迫制度,在不触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的条件下,试图对社会、文化等生活世界的基础进行社会改良,起到的只是隔靴搔痒的作用。所以,当今西方批判理论学者认为,“对于‘种族’这类双重集体来说——至少当两者被视为相互分离时,解构的文化政治与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最佳方式”。[5]35
二、从社会视角处理民族问题
与西方文化承认模式不同的另一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再分配模式。马克思主义民族殖民地理论,揭示了“资本”的本性决定了“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8]。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安排中,无产阶级、有色人种、妇女同样受到不公正的剥削,从而使种族、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成为一个集体。所以,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民族压迫、种族压迫,都是私有制、阶级压迫在人类自然群体方面的社会延伸,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压迫源于私有制社会经济基础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
1.生产关系的深层重构
20世纪初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一方面整个社会结构分化为两大对立阶级,少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另一方面,清末以来,帝国主义一直在利用一些少数民族上层精英分子搞所谓民族“独立自治”,企图脱离中华民族。面临阶级、民族的双重矛盾,中国不能选择西方单一承认文化价值方式,而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层重构方式,推翻各民族共同面对的阶级压迫制度,争取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
中国共产党将无产阶级革命目标与利益同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整合在一起解决。“彝海结盟”成为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民族政策的真实写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国体是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废除了民族地区奴隶制、农奴制、土司制、伯克制等阶级压迫制度,用“人民”身份整合民族身份,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的政治制度。在这种体制中,“人民”作为宪法的主体,少数民族共同享有国家主权。中国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民族识别工作”在法律层面重新确立了民族身份,保障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形成了共同的政治认同。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超越了西方国家的文化承认逻辑,将社会经济结构改造与承认少数民族身份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全方位的民族政策体系。在政治方面,把少数民族精英纳入国家体制;教育方面,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在社会现代化方面,帮助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使少数民族成员有机会和渠道实现政治流动和社会流动,很多少数民族成员由此进入了政府机关、工商业机构和事业单位。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塑造一体化国家和满足了少数民族自身诉求,民族关系达到了空前的和睦与团结。
2.多维交叉的综合模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但自我发展能力普遍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进一步明确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9]。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加快了民族地区繁荣发展,但过度追求经济效益,也容易忽略少数民族平等参与经济的可能性与文化差异性。一方面受信息、技能、语言、教育等因素限制,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存在障碍,少数民族农牧民无法依靠自身能力实现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价值与现代文化无法衔接。少数民族乡村传统文化习俗与现代社会以理性效率为导向有很大反差,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不能很好的适应城市的生活和管理方式;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群众感到陌生神秘,不能很好理解他们的某些生活和行为方式,特别是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身份、民族文化不断做文章,使过去一度被忽视和隐藏的民族文化差异被人为地扩大,影响到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这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不同于改革开放生产力水平较低、分配关系较为简单情况下的民族工作,更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感情高于民族感情背景下的民族工作。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10],在政治方面,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将发展经济与民族团结紧密结合,既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实施好差别化支持政策,也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在文化方面,要推动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要促进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等。这些重大创新观点,标志着新时期我们党深刻把握了政治经济要素与文化要素之间“盘根错节”的互动关系,形成多维重叠交叉的综合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超越。
三、结论与讨论
事实上,族裔是典型的双重集体,包含了政治经济因素和文化评价因素,两者在每一个民族身上的具体表现是相互渗透的,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回溯历史可知,西方国家把族裔成员不公正都归为单一的文化评价结构,抛弃政治经济体制的制度根源,寄希望于矫正文化评价体系,确有舍本逐末之嫌,这种简单化、孤立化的方式显然是不成功的。相反,中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把民族问题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来解决,将政治经济结构与文化结构紧密联系起来,进而建立了全方位公平正义保障制度,形成了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这种方式无疑是成功的,也为今天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重组留下空间。当今,中国不存在西方所谓“争取身份承认的政治诉求,”但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结构始终处于不断分裂和变化之中,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进程,一方面是现代化的经济社会文化成果空前积累,一方面是科技竞争将弱势群体排斥于现代化的新成果之外,在这一点上,中国所面对的现代化悖论和相应境遇与西方国家有相似之处。因此,面对少数民族经济与文化的双重适应问题,应突破对现代化的单一认知,确立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机制。
那么,应如何整合经济差异和文化价值差异,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机制。当前,西方学者引入“参与平等”的概念。参与平等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物质资源和公共服务确保各民族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之中,它排除了阻碍参与平等的经济依赖和不平等,称为“参与平等的客观条件”;第二,文化价值模式对所有参与者表达平等尊重,并确保取得社会尊重的同等机会。这称为“参与平等的主体间条件”。客观条件和主体间条件对于参与平等都是必要的,客观条件使人关注属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上被定义的积极差别的关系。主体间条件开始使人关注属于社会的身份秩序和文化上被定义的身份等级的关系[11]。所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需要建立一种包容式发展,协调整合社会正义的经济制度与文化价值两个方面,加强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各要素相互渗透,形成一种共同合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理论的时代内涵,也是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必然选择。
[1] 王希恩.多元文化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两点比较[J].科学社会主义,2010(2):8-12.
[2] 杨须爱.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自信——基于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民族政策的几点比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6):21-27.
[3] 范可.文化多样性与群体认同[G]//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74).
[4] 伍斌.种族批判理论的起源、内涵与局限[J].民族研究,2015(3):108-109.
[5] 凯文·奥尔森.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M]. 高静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6] 关凯.族群政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149.
[7] 加拿大原住民小镇11人试图自杀案震惊全国 [EB/OL].[2016-04-11] .http://news.sina.com.cn/o/2016-04-12/doc-ifxrckae7792130.shtml.
[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7.
[9]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新中国民族工作十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32.
[10]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22.
[11] 弗雷泽,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M].周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8.
(责任编辑 张瑾燕)
Two Approaches to Dealing with Ethnic Issues for Multi-ethnic Countries
SUN Kui
(Research Institute of Northeast Minorities, Dalian Minzu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605, China )
In today's world, there are two ways to solve ethnic issues. One is to treat ethnic issues as culture ones, and the other, as social ones. The former is the political appeal based on the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the latter is the demand based on the unfai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The paper, with the comparison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wo ethnic policies, elaborat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ppeals and cultural demands which is helpful to further clarify the nature of ethnic issues.
ethnic issu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ppeals; cultural demands
2016-06-21 ;最后
2016-07-08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50211)。
孙岿(1968-),男,新疆乌鲁木齐人,教授,主要从事民族问题理论、民族社会学研究。
2096-1383(2016)06-0539-04
C9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