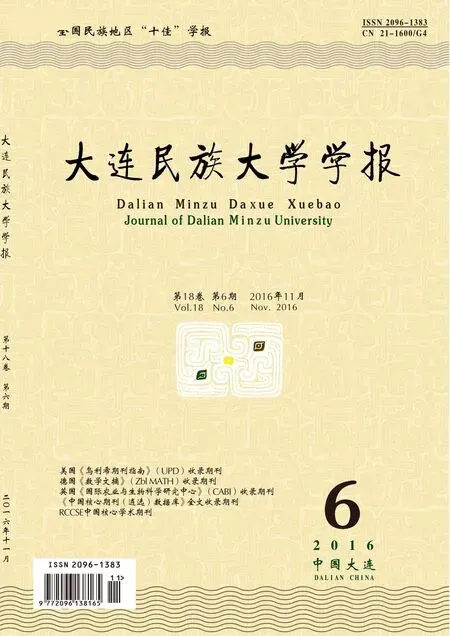萨都剌研究综述(1949-2015)
刘嘉伟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萨都剌研究综述(1949-2015)
刘嘉伟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萨都剌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家的杰出代表,公认的元诗大家。从“文献”“文本”“文化”三个维度对萨都剌研究史进行了梳理。萨都剌作品研究、文化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萨都剌生平、族属、文本归属情况依旧存在争议,尚期待新文献的发现与习见文献辨伪、辩误的深入。未来,可以深入探讨萨都剌的文学成就对于整部“中华文学史”的贡献,并且期待能够运用多学科、跨学科的视角与方法对这位色目才子进行全面的解读。
萨都剌;文献;文本;文化;研究史
萨都剌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家的杰出代表,公认的元诗大家,甚至被誉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萨都剌在当时的文坛影响就很大,他所作的《西湖竹枝词》,“一时北里皆歌之[1]”。萨氏的文学作品,至今仍广为流传,受到各族人民的喜爱。在《毛泽东手书选集》第十卷中,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两次书写萨都剌的《木兰花慢·彭城怀古》,这首词被谷建芬先生谱曲后,名之为《一饮尽千钟》,作为徐州市推荐歌曲广为传唱,足见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学术界对萨都剌的研究较多,争议也较大。诚如查洪德先生所言:“在元代诗人中,他可以说是被研究的最多的一个,但也是研究中问题最多的一个。他在元代诗坛的巨大影响,和有关他文献记载的缺失,形成极大的反差,像他这样的情况,在元代诗史为仅有,在中国诗史上也不多见。”[2]鉴于此,查先生曾对20世纪百年来的萨都剌研究作过回顾。进入新世纪后,萨都剌研究又陆续有新成果出现,20世纪成果的价值也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提炼,萨都剌的研究史遂有重新勾勒的必要。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1949-2015)的萨都剌研究,笔者拟从“文献”“文本”“文化”三个维度进行概括,希望对于萨都剌研究的推进,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构建有所助益。
一、萨都剌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文献是一切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展开的基础,萨都剌的研究,也以文献研究为起点。萨都剌作品集版本问题极其复杂,“据学者考证,有六十三种之多,其中已佚或存疑者十二种,一种存佚不明,五种为日本刻本,六种为词集,现存三十八种诗集版本,分《雁门集》与《萨天锡诗集》两大系统。”[3]早在1944年,朱陵就曾发表过《考雁门集版刻答萨士武》*此文可见于《学海》第1卷第5册,1944年11月。,对萨龙光编《雁门集》所用版本进行了补充。
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对于萨都剌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皆有所推进。1966年,葛树人在台北私立中国文化学院中文研究所取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为《〈雁门集〉校注》。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点校整理本的《雁门集》,署名“萨都拉”。1982年,刘试骏、张迎胜、丁生俊选注的《萨都剌诗选》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巴蜀书社出版了龙德寿译注的《萨都剌诗词选译》,2011年,该书又由南京凤凰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2011年,南京凤凰出版社推出了“历代名家精选集”,龙德寿又将萨都剌和元好问的诗编选到《元好问萨都剌集》中出版。2013年,杨镰先生主编的《全元诗》由中华书局出版,对于元代文史研究,功莫大焉!《全元诗》第30册收录萨都剌诗794首,在选录校勘时,其编者以刊刻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的《萨天锡诗集》和刊刻于明成化二十年(1484)的《雁门集》为底本,并进行了辑佚、辨伪的工作,对于重见于他人别集的诗一一注明。对于萨氏别集、选集的陆续出版,无疑是对萨都剌相关研究的有力推动及相关文献基础保障。
关于萨氏文集版本情况研究,较早的有张旭光、葛兆光1986年发表的《萨都剌集版本考》(《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该文梳理了明萨琦刻六卷本《雁门集》,明张习刻八卷本《雁门集》,明赵兰刻六卷本《萨天锡诗集》之间的版本源流;评价了萨龙光编注刊刻的十四卷本《雁门集》;并列出《萨都剌诗文辑补目》。进入90年代,有学者撰文研究日本所藏永和丙辰(1376)《新芳萨天锡杂诗妙选稿全集》(简称《萨天锡逸诗》)*关于日藏本情况参见刘真伦《北图藏本〈新芳萨天锡杂诗妙选稿〉考述》,《文献》1990年第4期;李佩伦、孙安邦《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初探》,《晋阳学刊》1991年第6期;李佩伦《论永和本〈萨天锡逸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不过杨镰先生考证后认为此书(至少它所依据的底本)是一部伪书[4]。
进入新千年,对于萨都剌文献研究,成果较丰者,当属杨光辉和段海蓉两位学者。杨光辉发表了《萨都剌佚作考》,从各种文献辑得萨氏佚作30余篇;并发表有《和刻本萨都剌集版本考》《关于卢琦〈圭峰集〉中与萨都剌等人相同作品的版权问题——兼论〈圭峰集〉的版本》*杨光辉论文情况分别见《文献》2003年第3期;《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复旦学报》2010年第1期。。200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杨光辉《萨都剌生平及著作实证研究》,该书对于萨都剌生平和作品进行了全面考辨。其中三至六章考证了萨都剌的著作版本、诗作真伪与编年笺注问题。全面勾勒明成化刻《雁门集》与明弘治刻《萨天锡诗集》两大版本系统及日本刻本(和刻本)流传情况。对通行的清嘉庆间萨龙光编刻《雁门集》十四卷本之编年笺注问题作了全面考辨。杨光辉博士导师章培恒先生评价其有三个特点,即寻根究底的精神,古典文献学的扎实基础,不盲从成说乃至权威的理性思考精神。并说:“这三个特点不但体现于萨都剌生年的考证中,也贯穿于这部《萨都剌生平及著作实证研究》全书;此书之能列于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之中,其故当也在此。”[5]
萨都剌名下的诗歌中,存在着大量的作者互见诗。不把这些诗歌的真正作者考述清楚,萨都剌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就都会受影响。段海蓉在萨都剌诗歌辨伪、诗集收诗辩误等方面用力较勤。例如,萨都剌研究者,多用萨氏后裔萨龙光编注的《雁门集》(十四卷本)进行研究,但段海蓉指出,《雁门集》存在诸多问题:“第一,该集中误录他人诗歌28首;第二,该集存录143首作者重出诗歌;第三,该集的编年和注释中有错误。此外该集附录收录的文献,有版本不善的问题。”[6]文章指出了《雁门集》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详尽考辨,有助于研究者对于萨都剌文学文本价值进行正确的评断。此外,段海蓉还出版了《萨都剌文献考辨》(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而这些研究的价值,如段海蓉自己所说:“不仅在于辨别萨都剌诗歌真伪,能为勾勒萨都剌生平、评论萨都剌创作提供可靠的文献基础,从分辨作者这个过程看,对我们整理整个元代文学文献,评估成书于元、明、清各代的元诗(甚至唐诗)别集、总集、选本的质量乃至辨别文集的真伪都有重要的意义。”[7]
萨都剌允为元诗大家,但《雁门集》外,至今尚未见今人整理的萨氏全集出版。其实,萨都剌诗、词、文皆有传世之作,完全可以出版今人整理排印的《萨都剌全集》或是编年校注。这当然需要萨氏文献辨伪、辑佚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二、萨都剌生平、族属问题的研究与争论
处于元明异代之际,萨都剌晚年可能隐逸江南,生平未见碑传。这样一来,萨氏生平、族属、身世都变得扑朔迷离。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文学篇》中,就论定萨氏为“回回教世家之中国诗人”[8]。新中国成立后,萨都剌生平考证,学界多有人研究,且争议较大。我们可分而叙之。
1.生卒年研究
关于萨都剌的生年,说法不一,且分歧巨大,从1272-1308年,跨越三十多年。署名元人干文传的《雁门集》序明确说:“踰弱冠,登丁卯进士第。”而萨都剌中举的时间有可靠的记载是1327年,古人称二十为弱冠,那么萨氏生年应该在14世纪初。清人吴修据此直接认定萨都剌生年为1308年,今人亦有持此说者*持萨都剌生年1308年说者,如吴修《续疑年录》卷二,清嘉庆刻本。今人持此说者,如唐圭璋《全金元词》(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89页;张俊、郭英德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页。。清人萨龙光编注的十四卷本《雁门集》卷十《北人塚上》案语:“元世祖至元九年壬申,是公之生年也。”[9]也就是将萨氏的生年定为了公元1272年。这种说法影响很大,现在一些文学史、文学编年史、文学作品选依旧沿袭此说*持萨都剌生年1272年说者,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页;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宋辽金卷》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7页;朱东润主编《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张燕瑾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5页等。。
新中国成立后,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于1965年发表《萨都剌的疑年》*陈垣:《萨都剌的疑年——答友人书》,《香港大公报·艺林周刊》1965年7月18日。后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0-83页。,认为萨氏生年1308年抑或1272年说皆不可信,并审慎地推断可能在1287年之前,确切结论须待将来之发现。1979年,张旭光先生的《萨都剌生平仕履考辨》,主要还是依照干文传之序,但把“踰弱冠”的范围扩大至二十六七岁,从而认为“1300年左右可为定论也。”[10]1983年,张旭光又根据《皇元风雅》、《元诗选》等诗选的诗人排列顺序以及前人的诗集序跋、诗论中的叙述顺序,确定萨为元代后期诗人,应与杨维桢、李孝光年龄相仿,再综合干文传序,再次推定萨氏生年为1290年前后[11]。1993年,刘真伦发表《萨都剌生年小考》一文,他以萨都剌《寄金坛元鲁宣差行操二年兄》诗为线索,考证出唱酬对象李质生年为至元二十八年(1291),得出萨氏生于1291年后。接着,又引用萨母年岁问题以及萨仲礼元统元年中进士之说,判定萨都剌生年下限为1293年。(《晋阳学刊》1989年第5期)1993年,周双利先生所撰《萨都剌》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萨都剌简谱》中推断其生年为1282年。主要理由是干文传与萨都剌彼此以朋友相称,年龄相距不应过大。杨镰亦称:“感到今人周双利所拟生年,即生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比较接近实际情况。”[12]
刚刚进入新千年,杨光辉就发表了《萨都剌生年考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文中考察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存署名萨都剌的《梅雀图》是伪作,《研北杂志》记载的“霜鹤堂之会”靠不住,弘治本《萨天锡诗集》所收《溪行中秋玩月》诗为卢琦所作,《雁门萨氏家谱》内容并不可靠。以文本证据和推理过程的不可靠对之前诸家学说进行详尽辩驳。杨文依据干序和虞集《与萨都剌进士》诗重新论证萨都剌的生年问题。认定其生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
此后,少有人再撰文专门研究萨都剌的生年。但2014年,段海蓉出版的《萨都剌传》,还是没有采信杨的说法。因为她列举了明人张莱《京口三山志》卷四有署名萨都剌的《送长溪归金山》,而该诗又作于至大年间(1308-1312),且萨氏还写有《次学士卢疏斋题赠句容唐别驾》,而卢挚大约卒于延祐初年(1314)。综合这些推断,萨都剌不可能生于1300年左右,而生年应该大约在1280年。
比起萨都剌的生年研究,萨氏卒年研究,歧说略少一些。清人萨龙光所校注的《雁门集》,将萨都剌作品逐篇进行了编年,其编年的时间下限是至正十五年(1355)。也就是说萨都剌应该卒于1355年后。但萨龙光编年粗疏之处甚多,当代学者很少有人采信他的说法。20世纪60年代,前文所引陈垣先生《萨都剌的疑年》,据杨维桢《西湖竹枝集》的记载,确定萨氏卒年下限为至正八年(1348);并根据萨都剌为干文传七十大寿所作的《法曲献仙音》一词,判定萨氏卒年上限为至正五年(1345)。1979年,台湾学者潘柏澄先生又提出了萨都剌卒于后至元六年(1340)之前说。主要论据是署名虞集的《傅与砺诗集》序:“进士萨天锡者,最长于情,流丽清婉,作者皆爱之。而与前之诸公先后沦逝,识者然后知其不可复得也。”该序篇末的题署是:“至正辛巳(1340)六月朔虞集伯生序。”这样看来,萨都剌卒年的下限应该在1340年[13]。
此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对于萨都剌卒年的讨论没有太实质性的进展。新千年以后,杨光辉在探讨萨都剌生卒年时,列出萨都剌《题董展〈三顾茅庐图〉》,署名“至正甲午(1354)秋八月燕山天锡山人萨都剌识”;朱镡《御史大夫康里公勉励学校记》碑,其中记载了萨都剌在至正十九年(1359)年的活动。这些材料证实萨都剌应卒于1359年之后。同时,杨光辉也对记载萨氏已死的文献进行了辨伪、辩误工作[14]。以此证实了萨都剌应卒于1359年之后。
要之,萨都剌的生卒年考证的推进,主要依据是新文献的发现与习见文献的辨伪、辨误。如署名元人干文传的《雁门集》序,是研究萨氏生平的最直接材料,但桂栖鹏、杨镰学者认为这是一篇伪作*质疑干文传《雁门集序》者,如栖桂鹏《萨都剌卒年考——兼论干文传〈雁门集序〉为伪作》,《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第318-320页。,杨光辉、刘真伦等学者又为干文传“辩护”,证明其可信性*不同意干文传《雁门集序》为伪作者,如杨光辉《萨都剌生平及著作实证研究》,第37-40页;刘真伦《陈垣先生〈萨都剌疑年〉补证》,《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但文献的证伪、证真有时又难于一锤定音,这就使得萨都剌生卒年充满疑窦的同时,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2.族属研究
关于萨都剌的族属,学术界也存在争议。概而言之,有如下几种说法。
(1)回回说。元人俞希鲁[至顺]《镇江志》载:“萨都剌,字天锡,回回人。”[15]上文已述,陈垣先生即主此说。当代学者对于萨都剌的研究,持此说者亦多,如试骏、穆德全、陈得芝等*持萨都剌族属为“回回”者,如试俊《论萨都剌及其创作》,《宁夏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穆德全《元代山西回回诗人萨都剌》,《晋阳学刊》1983年第6期;陈得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页。。
(2)回族说。此说即“回回说”的生发。如杨志玖先生指出:“萨都剌的族别是清楚的,他是回回人,也就是今天的回族。”[16]赞同并论证此说,或者以萨都剌为回族撰文者还有王志华、弓月、林松、龙德寿等*持萨都剌族属为“回族”者,如王志华《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剌》,《山西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弓月《著名的回族诗人萨都剌》,《回族文学丛刊》1979年第1期;林松《元代杰出的回族诗人萨都剌》,《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龙德寿《也谈萨都剌的族别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当代人所写的回族族别文学史,如张迎胜《元代回族文学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朱昌平、吴建伟主编《中国回族文学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也将萨都剌收入其中。
(3)蒙古说。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七《雁门集》提要言萨都剌“实蒙古人”。当代学者多以此为据,进行生发。如润生、李文进、云峰等*持萨都剌族属为“蒙古”者,如润生《浅谈著名蒙古诗人萨都剌》,《山丹》1979年第6期;李文进《元代蒙古诗人——萨都剌和他的〈上京杂咏〉》,《内蒙古日报》1983年3月17日;云峰《元代杰出的蒙古诗人萨都剌》,《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增刊。。 荣苏赫,赵永铣主编的《蒙古族文学史》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云峰《元代蒙汉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等族别文学史也都将萨都剌收入其中。萨兆沩还提出萨都剌是“蒙古族化”了的色目诗人[17]。
(4)维吾尔说。元人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言:“萨都剌,字天锡,回纥人。”有学人“据此判断萨都剌是新疆的维吾尔族。”*持萨都剌族属为“维吾尔”者,如谷苞《元代维吾尔族诗人萨都剌》,《新疆文学》1963年第11期;夏启荣《元代维吾尔著名诗人萨都剌》,《新疆日报》1982年4月18日。
此外,元人孔齐(孔克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一载:“京口萨都剌,字天锡,本朱氏子,冒为西域回回人。”这种说法经陈垣先生批驳后,“汉族说”,当代几乎无人支持。
学界一般认为“民族”作为一个现代学术概念,根源于西方,晚清民国才广泛使用的。具体到萨都剌的族属,把他作为今天某一民族的成员,恐怕有失妥当。在学界论争中,“回回说”“回族说”的支持者有不少是回族,“蒙古说”的论争者多是蒙古族,大概有学者自身的民族情感融入其中,这会不会影响到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也值得思考。
三、萨都剌作品研究
对于萨都剌文学作品的研究,是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渐次展开的。早在民国时代,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欧阳溥存《中国文学史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都提到了萨都剌,做出了简要的评价。
1.20世纪50-70年代萨都剌作品研究
这一时段,比照萨氏文献研究,文本研究略显薄弱,专门研究萨都剌的长篇论文较少,基本是文学史教材对其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进行概括。1964年出版的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介绍萨都剌时,说:“他在当时以宫词、艳情乐府一类的诗著名。乐府名作如《芙蓉曲》、《燕姬曲》等学晚唐温、李乐府,秾艳细腻之中,时得自然生动之趣。”又举《上京即事》中的两首,说萨氏“以婉丽之笔,写蒙古祭天礼俗和塞外风光,确有不同于唐代边塞诗的新鲜面目” 。但批评说:“可惜他的诗往往只是流连光景,揣摹声色,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却缺乏充实的思想内容。”[18]介绍萨都剌文学成就的单篇文章,较早的有长安《萨都剌和他的诗词》,曹马《萨都剌和他的词》,谷苞《元代维吾尔族诗人萨都剌》等*这些论文分别见于《新民晚报》1960年10月31日第六版,《羊城晚报》1961年2月5日第二版,《新疆文学》1963年第11期。。其中,谷苞认为,萨都剌诗词成就是很高的,他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和官吏的暴虐。其山水风景诗是热情洋溢的,其中对北国风光的描写是深刻而感人的。
1978年,台湾学者包根弟先生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元代诗歌研究的专著:《元诗研究》,该书第三章“元诗之分期”中,以一定篇幅介绍、评价了萨都剌诗歌的艺术成就,认为:“天锡诗清新婉丽,纯宗晚唐,才华高纵,其造诣可说在许浑之上。”对于萨诗的题材,包著主要介绍了宫词、题画诗、山水诗,认为:“天锡题画诗,皆兴寄高远,深寓讽谏之意”;《台山怀古》一诗,“和雅典重,又类道园(虞集)之作”。最后评价说:“各类题材中,以宫词绝句成就最高,五律次之,七古七律又次之,五古又次之。”[19]虽然简要,但包著注意到了萨氏不同题材、体裁诗歌的艺术成就高下,和大陆同时期著作的关注点多有不同。
2.20世纪80-90年代的萨都剌作品研究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萨都剌文本的研究,多是概括式介绍的话;那么,80年代以后,学者多注意研究萨都剌诗歌别开生面的艺术特色,单篇论文大幅增多。前文已述,80年代初出版了整理本《雁门集》和《萨都剌诗选》,而两书的前言,也可以看作是相关研究的专论。如《萨都剌诗选》序中说:“萨都剌的诗词以娴熟的艺术手段,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生活,绘成一轴生动的历史画卷。”对于萨诗内容,作者概括为“勇于写出民生疾苦”“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各种丑恶行为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并重点褒扬和绍介了其宫词与山水诗。对于萨诗的艺术特色,序言概括为:“他的作品‘诸体俱备,磊落激昂’,乐府诗真切而明快,律诗凝炼而酣畅,绝句质朴而含蓄,怀古词尤为洒脱、奔放、气势磅礴。前人还评价萨都剌的诗词‘婉而丽,切而畅’,‘雄浑清雅,兴寄高远,读之令人自不能释手’。”[20]
80年代后半期,周双利先生的萨都剌研究较勤,成果较丰。他的《自是诗人有清气,出门千树雪花飞——萨都剌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一文,将萨诗的艺术特色概括为“清新俊逸的艺术风格”“情真意切的诗歌意境”“优美的语言艺术”;并揭橥了“萨都剌对古代诗歌传统的继承”(《固原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周作注意到了萨氏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详尽分析了萨都剌常用的艺术手法,并指出了萨诗在元代诗歌发展史上的贡献,是此一时期较为全面细致的研究成果。进入90年代,邓绍基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史》,更明确地概括出:“萨都剌的诗歌确实具有题材多样、风格多样的特色。而且诗歌佳作极多,他实是元代诗坛的重要人物。”[21]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萨都剌研究,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其诗歌分类研究渐次得到了重视。如曾明《足迹遍南月,神韵兼刚柔——读萨都拉的记游诗》称萨氏记游诗“既不失‘北贵写实’的特点,又兼有‘南主神韵’的魅力”“萨都拉对江南塞北都有情,因此、时常从他一管笔端中涌出的是生动神奇、刚柔不衰的记游诗*《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类似的研究还有石晓奇《清而不佻,丽而不缛:漫论萨都剌的写景纪游诗》,《新疆社科论坛》1993年第1期。”。再如李延年《试谈萨都剌别开生面的妇女题材诗》称:“萨都剌妇女题材诗涉及范围广体裁多样,通过对妇女命运的关注表达了一定的政治见解,表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进步妇女观和民主主义思想,并‘最长于情’,未染道学气,客观上表现了以情抗理的进步倾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萨氏边塞诗、怀古诗,也有学者关注。*此类论文如曹新华《清新绮丽,自成一家:试论元人萨都剌“边塞诗”的民族特色》,《文史知识》1986年第2期;马志福,马卫平《论萨都剌怀古诗中的忧患意识》,《民族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
3.21世纪的萨都剌作品研究
进入新千年以后,萨都剌文本研究走向深入与细化。2005年,出版了郎樱、扎拉嘎主编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该书以较大的资料和理论容量,通过多侧面、多角度的总体性考察,勾勒出中国各民族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并且显示出这个格局的多层次结构。具体到萨都剌,论者注意到“萨都剌有一点像明初的文人解缙,在民间甚至比文坛更知名,更有影响,他的诗词一时风行草偃,流播人口,传颂颇快,这个现象是萨都剌在元代诗坛的特殊地位所造成的”。并指出:“萨都剌其实就是贯云石与杨维桢之间的桥梁。可以说,弥漫元末诗坛的‘铁崖体’一直是以宗唐的总体面貌受到关注。这种风格在元代前后期都有特殊的影响。而居中的萨都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杨维桢‘铁崖体’的僻冷,因之实际上更为‘当行’。”[22]这些论断,注意到元代特殊历史文化时期,色目人萨都剌的文坛影响,以较为恢弘的视野审视了元代多民族的文学创作及其相互关系。马晴从族别文学史的维度《论萨都剌在回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认为:“萨都剌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回族文学的‘鼻祖’。元代是回回民族的形成期,也是回族文学的形成期。萨都剌以他丰厚的诗作,过人的才思,刚柔相济的风格独占元代文学的鳌头。”(《宁夏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也有学人从萨氏创作的审美特征维度进行思考,将萨都剌诗歌的审美特征概括为三点:“中国画的写意风韵,色彩纷呈的优美境界,咏史诗歌的时事感伤。”[23]
这一时期,关于萨都剌文学作品的体裁、题材分类研究更加深入。如张维民《论萨都剌词》一文,据唐圭璋主编的《全金元词》,分析了萨氏流传至今的15首词作,认为:“其词上承苏轼、辛弃疾优良传统,形成雄奇豪迈、刚健质朴的词风;其怀古词所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和兴废之感构成词作的思想精髓;隶事用典、融化诗句以及锤炼字句是其鲜明的艺术特色。研究萨都剌词,对于把握宋以后词的发展变化,全面客观地评价萨都剌的创作,进一步认识汉文化对他族文化的亲和力与融合力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也有学人从色彩的维度分析萨都剌词,还有学人专门关注其咏史词*此类论文如刘宝《萨都剌词的色彩艺术探论》,《广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陈忻《游走于宋词元曲间的萨都剌咏史词》,《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王锡九《论萨都剌的七言古诗》称:“他的七言古诗取径宽广,特色鲜明,创获显著,不愧是元代诗坛上的佼佼者。”《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在萨诗分题材研究上,龚世俊等人注意到了萨都剌的宫词,认为:“他将‘清新’的气息贯注于宫词,使之与绮丽完美结合,形成迥异于前人宫词的艺术个性,而‘自成一家’”“在新兴的戏剧、散曲、小说等市井文艺和浓郁的商贾、艺人、市民等世俗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下,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也在逐渐接近市井民众,如那些通常由散曲来表现的题材内容也不同程度地进入诗人的视野,所谓“雅文学”和“俗文学”的界限被打破了。”[24]该文通过时代背景、作者的民族属性等维度分析萨都剌的宫词,并尝试将元代多种文体进行通观式的思考,为整个元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萨都剌的题画诗、送别诗、咏物诗,也得到了学人的关注*此类论文如岳振国《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剌的题画诗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葛琦《元朝诗人萨都剌题画诗的民族特征》,《文艺评论》2013年第2期;姚鲜梅《元代诗人萨都剌诗歌中的别情》,《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年第8期;姚鲜梅《萨都剌咏物诗赏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等。。
如何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上为萨都剌定位,除了其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外,还应该纵深探讨其对于中国文学史上“主流”知名作家的接受与影响,区别与联系。2010年以后,在这一维度上研究萨都剌的文学成就,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刘嘉伟、徐爽《色目诗人萨都剌对李白的接受》,注意到了萨都剌“‘诵法青莲’,借鉴李白诗歌的意象,承继太白清新俊逸的诗风,而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并“从盛世心态、胡人血统、仕履坎坷”等几个角度探析了萨都剌能够学习李白,敢于学习李白,又学得很好的原因[25]。此外,也有学人谈到杜甫对于萨都剌的影响;还有学人将萨氏与称名文坛的元诗“四大家”进行比较,证实其文学成就*此类论文如徐希平《杜甫对古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影响(上)》,《杜甫研究学刊》2012年第2期;刘淮南《萨都剌与元诗“四大家”之比较》,《中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
纵观萨都剌诗词的文本研究,从简单介绍逐渐走向全面探讨,从宏观研究逐渐走向分题材、分体裁的探索,并将萨都剌的文学创作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上进行定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未来,关于萨都剌的文本研究,分题材研究等问题当然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其文学史地位等问题的探讨还可以进一步深化。在批评方法上,也显得比较单一,很少有学者借用西方最新的批评方法研究萨都剌,可能是学者们为避免东西方文本与方法碰撞中的削足适履,也可能是整个元代诗文研究尚未充分展开使然。
四、文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西方人文学科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文化研究日益取代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国学术界也深受影响。“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二者并不对立:前者将文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应用于其他文化客体,而后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实践与其他话语方式相联系也会获得新的活力。”[26]具体到萨都剌的研究,从民族学、文化学、哲学、宗教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地理学、传播学、艺术学等维度观照,当可以列入文化研究的维度进行梳理。相对于文学,文化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有时和文学研究难以截然分开,所以笔者的萨都剌文化研究情况梳理难免重复或者遗漏,特此说明。
1.80-90年代萨都剌研究中的文化研究
相对于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文化研究的范式“起步”时间比较晚,成果数量自然不如前两者丰厚,所以我们可以21世纪为界,进行梳理。
萨都剌是非汉族诗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从民族特征的角度探讨萨都剌艺术成就,自然会丰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视域。将文学与民族特征通融思考,自然应当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而这方面研究最早的,当属黄慧芳、王宜庭《萨都拉诗词的民族特征》(《民族文学研究》1984年第2期)。文章指出:“一个诗人,他只能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阶级的诗人,民族性格的烙印必定会在他的诗作中表现出来。”作者从民族性格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萨都拉的诗词,在题材上无论是针贬时弊还是写景抒情、凭吊古迹,在体制上无论是古体还是律绝,都秉赋着一种雄健的气势和质直的品格。”又称:“萨都拉诗词的民族特性还表现在诗词中反映着民族的生活习俗和表达感情的独特方式。”作者还注意到了“(萨都剌)诗中的江南景色也具有一种悲壮苍凉的意境,与汉族诗人的描绘很不一样。”最后总结说:“萨都拉是用汉族诗歌形式创作的草原民族诗人,他把草原的气概注入到元代孱弱的诗坛,他和同时代其他少数民族诗人一道,打开了一个诗歌创作的新局面。”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多关注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家如何汉化,很少注意少数民族文学家以其独特的民族性格对中国多民族文学史所作出的贡献。黄慧芳等人的文章从民族学的角度分析萨都剌的诗歌,更好地揭橥了萨诗特色,也给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以有益的启示。
从文化学角度阐释萨都剌的,较早的当属罗斯宁《民族大融合中的萨都剌》(《中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文章指出:“萨都剌的创作心态有三个来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和汉文化。回回族的性格使他的诗较少羁旅之愁和地域偏见,具有宽宏的观察角度,但缺乏整体感,难以与汉族的诗大家比肩。他对蒙古族文化采取欣赏接受的态度,但对其以征战为荣的思想不苟同。与汉族文人、僧侣密切交往,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汉族的历史意识、哲学思想、文学传统。诗作风格兼有北方文学的阳刚之美和南方文学的阴柔之美。”前文已述,对于萨氏族属问题争议较大,但确定萨氏族属对于文学研究意义何在呢?罗斯宁先生的文章给予了较好地阐释——从多元文化的视角解读萨都剌,自然发现了他的文学艺术特色。
这一时期,杨法震探讨了萨都剌的绘画艺术;曾晓玲从政治学、历史学的维度解读萨都剌的文学作品,从其诗歌看元朝政治的衰变;李延年则从地域文化的视角,解读南京与萨都剌的诗词创作*这些论文分别见于杨法震《萨都剌的绘画艺术》,《平顶山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曾晓玲《从萨都剌诗歌看元朝政治的衰变》,《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李延年《平生梦想金陵道,次日偶然身自来:南京与元代诗人萨都剌的诗词创作》,《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2期。。
2.21世纪以来的萨都剌研究中的文化研究
这一时期,新视角、新方法不断登上文学研究界的“舞台”,从文化视域解读萨都剌的文章渐次增多,较为引人注目的是从宗教学的视域观照萨氏其人其诗。较早的,当属张泽洪《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剌与道教》(《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文章考察了萨都剌在江南道教名山道观的游历,与道士(尤其是茅山道教高士)的交往情况,认为:“其涉道诗所记载武夷山道教实况,至今于道教史仍有参考价值。”文末作结道:“萨都剌与道门人士融洽无间的交往,成为民族宗教史上的一段佳话,这在比较宗教学上有着典型意义。萨都剌作为一个东来的回回人,必然格守其固有的伊斯兰信仰,但他置身于多元一体的中国社会,能够主动了解传统的道教文化,以实际行动践行“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圣训。他对道教的了解和记录,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一代回回精英的识见以及主动对话的开放心态。萨都剌的数十首涉道诗,展示出元代回回文化人视野中的道教。他与道门人士的诗文酬答,实质是回回人与道教的对话。这种不同民族宗教间的对话,无疑有助于双方的了解。这或许能从一侧面,折射出回族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这样的文章,是以萨都剌的作品作为历史文献,展现元代多元宗教融合,阐释宗教发展史,这种研究思路也值得文学研究界借鉴。稍后,龚世俊发表了《萨都剌的诗歌与元代宗教》(《宁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指出:“在萨都剌的诗歌中,有180余首涉及元代宗教及其人物。从这些诗歌可以了解到,在蒙元统治者包容优待的宗教政策扶持下,诸宗教在与社会各阶层的互动中得以传播发展,以及释道著名宗教人物的活动。与此同时,由于身处在元代社会的浓郁宗教文化氛围之中,加之出身于答失蛮,受到穆斯林家庭的熏陶,因而萨都剌对宗教带有特殊的情感。在其宦游中,所到之处无不遍览寺观,并与释道大师过从唱酬。这种自觉地接触了解诸宗教,对萨都剌的思想造成深刻的影响。而在诗歌创作上,既丰富了萨诗的内容和形式,也对其‘别开生面’的诗风的形成产生积极的作用。”此文更将文学与宗教进行了通融性的研究。龚世俊又发表了《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萨都剌道教诗歌探析》《萨都剌的涉道诗及其符号意义》《萨都剌与僧道的交游酬唱述论》,使用的批评方法更加多样*这些论文分别见于《宁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学术交流》2008年第7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这一时期,李延年从传播接受的视域解读萨都剌诗歌,“从创作方面、评论方面以及萨都剌诗歌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定位等三个方面,探讨萨都剌诗歌创作的传播与接受”[27]。黎林《从萨都剌诗文看萌芽时期的回族哲学》,认为萨都剌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回族哲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理欲结合的人生观;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法律观,提倡社会公允的社会历史观,“信前定”的宗教观(《昌吉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宋晓云从“丝绸之路”的维度解读萨都剌诗歌,认为其“作品在内容上主要是以反映上都、大都的自然风光及现实社会生活为主,体式、风格多样,为蒙元时期丝绸之路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8]何跞绍承前文所引罗斯宁《民族大融合中的萨都剌》中的观点,分析得更加仔细,认为:“虽然萨都剌之游,是游商和游宦,不同于一般的游牧,其祖上西域回回人,也以经商为主,然逐利而游的实质却同于游牧。萨都剌的‘游’更不同于庄子之‘游’的目的,后者在更高的宇宙境界而实现想象式的齐万物的神游境界,这又上升到最高的人生宇宙融合的哲学境界。萨都剌的‘游’,因为具有了北方少数民族以游为牧的现实特点和心理因素,因而其为个体生计而囿于一种生存的焦虑,进而呈现出的是一种孤独漠然的悲感,而于中又自然生发出一种对现实生存条件的抗拒,而体现出人对自然的力量,产生一种豪壮力量之美。”[29]这种分析方式,结合了萨都剌的民族特征,文本内容和艺术风格,文心较为缜密,得出的结论自然令人信服。
萨都剌本身是西域人,且工书善画;又可能出自伊斯兰教世家,且在中土深受儒释道思想浸润。所以,从文化维度对萨都剌进行解读,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会切中肯綮。而这些文化研究的文章,也无疑扩大了萨都剌研究的视域。萨都剌是较为全面的文学艺术大家,从文化角度的解读,也需要研究者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和知识背景,甚至多学科研究者通力协作。鉴于此,这方面的研究可说是未来萨都剌研究的“生长点”,值得探索。
五、结 语
综上所述,萨都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文献研究方面,萨氏生平、族属、一些作品归属的情况依旧存在争议,尚期待更有力的新文献的发现;在文本研究方面,发表平面式、概念化的文章者不乏其人,一些细节问题还有深化的必要;在文化研究方面,由于萨氏族属、时代的独特性,期待有学者能用多学科、跨学科的视角与方法对于这位色目才子进行全面的解读。
2015年第4期,《文学遗产》开辟“中华文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笔谈栏目,旨在阐明“中华文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文学交流与融合的产物。”具体到萨都剌,他的创作实绩,可说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晶。我们认为,萨都剌研究最有价值有两个部分,一是对其文学史的地位和影响和研究,二是将其作为少数民族作家进行的研究,后者深化和拓展了主流古代文学史对其的研究。萨都剌的文学创作、文学交往、文学活动对于整个“中华文学史”发展进程有何影响,或许,这是未来值得我们思考的话题。
[1] 徐釚.词苑丛谈[M〗//萨都拉(剌).雁门集:附录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39-440.
[2] 查洪德.20世纪萨都剌研究述论[J].民族文学研究,2002(2):47.
[3] 査洪德.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金元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316.
[4] 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326.
[5] 章培恒.《萨都剌生平及著作实证研究》序[Z]//杨光辉.萨都剌生平及著作实证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5-6.
[6] 段海蓉.萨都剌《雁门集》(十四卷本)辨误[J].新疆大学学报,2015(6):109.
[7] 段海蓉.萨都剌诗歌辨伪管窥[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3):109.
[8]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M].陈智超,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68-70.
[9] 萨都拉(剌).雁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69.
[10] 张旭光.萨都剌生平仕履考辨[J].中华文史论丛,1979(2):331.
[11] 张旭光.回族诗人萨都剌姓氏年辈再考订[J].扬州师院学报,1983(3):53.
[12] 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319.
[13] 潘柏澄.萨都剌生年考略[J].史原,1979(9):21.
[14] 杨光辉.萨都剌生平及著作实证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2-27.
[15]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十六[M].杨积庆,贾秀英,蒋文野,等,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637.
[16] 杨志玖.萨都剌族别及其相关问题[J].南开学报,1983(6):24.
[17] 萨兆沩.一位蒙古族化的色目诗人萨都剌[J].北京社会科学,1997(1):86.
[18]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中国文学史:第三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318-319.
[19] 包根弟.元诗研究[M].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107-108.
[20] 刘试骏,张迎胜,丁生骏.《萨都剌诗选》序[Z]//刘试骏,张迎胜,丁生骏.萨都剌诗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1-15.
[21] 邓绍基.元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478.
[22] 郎樱,扎拉嘎.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元明清卷[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105,108.
[23] 李新涛.萨都剌诗歌的审美特征[J].晋阳学刊,2001(6):97.
[24] 龚世俊,皋于厚.试论萨都剌的宫词与艳情诗[J].宁夏大学学报,2005(6):52.
[25] 刘嘉伟,徐爽.色目诗人萨都剌对李白的接受[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3(5):121.
[26] 王逢振.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J].天津社会科学,2000(4):95.
[27] 李延年.试论传播接受视野中的萨都剌诗歌创作[J].民族文学研究,2006(3):27.
[28] 宋晓云.萨都剌丝绸之路相关题材诗歌创作引论[J].民族文学研究,2009(1):37.
[29] 何跞.论萨都剌诗歌的民族本色和学汉特点[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3):48.
(责任编辑 王莉)
Research Reviews on Sa-Dula (1949-2015)
LIU Jia-wei
(Literature School,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Sa-Dula is an outstanding minority writer in ancient China, universally recognized as a great master of the Yuan dynasty poet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mb the research history with respect to Sa-Dula from the angle of “literature”, “text”, and “culture”. It is stated that satisfactory results have been obtained concerning the research on his works and culture, but controversial still remains about his life, his ethnicity identity and the ownership of the texts. Therefore, it is expected that new literature can be uncovered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be discerned, further probe be made into his literary contributions to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be provided regarding the talented Semu from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Sa-Dula; literature; text; culture; research history
2016-07-07; 最后
2016-07-17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121);江苏省“青蓝工程”资助项目(苏教师〔2016〕15号)。
刘嘉伟(1982-),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2096-1383(2016)06-0552-09
I29
A
① 这句评语可见于林人中《雁门集》序,《雁门集》殷孟伦、朱广祈整理本附录此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