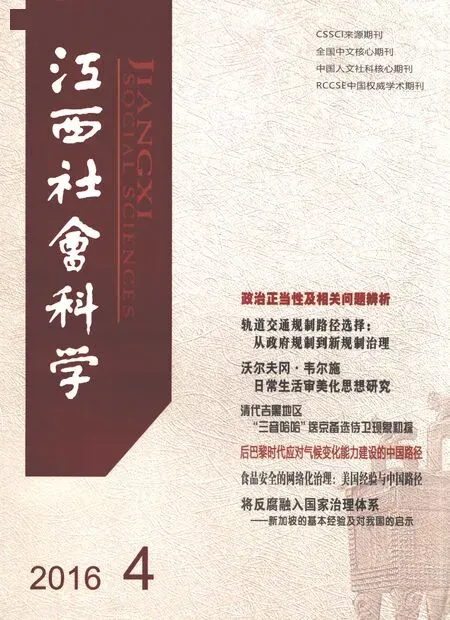作为溢满性现象的绘画
——马里翁《论多余》中的分析
■陈艳波 张雨润
作为溢满性现象的绘画
——马里翁《论多余》中的分析
■陈艳波 张雨润
当代法国现象学家马里翁对“被给予性”的强调和以此展开的分析,使得他更彻底地贯彻了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精神。在马里翁看来,作为溢满性现象的绘画,通过其画框对纯粹可见性领域的划界和这个纯粹可见领域所获得的作为偶像的权力,使得它真正完成了现象学还原。同时,作为溢满性现象的绘画,不再是对原型的模仿,而是成为原型的原型,这或许让我们不再将艺术看作是对现实的模仿,而是现实在摹仿艺术。
马里翁;溢满性现象;绘画;《论多余》
陈艳波,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张雨润,贵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贵州贵阳 550025)
当代法国现象学家马里翁 (Jean-Luc Marion)在继承现象学传统的基础上,又有重要的突破,他对“被给予性(giveness)”的强调和以此展开的分析,使得他更彻底地贯彻了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精神。在马里翁看来,在全部被给予性的现象当中,溢满性现象最典型地体现了被给予性的现象特性,因此,溢满性现象在马里翁的现象学分析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也是他的现象学颇具特色的方面。本文主要讨论马里翁在《论多余》(In Excess)一书中将绘画艺术作为一种溢满性现象的分析,展现马里翁现象学思想的特色以及一种对绘画艺术理解的新的可能。
一、何为溢满性现象
在马里翁看来,依据呈现过程中的直观与认识概念之间的充实关系,现象可分为溢满性现象(saturated phenomenon)、贫乏现象和普通现象。贫乏现象是指充实概念的直观比较贫乏,如数学或逻辑的概念,只需要一些纯形式的直观来充实和完成此类概念的现象显现。此类现象的贫乏性是由于它们的普遍性和确定性,它们恒久地保持自身不变,每一次显现都是重复自身。普通现象指涉的则是物理世界中的自然现象,如我们对于自然界中某种事物的性状的描述。诚然这里有了更具体的直观内容来充实这种描述,但它仍然面临并非事物本身的指控,因为“思想所意指的东西都是充实的直观完整地作为隶属于思想之物而表象出来的东西”[1](P126)。贫乏现象和普通现象都因为是被构造的而不能完全显现现象自身。
与以上两者不同,溢满性现象中的直观并不服从于意向,相反却超出意向,“第一性的现象依然通过直观满溢出(saturate)所有意向”[2](P44),是自身向意向涌现出来的现象,现象的显现因此就不是意向可以随意左右的,事物以此方式才能真正地将其自身呈现出来。马里翁因此认为,溢满性现象才能真正地实现“回到事物本身”。
马里翁对溢满性现象的规定和理解来自这样一条原则:“一个现象只在它首先给予自身的程度上显现自身——所有显现自身的东西,为了能够显现,必须首先给予自身。”[2](P30)胡塞尔将现象规定为“显现”与“显现者”之间的本质关联。[3]在解释这种关联时,他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找到了一种现象显现的机制,即先验自我的意向性构造行为,这个先验自我就成为那个使“显现”得以显现的“显现者”。这个先验自我被胡塞尔认为是不能再被还原的东西,现象的显现须得以它为根据。
然而,既然现象学宣称回到事物本身,又怎能接受一个先验的前提来为现象的显现提供支撑呢?马里翁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先验自我把现象构造成对象,把它置于自身的掌控之中,并完全控制它,那么,现象如何能宣称依赖自己并在自身之中展开呢?”[2](P30)在一个以先验自我为依据而建立的世界中,现象只能作为这个先验自我的对象呈现出来,这种对象的现象性仍然是从我们的意向性之中派生出来的,并不能称之为事物本身。马里翁认为,要承认事物显现自身,就需要将显现的主动权交还给现象,而为了行使这种主动权,现象需要有一个自我(self)。这并不是一种本质主义意义上的行动载体,而就是那行为本身,一个自转的主体,一个意志。这个自我就是前述原则中那给予自身者的自我(self of what gives itself),而所谓显现自身者正是这个自我的现象化,“人们在显现自身(showing itself)的现象中确认的那同一个自我(self)是从那给予自身者(what gives itself)的源初自我中发展来的”[2](P31)。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自我并不是完全可见的,它是通过自身的涌现,自身过度的丰饶向可见者亦即显现自身者的领域流溢出来的。现象的显现是对那给予自身者的证实,因此,在马里翁看来,“所有那些给予自身者并不必然显现自身——给予并不总是被现象化”[2](P30),可以说溢满性现象中直观对意向的超出,实际就是因为给予的无法完全被现象化。
“事件(event)”是马里翁用来描述溢满性现象的重要概念,是他针对以往现象学家,特别是胡塞尔将现象理解为意向性对象而提出的,旨在针对象概念的第二性 (因为它是被意向性构造出来的)和客观性。由于每一个被构造出来的对象意味着它只能如此被构造,只能按照一种固定的方式去再现它,正如科学实验中要取得同样的观测结果就要严格控制实验条件的一致性,否则便不能制造出同一个现象一样。因此,对象也是可复制的,一经产生便不再变化,即便这世界中再也没有这个对象的实在,它也仍然存在于某种理念之中,因而是一种静止状态的现象。
“事件”却不是这样,它拥有一个自我,自己决定自己的显现,换言之,它显现的东西都来自它自身,并不从别处借用什么。事件往往都是在它发生之后才被人们意识到,并且这种意识并不是一下子就直指事件本身,而是首先指向事件的影响,然后才注意到一个事件发生了。而且,更可能的情况是,人们只能从事件的影响去追溯事件本身,我们看到了事件造成的影响,却看不到事件本身。时下互联网世界里时常上演这样那样的网民群体性事件,其导火索往往只是某些不经意的发帖行为,经由无数的难以全面把握和理解的情境不断酝酿累积。这种事件的特征是当它发生的时候,它就已经发生了,人们意识到它的时候实际也只是在意向性地构造它,同时也落入了它的影响之中。
因此,事件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种正在发生的东西,它造成被意识到的或不被意识到的影响,并在这种影响的积累和扩散中取得显现的权力。事件并不是发生在一个物理时空的点上,任何一个点都只能是事件的一个环节,人们很难将它的边界划定出来,因为它的自我是在时空中绵延展开的。因此,在马里翁看来,事件是我们得以回到事物本身的有效途径,它在自身中保存了给予自身者的踪迹,它不仅敞开了通向现象源初自我的入口,而且使这个自我的现象成为不可置疑的。“通过其发生,事件证实了一个不可预见的原型,这原型从常常是不被认识,甚至是不在场,至少是不可被指认的原因处升起。”[2](P31)
马里翁举他在报告厅中做讲座为例来说明“事件”现象显现的模式。
首先,报告厅实际上在我们这些听讲座的人之前就矗立在那里,等候我们进入。我们或许见过它的设计图纸,抑或是它的宣传图片,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亲眼看见它以及进入它内部的那一刻获得的真切体验。因为它有自己的历史,它有自己的记忆,这些我们都不曾参与,当我们与它相遇时,它的过往就会向我们走来,我们越是试图去体验它,它带给我们的冲击就会越强,因为在漫长的岁月里,它积累了无数时间的故事和细节等待我们去发掘。这些是我们毫无准备就迎头撞见的,这种真切的体验向我们证实了它作为一个事件对我们的影响,超出了我们对一个报告厅的理解。
其次,这个报告厅也在经历一个现在,此时此刻,这个正在进行的讲座或许是众多在这里举行的会议、讲座中的一个,但却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它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被复制出来。正在发生的一切都超出了我们的建构,这讲座中出现的每一个声音都不间断地联系和预示着下一个声音,它们的总体效果是无法预先知道的。一个事件的现在是无法在物理时间中被理解的。这个讲座现在正在进行,但物理时间点上的现在只有一个短暂的声音出现,“现在”必须被看成是流动的,才能给出一个完整的可以被理解的东西,我们恰恰是通过正在发生的事件来理解“现在”的,而非相反。因此,“现在”证实了“现象的自我”[2](P33),由于正是这个自我的自由发生使现在显现出来。
最后,在将来的日子里,人们可能还会谈起这次讲座,描述它的精彩或乏味,争论它的创新或陈腐,但没有人可以穷尽这次讲座中发生的一切并以此来完成对它的描述。这种描述任务将是一个没有终点和不确定的解释学工作。[2](P33)而且,只要人们未来还继续谈论这个讲座,就可以说讲座这个事件仍然没有结束,它通过这种被谈论展示着它的影响力,不断向未来拓展着它的边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武断地斩断这种事件向未来的延伸,这就证实了事件的发生就是从自身开始的,是给予的自我的自身展开。事件就是这样一种不可预见、不可复制、不可穷尽的发生现象,它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毫无保留地超出了意识对它的构造,它实际在自身的发生之中使得时间的三个维度呈现出来。因而我们说,事件作为一种自身显现是现象显现的基本模式,是一种溢满性现象。
显现与显现者是现象的两端,马里翁的溢满性现象之所以成为现象学的新进展,就在于它倒转了这两者的关系:将主动性和第一性赋予了显现一端,而将显现者认作是第二性的,需要由显现来构造。这种构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马里翁以“出生”现象为例,说明我们实际上是伴随着一个给予自身的现象 (即 “出生”)而被开启的。出生本身是一个事件,因为它给予自身却并不显现自身,但又在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不断地展开自身,“我的整个一生,在某种本质意义上,都仅仅用来重新构造它,赋予它以意义,以及对于它沉默的呼唤的回应”[2](P42)。我的出现是因为出生作为一个给予自身的事件把“我”给予出来,“它启动了l′adonné[被赋予者]”[2](P43)。这个“我”在马里翁的表述里用的是宾格,但并不意味着在“我”被给予之前还有另一个属我的东西在等待接受,被给予的和接受这给予的是同一个“我”,马里翁称之为“从所接受的之中获得自身者”。这个“我”就是一切现象得以显现的条件,也就是那显现者。因此,出生也被马里翁称为“第一现象”,它是所有现象的原型。[2](P43)“我”作为一个l′adonné就总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出现的,是被事件构造出来的。“自我在其源初意义上是事件的自我,其次才是作为l′adonné的自我。”[3]
其次,这个实践性的自我本身是不可见的,它需要l′adonné来使它现象化,“被赋予者的功能就是在自身之中丈量被给予者和现象化之间的缝隙”[2](P49)。被赋予者的自我就是给予自身的东西显现的尺度,但这尺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胡塞尔的先验自我一样处于绝对的地位,而是在每一次使给予者现象化的过程中不断获得的,因此,也可以说被赋予者并不在出生之时就一蹴而就,而是伴随每一个现象的显现不断更新。进而言之,被赋予者的自我也正是在给予的显现中得以显现出来,这得以显现的正是被赋予者的尺度。在马里翁看来,被赋予者的显现得益于它对给予者的阻力。被赋予者的有限性本来是对无限的给予者的限制,但实际却成了给予者现象化的条件。因此,给予者现象化的程度也就反映了被赋予者的有限性的程度。这种共轭的显现使我们能通过对现象的把捉来获得对我们自身尺度或限度的理解,抑或是在现象中窥见那不可见的给予者,进而扩展自身的边界,因此,可以说,绘画作为溢满性现象就是我们理解自身并超出自身的方式。
二、绘画是一种溢满性现象
溢满性现象是直观对意向的超出,这在绘画的现象里就是图像外观对其原型的超出。人们往往会认为绘画作品的出色与否在于它是否能毕肖地模仿现实中的事物原型,因而对绘画作品的赞美实际就成了对作者绘画技巧能力的赞美。但是,很多时候绘画并不是毕肖原型的,绘画史上故意改变人体或景物比例的名作多不胜数,可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对这些作品的赞赏,甚至超出对那些比例精确的作品的称赞。这似乎在提醒我们,在欣赏绘画作品时,人们实际上忽略了它与原型之间的相似关系,至少外观上的相似关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在艺术之中,原型引起的欣赏要比它的‘相似外观’少”,这是因为两者绝对不同,而且其差别正是在于这种绘画作品的“相似外观”(resemblance)是以夺取人的欣赏目光为能事的。绘画因此并不因为它与原型之间的相似关系而得到人们的欣赏,而是作为它本身——一种纯粹的外观(pure semblance)——而被欣赏。在绘画作品的面前,“只有那相似的外观 ‘相似着’(seems)——显现着,发着光,闪耀着”。[2](P58)
因此,绘画作品实际带来的并不是与原型的比较,而是对原型的遗忘,这是因为,绘画现象的显现模式不同于其原型的显现模式。原型的显现是一种普通现象,意向性的目光在杂乱的可见世界中指向它,将它构造出来,它因此服从于这种意向性——随时可以被其他东西 (的现象)取代,或成为某个更大的意向性对象的局部。绘画现象则是溢满性现象,它自己从可见世界中跳脱出来,以自身纯粹的可见性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同时排斥着其他的可见者。正是作为一种从自身展开来显现自身的现象,“那相似外观比原型更充分地显现出来,以至于将原型驱逐出目光之外”[2](P58)。同时,这外观“不再凭靠它自身以外的东西,以自身为唯一的光源,及足够产生其适当形式的母体”,“外观提升到原型的原型的等级”[2](P59)。
之所以说这种外观能夺取欣赏的目光,是因为它获得了自身的完整性,不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附庸,因而获得了一个给予者的自我,作为一种纯粹的可见性而无法自抑地向目光涌去。因此,我们在欣赏一幅精彩的画作时往往感觉周围的世界消失或者静止,无数生动鲜活的细节、笔触接连不断地出现,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绘画作品所给予我们的可见性是如此纯粹和强烈,以至于我们的目光是被它强行扣留下来,被它捕获,被它冻结住了。马里翁用“眩目”(dazzle)来形容绘画对我们目光的这种强烈刺激,正如纯粹可见的光直射入眼睛造成眩晕一样。因此,绘画作品之所以能超出原型,就在于它作为一种纯粹外观的显现是一种溢满性现象,在其中,纯粹的可见性主导了一切。
“事件”是马里翁给予溢满性现象的基本规定,绘画当然要满足这样的规定,但它显然并不限于此,绘画还通过展现一个自身完整的时空而将这种事件性变成了它显现自己的唯一方式。我们对绘画作品的欣赏当然是一个发生的事件:我们走进美术馆,抱着要欣赏一件艺术品的雄心,急切地要去与那些伟大的作品对话,然而,无论我们如何做好心理准备,我们仍然要遭遇绘画作品的当头棒喝——没想到它会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我们面对绘画作品时常常暗自在心理琢磨的一个评价。我们继续欣赏,直到走出美术馆,心理暗自感叹:“原来绘画还可以这样。”这样一次审美经历,首先将绘画作品的过往拉回到我们面前,它在历史中遭遇的种种褒奖和贬斥都是促使我们去观看它的理由,让我们满怀期待;然而当我们站在它面前的时候,它的线条、色块、构图以及笔触等等又让我们摸不着头脑,我们或许在这一个线条的弧度中获得了快感,却又会在那一种颜色的纯度中迷失方向。这样的观看似乎完全超出了我的掌控,只剩下一个正在观看的现在在画布上来回游走,每一个时刻都被充满又被抛弃;最后当我们离开的时候,那画作还不时浮现在我眼前,当我们下一次面对其他的作品的时候,某一种细节的处理方式仿佛在这里重现,那之前的画作通过我们走向未来。与那绘画相关的一切,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超出了我们能设想的范围,这无疑体现了绘画欣赏的事件性。但绘画本身似乎仍然只是这一事件中的一个要素,而非全部,这里的事件性更多集中于欣赏绘画这件事上,似乎绘画并不是事件发生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实际上正是绘画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欣赏只能这样发生,即绘画主导了欣赏。
三、绘画如何成为溢满性现象
马里翁在回答绘画是如何占有现象性——溢满性现象的现象性或曰事件性时认为,其中一方面是因为面对绘画作品,“我们通过切断和删除凝视着一个孤立的画框(frame),它独立于没有起始也没有结束的无限的可见者之流”[2](P62);另一方面是“目光被固定在偶像(idol)这个视线无法穿透和抛弃的第一可见者之上,因为偶像首次溢满出目光并聚集了所有的欣赏”[2](P62)。
画框将绘画从现实世界中隔离出来,使绘画呈现一个非物理的空间,至少是不再受物理的空间干扰。在马里翁看来,我们的世界是被各种可见的东西充满的,我们的目光无论如何也逃不开可见者的领域,但被可见者包围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能看见(look at)它们。当我们被命令去看(see)的时候,我们首先的反应是看什么,但如果这个命令伴随一个指向某物的手势,我们便轻松地将目光集中到(look at)手势所指的东西上。画框首先起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指示的作用,它限定我们目光的范围,使它避免了漫无目的地游晃。这种指示实际就是指导我们先不去注意被指之物周围的其他事物,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删除或使某些背景虚无化的力量。
但是,日常生活中的指示并不能真正消除背景对我们目光的影响,比如指向黑板的手会让人疑惑是注意黑板还是黑板上的字。这是因为物理世界中的可见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在可见性上事物之间都是平等的,因此是杂糅在一起的,须得依靠意向性的整理才能区分开来,因而这样的可见世界并不纯粹。从这个角度来说,画框又起到一个划定边界的作用,阻断可见者之流进入绘画的空间,同时提示观看者,所有需要被看到的东西都已经呈现在这框架之内了,因而并不需要意向性再去对它做出区分。易言之,画框之内形成了一个纯粹可见的空间,它只允许目光进入其中。
马里翁通过分析显现(presentation)和再现(appresentation)指出,“世界中的所有表象都由显现和再现构成”,然而 “在绘画的画框之内……这里而且仅在这里,被再现者趋于消失,将一切全留给了显现者”[2](P63)。因此,绘画作为一个在画框之内呈现的空间已经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物理的空间了。随着物理空间被画框阻隔在外,那些只能在物理空间中呈现出来的客观化的物体也被排除了,因为在一个只有显现的空间中它们那只能在再现中呈现的不可见的三个面变得无关紧要,没有纵深的绘画平面决定了绘画中呈现的东西与客观事物的绝对差别,因此要求以另外一种的方式来显现自身。这另外的方式就是纯粹的可见性对观看的目光的满溢,倾覆了客观化事物得以显现的意向性。在绘画中,“我们直接看到画家的视野,不再是他或她意向的物理对象;绘画既不显现持存的物体也不显现对象,因为它与对象性(object-ness)或存在性(being-ness)毫不相干”[2](P65),“绘画在显现之上增加显现,而自然在这显现中保留了空间,亦即不显现(absence)”[2](P66)。
审美理论中有一种“距离说”的观点,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够欣赏美,或者说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之所以能够变成审美对象,是因为我们与它之间保持了一定的心理距离,不能太近以至于产生利害计较,不能太远以至于不能理解而引起理性计较。如果从我们上述对画框的论述来看,这种心理距离实际上正是起到了一个画框的作用,试图使我们对事物的观看摆脱利益或理性这些意向性的干扰,使事物以纯粹外观的方式向我们显现出来。中国古代美学的审美心胸理论推崇庄子所谓的“心斋”、“坐忘”,实际也仍是将艺术作品或审美对象当作一个溢满性现象,让现象来充满观赏者,否定一切意向性的构造,让纯粹的可见者自身显现。
画框使纯粹可见者自身得以涌现出来,捕获观看者的目光,包围着它,由此形成了 “偶像”。“画家除了使我们眩目之外并没有别的目的”[2](P60),陈腐的东西并不会使我们眩目,习以为常的东西甚至常常被我们忽视掉,更不用说吸引我们的目光了。只有新奇的、以前并未见过的东西,才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多看两眼。绘画之所以使我们眩目,就是因为它向我们呈现以往不曾被看到的东西,这些不曾被看到的东西具有如此强大的魔力,使人为之着迷。人们无法把它与其他的可见者放在一起比较,或者说无法把它归入任何一类其他的可见者之中,它的独一无二迫使我们在它面前停下来,欣赏它。“偶像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完成:目光无法穿透和抛弃它的第一可见者,因为它首次满溢出目光并将所有欣慕都聚集在它身上。”[2](P60-61)因此,我们可以说偶像即是一个首次出现的可见者,绘画之为偶像就在于它作为一个纯粹外观总是呈现出不一样的东西。
那么,绘画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新鲜的、不曾被看见过的可见者又来自哪里呢?显然只能来自不可见的领域,因为绘画中过往的可见者毕竟是有限的,更何况这其中仅有少部分是真正的第一可见者,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总能被后世的绘画艺术家全部看到,但这并不妨碍新的作为第一可见者的绘画横空出现,因此,绘画艺术家必定是从一个对所有人都不可见的领域中抓取出他们的绘画语言,这个不可见的领域被马里翁称为“l’invus”,这是一个不会因为物理时空中物体的遮挡或随时间消亡而不再被看见的领域,它是纯粹的不可见。绘画就是“从不可见(unseen)到偶像的突然转化(metamorphorsis)”[2](P69),它将新的可见者增加到这个可见者的世界之中,并由此超出这原有的世界,使之废弃。因此可以说,艺术家才是世界的创造者,是他们将这个可见的世界从不可见的领域中一笔一刀地刻画出来。艺术家作为中介,实现不可见领域向可见者的转化,他们制作的绘画作为偶像受到人们的追捧、崇拜和摹仿,才有了可见世界的改变。时下的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特别是乔布斯主导的苹果系列手机)不正是一个艺术家制造偶像来改变世界的生动案例吗?
正如马里翁所言:“正是偶像主宰了每个时代自然的可见者和被构造者的外观,并迫使我们从它们的带有魔力的范式出发去观看所有的一切。”[2](P69)绘画作为偶像的魔力来自于它自身要求被反复观看的不枯竭的显现方式。在马里翁看来,物理时空中的物体对象往往在一次呈现中就穷尽了自身,并可以被无限地复制,而绘画“由一个清楚的原则区别开来:我们不能一次全部看完它,我们必须经过间歇来重看(re-see)它”[2](P70)。绘画自身是一个无限的世界,我们作为被赋予者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们并不能一次性将它全部现象化出来 (这也同时是它得以通过我们现象化的条件),只有在重看之中绘画本身的生命力才能呈现出来,也就是它的丰富性才得以显现。而一种真正的时间也在绘画的“看—重看”的现象结构中呈现出来:变化是时间的首要含义,时间只能在变化之中显现,绘画不仅保留变化,发生变化,还预示了变化,因为“它敞开自己作为曾被看见的(have seen),正在被看见的(see)和将被看见的(will see)潜在总和”[2](P72)。绘画因此才是不可预见、不可复制和不可穷尽的溢满性现象。绘画自身可见性的涌现超出了观看它的目光所能承受的范围,同时也将这目光潜藏的能力激发出来,否则绘画不能作为偶像去捕获目光。它就像一面不可见之镜(invisible mirror),映照出目光的尺度和界限。由于观看的眼光不同,同一幅绘画就将显现出多层次的第一可见者,由它们阻截各自的欣赏目光。绘画测量观看者的尺度,但也会作为一个调节性的理念 (regulatory idea)来引导目光发生和提升,从而也塑造了观看的尺度。
审美理论中有一派影响很大的移情说,认为审美活动中的快感体验实际是对自我的体验,是人将自我投射到对象之中,使得他能一方面暂时忘记自我,另一方面又真切地体验自我。从我们以上分析的绘画作为偶像能反映观看者目光的尺度来看,移情理论实际是符合绘画所代表的溢满性现象的。而且,虽然移情理论使用“投射”一词来形容自我向审美对象的转移,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投射是人主动发出的,相反,却是被眼前事物的外观引导的,正如那个经典的移情例子中上细下粗的多立阿石柱引起人耸立上腾的体验所意味着的那样。
四、结语
在马里翁看来,绘画通过其画框对纯粹可见性领域的划界和这个纯粹可见领域获得的作为偶像的权力,使它“不是提供了一个还原之现象学方法的有趣却可能只是随意的例证——它通过其显现的质量 (那种强烈性或 ‘极度的壮观’)彻底地完成了它 (现象学还原——引者注)”[2](P68)。正是在作为溢满性现象的意义上,绘画彻底实现了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精神,真正完成了现象学还原。同时,作为溢满性现象的绘画,不再是对原型的模仿,而是成为原型的原型。这或许开启了我们理解艺术甚至理解世界的新的角度——不是艺术摹仿现实,而是现实摹仿艺术。
[1](德)埃德蒙多·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M].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Jean-Luc Marion.In Excess.trans by Robyn Honor &Vincent Berraud.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2.
[3]郝长墀.逆意向性与现象学[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5).
【责任编辑:赵 伟】
B565.59
A
1004-518X(2016)04-0020-07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赫尔德文化哲学思想研究”(14CZX034)、贵州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赫尔德文化哲学思想研究”(13GZYB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