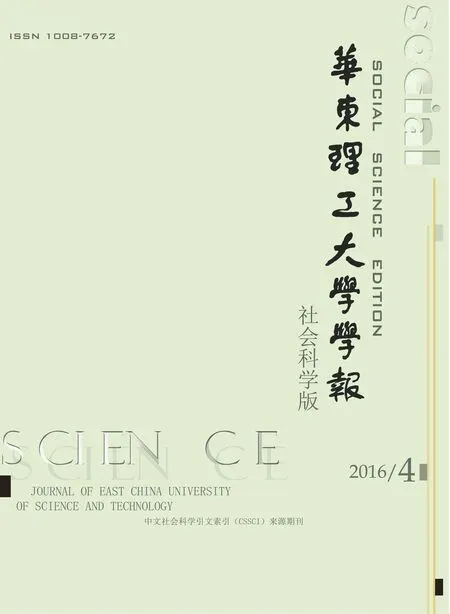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变迁、现状与反思
侯利文(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变迁、现状与反思
侯利文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极富张力与效力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引入,与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转型相伴而生。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中国基层社区研究的主导性分析范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近来的研究也明显呈现了一种“边际效应递减”、学术累进趋缓的困境。是“过度消费”之后的“疲软”,还是“充分研究”之后的“空白”,抑或是“重复生产”之后的“停滞”?带着这些疑惑,文章以“国家与社会”学术脉络的阶段分期为主线,围绕“国家与社会”范式在基层社区中的知识生产过程,追溯过往,系统梳理“国家与社会”引入之后学者结合中国城市社区实际进行的创造性论述;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归纳,提炼“国家与社会”研究背后的所呈现的趋同特征与潜在缺陷;最后,通过反思对话,破除“国家与社会”研究的“神话”,尝试走向更加开放和日常的“国家与社会”空间。
基层社区国家与社会范式变迁学理反思
一、引言
“国家与社会”缘起于西方的政治哲学论争,争辩的焦点在于,“社会先国家而存在,社会先于国家”抑或是“国家具有先导性,国家高于社会”,洛克、孟德斯鸠与黑格尔开起先河。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市民社会的不断崛起,米格代尔提出“社会中的国家”又开启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研究的新取向。“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极富张力与效力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引入,与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转型相伴而生。一方面,社会的转型提供了国家与社会范式在中国得以运用和验证的广阔天地(尤其是发生在基层社区的变化),国家与社会的范式获得了来自“东方社会”的佐证与完善;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范式的引入也使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巨变得以解读,产生了人们的理性认识和学理知识,反过来“国家与社会”知识范式的引进作为某种目的性的示范也形塑了对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并引发了实践中的改革,进而规范与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前者表现为一系列学者研究成果的呈现和累进;后者则表征为“国家与社会”知识范式对现实社会改革的规范价值,对“社会”成长的倡导与引领。
从时间分期上看,“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20世纪90年代经由西方汉学者的引介而进入中国,正是由于这一分析范式与中国社会转型实际的高度契合,它迅速进入了众多学科学者的视域中,短短几年间,就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①有关“国家与社会”在90年代取得的学术成果,可参见,郑卫东:《“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中国乡村研究综述》,《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2期;何海兵:《“国家—社会”范式框架下的中国城市社区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的论述。进入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视角又快速捕获了“社会组织”②参见丁惠平:《中国社会组织研究中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及其缺陷》,《学术研究》2014年第10期。领域的研究空间,并迅速成长为中国学术研究中的主导性分析视角。无疑,“国家与社会”已然成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理论分析框架,展开着对转型中国社会各领域的洞察;同时,也作为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工具,尝试在现实中展开对社会实体的积极建构和倡导。
就“国家与社会”范式的主导性学术研究领地③丁惠平(2015)认为,“国家与社会”研究的“势力版图”主要涵括了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城市社区研究以及社会组织研究等题域。笔者基本上赞同这一说法。——城市基层社区而言,正是因缘于“在最现实的生活层面上,国家与社会的相遇”,国家试图通过政权建设将行政权力下沉到基层社会,完成整合;而社会则希冀表达利益诉求、谋求自我服务,实现自治。这一“无意识”的历史性耦合碰撞出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就现有的研究来看,以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为主,兼有人类学、历史学④“国家与社会”的历史学研究相对较少,朱英:《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以及哲学的思考,相互交叉;研究内容丰富多样,相互深化;研究方法长短互补,各有所长;研究脉络互有传承,相互交融;学术脉络也经历了范式引进、范式运用、本土化尝试以及范式的反思对话等明显的阶段分期,相互累进。
尽管“国家与社会”视角取得了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也明显呈现了一种“边际效应递减”、学术累进趋缓的困境。⑤刘安(2015)在《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及其学理反思——基于政治社会学视角的分析》也认为,“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日益陷入一种同质生产、难以取得理论突破的境地,并从范式引入的学术背景、已有研究的爬梳、理论上的困境与突破进行了富有创造力的论述。是“过度消费”之后的“疲软”,还是“充分研究”之后的“空白”,抑或是“重复生产”之后的“停滞”?本文尝试对此进行解答。文章以学术脉络的阶段分期为主线,围绕“国家与社会”的知识生产,进行学术反思与对话,以期为突破现有的研究瓶颈贡献学术力量。首先,追溯过往,系统梳理“国家与社会”引入之后,学者结合中国城市社区实际进行的创造性论述;其次,理论归纳,提炼“国家与社会”研究背后所呈现的趋同特征与潜在缺陷;再次,反思对话,破除“国家与社会”研究的“神话”,走向更加开放和日常的“国家与社会”空间。
二、“国家与社会”范式在基层社区的运用与变迁
伴随着以“单位制”为主和“街居制”为辅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式微,国家与社会渐次展开了复杂、多样、动态的关系实践与博弈空间,学者们如张静、何海兵、余冰、丁惠平、刘安等,大都认为现有的以“国家与社会”作为分析框架的基层社区治理研究,存在三个明显的取向,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说以及国家与社会互动论,鉴于以往研究对此三个取向的梳理较为系统、全面,本文只是做出简单交代,重点针对“国家与社会”的其他替代性或是补充性的视角在基层社区治理研究中所丰富并深化的理论视域与分析空间进行梳理与分析。遵学术惯例,本部分也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
其一,“国家中心说”。这种研究路向把国家视为基层社会治理、变迁与改革的核心力量和关键推力,遵循国家政权建设的逻辑。虽然后期国家政权建设的痕迹有所弱化,但是国家对社会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控制能力,在一些领域以特定的、新的形式出现,以更为“隐蔽”和“柔化”的方式实践着国家力量在基层的渗透。其结果,国家仍然具有对社会的强大影响力,因此也被称为“国家权力延续论”。
其二,“社会中心论”。社会中心论的核心概念是“公民社会”(又译为“市民社会”、“民间社会”①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公民社会、市民社会以及民间社会”分指不同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存在显著差异。但就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视域而言,这三者又具有很大的关涉性。故此,本文并未对这三个概念的所指进行明确区分。)。该路向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存在于社会之中,国家对社会而言只是一种限制性的力量,国家是“必要之恶”,因而主张社会自治,国家干预越少越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基层空间中社会、市场等非国家力量的兴起,国内学术界对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多。研究者在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下,认为国家与社会存在明确的分殊,它们之间的界限应该明晰化和常规化。就现时中国而言,国家力量应该逐步从社会领域撤离,这是保持社会活力和提升国家能力的必要条件。
其三,“社会中的国家”,即国家与社会互动说。该路向的研究,通过对具体事件过程的跟踪分析而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以往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代表了从结构性研究向关系性研究的转向,②丁惠平:《“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应用与限度——以社会学论域中的研究为分析中心》,《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5期。也实现了从“静态学理分析”到“动态过程把握”的转变。该路向认为国家与社会并非二元对立、此消彼长的简单零和博弈关系,而是处于不断互动与形构的动态过程中。在方法论上多采用“事件—关系”分析,并通过引入“策略行动”和“过程—事件”的分析框架,致力于对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观层面进行深描。相关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早期多聚焦于以“国家与社会”应该如何互动,以及互动的性质而进行的规范性分析,以理论研究为主;二是晚近以来聚焦于以“国家与社会”的实际互动过程与事件在具体载体中展开的分析,以实证研究为主;三是治理视域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正和博弈研究。
其四,其他视角的尝试。以往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判基本上是预设了国家与社会的整体观,忽视了国家与社会的多样性、层级性,进而遮蔽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动态性与多样性,甚至是流动性。实际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随着国家主体与社会主体活动场域的变化而变化,整体上呈现为互渗中的动态边界关系。随着对“国家与社会”视角在基层社区治理运用中反思的进行,这一单一视角的一元论倾向得到修正。一些具有分析效度的替代性或是弥补性的视角相继被提出。比如,桂勇以“行动者”视角将国家与社会从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认为国家与社会是由各种不同取值的参数构成的一个连续系统,这些行动者集团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对立、合作、冲突与妥协是同时共存的。应用到社区建设中,社区居民、社区组织都是不同的行动者,都有自身不同的利益和目标,他们之间的友好互动构成社区的良性发展。因此,要从社区具体的事件发生的过程以及行动者的角度来理解社区发展的逻辑。③张冬冬:《国家与社会互动结构中的居民委员会——以开封市为例的研究》,开封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无独有偶,马卫红等通过对上海市的基层社区治理的经验分析,阐述了国家与社会如何被目的分殊的行动者分解,由此呈现碎片化状态。他们认为,“在邻里层面国家与社会也是模糊不清的,清晰可见的是各种有着不同利益与目标的行动者”,因此也主张从“行动者”的角度研判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的真实关系形态。④马卫红、桂勇、骆天珏:《城市社区研究中的国家社会视角:局限、经验与发展可能》,《学术研究》2008年第11期,第63页。徐丙奎通过对1990年以来有关社区研究文献的梳理,认为“现有的研究缺少对国家一社会、空间一行动者、权力与治理各种研究范式的一种整合性的研究”,①徐丙奎、李佩宁:《社区研究中的国家—社会、空间—行动者、权力与治理——近年来有关社区研究文献述评》,《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47页。提出了进行社区治理范式整合的观点。肖瑛在对以往“国家与社会”关系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该视角在中国的运用更多是规范层面的,难以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机制”。因此,他提出“制度与生活”的视角作为替代性视角,“以制度与生活的互动实践为切入点,把日常实践同社会结构变迁勾连起来,为探究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动力机制提供一种解释框架”。②肖瑛:《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第95页。
关于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的三种取向“国家中心说”、“社会中心论”与“社会中的国家”,前两种侧重于在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二元对立与紧张博弈中寻求中国社会建设的可能出路,本质上是一种“结构”式的静态解读,分别从不同的维度选取经验事实,“完成”了对中国局部现实的认识;他们显然忽略了国家与社会间“讨价还价”相互形塑的可能空间。而第三种分析却将视角转向了“国家与社会”的彼此焦灼与粘连,在彼此互嵌的视野中实验“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可能,其本质上乃是一种“实践”式的动态分析,侧重于从“过程”的视角来完成对社会现实的“客观”解读。但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嵌程度、国家与社会的不同原始起点等作为逻辑上的先在,形构着“社会中的国家”的具体“边界”与“势力范围”。再者,“社会中的国家”一经发明,马上就转化为中国真实建构中的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预设。正如邓正来所言,“而这种所谓的良性互动关系在中国市民社会论者那里既是一种欲求达致的结果,同时也是达致这种结果的方式”。③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页。于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作为理论与理解上的预设,开始了其在中国基层社区场域中的“自证”征程。
纵观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家与社会的研究,其指涉的核心问题涵括两个方面。一是遵循着“建构现实主义”的传统,将国家与社会作为现实层面的对象朝着“良性互动”的愿景加以建构,这在具体研究之中就表现为将西方“国家与社会”范式所内含的基于西方社会现实抽象出来的种种前置性要素(比如,国家与社会的相互独立、边界清晰、相互制衡等)作为参照和判断标准,把视野聚焦于对中国社会中新出现的体制外因素、空间、组织以及机制所展开的经验性分梳,找寻其存在的证据,并进行比附式的研究。从实际效果来看,该范畴的研究客观上起到了一种社会动员、批判现实及规范整合的作用。这样,理论知识就由对社会的认识转向了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所进行的筹划。另一方面则秉承了“解释主义”的传统,将“国家与社会”作为是认识、洞悉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独特分析框架和解释模式。这在具体的研究中就表现为对一系列经验现象,尤其是基层社区中的“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此消彼长进行的富有想象力的阐释。从实际的效果看来,它唤起了人们对“社会”的想象,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中国社会转型认识的视角切换。
总之,“国家与社会”作为理论分析范式在城市基层治理实践中显示了极大的理论效度,学者们都在这一极具张力的视角中提出了丰富多彩的治理实践与理论创见。国家与社会的范式也实现了由实体建构中“二元对立”到“互嵌互构”的转变,实现了“静态结构分析”到“动态过程展演”的变迁,也完成了作为分析范式的经验研究到作为规范取向的政策参鉴以及作为科学研究对象本身的反思对话的统一,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主导性分析范式。但任何范式都有其分析的效度与适用的范围以及解释的效力,忽略了对范式本身的研究,或是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实际抑或是缺乏了对范式的反身性对话,必然遭遇“范式的神话”与“范式的固化”,造成范式的“无意识运用”,无益于范式的进一步更新与发展。由此,我们需要对“国家与社会”范式的研究展开反思与对话。
三、“国家与社会”范式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反思的再反思
尽管“国家与社会”展开了对转型社会的深度解读,但解读的同时也存在误读的极大可能性。如果对误读缺乏足够的敏感,社会事实的呈现将出现极大的扭曲。误读一方面取决于“国家与社会”范式的舶来性。从学术惯例来看,作为外来的理论范式,其必然要经历一个完整的引入、运用、反思与重构的过程。缺乏了后续环节的推进,理论范式只能是一个“悬浮式”的解读,或者直接就是“观念裁剪的现实”,误读就成为了必然;另一方面,对该范式缺乏“前反思的对话”,规范性意义上的价值倡导,就会演变成为实际改革中的“急功近利”与“目标置换”,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作为一种改革愿景,通过对原有的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全能国家”的批判,将“国家”拉下“神坛”,将“社会”引入研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科学领域中研究框架的转换。但是,过犹不及,随着“国家”的被舍弃、被阉割,持续的发酵,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正如刘安所言,“正是政治实践意义上的‘社会'主体性的缺失,才导致了知识领域对‘国家主义'的无情批判以及对‘社会'的极力推崇”,①刘安:《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及其学理反思——基于政治社会学视角的分析》,《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5期,第34页。催生了“社会”的单向度治理。长此以往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东欧的剧变即是鲜明的例证)。鉴于此,此部分笔者以学者的反思性研究为起点,试图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研究的反思的再反思为范式的重构提供启发。
第一,反思的起点,在于“国家与社会”范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神话”。所谓“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神话,意指目前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中存在的“国家与社会”范式的“一元论倾向”,通俗一点讲,只要是基层社区场域中的相关研究,国家与社会是必然会涉及和运用的理论视角。那么为什么在基层社会中发生的一切现象都可以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加以分析呢?这其实就已经涉及到了问题的根本。正如丁惠平所言,“无论何种论题只要置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中似乎便天然地具有了某种正当性与合理性”,②丁慧平:《“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应用与限度——以社会学论域中的研究为分析中心》,《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5期,第19页。而且此种一元化的倾向“有过分重视和消费‘国家与社会'之嫌,不仅有可能遮蔽问题的本质而且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研究框架的更新换代”。③丁慧平:《“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应用与限度——以社会学论域中的研究为分析中心》,《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5期,第19页。但是,丁文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对“一元化”的“神话”过程进行探究。那么,为什么会形成基层社会治理中“国家与社会”范式的“一元化”局面?这应该成为我们反思的逻辑起点。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国家与社会”范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型地位是极富张力和理论解释力的范式与社会转型实际耦合的结果,也是近三十年学者在基层社区(国家与社会展开博弈的最佳场域)深耕的结果,同时不同学科的介入研究也彰显了“国家与社会”理论范式的跨学科解释力,进而使其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核心研究范式。加之学术热点与学术前沿的“象征意义”,“国家与社会”取得了理论范式中“符号意义”,并且通过这些过程的循坏往复实现了“神话”化。其表现就是,一方面,只要是一项研究涉及“国家与社会”范式的运用,似乎就代表着研究的前沿与水准;另一方面,基层社会治理背后的深层次力量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不断交织、角力与博弈,缺失了该范式的分析,就意味着研究的表面与肤浅。
第二,对“国家与社会”视角存在的系统论基础的反思。肖瑛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理解现代性条件下社会构成及变革的基本视角,是在社会系统论的支配下形成的”。④肖瑛:《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第88页。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运用有三个基本预设。其一,整体论。整体论预设了国家与社会内部的统一性,外在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国家”与“社会”都被想象成为一个有着自身独特结构、明晰边界和运作逻辑的实体,其各自内部构成的差异、分歧、冲突与互动被遮蔽。其二,二元论。这主要指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实体上二元对立的、功能上彼此依赖的、力量上相互制衡的表述模式,其常用的文本表述就是,“强与弱”、“大与小”。二元论其实是整体论在逻辑上推演的必然结果。其三,权力的两重性。一方面是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民族国家对社会的压制、控制与殖民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性也预设了成熟的“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度性约束与反控制。①肖瑛:《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第88-89页。其实,早在该范式的引进之初,邓正来就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该范式可能存在或可能导致的种种风险进行了提示。他认为,国家与社会范式容易诱导人们进入整体性、实体化的陷阱,在具体的研究中人们容易将“国家”与“社会”作为真实存在的同质化的统一实体看待,这就忽视了“国家与社会”在中国场域中的无限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整体性”思维的规约下相继而来的就是,人们将“国家”与“社会”化约为基层社区中的各种对应体,比如将国家等同于“政府或党组织”,将社会等同于“社区居委会”等,先不论这一“化约”的可信度如何(事实上“居委会”是“社会”还是“国家”是一个尚未厘清的问题;政府内部也存在严重分化的不同层级),单是将宏观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化约为微观社区中的对应主体这一过程就犯了“区群谬误”,难以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
此外,丁惠平和刘安在近来的研究中都围绕“国家与社会”视角存在的系统论基础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丁惠平认为,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分析策略中,“国家与社会都被先验地视为两个具有明确界分的实体,也即在本质上秉承的是一种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投射到具体研究中则演变成一种对二者影响力进行比对的结构性分析,即使是国家与社会互动取向也概莫能外”。②丁惠平:《“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应用与限度——以社会学论域中的研究为分析中心》,《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5期,第19页。刘安对“国家”与“社会”的主体性问题进行了系统反思。他认为,“无论是从概念形式还是理论逻辑的角度而言,‘国家与社会'范式中的‘国家'与‘社会'都被建构成相对独立和彼此自主的范畴”。③刘安:《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及其学理反思——基于政治社会学视角的分析》,《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5期,第34页。
由此可见,近年来的研究都注意到了“国家与社会”范式的系统论假设,以及对这一假设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反思,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以及针对“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同质性”假设,也对“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构、牵制保持了足够的敏感,有利于“国家与社会”范式效度的提升。
第三,对“国家与社会”范式因舶来性而引发的“本土性”问题的反思。学术移植与本土传统之间的协调问题一直以来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难题。作为外来引进的学术范式,也必然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一般来讲,范式的引入要经历引进、本土化、普遍化三个阶段。引进是初始阶段,需要解决范式的关注度问题;本土化是关键,需要解决范式的适用性问题;普遍化是目的,需要解决范式的本土贡献问题。层层递进,形成理论范式的更新换代过程,也即知识的生产过程。其中,本土化是难点,要突破范式的产生背景、逻辑预设以及融合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极容易发生“观念裁剪现实”和“框架置换与混用”。就其前者而言,往往发生研究者将该分析框架直接套用到对中国经验现实的研究中,直接用西方既有的理论观点进行解释,如若两者不符,则将其归因于社会、文化等本土性因素,致使研究流于表面,难以获得突破与深入;或者干脆直接在理论预设的指导下选择那些可以验证假设的经验现象进行解读,理论直接被“证实”。就其后者来说,作为西方舶来的理论范式,“国家与社会”具有解释和规范双重功用。具体来说,一方面该范式可以作为解释性分析范式,对既有的社会现实进行理论解读,形成社会知识;另一方面该范式也可以作为早发现代性国家的标准和模式,来规范和指导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发挥判准和建构的功能,推动社会变革。这两种功用的置换和混用,极易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致使本土化的过程演变为“西方化”的过程。
黄宗智认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经验中抽象出的一种理想类型,它并不适合中国”,进而提出了“第三域”的概念用以指涉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灰色地带”,涉及的是“国家与社会”范式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何海兵也认为,“在有关国家与社会的讨论中,无论是公民社会理论还是国家中心理论都是依据西方公民社会和国家概念来对中国社会作应然性判断,这些判断仅仅从宏观历史着眼,缺少对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观层面的描述”。①何海兵:《“国家—社会”范式框架下的中国城市社区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101页。丁惠平亦对“国家与社会”范式的本土化进行了反思,“对于中国研究而言,源出于西方历史经验及西方人价值理念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衍生的‘国家与社会'在中国既无历史踪迹可循也无现实经验对照”。②丁惠平:《“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应用与限度——以社会学论域中的研究为分析中心》,《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5期,第19页。刘安认为,“‘国家与社会'范式的西方血统与中国应用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作为社会科学概念的‘国家'和‘社会',无论是在知识还是在实践层面,中国与西方都存在显著的区别”。③刘安:《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及其学理反思——基于政治社会学视角的分析》,《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5期,第35页。
因此,作为舶来的理论范式,我们必须对其可能存在的“水土不服症”保持足够的警惕,对其范式的移植生态过程和其成长过程保持敏感,既不否定“国家与社会”范式所具有的对转型社会的理论解释力,也不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而是在中国自身的历史承传和发展实践中与西方的理论范式进行平等对话与理性沟通,不失时机地将其引向“中国化”。
第四,对多元视角互补与融合的反思。任何理论范式都是时代的产物,在发展中趋于完善,这也就意味着都是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解释力,有其长处也有其不足。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由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范式所具有的理论解释力和方法论优势,导致其在社区治理的研究中存在一种“一元论”的倾向,这就不利于范式的更新换代。诚然,一个理论视角的发明是学术界集体智慧的结晶,之后就会进入繁荣期,众多学者运用此视角把这个理论框架里可以研究的问题都进行了研究。但是,也会出现一个不利于学术累进的现象,那就是,正是由于该理论范式的解释力和公信度,久而久之研究就会出现重复性的简单再生产,难以突破。这时就需要对范式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视角过于宏观,实践中的研判也忽视了源自于西方经验的各种前提预设,因而对现时期中国的基层治理实践难以准确描述;国家与社会范式长于对宏观现象的解读和分析,偏重于宏观的“结构—制度分析”,失于实践层面的微观洞悉,存在将国家与社会复杂的构成与互动过分简化的风险,以致失掉了“国家与社会”的丰富内容与复杂面向,难以解释转型期国家与社会的多维度性、实体的延展性与实践的复杂性。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范式的演化以及一系列理论视角的浮现,④详见上文第二部分的文献梳理。“国家与社会”逐渐失去了其基层社区领域中“一统天下”的霸权局面,逐渐沦为了其他视角提出与兴起的“学术靶子”(毫无疑问,学术靶子也意味着“国家与社会”范式的地位之重要,影响之深远)。
由此可见,虽然“国家与社会”深化了对宏观层面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但理论上解释力的“神话”就造成对其他视角的屏蔽与排斥,日益进行范式内部的重复性再生产。而其他视角的引入与补充,打破了“国家与社会”范式在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一元化神话”的局面。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国家与社会”视角已经失去了其对中国基层社区的理论解释力,也不意味着其他视角实现了对“国家与社会”视角的有效“替代”或“转换”,笔者更愿意认为这是进入到了一种范式交叉融合的新时期。从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复杂、多元交织中,进入到了基层社区治理研究中的后“国家与社会”范式时期。其研究逐渐呈现两个特征,一是进行了视角的链接,实现“国家与社会”与“制度与生活”的相互促进与印证;二是实现了视角的切换,宏观议题有了微观层面上的注释,变得更为丰满和全面。
四、结语:走出神殿、走向生活
一言以蔽之,现有的研究取得了一些严肃而认真的研究成果。但系统梳理之后,发现现有的研究更多地是将“国家与社会”从方法论意义上使用的,将其当作是分析基层社区治理的有效范式,并且使用中带有明显的西方痕迹。中国论者更多是从中国现实经验中找寻恰切的方面,进行意义放大的研究,进而与西方的范式做比附。反讽的是,在具体运用中则对这一理论范式所具有的前提保持了“悬置”或是作了“模糊性处理”(不置可否)。换句话说,现有的研究将对作为分析视角的“国家与社会”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屏蔽了国家与社会的前提预设,并且因为“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的“相遇”与“契合”而导致其运用中的“不假思索”和“深信不疑”。但是缺少了对隐含预设的思考以及对范式运用的反思,将导致低水平研究的不断再生产,难以进行学术累进,也长不出中国范式。
从中国经验来看,作为一种规范性的观念,国家与社会范式出现了一种“过度消费”的现象。但是作为实体建构以及范式创新意义来看,“国家与社会”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仍然具有其建构性的意义。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对理论范式和实体建构两种取向的分殊,进而通过具体载体与空间的研究来链接这两个层面,消除已有研究存在的“厚此薄彼”,则可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研究的新突破。
其一,对象倒置。以往的研究,多是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范式和视角来透视和分析基层社会治理空间中主体互动。但是我们也可以将基层社区作为表述的载体来管窥“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社区组织平台上(笔者认为居委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平台)的现实展演,进而将“国家与社会”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中国情景的描摹、解构与重构,而此也应该成为“国家与社会”范式更新的重要尝试和有待进一步深化的主题。
其二,范式更迭。诚如上文分析,自米格代尔提出“社会中的国家”之后,国家与社会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互动的过程性的视角开始被涵括进“国家与社会”的范畴中。但是“社会中的国家”可能是西方知识话语映射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虚幻图景,与中国的历史实践和现实经验不符。在中国的基层社会中,可能“国家中的社会”①关于“国家中的社会”笔者将详细撰文加以阐述,由于篇幅所限与主题的考虑,在此笔者暂不详细展开。是更为真实的存在。一方面,从国家的势位来看,国家时刻保持了在基层的“在场”和“到场”,基层社会中也存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各种国家状态,国家通过多元化的途径与手段(尽管与以前的刚性控制的形式不同),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选择性培育”和“间接化控制”。另一方面,从社会的空间来看,现时“社会”不是独立成长起来的制度空间,而是在国家内部让渡出来的制度空间,是在“国家”关照下的“依附性成长”和“寄生性生存”,尽管社会表现出了一定的“策略性博弈的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讲,学术界关于“嵌入性”的概念难以描摹这一关系的始源,存在理论的效度与边界。而通过“国家中的社会”的视角切换,为本来宏观抽象的理论思辨注入了具象的实践文本,同时结合现时的基层治理场域进一步为“国家与社会”的理论命题注入了中国元素,具有理论自觉的意义。
(责任编辑:徐澍)
“State and Society”in Local Governance:Changes,Status and Reflection
HOU Liwen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State and society”,as a very perspective tension and effectiveness angle introduced into China,was associated with the re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This article takes the“state and society”academic context staging as the main line,focusing on“state and society”paradigm in grassroots community knowledge production process,tracing the past,and systematically combing scholars'creative studies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China's urban community.
grass-roots community;state and society;paradigm shift;theoretical reflection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8BSH002),2015-2016年度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编号:201506740014)。
侯利文(1985-),河南洛宁人,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研究人员,美国休斯顿大学国际社会工作学院访问学者(2015-2016),研究方向:社区治理、社会工作学。
C912
A
1008-7672(2016)04-0009-09